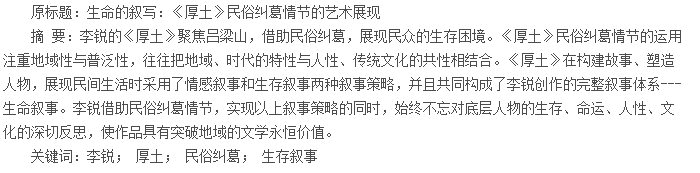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世界瞩目东方文化,中国文学也在经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开始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在此背景下李锐也开始倾心乡土,并在 80 年代末创作了《厚土---吕梁山印象》。《厚土》一经出版,广受好评,以其创作机制、价值影响为焦点的研究也纷至沓来。
这些研究或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其创作机制,或是对其民间、乡土创作视角的选用大加赞扬,对 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从《厚土》民俗纠葛的运用入手,结合叙事学与文艺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挖掘民俗纠葛的运用与作者生命叙事的内在关联,为李锐创作意图、文学态度的推断提供一种角度。
一、叙事视角: 民俗纠葛选用的地域性与普泛性
陈勤建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是具有群体意识、较为稳定的精神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但是由于时代、地域、家庭、教育、职业等民俗氛围的差别,个人所接受、存储的民俗信息在观念、层次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正是这些个体民俗的差异性,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产生民俗纠葛。“情节是被纳入文本中的那些表现人行为的事件,通过某种因果关系而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
用民俗纠葛建构情节的叙事方法与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创作的情节淡化趋势有一定联系。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相当数量的的文学作品,从情节、主题到背景、情感,都明显地淡化了”.李锐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择一个生活场景、片断或人物的对话进行叙述的同时,常将故事情节隐匿于民俗纠葛之中,去关注人们精神、心理、情绪的变化,表面上是情节淡化,实则是情节内化,强调故事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和逻辑性。
民俗纠葛的产生或是源于民俗活动本身的差异,表现为激烈的行为冲突,即情节性的民俗纠葛;亦或源于个人民俗观念的不同,表现为人物内在情感的丰富变化,乃至冲突和较量,引起事件突转,称为心意性民俗纠葛,即非情节性民俗纠葛。在文学创作中,心意性民俗纠葛构建故事情节更为普遍,通过作品主人公自身无意识地展现心意性行为冲突形成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力。民俗纠葛常受民俗的时代性、民族性、区域性、阶层性等制约。《厚土》中的民俗纠葛,不仅选用有地方特色的、真实的民俗事象,而且还符合作品整体时代背景和民族阶层心理。作者正是从民俗纠葛的地域性与普泛性出发,将吕梁民众的生存状态置放于特定环境下,揭露民众的物质困境与精神困境,叩问人类生命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鬼、崇鬼、祀鬼是初民时期就已有的民间信仰,人死为鬼和人鬼两界的观念在我国历数千年而不废。传统悠久、仪式繁复的丧葬习俗在交通闭塞的吕梁山区,表现为承袭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彰显地域个性,并渗入到李锐文学作品中。《送葬》描述了下葬拐叔的习俗情景:“棺材周围撒了五谷,棺材头上摆上几枚硬币,棺材前边燃起三炷线香,点着了一盏添了麻籽油的小小的长明灯。而后,碎石一块一块地把坟口封了起来,留下拳头大小的一个洞。队长拎起早就准备好的一只红公鸡,把鸡头塞进洞里,一面对着鸡屁股拍了两掌,那公鸡便急躁而慌忙地对着另一个世界嘶叫几声。随即,拍鸡人严肃而认真地问了一声”:掏墓的人出来了么?“众人也是严肃而又认真地答一句”:出来了!“而后,才把这惟一的孔穴堵死。再而后,用三块石板搭一个低矮的石案,在坟前烧掉几张黄纸。”
民间信仰认为,人死后肉体腐烂,但是灵魂就会变成鬼魂; 鬼、神、人三者有不同的居住环境。
《送葬》所述“另一个世界”的鬼世界是可怕的,即使掏墓的活人也怕沾染晦气,用问答的方式,用“出来了”的口彩来化解厄运和晦气。哭丧与下葬一样重要,但拐叔无亲无后,没人抬棺、摔盆、举幡,没人来灵前跪拜、抚棺大哭。作者利用这一民俗纠葛要素,笔锋一转,在严肃、悲伤的氛围里讲起了瘆人的笑话来: 棺材里头的人没声音,棺材外头的人也没声音。生命叙事要求对生命存敬畏、尊崇之心,《送葬》在展现民众对死亡畏惧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生命的无限眷恋和关怀。作者在展示古老吕梁山区的奇风异俗、神秘巫术、几近凝固的生活习俗时,还揭示与反思着人类深层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
《锄禾》中的黑胡子老汉将革命目的与金銮殿联系在一起,将文革运动比作《封神演义》的重演,这与“学生娃”的思维观念形成鲜明对比。《锄禾》中两代人的简短对话不足以推动整个故事发展,这段对话背后所包涵的时代背景以及两代人不同的思维习惯与民俗观念才是故事发展的真正支撑。如果说《送葬》在于体现中国民间对鬼神的认知和传统葬礼的普泛性,也融入了吕梁葬礼的地域性,那么《锄禾》笔下人物的个性话语中,在“金銮殿”、《封神演义》的传统文化中融入了“革命”、“文革”等特殊的时代历史文化。李锐很好地处理了文化的普泛性和特殊性,并注意在二者的张力下揭示不同文化对普通民众生活和心理的影响。
运用民俗纠葛建构故事情节,叙述者只是充当着风俗惯制的演述人,一定程度上,读者和作者之间更倾向于一种“讲述---接受”关系,而非“对话”关系。习俗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都有一定的规约作用,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也无法忽视民俗的这种控制性,读者能做的是等着叙述者告诉你故事的发展。尽管如此,读者还是可以结合文本的时代环境、习俗的地域特色、民俗纠葛等创作要素,了解故事人物行为的内在动机以及性格形成的原因,乃至揣摩到作者的创作意图。李锐《厚土》很重视借助民俗的控制和规约性引导故事发展,民俗纠葛的选用也往往把地域、时代的特性与人性、传统文化的共性相结合。
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始终在个性和共性文化中生存,始终立足当代现实,又无法隔绝历史而生存。李锐乡土小说中民俗纠葛的运用将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凝结起来构成文学创作内核,使民间、民众、民生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李锐小说立足吕梁乡土,又揭示了山西乃至中国的乡土文化。从这一意义上说,李锐创作中民俗纠葛的选用兼顾人物的个性存在与人性的永恒价值,兼顾地域文化与历史、时代、民族文化的特色,恰恰能更真实地展现民间生活的本真,更好地阐释“文学即人学”的理念。换句话说,李锐作品的生命叙写是基于民间、基于人学、基于共性和个性兼顾的文化理念。这应该是李锐创作的潜在作者意图。在此意图下,李锐小说叙事无论塑造人物,还是建构情节,表达主旨,都带有一种深沉的民间情感和对民众生存的思辨。
二、情感叙事: 民俗纠葛张力下的人物塑造
小说的情节模式对小说的创作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徐岱认为“:对小说创作来讲,作家使用一定的结构模式最终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创作目的……”作家的创作目的无非是叙事与抒情。民俗纠葛情节的合理运用,能更好地讲述民间的故事,抒发民众之情感,体现作家的人文情怀。
用民俗纠葛建构故事情节,是对程式化的民俗生活以及传统的生活观念进行艺术化处理。民俗纠葛的运用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写作素材,而且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一是通过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阅读快感,二是在叙述中潜藏叙述者的情感态度、价值2015 年彭栓红等:生命的叙写:《厚土》民俗纠葛情节的艺术展现观念,产生意味深长的阅读启发。
民俗纠葛内化为文本情节,作家将人物置于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民俗文化氛围中,通过展现人物固有的民俗观念在面对现实生活挑战时的复杂心理、对抗斗争,使人物形象更贴近生活的原生态,也有利于凸显人物性格。在此类心意性民俗纠葛的叙述中,作家在揭示人物生存状态的同时,更指向了其隐秘的情感诉求,这形成了生命叙事的隐形叙事模式。
《厚土》的情感世界,在于描写农村和农民时,更擅长呈现农村两性角色期待冲突下的人物复杂情感。《假婚》中丧妻 20 多年的农民,遇到逃难女人时性饥渴突然爆发,但得知她有丈夫,还被队长“过了一水”后,产生了变态的报复心理。《眼石》中被带了“绿帽子”后的报仇心理却终以车把式的特殊“补偿”所化解。对女性人格的极端漠视,在“男主女从”的社会中,这种畸形的两性关系成为常态。1949 年后新的公共权威生产大队出现,在特定时代里,队长的行政权力早已取代了族长、乡绅的民间伦理权力。《厚土》中的队长飞扬跋扈,专制腐败。他本性和农民相差无几,但独有的强权使他多了一份无休止的占有欲。女人成为他首先攫取的对象。《假婚》中他把一个外乡女人“过了一水”,《锄禾》里他和“红布衫的明来暗去”,但人们却从不反抗,甚至为了生存对他姑息纵容。
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男女之大防”主要是针对女性,对女性实行残酷的性禁锢,女人成了男人的装饰品和附庸,男人不惜泯灭她们的尊严、人格来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时代变迁,但封闭的吕梁大地对两性期待的固有民俗心理在新时代环境、生存需求、生命欲望的冲击下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厚土》人物内心的矛盾乃至变态、人物悲剧命运的发生,就置放于这种恒久不变的民俗场域中,让读者在领略人物情感的起伏变化后,更多了一份对人性、传统文化、时代等多重的思考。
这种传统两性观念民俗纠葛下的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情感冲突,构成了李锐农村叙事的两性情感困境模式,充满了情节的曲折性和悲剧性,极具乡土味。
除了人物情感冲突叙事外,李锐作品整体上还通过人物命运、故事情节、民俗事象等,共同建构一种悲凉的情绪。李锐的创作是将人物行动置于民俗生活相之中,缩短文艺与生活的距离,减少刻意斧凿之痕,同时调动一切手段使广大读者从情感上被深深地卷入一种生存困境,体验生活的现实、无奈。因此,《厚土》日常平凡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一种千年未变的凝滞,往往给人一种绵延久远的苍凉感。李锐作品中民俗纠葛引起人物内心的矛盾和事件冲突,终归陷于鲁迅式的“无物之阵”中,在沉寂的吕梁大地上很快消泯,归于平静。有学者将《厚土》的情感叙事结构概括为钟摆式结构,即“在事件即将达到高潮时又回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
这种民众生存、发展的尴尬困境,甚至让我们无法区别人物的悲剧是生存的现实困境还是民俗承袭的千年规约所致?
《驮炭》描写了吕梁山区特有的民俗景观“赶牲灵”,是一篇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品。在通往三晋大地的崎岖山路上,人稀路长,牲口不断。赶牲灵的人们有时用唱小曲消除疲劳、抒发情感; 耐不住寂寞的时候就和健壮的农妇打情骂俏,甚至发生关系,返程期间把毛链里的煤送给这个农妇,剩下的一块煤一分为二,给家里的婆姨留着。在古老沉寂的吕梁山区,产生任何一种与生存、生活相背离的观念都会最终被无声无息的湮没,被搅动的生活很快就会恢复平静。人们在传统的羁绊中苦命挣扎,他们的七情六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事准则都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框架,无论外界世事如何变幻,他们的生活终将回到原点。作者将自己的情感态度埋藏在民俗事象中,深刻揭示了民众的生存状况与心理状态,使读者产生一种痛彻骨髓的悲凉之感。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在作者对“吕梁人”生存状态的客观、冷静的描述中感受到李锐对解脱人们精神困境投入的真诚、热情的情感态度。
总之,《厚土》的情感叙事,在于作者借助民俗纠葛,把人物的情感细腻化、深刻化,人物形象塑造更加生活化。同时,作者始终不忘对人物“生存”、“命运”的深切反思,使作品的情感张力通过内化的民俗纠葛情节集中展现、放大。
三、“生存叙事”: 叙述历史之外的人生
李锐《厚土》在情感叙事的背后还潜隐着另一种叙事策略: 生存叙事。情感叙事与生存叙事构成了李锐创作的完整叙事体系---生命叙事,它们在其作品中并生共存,不可分割。有学者认为,“文学创作中故事情节与作者情感之间存在一种分歧: 若将情感体验作为叙述中心,常常会导致情节的延缓,甚至中断; 若把情节发展作为叙述焦点,便有可能忽略内心体验的展现。”
但民俗纠葛可以使故事情节的建构和作者情感的表达达到一种平衡,它使故事情节内化,使之成为内部情节,令外部情节得到内在情感的支撑而含蓄隽永。
人类生存中经常面对诸多困难难以抉择,陷入矛盾的情感冲突,甚至不乏哈姆雷特式的生死困惑。李锐小说叙事中把民俗纠葛的矛盾情感与人类生存的矛盾情感,甚至人性的复杂性相结合渗透,从而赋予了小说叙事之外的意义延伸,达到形而上的生命哲学探索。“很多传统的民间信仰和民俗观念……古老的精神观念可以对民众疲惫不堪的心灵起到抚慰、整合、制衡作用。正是因为它们,乡民们才能在艰辛的生存环境中基本保持住自己的心理平衡,从枯燥不堪的生活中感受到些微少的人生乐趣,获得生存下去的勇气。”
《厚土》的主人公面对由民俗纠葛引起的冲突和较量时,有的人通过自我安慰的奇特补偿方式达到心理平衡,有的人则在特殊生存状态下选择肉体解脱、放弃自我。李锐通过民俗纠葛的叙写揭示“吕梁”人的生存困境: 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
心意类民俗纠葛引起的矛盾有时通过主体自控就可以解决,调节失控时,作品中就会突兀地出现没有因果衔接的偶然性情节,此时的矛盾并未被解决,而是暂时的隐藏。《假婚》中汉子得知外乡女人被队长“过了一水”,一时怒火闪现,马上又开始取笑自己无名的火气,之后又发起火来“:吃过水面也叫老子等?! ”当看到外乡女人的泪水便有几分快意,同时也动了心,拿出十块钱让她离开,并流下了他温热的泪水来。汉子的情感变化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本应达到故事高潮的地方,他通过一种奇异的补偿方式达到了心理平衡,情节发展几近中断,但矛盾没有解决,在他意识深处传统观念的对立冲突依然存在,于是产生非理性举动。这种矛盾情感的背后,潜隐的不仅仅是民俗纠葛、传统观念的思考,而且融入了国民性和人性的思考。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自我控制来解决矛盾的。《锄禾》中的“红布衫”为了得到队长的照顾多分一点救济粮,甘愿做他的情妇。《青石涧》的主人公因为交不起彩礼,娶来的老婆是旧的。这种贫穷和落后是吕梁山人的现实困境,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就是普通民众的生存和生活。《看山》中放牛老汉对生命的感悟,《古老峪》中知识分子小李和农民之间的隔阂,《合坟》里的知青和村民的各自困惑和无奈,也折射出李锐对农民的精神困境的深刻体察。一些人甚至在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双重煎熬下,选择了死亡。当传统文化观念受到时代的一次次否认之后,人们的困惑和无助达到极致,死亡便成了最后选择。李锐小说中不同形式大量死亡的描写,不是《厚土》小说个例,而是李锐小说创作的一个特色。死亡是李锐笔下的人物形象对生存困境的无奈归宿, 是对现实苦难世界的超脱,也体现了作家对生命的真实关注。
李锐针对时代历史和民众生活采用不同的叙事方式。李锐在创作中尽量客观地真实描述民众生活,同时,又淡化时代背景,使主题含而不露。作者通过吕梁山民众生存状态的有意凸现,来“叙述历史之外的人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他不愿简单地回归鲁迅式的启蒙批判,也不想跟随沈从文理想化地肯定与赞美。他的笔触只专注在描摹世俗化的民间生活,将民众的生存困境,不惜笔墨地,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淡化历史和时代,并不是不写时代,不是不反映历史,而是用极其精简之笔暗示时代历史。作者只用“知青”、“毛主席语录”、“四清”等特定时代名词,以及《古老峪》里派知青去农村“宣读文件”、《锄禾》中学生娃的“天天读”、《合坟》里用那本《毛主席语录》寥寥几笔暗示作品的时代背景,旨在表现“历史对生存的压迫”.《厚土》将淡化时代历史与细化民众生活两种叙事策略加以糅合,使历史的残酷压迫和民众的悲剧生活构成一种复调,形成生命叙事的完整结构。正如杨矗所指出的“:作者特定的文化视角,只是为了展现被生存法则或政治霸权所决定的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
总之,李锐《厚土》远离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小叙事、底层叙事,更多地去展现民众世俗生活,描写吕梁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但是,这种倾注民间情感的叙事策略中,又始终潜隐着时代历史的痕迹,淡化时代历史,却又处处体现时代历史。李锐关注底层人物的现实生活,围绕他们普泛性的生存困境叙事,这种超越历史又渗透历史,关注现实又指向哲学思辨的生存叙事策略,使得李锐《厚土》有了一种冲击力和厚重感。
综上所述,在 20 世纪末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常常表现出一种浓厚的民间情怀。他们纷纷放弃启蒙立场、拒绝崇高,开始回望“民间”.李锐《厚土》的成功貌似偶然,实则必然。一方面,从创作方法上看,李锐在表达自己对吕梁山区独特乡土情感时,不是简单地将其习俗风尚作为一种地方性民俗知识介绍出来,而是将民众风俗观念引起的矛盾冲突作为情节发展的节点,以此构建甚至规约故事情节,即民俗纠葛成为贯穿故事情节的线索。另一方面,从创作视角上看,李锐不是单纯地做一种启蒙式批判,而是紧贴民间,又用现代意识来观照历史变迁,运用情感叙事和生存叙事的叙事策略将吕梁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洞悉他们潜意识中的历史文化积淀,跳出了历史、政治的叙事话语,企图获得超越时代的贯穿于漫长人类社会的永恒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勤建。 文艺民俗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徐 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3]曹文轩。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李 锐。 厚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5]翟永明。 李锐小说叙事结构分析[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 49.
[6]宋 洁。 论当代文学的民间资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杨 矗。 李锐“焦虑”的祛魅化分析[J]. 文学评论,2005(02): 124.
[8]杨占富。 论李锐小说的民间书写[D]. 重庆:西南大学,2013.
绪言(一)选题意义本文是以敦煌变文为探讨方向,以变文中所蕴含的教化思想为研究主题,期待能够藉由目前已经发掘和整理出来的变文资料,深入探讨隋唐五代时期,敦煌变文中所呈现教化思想的内容、特点及意义。意大利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
梁祝传说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传说,在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与学术价值。梁祝传说自东晋产生发展演变至今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在漫长而悠久的岁月长河中,由梁祝母题衍生的文艺作品蔚为大观。这些主题鲜明、...
(二)敦煌变文中的地狱审判地狱审判的观念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之中,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等都存在地狱观念。虽然不同文化和信仰对地狱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概念是大同小异的,地狱即人死之后灵魂的归宿,灵魂在地狱中接...
关于海洋文化这一概念,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中国海洋大学的曲金良教授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海洋文化,就是有关海洋的文化,就是人类源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
(二)敦煌变文中的符箓神功符箓,又名符字、丹书或墨箓,乃是中国道教通达天地召请鬼神的重要媒介,运用符箓的法师道士需要经过系统而严格的训练。相传符箓之术是由黄帝创立,《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记载元始天尊创制符咒文字,藉由云朵化为篆体传授给...
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也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广大的妇女起来参加抗战救国,则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的胜利与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妇女工作迅速的猛烈的广泛的深入的开展起来!”...
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电子游戏日益成为大众娱乐方式,在极大改变人类游戏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逐步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成为第九艺术.[1]在电子游戏这一自由的虚拟世界里,人类创作的各种艺术形式和文化类型都可能成为文化资源被吸收和再造.作为...
引言《珠江的传说》,属于胡人识宝传说类型,以羊城三石之一的海珠石为传说核,讲述了珠江名称来历的故事。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东卷》收录的版本,其情节内容可简括为:读书人崔炜,偶然帮助神医鲍姑,获赠井岗艾并以此救治了仙人安期生乘坐的白龙玉京...
《汉语大词典》将“商业”一词解释为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方式。商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直到商代,中国才出现商业。“商业文化意指商品流通领域中所表现的具有商业特性的文化现象的总和。...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一种形式,传说以其鲜活的角色形象,错综的情节单元,深厚的生活感染力在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传说的背后蕴含着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和深刻的心理结构,反映并满足着人类各种实际的或象征性的需要。在民间传说一系列家喻户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