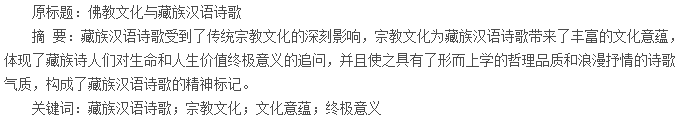
黑格尔指出,“古人在创造神的同时,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1]鲁迅也曾经说过:“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2],的确,诗歌与神话、宗教在浪漫主义倾向以及哲理化的品格等方面,都有着隐秘的精神联系。藏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又是一个有着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藏族诗歌里,留下了宗教影响的印痕,宗教构成了藏族诗歌产生的一大源泉,并且,它对藏族汉语诗歌的发展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宗教信仰以文化的形式向藏族诗歌渗透,对藏族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藏族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在远古时期,藏族人民就信仰原始的苯教,它是一种泛神论的信仰。
“苯”的含义,据德国藏学家霍夫曼考证,它源自“苯巴”,意为用咒语去交通神灵[3] 10。按照苯教的说法,宇宙间一切皆有神灵,这些诸神被分为天上神、地面神和地下神三类,并且传说吐蕃前身的雅隆部落首领即天神下凡,其后的七位首领都在其子13 岁时去世,沿天梯光绳返回天界。“天神以山为阶梯,上下往返于天地间”,这个传说被才旺瑙乳称为是藏族诗歌的“一个卓越的原型”[4],它成为当代藏族汉语诗歌书写的一个文学母题。其后,松赞干布任吐蕃首领的时期(7 世纪左右),佛教从中原和印度两路传入,并与当地的苯教斗争和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喇嘛教)。从此,苯教和佛教文化相互结合,形成了藏族文化的宗教色彩。丹珠昂奔说过:“文化的灵魂是哲学。藏族文化的灵魂是佛教哲学”[5],他还指出:“藏传佛教的形成,从另一意义上说,也标志着新的时代意义上的藏族文化的形成。”[5]
足以见出宗教对藏族文化的形塑作用。
佛教的传入,也极大地改变了藏族文学的精神气质,对此,才旺瑙乳说过:“直到后来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传入吐蕃,并开始逐渐普及,一个民族的灵魂才渐渐安顿了下来。渐渐地,他们由英武好战而变得慈悲和善。慈悲、怜悯、爱与和平,成为吐蕃人至高的人格成份。神性的光辉又回归到这个民族。”[4]
他们由一个尚武好战的民族,变得沉思默想而静穆庄严,并且开始沉浸在诗歌的艺术氛围里,从佛教理念中领悟生命的真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藏民族,佛经就是一首诗篇,是众多洞烛中对生命和宇宙的终极问题给出答案的学说。”[4]
这种运用佛教理念看待世界的方式, 已经渗透在人们的日常思维和活动中,正如藏族民歌里所唱的:“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体量过来的,白色的云彩是我用手指数过来的,陡峭的山崖我像爬梯子一样攀上,平坦的草原我像翻经书一样掀过。”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部需要参悟的经卷。
在佛教传入西藏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直到解放前,宗教势力掌握着文化的特权,寺庙不仅是宗教的活动场所,而且是传授知识、文化传承的所在。佛教徒既是宗教僧侣,又是掌握各类知识的学者,这就使得藏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禀赋着佛教文化的色彩,因此,有论者指出,“藏族传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宗教文学。”[6]
与整个藏族文化一样,藏族文学也深受宗教的影响。宗教对于藏族文学的渗透,既有它有利的方面,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它为藏族文学提供了一种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以及超越世俗世界的文学品格,但另一方面,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藏族文学起到了削弱文学性、而凸现了宗教主题的作用,如藏族作家益希单增,就发出了“宗教的辉煌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辉煌,这是西藏历史的一个悲痛点”[7]的感叹。
一、宗教文化与藏族诗人
藏族汉语诗歌产生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受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宗教文化的因子。由于在意识形态内破除封建迷信,推行唯物主义,在一段时期内还限制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使藏族的宗教文化受到了极大的遏制,对他们的民族感情造成了伤害,这些都成为后来他们进行历史反思的“伤痕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但是,宗教文化的巨大惯性是难以遏制的,有时只是变得更加隐晦,或者以另一种形态隐性地存在着。这一时期,藏族汉语诗人们把对于宗教信仰的虔敬和热情,置换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如擦珠 阿旺洛桑在《歌颂各族人民领袖毛主席》一诗中这样写道:“中央人民政府园林内有一株宪法檀香树,/在弥漫着檀香气氛的林荫下,/西藏人民剧烈的痛苦,得到了解除。”在《金桥玉带》里,也有这样的句子:“爱国主义思想,坚固得像须弥山一样”,在表现颂歌主题的同时,明显渗透着宗教文化的意识。正如丹珠昂奔所言:“就整体而言,藏民族在政治、经济上受宗教支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然而,在思想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宗教依旧占一定地位,庞大的藏族神灵家族依旧十分活跃。”[8]
所以一旦当思想得到解放,创作获得自由,他们的诗歌创作马上就流露出对于宗教文化的认同和皈依,如上个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藏族诗人,在他们 80 年代创作的诗歌中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以伊丹才让的诗歌为例,他在新时期创作的诗歌,就充满了宗教的意味:“我出生的世界,/是佛法护佑的净土”(《母亲心授的歌》),“太阳神手中那把神奇的白银梳子,/是我人世间冰壶酿月的净土雪域”(《雪域》),在他的诗歌里,布达拉宫这座宗教气息浓郁的建筑,充满了神性的意味,它是“屹立天界的城池”,“放射人间的真知”(《布达拉宫》)。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那里,如格桑多杰笔下的玛卿雪山,“寓含着险峻峥嵘的意境,/是高贵、纯洁、宏伟的象征”,“哪一个高原人对您不是怀着圣洁的感情?/人们以美妙的神话来描述您的行踪”(《玛卿雪山的名字》);丹真公布把“拉萨净土界/只是蒺藜多”的佛教格言写进了诗歌,等等,这些都可以体现出他们诗歌里的宗教文化特色。
在新一代藏族诗人那里,宗教意识明显得到了复苏,并成为他们关注灵魂世界、进行内心思考和生命体验的一种特殊表达手段,体现出他们心灵“朝圣”的一种写作姿态。在藏族年轻一代诗人中,女诗人唯色是宗教情绪最为浓烈的一位,她总是沉浸在宗教的彼岸世界里,执着于从宗教中汲取内心的力量,获取生命的真谛,宗教在她的诗歌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感觉和意绪。她曾经说过:“在诗人的笔下,那些情有所钟的元素:扑不起来的小小翅膀,养不大的指甲,来自天上的花朵,单单为谁而长的昂贵骨头,飞扬的尘土,秋日中落在喇嘛肩上的树叶,永恒的光芒,命中之马,紫气,水等等,当它们在诗人的手中熠熠闪烁时, 这就是诗。”[3]
她认为,诗人就是这样的角色:“诗人的心中自有一个宗教世界存在,它是浑圆的,周全的,自足的,它创造了一个高度,或者一个目标,这高度是天堂高度,这目标接近上帝,使诗人以严格而不失浪漫的姿态走出现实,并步入完美。”[3] 242在唯色的诗歌里,“寺院”、“经书”、“袈裟”、“祭司”、“剔净的骨头”等等这样充满宗教意味的意象和词汇,构成了她纯净而迷离的诗歌世界,她通过文字构筑了自己的精神“寺院”,完成了自己的心灵朝圣和内部修行。她的《前定的念珠》、《另一个化身》等诗歌,都是能够体现她诗歌特色的作品。以她的《德格——献给我的父亲》为例:
这部经书也在小寒的凌晨消失!
我掩面哭泣我反复祈祷的命中之马怎样更先进入隐秘的寺院化为七块被剔净的骨头?
飘飘欲飞的袈裟将在哪里落下?
我的亲人将在哪里重新生长?
三炷香火,一捧坟茔德格老家我愿它毫无意义!
我愿它无路可寻!
一万朵雪花是另一条哈达早早地迎接这个灵魂在人迹不至之处,仙鹿和白莲丛中最完善的解脱!
在对老家的思念和对父亲的悲悼中,唯色注入了强烈的宗教情愫。诗歌中对轮回、解脱的祈祷,包涵了诗人对生命与存在、世俗与超脱的思考,因而具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提升力量,一种清澈的净化功能,这是唯色的个人风格,也是藏族诗人们整体的精神特征。
二、宗教文化与诗歌艺术
丹珠昂奔指出:“我认为藏族文化存在着‘藏属民族文化圈’和‘藏传佛教文化圈’两个文化圈。”[9] 164这两个文化圈也对藏族文学产生着交互的影响,也构成了藏族文学的两大文化资源。藏族汉语诗歌也是如此,如果说“藏属民族文化圈”主要涵盖的是藏族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文化资源的话,那么“藏属佛教文化圈”则涵盖了它的宗教的文化资源,这两个文化圈共同滋养、渗透着当代藏族汉语诗歌的成长,为它的发展打上了醒目的精神标记。藏族汉语诗歌受到的宗教文化影响,除了表现在诗歌主题的表达上以外,还体现在诗歌艺术的表现上,在诗歌的文化意蕴、诗歌意象以及哲理性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宗教文化的印迹,形成了藏族汉语诗歌不同于其他民族诗歌的一个显着特征。
首先,它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汉语诗歌的文化意蕴。佛教重视心灵世界的修养,提倡忍让和奉献,重来世、轻现世,具有超脱世俗的精神品格,这些宗教理念渗透在藏族汉语诗歌里,就形成了它含蓄、内敛、宽厚、悲悯的精神气质,以及深层次意义上的悲剧感。有人曾经指出:“真正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对人的关怀,通过一种神秘体验的方式,来达到对人生最高存在的领悟。”[10]
正是由于禀赋了这种宗教文化精神,因此,藏族诗歌普遍表现出对于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刻同情,具有悲天悯人的苦难意识。在藏族古典诗歌里,就表现出对世俗功利的淡泊、对生命理想境界的追求,呈现为一种净土意识与空灵意境,如 14世纪格鲁派大师宗喀巴的诗歌就常常用“皑皑雪山”、“蓝天秋月”、“如银月光”等意象,来象征一种空灵的意境和纯净的品质。在藏族汉语诗歌里,这样的情形也很常见,如梅卓在《酒醒何处》里“雅砻,雅砻,/清洁无比的名字”的句子,唯色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剔净的骨头”等等。除此之外,佛教重视顿悟的思维方式,也潜移默化着诗人们的创作灵感和艺术风格,使他们注重诗意的表达空间和内部张力,往往表现得含蓄蕴藉,留下了许多空白,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如嘉央西热的诗句“一只鹰一掠而过/我隐约听见婴儿的啼哭”(《生命本源》)、“一个雨后的清晨,彩虹穿过峡谷/庙宇的金顶,修行禅室的灵光/逐渐普遍四面八方”(《庙宇精神》),拉目栋智的诗句“一个人坐在草坡上/望朝佛的人们涌向前方”、“一个人坐在草坡上/大脑空空如洗,总也/记不起任何事情”(《坐在草坡上》),等等,都言尽而意不穷,留下了许多余韵。
其次,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在藏族汉语诗歌里,还出现了大量的宗教语汇和诗歌意象,如修行、灵光之类的宗教语汇,以及寺院、莲花、玛尼堆、转经筒、桑烟、经幡之类的宗教意象,在藏族汉语诗歌中都极为常见。这种情形,尤其体现在年轻一代藏族诗人的作品中,如在嘉央西热的诗歌中写道:“一座红色建筑/ 耸立于须弥山的善域中央/日月星辰才为此旋转、闪烁”(《生命本源》),“额角刻有经文的牛羊/灵魂随处飞扬,一个行囊空空的香客/把一块石头放在更多的石头之上”(《庙宇精神》),对藏民族的宗教精神进行了阐发;吉米平阶诗歌中,有“头顶有灵光的老人”、“山脚下迷路的灵魂”(《城市》),以及“日子如库存的多节法号”(《日子》)之类的诗句,很有禅悟的意味;而道帏多吉笔下的布达拉宫,是“太阳和精神的圣殿”、“弥漫天地的六字真言”(《圣地之歌》),充满了神性的色彩。此外,女诗人阿卓在近乎迷醉的敬仰与崇拜中,发出了梦呓般的礼赞:“我要用松柏的枝叶舞动天上的风光/用好看的姿态为你奉上一百零八杯圣水”,“让我口诵无上的经语,把吉祥的长明千灯/托向八瓣水晶之心”(组诗《幻象与倾诉》),而唯色笔下的“经书”、“寺院”、“袈裟”等等,以及才旺瑙乳和旺秀才丹诗歌中的“大师”、“桃花”之类,都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诗歌意象。
这样的情形在藏族诗人们笔下,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风景。
按照佛教的观点,世界是由风、水、火、土四大元素组成的,因而,在藏族汉语诗歌里也出现了大量与这四种意象有关的诗歌,如阿来在《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大草原》写道:“部落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像匆匆鲜花不断飘香”、“野草成熟的籽实像黄金点点”、“泥土、流水/诞生于岁月腹部的希望之光/石头,通向星空的大地的梯级”,在这里,大地上最普通的元素,如泥土、石头、流水、野草、鲜花等等,都被他赋予了神性的色彩。诗人班果也写过许多这样的句子,如“作为石头,我必须获得土/作为土,我必须由水来养育”(《继承》)、“迎亲的骏马踏起尘土,众多的/元素在尘土之中闪耀,谁能看见/尘土中的一个坚固城堡,一个/新世界已接近诞生”(《婚典》),等等,其中就蕴含着宗教文化的因子。当然,类似的诗句在其他诗人的诗歌里也是屡见不鲜的。
此外,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藏族诗人还惯于思考天地万物和人生哲理,形成了藏族汉语诗歌沉思冥想的诗歌气质和形而上的哲理品格。藏族汉语诗歌经常描写到天界、佛、神灵等等,把它们作为理想、真理和价值的最高标准。才旺瑙乳说过:“无论从神话学的意义还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藏文化都从未间断过对神——终极真理的追寻。”[4]
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说,这种对神的叙写,正是体现了藏族诗人对于世界存在以及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的热情探索和不懈追求,体现了他们对于世俗生活和庸常人生观念的精神超越。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11]
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当代藏族诗人们的精神写照。
并且,藏族诗人对神灵的叙写,还为藏族汉语诗歌赋予了高度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浪漫抒情的诗歌特质,丹珠昂奔就曾说过:“佛教的这种时间观念给藏族文学的浪漫主义风格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崇信佛教义理的传统作家们不再拘泥于现实的小小天地,而使自己的思想常在这恢恢的佛教宇宙系统中游弋、驰骋,将自己的文思之光射向历史、现实、未来和虚幻的佛教宇宙之中。”[9] 134藏族诗人们正是凭借着本民族得天独厚的文化和精神资源,才得以在更加博大恢宏的空间里驰骋诗思,也为他们诗歌创作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提供了可能。
总之,宗教文化对藏族汉语诗歌影响极为深远,对于藏族诗人来说,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他们表达精神世界、理解外部世界的文学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藏族诗人还如德国学者汉斯 昆伯尔所说的,“把广义的宗教理解为宗教感,理解为与大自然、与人类、与事物的虔诚联系”[12],形成了他们普遍的宗教感,这种宗教感使他们获得了对现实生存状态的精神超越,对藏族汉语诗歌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美学: 第 2 卷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79: 18.
[2] 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M] //鲁迅全集: 第 8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315.
[3] 马丽华. 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4] 才旺瑙乳, 旺秀才丹. 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序 [M].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5] 丹珠昂奔. 佛教与藏族文学 代前言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6] 梁庭望, 张公瑾.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出版社, 1998: 22.
[7] 益希单增. 西藏文学的过去与现状 [J]. 西藏大学学报, 1999 (1).
[8] 丹珠昂奔. 藏族神灵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43.
[9] 丹珠昂奔. 藏族文化散论 [M]. 北京: 中央友谊出版公司, 1993.
早在1967年3月14日,福柯先生便在一场演讲中宣称: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当前的时代是空间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布...
白马藏族文学与白马语密切相关,是其口语语言的艺术。在流传形式上,其散说体也即叙事体,与韵说体也即抒情、叙事或抒情叙事体相间并存。白马藏族文学的散说体体裁,主要有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等;韵说体体裁,主要有古歌、山歌、劳动歌、酒歌、生活歌、...
思维是人类独有的高级心智活动,是大脑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客观世界反映、概括、记忆、综合、分析、比较、选择、创造等的认知功能。而思维方式是指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
历辈达赖喇嘛传记是藏族高僧传记中的经典作品,这些传记在如实记载历辈达赖喇嘛生平活动,还运用了许多文学表现手法,使传记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其中神异故事描写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族群的历史源流的线索,需要有众多的口头传说。尔苏藏族无通用文字,族群的历史源流线索,以宝贵的口头文化遗产的形式存在。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民族生活及民族迁徙经过等,都是口头文学的内容,都借口头文学代代相传[1]16。大量的...
一、藏族古典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自公元七世纪,第三十二代藏王松赞干布委派吞弥桑布扎等十六位天资聪慧的年轻英才到古印度学习梵文,后到吞弥桑布扎潜心钻研,参照印度的迦什弥罗文字字形,结合吐蕃语音创制了现代藏族人广泛使用的三十四个藏文字母。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