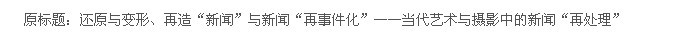
让我们从最近的事情说起。2013 年重阳节,安徽省宁国市副市长与当地民政局的官员为表示对于老人的关怀,一起去看望当地的百岁老人。这种政绩型工作,当地政府官方网站当然要报导。不过,当政府官网上出现了经过 PS 处理的众官员看望老人的照片时,却引起了各地网民的强烈反响。因为在报导官员的工作的照片里,手捧红包的老人低头蜷缩于屋子一角,而身材高大魁伟的官员们则居高临下地俯视犹如枯木的老人,双方的身形大小比例经过明显的 PS 处理后变得极其悬殊。以如此手法处理官员与孤寡老人,令老人成为了被官员们观赏的物件,无法不引起各地网民们的愤怒。在网民们的抨击之下,当地政府以官员视察时空间逼仄、无法完整拍摄到全部到场官员、无奈之下才出此PS 下策作为解释以自我解套。但这种“官本位”的解释结果更是弄巧成拙,反而进一步暴露官员的自大、自恋与蔑视民众,理所当然招致谴责与嘲笑。不过,这波风浪也反过来证明,有恃无恐的“官本位”意识至今仍然在主导一些新闻照片的生产与传播方式。
从这个最近发生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照片进行加工改造,以符合政治宣传与满足官员的自恋心态的做法,至今仍然时有发生。而在 PS 手段发达的今天,什么是符合官方利益的新闻与新闻图像,显然在那些习惯通过操控新闻的生产与发布,有意模糊宣传与新闻界限的人看来,似乎更是易如反掌了。但是,正是身处这样的现实之中,还是有一些艺术家与摄影家,更具针对性地动用摄影这个既“照”相又“造”相的视觉手段,来破解与抵制操控图像生产各种企图,以一种反操控的态度与立场,争取对于新闻事实与历史的自主解释,并且努力授予观众以反思图像及图像生产之可能。
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较早就有人意识到大众媒体的存在与作用,并且通过作品关注传播媒介的作用与影响。早在 1997 年,周铁海的《新闻发布会》就通过将自身置换成新闻发言人的方式,在宣布了中国艺术家与中国当代艺术亮相国际舞台的同时,也展示了他对于媒介在当代艺术传播中的作用的敏锐意识。而他将自己的个人形象以大头像方式置换进如美国《新闻周刊》等国际着名新闻杂志的方式,更清楚地展示了他对于媒介的利用意识。他的这些作品,都指涉到艺术与传播之间的复杂关系。
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像王璜生的《线象·南方周末》系列(2012-13)这样的作品,通过画家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媒介《南方周末》的版面上展开线条书写的方式,展开某种以图像来抵消新闻图像与文字的具体含意的实践。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当代摄影家与艺术家,如何采取摄影这一手段,或艺术地跟进新闻事件并再现之,或重考新闻中的历史与事件,力图对于新闻及其生产方式与制度作出更具阐释性的视觉呈现。本文也希望通过对于近期活跃于中国与世界艺术现场的艺术家与摄影家的实践的讨论,检视他们如何积极运用视觉策略与视觉手段,展开有关以新闻为焦点、以新闻图像与生产为对象的创作实践,发现一种新的图像生产以及艺术与社会对话的可能性。而通过艺术来揭发图像生产中的各种手法与惯习,除了激活艺术本身的表现力之外,也是提升公民破解媒介编码能力的重要方面,这同样需要艺术家之介入与参与。
排查与还原:张大力的《第二历史》
承接本文开头的例子,我想首先讨论张大力(1963-)的工作。如果说现在以 PS 的方式修改照片可谓易如反掌的话,那么在 PS 出现前,则是以手工方式加以剪贴拼接以达成某种特定的宣传与视觉效果。
现居北京的张大力的《第二历史》,指的是相较于存在于即存历史文献中的已经成为了文献的“第一历史”,通过他的严密排查所获得的不为人知的原真存在,是为“第一历史”的第二种存在方式,也即“第二历史”。这些被他关注的摄影图像,往往在中外媒体中流布甚广,有些甚至是革命叙事中的圣像式(ICONIC)的图像,对于革命叙事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张大力对于这些图像却并不盲信,反而展开图像源流的追索并检视其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比对其原始图像与最终传播图像,暴露、揭示出于各种目的而对图像的篡改,破除对于照片所代表的“真实性”的迷思。
这是一个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于档案馆、图书馆等视觉文献储藏空间的既令人兴奋也非常沉闷、同时也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通过他的工作,我们发现,在埃德加·斯诺在 1936 年在延安拍摄的毛泽东的肖像照片中,他一脸的忧虑憔悴的表情在他掌握政权政权之后被修涂为英姿勃发,毛泽东从年纪上看也年轻不少。而在 1978 年毛泽东去世后刊出的他参加 1945 年的重庆谈判照片中,陪同他来到重庆的美国人赫尔利被修掉了。在一些有关 1950、60、70 年代的中国建设报导的画报照片中,编辑们可以根据对于画面与“美好”未来的想象将几张照片加以组合,以得到更为美观、壮观的画面。张大力的工作,我们发现,对于摄影图像的改篡,基本上包括了对图像的裁剪、对于画面中人和物的处理(经常是消除某些人的形象,偶尔也会加上或者调换某个人的形象),以及说明文字的不同书写等多种方法。这些形成了“第二历史”的“历史”照片的“创作”手法,如美术史家巫鸿在本展览图录中所归纳的,基本有七。“(1)取消照片中的特定人物 ;(2)置换照片中的人物 ;(3)框定局部,取消形象的上下文 ;(4)改变背景,突出中心人物或主题 ;(5)增设或取消道具和细节 ;(6)对中心形象加以‘提高’和润色 ;(7)改换或增加照片中的文字部分,给予画面以不同的或加强了的主题。”(P7)巫鸿同时指出,“这些方法常常结合使用,其目的有多种,有时是直截了当地政治性的,有时则是带有‘艺术性’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理想的画面。”
张大力的图像排查工作,暴露、还原了出于各种目的对图像的放肆篡改及其过程,揭发了图像生产与流通的机制、惯习以及思想操控的意图,清晰地呈现了“新闻”(?)生产中的复杂的力量关系。这个工作当然触及了过去中国的新闻实践与伦理,同时也涉及今天的新闻实践与伦理,再次提出了至今仍然必须正视的报导底线何在的问题,这当然也包含了摄影家本人对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反思与批判。暴露“红包”的存在:张晓的《信封》系列。。
而以《中国海岸线》系列成名、现在成都生活与工作的张晓(1981-),在 2013 年的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上,通过 240 封信封来展示他在重庆担任报社摄影记者时所收取到的大量的“红包”(所谓“车马费”),将在中国新闻界司空见惯的陋习暴露无遗。这个名为《信封》(2010)的作品大量展示了他在采访时所收取的“红包”信封。据他自己说,在他担任摄影记者的三年多时间里,共收到了近 400 个红包。
他把这些“红包”信封都收存起来,即使不再从事记者工作后也保留着这些信封。在展览中,他以格子状密集排列的方式,集中展现了往往并不如此明目张胆地存在于人们视线内的“红包”的存在。
这些“红包”的信封上都印有赠送红包的单位的名称。从名字看,这些单位既有行政部门(如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也有或官商或民营或外资合营的各类工商企业(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重庆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等)。显然,人们只是从这些单位名称就可以发现,向到场记者派送“红包”是一个横跨了政商各界的普遍现象。
而且那些在自己本国不可能接受这种做法的外资企业也已经欣然接受这样的潜规则。
有意思的是,张晓在这些“红包”信封上面贴上了他为这些单位的活动所拍摄的新闻照片,直接地、直观地呈现了“新闻”(?)生产(?)中的赤裸裸的“银货两讫”式的支付与回报关系。张晓所提示的是一个成为了结构性的问题,如今却被他以这样的直白方式呈现了出来。在今天的中国新闻界,记者往往被称为“新闻民工”,意思是他们也是收入微薄、辛苦揾食的“民工”一族。因此,在收入没有可能体现职业与个体的尊严之时,“红包”在新闻采访中大行其市,也在料想之中。这不是为记者勇于收取“红包”辩护,而是在此给出考虑他们所以如此的思考空间。
试想,当所有的记者都习以为常地在采访活动中收取“红包”,以“红包”中的小钱补贴日常开支时,显然在他们跨越了职业伦理底线的同时,也失去了从事新闻工作所需要的自主性。而当他们后来再要从事某种深度调查型的报导工作时,任何当事方只要以他收取过“红包”为名即可治其罪,因此也就可以轻易地使记者的调查无法再继续下去。而这些贴在信封上的“新闻”照片,也已经不需要记者以拼抢方式来获得,这些照片或可安全拍摄,或被安排拍摄,无需记者冒险犯难,因此长期从事并且乐于这类“新闻”的报导,记者的专业能力之削弱似在情理之中。而当媒体充塞了这类报导时,其公信力的衰亡则是不争的事实。从根本上说,“红包”是对于新闻业的致命破坏之一。
不过,人们也可以通过分析这些被张晓打印在“红包”上的所谓的“报导摄影”照片,知晓这些照片在哪些方面具有所谓的新闻特性、拍摄者遵循了什么样的原则选择了这些照片的瞬间等角度去展开思考。它们同时也都成为了了解当下中国“新闻摄影”实践的有意思的样本。张晓的这个触及了当下中国新闻伦理的作品,也提出了必须正视的新闻报导的底线何在的问题,当然也包含了摄影家本人对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反思与批判。
历史影像的变形及提问:王国锋的《报导》(NEWS)虽然与张大力一样是以过去的新闻照片作为处理对象,但北京王国锋(1967-)的《报导》(NEWS)系列则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与手法。
王国锋近年来一直拍摄前苏联、朝鲜等国的大型国家建筑与举国庆祝的超大型集体活动的巨幅全景式照片。这些将国家的超级权力意志通过大型建筑与超大型活动加以呈现的摄影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这些巨制作品相平行又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开始于 2005 年的系列作品《报导》系列。这是一些从平面媒介到互联网等各种不同的媒介形式中挑选出来的传播比较广泛的新闻图像,但王国锋通过电脑软件对它们再作一定程度的模糊化处理,在制造一种似是而非式的视觉认知障碍的同时,他再在画面中加入导引性的同时又具质疑性质的文字,引发人们对于新闻背后的、以及之后的事实与事态展开新的思考。
比如,在一张展现了众人蜂拥于柏林墙上的照片中,他压印了“他们是谁?”“这里发生了什么”的中英文问题,而在美国白宫官员观看击毙本拉登过程的照片上,他压印了“他们是谁?”“他们看到了什么?”的问题。显然,这些看似最简单、直白的提问,更进一步挑起了对于历史与成为旧闻的新闻的疑问。他的这些提问式的文字,对于习惯于以文字来说明新闻照片的人来说,它们究竟是限定了还是再度打开了成为了历史的新闻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策略所采取的使得画面有意失焦的手法,可不可以说是一种通过对历史(新闻)的选择性对焦而表明作者对于新闻与历史本身的质疑?
新闻的跨形态转化:李郁+刘波小组的《暂未命名》
如果说上述张大力与王国锋的策略是或还原或变形新闻(历史)照片提示有关新闻与历史的疑问的话,那么在武汉生活与工作的李郁(1973-)+刘波(1978-)二人小组的作品则是将发生在当下的新闻照片再作跨形态的改变,以求得对于现实与真实的某种重述。
他们的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 2006 年到 2010 年 , 他们根据当地报纸上的某一段文字新闻的描述,提炼出一个画面,然后请人扮演其中角色再加以拍摄,做出一张新闻照片,将文字新闻可视化。而从 2011 年起,他们开始尝试将取材于当地报纸的一张新闻照片转变成一段片长为六分钟的视频录相,从视听效果上使新闻照片发生某种变异,以产生更为奇异的荒谬效果。所有这些视频录相作品都被冠之以《暂未命名》。这些平面摄影与视频作品,都取材于他们生活的城市武汉的两份报纸《楚天都市报》与《楚天金报》。在今天的中国,这类市场化的报纸被称为都市报,具有报导社会新闻、满足市民趣味的功能,还负有创造利润的职责。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都市报上刊出的新闻,在一定意义上说可能更符合新闻的定义与专业标准。也因此,刊出在都市报上的这些社会新闻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被转换成照片或视频后更具某种荒诞性的基因。
当然,这些所谓的“新闻”,在报纸上被选择刊出时,本身已然具备了某种新闻性(荒谬性)。
李郁+刘波小组及时跟进媒体上的新闻,再做执导性演出与视频的拍摄,赋予其某种时间性,并且通过这种“新闻再叙述”的方式来放大、强化新闻中容易被忽视的某些方面,凸现其新闻效应,或加深人们对于新闻事件的认识,或质疑所谓的新闻的定义。他们以“再造新闻”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立场与观点。面对他们对现实生活与新闻所展开的“平行叙事”的“伪新闻”作品,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发问 :艺术与现实,到底哪个才是今天的真实?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工作到底是在模仿现实还是在创造现实?这种属于“新闻再现”的策略,对于人们对现实与新闻的看法带来了什么改变?
尤其是《暂未命名》这批视频作品,不仅只是简单的新闻形态的转变,更是一种对于新闻的事态的转变。从被压缩成瞬间的照片到被制作成具有一定时间长度的片断化的视频,视频首先在时间上恢复了这些“新闻”的某种进行时样态,但这些事件在视频中被“变形”、被呈现得似乎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与结果,因此反而强化了一种反新闻性的叙事,同时也因此更具有了某种荒谬性。它们让观众浸泡在一个时间片断里,因此他们所获得的感受与面对一个作为新闻照片的瞬间切片时的感受生产了区别。这种把过去的新闻再距离化,同时也再提问的“变形”方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新闻及其定义的新面向。
虚构“伪”新闻:王宁德的《最佳新闻奖》
在数码时代如何反思新闻生产以及大众娱乐,因为数码技术的再造可能而使得这种反思有了新的可能性。以下两位艺术家与摄影家王宁德与傅为新的实践可能更接近于对于新闻生产的标准与形式加以批判,而他们所运用的手段却与数码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李郁刘波小组的平面摄影与视频的素材尚且有所本不同的是,现在北京生活与工作的王宁德(1972-)的《最佳新闻奖》(2004-2005)系列是根据“跳楼”这一社会现象来概括、提炼,然后加以执导,创造出一种作为“新闻”赝品的画面。这是一种虚构,但可能是对于现实的更为艺术化因而也更具新闻性的再现实践。
王宁德的《最佳新闻奖》系列创作于他即将离开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时。他在广州做过 10 年的都市报新闻摄影记者,曾经目睹了大量的类似事件。这组模拟了突发新闻照片的作品出现的背景,则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个体因为受到高度压榨而走上自杀之路。这种的愈演愈烈的跳楼现象的发生,尤其以台港资本巨型跨国代工企业普遍驻扎的广东、深圳等地发生得最多。而在他要离开摄影记者职业赴北京转型为职业艺术家时,他在一段时间里集中精力、通过建构的方式再现这一现象,了却心头郁结。
他请人扮演跳楼者,然后再以数码技术加以重新组合,以更“专业”、更到位、更精确的瞬间来展现跳楼自杀这一悲剧性画面。但讽刺的是,画面中所呈现出来的一切,都是以新闻摄影美学(如果有所谓的新闻摄影美学的话)为参考、为标准而虚构的画面。在万里晴空中,失重飘浮的人以及分崩离析的现实的呈现,既有一种残忍的美感,也更突出了新闻对于突发事件的幸灾乐祸的本质。
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指出的,“拍摄下来的暴行画面带来的震撼,随着反复观看而消失,如同第一次看色情电影感到的吃惊与困惑。”
“震撼”之后的麻木,接着是要求更多的震撼以确认自己是否还麻木。如此往复循环,新闻摄影在追求不断升级的视觉“震撼”的不归路上绝尘而去。一度盛行于新闻摄影界的“视觉冲击力”之说,恰恰就是一种只从视觉上去讨论画面效果的专业要求,而专业新闻摄影评奖也多以“冲击力”如何作为衡量标准因而陷入一种人性与专业的冷酷。
王宁德的这个作品的标题,其实就在讽刺这种专业标准。他想要指出的是,当面对人的悲剧时,“最佳新闻奖”以及其背后所支撑的专业理念其伦理意义何在?“最佳新闻奖”的颁布,究竟在是哪个层面上来肯定与表彰这样的照片是“最佳”?因此,《最佳新闻奖》系列,既呈现了中国的社会现象,也深刻触及专业主义要求下的新闻摄影的伦理困境。
当人们震惊于在广东的超大型跨国代工企业的接二连三地发生员工跳楼自杀的新闻时,他及时制造再现跳楼这一行为的伪新闻照片,通过对于模仿了新闻照片格式的伪新闻照片的美学化处理,在突出了这个现象的震撼力的同时,也反思专业主义的标准的冷酷一面。
反思大众文化:傅为新的《中国电视》
电视既是大众娱乐产业的一部分,也是新闻产业(我们终于触碰到了新闻与产业的关系了)与舆论宣传的一部分。电视娱乐节目的生产,在今天中国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大众麻醉品加以生产,并且参与对于大众价值观的塑造。
浙江傅为新(1973-)的《中国电视》处理的就是当代电视节目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他聚焦于各种生活空间里的电视机的存在,传达了电视作为一种信息获取与娱乐形式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高度渗透。同时,他也刻意选择电视机开启时的图像,在拍摄之后通过电脑软件把它们嵌入到电视机的荧屏中。由此,他把电视机图像、电视图像以及电视机所在空间的景象拍摄在一起,既扩展了图像的信息量,也通过电视图像中的人物表情(一概都是闭眼)与室内空间景观的并置达成某种特定的视觉效果。他说 :“我直接将各类电视节目中人物闭眼的瞬间状态抓拍下来,以喻当下电视节目存在的‘无视现实、盲目生产和价值短视’之现象,并将这些画面附着于各种差异性的现实环境。各种现实的环境又反映了电视主人的不同社会身份、地位和文化背景,折射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
傅为新的策略是通过电视人物闭眼的形象来制造矛盾与讽刺效果,或者说用他们闭眼的形象来消解他们的权威性。对于电视要打造的明星们来说,眨眼时的闭眼瞬间,在连续性的节目时段里属于日常生理现象,观众也不会认为他们眨眼时的闭眼有什么反常。但如果闭眼这个瞬间在平面照片中呈现时,就是个反常的而且是要刻意回避的瞬间,而傅为新偏偏从这个具有反常特殊性的瞬间着手,显然表明了其个人的有意为之的批判态度。他通过这种再框取,表达了对于电视节目的厌倦与讽刺。而荧屏中的表情与荧屏外的周边景象也构成了某种对比性,因此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对比。
这是一部在外形上具备了新纪实摄影特征的作品,主观取景的意图明显,图式上也形成鲜明的一致性,但因为 PS 手法的运用而使得它无法归入纪实摄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也是一部令纪实与艺术之间的边界发生滑移的作品。
新闻的再事件化:区志航的《俯卧撑》系列
相比较于如实地记录突发事件,面对各类触动人们神经的新闻事件,现在广州的区志航(1958-)采取了将行为艺术与个体纪实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处理方式。他的《俯卧撑》系列是以一种个人行动与身体行为来表达自己对于新闻以及现实的态度。
每当中国各地有重大社会新闻发生,而且这些事件有被纷至沓来的其它新闻湮没之时,区志航都会根据自己对于事件的影响与社会意义的判断,迅速赶赴事发当地,在仔细勘探好事件现场之后,脱下衣服,以自己的全裸形象向着事件现场作闪电式的俯卧撑动作,并且让事先安排好的照相机迅速拍摄下自己的行为。他以这样的“不逊”的裸露姿态,抗议包括权力在内的事件制造者对社会、公民以及公民知情权的傲慢,也希望被画面中的这些建筑与现场所象征的重大社会事件,可以像他所愿意主动裸露的身体那样,有真相被“裸露”出来。
把社会事件与自己的身体胶合于影像中,使得那些可能就此被掩没于信息洪流中的重大事件,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加以放大,是区志航的艺术策略。区志航的《俯卧撑》系列开始于 1999 年,至今已经就近 300 个新闻事件实施了他个人的“俯卧撑”表态。他之所以在作品中持续采取俯卧撑这个动作,并且给整个作品系列命名为“俯卧撑”,是因为他激愤于贵州瓮安事件时当地公安局发言人所给出的解释的荒谬性。据当地公安发言人介绍,死者李树芬的跳桥自杀发生于一同在桥上的朋友刘某某做俯卧撑之时。区志航以此说法作为这个系列作品的标题,以志对于此说的永久疑虑与讽刺。区志航确信,只要他的这个“俯卧撑”行为继续下去,此解释、此行为以及这个系列作品本身就会成为对于“俯卧撑”一说的永久质疑。当然,这也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对于他认为不可忽视的社会事件与现象所作出的一种个人反应。
区志航的这种将新闻事件身体化、事件化后再予以放大、扩散的方式,对于新闻当事者造成一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将社会问题公开化、可视化的目的。他把自己的身体插入到已经将要成为旧闻的新闻现场,再度使之事件化与新闻化。同时,他的持续连贯的行为艺术摄影实践,其记录图像串连起来,也构成了一部出自他的个体判断的有关某个时代的新闻事件编年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报导就是一种暴露的实践。但吊诡的是,由于许多新闻没有被应该实施曝光调查的新闻机构加以深究,因此许多事件以及背后的原因无从揭发。而区志航则以“苦肉计”的方式暴露自己身体,以此突出事件被掩盖的事实并且要求事件真相的揭示。他的身体如同一个箭头,指向发生事件的现场,直接指引人们视线再次投向新闻事件本身。
如果说李郁刘波小组的作品是根据新闻事实有所依据所展开的再度创作的话,那么广州的区志航的《俯卧撑》同样也是依据实际的新闻事件而展开的再度创作。但区志航的作品仍然具有真实性,发生事件的场景没有变化,也作为一个新闻事件的真实要素而存在,而被记录下来的他在事件现场的个人行为表演,也真实存在过。唯一缺席的是曾经发生的新闻事件的主人公,而区志航以自己的在场的身体替补了、取代了已经消失的事件主人公的身体。不像李郁刘波小组的《暂未命名》,那是通过他们的执导演出而使得一则新闻转变成一种完全的虚构,并且更具有了某种戏剧性,区志航的《俯卧撑》则仍然努力保持其新闻性并且加入了其个人性要素,使之成为了一种结合了个体(身体)与事件的对于新闻的主观解释。
结语兼讨论
发生在今日中国的五花八门的新闻事件,其强度前所未有,其怪异性也远远超越常人想象,或者说在在挑战众人的想象力。难怪电影导演贾樟柯、作家余华都会毫无顾忌地以新闻事件为素材,创作了电影《天注定》与长篇小说《第七天》。而负有全面报导社会新闻职责的专业新闻与报导摄影师们,除了自身所受的新闻管制与专业标准的多重限制之外,也在新媒介时代因为媒介形态的原因反而经常面对社交媒介上及时发布的新闻与消息而面临报导滞后、不在现场的尴尬。
面对这样那样的严峻挑战,以视觉叙述为主要手段的新闻人如何以更具社会责任的、更专业的、更具前瞻性与问题意识的报导引领公众来思考、关注社会发展的当下与未来,当然是媒体的也是新闻报导摄影从业者的重要社会职责。作为专业从业人员,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实践给予答案。而当代艺术家与摄影家,则更可以撇开专业伦理与标准,大胆灵活地运用艺术手法,担负起反思新闻的生产与体制的任务,并且通过给出别开生面的反思与新启示也展示他们对于作为现实的新闻以及作为新闻的现实的态度与思考。本文所述及的摄影家与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从根本上说都是致力于从各种角度来提问“何谓新闻”这个问题,同时也提问“何谓现实”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尤其是在新闻本身已经受到了诸力操控的情况下,以艺术的方式展开的形式丰富的提问显得极其重要而且也很有必要。
本来,新闻报导的基本责任与立场就是报导与揭示事关民生的、有关社会发展的较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新闻报导或停留于事象或止步于权力,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在这样那样的无奈之下生产出来的新闻,既成为了了解特定时代的新闻生产的标本,也成为了上述艺术家以之展开艺术生产的素材。尽管我们仍然需要典型的报导摄影手法对于现实的观察、描述与分析,但意识并且反思其局限更需要某种勇气与努力。
媒介的发达使得资讯的传播达到了惊人的效率。从当代艺术的角度看,我们有时甚至无法确认现实与影像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无处不在的影像在绑架新闻生产,还是新闻带引着影像生产?
不管怎么说,大量的新闻的生产,无疑刺激了摄影家与艺术家们的现实感。面对新闻与新闻背后的现实,有一批人起而行,赴汤蹈火地去获取并展示他所认可的真相图像,期望让更多的人从中发现世界的复杂。这可称为是一种“在”现场的报导摄影实践。另有一批人,从新闻图像获取资讯与灵感,将它们作为再造现实的素材与线索。这种结合了现实态度、艺术观念与表现手法的实践,可称为对新闻事实作艺术“再”处理的创作实践。
这种对于包括电视娱乐在内的广义的新闻及其生产方式的“再”处理,手法多样,形式多元。既有张大力与张晓这样的重新还原新闻生产方式与机制的努力,也有王国锋与李郁刘波小组这样的更具主观性的变形记式的再现与再考。而王宁德与傅为新则积极运用数码技术的便利,来虚构新闻的内容与场面,达到反思新闻原理与现状的目的。最后,这种“再”处理在区志航这里演变成通过新闻“再事件化”的方式让自己也进入到了新闻之中,以此唤起人们对于新闻与现实的再度关注。因此,在“再”处理新闻的这个议题之下,无论新闻还是旧闻,在这些人的手中,创作虽然以新闻中的事实为缘由而展开创作,但最终并不完全依赖新闻也不迷信新闻本身的权威性,而是在原有新闻形态的基础上,有时甚至采取“反新闻”的立场与方式来造成质疑新闻以及新闻生产机制的契机,打破对于“新闻”的迷思。而这种质疑与挑战,或许正是艺术所可能达成的。这种从艺术的角度所展开的讨论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更有利于我们以此为契机审视眼前的新闻与现实本身。
他们通过对于新闻的艺术化的“再”处理,同时也处理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新闻制度与新闻生产的关系,艺术与新闻的关系,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这对于促进反思新闻生产本身也有一定的助益。他们的艺术实践还抛出了另外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他们选择新闻图像作为创作的素材,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与生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也许并非如此。因为新闻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如何面对它甚至反制它,其实也是通过艺术与生活重新发生关系、以此介入社会生活的途径之一。同时,产生某些问题的结构性原因能否展现以及如何展现,也考验到了他们对于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度以及如何运用艺术来展开讨论的能力与智力。当然,这种艺术讨论本身有时也会暴露所运用手段本身的局限。
目录摘要Abstract第一章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文献综述与述评(一)国外文献综述(二)国内文献综述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一)研究视角(二)研究方法四、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一)研究目的(二)研究意义五、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艺的创新发展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只有文艺的繁荣发展,才能使人们增强文化自信,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从图腾符号、语言文字、印刷传播、再到以视觉化影像作为传媒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符号和图像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串连起来,并展示着人们在不同社会时空独特的观看与表达方式。与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影像文本因其能更加精确客...
感悟在摄影中分为艺术感悟和生活感悟。就艺术感悟而言,感悟这一概念几乎可以构成一切审美创造的前提因素,不管是何类艺术活动都不能离开感悟。摄影家的感悟来源于他们的亲身经历与视觉感受,有的是渐渐的领悟,有的则是瞬间的开悟。正是他们不断的感悟,对...
结论摄影技术的诞生到当代数字化相机普及的发展过程中来看,摄影技术是在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进行的。从早期的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到数字化摄影技术的发展;从早期胶片的存储模式到今天储蓄卡的存储模式的转变,从早期镜头的不可替换到现在的多...
第四节产生COS摄影的当代环境背景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的,主文化是如此,亚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70或80年代的我国会出现Cosplay,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尚在为温饱而奔波,或是刚刚能够解决...
在中国,纪实摄影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1981年。当时《国际摄影》杂志编辑部要翻译美国时代生活文库的一篇文章,其中Documen-taryphotography一词,老翻译家王慧敏将初稿文献摄影改译为纪录摄影,后又与老编辑林少忠商定改为纪实摄影。但随着时间的演进,纪实这两个...
1、当代艺术的一大主题身份翻开艺术史我们不难看到各色各样的艺术家自画像。实际上,这种自我表达方式也催生了那个把艺术家浪漫化为特殊人群的广为流行的神话,想想凡高那些富有戏剧性的自画像便是如此。更接近我们时代的安迪沃霍尔在内的二战后的著名艺术家...
中文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文化方式,纪实摄影自西方传入中国以来的一百七十年间,始终影响和传达着中国人的现代性文化经验。可是相较于西方成熟的纪实摄影话语,中国纪实摄影在体系性话语建构方面却较为欠缺。论文主要论述纪实摄影于中国的发展流变,在...
由中宣部批准设立,中国记协主办的中国新闻奖,是检阅我国优秀新闻作品的年度最高奖项。它不仅是广大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专业荣誉的基本来源之一,也是国家认可和肯定的主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①笔者统计了第17届至第24届连续8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