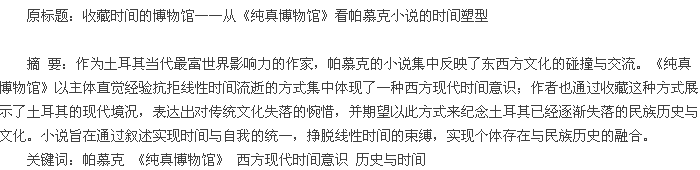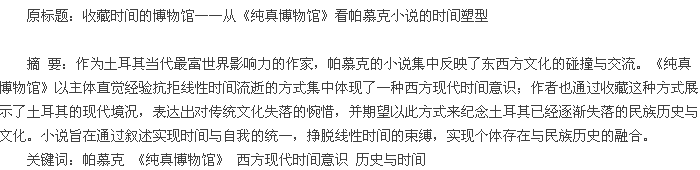
小说《纯真博物馆》是帕慕克近年来的一部力作。从表面上看,主人公这座为了纪念逝去的爱情而建立的博物馆承载了作者对一段刻骨铭心爱情的记忆,实质上这里面同样交缠着一座城市的过往,而这座城市的记忆中积淀的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过往。小说中,贵族青年凯末尔为了缅怀他和芙颂之间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将和这段爱情相关的物品收藏在一座名为“纯真”的博物馆中。小说共分 83 章,展示了即将开放的博物馆中的 83 件展品,每一件展品都与每一章所叙述的事件相对应。
作者将这些藏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芙颂消失之后凯末尔用来寻求安慰的东西,比如芙颂遗漏的一只耳坠,在两人幽会的公寓里芙颂曾经触碰过的东西;另一部分则是在漫长等待的七年十个月中所累积下来的从芙颂家偷窃来的物品,比如达到可观数字的带有芙颂手上味道的勺子,芙颂用过的手绢等。这两类属于和芙颂相关的藏品,也是纯真博物馆藏品的主要部分。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些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记忆相关的藏品,比如土耳其第一个果味汽水品牌梅尔泰姆在报上登的公告,和宰牲节场景相关的明信片和照片,这些物品展示了一个在东西方文明交杂之中既传统又现代的土耳其。纯真博物馆里收藏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一段爱情时光,还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对个体而言,“向死而生”的经验构成了时间经验,对一个民族而言,时间意味着民族记忆,也意味着对民族历史事件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不仅是对时间的刻写,同时也是对物理时间的超越,从叙事意义来看,这种对时间维度的超越意味着一种超越线性时间的永恒。“尽管时间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的,但在一个文化体中,对时间的刻写和描述总伴随着对超越时间维度的设置,此维度即是永恒。”
一
在小说《纯真博物馆》第 53 章“时间”中,帕慕克这样写道:“生活让我懂得,想起时间,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条把一个接一个时刻连在一起的直线,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把那些携带着时刻的物件连在一起的直线会让我们伤心,因为我们会想起直线那不可逃避的结局———死亡,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痛苦地认识到那条直线本身———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自己感觉到的那样———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然而很多被我们称为‘现在’的那些时刻……有时候能给予足够我们享用一个世纪的幸福。”“幸福对于我来说就是能够重温像这样的一个难忘时刻。”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把时间与运动、变化关联,将之定义为“时间乃是就先与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并且是连续的。”
这种线性的历史时间观认为时间是一个由过去、现在、未来组成的不可逆转、绵延不断的序列,在时间中产生的事物又在时间中消逝,对于个人,它是一个从生到死、有着开始和终结的过程,对于人类,它则以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为表征,个人的存在成为人类历史中一个个出现又消逝的点。如何摆脱线性时间流失的失落和无意义感,从而使我们得以找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秘密就在那一个个难忘的时刻中。这里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自在物,它是在人觉察到、意识到之后才生成的一个对象,与其说存在着客观的可以计量的时间,不如说存在着对事物变化的永恒意识。通过主体的自我体验,时间不再是与主体相割裂的客体,而成为和主体相连的共同存在。在收藏旧物的博物馆里,收藏的不仅仅只是一些回忆,还有和回忆相关的时间。深受柏格森心理时间影响的普鲁斯特认为主体对于过去的持留可以借助“自觉地记忆”和“不自觉地记忆”两种方式实现。“自觉地记忆”,是一种理智与眼睛的回忆,这种回忆所构造的过去仍然是一个个孤立的碎片,它在叙事过程中稍纵即逝,它仍然被禁锢在时间的线性链条之中,还不能为叙述者揭开遮蔽着从前生活的面纱;后者受某种味觉或嗅觉的感官刺激的启发而出场,并恢复过去仿佛身临其境的情态与有关经验,它是一种不为理性控制的知觉的回忆。普鲁斯特对此曾作过这样的阐释:“我们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领略到同样的感受,因此这些回忆便把这种感受从一切偶然性中释放出来,使我们看到其中超越现时的实质。”
二
对帕慕克而言,让过去进入现在的空间,让过去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中获得再生,这正是《纯真博物馆》中主人公想通过建立博物馆而达到的目的。在帕慕克的小说中,物品引发了普鲁斯特所说的“不自觉地记忆”,把凯末尔带回到他和恋人经历过的每一个时刻和每一个场所。为了不让这样的时刻和场所再度失去,完全沉入无意识,他便把使他“触景生情”的物品保留起来,收藏在一个博物馆里,而这正是普鲁斯特所说的“自觉地记忆”。和普鲁斯特不同,帕慕克将“自觉地记忆”看作“是一种理智的记忆,它传达过去的信息但不留踪迹;它所包含的是回想起来的事实,而不是经验的深度储存;它所生产的知识是可以重复的,并将自身强加于物品之上,使物品成为纪念品,进而发展成博物馆。”
从这个意义上说,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不自觉地记忆”与“自觉地记忆”结合的产物。在凯末尔身上,过去的持留常常通过“自觉地记忆”和“不自觉地记忆”共同的作用才得以实现,并且以这种方式将过去带入现在,也可能在未来留下痕迹,这些物品触动人的知觉反应,并进而沉入到过去的情境中,正是柏格森所说的时间的绵延。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玛德琳点心的味道在不经意间触动了普鲁斯特回忆的大门,往事如潮水般将过去带入现在。在《纯真博物馆》中,凯末尔和芙颂初次做爱时芙颂遗留下的一只耳坠,不经意间触动了凯末尔,使得他又一次回到了那个人生当中最为幸福的时刻。之后这只耳坠反复出现,它成为凯末尔缓解相思之苦的良药,两人再次相逢后它被芙颂秘密收藏,最后又伴随着芙颂的死亡再次出现。
这只耳坠见证了芙颂和凯末尔爱情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最终被收藏在纯真博物馆中成为两人爱情的纪念物。可以说,这只耳坠就如同玛德琳点心一样,在芙颂消失后它出现并触动了“不自觉地记忆”,将凯末尔带回到初次和芙颂相会的幸福时刻,这种记忆进而引发主人公有意识地借助它来挽留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个幸福时刻,这时不自觉地记忆转换成为自觉地记忆。这只耳坠具有了一种魔力,只要看见它,就能回到那个时刻,耳坠和那个时刻紧密相连,进而成为一体。起作用的不是耳坠,而是和耳坠相连的知觉和体验,“是居于其中与现在共同拥有的有关幸福的经验,是过去与现在的事物所拥有的共同特质,因此它也就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关于过去的幸福时光永恒地被再度唤回。”
在作家看来,纯真博物馆中收藏的是凯末尔和芙颂相爱过程中所有触动他“不自觉地记忆”并进而转化为“自觉地记忆”的物品,这些物品背后是一个个难忘的时刻,这些时刻组成了一段光阴,而只要博物馆存在,这段时间就不会消失,由此这段爱情摆脱了线性时间的束缚而成为和时间共存的永恒。
如果说纯真博物馆里收藏了凯末尔和芙颂的一段爱情时光,伊斯坦布尔如同凯末尔的另一个情人也同样被收藏在这座博物馆中。凯末尔和芙颂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相识、相恋、分离、相聚,最后天人永隔。伊斯坦布尔成为这段爱情故事精彩上演的舞台,然而它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小说中有大段对于伊斯坦布尔街景、建筑物,独特的送葬风俗的描述,将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内幕,底层生活的艰辛,甚至是不中不西的伊斯坦布尔的商业文化全都囊括在内。可以说,那些收藏在博物馆中用来纪念小说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物品,实际上展示的是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帕慕克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密切相关,伊斯坦布尔不仅只是那些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有时候也成为小说的主题。在作者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记忆之城》中,帕慕克通过自己的童年记忆展示了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商店、人群、物品、细小的日常生活琐事和给人以惊颤感的新奇事物,流露出一种世事变迁沧海桑田的忧郁感伤。而在《纯真博物馆》中,小说通过凯末尔的成人视角,以展示博物馆中物品的方式把“读者带入作者成年的记忆之中,而这两种记忆的刺激源却是相同的:即把记忆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物质与灵魂相交织的物品,它们本身都凝聚着都市经验的碎片”。
在这些物品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城市的社会现实,一个处在动荡、暴力、贫穷,和不同文化冲突当中的伊斯坦布尔。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以西化的生活方式表现自己的现代和文明,但又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不知所措: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生活方式,但在观念上仍然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小说中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茜贝尔,虽然冲破传统禁忌和凯末尔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但那也是在确定对方一定会娶自己为妻的情况下。当凯末尔移情别恋、取消婚约时,她也只能飘洋海外来掩饰自己婚前失去童贞的尴尬。下层社会的人则在贫穷的生存境遇中苦苦挣扎。在严格的等级划分下,家境贫寒的芙颂只能通过参加选美比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被凯末尔抛弃后,不得不仓促下嫁给贫寒的电影编剧费力顿,并且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通过和凯末尔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期望得到后者资助以实现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即使最终能够和凯末尔订婚,也逃脱不了遭遇车祸惨死的结局。在长达七年的凯末尔对芙颂家的夜晚拜访中,通过那些大大小小的阴暗的伊斯坦布尔的街道,芙颂家所在的那个贫困社区,一个和凯末尔平时生活的完全不同的伊斯坦布尔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一切的大环境则是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的土耳其政局。作者描绘了那些宵禁的夜晚凯末尔回家路上所见的景象,在芙颂家看电视时新闻里不断出现的暴力冲突的新闻,处在民族现代化进程当中的土耳其不断涌现的新鲜事物,第一个本土品牌的果味汽水,当红的广告模特,这些不伦不类的西方文化侵袭之下的变异物品,展示了一个处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之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不定的土耳其。和作者通过博物馆收藏爱情时光的努力背道而驰,现实中的伊斯坦布尔踯躅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所实行的“全盘西化”的民族现代化政策,一方面使得土耳其遗落了灿烂辉煌的奥斯曼帝国文化,另一方面也没有将其带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相反,多年以来土耳其一直为西方主流文化所排斥,一直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和新奥斯曼主义所倡导的通过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文化来质疑和抵抗民族现代化的宏大民族叙事一脉相承,帕慕克也期望通过对帝国伟大历史的回顾来为现代的土耳其争得在西方强势语境中的话语权。
三
在《纯真博物馆》中,西方时间意识特别是西方现代时间意识对于帕慕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帕慕克而言,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由西方文学的影响而来的,比如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作者也十分明确地谈到过这些作家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影响。西方现代时间意识中主体和时间之间的紧密联系,主体存在高于时间存在,时间建立在主体知觉体验的基础之上这些观点,成为作者期望以博物馆收藏物品来挽留时间,进而留住一个城市的过往,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基础。可以说,帕慕克的博物馆中的收藏就是本雅明所说的“真正的收藏”:“收藏者(包括儿童收藏者)并不是出于经济或名誉地位的动机而收藏,而出于对物品的一种感性,一种能够注意和聆听物的世界的能力,以及要把物品从使用价值中解放出来的愿望,也就是使物品摆脱生产—消费的商业循环,而回归它们的历史地位,同时赋予它们以‘现实’的意义”。
由此可见,帕慕克的博物馆收藏的不仅仅是一段时间,更是时间背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正如他自己在《博物馆和小说》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我希望论述的小说类似博物馆的性质,与其说可以激发想象,不如说更多的是保存记忆、保持传统和抗拒遗忘”,并且阅读小说的快乐和参观博物馆给人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这种快乐也许与我们在博物馆中所感受到的幻象和随之而来的自豪是相对应的:我们感到历史不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某些东西应该被保存下来。”
在小说中,对伊斯坦布尔的记忆以收藏逝去爱情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收藏带来一种满足感:“这是一种时间停止,一切将永不改变的情感。伴随着这种情感的是一种被保护、持久和在家的愉悦。另外还有一种关于世界是简单的和美好的信念,这种信念让我的心灵得以放松……这就是一种世界观。”正是这种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所带来的安全感,使得像凯末尔这样的土耳其人在纷繁动荡的世界中,在错综复杂的文化冲突中能够安稳生活,而这种世界观也是帕慕克的时间观。
通过小说的叙述实现时间与自我的统一,挣脱线性时间的束缚,实现个体存在与民族历史的融合,帕慕克以个人挽留爱情时光的努力来抗拒对民族历史的遗忘和失落。因此,如果说“纯真博物馆是人们与死者共存的一个地点”,那么,这个死者就不仅仅是凯末尔所要纪念的芙颂(死于车祸),而是帕慕克所要悼念的、将迅速被现代化所淹没的伊斯坦布尔城,以及这个城市所代表的土耳其。
参考文献:
[1]牛宏宝.时间意识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与西方比较的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2](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M].陈竹冰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法)马赛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随笔集[M].张小鲁 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
[5]尹星“.收藏式写作”:帕慕克《清白博物馆》中的都市现代性叙事[J].外国文学研究,2010,(4).
[6]谢雪梅.在知觉信念中重构的世界———《追忆似水年华》的时间艺术研究[J].外国文学评论,2006,(2).
[7](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M].彭发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