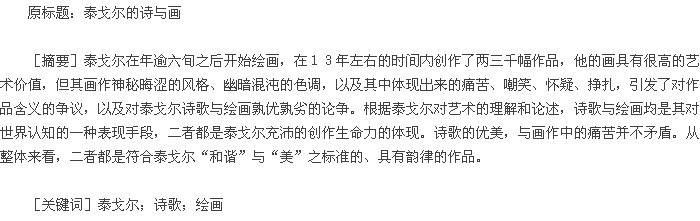
2010年5月,一场在德里举办的泰戈尔绘画作品展揭开了印度政府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的帷幕,时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辛格为展览致开幕词,随后其中的12幅作品在当年苏富比印度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出了1.5百万英镑的高价,比估价高出3倍。
2012年,另一场名为“最后的收获:泰戈尔画作”的画展在全球范围内巡回展出,展览地包括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Asian Art)、巴黎小皇宫博物馆(Petit Palais)、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首尔韩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Korea)、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吉隆坡国家视觉艺术美术馆(National VisualArts Gallery)等。这两场引起了轰动的展览,再次将泰戈尔的绘画带入了评论界的视野之中。以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家甚至哲学家身份而闻名于世的泰戈尔,其画作有何意义?泰戈尔始终宣称自己“仅仅是一位诗人”,那么他的画与他的诗又有何关系?
一
“最后的收获”:泰戈尔的绘画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泰戈尔开始尝试创作绘画作品的时间是1924年,即他63岁时。是年他在出访秘鲁的旅程中因病滞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得到了阿根廷才女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的悉心照拂。养病期间,泰戈尔创作了《吟唱集(Purabi)》(1925年)中的部分诗歌,在这部诗集的手稿中,出现了泰戈尔最初的画作。这些画是泰戈尔在修改诗句的过程中完成的。修改诗稿不可避免出现涂画和删改,而这些杂乱的涂改痕迹是泰戈尔所无法忍受的,于是他要将它们变成“具有韵律”的事物。维多利亚·奥坎波曾目睹了泰戈尔在手稿上作画的过程,“他用划痕来游戏,用笔将它们从一行诗连到另一行,画出线条,然后生命就忽然从这种游戏中跃了出来:出现了史前怪兽、鸟和面孔。”[1]泰戈尔自己如此描述他这个时期的创作:“当我手稿上的划痕像罪人为了得到救赎而哭泣,并以它们的凌乱丑陋痛击我的双眼,比起完成正当任务,我常常花费了更多时间去解救它们,将它们带入韵律这一仁慈的结局。”[2](P70)可见在开始进行绘画创作时,泰戈尔的创作冲动并不是针对绘画本身,而是出于一种对混乱状态的无法忍受。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绘画创作还类似一种涂鸦,那么经过4年的练习后,在1928年,泰戈尔开始了比较正式的绘画创作。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Krishna Kripalani)将这一年称为泰戈尔的“丰收之年”。自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泰戈尔频繁地周游世界,发表演讲、进行讲座。但在1928年,部分地因为身体欠佳的缘故,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印度休息疗养,这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和足够的精力去发展他的“新游戏”———绘画。“人生暮年的疲惫之尘土也随着精力的衰退而落身。我想给自己放个假,并需要一种消遣来充实我的假期,以免它被无聊地打发。就是通过我的工作间隙的空漏这条小道,画画和涂抹的热切渴望登场了。……这种行动不再是由外向内,而是由内至外。我像个孩子一样开始着迷于我的形式之玩具———涂绘或作画。”[2](P65)克里巴拉尼指出“从1928年以后,他不仅仅因为给他的手稿删改加上具有韵律的图案而画画,而是因为他喜爱。……幸运的是,他以前没有接受任何训练也没有作为画家的声誉之虞,所以他可以毫无禁忌、毫不做作地绘画”[3](P339)。如前所说,泰戈尔在进行绘画之初并不是有意为之,他往往是在诗歌写作的间隙进行绘画创作,绘画工具基本上就是写作用的钢笔或铅笔,作画用的纸张也多是就地取材,虽然之后泰戈尔开始逐渐使用更多的色彩来进行创作,作画方式也从涂鸦发展为素描并演化为较为正式的绘画,但这些习惯却基本上被保留了下来,因此泰戈尔的绘画创作往往下笔很快,一气呵成。
从1928年直至1941年逝世,泰戈尔一直保持着对绘画的热情。在13年 的 时 间 里,他 创 作 了 几 千 幅 作 品,其 中1580幅现存于国际大学泰戈尔博物馆内。如果考虑到他同时还出版了数部诗集、小说以及散文,这个数量对于一位耄耋之年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创作量。但泰戈尔随时、随地、随手、就地取材的绘画习惯,给完整地保存他的所有绘画作品增加了困难,这是其画作数量难以确切统计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目前他的部分现存作品上或没有署名,或没有创作时间,或两者皆无。
虽然泰戈尔开始画画的时间很晚,但绘画为他赢得的声誉却来得不晚。1930年他就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125幅作品。随后,他的画展在伯明翰、伦敦、柏林、慕尼黑、莫斯科、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相继举行,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巴黎的艺术评论家认为这些作品“成功完成了他们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在德国它们受到了超乎泰戈尔期望的非常热烈的欢迎,“其中5幅已经在柏林国家艺术馆获得了永久席位,还有其他中心邀请约展”,[4](P328)在莫斯科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艺术家生命的极好展示”、具有“高度的技巧”。[5](P928-929)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以上各展览地当时在意识形态上并不一致甚至有些是尖锐对立的,但泰戈尔的绘画却在各地引起了同样的强烈反响。泰戈尔在1930年8月写给罗森斯坦的信中提到这种情形“与《吉檀迦利》出版后那段时间有奇怪的相似———它突然而喧嚣,就像阵 雨 过 后 的 山 溪,像 洪 水 会 偶 发 也 会 同 样 突 然 消失”[4](P328-329)。以泰戈尔谦逊的个性,他对罗森斯坦的描述不应当是夸张之辞,画展所引发的反应与《吉檀迦利》问世后的情形相似,这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泰戈尔的绘画所具有的艺术价值。
在2012年“最后的丰收:泰戈尔绘画”画展上,泰戈尔的作品被按主题分成了四组:第一组包括他最早的一些作品,画面构图或为几何形或呈藤蔓状,在形态上具有无视现实的创造设计。第二组作品中的风景画和花卉画,体现出他对自然的一种更富沉思和更细致入微的观察。第三组作品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人物姿势及其所具有的戏剧性和叙说性这一点上。第四组作品主要是人像,它们来源于泰戈尔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理解,是观察与心理探索的产物。[1]如果按照创作阶段来分的话,笔者以为泰戈尔的绘画可以分为早期的尝试期作品和后来的成熟期画作,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分界应该是在1928年之后。第一阶段的作品基本是黑白两色,创作方法以较为简单的线条连接和色块涂抹为主;在逐渐成熟之后的时期,泰戈尔的绘画作品开始出现多色彩,最初是黑白加蓝色、红色,后来更多的色彩被他使用,这一时期的创作方法也更多样,最初的线条连接基本上被舍弃,尤其后期,出现了很多具有戏剧感的人像彩画,其中尤其以女性画像居多,此外他还为自己创作了一系列自画像。
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泰戈尔最初的画作仅仅是一些在诗行间穿插的具有优美形态的曲线,继而这些优美的曲线开始演变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其后期的创作仍保留了一部分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但这些图案不再仅仅是线条,而是一种绘画,而他创作的人像,则具有一种介于写实和表现之间的意味。
二
诗与画:相悖或相向?泰戈尔画作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绘画作品神秘晦涩的风格、幽暗混沌的色调,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痛苦、嘲笑、怀疑、挣扎,与泰戈尔长期以来冷静肃穆的诗哲形象相去甚远,因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评论界由此对泰戈尔画作的精神内涵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1930年,就在他的画展在巴黎举行之后,当时法国着名的女诗人诺阿耶伯爵夫人(Anna,Comtesse Mathieu de No-ailles,1876-1933?)就发表评论,称不明白 “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泰戈尔为什么突然让他心中的怀疑、讽刺、失望全都恢复了自由,并称希望能再见那位曾经的天使。类似的评论认为泰戈尔的画反映了暴力、冲突和对稀奇古怪事物的一种偏爱,“冷酷”或者“像梦游病患者的杰作”。[6](P213)在当时的印度,对其绘画的批评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潮,这应当是导致泰戈尔画展迟至1932年才第一次在印度国内举行的部分原因。对于这一点,泰戈尔似有先见之明,他曾说过:
“我相信,我的同胞们会以批判的眼光来观看这些画的。在我看来,将这些画儿藏起来,避开世人窥探的目光,可能会更安全些。”[7](P23)而克里拉巴尼在他1962年创作的传记中还认为“……但是当他画画时,更像是梦游者在行走,虽然看不见但却步伐稳健,被一种力量所驱使,而力量的方向却不受他控制。那些怪诞的、奇异的、痛苦的、讽刺的,所有那些他在自己的写作中小心翼翼地避免的东西都从他的画作中向外窥探。”[3](P340)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泰戈尔的画中充满了力量,这是他之前的散文和诗歌中所没有的,在他的画中“一切都是从光线到光线。整个氛围都是关于力量和力量的欢乐。……画家罗宾超越了诗人罗宾,画家不仅仅是诗人的翻译者或诠释者。”[8](P76-77)还有一些对泰戈尔画作赞誉有加的评论则认为,这些画表明,泰戈尔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终于挣脱原来束缚他的旧枷锁,他的画是其内在自我摆脱超我限制的表现[9](P67),持这种评价的多是欧洲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近年来,有不少印度艺术批评家对泰戈尔的画作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他的绘画所继承的并非是孟加拉或印度传统的遗产(曾任泰戈尔学院院长的希那拉扬·雷Sibnarayan Ray语 ),它们更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游历世界的过程中所接触的西方“原始艺术”和人类学的理念,因此在泰戈尔的画作中同时存在现代主义与“原始艺术”的回响(着名艺术批评家S·希瓦·古马尔S.Siva Kumar语),但是我们认为泰戈尔的诗歌和绘画是互补的,两者都分享了泰戈尔天赋 中 的 某 些 共 同 品 质 (S.K.南 迪S.K.Nandi教授语)。
泰戈尔的诗歌与绘画在艺术理念和精神内涵上究竟是背道而驰还是相向而行,也许从泰戈尔自己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到更明确的答案。
首先,我们来看泰戈尔如何看待他自己的绘画。
1929年2月,也即泰戈尔开始正式绘画创作后不久,他在给罗森斯坦的信中写道:“如果有机会我很想给你看一些我自己完成的画作,我希望它们能让你再次惊讶和欣赏,就像《吉檀迦利》那样。”[4](P325)将自己的绘画作品与带给他巨大声誉的《吉檀迦利》相提并论,可见泰戈尔对他的画作有着较高的自我评价和期待,因此,虽然他也承认它们具有某种“心理学的意义”,但如果完全将其看作是心理或情绪的“发泄”显然是不合适的。当被问及为何在年过60之后开始作画,泰戈尔曾一再提及,是绘画艺术“突然”造访了他。他无法忍受没有规律、没有秩序、毫无美感的手稿页面,因此不自觉地提笔开始将这些混乱的划痕纳入具有韵律的图案之中,并由此开始迷上了绘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使泰戈尔开始了这种“不自觉”的创作?
其次,泰戈尔从未对自己的画作命名,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要给他的绘画命名“是不可能的,理由是我在作画时从来没有一个预先想好的主题”,如果有人一定要让他命名的话,他建议那些看他的画或买他的画的人,自己为这些作品“举行命名礼”,“我的工作是作画,给画命名就留给其他人做吧。”[7](P25)而对于那些询问他的画作的含义的人,他的回应则是“线条和颜色没有声音……它们安静地伸出手指指向画作自身:‘看,自己看,不要问。’”[2](P69)他还用玫瑰来作比,“我们满意于玫瑰就是玫瑰,这就是说它在它自身之内包含了一种关于其部分与环境的完美的和谐,……生物学有助于在普遍规律上了解作为花朵的玫瑰,但是那与玫瑰自身无关,艺 术 家 的 创 作 之 道 也 与 此 相 似,就 像 那 朵 玫 瑰 一样。”[10](P273)不命名、不阐释,让作品说话,泰戈尔的这种态度似乎更能说明他的画作并不是没有含义的,但这种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最后,泰戈尔经常将自己的诗歌与绘画并论并作比较,1928年11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说道:“我已经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线条环绕着布下的咒语之中。诗歌女神已经永久地离开这些地方,她气恼于我对这未知事物(inconnu)的偏爱———尽管我已过了鲁莽的年纪。我几乎已经全忘了我以前是惯于写诗的。似乎是艺术中那不可预料的因素让我深深着迷。诗歌的创作题材可以追溯到头脑中某些模糊的想法。一旦它离开湿婆乱糟糟的王冠,诗之溪流就沿着它精确的路线流淌———被两岸牢牢限定。然而我绘画的过程与此完全相反。首先,出现条线的提示,然后线条成为一种形态。
这种形态越明晰,我构想的图画就越清晰。”[2](P63)1941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写给比素·穆克巴塔耶(Bisu Muk-hopadhyay)的信中,他再次将他的诗歌与绘画相提并论:“过去50年,我一直在耕耘语言艺术。因此可以说,我基本上掌握了语言的技巧以及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是这让我突然着迷的绘画艺术,我对它并不熟悉。它四溢的魅力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我想我掌握了原动力或内在规律的秘密,能沿着某一渠道推动这种无拘无束的力量。……绘画的艺术就像一位害羞的情人一样躲避我,并沿着一条我所不知道的隐幽道路行进。她的路线如此隐秘以至于我忆起了‘吠陀’里说的:Ko Vedah。没人知道———也许甚至造物主也不知道。也许我们不会在其他的圣典里遇到这样一种怀疑的声音———甚至竟敢宣称造物主自己也不完全了解他自己的创造物。这正是创造物自己的潮水沿着它自身的流向承载着自己。”[2](P69)泰戈尔的这些表达,似乎很有抑诗而扬画的意味,那么,究竟他的诗歌是不是比不上他的绘画?如果真的绘画优于诗歌,那么是在哪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呢?
三
艺术与美:诗画同根生虽然泰戈尔开始创作绘画作品的时间是在1924年以后,但我们在1905年《渡口集》的手稿上就可以发现他早期的涂鸦痕迹。事实上,泰戈尔对于绘画的热情应该说从他年幼时就已经产生,这种热情与他对诗歌的热情一样,是终其一生都存在的。他在1874年即十二三岁时,曾短暂地跟随三哥海门德罗纳特·泰戈尔学习过绘画,此后他断断续续偶尔作画,为妻子、儿媳和朋友画过素描像,还画过黑天与罗陀像。
1893年在写给侄女英迪拉·黛维的信中,他坦承:“我并不十分清楚我真正的禀性是什么或该是什么。……如果要我不害怕、不羞愧地坦白,我也可能告诉你,我就像一个受过挫的恋人,总是热切地望向美术女神。”[3](P339)据梅兰芳回忆,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还向他提到“美术是文化艺术的重要一环……我一向爱好绘画,但不能画,有几次我在诗稿上涂 抹 修 改,无 意 中 发 现 颇 有 画 意,打 算 由 此 入 手 学画。”[11](P213)由此可见,虽然泰戈尔是从1928年之后才正式开始有意识地绘画,但绘画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一位不速之客,毋宁说,绘画是一直潜藏在他艺术生命中的一种能量与冲动,它在泰戈尔年逾六旬之后出现,是经过长久酝酿的有备而来。回顾泰戈尔的诗歌生涯,早在1884年,他就出版了一部名为《画与歌》诗集,他在回忆这部诗集时写道:“我在用自己心灵的想象所绘制的图画里获得了一种欢娱和情趣。
在那里没有其他念头,只有描绘一幅幅生动的图画的愿望,这是用肉眼观察心灵的东西和用心灵观察肉眼所见的东西的愿望。假如我能用画笔绘画,就会力图用线条和色彩在画布上描绘出自己那颗不安的心的意愿和创造,但我不掌握那个艺术手段,只有诗歌的韵律和字句听从我的使唤。”[12](P243)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部诗集可被看作是不精通绘画、没有画笔的诗人用诗歌之笔所做的“图画”。虽然诗歌与绘画的创作技法、创作方式不同,但二者在泰戈尔的创作中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而只是不同的手段。当泰戈尔更精通或更乐于使用其中一种时,他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表达。
泰戈尔是一位充满了创作冲动的人,诗歌、音乐、绘画都是他充沛创作力的产物。对于他而言,创作可谓是一种本能需求,只要生命还在继续,创作就不会停下,而有所变化的,只是创作强度、创作方式和创作手段。英文版《吉檀迦利》的诞生开始于1912年他由于健康原因在谢利达庄园修养期间,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创作冲动但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创作新的诗歌,因此转而开始将以往的一些诗歌翻译成英语,并在这个过程中再一次体会到了重新创作的快乐。这样的描述与上文提到的泰戈尔开始作画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1912年因病开始翻译所诞生的是引起轰动的《吉檀迦利》,以及之后的各种英译诗集;1924年因病开始绘画游戏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称呼———画家泰戈尔。因此,诗歌与绘画,都是来源于泰戈尔的创作天性,绘画是他晚年之后艺术生命的再次焕发。他在莫斯科见到青少年学生时,曾对他们笑言自己虽然年迈,但心却和他们一样年轻。俄罗斯艺术批评家访问他时称“在你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青春的精神,……青春的精神在寻求合适的表达方式时毫无障碍,你的画作已经创造了它们自己的技巧”[5](P929),泰戈尔则对此予以了默认。诗歌与绘画两种方式,在泰戈尔以艺术方式追寻生命之神的过程中,是并行不悖的。而在泰戈尔的理想中,这两种方式在艺术中应该能实现“相通”,他在《什么艺术》中指出,“在诗中我们只能使用具有正味的词———这些词不仅能说明什么,而且要能幻化成图画,发为乐声。而图与歌不仅仅是事实———它们是有人格的事实。它们不但是它们自身,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它们蔑视分析,它们能够直接进入我们的心灵。”[13](P160)在《艺术家》中他再次强调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运用这些不同的方式,把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感知表现出来。“艺术是人的具有创造性的灵魂对‘实在’的呼唤的回答”[14](P329),“在绘画、造型和文学等艺术部门中,客体和我们对它的感觉,犹如玫瑰和它的馥郁气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4](P330)我们都知道泰戈尔是“为艺术而艺术”者,他对艺术的最高追求是“美”。那么,泰戈尔画作中的阴暗、讽刺、痛苦又如何是美的?泰戈尔认为,“善”是“美”的,而这种“善”并不是社会道德伦理的善,不是具有实用的善,泰戈尔的善是“与整个世界有着十分深刻的和谐的关系,与整个人类的心灵深深结合在一起”[13](P76)的,可以看作是对世界的真实理解。那么何谓真实的理解?真实的理解必然不是肤浅的理解,也不是片面的理解,泰戈尔曾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在观察事物时,绝不只是囿于细枝末节的真实,也不致力于一笔一画地描摹和再现具体的事物,真正的艺术家是从整体观察事物,并表现事物。因此,对于丑陋的事物,他在《美》中指出我们认识世界时“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些矛盾、不和谐甚至变形的丑的东西。当我们再从整体上观察时,就会发现局部的不和谐与丑已被整体上的和谐与美所掩盖”[13](P146)。和谐与美,是由具有韵律的事物表现出来的。泰戈尔在谈及他的诗歌时,曾多次强调“韵律”的重要性,这种韵律是语言的韵律,他因其对诗歌韵律的高度控制而被称为“韵律大师”,泰戈尔称自己基本掌握了语言的技巧,也是针对这一点而言。在谈及自己的绘画时,1930年他在《我的绘画》一文中将自己的画作称为“我线条形式的诗,如果它们凑巧被赋予了求取认可的权力,那一定主要是因为其形式具有韵律的意义,这是最根本的,而不是因为对思想的任何阐释或对事实的再现”[2](P70)。
可见,在实现诗歌与绘画的和谐之美时,韵律都是泰戈尔所依靠的手段与衡量标准。而在实现韵律的过程中,泰戈尔从来都是不惮于尝试且乐此不疲的。在诗歌方面,他不但尝试了将孟加拉语韵律诗译为英文散文诗,还在后期直接创作了孟加拉语散文诗;在绘画方面,他则尝试了将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方法与他长期以来对印度艺术的理解、对外部世界的融合在一起,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呈现出来。正如在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诗篇中,死亡与生命并不相互矛盾,在泰戈尔的画作中,丑陋、痛苦与美和宁静也并不相互排斥。
在70岁诞辰时,泰戈尔发表了题为《一位诗人的自白》的讲话,他坦承:“我投入到了各种活动之中,结果就是本质的‘我’散成了碎片。……我现在意识到对于世界来说我只有一种自我介绍———那就是我仅仅是一个诗人。在多种活动、在不同时候、展现给不同人群的我的人格,并没有表达作为一个整体的我。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熟知经典;我既不是老师也不是人类领导者。…… 我们艺术家和诗人是光明(abih)的使者,这种光明沉醉于创造世界的天真的欢乐之中。……意识到这个‘多样的一’在我心灵深处的游戏并将它表达出来———这是我的任务。”[10](P276)这或许是泰戈尔诗歌与绘画关系的最好注脚。
[参考文献]
[1]“The Last Harvest:Pain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EB/OL].[2]Rabindranath Tagore.My Pictures[M].Kolkata:VivaBooks Private Limited,2005.
[3]Krishna Kripalani.Rabindranath Tagore:A Biography[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edited,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ary M.Lago.Im-perfect Encounter:Letters of William Rothenstein and Rabin-dranath Tagore 1911-1941[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72.
[5]edited by Sisir Kumar Das,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Volume Three):A Miscellany[M],NewDelhi:Sahitya Akademi,2006(Reprinted).
[6] [印]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M].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7] 董友忱.[印]阿弥陀弗.诗人之画———泰戈尔画作欣赏[M].上海:中西书局,2011.
《樱桃园》写于1902--1903年,讲述了出身于俄罗斯传统贵族家庭的柳苞芙、加耶夫兄妹因为大笔债务而不得不拍卖祖传的樱桃园的故事...
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1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尤以北美新移民文学为重。在众多的新移民作家中,李彦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大胆以英文创作进军加拿大主流文坛,并以中文译写的方式重返中国,演绎着从边缘走向中心...
伊什梅尔里德(IshmaelReed,1938-)是美国后现代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黑人作家之一,也是备受争议的作家之一①。小说《春季日语教程》(Japa-nesebySpring,1993)自出版以来,作品中的种族主义,反讽艺术,人物形象,戏仿特征以及文化多元主题等问题引...
语言和图像一直是人类认识和展现世界的两种方式,对于两者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尤其是对于分属两者的艺术形式---文学和绘画。在西方对此问题进行过细致而深入的探讨首推莱辛的《拉奥孔》。莱辛在《拉奥孔》中对诗画之间的界限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被米歇尔称为...
戏剧性独白经常出现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英美文学作家的主要表现形式。戏剧性独白有其独特的特点,通常以诗歌的形式出现。...
《雾都孤儿》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在19世纪出版的长篇小说,该书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孤儿奥立弗悲惨的身世及遭遇。作者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当时伦敦残酷的社会问题。...
幽默是一种文化、是一门艺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看似寻常、无所不在,却又抽象、难以用精确的语言给出最恰当的定义。林语堂先生曾这样解释幽默,幽默是一种能激发起人类心理某种情感的智慧,某种在对逻辑性进行适当调控后对现实进行某种形式的加...
文章以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例,对视听语言中包含的景别、角度、运动、照明、色彩、镜头、人声、音响、音乐等元素进行探究,让观众更好地去体会作品,去理解菲茨杰拉德要传达的时代故事。...
摘要2013年,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自此,世界范围的门罗研究越来越多。艾丽丝门罗在其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专注于短篇小说创作。她的小说书写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思索个人的成长、婚恋、老年晚景等,探索生命的无奈苍凉。其...
一、作品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1.工业革命18世纪50年代,隆隆的机器声预示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革命使英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使英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然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人对自然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