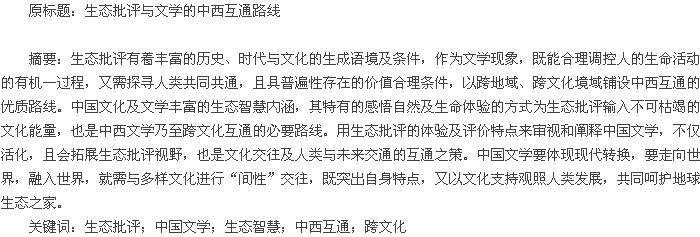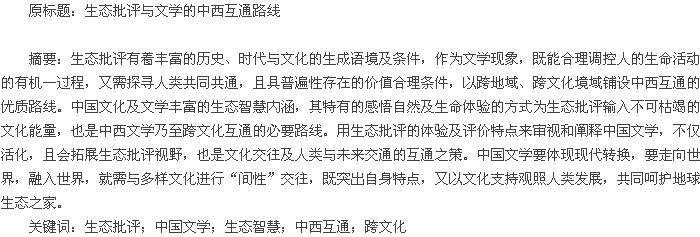
生态批评产生于欧美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基于问题意识而展开,但作为文学现象,其所指涉的“问题”并非局部,亦非限于某个地域及国家,而是人类整体的,是历史的、文化的,更关涉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问题。生态批评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的生成语境及条件,而且其最为基础性条件是人作为生命有机性存在,是如何调控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机—过程。生命的有机—过程显示了生命的实在,这是人与万物的“天然”之合,是“神遇”,是“无迹之化”,用清人石涛之言,这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人要亘古延续、永存,既无法逃离这种“神遇”之迹,更不可背弃生命的“实在”。生态批评的文学表达,将这种生命的实在给予历史、时代及文化的拓展:既凸显文学自身魅力,又融括人类活动的多向领域;既要超越性地汲取人类发展过程的一切有益的历史文化滋养,又要探寻人类共同共通,且具普遍存在的价值合理条件,选取跨地域、跨文化的互通路线。中国文化及文学中特有的感悟自然及生命体验的方式,不仅内存丰富的生态智慧元素,是生态批评必须汲取的文化能量,而且也是考察中西文学乃至文化互通的必经路线。
一、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天然”的神合
生态批评的构建机制,学科视野,理论思维的方法,情感表达方式,审美体验程度,对生态、生命及生存问题的特别关注,与中国文学都有着一种“天然”的神合性。我们细致鉴析这种“神合”之迹,把控何以能够“相互反映”及有机对接,也意在在当代条件下生发出新的意义及价值。相互支持与“神合”。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对自然及生命存在有着先天的崇尚与膜拜,那种对“道生”性,对“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诉求;对天地归位,万物化生、化育及“法自然”的生命有机—过程的体认:对“大化”、“生化”、“大美”境界的寻求都包蕴着深层次的生态智慧。中国人对生命存在特有的感悟及体验方式,为文学与审美奠定了自然、生命体验的基础,不仅为其输入了基本的方法及思维品性,而且铺设了人们特有的情意体验及诗化生存的表达路线。
这使得中国文学中满含着生态及深层次的生命感悟的元素,尤其是这一系列的生态智慧精华在诗论、词话、画论及书论中给予体验性实践,显然也已贯通着朴素的生态批评的理论品质及思维方略。事实上,在工业文明及现代性反思条件下产生的带有科学性视野的生态批评尽管产生于“西方”,但与中国文化之“东方”化的满含深生态智慧的艺术与审美传统既有着同归之途,又可以相互反映和参照。借用萨义德《东方学》中的话说:“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
中国文学满含的生态智慧是先在的、丰富的,其现代意义及价值仍然是巨大的,并且有着极大的挖掘潜力及再生能力。“报偿生命”与“神合”。共同印记生命有机—过程的辙履,并且作为共同祈望,就成为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的“神合”铺垫了现实基础。从生态视野审视这种基础条件会给予我们一种对生命的全新体验,这不仅是人作为生命活动体的基础要旨,也是人必须生态永续存在的体验策略;不仅是生态主义的践行领域,也是生态批评基于文学体验的拓展线路;不仅是对中西文学精义传播、延伸、再造的重要路径,也是共同繁复人类文化及精神魅力的一种“报偿”。
英国学者巴克斯特言:“生态主义赞赏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因而也是精神的,有报偿的生命。”生态批评作为生态主义的延伸及体验策略,同样是通过对这种关系进行理论的拷问及对“有报偿的生命”的体悟。“有报偿的生命”尽管需要关注地球生态中每一个个体生命,但作为一种观念的体认,更强调地球生命系统的整体,是万物的生命有机、过程在整体与系统的“神合”,或者说,只有这种整体性地“报偿”与“神合”,才能使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沿着有机—过程的路途亘古延续。生态主义不仅需要这种广阔视域,而且生态批评也必然在超越时空限定的条件下,在对未来世界发展的状况设置中确立共同的学术视野,既需多种学科共续承接,又要超越时空界限,而必然使多路人马对接,弱化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理想信仰、价值取向、民族习性、思维品性、生活方式的差异与歧见,在全球视野中趋向一致,体现全球人类对自身生存整体及地球家园的共同关注。
“道”性自然与“神合”。体认“道”性自然关键之处是识道、观道、品道、体道,乃至韵道。这可以有几重路向:一是体认作为自然、生态、生命本源存在的自然之“道”;一是把控老子所言的“道生”及“道法”性的自然,并且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生态智慧滋养,而补给且沉淀着民族精华;一是延续历史及文化含义的精髓及精义,使之在现代条件下大放光彩,并且在现代价值生发上浓墨重彩;一是在跨文化阐释中,跨越时空限定,不仅在中国文化土壤之外的一切地域中观览其对自然、生态、生命及人的活动的共同作用,而且在其中再生及丰厚本应有的内蕴。这多个层面不仅内存“道”的有机—过程性,而且会在文学视界中通过展示多向度的“神合”,既显化生命的实在,又推及人类整体的永续存在。由“道”到文学,尽管是一个延伸性序列,但却呈现了精神转换的必然,其“神合”必然是海纳百川,而原因就在于这必须指涉人作为生命有机性及生态永续存在必然。不管人的未来路途如何行走,对人的任何活动方式及交往方式所内存的“道”性“神合”不是去改变,而必须是丰厚、完备,并有机调节,且再生新价值。西方学者也能深谙“道”的玄机,如云,道“是一种有创造性的、活生生的存在,它和感性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道在它的本质上被理解成是在现象世界中可被感知的,并且在其中表达着自己”。“在中国,道家思想家们一开始就面对着一种属于古老精神文化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这种观念是由对世界细致的思考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具有非常明显的伦理性的特征”。海德格尔对老庄思想那种比较深刻的体味实际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为自己在中国出版的系列着作写了一个题为《东方与西方的交融》的总序,其中谈到,他曾经引用老子的“谷神”,以表现他对“道”的那种“吸纳百川”精神的体验与理解,他认同东方的“道”及统一的阴阳原则。莫兰感到,他自己的思想方式与中国传统所固有的,深刻的思想方式处于共鸣之中。在研究“复杂性原则”时,莫兰还认为,复杂性方法中两重性逻辑原则与回归环路原则,都可以在中国找到以其他词语所做的同样的表述。他还称自己总是自然地感到与中国的注重联系、变化和转化的思想相沟通。他特别强调了,正是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这种统一性中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精神的财富。
由文学而赋魅的“神合”情结。文学与生态的联姻原因会有多样,但究其根本,则因于相互共同及共通之处,即一方面共同表达人的活动整体性及有机性,另一方面,以自然与生命作为共同与共通的阐释基础。自然是生态的实在,生态是自然的肌理;自然是文学基础,文学是自然升华。当然,人的任何的活动方式都无法别离自然与生态,但文学与其相比,则是更加全面、整体地表达,更富有情意体验地使之全方位显现,其“神合”更会彰显自然、生态及生命的无尽魅力。文学不仅赋魅了这种“神合”情境,而且也在跨地域、跨文化的交融阐释中使“神合”魅力无穷。
文学赋魅自然是一个永久性话语及其表达,文学将自然之魅无尽地表达与美化,这不仅是人的情意体认,更在于自然本身的魅力无穷。人的魅力全得自于自然之魅,而自然之魅就在于其生态有机性及过程。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活动方式被认同、体验、表达及放大,对自然的观照是其主要策略。特别是那种崇尚描述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及肉身与精神体验的“自然写作”,其文本解读往往将爱默生的“自然情结”,将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中人与自然的天然“神合”及“神交”方法视为范本,视为经典。
尽管古已有之的文学经典文本中,并非皆畅扬自然,有的还在极尽张扬人的活动无限性及对自然的征服性,但生态批评也会通过对自然的共通与共同的交往之“神合”情境,不仅挖掘自然的之魅,而且通过评价及反思人的活动,以阐发人与自然的无法别离性。
我们用生态批评的体验及评价特点来审视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学,观照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特有情意,这不仅会丰富生态批评活动,而且也是人类文化交往及与未来交通的互通之策,由此,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经由文学而在自然面前,在生态体验的情境中实现对接,进行“神交”。
二、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互通的多重路线
文学艺术体验的发生,是环绕对自然的感悟及生命的体验而展开的,且将“自然”作为必然的连接点,这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审美活动中都有似曾同一的感悟方式。中国文学不仅对自然之“道”性有至深悟解,且对自然之美亦有特殊关爱及情意体验之法,或者说,自然审美构筑了中国艺术审美的历史及家族相似性,这就使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互通有着多向度、多层面必然性。
系统整体性的互通性。古代中国人以系统整体性宇宙观为基础,通过对人的生命存在,对自然的特有感悟方式,展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中国文学与审美尽管有着体悟自然、表达自然的独特情境,但并未脱离社会存在,而往往是缠绕在“入世”与“出世”的关系分野中,不仅表现人们整体的社会关注及责任意识,将自然与人的情意、人生、德性品质的铺设紧密相连,并且往往设置一种环境,将人的活动和情意放在与多种自然物的共生之境中。如春不仅是一种自然演化的节气,更似触发着情意及激越着的态有机体。言春者自古以来无以计数,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春同样是一种每每写之、诵之,且充蕴无尽情意的生态肌体。春既是季节,更是有机、过程的实在,是“生”之运演节律的生态显现。尽管古代中国人并非懂得“生态”何谓,但他们将春与多样自然物象有机合成,将自我的情意、人生与生命体悟在春和自然物象的生态有机性中融入,却已经极富生态意蕴。生态批评建立的生态学思维路向本身是系统整体的,同时自诞生那天起,它对人与自然生态有机关系的体认,就不仅仅是文学自体性的存在,它的后现代指向,它的批判性、颠覆性本身就表现了它的社会存在意识及社会属性,其蕴涵的深层次文化意义,内存着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及历史的趋向。
生存关注的共同问题。深究问题,往往使文学活动更具有色彩感,更突出其对自然、对生命、对人生的特殊关爱。中国文学中的问题意识最经典的表现往往是面对重大社会、国家及人生出现问题,仁者君子、贤哲雅士、文人墨客们便产生了对自然、对人生的特定关注,由此而生成对自然之美的至深悟解。
他们会呼唤自然,向生命呐喊,或者是向道、禅中寻求精神的慰藉,进而在自然体悟中,在文学审美体验中进行宣泄,以沉淀情感,积聚生命的能量。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云:“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此 诗 书 写 “山 中”“松 下”的 清 静 悟“道”,这既是王维人生境遇不畅而产生的一种问题性回盼,也是融入山野之境而清静顿悟,且与万物、“野老”交相融合,表征对困顿人生的超越。王维的另一首诗《归辋川作》云:“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
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菱蔓弱难定,杨花轻易飞。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这里的田园之意、之趣与“惆怅”的心灵境况,实际也是对社会、人生之途的拷问。生态批评所针对的问题意识往往不是个体的,而是社会的,是历史的、文化的,且是全球性的,是人类发展而产生的过程性问题,同时也涉及由工业文明而带来的人们具体的生存境况、消费观念及发展观问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关注与重新审视恰是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如果真正从这重领域里为人类提供生存的方略,提供感受生命,亲近自然的策略,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对自然、生命,对美的爱,继而汇聚为对人生之爱。
爱默生曾经畅言人与自然那种永久无法隔离的至深情谊,因为大自然是无私的,只要我们能够真诚地面对自然,呵护自然,各种自然生物对人来说也将是无私的。他说:“当心灵向所有的自然物体敞开之后,它们给人的印象却是息息相关、彼此沟通的。大自然从不表现出贫乏单一的面貌。最聪明的人也不可能穷尽它的秘密,或者由于寻找出它所有的完美而丧失自己的好奇心。”
“大自然满足了人类的一个崇高需求,即爱美之心。”诗意体验与共有寻求。言诗意体验,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也不仅在于中国文学总是溶解在诗与画的创造中,而是因为中国的艺术与审美历程本身就是一种诗意呈现,是诗意的生命演历过程。古代人通过构筑人的诗意体验方式,引领人们深层次地体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其中的自然话语、生命话语、美的话语,乃至生态话语、“生生”节律,都转换为诗性话语及诗意表达,且依据生命活动运演逻辑及韵律感来呈现。生态批评同样是力主构造一种生态诗学,威廉姆·鲁克特最早界定生态批评时,就设其为“生态诗学”。
当然,鲁克特这种界定主要是出于对生态性这门科学在文学实践,在阅读及教学运用而表现的,还不同于我们所言生态、生命有机节律及在人生、生命活动中而呈现的诗意状态。事实上,生态批评以诗意性的生命体验方式,找寻人类所应有的“诗意地栖居”之地,使诗意的存在家园“显魅”,这实际已经表现了强烈的生存关注,是一种诗意性生存策略。
话语构建语境的相通点。生态、自然、关系性、系统整体性、生存论、生命体验,共生共荣,以及“生生”韵律、“天人合一”、“天人共存”、可持续性、诗意性等形成的话语系统,适用于生态批评的整体结构。
其中一个核心构建机制,这就是知“生命”。中国文学中对生命的体验及其话语系统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表意性、有机性及生态性,且具知识性,有许多的概念与命题在西方批评话语中也可以使用。我们仍就“道”而言,作为一个核心范畴,“道”不仅是本体与生命的原初观照,而且也是上述系列话语表述及整体构建的一个凸显标志。“道”不仅为其内在肌理,而这一切又积聚并集合为“道”;对“道”的不同解读及体验,不仅是古代人的常理,而且亦会生发现代的阐释。“道”的原初性、聚合性、内在性及统领性,在知识论及阐释方面的真实性,其不可拆解性,使其有独特的表达线路,继而体现一种超越语言的特性。叶维廉就说:“宇宙现象整体运作的演化生成超乎人智与语言,道家早就悟到。与其把‘知’的可能放在人智,一步步远离真实世界,与其用概念对万物之为万物、对其自然生发衍变质疑,反不如对这些质疑的行为本身质疑。因为人为的假定不可以成为宇宙的必然,实在是不辨而明的;所有意图以抽象的意念或圈定、范定的方式去类分天机都是徒然的,都是限制、减缩、歪曲、片面不全的,都是不可靠的假象。”
从这种意义上看,道家对世界、对生命、对人生、对伦理,拟或是对“天机”的体验性把控及悟解,可以充蕴西方分析、抽象性及思辨性解释原则。这就是说,“道”并非是不可阐释的,不可分解的,而是在阐释、分解中是否把握其内里及真义,是否给予自然、生态及生命以体验性阐释,而非仅仅限于话语及概念、范畴及体系性的分解,也非只是对之进行条分缕析。
三、生态批评与跨文化互通的超越性
我们之所以要从跨文化境域观照生态批评与文学的中西互通,一方面是基于生态与文学的有机联合,而表现出一种多样性文化的互为阐释及“间性”交往,另一方面,则为跨越时空文化交融的历史必然性。生态批评欲产生更加广泛的全球影响,并惠及人类整体及未来,需要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学中获得滋养。中国文学亦要体现现代转换,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与多样文化进行“间性”交往,既突出自身特点,又以文化支持观照人类发展,而生态批评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则为其铺设了优质的互通路线。
生态批评与跨文化原则。未来世界的发展更基于文化的发展,同样未来世界的交往更基于文化的交往,未来世界体系的构建,实际是文化体系的构建。发展、交往及体系构建中的文化构成必然体现多样性,且体系是多重价值功能的聚合,并且能够呈现文化间性的特性。加拿大学者D.保罗·谢弗在《文化引导未来》中称文化是“未来的钥匙”。谢弗说,创建文化体系的“关键在于使文化和各种文化形态成为全球活动和人类事业的中心,辅以必要的安全和预防措施,这将能使人类根据文化的最高、最聪明和最能容忍的原则而不是最基本和最粗略的实践来创建世界体系。这些原则包括:寻求平等、公正和真理;爱美好的东西、知识和智慧;对稳定、秩序和多样性的需求;合作、关心和共享的重要性;承认别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寻求完美……要想为制定一个更平等和有效的体制奠定基础的文化潜力得以实现,那么人类、大自然、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之间将必须更加和谐地相处。这种相处应基于与自然的统一,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都兼具了这种体系构建的基本条件及跨文化原则,并得以彰显平等、公正、友好的文化潜力,通过文学活动的延伸,而呈现对自然与人之间生态有机关系的调控。跨文化往往是不同文化间的审视、阐释及交往,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之所以对跨文化现象也具有超越性,原因在于其交往及间性基础是基于人类整体对自然、生态及生命演化的态度,关注的是人类整体及家园共生性存在,因而并非是基于泛文化状态。两者皆从文学活动特性及各自的文化特点进行延伸,从生态与文学之所以能够合作且联姻的特性中延伸。这就成为一种人类个体及整体生命的永续性展示,且具未来性视野,其所建立的并非仅仅是一种世界秩序,更是人类与自然生态有机关联,是地球共同体的有机演化的必然抉择。
生态批评与“文化间性”问题。“文化间性”首先认同不同文化间的关系,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的“文化间性”表达,并非仅限于不同文化间的关系,还显示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既涉及文化影响、渗透及兼收并蓄问题,更要关注如何能够在这种文化交往中使人类得以生态美好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美好不仅以生态有机及诗意性家园存在为基础,而且必然关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化的生存条件,且都能呈现生态有机性。法国跨文化研究学者米歇尔·苏盖和马丁·维拉汝斯在《他者的智慧》一书中这样谈到:“各种文化都是深深地依赖于文化渗透现象或跨文化现象,文化间的互为影响甚至可以达到‘文化杂交’或‘诸说混合’的程度(不同地理文化或宗教元素被整合进同一类立场态度之中)。“意识到不同世界间对话与互动的必要性并意识到其现实性,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现象,一种能使‘共同生活’更为美好、减少冲突、甚至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实现从文化到跨文化的一个心理过渡。”
事实上,生态批评与文学的中西互通也呈现文化间的交往与对接,这既是现实与必然,也是一种艺术调节和发展。苏盖和维拉汝斯在阐释文化间关系时也明确,“文化间”一词,涉及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现实,也可以看做一门艺术。跨文化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唯一的事实,就是文化间性,亦即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的关系。自然、生态与生命的本根性是生态批评与文学中西互通及文化间性构建的基础条件,而之所以相互间能够渗透、跨越,原因在于其各种不同的文化特性。其中既有自然地理及环境条件的决定性,又有其经济文化生成的条件,同时又据此成就了不同的文学、审美及生命体验特性,并呈现文化多样性、语言表达及学理阐释特性。从文化间性层面把控生态批评与文学的中西互通,既需认同其融通、交往性,更需彰显其超越性,这一切又不应过度拘泥于各种文化特性及标准。苏盖和维拉汝斯也指出:“一旦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方式、自己的习惯来理解世界,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试图使这个世界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方式、我们的习惯,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这既要坚守个性、特殊性的文化样态,又要超越自我禁锢,定势及习性的缠绕,一切寻求共通性,同建共同的目的性及价值。
生态批评与文化阐释。美国着名汉学家,达慕思大学的艾兰教授认为,当代西方学者之所以要研究古代中国,其简单原因在于:中国不是欧洲。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没有传承关系,两者地位完全平等,中华文明则有更强的连续性。她在每每赏析中国文明构成的器物、文本时,都会被它们的美所感动。艾兰深情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无论古今中西之人在时间、空间和文化语境上多么迥异,但我们都享有共同的人性。艾兰有多部着作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在《水之德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一书中,她从“水”的自然性状及中国早期文字的性状入手,揭示古代中国人对水的认识,并确定其本体性特点,由此而延伸至对“道”与“德”的丰富内容以及富含自然实体及现象之状的阐释。由“水”至“道”,其特性是因于共同的动势及流溪之状。故艾兰指出,哲学意义上作为自然规律的“道”,是基于水之流溪的本喻,而“水”的特性之一就是循道而行。
她这样说:“‘道’的概念,作为一条溪流,作为一条指导人们行为道路的方向原则,由此,‘道’的概念被拓展延伸,蕴涵了这样一个条件状态,每一事物都应因循自然规律而动。”艾兰还进一步明确,《老子》和《庄子》中的“道”的功能构造不仅源于这种溪流及水道,而且其特性都是源之于水自身。尽管艾兰并非出自于生态批评的视域阐释中国文化,但却在把握“生态”存在根本现象,其对“道”的阐释不仅把握其本喻及本根特性,而“水”与“道”的流动之状也明晰了生命运动的节律状态,凸显了有机性及生态关联的本根性。作为西方学者,艾兰的阐释以更加明晰、确证、逻辑及辩证的方式,不仅有效及合理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与哲学、文学及审美的概念和范畴的基本特性,而且还能够至深体验性且标识其隐喻及本喻。艾兰指出,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水是最具创造活力的隐喻。在阐释“万物”时,艾兰指出:“‘道’是一种创造生命的力量,生成万物,但它是以水赋予生命的方式而不是上帝创造的方式创造万物。……万物的自我更生是生命序列的一个环节,生物依次开花,生育,并由此走向消亡。”
显然,这又是一个溪流及生命流动序列的隐喻及其表征。生态批评与诗性阐释策略。就生态批评作为评价及学理活动本身而言,西方学者还少有对于中国文化及文学现象进行生态阐释例证,但从文学的中西互通及跨文化视阈的阐释却不乏精到者。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对中国诗学阐释有着独到之处,但他的阐释理路,其概念、范畴、逻辑推演及系统的构建显然是西方化的。比如在《自然景观的解读》一文中,他用西方的景观话语替代自然,并分析了诸多诗篇。事实上,景观与自然看似皆出自于自然生态的本有之状,但景观更具人本性及构造性,同时作为西方话语的惯用词语,有时指代自然、环境,当其替代了自然而进行诗学阐释,以其阐释中国古代诗歌时,显然会将诗性体验的自然而然之状,将其万物一体的有机结合进行分解。因而宇文所安使用了“建筑结构的自然景观”的说法来阐释诗篇,并指出这种现象在中古时期的秩序中可以被清楚明晰地表述出来。在宇文所安那里,“大自然被表现为具有建筑性结构的、刻意构造而成的、清晰明澈的,每一部分都融会入一个整体之中。对于在大自然中找到结构完整性的强烈需要,本身已经包含了它截然相反的立场。在这一相反的立场中,自然不过是众多细节的大杂烩和拼盘,或缺乏内在统一性的秩序,或暗含一种隐秘而晦涩难懂的秩序。面对着具有建筑结构的自然,人的主体意识可以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整体;而当置身与支离破碎的大自然之中,主体意识则迷失了方向,沉湎于局部的细节当中”。建筑结构性显然是一种结构性的组合体,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排斥诗歌创造中的这种自然物象的组合,但根本点在于它是合成的情意滋润及有机性,还是物象堆砌,或者是“碎片化”再现。当然,依循古代中国人体验方式,或许难以解析这种建筑性,但西方话语解析及其体验却会成就这种建筑性。而这种建筑性的诗性体验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解构,以其回复“支离破碎的大自然”,而是满足“在大自然中找到结构完整性的强烈需求”,显然,可以看到这种诗性阐释方式的可行性及必要性。中国文化及文学体验中,这种有机系统性、完整性是一种亘古的追寻,尽管其中也不乏物象堆砌、情意与物象分离的表达,但却总是会在情感、德性及人生路途的寻求中建造有机整体,使自然物象、主体情感、德性品质等融汇,并会伴以“道”性及生命、情感之动,以表达其“真意”,而在诗性的解析及阐释中,往往也会以这种物、事、情的动势展开。
叶维廉在《中国古典诗的传释活动》一文就说:“中国古典诗的传释活动,很多时候,不是由我,通过说明性的策略,去分解、串连、剖析原是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不是通过说明性的指标,引领及控制读者的观、感活动,而是设法保持诗人接触物象、事象时未加概念前物象、事象与现在的实际状况,使读者能够在诗人隐退的情况下,重新‘印认’诗人初识这些物象、事象的戏剧过程。”物、事、情的动势体验及合成作为中国诗学的阐释要义,其中合成的也是多样性的物象及人相的生态组合,既有自然物及生态原发态,有“隐退”诗人继发态,有接受“传释”者的合成态,这种多态的生态有机合成,恰复合接受美学的自由性。叶维廉又说:“中国古典诗里,利用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法语法,使读者获致一种自由观、感、解读的空间,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
生态批评在跨文化阐释方面蕴积的超越性,不仅指涉自然生态及生命体验的方式,同时还呈现语言及话语构成的超越。超越并非剥离,这首先是立足文化多样性、原有的生态根脉及环境特性的清晰梳理,对由此而生成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习性、德性品质、人格样态及价值构成等智慧内涵,在兼收“他者的智慧”中丰富自身,体现“间性”交往及交流。这既是生态本有的,又是生态及生命体验的;既是话语构成的,又是超越知识论的;既是历史与现代的,更是未来的。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
[2]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M].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25.
[3]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M].常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爱默生.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5]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9-10.
[7]米歇尔·苏盖,马丁·维拉汝斯.他者的智慧[M].刘娟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艾兰.水之德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M].张海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9]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M].陈引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