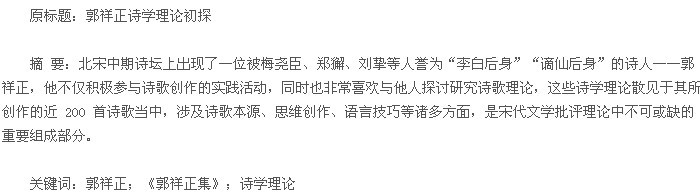
北宋中期诗坛上出现了一位被梅尧臣、郑獬、刘挚等人誉为“李白后身”“谪仙后身”的诗人——郭祥正(1035―1113 年)。祥正字功父、功甫,号谢公山人、醉吟居士、漳南浪士,太平州当涂人(今属安徽),少有诗名,皇祐年间中进士,曾任星子主簿(今属江西),后知武冈(今属湖南),签书保信军判官,又通判汀州(今属福建)、游历漳州(今属福建),为官颇有善政,后知端州(今属广东),归隐家乡青山而卒。他一生五次出仕,五次归隐,足迹遍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留下诗文作品 1400 余篇。其创作以及后世流传作品数量之多,就整个宋代来说是比较少见的。郭祥正不仅积极参与诗歌创作的实践活动,同时也非常喜欢与他人探讨研究诗歌理论,对自己在诗学领域的心得体会十分自信,自言:“子善评文我不如,我亦谈诗子许深”;“南风一送轻舟去,更与何人细论诗”;“论诗慰白头”。这些诗学理论是诗人毕生创作实践的总结,散见于近 200 首诗歌当中,占他留存创作总量的近 1/7,值得深入研究。
这些理论涉及诗歌本源、思维创作、语言技巧等诸多内容,是宋代文学批评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所收录之《郭祥正诗话》,共 13 则,张福勋《“我亦谈诗子许深”——郭祥正诗论发微》中提到郭祥正诗论 83 则,刘中文认为《宋诗话全编》所辑不全,又增补诗话 26则。除去 3 人重复所见之处,前人所辑郭之诗论共89 则。笔者认为,郭祥正文艺理论,特别是诗论远远不止于此,前人尚有遗漏之处。笔者根据孔凡礼《郭祥正集》以及四库全书本《青山集》《青山续集》重新整理,又补辑诗论 98 则。笔者拟对这些诗学理论加以整理分析,以期对郭祥正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一、诗之本源与创作思维
诗人出身的郭祥正重视文学创作,赞同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之观点,指出文学是千古之大事,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祢衡应先著述科”,“唯有文章道德能日新”,“文章千古重,富贵一毫轻”,“人亡国变今几年,唯有文章记崷崒”。他将文章地位提高到与国家、道德等同的地位,认为文章能够超越时空而存在。当济世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便发出“有才不得施,著书贻后世”的感慨,这显然是对儒家经典《左传》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由此不难发现,郭祥正的诗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儒家诗论基础之上。
(一) 诗之本源与评价标准
先秦时代儒家倡导的“诗言志”和魏晋时期陆机提出的“诗缘情”构成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两大体系。传统儒家诗学理论中“诗言志”即《尚书·尧典》中所言:“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汉代儒家学者认为此“志”应当是“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世情,如治世之情、乱世之情、亡国之情等。总之,诗歌要“言志”,要体现与政治教化、人生意义相关的内容。“诗缘情”来自于陆机《文赋》中提到的“诗缘情而绮靡”,源头可追溯到《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人心感物而动,付诸诗歌借以表达情感,也就是钟嵘在《诗品·序》里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言志说与缘情说引起历代评论家的争论,直至当代,才有学者指出二者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郭祥正根据个人创作实践活动指出两种观点可以并行不悖,共存于诗学体系,共存的前提是他将“诗言志”之“志”与“诗缘情”之“情”通过创作者这个中介联系在一起,“情”属于“志”的范围。
首先,郭祥正认为,诗歌“其词有同有不同,亦各言其志也。必有读者能得之”,诗歌因“言志”而生,或者也可以说诗歌的功能在于“言志”。具体之“志”含义是多重的,儒家诗论强调的“天下之志”是其中一种,这一点郭祥正虽然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提出,但是却通过具体的创作实践予以表达。他说诗歌的社会功能在于“直笔正褒贬”,因此诗歌要能够反映民生疾苦,关注社会现实,诗人要为民鼓呼。他热情歌颂儒家理想社会,重视诗歌教化作用:“愿令里巷歌《召南》,风化流行成乐土”;他为孝子作诗扬名:“谁为孝子传,吾诗信无伪”;他崇敬杜甫、白居易忧国忧民的精神,很多诗歌反映了他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注,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和愤恨,体现出儒家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他同情人民在自然灾害之后得不到官府的救济,反而被逼缴纳赋税;他指责身为民之“父母官”却全然不顾人民生命的行为:“高村既无麦,低田又无谷。民间已乏食,租税仍未足。县令欲逃责,催科峻鞭扑”,发出“世无采诗官,悲歌寄鸿鹄”的哀鸣;他揭露社会政治的腐败:“政宽法不举,将懦边无威”,指出政令不严,法令不行,武将懦弱,军事失利,国威何存?他痛恨朝廷不能知人善任,导致将帅无能,内乱难平,杀害百姓,冒领军功,“刺史亟闭户,神理默垂佑。城头无百兵,坐待五羊救”,“权帅计仓卒,遣将速诛蹂。贪功恣杀戮,原野民血溜。婴儿与妇女,屠割仅遗脰”。这些无疑是对“诗言志”说的有力支持。支持赞同诗歌要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现实生活、仁民爱物为职能的同时,郭祥正并不反对诗歌可以表达个人情感。在他看来,既然诗歌可以“各言其志”,那么诗歌既可以表达天下之志,同时也能宣泄个人情志。
他在《泛江》一诗序言中说到此诗是由于“感慨其怀,而为之辞云”,“起予思之无穷兮,既局影以自慰,又苦辞以招魂”。心中苦闷难以排遣之时,他常常会“欲吐哀音写心曲”“悲歌写哀弦”,消解内心之忧愁;在心情欢快的时候,同样可以“朗咏佳兴发”“题诗写高兴”;他认为诗歌还能感怀抒情:“遇胜寄幽怀,览古兴绝唱”“觞酌每追随,啸咏舒悰襟”“览古发遐想,缘情还独哦”。
诗歌的功能在于抒写情志,那么是否只要是抒情写志的诗都是好诗呢?郭祥正进一步提出诗歌的评价标准,认为诗歌应当有所兴寄,要中正平和,不能伤之太过,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只有“思无邪”的诗歌才是优秀作品:“李翰林杜工部,格新句老无今古。我驱弱力谩继之,发词寄兴良辛苦”;“明时不作《离骚经》,与君高咏思无邪”;“况攻李杜吟,字字无淫声”。李白和杜甫是郭祥正心中的典范,他们的诗歌格调新颖,句法老成,他尽力去学习,然而总觉得力弱而无法追赶,因为“发词寄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郭祥正认为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歌是真正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评价标准的好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他也认为屈原作《离骚》,虽也是抒发个人心中之郁结和忠君爱国之理想,但是却怨愤过度,违背了中正平和的原则,不能视为优秀作品。
郭祥正认为好诗的创作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创作者要自觉地向前贤、他人学习。他认为模拟李白、杜甫等人的创作,与友人论诗谈诗都是在向他人学习。此外还要向书本学习,即用心揣摩儒家经典文章:“五言雅重参二典”,“琳琅谐八音,雅重参二典”,只有这样,创作出的诗文才能雅正庄重。
二是要具有创作能力。郭祥正认为,创作者首先要有“心”,由内心而发,“笔下琳琅写心素”,接着作者之“心”因外物感发而“思”,产生“诗思”,只有通过“诗思”将客观存在的物象转化为诗歌中的意象,才能传情达意。
(二) 思维与创作:言不尽意与言外之意
通过欣赏他人诗作并结合个人创作体验,郭祥正注意到诗歌语言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距离。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意识到语言与意义之间存在不对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即使在同一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与所要表达的意义也不能形成完全对应,创作者很难使用准确的语言在作品中传达个人的真正意图。这可能并非创作者自身使用语言能力的不足,而是作为工具的语言自身所蕴含着的遮蔽性造成的。郭祥正常常感叹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词不足以尽寄兮托余思于江流”,“诗辞搜亦苦,物状竟难肖。终篇写亭壁,翻惭画师妙”。
郭祥正还发现,由于诗歌语言具有较大的张力和包容性,在有限的语言词汇里往往包含无限的内容和意义,因此对诗歌的理解接受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语言上,诗歌中蕴藏的“味”才是诗之精华所在。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富于想象、情感、理想和自由的文学样式,不同于小说、戏剧、散文,它没有足够的语言空间来展现创作者的意图,它对语言的要求最为苛刻。诗的语言是高度艺术化、审美化的语言,通过比兴、象征、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而形成诗歌所特有的诗性语言:含蓄、隽永、蕴藉、朦胧。郭祥正认为优秀的诗歌往往具有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对诗歌的欣赏需深观其意,而后去意尚味,抛弃语言桎梏,体会其中之味。他认为即使如图画,也只能描摹现时片刻场景,体现现下暂时之像,而场景之外的作者之“意”与“味”便无法展现了,然而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却恰恰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二、诗歌语言艺术
郭祥正十分重视诗歌语言,他指出诗歌的语言应该豪迈奇峭,气势浩荡,同时也要精雅里现出自然,平淡中现出真醇。从音韵方面看,诗歌语言要注意音调的和谐,因此语言的选择必须是谨慎的。
(一) 豪迈奇峭,气势浩荡
郭祥正不仅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好用气势宏大的意象,如大鲸、巨浪、险山、雷电、长虹、宝剑等,在品鉴诗歌时,同样好用此类意象来传达个人对诗歌语言风格雄壮浩大气势的推崇。和古代许多文艺批评家一样,郭祥正喜用形象化的语言或意象来评论诗歌,常用三类意象来表达对诗歌语言豪迈壮阔、气势浩荡的赞赏。
第一类是直接使用“椽笔”“大笔”“鸿笔”“健笔”“巨笔”“大轴”“大句”“雄词”“雄文”“大字”“劲笔”等带有宏大、壮阔意义的语词来称赏他人诗歌之豪迈大气,例如:独携椽笔发清唱,老鹤昻藏映鸡鹜。手携大笔恣吟览,老句气焰摩星躔。长碑突兀压巨鳌,字刻雄文入模楷……谁曽磨崖记名姓,习之健笔深镌镵。其中“椽笔”一词使用最多,在《郭祥正集》中出现 10 处。“椽笔”即“大笔如椽”,语出《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
此后,“大笔如椽”便逐渐成为大手笔的代称,郭祥正精简为“椽笔”,用来形容诗歌气势如虹、大开大合的豪壮。不难看出,“大笔”“鸿笔”“巨笔”“健笔”“雄词”“雄文”等词汇均是由“椽笔”改造而来,其意义与“椽笔”相同。
第二类是用自然意象,通过直觉感悟式的通感描写,将诗歌语言比作奔流而下的浪涛,惊天动地的雷电,高耸入云的险峰,漫天飞舞的龙蛇等,用视觉、听觉、感觉的冲击性来比附诗歌高昂激越的气势和诗人喷薄而出的才情,例如:
词源奔激吼波涛。
词源感激泻江海。
崩腾还与海涛深。
落笔成千言,霹雳震白昼。
胸中策画烂星斗,笔写纸上虬龙奔。
滚滚而来的惊涛骇浪奔腾不息,气势壮美,声震天地;振聋发聩的轰轰巨雷,刺人眼目的耀光闪电,给人以视觉、听觉、心理上的巨大震撼;想象中遨游天空的蛟龙大蛇之雄姿刺激着人们的感官。郭祥正以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想象,将豪壮奇崛之风格形象化、具体化了。
第三类是以战论诗,即用武器、兵马、战阵、战争等森严的气象和恢宏的场面来比拟诗歌的豪迈壮阔。以李白后身自诩的郭祥正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努力模仿偶像,在心理性格上同样尝试着向李白学习。他喜欢李白潇洒不羁的个性,喜爱李白豪迈奔放的诗歌,然而在“宋王朝重文轻武的背景下,当沙场立功的愿望被科举出仕的现实利益所压抑之后,诗坛立奇勋便成为书生无法实现的英雄梦想的心理补偿”。郭祥正沙场建功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于是只能从诗歌里找到些许安慰,他想象中战争的宏大场面便成了诗歌豪迈壮阔风格的最佳语言表达之一,例如:
又如窥沙漠,铁骑万余匹。
又如崆峒兵,百千森甲铠。
洪河喷作三门流,突骑长驱五千匹。
留郎更赋多情曲,直欲豪华将杜坛。
论归学海方无迹,吟到诗坛始有功。
一望无际的瀚海大漠,鏦金戛玉的战鼓金锣,寒光凛冽的矛戈剑戟,长驱直下的铁骑雄兵,训练有素的马队战阵,运筹帷幄的将帅,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展现出一种昂扬向上、壮阔奔放的气魄。
此外,“诗坛”“杜坛”等词汇显然是“将坛”的仿词,郭祥正将在诗歌领域中独领风骚比喻成军队出征登坛拜将,作为诗歌竞赛中获胜的一方。郭祥正把诗歌创作看作沙场征战,惊心动魄,充满了惊险。
对如何实现诗歌语言风格之豪壮奇崛,郭祥正指出,可以用“险”字、“险”韵来追求奇崛之效果,达到动人心魄的目的:“能来同我游,险绝共长啸”,“能诗又敏速,往往造险语”,“险句卷起谷帘水”,“高吟成章又奇绝,睥睨韩杜君何谦”,强调以险峭的语言追求雄浑壮阔的气势。
(二) 清逸自然,雅致精妙
郭祥正认为,诗歌语言除了豪壮之外,还离不开“清逸”和“天然”,他多次在诗歌中提到一个“清”字:
属笔成篇兮,发天机之锦绣。
视笔添清逸。
清吟佳句新。
句泻碧潭月,篇成清夜秋。
“清吟”“清音”“清逸”之“清”非语言所能形容,诗人只能用清秋夜月、碧潭月影、冷月青光、漱齿寒冰等清寒冷洌之物象来传释。这种“清”是一种静默平淡中现出的宁静和飘逸,是如此难以言说。
因此他以为,“清逸”之诗,其音、其韵都得自于“天”,因而是妙不可言的,非人间丝篁音乐所能比拟:
卓然风格出天造,冰盘洗露银蟾秋。
又如李白才清新,无数篇章思不群。
文章贵天成,追琢饥鼠窃。
“天然”之诗是“天”之所赐,是“天”之所造,是发于“天籁”之音,非人力可穿凿模拟,更非靡靡之音:“谢公秀句发天籁。”
既是天籁之言,那必然与世俗之音格格不入,首先便要脱去一个“俗”字,“千言不落一字俗”。
郭祥正认为诗歌的语言可以“丽”,但“丽”的同时还须做到极物尽象,“联吟极物象”。他认为有些诗“词则丽矣,然未能尽碧落之状”,不能穷形尽相描绘事物,因此不能称为好诗,好诗应该“更读琳琅篇,叙事何其周”,语言不仅要精美,更需极尽描摹物态之能事。他认为有的诗人过分注重语言的雕琢,违背天然之道,这些都与“清”的要求不符。真正优美的诗歌语言之“丽”是一种浑然天成的“清丽”,其声应该如同珠玉般清越,其味应该如芝兰般馥郁:桓桓翠琰文,愈读愈精妙。
经罢哦五言,珠玑沧海头笔洒二韵铿琼琚。
优秀的诗歌语言应是于平淡中见出真醇,雅致精丽里透出清逸,发自内心,自然流泻而出,不露人工雕琢之痕。在“清逸”与“天然”基础之上,通过指摘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弊病,批评时人失去正确的审美判断,郭祥正进一步指出诗歌语言应当是“清逸”与“天然”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梅尧臣式的“平淡”,这才是诗歌语言风格之至境。什么是梅尧臣的“平淡”,郭祥正并未正面做出解说,只能从当时名家评论以及梅尧臣的个人创作来了解。梅氏的“平淡”并非淡到无味,而是一种“以深远闲淡为意”,“清切”如“石齿漱寒濑”的风格,是经历种种之后重归自然宁静的平淡,而这种风格恰恰来自于郭祥正最为欣赏的李白、杜甫、韩愈三人。
在郭祥正看来,诗歌应当是豪迈奇崛与清新雅致并重,“独携椽笔发清唱”,形成一种清雅俊逸的风格:
词气有余,顿挫铿锵。矫垂天之翼,粲琼瑶之章。
俊逸自追天马健,崩腾还与海涛深。
公余缀吟笔,烂漫排珠玑。又如崆峒兵,百千森甲铠。
郭祥正将自己的诗歌语言主张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写下许多雄壮与清逸风格并重的诗篇,如《金山行》诗中既有“卷帘夜阁挂北斗,大鲸驾浪吹长空”的雄豪壮美,也有“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的雅致清淡;庐山脚下“秋空漠漠秋气浅,碧天蘸水如刀箭”的眼前清冷秋色与想象李白骑鲸“倒回玉鞭击鲸尾,锦袍溅雪洪涛里”的惊心画面和谐融合,诸如此类的诗句不胜枚举。他极为欣赏大小谢、鲍照、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等人的诗风,认为他们的诗歌既有豪迈壮阔的气势,也不乏清逸雅致的出尘之格调。他认为,只有多向前人优秀作品学习,才能写出富有生命力的诗歌。
郭祥正身体力行向前人学习,不仅对前代和当代优秀诗人大加赞扬,同时也努力模仿他人创作,尤其以模仿李白为最。
综上所述,郭祥正的文学理论,主要是诗学理论,包含本体论、实践论两个部分。其中对诗歌作用的认知,受到当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并接受了儒家传统诗教观中的经世致用思想,重视诗歌教化、言志的社会功能,提倡诗歌内容要反映社会现实,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这与他本人所接受的儒家道德教化以及所处社会密切相关。他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国家政治的革新运动反映到思想领域中就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和强化。
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心中充满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关注社会、人生,因此其文学主张也染上了浓厚的儒家色彩。作为诗人,郭祥正并未忽视诗歌作为文学作品应有的审美抒情作用,他对“情”之内涵的扩大解说将“言志”与“缘情”两种对立的文学观联通起来,是对宋代诗学批评的一个重大贡献。郭祥正要求诗歌语言豪迈雄浑与雅致清淡并重,其中清逸淡泊的一面显然是宋初诗人所提倡的“禅悦之平淡清远”诗风的继承和发展,而豪壮险峭则是变革时期诗人积极参与国事、济世热情迸发的结果。两者的最终结合则是诗人在现实中屡受挫折、遭受打击之后重新归于冷静思考的结果,是一种“处于困境而又力图奋发的理智要求,它往往与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不满连在一起,虽然豪迈,却不痛快淋漓,而是隐含着穷愁困顿,进而衍变为奇奥峭拔,奸穷怪变。而且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和熙宁变法的难以进行,作家的政治热情开始减退,一时的激励豪迈之后,归于平淡自然”。郭祥正的诗学主张是个人生平经历、创作经验和社会文学思潮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既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也深深刻上了时代的印记。
参考文献:
[1] 孔凡礼,校点.郭祥正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5.
[2]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詹福瑞.“诗缘情”辨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4]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周裕锴.以战喻诗:略论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J].文学遗产,2012(3).
[8]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中国的西方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按时序有关西方的学说大概被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上古时期内外关系基本之形式之形成。第二,秦汉帝国时期神圣方位的东移。第三,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天观点之诞生及神圣方位复归于西的进程。第...
郭绍虞先生在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撰文,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多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现状:较多注意汉民族的理论而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这种情况,近年来已有所改变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但是,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还需要有人...
一、引言。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盛行,给经典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经典在不断的平面化、娱乐化和商业化过程中,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崇高的审美价值以及高尚的人文关怀等价值被不断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经典文学陷入了尴尬的生存境地。然而,大众文...
一、文学史如何可能?谈论文学理论的历史,还是要从文学的历史说起。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专门谈,但我想在这里提示一个大意。学界都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这个说法受一种三分的逻辑所支配:历史=个别;哲...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用抒情、唯美、自然的笔触,创作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小说,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用平静优美的感悟式的散文化语言表达了他对评论对象的品味。从他的《沫沫集》等一系列批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着名领袖,第二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着名的宣传鼓动家和组织家。李卜克内西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和革命家庭影响下长大的,他的成长也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切关怀和教导,...
每个人都有他理解的局限性,用自我的方式来理解和表述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所谓的意义都完全基于不同的理解。在文学和文艺评论中,有谁能说他对于文本的解读是彻底正确的?每一位评论家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诠释文本,建立自己的理论。...
2琳达哈琴的后现代戏仿理论产生的背景2.1琳达哈琴之前的戏仿理论概述戏仿是哈琴在后现代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作为古老修辞学范畴之一的戏仿,从古至今,无论是戏仿的表现形式和内涵,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流变,也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深入探讨和研究。但...
南帆新著《文学理论十讲》系统阐发了文学的意义和文学理论的使命, 建构了理解与阐释文学问题的坐标体系, 以关系主义为方法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感性论, 多角度、多层面地回答了文学以何种特殊的方式重新介入社会历史。...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域中,文艺影响力有着多种形态,即情感的、审美的和理论的三种基本的形态。一方面,由情感到审美再到理论,其形态越来越精炼。另一方面,从文艺影响力形态的整体性来说,三种形态又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