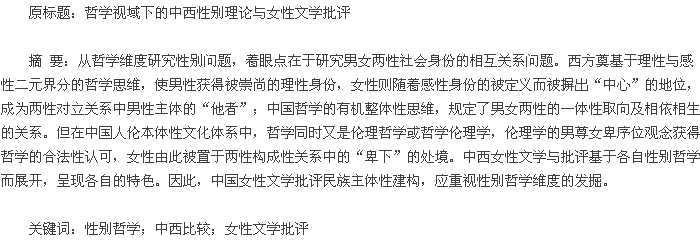
从哲学维度研究性别问题,着眼点在于研究男女两性身份历史生成与现实存在的相互关系问题。“女性”乃至“女性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域,成为一个肯定的命题,就在于它们是这种关系的呈现。生态学意义上说,男女两性作为人类的共同存在,应该是在差异中互补、相依相融、互为表里的和谐存在,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应该是一种“诗意”的存在。然而,历史没有提供这种“诗意”,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文化越来越表现出“自恋”倾向,“女性”在这种“自恋”中出离了本应和谐相处的两性共同体,成为被男性“第一性”文化设定的“第二性”。20 世纪到来,西方女性意识到了这种文化“阴谋”,她们“揭竿而起”,为自己的性别“起义”“,女性”作为一个政治命题、一个文化命题,在对“男性”政治与男性文化进行抵抗的过程中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在历史上将女性铸造为“第二性”的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构型中,哲学的世界观与认识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哲学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方关于两性相互关系的不同认知,这一认知的实践效应便是中西女性在由两性相互关系构成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活动中存在着不同的生存情形,反映于文学领域,也便形成中西不同的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形态。
一、中西性别哲学特质
西方哲学常采用“二元论”认识方式认识世界,即将世界看成精神与物质两个本源,并认为这两个本源各自独立,性质不同,互不联系。“二元论”是将整体加以割裂、分立的思维方法。用这种思维方法去认识世界,便将人从世界中分离出来,将人作为主体,世界作为客体加以认识;或者,在作为主体的人之外去寻找世界的精神本源。用此去认识事物包括主体的人自己,也习惯于将此割裂为“二元”去加以认知,在这样的世界认知中,世界成为精神与物质、本质与现象、灵与肉(灵魂与身体)、理性与感性等等一系列两两对立、相互排斥的概念与范畴,由此构成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认知系统,20 世纪西方哲学家对此多有反思。
认识论除了二元论地解析世界外,又在二元中分出主元与次元、本体与分体,把以物质实在为主体或主体者称为唯物论,把以精神实在为主体或主体者称为唯心论。在西方哲学史中,崇尚精神或理性的唯心主义要远比唯物主义阵容大。早在古希腊的哲学中就有崇尚精神、灵魂贬低现象、身体的倾向,一些哲学家认为,精神、灵魂通达善,现象、身体因与尘世欲望相连而充满罪恶;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时代,具有终极精神意义象征的上帝成为唯一的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在这一尺度衡量下,尘世的与物质、现象、身体、感性相关的一切都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文艺复兴之后,上帝失语,理性上升为主体,但与感性相关的一元仍被压抑,直到尼采开始为与感性相关的一元讴歌,此一元才逐渐为 20 世纪哲学家们所重视,逐步提升它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
20 世纪法国文学家、存在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所称的西方女性的“他者”地位的形成,与西方二元对立且不对等的哲学思维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西方认知系统中理性与感性、精神与肉体截然两分的分类原则,使男性获得被崇尚的理性身份,女性则随着感性身份的被定义而被贬抑甚至放逐,因此成为男性主体的“他者”。亚里士多德就以这样的思维给“女人”下了“判决书”,他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女人因天然缺失理性而只配受男性的统治,在这一点上女人与奴隶甚至与动物无别:
身体的从属于灵魂(人心)和灵魂的情欲部分的受治于理性及其理智部分,总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要是两者平行,或者倒转了相互的关系,就常常是有害的。灵魂和身体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兽之间的关系。驯养动物比野生动物的性情更为善良,而一切动物都因受到人的管理而得以保全,并更为驯良。又,男女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存在高低之别,也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遍适用的。这里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人类的分别若符合于身体和灵魂,或人和兽的分别,———例如在专用体力的职务而且只在体力方面显示优胜的人们,就显然有这种分别———那么,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有益〔1〕。
后来成为西方主导文化的希伯来文化,虽然与希腊文化有本质的不同,但在对女性地位的宗教哲学认识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在希伯来宗教哲学中,世界的起源来于上帝,上帝先创造了男人亚当,接着才用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做成女人夏娃,这传达了对于两性关系的认知:男性是世界的主体,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如果说这一情节的设置还暗含着男人与女人有着难以分离的联系的话,那么,《圣经》中夏娃诱惑亚当的情节则诠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女人等同感性情欲的观点,并强调了男性的理性与女性的感性之间的对立。后来西方最有影响的神学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ras)明确指出男性是同理性和精神相联系的,女性是同身体和物质相联系的,更完全是亚里士多德论女人的翻版。文艺复兴以后的近现代时期,西方哲学家们在对上帝的否定中关注生活于尘世的人的主体性,人高昂起头颅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主人,但这“人”的概念中却并没有女人,女人感性论、女人情欲论的论调仍在哲学家们的着作中作为高傲的、理性的男人们的对立面而呈现,类似叔本华的“女人的理性薄弱”,女性的美“只存在男人的性欲冲动之中”〔2〕的论调仍时有所见。对此,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尖锐地指出:
女性要素既包括在善与恶、吉与凶、左与右、上帝与魔鬼这些鲜明对比的概念里,也包括在阴与阳、尤拉纳斯与宙斯、日与月和昼与夜这些成双成对的概念中。他性(Otherness)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列维 - 斯特劳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自然形态到文化形态的转化,以人类把生物学关系当做一系列参照物来观察的能力为标志,二元论、交替性、对立性和对称性,不论是以明确的还是以含糊的形式,与其说构成了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不如说构成了社会现实的根本而直接的既定论据”。……如果我们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意识本身当中发现了对其他所有意识的敌意,那么事情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the object)相对立。……没有一个主体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3〕“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波伏娃向整个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给予女人“他者”地位的设定作了宣战。西方奠基于理性与感性二元界分的思维方式为西方性别哲学提供了合理性,在理性—男性、感性—女性的思维中,理性—男性的崇尚借助历史的力量,不仅将感性—女性逐出政治生活,而且将其逐出了世界———因为在主导性的西方哲学史中,世界总是理性的世界。
中国哲学在世界观与认识论上都与西方不同,中国世界观与认识论强调有机整体性的世界理解与把握,对世界的生成认知坚持一元论,认为“万物得一而生”(《老子·三十九章》),“道无双,故曰一”(《韩非子·扬权》),“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淮南子·诠言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在坚持世界生成的一元论基础上,中国古人“推天道以明人事”(《周易·乾卦》),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亦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浑融思维。基于浑融思维的认识论,在看待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时,强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看待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时,强调两者的统一性与一致性。此外,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五行思维,把世界万物归为金木水火土五类,又贯以阴阳,阴阳是万事万物互联互构、流变生成的基本属性,它们本于自然,来于天地,无可独立,无可单行。阴阳对应于男女,阴阳相作而成,对应于男女交互而生。
中国哲学的有机整体性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规定了中国性别哲学男女两性的一体性取向及交互而动而生的取向。在男女关系构成性的认识上,与西方在分立中强调两者差异不同,中国是在整体观照中强调两者关系。首先,肯定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天人相合的关系,即是一种互为一体的自然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统阴阳,当见传,不得中断天地之统也,传之当象天地,一阴一阳,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然后能生也”(《太平经》);“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周敦颐《太极图说》)。这些都是在说男女作为阴阳万物的重要体现者,是与天地一体的,具有自然生成的一体性;其次,肯定了男女作为统一关系体的共同作用。“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这段话说明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礼义规约,都是前感后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这整体中,男女关系起着重要作用,男女交感是世间万物之始;第三,肯定了处于统一体中的男女之间关系的相依相生性。“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四十二章》),“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周易·序卦》),男女夫妻之间的融合互生,是万物获得秩序,社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些都强调了男女两性的相互依存关系,男人与女人正是在这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获得性别定性。
然而,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思想面对世界何是、世界何为进行探索的自成一体,而是注重人伦关系的思考与研究,因此它同时又是伦理哲学或哲学伦理学。哲学与伦理学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实践特征突出的伦理学思想同时就是哲学思想。伦理学的男尊女卑序位观念也就成为哲学观念。所以,尽管中国哲学在其有机整体性的思维框架下,强调了男女之间关系的相依相生、不可或缺,但并没有赋予这相依相生关系体中的性别双方以平等的地位,中国以维护男性为主体的血缘承继和以男性为体现的嫡长制创建的森严的等级伦理秩序,将这性别双方给予了尊卑的等级定位———男尊女卑,致使和谐的关系体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向有利于男性性别的一方发展,两性等级差异在历史中酝酿并作用于女性生存的实践,中国女性在“男尊女卑”的哲学伦理秩序中被整体地置于“卑下”的处境。于是,中西文化在性别关系认识上出现了结论的吻合:男性是高贵的“第一性”,女性是卑微的“第二性”。中西女性在特质完全不同的文化路径中走向了相同的“第二性”结局。
还需提及中国“孝”范畴在两性关系中的意义。中国哲学在与伦理学相融合中,理所当然地把构成伦理学重点问题的“孝”意识提升为人伦等级序位的基本范畴。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角度、阴阳相合角度、血缘亲情角度、人性天然角度、天理性命角度,对“孝”范畴进行思考与阐释,把伦理学基于“孝”的家国关系规定进行综合的哲学阐释。“孝”是中国有机整体性哲学观的产物,是中国性别文化独有的文化元素。就两性关系而言,“孝”在中国“男尊女卑”文化设定必然带来的两性文化冲突中,起着弥合两性间的尊卑序位、缓解性别冲突的作用。中国伦理哲学给予孝道相当高的位置,不仅将其视为立身之本,更视为治世之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利也”(《孝经·三才章第七》)。“孝”可以广于礼乐,可以移于忠君、顺长、治官,又可用于诤臣、诤友、诤事,因此无所不通。但从根本上说“,孝”在于事亲,即体爱、敬崇生养自己的父母。在尽孝的活动中,父母是被“孝”的共同承受者,身为女性的母亲与身为男性的父亲同样拥有被子嗣所“孝”的权利,父母在“孝”中被一体化。从两性关系看,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法性,女性在处于母亲角色时便具有了超越两性尊卑序位关系的可能性。所以,中国女性被规定的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中,前两种在男尊女卑性别伦理压迫下,处于卑从的地位,待到做了母亲便会冲破这重压迫,在男性子嗣面前获得超越男尊女卑文化设定的“解放”。当然,这种“反卑为尊”式的解放不是女性获得性别主体性权力的解放,而是父权制文化设定的结果,目的是保证父权制的文化秩序,所以,很多女性在母亲的位置上,甚至比父亲更严厉地教导子嗣遵循维护男性权力的社会规范,包括对女性制定的严格的规范,在中国依照灭绝人性的贞洁观制裁失贞女子最严厉的执行者恰恰是经由“母亲”位置而位居家族高位的女性自己。但从两性关系看,“孝”起到了弥合两性关系冲突的作用,使在男尊女卑的伦理秩序压迫下的女性有了喘息与宣泄的机会,这也是西方能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发生女权主义运动而中国则不能的原因之一。
中国哲学的上述四个方面,即世界的有机整体性把握,阴阳互动互构的生成性把握,与伦理学相融合的人伦序位把握,以及“孝”范畴的综合阐释,综合一体地规定着中国独有的性别哲学。在这一哲学意识中,男女互构而与天地齐,男女互动而与天地参,男女相合而与天地一。同时,男女又并非彼此平等,而是比与天地,天上而地下、天尊而地卑,这就有了千古如斯的合于天地的男尊女卑。
二、性别哲学的文学表征
中西女性文学书写与文学批评基于各自性别哲学而展开,以书写与批评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呈现着各自的性别哲学意识,由此形成中西方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不同。
二元对立哲学思维对西方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也包括女性自己的书写及其文学批评。从文学表现来看,20 世纪兴起的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们发现了西方文学传统对于女性的书写存在一个隐秘的二元对立的范式,即将女性塑造成两种对立的形象,一种是天真、美丽、纯洁、可爱、无私的“天使”;一种是复杂、淫荡、刁钻、自私的“妖妇”,对此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多有阐释。两种对立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西方父权社会源于二元不对等思维方式的对女性的认知,“天使”形象是男性对于女性审美期许的文学投射,“妖妇”形象则是女性等同于感性—欲望动物的西方哲学认知的文学演绎。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sne Showalter)称这种现象为“文学实践的厌女症”和“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格芭(Susan Gubar)在合着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这两种女性形象都是对女性的歪曲与压抑;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大声疾呼要杀死房间里的“安琪儿”(天使)。
从女性自己的文学书写来看,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思维也在发挥着潜在的作用,只不过她们用隐蔽的方式传达着自己性别一方的意愿。以《简·爱》为例,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读解是,夏洛蒂·勃朗特在这部类似自传体小说中讲述了女人只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就会获得“灰姑娘”式的幸福的故事,然而,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夏洛蒂实现“灰姑娘”的梦想采用的是在二元对立思维构架上的男性价值标准的女性置换,是将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的在《思考妇女》中提出的“性别类比的思维习惯”的逆转式运用。小说在描写女主人公简·爱与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相遇时,按照西方男女相爱结婚的价值标准,女性处于劣势。女主人公简·爱矮小不美,除有一颗不为西方男性看重的自尊心外身无分文;而身为特恩费德庄园主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拥有财富和强健的体魄,身边不乏富家美女追随,就是这样,罗切斯特还是摈弃富家美女爱上了贫穷不美的简·爱。如果小说让简·爱不顾一切接受了罗切斯特带有“恩赐”意味的爱(这是一般小说选择的结尾),这就是个“灰姑娘”的故事,对于爱情婚姻中的男女双方,“灰姑娘”的故事更证明着男性主人公的睿智与高尚。然而,《简·爱》不是在演绎“灰姑娘”的故事,它是在向整个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的不公宣战,在向男性只认女性美貌外加有财富更好的价值取向宣战。夏洛蒂用以宣战而取胜的武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让所有男性自认为优势的东西都赋予女性,并让男性丧失优势处于劣势,处于被“恩赐”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了小说结尾处男女主人公拥有谈婚论嫁条件的逆转: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因庄园被烧毁变得一无所有,身体因失去一只胳膊、一只眼睛而不再潇洒强壮;女主人公简·爱却不再是原来贫穷不美的简·爱,她获得了远方亲戚的一大笔遗产,虽然还是原来的容貌但比起残废的罗切斯特就是身体健全的美女了,而且此时还有一位英俊、坚毅的男性(简·爱的堂兄圣约翰·李维斯)追求者。罗切斯特最初的优势简·爱都具备了,她有资本居高临下地面对罗切斯特了,于是她回来以“救世主”的身份做了罗切斯特的“拯救者”。夏洛蒂以男性价值标准为参照,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完成了男女角色在社会地位、家庭财产、身体容貌的互换,在这一互换的实现中赢得了整个女性群体对于整个男性群体的胜利。
从文学批评来看,由于二元对立哲学思维在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作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伊始,就以西方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为批判目标,但女性主义批评者们用以批判的武器自觉与不自觉地同样带有“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波伏娃“第二性”的命题、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性政治”①的判定、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对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二元对立范式的揭示、肖瓦尔特倡导发掘女性“自己的文学”等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当然,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也同时做了消解“二元对立”思维的努力,如伍尔夫提出了“双性同体”写作理论、埃莱娜·西苏(Elena Ceausescu)提倡以身体写作来颠覆男女二元对立文化传统等,20 世纪以来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有意消解男女性别的对立,其理论呈现出由“性别强调”到“性别包容”的批评态势,而这也恰恰说明西方性别哲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学与女性自己的文学书写中,就难觅二元对立哲学思维的文学产物,有学者试图对应性地将西方文学“天使”与“妖妇”二元对立范式书写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虽然也能举出个案来加以印证,但却不符合中国文学的整体精神。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认知下,中国文学审美取向不强调对立而强调“中和”,先秦时期形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中和”审美观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已积淀为中国文人深层的审美心理结构,在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中,这一审美观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文学实践的厌女症”的现象在中国文学中很难发生。如对于女性“色”的描写,一方面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规约,对违反家庭伦理的“女色”以批判性地文学展示;一方面却在诗性精神领域给“女色”留了一片自由舒展的天地,这便是中国独具特色的“青楼文学”,唐诗中有 2000 首创作灵感源于青楼女子的作品,李白的“对舞青楼妓,双鬓白玉童”、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诗句更见出“女色”与文人雅士诗性的精神同构。所以中国文学对于“女色”没有像西方那样将之驱除于理性的精神领域之外并予以蔑视,而是作为文人墨客的另类精神慰藉与情感补给为文学所拥抱。中国文人善于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异质统一”的调适,这形成中国文坛“女贞”形象与“女色”形象共时性地活跃甚至交映生辉的奇观。
中国女性自己的文学书写也少有西方女作家明晰地向男权本位文化挑战的意识,中国古代女作家的书写指向更多的是向内,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苦愁怨为主,乔以刚教授将此概括为五种情形:“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的宫人怨、“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的商妇怨、“从此不归成万古,空留贱妾怨黄昏”的征妇怨“、良人何处事功名,十载相思不相见”的离妇怨、“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知”的青楼怨,这些悲苦愁怨虽暗含着对造成自己愁怨的男性一方(或丈夫或情人)的指责,但指责中不含有对峙,不含有较量,相反是向着欲“和”的方向发力,“怨”的是夫妻或情人间不能琴瑟相合,长相厮守,是一种“对立统一”的文学表现。“浏览古代女性的作品,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些跨时代的共同主题:闺中相思、弃妇忧愁、感物伤怀等等。
她们的视点往往如此接近,心境又常是那么相通。朝代的更迭、世事的变迁在多数女子的创作中留下的只是淡淡的痕迹,以致我们可以纵跨千年,将这些作品的内容上大体概括为‘身边文学’”〔4〕。“身边文学”,这是中国传统女作家文学书写的形象概括。至于五四运动中崛起的新女性文学书写,由于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西方式的以鲜明的性别对峙为特征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国的女性解放是为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所促成,其呼唤解放的引领者又多为男性先觉,女性主体意识自觉缺失,其女性书写便不可能像西方女性那样有强烈的、抗拒性的性别指涉。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崛起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理论资源更多地取自于西方,建立于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随之也被运用于中国女性文学(包括写女性与女性自己写两种文本)的批评实践,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概念的比附与套用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常见套路,反而遮蔽了中国女性文学书写源于民族文化的生存呐喊与文学诉求,中国“一元论”的哲学文化与男尊女卑的伦理文化共同铸就的中国的性别文化,形成着中国女性“第二性”生存与文学诉求的更复杂、更隐约、更沉痛的情形。21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步,已意识到“二元对立”思维的弊端,尤其是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弊端,其理论主张已由强调女性立场的“女性主义”视域转入开放的、平和的“性别”视域,“性别”视域使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摈弃了来于西方的性别激见,批评更向合于中国女性文学实践特色、合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性别文化实际的方向发展。
三、性别哲学维度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
从新时期女性文学批评开始主体性建构算起,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度过了 36 个春秋。这 36 个春秋,中国坚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们在大量涌进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践行的文本中钩深取极,结合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开创性地进行着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纵观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以及西方其他文学与文化理论解读与阐发中国女性文学文本的成就,要远大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原创理论的开掘。当下的女性文学批评,“借西论中”“借西构体”仍然是大多数学者选择的批评范式与批评路径。不可否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具有来于女性性别体验与女性书写普遍性的世界可适性,但由于西方性别文化导致的西方女性的历史及现实生存与中国女性历史与现实状况的差异,前者的女性性别体验又有着体现西方文化印记的特殊性;同时西方文学传统也迥异于中国文学传统,基于这样的文学传统的西方女性书写也有着鲜明的西方特色。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是面对西方的女性书写,以西方传统的性别压迫为批判指涉而创构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适用性的程度值得分析,盲目地将其作为圭臬奉为至宝地拿来衡量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更不可取。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生发于中国土壤,浸润着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即使是当下的女性文学创作,无论它如何追逐西方文学创作的脚步,如何开放和新潮,但只要它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它写的是生长于中国的体验,就具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借西论中”的批评会屏蔽掉作品中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刻而复杂的意蕴,甚至指鹿为马。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性别文化特征,探究中国文学传统之于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作用,进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理论,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走出“唯西是尊”藩篱,破除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以更适合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态势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所在。
鉴于中西哲学差异而导致的中西性别哲学认知的不同,乃至这一不同带来的中西文学实践的迥异,建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理论,应考虑哲学维度的建构,即应建构“中国性别哲学”视域下的女性文学批评。2010 年由全国“妇女/性别学科发展网络”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和哲学系承办,召开了第四届“性别哲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论证了“性别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给予“性别”作为哲学思考的一个维度在学科层面上的肯定,我们这里提出“中国性别哲学”的概念,即基于这样的学术研究前提。
从女性文学批评坚持民族主体性视角提出建构中国性别哲学,旨在在中国性别哲学的视域下达到对女性文学书写的观照与审视,其研究应包括基础理论与文学形态两个方面,前一方面主要研究中国性别哲学特质、中国哲学性别维度思维与西方哲学性别维度思维的差异、“天人合一”认知框架下的男性与女性的主体间性、中国两性关系的哲学认知对于女性现实生存的文化效应等;后一方面研究中国性别哲学旨要及其思维方式对于创作主体、文学文本形态与文学文本接受的作用,可进行创作主体的性别哲学思维之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性别哲学视域下的男性书写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书写中对性别关系的认知与呈现“、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女性书写的情感形态等方面的探索。同样,前一方面研究成果构成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批评依据,后一方面则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应予重视的批评指向。
参考文献
〔1〕〔希〕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15.
〔2〕〔德〕叔本华. 叔本华的智慧〔M〕. 刘烨,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76-178.
〔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2-13.
〔4〕乔以钢. 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8.
郭绍虞先生在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撰文,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多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现状:较多注意汉民族的理论而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这种情况,近年来已有所改变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但是,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还需要有人...
绪论研究意义女性主义批评简而言之就是以女性意识为关照,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一般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在此,笔者主要分析的是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先驱代表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
第2章双重标准的拒斥与重构早期的女性作家在试图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受到了传统批评标准的不公平对待,长期垄断话语权威的男性力量贬低、拒斥女性作品,女性作品的价值未得到应有的肯定。面对这种境遇,肖瓦尔特等一批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了...
二、女性主义他者(Other)思想。本篇论文所研究的女性主义他者(Other)思想包括传统女性主义的他者(Other)思想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他者(Other)思想两部分。其中。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本文专指法国女性主义思想。(一)传统女性主义他者(Other)思想。...
三、女性主义文论语境下他者(Other)思想对文学批评实践的启示结合前两部分的小结论可知女性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经历了从超越他者(theOther)到尊重他者(theOther)的思想流变。这也正构成了女性主义文论多元化和差异化叙述策略的生成和流变机制的主要线...
一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一)家庭环境的熏陶弗吉尼亚斯蒂芬1882年1月25日诞生于英国伦敦肯辛顿,海德公园门22号。她是莱斯利斯蒂芬爵士与裘丽亚达克沃斯女士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位中产阶级的哲学家、作家...
第4章女性批评的建构与践行持修正论观点的女权批判虽然认识到女性的屈从地位,但它带给女性更多的是负面的、否定性的文学经验。正如肖瓦尔特所言,女权批判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它以男性为中心。如果我们研究陈旧的女性形象模式,研究男性批评家的性别歧视行...
引言(一)本选题研究背景和意义。1、选题的研究背景。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德国现象学--存在论哲学传统中,他人/他者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从德国哲学家托尼逊的着作《他人》中:他人问题是二十世纪第一哲学主题的论述可以得知其中端倪。在现象学...
结语纵观新世纪女性文学十几年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其媒介化、市场化、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基本走向,联手推动着女性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变迁。在全球化的消费语境,以及中国当代多种形态共生、错综复杂的语境影响下,新世纪的女作家们的意识形态也处于消费文...
通过现实主义精神揭示与反观农村熟悉的生活,是对鲁迅先生说过的“揭除病痛,获得疗救关注”做到切实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