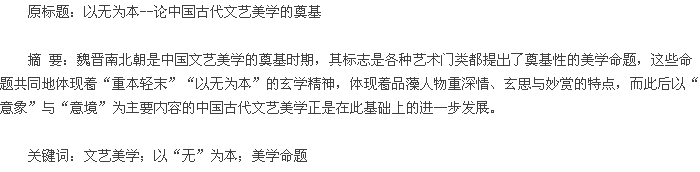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艺发展的转型时期。这可以从艺术类型与审美特征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说,秦汉艺术的主要类型是宫殿建筑、陵墓雕塑、汉画像石以及汉赋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艺术的主要类型则是音乐、绘画(人物与山水)、园林、书法、诗歌等;如果说,秦汉艺术以其包容万有、气势雄伟的美学风格表现着一种集体的意志,那么,魏晋南北朝艺术则表现出个体的深情、玄思与个性。
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深刻地决定并影响着中国后世艺术的发展。如果借用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的话来说,表现集体意志的秦汉艺术基本是一种“附庸的艺术”,而表现个体的深情、玄思与个性的魏晋南北朝艺术则是一种“自由的艺术”.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发展的转型时期。其标志是,各种重要的艺术门类都提出了自己最为基本的美学命题,这是前所末有的。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先秦的美学基本上是哲学美学,儒家在社会功用的前提下谈论艺术,道德伦理严重地束缚着艺术审美;道家倡导的确实是艺术精神,但由于其排斥文明的态度,也使他们不可能具体地去探讨艺术审美。两汉文艺美学虽有发展(如诗歌中的“比兴”的提出,绘画中“形神”的论述等等 ),但在儒家政治教化思想的束缚下,他们的探讨还是比较零星的。但是,到了魏晋六朝,随着魏晋玄学与品藻人物风气的兴起,在魏晋玄学“重本(无)轻末(有)”、“得意(无)忘言(有)”思想的影响下,在品藻人物的重视“玄心”、“深情”与“妙赏”风气的影响之下,文艺美学才开始由汉代的重视外在的社会规范而转向重视内在本体的探寻。所谓魏晋六朝的“文的自觉”,其实也就是“美的自觉”.中国的文艺美学就在这时才开始与哲学美学、伦理美学相互分离。“文的自觉”与“美的自觉”带来了人们对艺术创作与欣赏的重视,对文艺美学的重视--文艺美学方面出现了诸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嵇康《声无哀乐论》、谢赫《古画品录》、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重要美学着作,特别是各种艺术门类都提出了一些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文艺美学的命题。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这些文艺美学的命题还共同地体现着那个时代重视“玄心”、“深情”与“妙赏”的风气,以及“重本轻末”“以无为本”的精神,即在谈具体的文艺时更重视文艺的“道”、“意”、“神”“趣”这些“存在却又无法言说”的“空灵而玄妙”的精神本体,从而典型地体现出了封建社会中期的文艺美学的基本特征。
很显然,如果没有魏晋六朝的这些文艺美学思想,唐宋的意象与意境理论的产生就会显得没有根基。
魏晋六朝文艺美学的命题大都是结合着具体的艺术门类而提出来的,下面,我们对魏晋六朝文艺美学的这些重要命题略作些探讨。
一、声无哀乐 ( 音乐 )
嵇康是一位玄学家,也是“妙解音律”的音乐家。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表达了他独到的玄学音乐美学观,此文称得上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少有的充满思辨色彩的杰作。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导源于他的玄学宇宙观。玄学家一般都是把自然之道视为宇宙本体,嵇康论音乐也是如此:“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①嵇康这里所说的“其体自若”之“体”,既是指自然之体,也是指音乐之体,在嵇康看来,音乐的本体就是声音的自然,它与人的情感是没有关系的。持这样一种音乐自然本体论,嵇康对音乐本体与听众情感的关系作了颇具启发性的辨析:
“五味万殊,而在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 ? 然人情不自同,自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皆由声音也。”②嵇康认为声与心原是二元的,音乐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而哀乐 ( 情感 ) 只是人“发其所怀”的产物,就像酒的味道是甘醇的,然而喝醉酒的人却表现为喜怒,但不能因此便认为酒有喜怒,所以他说:“声之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③儒家乐论向来讲什么“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把音乐的本质归于外在的政治与情感,而嵇康则把音乐的本性归为自然之道,在他看来“和声无象”、“言声无常”,音乐之美就在于它的“自然之和”,在于音乐和谐的乐音本身。所以,他说:“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④嵇康的音乐思想对先秦庄子“与道合一”思想也有继承与发展。嵇康认为音乐之美在于音乐本身,在于它的高低、强弱、动静、舒缓的自然和谐,所以人们听音乐“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安得哀乐于其间”.⑤应该说,音乐与情感的问题是个相当复杂的美学问题,就是到现在也仍是音乐美学中一个棘手的难题,音乐的内容本身比较抽象,像儒家乐论那样“它律”地把音乐之美归于外界情感乃至政治的影响、甚至直接地等同起来,显然是缺少美学依据的,因而嵇康主张“自律”的“声无哀乐”显然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嵇康的音乐理论很有些像西方音乐家汉斯立克的“音乐自律”论。但是,如果说音乐完全引不起欣赏者的情感,也显得说服力不够。或许,我们可以参考现代西方的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说音乐与人的情感与政治直接同构是错误的,这点嵇康说的是对的,因为这种说法把音乐的审美情感与人们的一般情感混同了,人们在欣赏音乐时所产生的情感是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情感,是一种为音乐的形式所唤起的审美情感,是一种音乐形式与人的感知异质同构而产生的审美情感,这也就是一种“与道合一”.
在《声无哀乐论》里,嵇康还提到天下清静无为、人心自然平和的理想社会,他认为那时的人们是无乐无哀的,演奏的只是“以平和为体”的音乐。这种音乐的功用在于让人体味到自然之道,从而进入与道合一的境界,这实际仍然是强调音乐的审美自律。他在《赠向秀才入军》中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①“太玄”就是指道家的自然之道,是指一种精神本体,欣赏音乐能使人心归于平和,感受到与道的合一,所以如《琴赋》中所说“导修神天,宣和琴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②。嵇康充分地认识到了音乐对人所具有的独到的让人心身和谐的审美功能与修身功能。嵇康认为,音乐能让人处于自然宁静的“大和”境界,是有益于身心的。嵇康的自然平和的音乐有修养身心的音乐功用论与儒家移风易俗重政治教化的音乐功用论是截然不同的,它显然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在音乐美学上的具体体现。总体上说,嵇康“ 音无哀乐”论的艺术自律的色彩较重,这显然是对儒家音乐它律思想的一种审美超越。
二、传神写照 ( 人物画 )
宗白华、王瑶等先生早就指出:魏晋画论、文论都起源于当时那热闹的品藻人物的风气,许多文论、画论的术语都源于人格美的评赏。顾恺之的传神、谢赫的气韵以及刘勰的体性、风骨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顾恺之为东晋名士,也是当时杰出的画家,而他的传神写照论就是他对人物画实践的理论总结。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说:“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③顾恺之认为画家在描绘人物的时候,被画人物的面前必须有个对象,这样他的形象与神情才能够生动,如果没有这个对象,人物的动作、表情就会显得呆滞。“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顾恺之强调画人物要让人物“有所对”,其用意就在于,强调画家画人物时,必须要传达出人物的精神风貌来。
《世说新语·巧艺》中,有一些关于顾恺之人物画创作实践的记载,它们对人们理解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是有帮助的。“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灵只有通过眼睛才能被看见。刘劭《人物志》就有“征神风貌,情发于目”的说法⑤。顾恺之之所以画人“数年不点目睛”,就是因为他对画出人物的精神非常重视,这显然是与当时品藻人物重视玄远精神的风气是完全一致的。《世说新语·巧艺》还记载:“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郎有识具。此正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⑥裴叔则是玄学中的重要人物,顾恺之为他画像时,“颊上益三毛”,之所以要如此,显然也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个性特点,从而更好地表现出裴叔则独特的精神风貌,这也就是所谓的“如有神明”.《世说新语·巧艺》还记载: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此子宜置丘壑中。”⑦谢鲲也是位东晋名士,不喜功名而爱隐逸。顾恺之在画谢鲲时之所以让他置身在岩石之中,就是为了借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来烘托谢鲲那种喜欢隐逸山岩的名士志趣,从而更好地表现出谢鲲的精神风貌。
有些论者用“以形写神”来概括顾恺之的人物画的美学思想,似乎把顾恺之画论的时代特征给忽略了。
事实上,绘画中的形神关系前人早有论述。荀子曾提出“形具而神生”的见解⑧。《淮南子》对形神关系则有了更进一层的认识。《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⑨《说山训》中也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 ( 悦 );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⑩“君形者”也就是“生之制”的“神”.画面上的美女西施不可爱,猛士孟贲不可畏,原因就在于画家只画出了他们的外形,而没能画出他们特有的内在精神,即“神”,这样的人物画当然是无生动可言了。《说林训》对人物画中“画者谨毛而失貌”的现象提出批评①。“毛”指画的局部与细节,“貌”则指全局与整体,为了细节的严谨而忽略了整体的准确,《淮南子》认为这是不懂绘画美学的表现。在“毛”与“貌”上,《淮南子》更看重后者而轻视前者。这些论述表达的都是“以形写神”的美学精神,确实可以说是顾恺之“传神”论的先声。但是,顾恺之“传神写照”毕竟是在品藻人物的风气下产生的,所以,不管是“点目睛”、“益三毛”,还是“置丘壑中”……顾恺之的意图都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要为那些具有玄远精神的名士传神写照,画出他们的精神风貌。《世说新语·巧艺》中记载“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②手挥五弦之所以容易,是因为它只是写形;目送归鸿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指涉到了人物玄远的精神。正像汤用彤先生早就指出过的:顾恺之“数年不点目睛,具见传神之难也。四体妍媸,无关妙处,则以示形体之无足轻重也。……顾恺之的画理是得意忘形学说之表现也”.③此实为知人论世的不刊之论。
顾恺之在《论画》中还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④人物为什么最难画?因为其它东西相对于人而言是死的呆的,而人物则是鲜活的,不但有形体,而且还有玄远的内在精神与个性,画其它东西描摹即可,但画人物则一定要传出其神,而这就需要画家费心地去“迁想”--去调动自己的艺术想象,去揣摩体会所画人物的个性特点;去“妙得”--去把握被描绘人物的精神个性,并把它精妙地表现了出来;而前面所说的“点目睛”、“益三毛”、“置丘壑中”,都可以视作顾恺之在这方面的成功艺术实践。
三、气韵生动 ( 人物画 )
“气韵”见于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六法者何 ? 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⑤“六法”是谢赫对绘画艺术的一个比较朴素而系统的总结,后世对其评价非常之高,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⑥六法的后五法谈的主要是绘画技法方面的内容,第一法“气韵”显然最为重要,但也比较费解。意大利学者维柯曾指出:“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 ⑦谢赫的“气韵”也属于这种情况。
“气”与“韵”在当时,都是对着人的精神风貌而言的。先看“气”.《庄子·知北游》云:“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⑧《论衡·无形》云:“人以气为寿,形随气而动。”⑨中国古人认为人禀元气而生,并把气当作生命的象征与标志。曹丕《典论·论文》中更进一步认为,各人所禀受的“气”是不同的,“气之清浊有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⑩,这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人对人之“气”的看法。谢赫在此基础上把“气”移用到了人物画的评价上来,要求画家在画人物时,一定要画出“气”来,即在画人物时一定要超出形似的水平,而达到栩栩如生的程度,画出了人物的“气”,人物才能有个性,有神彩,才是“活”的。《古画品录》用“气”共有六处:卫协--“虽不形妙,颇得壮气”;张墨、苟勖--“风范气候,极妙参神”; 顾骏之--“神韵气力,不逮前贤”;夏瞻--“虽气力不足,而精采有余”;晋明帝--“虽略于形色,颇得壮气”;丁光--“非不精谨,乏于生气”①。从以上“气”的具体用法中,人们不难看出谢赫是把“气”当作画人物是否成功的标志的,画出了“气”,人物的形象就生动鲜活,否则,则相反。
如卫协的画“虽不形妙,颇得壮气”,而被列入首品;丁光的画“非不精谨,乏于生气”,便被列入第六品。
再看“气韵”之“韵”.谢赫《古画品录》中用“韵”共有四处:陆绥--“体韵道举”;顾骏之--“神韵气力,不逮前贤”;毛惠远--“力道韵雅”;戴逵--“情韵连绵”.②《古画品录》中“韵”的用法,可以说与《世说新语》中“韵”的用法是大体一致的,即都指人物的气度风神,亦即通过风姿形态透露出的个性精神之美。谢赫所说的“体韵”、“情韵”、“神韵”以及“韵雅”都是如此。再如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说:“少无适俗语韵”③,这里的“韵”同样是指一种个性风度,此类用法在当时是较通行的。后世学者也曾给予它很好的解释,如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云:“韵者,态度风致也。如对名花,其可爱处必在形色之外。”④可见,“韵”正是指人的一种不粘滞于物的玄远自由的精神,一种个性精神之美。
谢赫所说的“气”、“韵”乃至“气韵”,显然都是就人物画而言的,它们意思虽有相叠,但也有些区别:前者更基本,贴近生命的本原;后者更飘逸,指一种空灵玄远的神味。谢赫把它们结合起来作为“六法”的第一法应该说是很有功绩的。谢赫的“气韵”与顾恺之的“传神”一样,都表露出重神轻形的倾向。
谢赫崇简厌繁,甚至说“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此语已开晚唐司空图“取之象外”之先声。很显然,谢赫的“气韵”与顾恺之的“传神”一样都体现出了那个时代品藻人物所显示出的审美风尚。
谢赫的“气韵”后来与顾恺之的“传神”一样,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美学术语,并被移用到后来的山水画与文人画上。
四、澄怀味象 ( 山水画 )
魏晋名士喜爱山水,喜爱山水的审美风习不但使旅游风行起来,而且也使得山水诗、山水画兴盛起来。
宗炳的《画山水序》,便是一篇反映当时人们关于山水画的美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 ⑤庄子曾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真正对山水的审美欣赏可以说是从魏晋开始的。在宗炳看来,山水之所以是天地的大美,是因为它“以形媚道”,“质有而趣灵”,因而能让人身游、神游其中,“澄怀味象”,从而在这种“天地大美”中感受到一种心灵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宗炳对山水审美的理解反映了当时名士的普遍想法,它完全超越了儒家“君子比德”说的功利羁绊,达到了一个真正审美的境界。
在宗炳看来,描绘山水之美的山水画,它的功用仍然在于满足人们对山水之美的欣赏与喜爱:“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砧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⑥《南史·隐逸传》说宗炳:“ 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之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⑦宗炳对山水画的兴趣,是源于他对山水之美的一往而情深。因为山水画可以弥补他年老体弱旅游不便的局限,满足他“卧游”的需要,因为山水画与真山水一样可以“以形媚道”.其实,对宗炳来说,不管是“身游”还是“卧游”,其精神实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澄怀观道”.山水画的本质如东晋王微在《叙画》中说的是“以一管笔拟太虚之体”⑧,“太虚”也就是道,山水画也就是“以形媚道”;而“澄怀”则是指老庄所说的体道时的虚静自然的心境;“味道”则是指在欣赏山水中感受到的“与道合一”的精神自由。
“万理融其神思”.“澄怀观道”说到底,就是通过对山水画的欣赏来作精神上的逍遥游,从而获得“畅神”的审美境界。东晋王微的《叙画》对此说得更为具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圭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 !”①可见东晋名士多么看重山水画给人的精神高度超越的审美快感。
宗炳对山水画的构图原理也作了探讨:“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以寸目,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目。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素绢以远应,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②宗炳在这里指出了中国山水画构图的基本原理。为了使山水画咫尺有千里之势,为了更便于“畅神”,中国山水画采取的是一种散点式或者无点式的透视方法,采取一种应目会心的象征性的表现方手法,与西方焦点透视方法以及感知真实的表现方法完全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可能展示“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的艺术境界,才能具有“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审美效果。宗炳的《画山水序》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山水以及山水画的审美理解,而且也为唐宋山水画的真正兴起作了理论准备。
五、涉园成趣(园林)
汉代是大一统的国家,当时宫殿与园林联在一起的,被称为宫苑。宫苑的特点是法天象地,容纳万有,规模宏大,具有一种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魏晋以降,随着汉代大一统的破灭,氏族地主庄园经济的兴起,加上玄学的影响,人们开始对自然山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水诗、山水画出现了,讲究自然之趣的园林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
山水画则是平面的中国园林,中国园林是立体的山水画。魏晋园林的发展有一个历程:它的最初形态是王侯宫苑,如曹氏父子园苑。曹植的《公宴》诗中对这种宫苑作过描述:“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逐。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③这样的宫苑仍然是比较富丽的。接着是东晋的“竹林”.《世说新语·任诞》中说:“陈留阮籍、樵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④“七贤”把“竹林”当作聚会与放达之所,“竹林”虽说不上是园林,但它却体现了当时士人们已经以自然风景来取代富丽宫苑的审美转向。再次是“兰亭之会”.兰亭聚会原是古俗,但到了王羲之的时代,由于士人的到来,古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⑤兰亭的景致与竹林在自然之趣上是相通的,但是兰亭之景比起竹林显然要丰富精妙;士人们在兰亭游玩,有酒有诗,与竹林也有些近似,但竹林体现的是放达的醉境,而兰亭体现的则是轻松的愉悦之境,因为人们更重山水自然之趣,所谓的“仰观”、“俯察”、“游目骋怀”,已经表明了这里已经具备了真正游园的性质与意趣。而再进一步则是山水与园林的结合,因为有了这关键的一步,园林才真正成为了人们心灵的安顿之所,因而游园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而且也是一种审美形式,它把生活与人生意义的探讨融在一起,因而为园林开出了新境。东晋士人热衷于造园原因就在这里。高门名宦如谢安、王羲之、孙绰、谢灵运等,“贫寒之士”如“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陶渊明,都无不悉心地经营着自己或大或小的园林,而园林也就在这时才成为了真正的艺术,这时私家园林与士人情趣被交融在了一起,生动地体现出了魏晋审美的意趣。因此,不是石崇的富丽的金谷园,而是有自然之趣的谢灵运的别业(庄园)与陶渊明的田园才是魏晋园林的代表。谢灵运的别业是大园,陶渊明的田园则是小园,小园中的自然之趣体现得要更为典型充分,因而在魏晋园林中更是占尽风情。
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这样描写他的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①陶渊明的田园虽小,但由于注意园内门窗的对景位置和园与周围环境的借景关系,更加上园主人的深情与玄心,小园就被艺术地融入了周围的自然,同时周围的自然又把自己纳入了小园。因而园虽小,情致却十分丰富: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②,可见“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还可以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③,同样,还可以“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④……小园虽小,却占尽风情,充满自然之趣,就像主人自己所说“园日涉以成趣”.可以说,到了“园日涉以成趣”⑤,中国的园林才真正成为了艺术,开出了独特的境界。它可大可小,因地制宜,随遇而安,趣味天然,超越了礼法的束缚,洗尽了皇家的富贵,在自然中显示着宇宙的情韵,成了魏晋士人性格的艺术表现。
魏晋六朝士人园林艺术特色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首先,东晋大批氏族过江,使得文化向南迁移。其次,江南的山水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山水:江南之山,峰峦岭壑,自然给园林的内外之景以天然风姿;江南之水,涧潭溪泉,自然给园林的营造以柔美意趣;这使得士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大量的人工雕琢,便可以依山顺水,因地制宜,略微点染便可以创造一段“纡余委曲,若不可测”的雅致空间;还有,再有选择地种以各类植物,根据地形高下而建造些房屋亭台,这样的人工可以更好地点化突出原本的自然之美,这就使得士人的园林成为体现玄学山水观的人化自然,从而可以满足士人们“澄怀观道”或“畅神”的审美需求,满足他们“园日涉以成趣”的玄心。在这种艺术实践的过程中,魏晋六朝士人的园林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这就是景观体系以山水与植物等自然形态为主导,艺术空间以“纡余委曲”为行色,并将诗歌、绘画等士人艺术融于其间,从而达到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在中国后世的园林艺术中,人们不难发现魏晋六朝士人园林“涉园成趣”的深远影响。
六、神采为上 ( 书法 )
我国书法到了魏晋是一个大转折,书法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名的书法家,特别是出现了王羲之和王献之这样的书法革新家,使中国书法的面貌为之一新,从而进入了真正的书法时代。曹魏改制,把汉代流行的刻碑的风气禁止了。曹操想以禁碑的方式,节约资财,恢复经济;晋的经济实力本来就很薄弱,所以这道禁令依旧被沿用着。虽然执行上可能不一定很严格,但刻碑风气大体上还是被制止了。
这个历史偶然事件使得书法家们另辟蹊径,改变了书写的方法,把字用毛笔写在绢上或纸上。这与刻在碑上,是很不相同的,于是西晋尺牍形成了与碑版不同的书风。魏晋书家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与王献之,他们的出现使中国书法的面貌为之一新。王羲之的书法与他的人品一样,呈现出来的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风神姿貌,是魏晋风度在书法上的生动体现。
这个时期,在书法美学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书论专着,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王僧虔的《笔意赞》:“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相忘,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⑥王僧虔把书法分为“神采”与“形质”,很显然,书法中的“神采”与“形质”是分不开的,但是,有些书法有“形质”却谈不上有“神采”,王僧虔认为,这样的书法是没有审美价值的,因为它不能给人以真正的美感。只有既有“形质”更有“神采”的书法作品,才可能给人以真正的美感。
王僧虔的书法贵在富有神采的见解,显然是与当时的人们论艺重精神是一致的。“神采”不同于“形质”,虽然它是通过“形质”而体现出来的,但它却不像“形质”是具体的“有”,它也是“有”,但却像“无”,一种不可以形求无法言说的空灵玄妙的精神或境界。王僧虔对书法创作也谈了自己的理解。作为创作主体,书写者书写时必须达到一种心手双畅、心手两忘的境地,这样才可能真正抒心写意,笔下流美,创作出富有“神采”的书法作品来。
汉代也有人曾对书法艺术发表过较好的意见。如杨雄在《法言·问神》中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发动情乎?”①蔡邕在《笔论》中也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②这些说法都涉及到了书法的抒心写意的审美特征以及书法创作中要心手双畅的审美特点,但王僧虔的“神采”说似乎比它们说得更为通透些,这显然与王僧虔接受了魏晋人物品藻的影响有关。
七、以气为主(文章)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曹丕认为,文章的根本不在于“言”,甚至也不在于“意”,而是在于“气”.所以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③气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它被理解为是指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王充还曾用它来解释人性的差异。《论衡·率性》中说“人之善恶性,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有贤愚。”④《论衡·无形》也说“气性不均,则于体不同”⑤。
曹丕的论文显然接受了上述思想,并把它首次运用到了论文上。如“徐干时有齐气”,“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⑥,这样,曹丕就把作者个人的与元气相关的体性气质与文章中体现出的文气联系起来了。《黄帝内经·阴阳应象》说“清阳为天,浊阳为地,气分清浊。”⑦曹丕的“气有清浊”,以及刘勰的“气有刚柔”⑧,其实也就是“气分阴阳”.我们完全可以说,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就是在主张文章之美源于作者内在生命的生动表现。中国古代美学谈文章之美,往往不是以形象、言辞、音调为根本,而是强调以无形而存在的气为根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审美现象,这个现象是从曹丕开始的,之后如韩愈、苏轼等人都曾提出过文气说,这些文气说其内容虽与曹丕的不完全相同,但联系却又是十分明显的。
如韩愈就曾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⑨
八、有滋味者 ( 诗歌 )
“羊大为美”.如果说,西方的美感源起于性文化,那么,中国的美感则源起于食文化。“味”这个中国独特的审美范畴正是从“口味”、“美味”转化而来的。孔子曾用“三月不知肉味”来反衬韶乐之美,老子曾用“味无味”来形容体道的滋味。到了魏晋六朝,以“味”论艺术更趋于普遍。刘勰曾把“味”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鉴赏的重要标准,从思想内容、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方面对“味”的内含作了探讨,他的“味”明显地具有审美的性质与特点。如《隐秀》云“使玩之者无极,味之者不厌矣”,“深文隐蔚,余味曲包”⑩ ,用“味”来形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不尽之美。《体性》云:“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①。用“味”来形容扬雄作品思想情味的深长,说明扬雄的独特审美风格。而把“味”与诗联系在一起的应推南朝的钟嵘,他把诗歌的美称之为“滋味”.他在《诗品序》中这样论五言诗:“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②钟嵘这里似乎只是在谈诗体,其实这里涉及到诗歌审美的本质问题。他推举五言诗为“众作中之有滋味者”,是因为相对而言,四言诗往往“文约而意广”,而五言诗则“丰瞻而意复”,五言诗比起四言诗来,更能生动地描写客体的形象,充分地抒发作者的情感,因而比四言诗更能产生出强烈而丰富的审美效应,这也就是钟嵘所说的“滋味”.
在《诗品序》中,钟嵘从他的“滋味”说出发,对诗歌创作的动因、基础、过程以及诗歌的审美特质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诗歌的内容上,钟嵘突破了儒家事父事君的伦理规范,认为诗歌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自然产物,而春风秋月,暑雨冬寒,“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都可以是诗歌表现的具体内容。钟嵘还指出:“观古今胜语,皆由直寻。”③诗人只有从生活出发,写出了真切的生活感受,诗歌才可能具有“自然英旨”,这可以说是诗歌滋味产生的发生学基础。钟嵘还认为诗歌的“滋味”与创作时作家对“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酌而用之”也有关系。诗歌创作固然也运用“直陈”的方法,但主要还是要运用“比喻”、“象征”这样一些想象的方法,才可能创造出诗歌的“滋味”.在诗歌意象创造时,钟嵘强调,作家必须“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④。“风力”是指思想情感的力度,“丹采”则是指生动感人的辞采,钟嵘认为诗歌的审美意象只有“风力”与“丹采”互融而俱佳,才可能产生使读者“味之者无极”的审美滋味。钟嵘在《诗品序》中,还从他的“滋味”出发,对“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与“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永明体都提出批评,认为它们都背离了诗歌的审美要求,缺少“使味之者无极”的“滋味”.
钟嵘的“滋味”说,可以说是魏晋六朝诗歌美学的最高体现,他所说的诗的“滋味”基本来源于“感物而动”、“穷情写物”的创作过程以及对诗歌意象“风力”、“丹采”的审美追求。钟嵘的“滋味”说,突破汉代儒家特重政治教化作用的诗学的束缚,体现出的是魏晋六朝的诗歌审美观。钟嵘强调“风力”与“丹采”的“滋味”说,与此后的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等人提倡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诗味说、妙悟说是有着质的不同的,但却有一种历史上前后的关联。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艺术到了魏晋南北朝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时的文艺思想也开始由汉代的重视外在的社会规范而转向重视内在本体的探寻,中国美学开始与哲学美学、伦理美学、政治美学分离开来,而成为真正的文艺美学。这时除后来才出现的小说与戏曲之外,中国的古代的各种主要艺术门类都提出了自己最基础性的文艺美学的命题,而这些文艺美学命题的提出,共同地体现着那个时代“重本轻末”、“以无为本”的时代精神,并如品藻人物那样体现着对“深情”、“玄心”、“妙赏”的重视。如,音乐对“希声”的“大音”的重视与追求(王弼)⑤、对“自然”或“道”的重视与追求(嵇康),人物画对“神”的重视与追求 ( 顾恺之 )、对“气”、“韵”或“气韵”的重视与追求 ( 谢赫 ),山水画对“道”与“神”的重视与追求(宗炳与王微),园林对“趣”的重视与追求(陶潜),书法对“神采”的重视与追求(王僧虔),文章对“气”的追求(曹丕),诗歌对“滋味”的重视与追求(钟嵘)……而这些所重视与追求的又都是“本”而非“末”,都是“无”而非“有”--它们是艺术中存在着却又无法言说的玄远的精神意味。完全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艺美学才开始真正确立了起来。不再是“成教化,助人伦”,而是“为艺术而艺术”,从而体现出了一种“文艺美学”的“自觉”,而此后以“意象”与“意境”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如宗白华先生曾深刻指出的那样:“学习中国美学史,在方法上要掌握魏晋六朝这一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这个时代的诗歌、绘画、书法……对唐以后的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开启作用,而这个时代的各种艺术理论……更为后来的文学理论与绘画理论奠定了基础。”①
第三章陆九渊文艺思想的理论构成通过前文的叙述,已经对于陆九渊的主体思想有了大致的把握,也对其文艺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对于陆九渊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向来缺乏较为系统的整理。我们知道陆九渊的理论成就以心学为主要依托,对文、道、气都有一...
“文如其人”作为文艺欣赏的一种方法,古今中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有过思考,但其作为在中国有着千年历史的重大命题,古人有着非常思辨的看法。...
第一章陆九渊文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任何重要的哲学、文学以及文艺思想的诞生都不是偶然发生的结果,任何伟大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与整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陆九渊作为南宋重要的思想家,其独具一格的思想主张也一定与其生活的时代有着重要的联系。陆九...
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中的艺术思想与审美理想是当时背景下民族理想、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处于明中后期的中国在艺术上与思想上也正经历着艺术革新、思想解放的碰撞、荡涤与变革。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的自我批判总是在其自身尚未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的...
从文艺美学提出之时,作为跨学科、边缘学科的文艺美学,成为文学理论界争论的一大焦点问题之一。文艺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性学科,学科的归属是否妥帖,学科的研究范畴如何定义,诸如此类的学术问题至今仍无确切定论,而其探讨争论的过程却有助于我们对此门...
西蜀园林作为四川平原地区的地方性古典园林, 蕴含着丰富的蜀文化内涵, 同时又具有西蜀地域特色的文艺美学特征。...
方东美,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之一,作为现代新儒学代表,方东美学贯中西、自成体系,尤其在文艺美学思想方面,方东美更是成绩卓然。虽然我们看到的阐释方东美哲学思想的专着论文不少,但是,专门论述方东美文艺美学特色的论着并不多。方...
物感说是我国文艺创作理论的基础,是我国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的理论,后来的神思论、意境论是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张晶通过与西方文艺创作的神赐论、天才论、灵感论的对比指出:中国古代关于艺术思维或者说神思的来源、动因的论述则不然。它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
一、作为学科定位的争论文艺美学自诞生起,围绕它是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一直受到争论。在《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综述》中,龙辛总结了文艺美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四种观点:一是文艺美学是一般美学的分支;二是文艺美学是在审美关系中确立其对象与范围...
视频游戏将在未来5年内击败电影和电视产业,领军娱乐行业。这是网络游戏业旗手暴雪公司在美国财经杂志《巴伦周刊》网络版上发出的预言。当今,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时代,网络游戏早已成为我们身边最常见的娱乐消遣方式,受到青年一代的普遍喜爱,其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