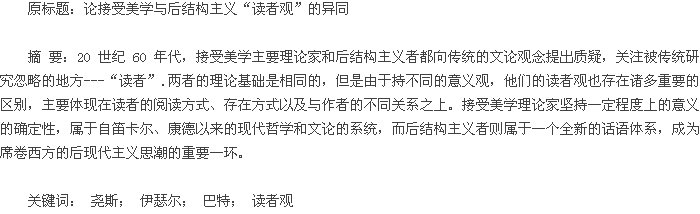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批评范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其理论关注焦点的变化上。自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对象是作者,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与“作者”相对应,作为文学活动重要一环的“读者”,还只是理论家们偶尔涉及的对象,完全是“作者”的陪衬。这种情况直到德国康斯坦茨学派那些年轻学者们异军突起才被根本改变。血气方刚的尧斯与伊瑟尔向传统的文论观念提出质疑,他们将关注的焦点指向了被传统研究忽略的地方---“读者”.差不多与他们同时,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们大声地宣称“作者之死”,认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1]507,把单一的本文发展成复数性的本文,提高了读者的功能性作用。有研究者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接受美学向整个西方批评发动冲击,后结构主义也大步迈向读者。”[2]3但是,虽然都呼唤“读者”,这两种理论各自的侧重点却并不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本文从分别作为两种学派代表的尧斯、伊瑟尔和巴特的相关观念出发,讨论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1 相同的理论基础
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从笛卡尔开始,主体性思想逐步成为哲学探讨的中心。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观念中,人即主体,是自我和世界意义的确立者,这种观点投射到文学理论中来,与作者的权威性相呼应: 作者是文本的本源,文本是被创造者,没有作者就没有文本。这种批评模式与神学模式相比,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并不是不存在问题。
作者中心论的哲学基础---理性宇宙观建立在笛卡尔“我思”主体之上,在这种乐观的图景中,人可以凭借理性认清世界,把握严密有序的宇宙结构。与之相应审美的世界也是理性的,作者就是高踞于王位上的国王。19 世纪之后,人们开始质疑这种理性中心的模式,认识到世界是纷纭复杂的、多面而又易变,单一的理性结构看似宏大、严谨、完美,其实却充满了漏洞与缝隙。自信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能力是无限的,可事实上它不但不能帮人全面把握世界,甚至无法让人真正认识自己。
现代以来的哲学的重要的主题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无论是笛卡尔还是康德,抑或胡塞尔,他们都没有逃避“唯我论”的指责,从而都没有很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主题。笛卡尔的沉思开辟了人类认识论的新篇章,“我思”主体成为意识的中心和基础,这一步被胡塞尔所继承并进一步化约,剩下的只有自我自己的领域本身。胡塞尔晚年提出了“他人”问题,他把他人设想为我的原初世界的意蕴,这样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人的原初领域与我的一样是一种先验意识的结果,主体便可以通过移情作用向一种先验的主体间性敞开了大门。可是正如多尔迈所批评的那样: “这种先验的主体间性仅仅是由我自己的意向性之源所培育起来的。”[3]46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对老师哲学中的先验性和唯我论很是不满,最终他与老师分道扬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重新思考存在的问题以及主体与他人的关系。海德格尔的思想对 20 世纪哲学、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存在与时间》中在世之存在与共在的思想,为主体间性理论的推进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这种影响再通过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折射到文学理论领域,其至为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读者终于出现,成为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比如海德格尔指出:“对在世存在的解释已经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作为一种出发点或作为一种既定实体的无世界的纯粹主体。同样,我们也不能把自我作为一种没有他人的原则既定的孤立自我来处理。”[3]65因为“这个世界的世界性结构蕴涵着,他人首先并不是作为自由漂浮的主体或与其他客体并列的自我而被既定的,而是在他们不同的世界性地位上,他们显露于上手的生活情景之中。”他人不是既定的,不是自我主体的派生物,而是自我主体在共在世界中的遭遇者,对于文学来说,与作者( 自我主体) 在上手的生活情景之中( 作品) 中遭遇的他人,当然就是读者了。
2 不同的意义观使得各自的读者观呈现不同的方式
哲学基础的变革成为读者进入文学史的重要契机,但是由于各自理论渊源、取向的不尽相同,接受美学和后结构主义者们的读者观体现了诸多重要的区别。前者主要是接受了伽达默尔阐释学以及英伽登美学的影响,注重主体间性的建构,而后者则更多地受到非理性思潮的影响。而对两者的读者观影响最直接的便是他们持不同的意义观。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阐释者的地位与文本的地位是平等的,两者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视野,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一个人与他的谈话伙伴”的关系一样[4]490.
只有当解释者与文本的视野融合时,理解才会产生,而这种“视野的融合”,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4]377.尧斯继承并发展了伽达默尔的视野概念,提出“期待视野”,伊瑟尔则提出了“召唤结构”说,认为本文作为一个具有意向性活动的结构提供了读者创造性阅读的前提和条件,真正的美或审美还有待于读者的参与才能最终实现,这最终完成物才是作品。不确定性与空白在召唤结构中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主体性就体现在他最大限度地调整自己的想象和幻想,以填补文本留下的空白。可是读者的“填空”并不代表他可以想怎么填就怎么填,必须在文本所能提供的正确范围内活动。伊瑟尔尤其强调读者在建构作品时必须保持其内在的一致性,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 “按照伊瑟尔显然权威主义的说法,不定因素必须被正常化',亦即使其驯服并且屈从于某一坚固的意义结构,读者似乎是既在解释作品也在与作品作战,以奋力将作品的混乱的多义潜能固定在某个易于驾驭的框架之内。”[5]79以巴特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认为存在着什么确定的意义,哪怕这种意义只是相对确定。对于巴特他们来讲,意义消解并沦为文字的游戏。在能指的不断滑动和游移中,一切坚固的意义都烟消云散。写作对于巴特来说,就像是“编织”,编织的产品是多元化意义的巨大网络,没有开始更没有终结。作者被放逐,不再是作品意义的源头,文本自成系统,独立于现实世界,是无穷无尽的能指链,能指总是处于滑动中,意义被无限期延宕。
因为对于意义持不同的态度,接受美学的读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读者的阅读方式和存在方式也是不同的。尧斯说过,“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注定是为接收者而创作的”[6]23.对于尧斯来说,不存在抽象的、超验的读者,读者总是具体的、现实的,在活生生的历史中与文本相遇。读者的位置是由社会和历史决定的,他们解释文学作品的方式也受这种位置的影响。由于作品的世界与读者的世界不会完全相同,读者在阅读时需要充分发挥能动作用,不仅要调动生活经验,还要调动想象力,这样一来读者在理解文本时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但这种想象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而是在特定的媒介---语言符号中展开,将文本语言转化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接受主义者的读者是历史意义中的读者,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特经验,有喜怒哀乐。与这种读者比起来,后结构主义的读者“是个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仅仅是在某个范围内将作品的所有构造痕迹汇集在一起的某个人。”[7]135巴特在《S/Z》一书中这样描述“读者”:“这个探究文的”我“,本身就已经成为其他诸文的复数性( pluralité) ,成为永不终止的( in-finis) 符码的复数性,或更确切地说: 成为失落了( 失落其起源) 的符码的复数性。”[8]69在巴特这里读者本身也是一个文本,由无限多的符码构成。他不是具有源发意义的解释的中心,只是一个功能性的结构。
与接受美学者们寻求稳定的意义不同,巴特显然是在消解意义。在《S/Z》中,他区分了两种文本。
一种是“可读的”文本,这是一种定型的文本,具有稳定、统一并且确定的意义,这种文本正是巴特要予以抛弃的,他所心仪的是与之相对应的一种“可写的”文本,它不存在封闭而又统一的意义,处于读者阅读实践之中,是一种未完成结构,等待着读者去再发现和生产意义,因此为读者的“重写”留下了无限的空间。不过读者只是阅读游戏的一个部分,是文本实现自身的一个通道,他所发现的意义,虽然不是由作者确定,但也不是读者自己确定,而是由游戏的过程和体系所确定[9].文本就在这种阅读的游戏中获得推进,读者只是阅读游戏为了实现自身、完成自身所不得不依靠的一个工具而已。读者不同,游戏也就发生变化,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任何终极意义都不存在,或者至少会被不断拖延下去。
3 与作者的关系不同
针对罗兰·巴特《文之悦》中所提出的“色情学”,尧斯曾经明确加以批评,认为这种“色情学”只属于学者的自娱自乐。他认为: “( 巴特) 实际上把审美欲望减缩为语言交流的愉悦,……他最高的幸福最终不过是重新发现了思考的语文学家的自我和他平静的隐衷词的乐园.”[6]357这是两种流派直接交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但并没有引起巴特的回应。
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德国的接受美学都属于革命性的理论,前者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既消解了作者,同时也将读者抽空,读者失去了历史和个性,只剩下了游戏的能指。后者将现实的、具体的读者提到了舞台中心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伊瑟尔将读者分为“现实的读者”和“隐含的读者”,前者是现实生活情境中实际存在的读者,这一点与尧斯是相通的; “隐含的读者”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一般认为它是一种本文条件,或者是一种意义产生过程,而不是历史情境中实际存在的读者,看上去似乎与后结构主义者的主张相同。但是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中,读者的出现并没有否定作者的存在,而是肯定作者---文本---读者的相互作用,作为完整文学活动中的一环,谁也不可或缺。尧斯宣称: “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即从作者与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6]339伊瑟尔“隐含的读者”概念更是在立足于作者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它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动力学结构,植根于作者创作、构思的过程之中。
伊瑟尔在《隐含的读者》这本书中指出在思考文学作品时,人们必须考虑具体的文本和涉及该文本的反应活动。文学作品具有两极: 作者创造了“艺术的”一极,读者则实现了作品的“审美的”一极。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仅仅看成是文本或涉及该文本的反应活动,事实上“作品处于两者之间”,“有待于文本和读者的会合”,是“写定的文本和具有各自特殊的历史和经验、意识和见解的读者相遇的产物”[10]284.阅读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带有创造性的活动,它使得文本成为作品,并且使得文本内在的动力品格得以实现。伊瑟尔依靠英伽登的“意图句相关物”理论,英伽登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一系列的句子并不指向它之外的任何客观现实,事实上这些句子的合成指向“一个特别的世界”,这个世界只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伊瑟尔对英伽登略作修改,认为这些句子间的联系并不是由作品确定的,而是由作者、读者共同确定,因为在任何文学作品中句子“都有弦外之音”.在这里,伊瑟尔并没有因为强调读者而取消作者,读者与作者是合作的关系,作者创造出了文本,但作者并没有完全实现作品,他在文本中留下了很多“缝隙”,并且使用了各种技巧、手法来限制这些没有完成的“缝隙”,而读者则需要调动自己的想象来使之充实。
以上从几个角度探讨了接受美学理论家与后结构主义者的“读者观”的联系与区别,我们可以说,相比起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接受美学理论家还属于自笛卡尔、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和文论的系统,因为他们仍然坚持一定程度上的意义的确定性,而后结构主义者则属于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成为席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环。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西方理论界,尤其在德国之外,接受美学的影响要比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暗淡许多。
参考文献:
[1]巴特。 作者之死[C]/ /赵毅衡。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金元浦。 接受反应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3]多迈尔。 主体性的黄昏[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尧斯,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7]汪民安。 谁是罗兰·巴特[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8]罗兰·巴尔特。 S/Z[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李天道。 中国古代美学之自然审美意识[J]. 天府新论,2014( 5) :148 -153.
所谓接受理论是以读者的解读活动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它认为作为解读对象的文学文本,不是由作家独创的,而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文本中的审美现实只有在读者的解读接受中才能实现为有生命的审美现实。在它看来,真正不朽的作品并不只是作家个人的产...
一部好的英文悬疑电影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首先要有吸引观众的汉语片名。电影片名让观众对电影有一个大致了解,因此,英文悬疑电影名的汉译十分重要。...
0引言:陌生化理论陌生化,又称奇异化、反常化,是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论中最具原创性的概念。陌生化是指有意识地使被感知对象变得困难,使它和读者原有的体验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使意义的获得变得艰涩,延长了读者对形象的体验过程[1]。日常语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