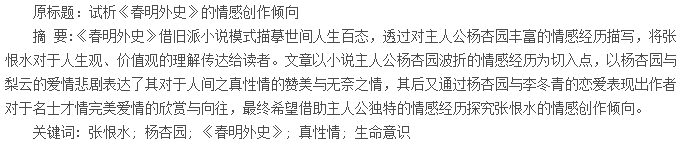
张恨水,这位曾被老舍先生赞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以其洋洋洒洒上千万言的创作位列中国现代作家最多产者之中。无论是其早期长篇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名士才情、市民趣味,还是后期中短篇讽刺小说表现出来的犀利透彻,都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摸不去的印记。对于张恨水的理解,有学者将其归位于“旧派言情小说家”或者“鸳鸯蝴蝶派作家”,认为他对于世界人生的认识在当时恰恰被新文学予以否定; 也有评论家把他看作“紧跟时代潮流的先锋”,认为其篇篇讽刺小说无不揭露时弊、挥斥罪恶。张恨水出身将门行伍之家,因此他会自然流露出除暴安良结贫济世的豪侠气质,日后的报人身份更赋予其针砭时弊的历史责任感; 而旧式传统教育的熏陶加之其对明清言情小说与生俱来的偏爱,又使他结下了浓得化不开的名士情结。但无论是张恨水自家所言还是个人好恶,他早期创作的传统章回体小说似乎更经得起历史的沉积,尤以那部耗时五年之久的《春明外史》为甚。
《春明外史》,这部自 1924 年 4 月起就在北京《世界晚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不久就引起了文坛和社会的广泛注意,而它也成为张恨水创作道路上的一座界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日后漫长的创作生涯。张恨水于创作之初,希冀借助旧派的小说模式描摹世间人生百态,“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条路子”[1],但随着小说连载五年97 万字的漫长创作历程,作品所体现出来作者创作中的热情与冷漠,严谨间或散漫,执着追求和思维矛盾,以及对于社会、人生诸多无奈所流露出的清高脱俗亦或沮丧避世的情绪,是张恨水始料不及的。而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结合体,恰恰由小说主人公杨杏园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串联而成,这也印证了张恨水创作伊始的体悟: “我写《春明外史》的起初,我就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这样的写法,自然是比较吃力,不过这对读者,还有一个主角故事去摸索,趣味是浓厚些的”[1]。应该说在主人公杨杏园身上,张恨水确是倾注了他所有的创作激情,他甚至把主人公构思成另外一个自己,期图在文字的世界中去尝试异样的人生。所以,无论家世背景、报人身份还是所见所闻,杨杏园都代表另一个张恨水在实践着他所走过的人生历程。而透过小说对杨杏园的描写,张恨水早先的创作激情、创作倾向和主张正在点点滴滴流露给读者,得让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有幸感受作者对于世界、价值、人生、爱情的理解。在此,仅以小说主人公杨杏园短暂一生中波折的情感经历为切入点,探究张恨水独特的创作倾向。
1 初次恋爱———对于人间之真性情的赞美与无奈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似乎更能体现出中国言情小说转型过程中的典型特征。
“言情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描写情为主,但他又不同于描写一般人的七情六欲,而是着笔于男女之间各色真挚的感情经历。《春明外史》,一方面代表了民国时期世情小说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于社会时势深刻而冷静的思考与把握。小说在言社会百态的过程中,加入了浓重的“情”的砝码,使得这部言情小说自创作之初就具备了与众不同的鲜活性。
《春明外史》以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铺排开去,描绘了上至总统议长,下到学生记者的人间万象,融言与情、市与井于一炉,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作者在描写种种男女真爱时,无论是杨杏园与梨云真挚的情欲之爱以及与冬青以诗为媒的精神寄托,还是何剑尘与妓女花君终成眷属的美满姻缘,或者种种师生、叔侄甚至同性之间的情感经历,只要是恋爱双方的爱情以真性情付出、以真心对待,作者多以主观、宽容的笔法自然记录各色主人公情感的发展历程,甚至不惜忽略传统伦理纲常,行文也显得流畅自然且富有文才。且不论小说中所描绘的种种乱伦、私奔、移情之事,单看五旬老太一句: “我来世还是处女,你只要把处女还我则不追究”,就能凸显出张恨水在对待男女之间的真性情时所表现的那份宽容甚至欣赏之情,这却与当时主流的时代取向格格不入了。而与此同时,作者在描写揭露官宦、乡绅、军阀、文人欺瞒诈骗鱼肉乡里时,虽深入透彻入木三分,却不时让人感觉有些松散、拖沓进而流露出作者在描写此类人物时带有的客观厌烦之心理倾向。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此时的张恨水在创作中多带有一种追求人间快乐、享受人生幸福的情感倾向,对于世间的种种真性情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甚至赞赏之意。这一切,首先在主人公杨杏园与妓女梨云真挚的爱情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小说开篇,张恨水就预期为主人公设定了性格特征以及最终的命运皈依。
“春来总是负啼鹃,披发逃名一惘然!
除死已无销恨术,此生可有送穷年?
丈夫不顾嗟来食,养母何须造孽钱。
遮莫闻鸡中夜起,前程终让祖生鞭。”
开篇的短短几句诗就含蓄地诉出了主人公短暂的一生,它寓意了杨杏园的满腹牢骚,又彰显了其高远的志向。杨杏园,一个处于半旧半新状态中的人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清高脱俗,因此总是极力避开功名利禄; 他一人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却自尊心极强、洁身自好,不愿得到分毫不义之财或受人怜悯; 他贫困而又厌世、痛恨这个丑陋的世界,因此尽管生活贫寒恶劣,却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而梨云,这个京城松竹班的雏妓,虽是“清倌人”却“小鸟依人,很是可爱”,仅仅“微微的一笑”,就让那名士才子“心里不免一动”了,随后也就开始了他们真挚缠绵却凄凉哀伤的爱情历程。两人的恋情成就了小说前半部分的故事线索,而他们之间由相识相恋到结束,又延续了历来“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杨杏园“立志甚佳”,开篇便以“才子”身份出现,而梨云虽为“风尘沦落的佳人”,却清纯美丽不染恶俗,连杏园初见时都不觉称赞她“不愧梨云二字”。这段青年才子佳人的恋情在当时社会境遇之下尚存生机并让人满怀希望,只不过张恨水戏剧性的将其安排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妓院,因此纵使二人拥有纯情、高雅的爱情,也最终抵挡不住历史沉积、伦理道德意识所赋予这段凄美爱情故事的最终结局,唯有以“遗憾”二字收场。
不可否认,杨杏园绝非风流才子且留恋烟花柳巷之人,他与梨云的爱情虽说含有青楼的遗憾,却是由“怜”生“爱”,继而寻找真挚的情感寄托,以红颜知己疗救孤身羁旅异域的苦闷与荒凉。与梨云的恋爱,一方面使杨杏园初次品尝到了情与欲的人间快乐,另一方面也让他找寻到了精神的暂时寄托。可以说他们的爱情是纯洁,作者在描写时也有意识的剔除了妓院情景中常常出现的猥亵场面,这种“才子文人 +恬静倌伶”的格局设计也为小说增添了几分高雅娴静的气氛。但无论是旧时的焦仲卿、《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直至杨杏园,因其深受传统伦理道德操守的影响,另外受制于经济上的拮据无助,致使他们注定将要辜负女子的一片倾心。杨杏园用情至深至专,但他既无力为梨云赎身又抵抗不了老鸨从中作梗,一场至情至爱只能如水中月一般,徒然终了。
当杨杏园面对故事的发展,或者说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番结果,一切竟然来得似乎有些平淡且自然。也许由于作者在杨杏园身上所必然体现出来的传统道德意识,或者说由于作者本人时年已经历了重重人生磨难、饱偿人间心酸、参透人生悲苦,因此在他的笔下,主人公的情感世界虽注定坎坷,却没有太大的疾风骤雨式的情感激流: 思念佳人时,翻开枕边的六寸照片廖解相思; 看到剑尘与花君喜结良缘时虽不免触景生情也只不过松竹班一聚,仅此而以。
不难看出,此时的杨杏园,还没有柔石《二月》中萧涧秋那种以“爱”来拯救世界、唤醒女性的意识和信念。但惟有如此,他的无奈以及最终的悲剧才更加触及到同时代普通知识分子的心扉。对于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同杨杏园一样,凭借某种理想去救世,而其所能及的,只不过是在保持自己人格的情形下,安心的混口饭吃,过上太平的日子,干一点个人的事业而以。
虽说杏园恋着梨云,梨云也深爱杏园,但仅就一张六寸照片和那半旧不新的大红结子是无力促成这段姻缘的。既然生无望结合,那梨云注定是要死的,也实在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也惟有如此结局,才能衬出二人精神恋爱的纯洁,显现出杏园的一片痴情。
另外,也许就连作者也无从把握这段爱情的最终结局,唯有让梨云一死才能了却这段本来可能就错位的尘缘,还杏园一份安心罢了。如果说活着的梨云因为杏园无能为力的辜负而黯然神伤的话,那么死去的她倘若看到先生绞心裂肺的悲伤以及义园墓碑上“未婚妻”三个字时,想必倒也可以瞑目了。不要说杏园的一班朋友故人,就连松竹班的姐妹们甚至“风流场上的恶魔”老鸨“无锡老三”都被杏园的痴情所感动,直说梨云有此知己“死也值了”。
当杨杏园在经历了梨云短暂的人生悲剧之后,作者似乎并没有让主人公或者读者走出困苦与悲剧: 短暂的梨云终于以“清倌儿”之身入葬义园,而留下形影相吊的杏园一人,最终沉湎于佛学,也就预示了其最终应有的结局。此时的义园冷风萧瑟,谁又能想到不久也将有一位才子入主此地呢? 无独有偶,就像京华的陶然亭见证了石评梅与高君宇无限遗憾的爱情一般,它也同样永远留住了杨杏园短暂的生命感慨。也许此时只有张恨水最明白,处于当时特定生存境遇的人们,是无从且无力寻找出路的,更不消说那寂寞寥落的凡夫儒生和生就命苦的青楼女子了。
也许正是由于死亡的存在,现实世界对于主体来说也如同另一个荒诞的世界。写作对于张恨水来说似乎是一种对于现实的超脱,而他把读者读小说也看作另一种对于现实的超脱方式。因此,此时的张恨水从未设想可以把小说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以期图通过小说对黑暗社会起到鞭挞作用,对劳苦大众产生革命者希望的影响———帮助他们翻身革命,推翻整个黑暗的社会。他虽然也觉得社会黑暗、痛恨腐朽统治,但他还是不太相信小说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也不相信自己一个小说家就具有改造社会的本事。在此,他借杨杏园之身,表达了如同周瘦鹃一样的设想: “既然现实是如此荒诞,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痛苦,需要解脱; 为什么我不选择写作来减轻我的痛苦,为什么我不能提供一些作品来帮助读者解脱现实的苦难呢?”[3]也许正是源于他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这种创作倾向,使得此时《春明外史》的写作显现的如此自然流畅、信手拈来。而日后张恨水的系列反映时代特色的小说创作,虽也功力十足,但或许因为某种功力目的而显得有些晦涩生硬,此处不肖说了。
2 再次恋情———名士才情的欣赏、向往直至破产
如果说张恨水把杨杏园与梨云的爱情看作人间真性情的象征与寄托,那么小说后来出现的女主人公李冬青则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名士才情完美爱情的欣赏与向往。而李冬青身上所流出来的精神气质,也让杨杏园在梨云身上留下的遗憾与缺失得到了另外的补偿。杨杏园与梨云的爱情悲剧,放在任何时代背景中,杏园仍旧多情,梨云注定命运波折,老鸨也必然会成为二人之间最直接的障碍,这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侧重描写的也多是“人情”。而随着李冬青以及她那本《花间集》的出现,直至杨杏园与之相识、相恋,一步步情感历程都深深烙下了时代的印记。可以说,脱离了民国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离开张恨水超逸淡薄的名士趣味,杨杏园不可能与李冬青相恋,李冬青同样不可能视杨杏园为知己,因此,比起与梨云的爱恋,张恨水于杨李二人的这段情缘中更多的则是抒发了他对于“世情”的感怀。
“拈韵迎春诗情消小恙,放怀守岁旅感寄微醺”[4],单凭一本遗失民间的《花间集》,李冬青的出场虽说不免有些平淡甚至俗套,但与梨云刚出场时给人的感觉却是完全不同的。与梨云的亮丽不同,李冬青自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淡雅朴素的感觉,令杨杏园“很是佩服”。一句“佩服”,以及日后由此衍生出的好感直至日久生情,一方面说明两人感情的发展自始至终就是建立在平等的相互的基础上的,这与杨杏园对梨云的由“怜”生“爱”的感情模式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花间集》上的涓秀字迹和明丽的诗句让杨杏园首次感觉到了才气相通的快乐,这也使得正处在失去梨云的失意中的他“身上新的半个生命就活了起来”。因此,在张恨水精心布局巧妙构思之中,两人以诗为媒,在慢慢疏缓的接触中由文生情,由情生爱,感觉文气相通、情投意合,彼此也顺水推舟有了感情的发展。但作者在此时却让冬青以终身的暗疾为由只肯与杏园兄妹相称,并有意安排义妹史科莲代替自己与杏园结此良缘; 而此时的杨杏园也因深情遭拒,使多情善感的他再一次面对感情的打击。爱上梨云虽让杨杏园感受到了惺惺相吸的快乐,但身为文人的他似乎更加钟情于与李冬青的情投意合。可是面对两人在爱情、婚姻上的无法沟通,杨杏园最终心灰意懒,期图借佛学来疗救痛苦逃避现实。他表面装作十分彻悟,实则极其忧伤,原本就体弱多病,终于一病不起,客死京华。
在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路的牵引下,杨杏园不仅要负担起家庭的责任,更以济世报国为己任,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但与此同时人类又是渴望自由舒展的生灵,除了追求外在的价值理想之外,他们更注重的似乎还是自我内在的自由丰富发展。倘若前者是出自于责任良知,那么后者则源于人之本性的追求。对于杨杏园来说,和李冬青的交往似乎更似一缕无从斩断的情丝,他既能抚慰其入世沧桑情感受创的身心,又不时给予他自在悠远的人生回味,使他的心灵能够得到哪怕短暂的净化与提升。在那个急功近利的年代,能让杏园暂且远离人世的纷争、权利的掠夺,在其倾心向往的淡薄飘逸中领略人生难得的情味实属不易,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冬青的离去能够让杨杏园从此心灰意冷而遁入空门! 因为她选择离开,不仅带走了杨杏园对于美好情致的向往,更最终破灭了他抵御污世的决心和力量。
也许孤独和寂寞始终都要伴随着杨杏园短暂的一生,而原本就处在孤苦无助的地位,使他此生注定无法逃避笼罩在其头上的悲剧命运。杨杏园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孤寂无助的处境,同时也借此爱情悲剧寄托了作者自身了然无望的生活情趣。仅以张恨水 1931 年所创作的《满江红》自序就颇能说明他写作《春明外史》时流露的创作倾向:“《满江红》何为而作也? 为艺术家悲愤无所依托而作也。韩愈有言: 文以穷而后工,扩而充之,以言于文艺界,又何莫不尔? ……物不得其平则鸣,世之艺术家,而贫,而病,而卒至倦狂玩世,为社会疾病而无所树立,岂无帮哉?”。
由此可见,张恨水清晰地道出了他对于爱情悲剧的寄托意味,恰如《离骚》中的香草美人一般。也许在今天看来这种寄托方式已近乎陈旧,今时今日的读者也不免对此产生隔膜。但倘若退回到民国时年,能够领会这层意思的共鸣者恐怕不在少数,它所展现出来的人物一系列悲剧命运,也早已超过了艺术家本身。试想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若不为官经商而选择教书、学术,亦或搞工程建筑、行医救人,要想保持自身人格,哪个不是怀才不遇,“悲愤无所依托”? 由此可见,《春明外史》的一纸风行,与读者“共掬一把同情之累”的情感共鸣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个作家主观思想上一心寻求超脱现实,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要经历诸多困惑和无奈。在《春明外史》的创作中,当他描绘整个乌烟瘴气的黑暗社会时,常常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看透世间一切的从容感,同时也会在笔端自然流露出面对阴暗丑恶社会时的痛苦与无奈。儒家思想的伦理教训使他曾经希图通过伦理道德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虽然他也批判儒家训条但却从未否定过道德和理性的社会价值尺度。因此,无论是张恨水还是杨杏园,当他们心中的这份痛苦无处排解时,唯有借佛禅来片刻疗救那濒临死去的心。
3 结语
身处政治局势敏感多变的民国时期,遵循传统依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但时代浪潮的强烈冲击又使他们不得不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杨杏园便是其中的代表,《春明外史》也多流露出类似的主题。不可否认,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有充分的理由批评《春明外史》所流露出的旧意识、旧手法,因为在当时它们是属于将被历史所淘汰的不良因素。然而,试想杨杏园倘若真的被新意识、新觉悟所左右,他便将立即失去他的读者群,小说的社会影响也将只及于少数文化觉悟较高的社会层次。张恨水此时的思想认识和创作倾向正是适应了由旧转新的社会阶层,也就成就了自然浑成的杨杏园。作者此时正是借杨杏园之身寄托了自己于现实中无法抒发的情怀,而《春明外史》更是自然透彻的体现出影响他余生的主要创作倾向。恰如茅盾于 1946 年在《关于吕梁英雄传》的对于张恨水章回体小说的评价一般: “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7]。
参考文献:
[1] 张恨水. 写作生涯回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5.
[2] 张恨水. 春明外史( 上卷)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1.
[3] 袁进. 小说奇才张恨水[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90.
[4] 张恨水. 春明外史( 下卷)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212.
[5] 王玉佩. 张恨水散文( 第 3 卷)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18.
[6] 茅盾. 茅盾全集( 第二十四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34.
冰心被誉为伟大的讴歌爱的作家,她努力地构筑她的爱的哲学体系,高举爱母亲,爱孩子,爱大自然的旗帜,一路走来,满怀爱心进行创作,着意描写母爱的博大深沉,友情的无私真挚,亲情的温暖感人因此她是当之无愧的闺秀派作家。她的作品飘洒出淡淡的幽香,清丽...
融媒体环境下,网络文学的发展具有一些突出特点,这也是网络文学能够越来越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但是融媒体环境下也会给网络文学的传播与发展造成一定阻碍,比如网络文学作者的着作权没有保障,盗版现象很严重,而且网络文学内容还存在同质化问题,无法体现...
摘要本文通过对作品中有关地域文化、支撑作品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吕氏乡约》的背景描述,对人物形象及其命运的分析和解读,揭示在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人生命运的必然性,展现作品揭示的有关民族命运的主题。全文共分四部分,具...
目录中文摘要Abstract绪论第一节传统乡土伦理的特点及内涵第二节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第三节孙惠芬的乡土情结及乡土世界第一章乡村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异第一节尊卑失序的孝悌关系第二节冲突升级的婆媳关系第三节琴瑟失和的夫妻关系第二章乡...
徐则臣的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讲述的主体是几个来自南方乡村的“京漂”,和以往写“京漂”的小说不同的是,《如果大雪封门》写的绝不仅仅只是“京漂”生活中的艰难与挣扎,这篇小说更大的闪光点反而在于它写出了困窘现实生活里折射出的“京漂”内心纯粹的理...
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很多作家们都喜欢立足于封建社会,对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进行描写,以揭示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残酷,表达自己或爱或憎或批判的思想情感。...
作为金庸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周伯通和黄蓉既有一定共性,又各禀个性。周伯通身凝“真人”品格,将游世精神发挥到极致,而黄蓉广汲先贤之长,且加以融通,在人格层面可以与传统的“圣人”互映。“真人”和“圣人”固然有别,但金庸笔下周伯通和黄蓉的互动,...
摘要作为新感觉派的重要作家,穆时英在小说文本中给我们呈现了一种别样而丰富的都市体验。这种都市体验无疑受制于上海半殖民的历史文化语境。穆时英正是在这种半殖民文化语境中,以一种西化的或者是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对现代个体进行观照和剖析,为我们提供...
刘震云作为一名致力于描写普通人生活境遇的作家,不是简单地描写看似荒诞的生活,而是透过这些生活的表象,发现人们精神世界的状态。...
目录中文摘要Abstract导论第一章莫言作品中方言运用的方式第一节方言词汇的直接运用第二节方言句法的鲜活运用第三节地域声音的鲜明运用第二章莫言作品中方言运用的深层原因第一节方言运用与民间立场第二节方言运用与大地情结第三章方言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