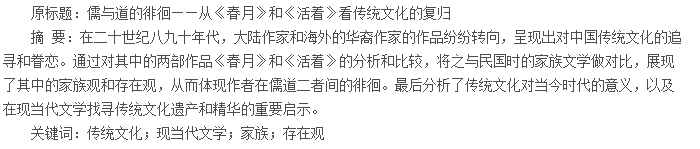
20 世纪 80 年代,华裔作家包柏漪写下描绘中国旧式家族百年兴衰的长篇小说《春月》,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成为美国最佳畅销书之一。90 年代初,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一反此前书写暴力血色与荒诞的人生的风格,以质朴的现实主义手法赞美中国人骨血中蕴含的坚韧,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好评。为何中外作家们纷纷选择了这个时间段重新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遗落的一部分?如果说包柏漪作为定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向往和怀念着她早已失落着的中华传统,故而写出了这本充满做旧与流光色调的作品,向世界展示了她心中的中华;那么余华作为接受西方现代文学(如福克纳)颇深的先锋派作家,却也在漫长的先锋写作后复归了坚实的土地。或许是因为血脉呼唤着他们,无论行走了多远,对中华的追寻永不止息。
一、对家族意义的肯定
从上古三皇五帝之时,氏族的概念就已出现,人们以结成不同的团体的形式对抗外族;到了封建社会,相同血缘的人聚居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分享荣光与困苦。家族被看成一个人的大树与依靠,记载着先祖至今的变迁与发展。从《红楼梦》到《激流三部曲》再到《四世同堂》,都讲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四世同堂》里说过:“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家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象征着没落腐朽并终将灭亡的事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的当代作品中,“家族”的形象却呈现为脉脉温情的守护者。《春月》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故事。以女主人公春月的一生串联起整个苏州张家的变迁。经历了维新变法、民国的成立、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与文革之后,春月相继失去了亲人,显赫一时的张家族人也散落在世界各地。
但是她终究等到了五世同堂,带领从各地赶来的族人汇聚在张家祖坟前,向后辈们讲述家族曾经的过往。作者在每章的开端间隔着插入了家史和族史,以家史开端并以族史结束,文言和神话的使用让行文古朴雅致,洋溢着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怀念。在开篇的家史中,“状元遂构屋于其地,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立宅门于柏树之阳,筑园墙以围之”[1]4,到了尾声里,“皆因: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此盖世之道也”[1]367,岁月的无常和道法自然的观感隐于其中,因而有人将之比作民国版的《红楼梦》。然而,《红楼梦》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天地茫茫一片真干净,而《春月》的结局是饱经磨难的张家重新聚拢在一起,孕育着新的生机。
尽管作者包柏漪成长于美国,但是《春月》中却渗透着儒家集体与家族主义的浓浓影响。儒家有坚持集体主义的传统,而强调集体主义也是儒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所说的集体是人伦的交织。所谓“人伦”,就是按照一定的高低序列形成的人际关系。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2]174在春月归宁这一节尤其能显示出对家族的依靠和家族显示出的包容:“两人都泪眼迷离,这时亲眷们和仆妇们纷纷围拢来,一面哭,一面尽力说些劝慰之词,并且对孩子百般爱抚。春月想:我到家了。”[1]155
家族如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给了失去依靠的孤儿寡母有力的支撑。而作家之所以写出了对家国故乡的眷恋,与她返乡的经历密不可分: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华裔作家看到了一个更温情和更有召唤感的中国,写下了对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回应。
《活着》创作于 90 年代初,在经历了改革的躁动与迷惘之后,余华写下了这个讲述普通人生命历程的故事。主人翁福贵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福贵一家成为佃农,自己被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建国后随着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也不断经受着苦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命。尽管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故事中每一个人都尽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安宁与幸福。
福贵的父亲因为儿子嗜赌输光家产气昏在地,醒来后仍旧变卖财物帮儿子还债;妻子家珍则抛弃富裕的娘家生活与他共患难。福贵一度想把女儿凤霞送走,却还是没有忍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3]77贯穿小说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3]67余华看似受到西方荒诞派的深刻影响,实质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可以用一种纯朴的方式传达出对家族和亲情的眷恋。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3]3因而,余华在创作了一些以暴力血腥折射人生荒诞的作品之后,笔触一转写下了《活着》。
《活着》是充满温情的,主人公福贵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维系家庭的幸福并延续下去。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从锦衣玉食中跌落的福贵开始耕作;为了守住去而复返的家珍,他懂得怜爱妻子;为了儿子的学费,他一度想卖掉女儿,却又因为渴望家庭完整而放弃;他为了让饥饿的外孙苦根填饱肚子,煮了一大锅豆子。尽管一切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家族的记忆成了他活着的支柱。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精神:“乃以‘应该’如此。至于如此之必无结果,‘道之不行’,则‘已知之矣’。”[2]55
也就是说,坚守行动的目的的正确性,而并不以行为最终的结果衡量。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4]
福贵和春月这两个人物因为“家族”的存在得到了沟通,他们都展现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儒家家族主义的珍视与坚守。
二、在有所作为和顺应天命中徘徊的存在观
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只要符合礼的事都要去做,就算难以逆转结果,因为他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55道家则倡导着一种顺应自然的存在观,因为道法自然,“惟其如此,故道可‘无为而无不为’,如《老子》所说。”[2]132《春月》和《活着》里角色的人生观,正是徘徊于儒道之间。
《春月》的故事背景是在清末民初,留学海外的张家长子回国后本打算用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改造社会,但保守势力的强大远超其想象。万般无奈的新族长重新盘起辫子,以中庸温和的方式对待族人,只把希望寄托在他悉心教导的侄女春月身上。
族长的弟弟却是坚持了儒家的入世精神,一生都作为一个军人为革命和同伴征战。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似吸收了西方的思想,骨子里却还在儒道二者的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对于女主角春月,曾有人因其坚毅的个性将她比作《飘》中的郝思嘉。然而,春月毕竟不是喊出“我是我自己”的汪子君,尽管通晓英文,她仍旧遵循顺应天命的传统伦理。
很多人从春月和伯父秉毅的不伦恋情出发,将其定义为新女性,却忽视了她处置这段感情的态度。春月接到电报后立刻返回婆家,只留下一封信,其中写明“予二人之情将长存,而向日之梦则永不可再矣。”[1]223
她最终恪守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即使这样斩断了她和秉毅的情缘,但正如春月所说“为了克己——为了尽到责任——为了名誉。”春月和女儿明玉的一场争执则更加说明了儒家施加在春月身上的影响。明玉通过跪拜让商人抵制日货,春月得知后怒不可遏,命其跪下:“回答我。没有了孝道, 还剩下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春月认为明玉的行为是对祖宗的不敬和家族的损毁。她不问人的行为是否能带来社会的进步,礼。但春月却是靠着道法自然的精神熬过人生的苦难。她将等到五世同堂看作自己的命,在族长坟前立誓:“我相信上天生我就为此。我答应等到山青水绿,风和日丽的时候,再召集族人来见你。”[1]362《活着》中的福贵更贴近道家,以平淡悠长的口吻讲述了自己苦难重重的一生。福贵在孑然一身时终于相信这是宿命,从而变得更为通达和明朗。
他没有愤世嫉俗,反而从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成了宁静温婉的人生智者,懂得了用平和坚忍的心态对待命运。或许对于福贵来说,“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 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他的这种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与‘死’的理解。”[5]
听了福贵讲述的“我”,似乎也变得更忧愁却也更睿智了。
这可谓是道家原始自然主义的圆满运用。福贵的一生中有着一次次逼近死亡的惊惧,但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死亡带来的讯息传达给后人。这其中,“余华对命运的反复播弄,死亡的如影随形,念兹在兹。”[6]
福贵的世界没有神灵可以乞求,命运遁入无形。他则从承担命运中懂得了“活着”的真谛,超越了自我。作者表面上渲染苦难,实质是赞美了生命的通达与高贵,“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智慧”[7]264包孕其中。在小说的最后,福贵和老牛渐渐远去,勾勒出一幅深沉平和的图景,在福贵如何活着这一命题上,“‘生’
战胜了‘死’,‘知命’战胜了‘宿命’。”[7]263
三、在创作中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离散文学和先锋文学纷纷以朴实追忆的姿态复归传统,企图在刚开启改革从而充满着迷惘与焦躁的文化中找寻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春月》和《活着》从而跨越了时空,通过对儒家和道家的辨析与徘徊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与资讯日益多元的今日,找寻传统文化带来的遗产与精华,应当是文学作品中仍旧大有可为的一个努力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往往着力于从西方文论和作品中找寻灵感,如对魔幻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模仿和应用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和弘扬则相对薄弱。然而只有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为当代文学作品提供了西方话语所不具备的民族品格。从而促使中国当代文学从世界文学之林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本土的现代性。“比起那些跟在外国文学后面亦步亦趋的作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与智慧的作品无疑更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意义。”[8]
那些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大多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活着》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春月》获美国图书奖提名也正是由于两位作者在作品中对儒道思想的剖析和反思。儒家由“孝、悌、信、忠、礼、义、廉、耻”组成的道德体系和道家淡泊自然、以柔克刚的精神在两部作品里交替出现,从中体现出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的冲突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弘扬传统文化容易走入“怀旧”的道路,从而使作品过于理想化及削弱批判力度。我们应当汲取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如给作品带来的敦厚温和的审美特质及精致大气的文字风格等,审视其中驳杂的部分,弘扬儒道等思想中永恒的人文精神命题——人道主义、对社会价值和自我尊严的肯定等。在超越了单纯的讴歌和反对之后,传统文化和当代审美在一定程度上重合在一起,使《春月》和《活着》两部作品实现了对现代性造成人的异化的批判。自“五四”运动以来,表面上看作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裂的现象,实则“潜意识里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体认”,这不仅是在写作手法上的传承和创新,“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努力恢复汉语的尊严”[9]。而现当代文学正是在对儒道等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古今的衔接与转换。如何熔铸古今中外,是现当代文学作家值得持续探索的一个重要命题。
参考文献:
[1] 包柏漪. 春月[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3.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 余华. 活着[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4] 王亚平. 在边缘处反抗——传统文化与余华先锋小说的写作立场[J]. 咸宁学院学报, 2006(8): 71.
[5] 胡健. 余华小说《活着》所渗透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J]. 兰州学刊, 2008(6): 95.
[6] 王德威. 当代小说二十家[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143.
[7] 王达敏. 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8] 樊星. 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J]. 图书馆论丛, 2006(3): 64.
[9] 刘文祥, 柳平, 谷新勇. 聚焦当代文学前沿问题 传承传统文化艺术精神——山东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会议综述[J]. 现代语文, 2013(1): 35.
叶梅,这位湖北恩施籍的土家族女作家,以执着自信地展现鄂西秀美神奇而又雄浑险峻的自然风光和书写鄂西土家族儿女的生存境况、精神品格及其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命运的作品名扬文坛。研究者则称其作品为土家族文化小说[1],极力挖掘其作品中所蕴涵的土家族优...
张炜是一个立足于大地的歌者,在这样一个追求物欲的时代,他的作品像一丝丝清新的风吹过文坛,而《刺猬歌》中呈现的民间意识也为文坛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指向与借鉴。一.《刺猬歌》中的民间立场与视角民间概念最早是由陈思和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
《月光》是海子的一首现代朦胧抒情诗歌。诗人于1964年出生于农村,是颇具影响力的当代青年诗人。自1982年在大学期间开始创作诗歌到1989年卧轨自杀,海子短暂的创作生涯给我们奉献了大量的诗歌作品。...
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晚清的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被打破,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被强行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殖民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应对外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着书立说表达自己对...
在钱钟书《上帝的梦》中,作者称上帝“真不愧进化出来的。他跟原始的决然不同。他全没有野蛮人初发现宇宙时的迷信和敬畏。他还保持着文明人惟我独尊的自信心。...
辽宁新宾是满族文化的故乡,那里有深厚浓郁的关东文化,连绵的群山、肥沃的黑土、风云际会的历史、波澜壮阔的现实,都在这里交汇、融通、碰撞诗人林雪以执着的热情,义无反顾地书写、表现、歌颂这块热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林雪诗歌里,故乡的意象内敛而...
在远古先民的世界里,有仇不报是难以容忍的耻辱和失职,愤怒和痛苦的折磨似乎只有通过酣畅淋漓而又血腥残忍的复仇才能得到解脱.因此复仇作为人类早期记忆的一部分,是在远古先民争取生存过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大到部落的沦陷,小到家庭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都...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池莉、刘震云、方方等一系列为代表的作家相继发表了贴近市民生活、言说世俗窘迫的作品,掀起了文学界新写实主义的热潮,在获得民众支持的同时掀起了评论界的评论热潮。新写实主义小说在大的方向上仍可归于写实主义流派,但在写实的基...
在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中,男人是世界的中心,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与权力,反而被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紧紧包裹着.《周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列子》云: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
第2章人与城的互喻:多维的都市女性世界虽然半殖民主体的都市眩晕体验显示出半殖民环境对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将人与都市的距离拉远,使人对都市产生一种排斥感。但是穆时英笔下的都市女性世界却为我们认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打开了另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