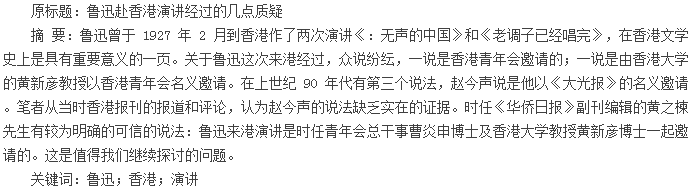
鲁迅曾于1927年2月到香港作了两次演讲:
《无声的中国》[1]和《老调子已经唱完》,[2]也曾两次路经香港,并就他对香港的所见所闻,写了三篇关于香港的文章,即《略谈香港》,[3]《再谈香港》[3]和《述香港恭祝圣诞》。[1]由于鲁迅与香港有了这样的渊源,"鲁迅与香港"也就成为学者一个热门的题目。
特别是鲁迅应邀来港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两场讲演,是香港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一直是香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课题关于鲁迅这次来港始末,刘随(即刘前度)于1981年2月7日写了《鲁迅赴港演讲琐记》[4]一文,作了这样的记述: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消息传来香港,引起广大青年和文化界人士的重视和关注。时正在香港大学教学的黄新彦博士(他曾留学美国,对文学有很深造诣,当时还兼任了香港《中华民报》总编辑),出于对鲁迅的景仰,也希望鲁迅来香港打破文坛上的沉寂空气,以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因此以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主动邀请鲁迅前来讲学。
鲁迅于二月十八日午后抵达香港,同来的还有许广平。据鲁迅日记云:"寓青年会",但据我的记忆似不寓青年会,而是住在皇后大道中的胜斯酒店,负责出面接待的除了黄新彦博士,还有黄之楝先生(时任《华侨日报》副刊编辑)和我。鲁迅在香港曾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题目是《无声的中国》,时间是鲁迅抵港当天晚上;第二次讲题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于十九日下午讲,两次都是由许广平任翻译。两次讲演会都由黄新彦博士主持。
谁知到了1993年,对谁邀请鲁迅来港演讲又有新的说法。刘蜀永先生在《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5]一文,推翻了刘随的说法。他认为鲁迅赴港演讲是赵今声先生通过叶少泉先生以《大光报》名义邀请而来的。杨国雄先生在《〈大光报〉邀请鲁迅来港演讲》中说:这次邀请鲁迅来港演讲的团体,在90年代前有两个说法:一是香港青年会;一是由香港大学的黄新彦教授出面,以香港青年会名义邀请。
在九十年代后有第三个说法,即是赵今声以《大光报》的名义邀请的。从种种迹象来看,第三个说法是比较符合事实。引起第三个说法是缘于刘蜀永教授为纪念香港大学成立80周年,编写了《一枝一叶总关情》一书,其中老校友赵今声(1952年前名为金振,为行文方便,全文称作赵今声)教授撰写的《八十八岁自述》一文,曾简介他当年邀请鲁迅来港演讲的经过,之后,当刘蜀永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得卢玮銮教授赠予其编著的《香港文学散步》一书,书内有刘随(前度)一文,说黄新彦以香港青年会名义邀请鲁迅来港演讲,刘蜀永便将刘文复印给赵今声并征询他的看法。通过书信访谈,刘蜀永撰写了《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一文,对赵的《自述》作了较大的补充,先在1993年第10期的《香港文学》刊载,后刊于《鲁迅研究》月刊。专门研究"鲁迅在广东"的课题的李伟江教授(1936-2000)与赵今声取得联系和征询后,对鲁迅来港演讲的种种问题,大体都得到合理的答复,写成了《鲁迅赴港讲演始末考》一文,刊载于2001年第3、4期的《鲁迅世界》,再由张钊贻和李桃补订,编在《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2007)一书内。两位编者觉得补订时,未能对当时的香港新闻检查制度和鲁迅的演讲稿问题解说,意犹未尽,又撰写《鲁迅在港讲演遭删禁新探》一长文,并于2008年春、夏季号的《上海鲁迅研究》上分两期刊完。[6]
这第三个说法得到某些学者的认同。
刘蜀永在《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一文中,对赵今声作了这样的介绍:赵今声教授生于一九零三年,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他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六十余载,历任河北工学院院长,天津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来(?)国内著名的港口工程专家。他从未将邀请鲁迅访港一事作为资本加以炫耀,只是到一九九一年应我们的邀请撰写自传时,才简要披露此事。
这就是说,赵今声是颇有来头的,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赵教授在《八十八岁自述》一文中忆述他当年邀请鲁迅访港经过:一九二七年春,我以《大光报》名义,邀请在中山大学讲学的鲁迅先生从广州到香港。二月十八日下午,鲁迅到港。当晚,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食堂设便宴,招待鲁迅夫妇及陪同人员叶少泉。我准备了黄酒,鲁迅先生兴致很浓,喝了好几杯。十九日下午,鲁迅在青年会礼堂为香港知识界做报告,讲题是《老调子已经唱完》。香港《大光报》及《华侨日报》均登载了他的讲话。对香港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之后,刘蜀永通过书信访谈,引述赵今声的谈话:赵今声教授说:黄新彦确有其人,我也认识,但他并未参与邀请工作,更未主持演讲会。刘文有不少漏洞。首先,鲁迅赴港演讲是我通过在广州的老乡叶少泉邀请的,并由他陪同前往。刘文根本未提叶少泉,似乎那次由广州到香港的只有鲁迅和许广平。其次,鲁迅在香港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叶少泉也住在那里,我请他们吃饭就在青年会二楼食堂。鲁迅日记中也说:"寓青年会".刘文却说他住胜斯酒店。再者,我是以《大光报》名义邀请鲁迅赴港的。刘文却说是黄新彦以基督教青年会名义邀请的。基督教青年会能邀请革命文学家鲁迅演讲吗?
这可说是一个死无对证的说法。黄新彦教授已于1985年作古,刘随、黄之楝未知是否还健在,恐再也不可能现身说法了。如果因为有来头说的话就可信,这恐怕不是做学问的态度。我们要的是真凭实据。当我们看了刘蜀永的大文,赵今声的说法漏洞更多更大,难免使人"大胆怀疑"起来。这是胡适先生教导我们做学问的方法,敢于求真就必须敢于怀疑,只要你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你的怀疑往往就是学术上的一大发现。
赵今声的说法漏洞在哪里?
第一,鲁迅和许广平当时还不是夫妇;第二,十八日晚九时,鲁迅即作了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而不是喝了几杯黄酒就醉了,就睡了。鲁迅日记,二月十八日",雨。晨上小汽船,叶少泉、苏秋宝、申君及广平同行,午后抵香港,寓青年会(注:指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香港荷李活道文武庙附近的必列啫士道街五十一号)。夜九时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广平翻译。"十九日":雨,下午演说,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广平翻译。"说得清清楚楚,更无和赵今声一起晚饭之记载。
第三,赵今声先生的说法,似乎是针对刘随的文章而发,坚持是他以《大光报》的名义邀请的,而反问道":刘(随)文却说是黄新彦以基督教青年会名义邀请的。基督教青年会能邀请革命文学家鲁迅演讲吗?"这个说法颇令人怀疑的。如果基督教青年会对鲁迅这位革命文学家有所抗拒或有所避忌的话,何以鲁迅讲演及住宿都是在青年会?事实上,《大光报》也是基督教办的报纸。青年会虽不是革命组织,但也不是反革命组织,它在世界各地,在中国各地从事社会服务,做了不少工作。周恩来也曾肯定青年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作出的贡献呢。
第四,赵今声说主持演讲会的不是黄新彦教授,而是他自己。难道刘随是大近视眼,他坐在前排(因为他要做记录)把赵今声先生误认作黄新彦教授?赵氏当时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只有23岁的小伙子,而黄氏却是一个已经36岁的大学教授,刘随竟然看错了么?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刘随先生又何必造这个假?我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我相信刘随未必认识赵今声先生,但一定认识黄新彦教授。在我看来,刘随的说法更为可信,他是一个热心的听众,可靠的见证者,认真的记录者。
第五,至于鲁迅说"寓青年会",但如果青年会宿舍不适合,而为他们一行人另作安排,住在"胜斯酒店",也非不可能的事。
第六,刘蜀永在《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港经过》又说到:"叶少泉是促成鲁迅访港的重要人物之一。
据《鲁迅日记》记载,此次赴港前,在二月五日,十日和十七日,叶少泉曾三次拜访鲁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安排鲁迅访港有关。应笔者要求,赵今声教授介绍了他与叶少泉交往的经过。"经过刘蜀永先生的这番提示,于是又产生这样一段故事:"他(赵今声)回忆说:我和叶少泉是在广州认识的……叶少泉当时四十多岁,河北保定人。"又云":叶少泉是广州国民党总部青年部的交通员,常往香港送党的宣传品。"所以经常有来往,并通过他邀请鲁迅来港。
不过我们检索百度网页时,却另有一个叶少泉,1896年生,广东省罗定市罗镜镇龙岩村人。他和蔡廷锴是同乡,又是邻居,更是莫逆之交。1922年,蔡廷锴在粤军任连长时,叶少泉便开始追随蔡廷锴。1927年,他才31岁。1930年,蔡廷锴任六十师师长,叶少泉随蔡廷锴参加了"中原大战".后为十九路军将领。
这样说来,当时在广州就有两个叶少泉:一位来自河北,40多岁,一位来自广东,30多岁,究竟和鲁迅有交往的是哪一位呢?这也是一个有待查证的问题。话再说回来,叶少泉是否是鲁迅赴港演讲的关键人物也是一个疑问,许广平是认识叶少泉的,他们和鲁迅一起赴港,后来还一起吃过饭。但她却说":曾有一位不相识的基督教徒来中大再三邀请到香港去演讲。"这又是一个存疑的问题。
我们不妨再看看《鲁迅全集》(日记和书信及其文章)有关前赴香港讲演的记载,更为可靠:一,鲁迅给孙伏园的信:寄给我的报(按:武汉《中央日报》),收到五六张,零落不全。我的《无声的中国》,已看见了,这是只可在香港说说的,浅薄得很。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讲演原定是两天,第二天是你。你没有到,便由我代替了,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一篇在香港不准注销来,我只得在《新时代》发表,今附上。梁式先生[11]的按语有点小错,经过删改的是第一篇,不是这一篇。
二,给李霁野信:前几天到香港讲演了两天,弄得头昏。
三,致章廷谦信: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四,致刘随信:前度先生:惠函敬悉。讲演稿自然可以答应先生在日报发表,今寄还。其中潜改几处,乞鉴原为幸。顺祝康健。鲁迅三月三日。原注云:刘随,又名前度,鲁迅讲演《老调子己经唱完》记录者。记录稿后来在香港报纸发表。
五,对于在香港演讲的情形,鲁迅在《略谈香港》中有这样的记述: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3](P446)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X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X府"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3](P448)
六,《鲁迅全集》有注:辰江:《谈皇仁书院》(载《语丝》第137期(1927年6月26日)。他曾亲听鲁迅在香港的演讲,在信的末段说:"前月鲁迅先生由厦大到中大,有某团体请他到青年会演说。……两天的演词都是些对于旧文学一种革新的话,原是很普通的(请鲁迅先生恕我这样说法)。但香港政府听闻他到来演说,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去问话,问为什么请鲁迅先生来演讲,有什么用意。
七,《三闲集》序言有云: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以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八,《鲁迅日记》(1927年3月15日)雨,午后李竞何,黄延凯,邓染原,陈仲章来。原注云:陈仲章,广东兴宁人。1925年任香港《大光报》编辑。1927年随友人访鲁迅。
从上述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到:
一,这就说明当时所要邀请的不只鲁迅,还有孙伏园。但在赵今声却提也没提,似乎也不知有这回事呢?要是他作为邀请者,是应该知道的,也应该提及的。
二,赵今声说他通过叶少泉以《大光报》邀请鲁迅来港,并无确凿的证据。只有时任《大光报》编辑的陈仲章随友人造访鲁迅而已。
三,赵今声先生说鲁迅的两篇讲演稿均由他整理并发表于《大光报》也成疑问,如果赵氏为两次讲演稿作了记录,照道理应先交鲁迅过目才是,刘随的记录稿就给鲁迅看过的,但赵氏却没有这样做。
即使两篇讲演稿在《大光报》发表了,应该寄给鲁迅吧,但没有,这也是有违常理的。这不是一句"疏忽"就可释疑的。如果他是主持,照理也不可能同时又作记录。如果说鲁迅赴演讲是叶少泉做的媒,在这之后,叶少泉还多次见鲁迅:二十四日,"下午叶少泉来";三月三日,"夜叶少泉来";四月一日,"午后叶少泉来";十四日,"夜黄彦远、叶少泉及二学生来访,同至陆园饮茗,并邀绍原、广平";六月十八日,"叶少泉来".如果鲁迅讲稿在香港《大光报》发表,叶少泉会不告诉鲁迅么?而鲁迅日记对刘随却有这样的记载:三月二日,"得刘前度信并稿",四日",上午覆刘前度信并还稿",并有信件为证。
四,按辰江说:香港政府听闻鲁迅到来,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去问话。如果赵今声先生是邀请鲁迅来港演讲的,应去交代的就是他,应该印象深刻,何以提也没提?
五,鲁迅这次赴港的两次演讲,香港文化界的反应是热烈的积极的。香港报纸于2月14日就以《著名学者来港演讲消息》作了报道:鲁迅与孙伏园将于2月18日联袂来港演讲,粤语翻译是同行的许广平。并说鲁迅的讲题是《新时代的少年》,时间是18日晚8时,孙伏园的讲题是《无声的中国》,时间是19日下午3时,地点均在青年会(YMCA)大会堂。而《华侨日报》更连续发表不少评论文章,17日有《鲁迅君的作风》,介绍鲁迅的新文学成就,翌日有《鲁迅先生来港》,报导鲁迅于18日晚作了《无声的中国》的演讲,而孙伏园未能来港云云。于21日发表了《无声的中国》的演讲,署"许广平女士传译,黄之楝、刘前度笔记",同时又有"周鲁迅君已离港赴省"的短讯。有署名"探秘"者于2月23日发表了《听鲁迅君演讲后之感想》,记述鲁迅第二场演讲的情况,有云:"大抵他是血性的人,所以所讲的话都含有严肃之气。这种神态,合于演讲的姿势,可不深论。但是他所发挥的话确有意在言外之妙,这是很可喜的",号召我们"创造一种新思想新文艺","与社会民众有密切关系的,然后文学方有一线曙光".此后,《华侨日报》还发表了好几篇对鲁迅演讲反应的文章:有碧痕的《文学革命》(2月25日),时济的《会晤鲁迅先生后》(2月30日),葆蓉的《我们如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了》(4月19日),绿波的《我们一致起来打破文学的阶级罢》(4月29日),等等。碧痕的文章指出:鲁迅的演词"不啻是一个暮鼓晨钟".真不知道《大光报》对鲁迅的演讲有些什么反应?发表了什么评论?赵今声先生又写了什么评论或感想?
六,陈仲章时任《大光报》编辑,既是该报邀请鲁迅的,就用不着随友人去造访鲁迅。那就是说,《大光报》并非主人家。
七,黄之楝先生时任《华侨日报》副刊编辑,作为鲁迅在港演讲的见证者,曾于1939年写了一封信给《立报》副刊"言林"澄清有关问题,编者以题为《关于鲁迅在香港的演讲》[7]发表。编者对黄氏的来信作了这样的说明:十九日本栏的鲁迅先生逝世纪念特刊,袁水拍君在《香港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提及当年鲁迅先生在本港的演讲词各报都未曾刊出,二十二日现象晚报载有吴理《致立报袁水拍君》一函,指出当年鲁迅先生在港演讲凡两次,各报都发表过,而且涉及当时笔记者黄之楝君之错误。昨日接黄君来函,对这问题有所声明。按关于笔记是否有误问题本与言林无涉,但借这机会可以改正袁水拍君所说演讲词未曾登载的错误,特为披露如下:
黄之楝先生的信是这样写的:言林编辑大鉴:关于现象晚报刊出之《致立报袁水拍君》一函,内有提及弟名,特将该时实在情形奉告。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到港演讲,系当时青年会总干事曹炎申博士及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博士所请求。鲁迅先生时寄寓青年会中,弟与刘前度先生对两次演讲都有笔记,登诸翌日之华侨日报(刘先生现为香港汉中教员),及鲁迅先生抵广州,各刊物(指广州方面的)多有论及笔记中错误,但弟十年来未提出声辩,因即有错误,责非刘先生及弟所敢担负,因弟与刘先生当时实不谙国语,系由转译笔记,当时两次演讲,约皆有五百人在座,且亦多不谙国语者,特将该时经过奉告,即代向袁水拍君声明。
黄之楝手上十月廿五日从黄之楝先生的信,可看到鲁迅来港经过的真实情况,也印证刘随先生的说法。所谓第一说法和第二个说法,事实上,只是一个说法,就是青年会总干事曹炎申博士及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博士一起邀请鲁迅来港演讲的。赵今声先生邀请鲁迅来港只是后来出现的另一个说法。我认为并不是最后说法的就是全部事实,并不就是权威,就可否定先前的说法。我"大胆怀疑"是有根据而提出的,如果没有实质的证据,这另一个说法(即所谓第三个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期待有心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的学者继续探讨。
对于鲁迅在港的两篇讲话,在他自己看来是"老生常谈"的,但对于当时的香港来说,其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对促进香港文学的向前发展是起着积极的促进的作用。鲁迅先生是高举着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而来的,所以他在《无声的中国》,他呼吁青年人应抛弃旧的僵死的语言:"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P11)这些话今日听来一样有着严肃的意义。在《老调子已经唱完》更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2](P321)对我们一样有警醒的作用。鲁迅关于香港的三篇文章:《略谈香港》、《再谈香港》和《述香港恭祝圣诞》,有着他切身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他说:"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苖瑶是我们的前辈",[3](P565)这种现象过去了么?鲁迅终竟是鲁迅,无时无地关注着中国人,特别是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和坎坷命运。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小思。香港文学散步(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刘蜀永。赵今声教授谈鲁迅访二卷经过[J].鲁迅研究月刊,1993(11):40-41.
[6]杨国雄。《大光报》邀请鲁迅来港演讲[J].文学评论(香港),2014(02)。
[7]黄之楝:关于鲁迅在香港的演讲[N].立报,1939-10-29.
一鲁镇意象与文化语境、意境的关联作为汉语的这一个,鲁迅无疑是使用汉语写作的典范,无论是情境还是社会文化语境,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制约着他,这也与他的生存习俗及其生存模式息息相关。作为汉语的这一种,鲁迅的小说文本,无论是叙事策略还是叙事审美形...
一、说出真实与说谎涓生和后羿都在人生的选择中呈现哈姆雷特式的自我挣扎,思想多于行动的延宕促成了二人的悲剧命运。对哈姆雷特而言,生存还是死亡是个问题;对涓生而言,追求理想中的新生活与麻木于现实是个问题;对后羿而言,追求个人飞仙与维护婚姻是...
意象是在过去已积累的大量表象基础上,主题头脑中新生的、超前的、意向性的设计图像。在中国,独特的文学审美作用使月亮变成一个多元综合的文化载体,一种蕴涵丰富的文化艺术符号。月亮情结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是月色如水水如天般的美丽景致,是月是故乡明那样...
李大钊和鲁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新青年》的旗帜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致力于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以及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虽然两人的文学理想和实践有所差别,但在时代的鼓动下却在现代杂文创作方面形成了共同阵线,不仅丰富了文学...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占有一席之地,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所创作的作品众多,具有重大影响,值得研究。...
鲁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革命性开拓,首先表现在他对《文心雕龙》"心力"说的历史继承和现代深化上。...
李欧梵撰《铁屋中的呐喊》(下简称《铁屋》)对大陆学界冲击力甚大,其第一缘由,是因为在他以王瑶、唐弢为代表的80前学科近乎失语的空白地带①,找到了破解鲁迅人格的钥匙,此即:鲁迅所选择的生命目的,完全不合乎那个时代知识者中着名人物如梁启超、严复、孙中山...
鲁迅先生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选材视角非常独特,常常没有过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有的是用朴实真切的语言对人物心理进行有效刻画,虽然不着痕迹,但是却又入木三分。...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写作涉及小说、散文、诗歌、议论文、杂文等多个领域,且在各个领域都建树颇丰,因此,到鲁迅的写作思想和作品中去探究写作的底层逻辑,以指导现今的写作教育是合理可行且行之有效的。...
中国鲁迅小说史学研究成就斐然,对于其探讨论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及至近期颇具代表性的青年学人鲍国华的论著《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研究》,专家学者的持续关注依然。鲁迅小说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其展示出了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研究中的开阔视野,科学方法与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