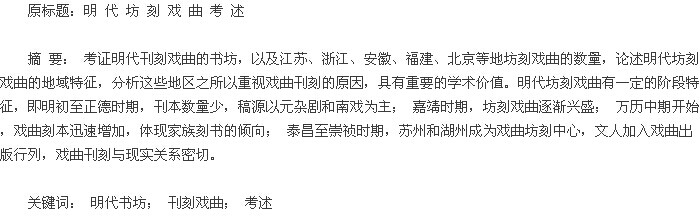
书坊,即是我国旧时书店的泛称。汉代已有专门售卖书籍的店铺; 唐代中叶,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和洛阳等地设肆刻书已很普遍; 两宋时期,书坊刻书、售书日见兴盛; 明代的书坊更为发达,坊肆遍布全国,其中戏曲刊本层出不穷,是之前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明代官刻、家刻和坊刻中均有戏曲刻本,尤其是书坊所刻戏曲,占现存明刊戏曲的绝大部分。
本文主要探讨明代书坊刊刻戏曲的概况、地域特征、阶段特征及其对戏曲文学的影响。
一、明代坊刻戏曲概况
笔者依据杜信孚和杜同书《全明全省分县刻书考》与《明代版刻综录》、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和《明代传奇全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书目,并结合笔者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图书馆所查阅的资料,统计明代书坊刊刻戏曲的情况如下:
江苏地区刊刻戏曲的书坊有 46 家,共刻戏曲230 种。俞为民在《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中认为明代南京刊刻戏曲的书坊有13 家,但据笔者统计,共有 27 家,分别是积德堂、少山堂( 胡少山) 、富春堂( 唐对溪) 、世德堂、文林阁( 唐锦池) 、广庆堂( 唐振吾) 、唐晟、德寿堂、继志斋( 陈大来) 、环翠堂( 汪廷纳) 、师俭堂( 萧腾鸿) 、文秀堂、长春堂、周敬吾、胡东唐、乌衣巷、博古堂( 周时泰) 、怀德堂( 周氏) 、丽正堂( 邓志谟) 、必自堂、汇锦堂( 孔氏) 、两衡堂、三元堂、石渠阁、天章阁、文盛堂、奎壁斋( 郑思鸣) ,括号内为书坊主人的姓名。据张秀民先生推断,明代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作品当有二三百种[2]349,笔者依据现存刊本统计为 196 种。
苏州刊刻戏曲的书坊有 19 家,包括起凤馆( 曹以杜) 、书业堂、萃锦堂、宝珠堂、毛恒所、蒸文馆、螂麟斋、叶戊廿、宁致堂、尚友堂( 安少云) 、嘉会堂( 陈勖吾) 、玉夏斋( 叶启元) 、志邺堂、柳浪馆( 袁于令) 、陈长卿、德聚堂、许自昌、周之标、汲古阁( 毛晋) ,共刻戏曲 34 种。
浙江地区刊刻戏曲的书坊有 23 家,共刻戏曲54 种。其中杭州书坊 14 家,分别是文会堂 ( 胡文焕) 、容与堂、翁文源、天绘楼、阳春堂、凝瑞堂、钟人杰、静常斋( 李氏) 、西爽堂( 吴敬、吴仲虚等) 、读书坊( 段景亭) 、安雅堂、山水邻、峥霄馆( 陆云龙) 、高一苇,共刻戏曲 32 种; 绍兴书坊有会稽县的半野堂( 商濬) ,及上虞县的泥蟠斋( 车任远) ,共刻戏曲 3种; 湖州书坊有吴兴县的雕虫馆( 臧懋循) 、茅彥徵,及乌程县的闵齐伋、闵光瑜、凌濛初、凌玄洲、凌延喜,共刻戏曲 19 种。
安徽地区刊刻戏曲的书坊有 11 家,共刻戏曲21 种。包括歙县的百岁堂、玩虎轩( 汪云鹏) 、尊生馆( 黄正位) 、敦睦堂( 张三怀) 、刘次泉、四知馆( 杨金) 、观化轩( 谢虚子) 、还雅斋( 黄德时) 、青藜馆、存诚堂( 黄裔我) ,以及休宁县的黄嘉惠。
福建地区刊刻戏曲的书坊有 28 家,共刻戏曲41 种。其中建阳书坊 26 家,分别是进贤堂、余新安、种德堂( 熊成治) 、与耕堂( 朱仁斋) 、忠正堂( 熊龙峰) 、乔山堂( 刘龙田) 、忠贤堂( 刘龙田) 、三槐堂( 王会云、王敬乔等) 、游敬泉、杨素卿 、叶志元、自新斋( 余绍崖) 、长庚馆( 余氏) 、余少江、刘龄甫、爱日堂( 蔡正河) 、陈含初、四有堂( 周静吾) 、燕石居( 熊稔寰) 、集义堂、刘应袭、崇文堂、文立堂、岁寒友、萃庆堂( 余彰德) 、清白堂,共刻戏曲 39 种。此外福州府闵县金魁、漳州府李碧峰与陈我含,共刻戏曲 2种。
北京地区仅有金台岳家弘治戊午季冬重刊印行《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及永顺堂成化八年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 陕西地区只有凤毛馆( 盛以弘) 在万历年间刊刻的顾大典撰《重校白傅青衫记》。
综合以上统计可知,明代可考的坊刻戏曲中,共有 111 家书坊,刊刻戏曲 349 种; 另外,还有所处地区不详的书坊 20 家,即春山居士、绍陶室、崇义堂、清远斋、陈晓隆、来仪山房、云林别墅、余会泉、七峰草堂、槐堂九我堂、梁台卿、岑德亨、杨龄生、纫椒兰馆、林于阁、漱玉山房、柱笏斋、映旭斋、慎馀馆、章庆堂,刊刻戏曲 20 种; 刊刻地区及书坊名称均不详者有戏曲 203 种。由此得出结论: 包括现存本、已佚本和翻刻本在内,明代坊刻戏曲共有 572 种。与此同时,笔者还对一些刊刻信息进行了订正和考证。如关于起凤馆的主人,《全明全省分县刻书考》认为是徐履道,估计是因为起凤馆所刻《沧州集》,书后有徐履道跋,但是《元本出像西厢记》有阳文方印“曹以杜印”,因此起凤馆的主人应该是曹以杜。又如《全明全省分县刻书考》认为许自昌所刻书籍为家刻本,但是笔者认为许自昌为书商。《甫里许氏家乘》收有许自昌与陈继儒的十多封信,其中谈到《唐类函》的刊刻问题,陈氏提出了建议:
其书局促不甚利益,弟半置之高阁。即使纂续,雅俗参半,前后糅杂,操翰之人,反多掊击,不如姑止之。即刻不行,即行不广。
这就充分说明许自昌刻书的出发点是畅销与否。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认为题为“梅花墅改订”的《玉茗堂批评节侠记》和《玉茗堂批评种玉记》出自同一个书坊,可能是许自昌刻印的。所言甚是,以许自昌丰富的刻书情况来看,他刊刻本人改订的戏曲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明代坊刻戏曲的地域特征
依据上述数据可知,明代南京书坊所刻戏曲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可以说,与坊刻小说不同,坊刻戏曲中心不在建阳,而在南京。笔者以为,南京成为坊刻戏曲中心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演剧之风盛行。余怀《板桥杂记》云: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王叔承在《金陵艳曲》中描写南京浓厚的歌乐之风: “春风十万户,户户有啼莺。”可见,明代南京是歌舞升平之地。杂剧、弋阳腔、青阳腔、海盐腔、昆曲都曾在南京剧坛流行。第二,戏曲创作和理论丰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物,南京的秀美山河,培育出众多群贤才俊。南京还是明朝的陪都,强大的社会背景也有利于学术团队的形成,正如梅新林先生所说: “都城( 南京) 可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转化或积淀为文学 资源”.第三,大量外地商人、文人、艺人流入南京,进行戏曲活动。据《松窗梦语》所载: “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金陵经济繁荣,吸引富商巨贾蜂拥而至。陈书录先生曾指出: “中华文化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文化,江苏正处在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因而形成了金陵文化的主要特征: 交融性、互补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南京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点,又吸引了四方来客。这些外来人口有的是寓居南京从事戏曲创作的文人; 有的是在南京开设书坊的异地商人,如徽商汪廷讷到南京开设书坊刊刻戏曲,富春堂、世德堂、师俭堂书坊都是外地人在南京所开设的; 也有到南京谋生的刻字工人,如歙县刻工多半移居南京。总之,南京戏曲稿源充足、受众广泛、出版商聚集,三者合力共同推进了戏曲坊刻的蓬勃发展。
江南交通发达、文化昌盛、士子文人众多。15世纪末,途径江南的朝鲜人崔溥曾这样描述道: “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闾里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浓厚的人文氛围使江南的戏曲创作欣欣向荣。王国维曾云: “至明中叶以后,制传奇者,以江浙人居十之七八”.因此,除了南京外,江南其他地区的戏曲刊刻也较为突出: 苏州府藏书之富,甲于天下,对于刻书来说,有助于版本校勘,提高刊本的学术含量。如毛晋就是著名的藏书家,所刻《六十种曲》是我国古代篇幅最大、流传最广的戏曲选集,与臧懋循《元曲选》堪称双璧。徽州版刻崛起,得益于刻工精湛的技艺,特别是黄氏家族的刻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常常受邀到外地刊刻戏曲。杭州书坊就喜欢聘用徽州刻工,插图风格与徽派接近,尤以容与堂为代表,图绘生动,版刻亦佳,并大多署名“李卓吾评点”,开启了名家评点戏曲的风潮。湖州位于太湖南岸,四通八达,经济雄厚,刻书业在南宋已经形成。随着雕版印刷发展,闵氏和凌氏两大富豪投入刻书业,使湖州一跃成为明末刻书业的中心,所刻戏曲善用套印技术,版刻精美,质量上乘。
江南刻书业兴起后,建阳在刊刻戏曲方面失去了优势,但是仍有不少书坊刊刻戏曲。建阳是弋阳腔、青阳腔的主要流行区,所以刊刻这两种声腔的戏曲选本占了很大比例,包括《大明春》、《全家锦囊》、《乐府菁华》、《词林一枝》、《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八能奏锦》、《乐府名词》、《尧天乐》、《徽池雅调》和《满天春》。北京作为京师之地,对书籍的需求量大,理应成为全国的图书集散地。但据史料记载,北京的书坊并不多,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统计为 13 家,[2]359且大部分并不出名。根据胡应麟《经籍会通》中“每一当吴中二,当越中三,纸贵故也”之语[12]42,很有可能是北京地区不产纸,用外地的纸张成本高,所以刻书较少,戏曲刊刻也不例外。
至于山西、山东、江西、上海、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广东等地,笔者未见明代坊刻戏曲刊本,但并不代表这些地区没有书坊刊刻戏曲,像山西平阳是宋金元时期全国四大雕版印书中心之一,戏曲艺术更是历史悠久,有“戏曲文物甲天下”之称,明代应该也有书坊刊刻戏曲,可惜均已失传。据笔者统计,现存明代无坊刻戏曲刊本但有家刻本的包括山西定襄县张宗孟刻《中山狼》; 山东李开先刻《宝剑记》、《改定元贤传奇》、《一笑散》; 江西汤显祖刻《汤海若先生批评琵琶记》、《临川四梦》,徐奋鹏刻《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刘云龙刻《昆仑奴》; 上海博山堂刻《梦花酣》、《花筵赚》和《鸳鸯棒》。
三、明代坊刻戏曲的阶段特征
戏曲刊刻史不等同于创作史。比如,邱濬《五伦全备记》、邵燦《香囊记》、沈采《千金记》、沈受先《冯京三元记》、姚茂良《双忠记》、陆采《明珠记》等作品均完成于嘉靖之前,但是要到万历年间才有刊本。笔者根据现存明刊戏曲的状况,从刊刻的角度将之分成三个阶段,并总结归纳每个阶段的特点。
前期: 明初至正德时期。现存明代前期的坊刻戏曲本仅有 3 种: 宣德十一年南京书坊积德堂刻《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永顺堂刻《白兔记》、金台岳家本《西厢记》。刊本数量少,稿源以元杂剧和南戏为主,是明初戏曲刊刻的特征,原因可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戏曲创作萧条,稿源匮乏。何良俊说:“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明初的文人鄙视戏曲文学。而且,政府为了巩固自身统治,诛杀功臣,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 在思想上倡导程朱理学,以八股文取士,凡是与程朱相违背的书籍,都遭到禁止。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创作一片沉寂,遑论通俗文学发展,书坊就算愿意刻书也缺少足够的稿源。二是明初统治者不断制定各种戏曲禁令,虽然未能遏制戏曲繁荣的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戏曲发展。关于明初颁布的戏曲禁令,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有详细记载,此不赘。从禁令可知,明初统治者对戏曲严厉控制和打击。如此繁复和残酷的刑法,使书商噤若寒蝉。就算有少数书坊敢于冒险刻书,物以稀为贵,昂贵的书价也使读者望而却步。
中期: 嘉靖、万历时期。明中叶起,政治上的严酷统治有所松弛,城市工商业勃兴,社会风气转向重文轻武。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坊刻戏曲逐渐兴盛。笔者统计,嘉靖时期刊刻戏曲有 13 种,即选本《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风月锦囊》、《杂剧十段锦》; 杂剧《璧筠斋古本北西厢》、《古本董解元西厢记》、《洞天玄记》、《梁状元不伏老》、《僧尼共犯》; 戏文《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荔枝记》、《荔镜记》。嘉靖时期的小说、戏曲作品都比较少,书坊主亲自创作小说以补充稿源,而戏曲稿源则主要来自当时的舞台表演本。像《词林摘艳》是内府演出的本子; 《风月锦囊》的全称是“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戏式”即可供演剧与观剧之用; 《荔枝记》与《荔镜记》都是适合于舞台搬演的戏文。万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已知刊刻年代的戏曲仅有 14 种,包括《西厢记》3 种,《琵琶记》2 种,杂剧选本 2 种,戏文 7 种。万历中期开始,坊刻戏曲刊本迅速增加,蔚为大观。传奇作品、戏曲选本、评点本的刊刻也都集中于此时。值得注意的是,戏曲刊刻呈现家族化倾向。比如南京著名的家族刻书有唐氏、周氏、陈氏、王姓等,刊刻戏曲的是唐姓书坊,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广庆堂均有戏曲刊本,是南京较为庞大的同族经营刻书集团; 建阳萧氏刻书比较有名,其中萧腾鸿所刻戏曲很有特点,书名一般加“鼎镌”两字,且多由陈继儒评点; 苏州叶姓一族的叶戊廿和叶启元刻有《荆钗记》和《玉夏斋传奇十种》; 杭州吴氏家族刻书中,吴敬刻有《玉茗堂乐府》,吴仲虚后人以“西爽堂”的堂号刻有《万壑清音》。
后期: 泰昌、天启至崇祯时期。天启、崇祯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明朝统治岌岌可危。但是戏曲坊刻并没有受到压制,反而借着万历的光辉继续发亮。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苏州和湖州成为戏曲坊刻中心。南京的坊刻戏曲在万历时期达到鼎盛,泰昌以后渐趋衰落。虽然也有师俭堂、汇锦堂、必自堂、两衡堂、三元堂、石渠阁、天章阁几个书坊刊刻戏曲,但是刊本很少,不能与富春堂等书坊相比。此期,苏州和湖州崛起。据笔者统计,苏州书坊除了书业堂、起凤馆、叶戊廿外,其余都是活跃于天启、崇祯年间。作为后起之秀的吴兴,闵齐伋、闵光瑜、凌濛初、凌玄洲和凌延喜虽然刻书不多,但是所刻版本甚佳。吴兴闵、凌二家长期合作刻书,难分轩轾,与江苏常熟毛氏汲古阁,构成明末坊刻戏曲的鼎足。二是更多文人加入出版行列,版刻精良。这阶段出现了集文人与刻书家于一身的所谓文人型书坊主,像闵齐伋、凌濛初和毛晋。这些文人本来靠治经起家,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鉴赏能力,加之交游广,人脉宽,这就使他们所刻刊本在文字校对、图画装饰等方面更胜一筹,成为坊刻戏曲中的善本。三是明末戏曲刊刻与现实关系密切。晚明社会风气衰败,戏曲刊刻开始侧重有关风化的作品。如毛晋指出他编选戏曲不是为了“穷耳目之官”,而是“俾天下后世启孝纳忠植节杖义”.同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得到刊刻。如崇祯刻本《喜逢春》演毛士龙忤魏阉事,《磨忠记》叙述东林党人与魏忠贤作斗争的故事。
以上是对明代坊刻戏曲历程及其特点的简要分析,从中可知,明代书坊刊刻戏曲主要集中在中后期,且紧随时代脉搏,刊本越来越精致。
四、明代坊刻戏曲的影响
如果说一个作品的产生,是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紧密结合的结果,那么书坊要完成一个刻本,就是书坊主、作者、文本与受众之间四者相互影响的结果。明清书坊主往往身兼多职,既要编辑文本,又要负责发行销售。也就是说,一个戏曲刊本,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精神,而且包含了书坊主对于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思考。由此可见,书坊在文学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明代书坊对戏曲文学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书坊促进戏曲刊本的繁荣。明代戏曲以坊刻为主,有利可图的戏曲刊本大受书坊青睐。在激烈的书市竞争中,书坊在书名、序跋、识语、牌记、版心、正文卷首、附录等处作广告,并且聘请文人编辑文本,增加音释、点板、插图、评点等辅助性内容,极大增加了戏曲刊本的销量。
其次,书坊推动戏曲文学的发展。书坊在很多方面刺激了戏曲文学的进步。一是戏曲稿源。据笔者统计,明代共有 9 位书坊主参与戏曲编写,即熊稔寰、臧懋循、汪廷讷、胡文焕、凌濛初、袁于令、周之标、许自昌、高一苇,书坊主的创作繁盛,佳作叠出,如汪廷讷创作了近 30 部戏曲。二是戏曲插图。刻家为了满足受众的审美追求,聘请名家刻图,使插图风格不断变化,日益精美。三是戏曲评点。根据现存刊本来看,早期评点本多是坊刻本,应是书坊主组织下层文人编写或本人所写; 凌濛初、臧懋循等书坊主的戏曲评点,是中国戏曲评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坊刻戏曲评点本的评语,尽管有些是抄袭和拼凑的,但仍存在不少亮点。四是戏曲体制、脚色、关目、曲词。出于读者阅读的需求,书坊组织文人改编戏曲,从而使剧本体制和脚色体制更加规范,情节结构和曲词宾白也更为精彩。尤为可贵的是,在明初戏曲稿源匮乏之际,书坊聘请下层文人改编宋元南戏,这批下层文人在传奇发展的崛起期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传奇发展过程中较早形成且规模较大的创作队伍。万历末年,在剧本案头化倾向严重之际,臧懋循、袁于令等书坊主改编传奇,使案头与场上兼擅的美学追求得到进一步实践。五是戏曲选本。明代书坊主本人编选的戏曲选本有 13 种,即继志斋《元明杂剧》四种四卷、文林阁《绣像传奇十种》、胡文焕《群音类选》、臧懋循《元曲选》、黄正位《阳春奏》、山水邻《山水邻新镌四大痴》、毛晋《六十种曲》、周之标《吴歈萃雅》及《增订乐府珊珊集》、李郁尔《月露音》、熊稔寰《徽池雅调》、凌濛初《南音三籁》和闵齐伋《会真六幻西厢》。书坊主的戏曲选本体现了明确的选曲观念,在戏曲发展中价值突显。
最后,书坊刊刻活动反映戏曲文学现象。以出版文化为视角可以加深我们对戏曲文学的理解: 从戏曲稿源和编辑工作可以发现书坊与文人的密切关系,像广庆堂与纪振伦,师俭堂与陈继儒、徐肃颖,两衡堂与吴炳,书坊周围应该有一批为书坊服务的下层文人,他们之间甚至形成了社团; 从选本的刊刻形态,即选本命名、刊刻时间与地点、版面设计、内容分类,可以考察明人的戏曲观念,声腔流传情况; 从戏曲的版本数量可以窥探读者对戏曲刊刻的影响,如据笔者统计,有 10 种以上明刊本的戏曲作品是《西厢记》、《琵琶记》、《玉簪记》、《红拂记》、《牡丹亭》、《邯郸记》和《拜月亭》,现存评点最多的明刊本是《西厢记》,共 37 种,其次是《琵琶记》18 种和《牡丹亭》7 种,这些剧本由于大众的喜爱而不断被修改和刊刻,并在读者与书坊的互动中逐渐成为经典。
此外,刊刻的作品也可揭示戏曲文学发展的脉络。比如传奇的演变轨迹。明万历之前,由于稿源不足,书坊所刊戏曲多改编宋元或明初的戏文。进入万历年间,传奇剧目大量涌现,折子戏表演频繁,于是戏曲选本刊刻十分风行。据笔者统计,明刊传奇选本共有 43 种,其中 28 种刊刻于万历时期。随着传奇体制的成熟和剧本演出功能的强化,万历末年始,书坊之间掀起戏曲改本刊刻的热潮,如臧懋循改订《紫钗记》、怀德堂刻臧懋循改订《牡丹亭还魂记》、许自昌改订《种玉记》和《节侠记》、崇祯刻高一苇改订《金印合纵记》、崇祯十五年刻冯梦龙改定《滑稽馆新编三报恩传奇》、蒸文馆刻《墨憨斋新定洒雪堂传奇》、毛晋刻冯梦龙重订《杨德贤妇杀狗劝夫》和许自昌改订《节侠记定本》。
诚然,铜臭与书香相伴是书坊业的特性,书坊刊刻戏曲也存在消极的影响。书坊主为了减低成本,提高销售额,随意删改和伪造作品,书名、插图、评点、曲辞宾白等都可以作伪,导致刊本粗制滥造,甚至版本混乱。但是总体而言,明代书坊刊刻戏曲利大于弊,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书坊与书坊主在戏曲创作与传播中作出的贡献。
关于戏曲文学,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作家和作品本身。笔者试图跳出这个框架,将焦点转移到明代书坊。陈大康先生曾说: “‘问世’是指创作的完成,‘出版’才意味着作品开始在较多的读者中流传; 前者表明小说史上增添了一部新作品,而惟有后者方能保证产生与该作品相称的社会反响,从而对后来的创作发生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在小说发展史的研 究 中,‘出 版’意 义 的 重 要 性 更 甚 于‘问世'.”
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小说出版的意义,但对戏曲出版同样适用。有鉴于此,本文整理明代坊刻戏曲概况、特征及其影响,希望对中国戏曲史研究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俞为民。 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J]. 艺术百家,1997,( 4) .
[2]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 黄裳。 银鱼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 朱万曙。 明代戏曲评点研究[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 ( 明) 余怀。 板桥杂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 赵山林。 历代咏剧诗歌选注[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7] 梅新林。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8]( 明) 张瀚。 松窗梦语[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9] 陈书录。 坚持与发展金陵特色文化[J]. 南京社会科学,2002,( 4) .
[10]( 朝鲜) 崔溥。 漂海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1]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12]( 明)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3]( 明)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M]. 北京: 中华书局,1959.
[14] 蔡毅。 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C]. 济南: 齐鲁书社,1989.
[15] 陈大康。 明代小说史[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曲品》着录明代戏曲作家戴子鲁所撰传奇《青莲记》《靺鞨记》各一本,从中知其号金蟾,永嘉人,而生平事迹不详[1]81。《曲品》是明代戏曲家吕天成万历三十年(1602年)撰写的一部戏曲理论专着,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曲目史料,并不乏真知灼见的评语。其将嘉靖...
明代曲家推尊正音、崇尚本色、宗法元人,又试图以北曲之宫调、韵律为参照系来重整南曲体制,体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曲学复古结合着种种社会历史条件,为元曲经典化营造出普泛性的文化空间。这里元曲经典化,包括元曲作品的经典化与元曲文体的经典化,①兼指...
明代中叶以后,在江南造园风潮推动之下,士人园林作为戏曲的重要资源和标记参与了戏曲艺术的构建,以昆曲为代表,戏曲艺术深刻地契入士人园林文化之中。清代康乾年间以后,江南士人园林声伎渐趋衰落,北方皇家园林演剧却日益兴盛,在南北园林演剧此消彼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