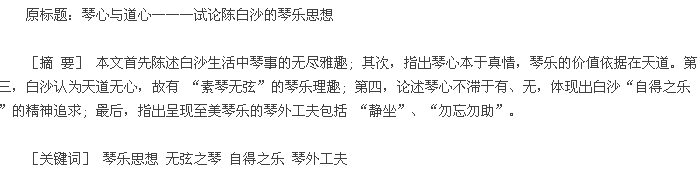
陈白沙①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其学说宗本自然,求达自得之乐,一改前世外求细究的为学理路,开启明代理学的新风气。在黄宗羲看来,明代之学 “自白沙始入精微”②; 白沙之学不仅精研极深,且融摄甚广,故黄宗羲又评曰: “先生之学……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③。观白沙诗文,自然天道活泼地流淌在生活的各个面向,其中也包括了古琴雅乐。
据载,白沙曾珍藏 “和龙吟”、 “天蠁”等名琴; 其诗文 “旋将幽意托龙唇” ( 《和娄侍御》) 、“东阁摩挲旧雨琴”( 《寄庭实制中》) ,则记载了他平素把玩爱琴④,寄托情思的琴乐生活。遍观白沙遗稿,我们发现: 关于琴乐的文字虽散见其中,却甚少论及琴艺技法; 而他 “寄语了心人,素琴本无弦”等诗句则表明: 在弦乐之外,存在着有待 “了心人”去体悟明达的精神境界。
那么,白沙弦外心境是如何展现的,与他的哲学有何关联? 在白沙琴乐思想中,琴人内心对“道”的体认对于琴乐的演绎存在着怎样的意义?
既然颇少论及琴技,那么琴人如何才能弹奏出最美的琴音? 白沙之道不离日用常行,要探究白沙的琴乐之道,就须先从他平日的琴事雅韵中说起。
一、琴乐中的无尽雅韵
在白沙看来,古琴并非寻常乐器,其乐音充满了雅韵情致⑤。白沙诗文中记录的各桩琴事,给人带来丰富的精神体验。
白沙性爱山水,或相约好友,或独自携琴出游,如 “道士来携三尺木,高山流水一声弦”( 《偶得》) ,又如 “春风卷骚怨,秋月照琴声”( 《树穴兰》) ,古琴成为人和万物交流的重要媒介,与风月、山水构成美好意境。白沙门人伍光宇曾置琴于钓艇之中,美其名为 “光风艇”,白沙回忆曰: “遇良夜,皓魄当空,水天一色,君悠然在艇尾赋诗,傲睨八极,予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啸,飘飘乎任情去来,不知天壤之大也。”①因为有了古琴与雅音,一只普通的钓艇也变得极具风色,以致人在其中,长啸放歌,任情游心。
琴不仅是赏玩山水的佳侣,琴音本身就蕴含着自然真趣。 “眼底两途分淑慝,手中三尺有雷霆,却疑夜半龙川雨,直为高贤洗汗青”( 《袁侍御挽诗》) ,手下三尺木琴,变现出龙川奔雷飘雨;白沙又试琴 “寒涛”,曰其音 “若长松茹风,清远而聚,往复匼匝而不厌”②,以琴音拟松风; 更有“何处秋声入短琴,江边萧瑟起枫林。空歌白雪儿童笑,不负沧波老子心”( 《余兴》) ,琴身虽短而秋意无边。诗句以琴音绘秋风,又以道心写秋水,自然、真心与琴音打做一片,真趣盎然。
白沙认为,琴音不但内含无穷天地,还能贯穿时空。如, “古锦囊中风韵在,几时弹向白沙门”,琴声虽有起止,音韵却无有间断; 又如 “同襟问为谁,定山携一琴。悠然一鼓之,不辨古与今”( 《和郭主簿寄庄定山》) ,自古琴心相契,丝桐之乐能带来超越当下的感怀。
古琴穿越时空的意境在白沙诗中又更加真切地呈露为恋慕知音、忆念故友的情思,“五羊不出独何心,万里行囊又一琴” ( 《赠张进士入京八首》) ,似写囊中琴,实写远行人,文字中注满了对友人的思念; 而 “拂试孤桐向明月,哀弦断绝不成音”( 《 总督两广军务都御史郴阳朱公》)的弦乐则浸透了失友之恸; “朱弦一弄白云深,山水何人共赏音” ( 《次韵梅侍御赠别》) 又点出了琴人对知音的思觅。
正如白沙所言,琴乃是 “雅乐”,她通过有形的丝弦桐板,表现出无尽的自然真趣与人文情怀。
琴与诗书、歌声及山水一同构成了活泼、高雅的生命。无论是携琴游山水、弄丝通古今、或抚琴觅知音,在白沙丰富多彩的雅乐世界中,贯穿着他的一颗真切自在的琴心。也正是由于白沙琴学中对于真切情感的呈现,才使他的琴韵含有无穷风雅。
二、琴心本于真情
在白沙那里,好的琴音源于琴人心中的真情,他通过论 《诗》来表达这一主张:受朴于天,弗凿以人; 禀和于生,弗淫以习。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而诗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锻月炼,以求知于世,尚可谓之诗乎?
今之名能诗者,如吹竹弹丝、敲金击石,调其宫商,高者为霓裳羽衣、白雪阳春,称寡和,虽非韶頀之正,亦足动人之听闻。是亦诗也,吾敢置不足于人哉? ( 《夕惕斋诗集后序》,以下简称《夕序》)孔子论 《诗》曰: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 朱子解释 “无邪”即 “善为可法,恶为可戒”③, 《诗》起到规范人心的作用。白沙则反对外从矩镬,强调率真而为。他认为七情禀受于天,不受后天习染,因而质朴无邪。以真情为根源的 “风”、“雅”与后世诗家眩耀技能的诗作判然有别。白沙的理路不同于朱子,他奉 “情”为圭臬,强调心的质朴、和谐出于先天。诗的言辞乃是 “心之声”④,琴音的变化也体现情感波动。
总之,真情乃是琴乐之内核,琴乐是真情的外现。
在白沙心中,“天”予人的禀赋确立了琴乐的价值根基。为了进一步探讨白沙的琴学思想,就不得不解读他的天道观。白沙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天、地与人皆因 “道”而成其为自身,所谓 “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⑤。那么,人如何得 “道”? 白沙指出 “心得而存之”⑥,人心本身具备了天道法则。天道与人心以 “诚”相贯通: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 一诚所为也。
则诚在人何所? 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天地之大,此诚且可为,而君子存之,则何万世不足开哉! ( 《无后论》)《中庸》曰: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①。白沙承接 《中庸》,指出 “开万世” 或“丧邦家”在于 “诚伪之间”②。 “诚”即 “真”、不伪。“诚”存于 “一心”而能开万世,那么人存得真情于心,发则为诗文雅乐,若能 “会而通之,一真自如”,便可 “枢机造化,开阖万象,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机”( 《夕序》) 。有了真心与诚意,人伦日用无非天机; 在俗儒看来,琴、诗等只是小技,在白沙看来却是天道展现。
由于真情之畅发,琴在白沙那里便成为了真情实感的载体。如 “百年会有尽,泪下雍门琴”( 《挽容珪三首》) 是对故人的悼念及人生短暂的感叹; 又,在白沙 “富而居畎亩,……引满高歌,吹竹弹丝,以相谐嬉” ( 《王徐墓志铭》) 的梦景中,竹丝表达出愉悦情感,使友人都融浸其中,诙谐嬉乐。白沙作为思想家,以究宇宙万物之本为己任,琴音中所寄托的更有哲人的幽思心绪,如 “古人不可见,空见古人心。春风开我琖,流水到谁琴”( 《春日醉中言怀二首》) ,“流水”一语双关,既指春日溪流,亦指古曲 《流水》; 诗句所言 “古人心”落实为求觅知音的深切诉求。古今虽异,此情此心却能通过琴曲相会。
白沙总是在情深处弹琴,他的琴诗充满了活泼、真切的场景,哀则泪打琴板、丝弦欲断,乐则弦韵浮动、谐趣横生。凭借琴与琴音,他的生命中平添一份 “任情去来”的逍遥。
三、天道无心与素琴无弦
白沙的真情并非有意、用心而为之。白沙认为真情之依据在于天道无心:天道至无心。比其着于两者,千怪万状,不复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为。圣道至无意。比其形于功业者,神妙莫测,不复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者,其此一元之所舍乎! ( 《仁术论》)天道无心,而能生成万千物类,这种极度的巧妙由于 “一元”; 圣道无意,圣人的 “一心”保有了天道的 “一元”,故可成就无量功业,同样体现了 “至巧”。白沙指出 “巧”与 “拙”的区别:桓文 “用意”故 “至拙”,周公 “用心”故 “至巧”,因此圣人不敢用意,不害此心③。
“用意”,即使用人为之私心; 而 “用心”,则运用天授之 “一心”。但 “用心”难免受习气牵绊,于是白沙用 “素琴无弦”的比喻指出 “了心”的更高境界:
古人弃糟粕,糟粕非真传。眇哉一勺水,积累成大川。亦有非积累,源泉自涓涓。至无有至动,至近至神焉。发用兹不穷,缄藏极渊泉。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 学患不用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戒慎与恐惧,斯言未云偏。后儒不省事,差失毫厘间,寄语了心人,素琴本无弦。( 《答张内翰廷书》)白沙提出了两种为学进路。一是 “积累”式学习,包括窥览陈编。白沙在庄子之后,重提“六经糟粕”说④,批判 “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其味”( 《道学传序》) ,内心不能超脱外在牵缠。为此,他提出了第二种进路: “了心”式的学习法。
“了心”的发用有如源泉活水,无穷无尽,其奥妙在于 “至无”与 “至近”。 “至无”即无意, “至近”近于 “一元”,只有这样才能把握 “天机”,超脱束缚。
在此基础上,白沙提出的 “素琴本无弦”哲理性琴论,既是以琴喻学,也是以学问发明琴道。
“素琴”之说,当源于有关陶渊明的典故。据载,陶公每在朋酒之会,会抚一张弦徽不具的木琴,并和之曰: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①。魏晋玄学的 “得意忘言”之说在陶公那里转呈为 “得趣忘弦”的琴学思想。与陶公一样,白沙强调了有形之琴乃是了知无形天道的工具,只有当人难以了心于 “道”,才不得不有意于抚弦弄丝以达天理。反之,若能得流行之天理,那又何须琴弦之声? 对于有为的 “用心”者而言,琴之意韵仅能展现在七弦之上; 而对于无为的 “了心”人,素琴虽是无弦之具,却有无穷的天机蕴含其中。
白沙的另一首诗更充分地展现了他对于无弦心境的推崇:海上有一士,来往不知年。或就胥靡饭,或投上方眠。游处各有徒,孰谓世情然? 饮酒不在醉,弄琴本无弦。借问子为谁,得非鲁仲连。 ( 《秋兴》其三)道家认为 “无”生万有,乃宇宙本体; 白沙则顺此理路,解开一切有形器具,曰: “……心元初本无一物,何处交涉得一个放不下来?”( 《诗文续补遗》) 。饮酒求醉、弄琴在弦虽有雅韵,但不免拘于有形器具,《秋兴》中的高士不羁于俗,他“饮酒不在醉,弄琴本无弦”的逍遥无为更近乎真心与天道。白沙在吟哦此诗时,一定达心于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 的虚无之境。
天道无心、心本无物,故而琴本无弦。正因为白沙的琴乐契心于 “无”,故而白沙常于无声处听真情,于无弦中觅天心。“人间铁笛无吹处,又向秋风寄此音”( 《赠邬文瑞》) ,诗人难以言写心中情意,正如铁笛无处可吹,只能托秋风传达心意,此时无声胜有声。又有 “子云休儗赋,元亮已忘琴。南山千丈石,可以明我心。”( 《春日醉中言怀》) 此诗以扬雄休做赋文、陶公忘怀琴音比拟诗人疏狂自在的山林之心。
白沙的无弦之境,到了屈大均那里,更加彻底地演化为 “无琴”之思。他曾作 《石琴歌》进一步阐述了白沙的琴乐意境:无弦吾欲并无琴,琴向高山流水寻。
人籁岂如天籁好,空中写出太初心。②首句发展了白沙的忘弦之趣,使白沙的无弦理趣更加明彻朗然。但白沙认为 “道至大,而君子得之”,七情之发本于质朴,无不是天理流现,因此他必不认同屈大均所谓 “人籁岂如天籁好,空中写出太初心”的乐论。正因如此,白沙并不言 “无琴”,只说 “无弦”。在白沙那里,太初之心既显现于山水间,也留存于真诚中,只要不限于器具、不染于习气,那么发情于指端,同样能呈露天籁。白沙之 “无弦”并不等同于屈大均之“空无”,他不是要刊落一切有形,而是要超越外在的束缚。虽寄托于弦,却不拘泥于弦,这种游心于有、无之间的琴学理趣体现了白沙 “自得之乐”的心学境界。
四、自得之乐与弦外之境
对于白沙而言,琴乐的至高境界是: 以丝弦之乐畅发内心真切情怀。白沙追求的雅境正是“自得之乐”在琴乐思想中的呈现:
迨夫足涉桥门,臂交群彦; 撤百氏之藩篱,启六经之关键。于焉优游,于焉收敛; 灵台洞虚,一尘不染。浮华尽剥,真实乃现; 鼓瑟鸣琴,一回一点。
气蕴春风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乐亦无涯也。……富贵非乐,湖山为乐; 湖山虽乐,孰若自得者之无愧哉!( 《湖山雅趣赋》)白沙在赋中借 “一回一点”表达出对 “自得之乐”境界的体认。此前典籍中关于孔颜、曾点之事鲜及琴瑟,为何白沙却有 “鼓瑟鸣琴,一回一点”之说? 在文献中,有两处关于 “弦歌”③的记载: 一是孔子困于陈蔡间, “不得行,绝粮。
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 《史记》) ; 一是孔子游至武城,闻弦歌之声,子游以“君子闻道则爱人,小人闻道则易使也 ( 《论语》) ”来解释 “弦歌之治”,受到孔子赞赏。弦歌是 “道”的承载,也表达出泰然自在的精神境界。在白沙处,道境与琴境同样相贯无碍,他通过琴瑟之音表达颜回、曾点之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自濂溪后,理学家对于仲尼、颜子所乐之事各有阐释。不同于宋儒的抽象理论,白沙的 “自得之乐”包括了颜回与曾点两人的乐境追求,更显出一派活泼生动: “鼓瑟鸣琴,一回一点。气蕴春风之和,心游太古之面”。白沙认为 “心”与 “道”相通,心得道而存之,如虚空灵台,且能生生不息,开启万物。当人剥落习气、利欲等浮华时,便显现出一派自得自在、生机无限的气象,故而认为这种精神上的怡悦是无穷的。
白沙的 “自得之乐”,也是一种无愧于己、不累于物的自足、自乐。他认为: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 ( 《书一: 与林郡博》)“道”超越一切时空、包裹宇宙内外,人若能会此道理,则宇宙万物在此一心,那么人心又何须向外求索? 因此,白沙认为 “自得者……不累于一切”。白沙的 “自得”境界又称作 “自然”。
他认为人与天地自然同体,自然无滞无为,则万物化生; 那人心也必须不滞在某处,才能运转无碍。由于 “自然之乐,乃真乐也”①,故当 “常令此心在无物处”、 “以自然为宗” ( 《与湛民泽七》) 。
白沙的 “自得之乐”呈露于弦乐中,则是一片天真流荡、无滞无碍的自然境界,如诗云:大崖居士此弹琴,谁系孤舟绿渚浔?沧海我真忘僻远,云山公肯到高深。鼠肝虫臂都归幻,雪月风花未了吟。满眼欲知留客意,庐冈孤月正天心。( 《次韵世卿,赠蔡亨嘉还饶平》)此诗赠还乡友人,借留客之意,表达诗人天真洒落的道心。诗中两个 “孤”字,一以 “孤舟”喻蔡亨嘉与诗人,同是身处僻境,独居高深; 又以 “孤月”表露人心契合天心的孤高之境,其中流露出对知己的挽留仅是淡淡的惆怅,反而更烘托出诗人置身天地间,留存遗世独立而自任自得的高妙境界。全诗沉浸在沧海高崖边的琴乐声中,在自得的真乐中,所谓 “鼠肝虫臂”等世间俗事皆归虚幻,一一化作寄情山水的弦歌雅韵。
结合这首琴诗,再看白沙所言 “富贵非乐,湖山为乐; 湖山虽乐,孰若自得者之无愧哉”( 《湖山雅趣赋》) ,则知: 雪月风花之雅趣,鼠肝虫臂之俗乐,都不及 “自得之乐”的真真切切;于是,琴乐中的雅韵真趣,不滞于丝弦之音,也不执于无形虚廓,而是落实在琴人心中的自得乐境。换言之,白沙自然洒落的心境追求映照着他的艺术情怀,他寄意于山水之间,与友人知己相酬答、抚其素琴、发乎真情,正有一片道心于其中呈现。
五、琴外工夫
白沙认为琴乐的真切根于精神境界的高妙。
他的琴学修养不重在琴谱整理或琴技修炼,而在于通过体认天道,复归本真以彰显琴心。天道与日用常行一以贯之,为学之人重在理会贯通: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 会而通之,一真自如。
……若是者,可以辅相皇极,可以左右六经,而教无穷。小技云乎哉? ( 《夕序》)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安事推乎? 此理包罗上下,贯彻终始,……自兹已往,更有分殊处,合要理会。( 《书一: 与林郡博》)第一则材料阐述了 “会通”之妙用。不能会通,“诗”只是雕虫小技; 能会通,诗中自有参赞化育之大用,诗如此,琴亦如此。第二则材料则强调天道贯通宇宙,若 “毫分缕析”则工夫 “尽无穷”,若得会通道理,则能化整为零,无须有为之徒劳。依此即能解答: 为何白沙诗文中关乎心境之处,常常提及琴乐,却又甚少讨论琴技。白沙以诗达琴心,以琴心会道心,所谓 “素琴不鼓繁弦调,点瑟偏宜好梦传”( 《同理张显迈》) ,不着意于琴乐的奇技淫巧。因此在白沙看来,要达至高妙的弦外之境,不仅在于琴技的磨炼,更在于内心的涵养。
“静坐”是首要的工夫。成化 18 年,白沙学归后,读书累年无所得,于是筑 “阳春台”,杜门静坐数年,终有所悟。静,是由繁入简,由外向内的工夫转向。他指出: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于书册,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不可不涵养也诗、文章、末习、着述等路头一齐塞断,一齐扫去,毋令半点芥蒂于我胸中,夫然后善端可养,静可能也。( 《与林缉熙十五》)白沙的 “善端”未必仅就伦理意义而言,也可指统摄义理的本心,即 “真”、 “诚”之端倪。
白沙认为至静的先行工夫是扫断外在诸端 “路头”,吹竹弹丝等末习也必须一并扫落,方能入“静”。但 “静”绝非是空无一物的死寂: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脗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 《复赵提学佥宪一》)在白沙看来, “物理”、 “圣训”以及日用的“种种应酬”外在于心,虽有形却繁琐。如果内心不能反观内求,则不能与根本大道吻合相契,称为 “未得”。只有通过静坐,由繁入简,观物理、圣训的源头,使隐藏的 “心之体”呈现出来,则做到随心所欲皆在道中。包括游历山水、抚琴弄丝等末习一概属于日间应酬,皆首在这一番心灵的修炼。清代岭南琴人黄景星在论及 《古冈遗谱》时,就曾指出白沙 “惟于静中养出端倪,以复其性灵”①的工夫论对后世琴人的影响。
白沙认为,虚静的心体是种种人伦日用的源头活水,他的心学工夫,同时也是琴外工夫,由至静而至动,从至虚而至实。在心彻万法之源后,日间人伦便如活水呈于眼前,此时更须另一番工夫以达至真乐境界,白沙曰: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
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 《与林郡博士》)“勿忘勿助”正是获取 “鸢飞鱼跃”的重要工夫,若非如此,曾点乐境一如说梦。“勿忘”即是不放松懈怠,“勿助”即是不有为造作,根本上而言就是顺应事物之自然②。这番工夫展现在琴乐中,便是任心之真情流淌于乐音,无意以丝桐取悦于旁人,在自得与自然中臻至高妙真趣。
小结
今人多推崇白沙先生为广东古琴史中重要的琴家,琴界更有称之为 “岭南古琴第一人”的说法。但历史文献亦鲜有记载白沙关于古琴技艺的论述,后人难以窥见其琴艺水平。作为一位哲学家与体道者,白沙的琴学贡献并不在于对有形技艺的精研,而在于他对琴乐之外无形意境的深入体认与阐发。
由上所述,白沙的琴音流淌着悠长雅韵,涤荡出天然真情,其琴道中含藏着无弦妙理,又呈显出自得至乐,更指点出了琴心之涵养。在白沙看来,琴心根于道心、道心现于琴心。白沙的琴乐思想充分体现了 “文人琴”,甚得白沙思想的真乐精髓。千百年后,学人欲得白沙琴乐的心传,是否能如歌中所吟,解外物之缚、存内心之真,再现白沙琴乐的无弦妙趣与自得之乐?
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文字语言到曲调的出现,体现了人类信息交流方式的改变。音乐逐渐成为人类用来表达丰富情感的艺术形式。...
前言一、关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期刊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是将精神文明固化在一定物质形式上的物质产品。它是一定时期内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参照物。它刊载、记录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品味。音乐期刊是期刊的一类,它可以...
中国古典音乐传承至今记载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更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为现代人了解古代的生产、生活、情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摘要在人类从古至今的社会生活中,任何的音乐活动都与音乐传播息息相关。通信科技的不断更新和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深深影响和改变着音乐艺术的创作与传播实践。纵观音乐传播媒体由报刊、广播、电视的传统媒体到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历程。媒介按照自身...
本文深入探究了实现多元化音乐教学的意义, 针对目前幼儿园音乐教学现状, 分析了如何高效开展多元化音乐教学。...
尽管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浩如繁星,但是凤阳花鼓艺术也绝对是其中星光璀璨的那一颗。因为它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厚重的历史底蕴使得这项艺术迸发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摘要秦腔是主要流传在我国陕西、甘肃两省的地方戏曲之一,与全国其他地方戏曲相比,秦腔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更以其独特的演唱特点,独存的风格、面貌屹立在我国戏曲之林。前人对秦腔四大行当中的角色类型都已有论述,本文依据秦腔不同角色的演唱特点,将...
对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民族民间音乐库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民族民间音乐库建设中的注意事项进行了探讨,以期能为民族民间音乐库建设提供参考建议。...
摘要自动钢琴是钢琴发展历史中特殊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它是钢琴的衍生品。自动钢琴在不改变钢琴击弦机原有机械运动和音板声学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新的设备,使钢琴在没有演奏家的情况下完成音乐的演奏和传播。自动钢琴的设计结构与应用,伴随着时代的发...
文章从建立多元化的音乐评价体系,鼓励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学习过程的评价,避免以偏概全;采用多种形式的音乐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