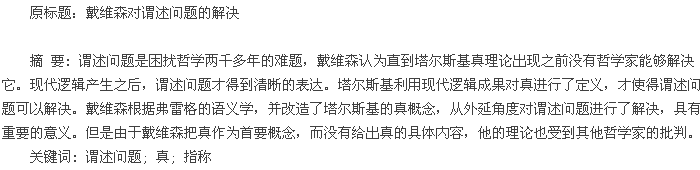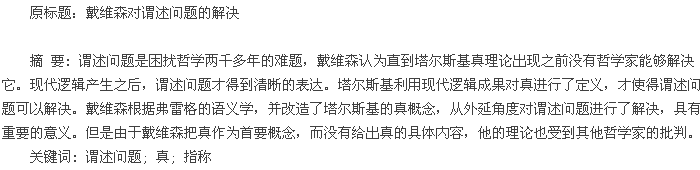
谓述( predication) 问题是关于谓词在句子中如何起作用的问题,它渊源于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是困扰哲学两千多年的难题。它关系到哲学的许多方面,是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绕不开的话题,因此建立一个谓述理论非常重要。戴维森说: “没有这样一个理论语言哲学就缺乏其重要的一章; 如果不能描述判断的性质,心智哲学就失去了关键的第一步; 如果形而上学不能说明物质( substance) 是怎样和它的属性( attribute) 相联系的,那是悲哀的。”戴维森认为,直到塔尔斯基真理论出现之前没有哲学家清晰地解决谓述问题。《真与谓述》是戴维森去世后出版的他唯一的一部专着,在本书和一系列论文中他对谓述问题的解决是对哲学的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谓述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是因为人们总是诉诸谓词指称的实体,并且该问题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刻画。只有按照弗雷格的意义模式给以刻画,并借助于塔尔斯基的真之定义才能解决谓述问题。本文将按照戴维森的思路对谓述问题何以不能解决以及如何能够解决给出论述。同时也指出,由于塔氏定义的真只适用于对象语言,所以戴维森的解决方案不能直接适用于元语言。
一 谓述问题的提出
苏格拉底在早期对话中拒绝承认具体的东西是共相,可以看做他已经假定了有两种不同的实体( entity) 的存在,即特殊的物理对象和抽象的形式( form) 。早期对话中的这些观点导致本体论上的二元论观点,并在后来的对话中出现了对形式存在的论证。从苏格拉底的思想中已经萌生出形式和个例情况( instantiations) 是如何联系的,形式和形式之间又是如何联系的问题,这就是戴维森所谓的谓述问题。柏拉图秉承了老师的思想,他关于形式或理念的理论直接导致了谓述问题。
柏拉图认为: “形式不是被感觉感知的,而是心灵的对象; 它们是不灭的; 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它们是优于物质对象的; 它们是我们判断物质事物所依据的标准; 它们有某种创造力( 智慧这种形式“使”苏格拉底聪明) 。”
根据柏拉图的思想,形式所具有的这些特性是物质对象所没有的。物质对象是被创造出来的,有生灭,占据空间并且在时间中存在。因此形式和具体对象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实际存在的实体。另一方面,形式与形式也是不同的,否则就无法区分这两种形式。
由此在柏拉图思想中派生出了谓述问题。如果认为特殊对象与其形式、形式与形式有联系,那么它们就分享另一种共同的形式,如此一来就会导致无穷倒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白马非马”的问题也反映了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是谓述问题的一种表现。
在中世纪,谓述问题导致了殊相与共相、个别与一般、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漫长的争论。直到现代逻辑出现之后谓述问题才被清楚的阐述,其中形式和个例情况如何联系的问题可以用公式 P( a) 表示,P是谓词或关系,a 是个体词。形式与形式之间联系的问题可以用公式x( P( x)→Q( x) ) 表示,P 和 Q都是谓词或关系,x 代表任意的个体,公式的意思为: 对于任意的个体 x,如果它是 P,那么它是 Q。与谓述问题相关的是命题统一性问题,即命题是如何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问题。命题要通过语句来表达,许多哲学家把命题看做句子的意义,因此谓述问题也就是句子的意义的统一性问题。命题的统一性保证了句子的统一性,从语言学角度看,系词“是”起什么语义作用使一个句子成为一个整体的?
谓语怎样使句子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单位的? 殊相和共相有怎样的关系才促成一个句子成立? 这些问题可称为命题统一性问题。谓述问题与命题统一性问题被戴维森称为孪生问题,它们涉及本体论、认识论、语义学和逻辑学。命题统一的标记是表达命题的句子具有真值,因此“真”与命题统一性密切相关。戴维森从语义学的角度认为,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可以解决谓述问题,其他哲学家的理论无一能解决该问题。
二 谓述问题不能解决的根源
在苏格拉底晚期对话中,“对假陈述是如何可理解的这一问题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认识到任何判断或能够被用来表达判断的句子的三个本质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第一,判断或句子必须以某种方式构成一个统一体; 它的部分必须结为一体而产生某种可以是真的或假的东西。第二,每一个句子必须含有一个动词和一个或多个确定‘主题’的要素。第三,这两种要素的作用必须是非常不同的。”
也就是说,一个句子必须有主语和谓语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整体,其中主语和谓语是如何连接起来的是问题的关键。柏拉图认为,可以用形式使之连接起来,这种形式就是“相同”和“差异”,比如“运动不是静止”被“差异”这个形式连接起来。但是,这样一来“运动不是静止”就命名了“运动”、“差异”和“静止”三种形式,而且这里已经没有了动词。这三种形式之间又是如何连接的,仍然需要引入新的形式,于是就导致了无穷倒退。
因此,柏拉图不可能解决谓述问题。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学说进行了批判,他虽然认为形式是一和不可分的,但不认为形式是完全脱离它们的个例情况的。形式是共相( universal) ,但它们却凭借以它们为性质的东西的存在而存在。
在《解释篇》中亚里士多德考虑了句子的真假,并认为一个句子有一个名字和一个动词。他在《范畴篇》中提出了可以作为谓词的范畴,根据戴维森,这些谓词是不是包含系词“是”或其变体并不清楚。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说,当一个动词自身或者与一个系词一起被表述出来的时候,它不必然隐含着共相的存在。只有当动词谓述某个存在的东西时,动词才表述共相。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系词“是”不引入实体,只是使主谓语联系起来。
如果一个动词的功能是引入一个共相,而系词“是”引入了必须在每一个句子中所表达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系词反过来不引入另一个共相呢?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明。如果“是”引入了一种关系,那么就同样陷入柏拉图式的无穷倒退。除此之外,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也不可能对谓述问题给出清晰的逻辑表达。所以,亚里士多德没有解决谓述问题。
直到 19 世纪末,谓述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随着现代逻辑的产生,谓述问题通过形式语言得到清晰的表达。与塔尔斯基同时代或稍早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大都遇到了谓述问题,他们试图解决谓述问题的路径有三种: 弗雷格 - 达米特路线,罗素- 斯特劳森路线和奎因 - 塞勒斯路线。但是,在戴维森看来他们都没有真正解决谓述问题。
弗雷格严格区分了对象和概念,把单称词的指称( 或意谓) 称为对象,把谓词的指称称做概念、函数。谓词是句子去掉单称词的部分,是把对象映射到句子真值的函数表达式。但是弗雷格所说的“概念”、“函数”也可以是一种实体,虽然是不同的实体,这就导致用实体来解释谓词的语义作用。一旦谓词通过指称实体来起谓述作用,就又回到柏拉图的老路上了。弗雷格的贡献是把真值看做句子的指称,把句子和词语的指称和涵义区别开来,把量词引进到逻辑中,为谓述问题的解决作了铺垫。
达米特对弗雷格思想进行了阐述和发展,他与弗雷格不同,认为谓词不能是函数表达式。弗雷格把句子看做名字,一个名字只指称一个对象,真或假,这掩盖了句子的多种语义功能,比如判断、下命令、提问题等等。达米特通过增加语义值对弗雷格思想进行了改造,语义值代表句子的不同语义作用,保持了谓词类似函数的特性,谓词可以看做是个体域到语义值域的函数。语义值是对句子作用的描述,但是我们在为句子寻找语义作用的时候,很可能又会回到谓述问题上来,因此达米特的改进也没有解决谓述问题。
达米特曾在《弗雷格语言哲学》中采用“标准语义学”( standard semantics) 的方法,把谓词转化为谓词在现实世界中拥有的外延的对象的集合。
把谓词解释为集合不能解决谓述问题,比如把“泰阿泰德坐着”解释为“泰阿泰德是坐着的对象的集合中的一个分子”,“坐着”并没有作为谓词出现,但是出现了新谓词“是……的分子”,它的语义作用没有给出,它是个二位谓词。塔尔斯基也采用了集合论方法来说明谓词,但是这并不代表谓词指称或代表集合,他是在元语言中使用这个概念的。
早期罗素认为命题的统一性要依赖于命题本身,命题是事物或实体,反对命题的统一性依赖于人类的判断行为的看法。“他在 1903 年首次发表的《数学的原理》中,罗素把命题当做完全脱离判断、词或句子而存在的实体。”
罗素实际是把命题看做事实的名称,以此来解释命题的统一性是行不通的,因为命题有真假逻辑特征,而名称没有。罗素后来认识到谓词可以表达一种关系使命题成为一个统一体,即他所说的谓述关系。但是他用一个词项表达这种关系,由此又导致柏拉图式的无穷倒退。罗素比弗雷格的进步是认识到一位、二位、多位动词同样是谓词,从而使谓述问题得到更好的表达。
再后来,罗素用信念、意向来解释命题的统一性。他认为相信一个命题就是认为命题为真,因此人们主观认为的“真”使命题统一起来。命题是否为真是命题是否符合事实的问题,与信念中的真是不同的。罗素的这种解决方式,就是在命题和事实之间插入信念、意向等心理因素,通过心理作用使命题统一起来,这种方式具有神秘性而难以为人们接受。
斯特劳森批判地继承了罗素的思想,他认为应该首先搞清楚单称词和一般词的形式区别的基础和原因。罗素认为只有殊相可以作主语,斯特劳森认为,共相本身和其他抽象对象也可作主语,如“勇敢是真正的美德”。斯特劳森认为,在这样的情况所指对象这个概念能够成为抽象个体而被命名,抽象词语也可以符合个体化原则,可以作主语,“因此一般或共相,即概念或理念( idea) ,就不再限于其基本的谓述作用,而是能够自身表现为一个对象,其自己谓词的主词。”
斯特劳森的观点也不利于解决谓述问题,因为他的个体化原则使抽象概念成为实体,由此导致谓词也是可以量化的错误观点。斯特劳森偶然碰到了谓述问题,但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如果按照斯特劳森的理论,解决谓述问题同样会遇到柏拉图式的困难。奎因与斯特劳森相反,他从唯名论立场出发否认谓词指称诸如性质、质量、殊相或属性这样的单称实体,或把谓词与这样的实体相联系而解释,从而成为第一个能够避免无穷倒退的人。奎因认为没有理由假定谓词符合任何种类的单个实体,如果像“漂亮的”、“机智的”这样的表示性质的词表示实体,那么可以对它们进行量化处理,但是这是违背谓词逻辑常识的。
奎因只是认为谓词适合于( true of)它谓述的各个事物。因此,按照奎因的思路可以解决谓述问题,可惜奎因没有深入讨论下去。威尔弗雷德·塞勒斯( Wilfrid Sellars) 真正对待过谓述问题。他和奎因一样认为谓词不代表性质、关系等抽象实体,或者不把这些抽象实体的存在用于解释谓词的作用。但是塞勒斯反对奎因根据谓词不能被量化来区别谓词的方式。塞勒斯受维特根斯坦影响提出了如下观点: 要说明谓词的作用,可以给每一个简单句加一个特殊符号,以表达被命名的性质是被命名的主词的性质,这个符号可以是“以例说明”( exemplifies)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这个符号省略后也是可以表达同样意思的,所以,可以根本不用这个符号。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是谓词本身使句子统一起来的呢? 甚至谓词也是可以省略的,我们可以采用多种约定的方式只说出对象的名字来表达出谓述的意思。由此可以得出,我们关于谓词的通常的假定是不成立的,甚至也不能像奎因那样认为谓词“适合于”对象,因为这样会使谓词处于与“非语言的实体的独立而自主的关系( distinct and autonomous relations to extra - linguisticreality) ”之中。
塞勒斯没有解决谓述问题,因为他没有谈到如何处理复合谓词和量词,也没有说明在不给谓词指派一个清晰的作用的情况下如何能给出一个真值。许多哲学家认为只要句子符合( 个体化的) 事实即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命题的统一性。事实是世界的客体,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思想,这有利于说明句子的统一性。但是,什么是个体化的事实? 怎么以合理的方式使事实个体化是个无法知道的难题,因此不存在事实和命题之间的对应,这种朴素的观点也是早期罗素的观点。
三 用真理论对谓述问题的解决
一些哲学家对谓述问题解决的失败使戴维森认识到,“一种适合于现代逻辑要求并且对大量的自然语言的表达力敏感的系统句法,配备上一种弗雷格那样的系统的语义学,甚至一种能够定义逻辑真和证明推理规则有效的语义学,并不必然构成一种对谓述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些哲学家之所以不能解决谓述问题是因为不能满足如下四个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对谓述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依赖于把谓述与句子的真联系起来。
原因是,如果我们不能说明谓词如何对含有它们的句子的真假起作用的,那么继续讨论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统一性就没有意义。有一些人对根据真之条件来理解句子提出质疑,他们试图求助于内涵概念,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内涵理论满足这个要求。如果我们非要假定意义和命题这样的实体,那么我们必须能够解释单称词如何指称对象的以及谓词如何适合于对象的才能解释这些实体是什么,也就是说仍然必须先解决谓述问题才能解释命题实体。罗素把命题的指称看做事实,试图从内涵角度解决谓述问题是行不通的。戴维森说: “在正式机制中,事实或者命题都不作为句子的意义或者作为罗素早期理论中世界的半外延、半内涵的实体出现。”
第二个教训是,把谓词与共相、性质、关系或集合这样的对象联系起来不能解决谓述问题,因为这总会导致无穷倒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素因为认为谓词指称形式或共相而遇到这个问题; 巴门尼德、莱布尼兹、布拉德雷等因此放弃谓词有所指称而信奉一元论; 休谟因类似原因不能解释句子内容和思想的统一性。弗雷格把谓词看做函数表达式,导致谓词应该命名对象或指称实体。达米特把谓词解释为集合,而集合本身也可以看做一种实体,也不能解决谓述问题。
第三个教训是,将谓词在句子中引入一般性( generality) 这种明显的观察与谓词必然在句子的主题中同时引入共相或其他抽象实体这种思想分开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从第二个教训推理出来的。
我们不能依据共相实体的存在来解释谓词的作用。在有系词“是”的句子中,不包含( 或包含) 系词的谓语部分可以引进共相或抽象实体; 在没有系词的句子中,谓语可以引进共相或实体。这些实体是否存在与谓述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必须把两个问题区分开来才可能解决谓述问题,很多哲学家混淆了两个问题,导致对谓述问题的困惑。
第四个教训是,谓述问题的完整范围和实质只与一种关于句子的逻辑形式的清晰看法一起出现。任何对谓述的描述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探讨量词和量化结构,则都不能被看做是成功的。谓述问题表现在一阶逻辑的量化结构中,能够被逻辑公式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是解决谓述问题的前提条件,而传统的形式逻辑没有这么清晰的表述。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一个人”、“所有人”和“有些人”
这些词语被看做主词,没有把句子处理为量化结构。直到现代逻辑的产生,弗雷格才把句子清晰地处理为量化结构,把单称词和概念词区别开来。按照上述四条经验,弗雷格把谓词的作用与真值联系起来,并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清楚地表述了谓述问题,符合一、四条。奎因和塞勒斯避免了把谓词与实体联系起来,又更进一步,符合第二条。但是,只有塔尔斯基关于真的定义符合第三条。“毫无疑问,塔尔斯基的真之定义,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真之理论,在性质和其他抽象实体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与谓词的语义作用之间作出清楚的区别。”
按照塔尔斯基的方法,采用弗雷格的逻辑手段和语义框架,符合了上述四条教训。戴维森说: “据我所知,塔尔斯基几乎没有想到他实际上解决了千百年来一直令哲学家们困惑的谓述问题; 他当然没有作这样的断言。”
塔尔斯基用约定 T 给出了真之定义,他所说的“真”适用于对象语言,是属于元语言中的词语。谓词的语义作用表现在对象语言之中,是与元语言中的语词“真”联系起来的。塔尔斯基还用单称词满足谓词的方法来说明句子的真,由此得到谓词适合于( true of) 单称词指称的对象的概念。“塔尔斯基的根本创新在于天才地利用这样一个思想:谓词适合于如下实体,这些实体是被占据它们空位的常元命名的,或者是由在相同空位上出现并且被量词约束的变元量化的。”“适合于”说明了谓词的作用,没有借助于谓词的指称,从而解决了谓述问题。
结 语
戴维森把谓述问题放在弗雷格的意义框架之内,使谓词的指称和语义作用分开,用塔尔斯基的真理论来达到对谓述问题的解决,具有高度的技巧性和创新性。但是,戴维森对谓述问题的解决仍然存在不尽满意的地方。首先,塔尔斯基的真定义只适用于对象语言,不适用于元语言。按照塔尔斯基对真的定义,对象语言中的真只能通过元语言来定义。
他实际上只是解决了对象语言中的谓述问题。而自然语言是其他语言的元语言,戴维森把塔尔斯基的真推广到自然语言,已经使真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他说: “这个结果并没有证明这个定义了的概念是清白的,因此如我所说,这个结果不会是塔尔斯基欢迎的。这是能够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实际语言的代价。”塔尔斯基的真之定义本身也受到许多批判。达米特说它关于真的重要性没有说任何东西。
普特南说塔尔斯基的理论是不成功的,要多糟糕有多糟糕。戴维森以这样的真理论为基础解决谓述问题,显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其次,塔尔斯基所说的谓词的谓述作用就是“适合于个体化的实体”,何为“适合于”恐怕需要人为的判断才能知道。依据“适合于”来说明谓述作用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适合于”的问题。即使“适合于”说明了谓词的作用,也只是说明了谓词在真句子中的作用,却没有直接说明假句子为什么是有意义的。尽管存在上述问题,许多哲学家也对戴维森的理论提出批评,但是完全可以认为戴维森和塔尔斯基用巧妙的方法从外延角度解决了谓述问题,其意义是巨大的。
【参 考 文 献】
[1]Davidson D. Truth and Predication[M]. Cambridge,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 解释篇[M]. 方书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8:56 -57.。
[3]Dummett M. 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New York,Evanston,San Francisco,London: Harper & Row,Publish-ers,1973: 173.。
[4]Tarski A. Logic,Semantics and Metamathematics [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56: 187 - 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