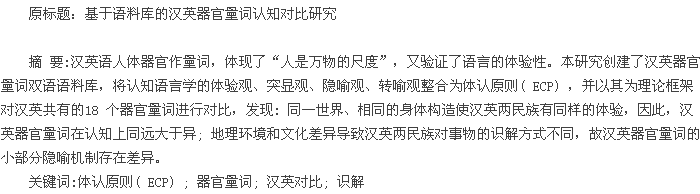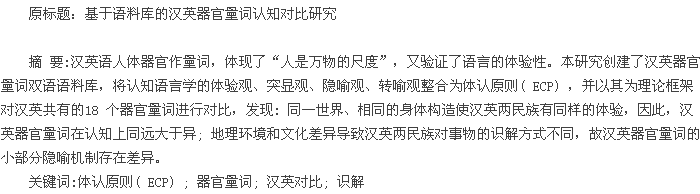
1. 引言
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数量单位的词,包括物量词和动量词( 张志公等 1950’s,转引自何杰 2001: 3) ; 英语语法中没有量词,但存在不少表量的词,其性质和功能类似汉语量词,故本文将其统称为量词( partitive)。器官量词( body partitive) 指用身体器官计量事物或动作数量的词,本文仅讨论汉、英语器官作物量词的现象,不讨论“一手好字,一手厨艺”。
学界对汉语量词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英语量词的研究偏少; 从认知角度对比汉英量词的研究有: 王文斌( 2008: 257-261,2009a: 6-11,2009b: 48-53) 、毛智慧( 2012: 61-64) 、陈道明( 2012: 126-132) 、陈颖子( 2012:281-282 /291) 、张东方( 2013: 7-10) ; 从认知角度研究汉语器官作临时量词的有刘晨红( 2007: 75-77)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器官量词的认知对比研究还是空白。为此,本研究拟建汉英器官量词双语语料库,调查并界定专职和临时器官量词,对比、解释汉英器官量词在认知机制上的异同。
2. 研究方法及语料
笔者调查《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及《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四版) ,综合发现,人体器官共约 50 个,如: 头发、头、额头、脸、耳朵、眼睛等。
调查 BNC ( British National Corpus,一亿单词) 、TimesMagazine( 美国时代周刊 1923 年至今,一亿单词) 、国家语委语料库、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语料库,发现:50 个器官名词中,汉语用作器官量词的有 23 个,共 928例; 英语有 21 个,共 920 例; 汉英共有 18 个。
3. 体认原则( ECP)
本文将体验观、突显观、隐喻观和转喻观综合为“体认原则”( ECP)。
3. 1 思维和语言的体验性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认知和体验紧密联系,可以用“现实 - 认知 - 语言”表示三者之间的关系。Herd-er ( 1772: 64) 从人类体验和认知角度阐述了人类语言的 起 源。Malinowski ( 1935,参 考 Halliday & Hasan1985: 7) 指出“所有词汇的所有意义最终是来自身体经验”。Lakoff & Johnson( 1999: 3) 提出,“人类心智具有体验性”; 他们多次强调,“心智是体验的,意义是体验的,思维是体验的,这是体验哲学的核心”( Johnson & Lakoff2002: 245-249) 。“心智的体验性”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即体验哲学的第一原则( 王寅 2005: 50) 。
3. 2 认知观( 突显观、隐喻观和转喻观)
3. 2. 1 突显观
“突显是引导认知加工的三大原则之一。突显作为注意力的焦点能反映不同的侧面。”( Langacker 1995: 1-62) 突显观是认知语言学三大基本方法( 经验观、突显观和注意观) 之一( Ungerer & Schmid 2001: F40) 。“人的注意力更容易观察和记忆事物比较突显的方面。”( 赵艳芳 2001: 99)
3.2. 2 隐喻观和转喻观
1) 隐喻和转喻———两种不同的认知机制。Lakoff &Johnson( 1980: 171-172) 强调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事物来理解、体验某事物。亚里士多德( 2003: 339) 把转喻和提喻都归为隐喻。Lakoff & Johnson ( 1980: 36-40) 指出,“和隐喻一样,转喻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一。它基于我们的体验,是语言体验观的重要部分”。Radden & Kvecses( 1999:17-21 ) 认为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一个认知过程。
2) 隐喻的两个域。认知语言学家对概念隐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如: Deignan ( 2001) 和Kvecses ( 2002: 16-19) 先后对英语中的始源域和目标域作了系统调查,分别列出 12 和 13 种常见的始源域,都把人体列为第一个、最常见的始源域。Kvecses ( 2002:20) 调查了最常见的目标域,主要是情感、欲望、思想等,未涉及人体。
3) 转喻的分类。转喻共 9 类( Ungerer & Schmid 2001:115-116) ,其中两类为: + PART FOR WHOLE + ( all handson deck) ; + CAUSE FOR EFFECT + ( his native tongue isGerman) 。
4) 转喻的始源域选取规则。Langacker ( 1993,转引自 Panther & Radden 1999: 30) 把转喻理解为一种参照点现象。识解的时候,始源域和目标域都出现在概念中。但是,总是一个比另一个更突显并且被选作始源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各种相对突显的规则: 人> 非人; 整体 > 部分; 具体 > 抽象; 可见 > 不可见。
4. 汉英器官量词的认知分析
4. 1 汉英器官量词的体验性
王寅( 2005: 50) 指出: “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体验世界…人类通常把自己的身体经验作为衡量世界的标准。”汉英器官量词体现并验证了人类心智和语言的体验性以及 Protagras 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原理。
人体本身占据一定空间,因此能够被借用为一个测量工具来表示现实世界乃至精神世界的事物的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换为“人体是万物的尺度”。人体作为人类自身最熟悉的事物之一,必然在形成人类认知概念即量的概念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人类首先通过身体与外界接触逐渐认识并体验外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林书武 2002: 38-45) ,人体作为一个实体,首先被人类自己认识和体验,然后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映射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身体本身映射到体外,从具体到抽象。
4. 2 汉英器官量词的突显和隐喻
“突显作为注意力的焦点,能反映不同的侧面”( Langacker 1995: 1-62) 。中心词和量词之间的搭配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制于突显。量词表示中心词的量且突显其某一属性。
4. 2. 1 Y 是人体( Y IS HUMAN BODY)
隐喻 Y IS HUMAN BODY 中,人体器官是始源域。即人体器官被用来描述并计量事物。隐喻性器官量词指被概念化为始源域并且描述事物的量的器官名词。
1) 隐喻性器官量词的始源域研究。在隐喻性器官量词表达中,器官名词是始源域,中心词是目标域。调查发现,汉英隐喻性器官量词分别是: 头、眼、口、指和指甲,共 5 个; body,hair,head,ear,neck,shoulder,breast,hand / handful,finger,nail,共 10 个。汉语最常见的隐喻性器官量词( 始源域) 是口,英语是 handful,汉英共有的为: ( 手) 指( finger) 、头( head) 、指甲( nail) ,指甲为汉英最不常见的始源域。
2) 隐喻性器官量词的映射。“当始源域应用到目标域时,目标域只有一些而非全部方面得到聚焦显现”( Kvecses 2002: 79) 。认知语言学把这些方面称为映射( highlights) 。隐喻性器官量词的映射是身体器官的某一方面特征( 如: 形状、数量、位置等) 投射到中心词。( 1) 映射: 形状。汉英共同的隐喻性器官量词( 手指、头、指甲) 有共同的投射机制: 形状投射。人头的形状( 圆形) 投射到大蒜、莴苣、包菜和洋葱等; 人类手指的形状( 长条形) 投射到雨、膘、光、水、土地等; 人类指甲的形状投射到土和光。因此有“一头蒜,四指雨,一指甲土,a head of garlic,a finger of light,a nail of light”等表达,其中,器官量词是始源域,其形状被投射到目标域上。另外,“一眼泉水,1000 眼井,三口钟/大缸,a neck ofland”等表达中,“眼”“口”和“脖子”的形状分别投射到相应的中心词( 目标域) 。( 2) 映射: 数量。器官作始源域,其数量属性被投射到目标域上的有: body,hair,handful,如 a body of dirt,a hair of real life,a handful ofpeople 等,这里 body 数量之多的属性被投射到 dirt,hair和 handful 数量之小的属性分别投射到 life 和 people。( 3) 映射: 位置。器官作始源域,其位置属性被投射到目标域上的只有: ear,如: an ear of corn/ wheat。
4. 2. 2 人体是容器( HUMAN BODY IS A CONTAIN-ER)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容器,有一个分界线和内 -外”( Lakoff & Johnson 1980: 29) 。赵艳芳( 1995: 67-72) 指出容器隐喻是一个概念隐喻,人类把容纳经验投射到其他领域,如: 房子、森林甚至其他无形的或者抽象的事件、行动、活动、状态等。因此,由隐喻“人体是容器”派生出一系列容器隐喻: 眼睛、嘴、胸膛、肚子等是容器。二维的人体器官———脸,也可被视为一个容器,有里外之分,能容纳各种面部表情,比如欢乐、愤怒、忧伤等,还有皱纹、麻子,甚至什么都不装。汉语有大量类似“满脸雀斑,一脸兴奋,一脸苦笑,一脸沉默”的表达。另外很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道,“突然笑不知去向,只余个空脸,像电影开映前的布幕”( 向二兰2007: 28-31) 。显然,这里的“脸”是一个比喻性容器,“空脸”就是脸上什么都没装。
在“人体是容器”的概念隐喻中,人体器官是目标域,容器是始源域。容器的属性即可以容纳物体或者物质,占据一定空间,故其中的物体/物质可被计量。这些属性通过隐喻被投射到人体可以容纳物体、物质甚至抽象事物( 情感、力量等) 的相应部位。语料库统计显示,汉英语有相当一部分身体器官被隐喻化为容器,可容纳事物,并通过其容量来计量事物。
1) 三维容器。( 1) 容纳物体 / 质的隐喻性三维容器( HUMAN BODY IS A CONTAINER FOR SUBSTANCE) 。在“一口茶,一嘴白沫/黄牙,两眼泪水,a mouthful of tea,handfuls of grain,an eyeful of bilge water”等表达中,“口 /嘴”、“眼”、“手”等被隐喻为三维容器,是目标域,容纳其计量的物体/质。汉语容纳物质的三维隐喻性容器按频次由高到低排列: 口/嘴、眼、身、肚子、胸膛,语料有147 例; 英语有 mouth,hand,eye,arm,belly,chest,语料有 148 例。汉英最常见的、容纳物质的三维隐喻性容器( 目标域) 是“口/嘴”,最不常见的是“胸膛”。( 2) 容纳抽象事物的隐喻性三维容器( HUMAN BODY IS A CON-TAINER FOR ABSTRACT THINGS) 。
本文“抽象事物”指心理活动( 如: 情绪、面部表情、梦幻、主意等) 、抽象事物( 如: 潜力/质、能力、知识、信息、传播、报告、话语等) 以及负面的事物( 如债务、灾难、疾病、噪 音、坏 习 惯、坏 行 为 等) 。Lakoff & Johnson( 1980: 25) 指出,“我们( 特别是我们的身体) 与客观事物的体验为大量的本体隐喻提供了基础,这些本体隐喻就是把事件、活动、情绪/感、主意等视为物体和物质”。
上述抽象事物之所以能被人体器官计量是因为它们被隐喻化为物体或物质,被人体某器官容纳,故能被计量。汉语容纳抽象事物的隐喻性器官量词按频次排序为: 肚子、腔、手、身、头/脑子、耳朵,语料 130 例( 如: 一肚子学问,一耳朵噪音,一头雾水等) ; 英语为: earful,headful,mouthful,stomachful,bellyful,eyeful,语料 24例( 如: an earful of criticism,a headful of ideas,a stomach-ful of courage 等) 。汉英只有 4 个器官 ( 肚子 / bellyful,腔/stomachful,头/脑子/headful,耳朵/earful) 相同,但其频次差异很大。在概念隐喻“人体是容纳抽象事物的容器”中,汉英没有共同的器官量词被隐喻化为最常见的目标域。汉语最常见的目标域是肚子,最不常见的是耳朵,英语最常见的是耳朵,最不常见的是肚子和眼睛。
2) 隐喻性二维容器。( 1) 容纳物质的隐喻性二维容器。汉语中如棉衣、尘土、汗、胡子、泥巴等物质,英语如 hair,beer 等物质附着在人体器官上,其量很难准确计量,故其附着的器官被借用来计量上述物质。汉语器官量词隐喻化为容纳物质的二维容器,按频次排序为:
身、头、肩、脸、脖子、手、腿、嘴/口、胳膊、膀子、胸脯、头发,共 12 个器官,语料 309 例( 如: 一身汗/污水,一头汗,一胸脯勋章等) ,英语为: leg,head/ headful,breast,faceful,fingerful,共 5 个器官,语料 39 例 ( 如: a leg oflamb,a head of hair 等) 。可见,汉语最常见的目标域是“身”,最不常见的是头发、膀子及胸脯; 英语最常见的是“leg”,最不常见的是“fingerful”。汉英两种语言器官量词隐喻化为二维容器的用法差异很大,汉语的器官量词及其相应表达都远远多于英语,但是也不乏相同之处:
汉、英语中,“头”( head/headful) 均排在第二,“脸”( faceful) 均排第四。因此,“头”和“脸”是汉英共有的容纳物质的隐喻性二维容器。( 2) 容纳抽象事物的隐喻性二维容器。人体器官还可以隐喻化为容纳抽象事物的二维容器,计量债务、灾难、疾病、潜力等抽象事物。依据本体隐喻( Lakoff & Johnson 1980: 25) ,这些抽象事物之所以能被计量是因为它们被隐喻化为实体或者物质。
调查发现,汉语容纳抽象事物的隐喻性二维容器按频次排序为: 脸、身、肩,语料 54 例( 如: 一身流氓习气,一脸笑容,一肩幻梦等) ; 英语为: faceful,mouthful,语料2例( a faceful of social outrage,a mouthful of ulcers) 。汉英语中,脸均被概念化为隐喻性二维容器( 隐喻载体) 计量抽象事物。
4. 3 汉英器官量词的突显和转喻
“转喻是意义延伸的最基本方式之一。”( Taylor2001: 124) 转喻涉及到突显和相邻性 ( 赵艳芳 2001:115) 。调查显示,汉英转喻性器官量词并非随意用来计量中心词,而是受制于器官的突显程度。
1) 转喻关系: 部分代整体 ( PART FOR WHOLE)
“部分代整体”是一个 ICM 中最突显的部分被人们的认知选用来代替整体。器官量词的转喻关系暗示出这些器官是构成人体这个 ICM 最突显的部分。语料调查显示,汉语“部分代整体”转喻性器官量词有头和口,语料共 130 例( 如: 一头野象/肥猪,三头牛,两口人等) ; 英语只有 head,语料共 9 例( 如: A head of cattle,six hundredhead of sheep 等) ; 汉英语共有的此类器官量词为头( head) 。“头”( head) 是人体最突显的部分,最重要,是智慧乃至生命的象征,因此最能引起注意,能代表整个人体。事实上,汉语的“头”最初是用来计量人的量词,古汉语有“一头人”( 高航、严辰松 2007) 的用法。久而久之,“头”被用来一些体积大的动物,如: 一头牛、一头牲口等。语料库显示,汉、英语中,“头”( head) 均用作专职量词计量体积大、头突显的动物,如: 牛 ( cattle) 、羊( sheep) 、猪 ( pig) 等。
2) 转喻关系: 原因代效果( CAUSE FOR EFFECT)
汉英“原因代效果”转喻性器官量词均为“嘴”( mouth-ful) 和“膀子”( armful) ,其语料相似,分别为 8 例和 7例,如: 一嘴地道京腔/湖南话,一膀子力气,a mouthful ofoaths / curses,mouthfuls of words,an armful of romance,意为“X 创造 Y”( X produces Y) 。
相对其产生的效果如方言、话语等,人的嘴有形、更突显。另外,人们由于认知上受到相邻关系的影响,倾向于选取嘴来代指并计量其产生、与其处于同一个 ICM的效果。类似地,与胳膊产生的效果如力气、浪漫( ro-mance) 相比,胳膊有形、更突显,并且受相邻关系的影响,在认知上胳膊、膀子与力气、浪漫( romance) 处于同一个 ICM。因此,人们倾向于选取“膀子”来代表并计量其产生的效果。
4. 4 汉英器官量词异同的认知阐释
4. 4. 1 体验性视角下的相同点
“人的器官,尤其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器官,都有一定的形体,占有一定的空间,人们容易认知,获得体验,所以人的认知经验就为由具有空间性的器官去表达认识抽象的数量提供了可能性。”( 刘晨红 2007: 75-77) “人类相同的身体构造和感知器官决定着汉英两种语言在人体器官及其名称的认知功能与规律方面具有同大于异的特点。”( 卢卫中 2003: 23-28) 汉英器官量词存在诸多相同点,其深层原因在于人类认知和语言的体验性。
由于人类的度量衡概念来源于身体对世界的体验,汉英民族共享同一世界,有大致相同的生理结构,因此其认知能力和语言有共同之处。器官量词,源于相应的器官名词,是语言的一种具体运用,具有体验性,且受人的认知机制( 隐喻和转喻机制) 驱动。同一个世界和相同的身体构造和感官使汉英两个民族有同样的体验,这是汉英器官量词在认知机制上的同远大于异的根本原因。
4. 4. 2 识解视角下的差异
人类相同或相似的体验并不能产生完全相同的语言表达,即概念相同,但其表达相异。Langacker 强调,“我们对同一情景有多种识解方式。”( 王寅 2006: 24) 由于处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语言社团,汉英两个民族有不同的识解方式,在语言表达上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同样的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有不同的表达形式。
识解从五个方面描述: 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和突显( Langacker 1991: 4) 。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文化背景导致汉英两个民族从不同的视角来识解身体器官和及其计量物,突显角度也不同。1) 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来源于人与外界的互动。张岱年、方克立( 2004: 23) 认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导致人们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条件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语言。英国多岛屿、四周被水包围,且呈狭长型,因此,英语中有不少器官量词用来计量海洋、陆地、水、岛屿等( 比如: a tongue of land,a finger of water,aneck of sea,a neck of land,a shoulder of land 等) 。汉语器官量词无此类用法,这与中国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2) 文化背景。汉英两个民族生活在不同地方,其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对计量概念有不同的识解方式,其视角和突显角度表现出较大差异。汉民族更倾向于形象思维,而英民族更倾向于抽象思维。在度量衡方面,汉民族更倾向于用具体的、可见的身体器官来计量事物。因此,汉语的器官量词要多于英语,其语料比英语丰富。
5. 结语
汉英语料库对比研究发现,汉、英语中,共有 18 个相同的人体器官都能通过隐喻或转喻方式计量具象事物和抽象事物,相同点如下: 1) 在概念隐喻 Y IS HU-MAN BODY 中,汉英共有的始源域为手指、头和指甲,“头”已固化为专职量词计量圆形根茎植物,如大蒜、包菜等。汉语最常见的始源域是口( 68. 54%) ,英语是手( 56. 12%) 。2) 在概念隐喻 HUMAN BODY IS A CON-TAINER 中,汉英共有的、最常见的目标域是“口 / 嘴”( 汉 39. 71%,英 72. 09%) ,共有的、最不常见的目标域是胸膛 ( 汉 0. 36%,英 0. 58%) 。3) 概念转喻 PARTFOR WHOLE 在器官量词中未发现 WHOLE FOR PART语料,汉英共有的转喻性器官量词是“头”,均已规约为专职量词计量牛、猪、大象、鲸鱼等体积较大、头突显的动物。4) 概念转喻 CAUSE FOR EFFECT 在器官量词中未发现 EFFECT FOR CAUSE 语料,汉英共有的转喻性器官量词是“嘴”和“膀子”,意为“X 创造 Y( X producesY) ”。
同一个世界和相同的身体构造和感官使汉英两个民族有同样的体验,因此,汉英器官量词在认知机制上的同远大于异。当然,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不同,汉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识解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了语言表达的差异。汉英器官量词的差异主要存在于隐喻性器官量词作始源域和隐喻性二维容器两方面。
参考文献
[1]Deignan,A.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uiders: 7 Metaphors[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Halliday,M. A. K. & Hasan,R. Language,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M]. Victoria:Deakin University,1985.
[3]Herder,J. G. 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M]. 1772.( 《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4]Johnson,M. & Lakoff,G.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J]. Cognitive Linguistics,2002( 3) : 245-249.
[5]Kvecses,Z.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2.
[6]Lakoff,G. & 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7] Lakoff,G. & Johnson,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Basic Books,A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1999.
[8]Langacker,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 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000;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9]Langacker,R. W. Raising and transparency[J]. Language,1995( 71) : 1-62.
[10]Panther,K. & Radden,G.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
[11]Quirk,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72.
[12]Radden,G. & Kvecses,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 InPanther,K. & Radden,G. ( eds. ) .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Thought[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Company,1999: 17-21.
[13]Taylor,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14]Ungerer,F. & Schmid,H. L.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15]陈道明.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量词分类与翻译[J].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 : 126-132.
[16]陈颖子,陈扬一,王银霞. 英汉量词隐喻比较研究[J]. 外语研究,2012( 6) : 281-282 /291.
[17]高 航,严辰松. “头”的语法化考察[J]. 外语研究,2007( 2) :7-11.
[18]何 杰.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1.
[19]林书武. 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J]. 外国语,2002( 1) : 38-45.
[20]刘晨红. 器官名词作临时名量词的认知分析[J],修辞学习,2007( 3) : 75-77.
[21]卢卫中. 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J]. 外语教学,2003( 6) : 23-28.
[22]王文斌. 汉英“一量多物”现象的认知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 4) : 257-261.
[23]王文斌. 论汉英形状量词“一物多量”的认知缘由及意象图式的不定性[J]. 外语教学,2009a( 3) : 6-11.
[24]王文斌,毛智慧. 汉英表量结构中异常搭配的隐喻构建机制[J].外国语文,2009b( 3) : 48-53.。
[25]毛智慧,王文斌. 汉英名量异常搭配中隐喻性量词的再范畴化认知分析[J]. 外国语文,2012( 6) : 61-64.
[26]王 寅. 认知语言学探索[M].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5.
[27]王 寅. 认知语法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8]向二兰.“脸”的隐喻意义探源[J]. 外语学刊,2007( 3) : 28-31.
[29]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0]张东方,卢卫中. 名量词的认知理据: 基于象似性的汉英对比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 6) : 7-10.
[31]赵艳芳. 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 4) :67-72.
[32]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3]亚里士多德. 修辞术. 亚历山大修辞学. 论诗[M]. 颜一,崔延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