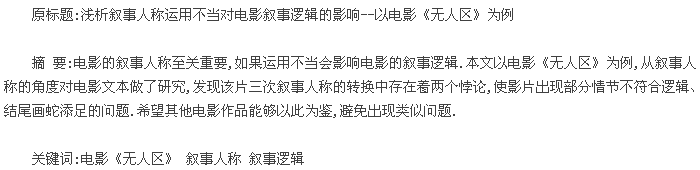
电影的叙事人称是一个重要且微妙的问题,叙事人称运用得好,电影行云流水引人入胜,但如果运用叙事逻辑不当,则可能影响观众对电影的欣赏与理解,甚至会影响影片的叙事逻辑.《无人区》是宁浩执导的国内首部西部公路片,影片的票房和口碑都不错,但是我们细细揣摩分析,却发现影片因叙事人称出现了一些逻辑上的纰漏.本文从该片为例,分析叙事人称运用不当如何影响叙事逻辑,希望其他电影作品能够以此为鉴,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一、何为电影中的叙事人称
电影尤其是故事片作为叙事本文,往往面临叙事人称的问题.电影由创作者(导演、编剧)来讲述,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经常经由创作者的"代言人"即叙述人来了解故事情节.例如在《红高粱》中,我们听到的是"我",即影片主人公的孙子来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在《阿甘正传》中,是"我"---阿甘在给我们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叙述人是联系创作者与影片中人物的中介,是引领观众进入故事的"领航员"."通过对叙述人的身份与层次的确认与划分,我们能够辨认出作者的意图与风格,故事的重心与指向,观众的'视野'与目光所在."[1]
因此叙述人这一角色在影片中至关重要,选择不同角色或不同角度的叙述人,影片的风格、意境可能截然不同.
李显杰在《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一书中将电影的叙述人分为第三人称的"它"、"它-他"、"他"与第一人称的"我"以及"多个我"或"多重声""、摄影机视点"等."完全不露叙述痕迹而由影像自行展示的'呈现式'叙述,简称为'它'者叙述;由字幕插入构成的'影像 + 字幕式'叙述,简称为'它-他'者叙述;以第三人称画外音代表的'解说式'叙述,简称为'他'者叙述."[2]
第一人称的"我"者叙述又分为画外"我"与画内"我",画外"我"重在追述往事,如电影《红高粱》中的"我"追述的是"我爷爷我奶奶"结合、酿酒、抗敌的往事,《走出非洲》中的"我"追忆的是"我"年轻时在非洲的生活与感情经历;画内"我"重在倾诉心声,如《野草莓》中的伊萨克·伯雷教授通过内心独白带我们进入他的梦境,"我"的倾诉不是回忆,而是"我"当时的所思所想.
许多电影的叙述人一般是以上几种类型中的一种,但也有不少的电影运用了多个叙述人的视角来结构电影本文.例如电影《我这一辈子》影片的大部分运用的都是画外"我"的叙述,但影片在 8 分左右时有一段关于"我"是否要做巡警的内心独白,这应该是画内"我"在吐露心声,同样影片在将近结束时有大约半分钟"它"者叙述,展现的是"我"冻饿而死之后儿子海福同其他八路军战士解放北京城的内容,因此仔细考究,影片运用了三种叙述人:画外"我"、画内"我"以及第三人称的"它".电影《走出非洲》运用的主要是画外"我"者叙述,但是影片在结束时用字幕提示我们"凯伦·伯利森在1934 年用艾莎·丹森的笔名出版她的第一本故事.她从未回到非洲."这又明显地从画外"我"转向了第三人称的"它-他"叙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 2013 年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影片主要是通过"叶问"的回忆推进情节,但是在影片中也多次运用字幕来表明年代和故事背景,如"一九三六年,广东 佛山"、"一九五零年,大年夜,香港"、"一九六零年,张永成病逝,叶问终生未再踏足佛山"等,因此叙述人是画内"我"与"它-他"相结合.
二、电影《无人区》中的三种叙事人称
具体到电影《无人区》,徐峥扮演的律师潘肖在影片一开始便以画外音讲到"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而我们的故事得先从这只鸟开始说起",这是以画外"我"的身份在追忆.但是随后影片中出现的四处潘肖的内心独白又明显地带有画内"我"的痕迹,如影片中潘肖赶到西部某城刚下火车时的独白"现在我特别想告诉我的老师,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因为放弃自私,而是因为人会用火."又如潘肖在被鹰贩子老二(由黄渤扮演)打伤后"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我就像那只猴子一样,置身在这猛兽横行的远古时代……","现在我……"的表述是明显的画内"我"的语气语境,展现的是"我"的独白、"我"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在影片末尾,又出现了"它"者叙述人的视角.此时潘肖为了救余男扮演的舞女李雨欣与鹰贩子同归于尽,电影的叙事角度又转向全知全能的"上帝"---"它"视角,为我们展示了李雨欣被警察救出,逃离无人区后与陶虹扮演的舞蹈老师之间的交流并获得其帮助找到工作的一段故事.因此纵观整部影片,叙事人称有三种:从画外"我"转向画内"我",最后又转向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它". 三种叙事人称的使用和转换存在一些问题,使得电影《无人区》的叙事逻辑出现两个悖论.
三、悖论之一:部分情节不合逻辑
首先,画外"我"出现的场合多是回忆,"作为叙述人的'我'与故事中的'我'不处于同一时空之中,作为叙述人的'我'的年龄要大于故事中的'我'的年龄."[3]例如《情人》、《走出非洲》等影片均是老年的"我"回忆自己年轻时的往事.但很少有电影中回忆往事的"我"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除了鬼怪片或者追求怪诞诡异风格的电影之外),一个死人给我们讲述故事是不符合常理的,讲述者在讲述往事时应该是活着的.假若真的是关于已故之人的故事,往往是通过留下某种媒介将我们带入"我"的故事,如《本杰明·巴顿奇事》中已故本杰明的故事,是通过黛西女儿读本杰明日记的方式引入.
在电影《无人区》中一开始的画外"我"---潘肖给我们讲述"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时,他应该是已经经历了整个事件,以回忆追述的口吻回顾在无人区的遭遇,可是随着影片的展开,我们突然发现,如果他经历完所有事件再回来给我们讲述故事是不可能的---他的最终结局是与鹰贩子同归于尽,一个在结局时突然死去的人,在影片开头以画外"我"回忆故事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可以说是该影片在叙事人称转换时出现的第一个悖论.
作为第一人称叙事的"我"在影片中死去的情节在很多作品中也存在,只要解决好叙述时态的问题即可.画外"我"者叙述在影片中是以"现在时态"的语气给我们"讲述"故事,带有现场交流的性质,那么只要在画外的"讲述"、"解说"进行时,我们能从影片的一两个镜头获悉这个"我"可能已经暮年或历经沧桑,但是"我"依然是活着的,那么影片中就不会出现死去的人讲故事的矛盾.例如在《我这一辈子》中,影片一开始是"我"的大段独白,但是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我"穷困潦倒,但是"我"倚着电线杆子回忆四十年前的往事时依然是活着的.在影片的最后镜头又回到"现在"的我,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本性善良却胆小怕事的"我"在死前的最后时光.在整个电影的回忆部分,这个不断用旁白给我们讲故事的"我"是"活着"与我们交流的,这是符合逻辑的.电影《无人区》如果在一开始给一两个潘肖临死前的镜头,再用旁白注解"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从一只鸟开始说起",那么在叙事逻辑上会更完整合理一些.又或者影片把这个开始的旁白去掉,即不使用画外"我"的叙述,也不会造成这种逝去的人讲故事的逻辑错误.
四、悖论之二:结尾画蛇添足
《无人区》叙事人称使用上的第二个矛盾在于影片最后要不要使用"它"视角来描绘舞女李雨欣逃出无人区后的"美好生活".在以画外"我"或者画内"我"为主要叙事人称的电影中,出现第三人称的叙事人并不突兀,但是叙事人称的这种转换往往是为了表现电影主题.例如《走出非洲》最后的字幕"凯伦·伯利森在 1934 年用艾莎·丹森的笔名出版她的第一本故事.她从未回到非洲."表明主人公之后从未回到过非洲,已经走出了非洲的往昔,紧扣影片主题"走出非洲";《一代宗师》中影片末尾打出字幕"一九七二年,叶问病逝香港,一生传灯无数,咏春因他而盛,从此传遍世界."也紧扣了电影名称"一代宗师",因此叙事人称的转换是为了更好地点出电影主题.而在《无人区》中,影片最后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用全知全能的"它"讲述了舞女李雨欣被救出,遇到善良的舞蹈老师陶虹,讲述并忏悔自己在无人区那几年的非人日子,最后获得陶虹帮助,成为可爱天真孩子们的助理老师,这段情节是否扣住了"无人区"的主题,其实很值得推敲.影片在之前的故事行进中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展示了无人区中人性的善与恶,我们通过电影看到李雨欣在无人区里经历了出逃、与潘肖起争执、看见鹰贩子老二开枪打死打伤众人、被其劫持、被黑店父子追回、被鹰贩子老大胁迫甚至活埋直至最后被潘肖救出,历经这么多磨难逃出之后她只要有一线希望也不会再去过"无人区"那种日子;从她想办法救潘肖的片段我们也看到了她的善良与机智,凭借她的善良与机智找一份谋生的正常工作应该也不是难事.因此关于李雨欣逃出之后是否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或者说"幸福生活",其实影片无须赘言.影片在潘肖死去李雨欣瘫坐在地上看点着的钱币漫天纷飞的瞬间结束即可,这个无言的结局留给观众的思索想象空间可能会更大,最后的"遇到贵人救助,与孩子打成一片"的情节反而有些画蛇添足.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影片一头一尾的两次叙事人角度的转换并无必要,这个画外"我"和第三人称"它"的视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影片逻辑上的严谨性、意义上的深刻性,如果删掉这头尾,丝毫不影响影片主题的展现,反而可能会更深刻.
通过对电影《无人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叙事人称运用不当对电影逻辑层面的影响.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应该值得各个角度的推敲考量,因此除了考虑故事是否好看,票房是否有保障的前提下,导演还应仔细琢磨一下叙事人称选用是否得当,以免出现因叙事人称的不当运用导致影片逻辑出现硬伤.
电影《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经典同名长篇小说。故事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以田小娥与三个白、鹿长辈(族长白嘉轩、乡约鹿子霖、长工鹿三)之间的是是非非及其与白、鹿两姓子弟之间的情感纠葛为叙述主体,描绘了白、鹿两大家族祖...
当毒品开始侵入更多人的生活,不再是印象中的流氓、混混的专属物时,它带给社会将是巨大的灾难,尤其是毒品侵害一个国家的青少年,这种悲凉异常突出。《毒品》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庞大的毒品之网,让人看后只觉得心有余悸。究竟影片是有什么魔法...
一、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20世纪60年代末,霍夫斯泰德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获得了大量数据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文化的效应》于1980年出版。在书中,他提出了文化维度(CultureDimension)概念,这五个文化维度...
电影《时间机器》是根据英国科幻小说家乔治威尔斯(GeorgeWells)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该影片由西蒙威尔斯(SimonWells)执导,盖皮尔斯(GuyPearce)主演。影片讲述了大学应用机械工程系青年教师亚历山大哈迪根博士在一次约会中遭遇抢劫,深爱的女友...
小说《崩溃》(ThingsFallApart)尼日利亚裔美国著名作家齐诺瓦阿切比(ChinwaAchebe)的代表作,1959年发表后立即获得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至今,本书在世界的销售已经超过1100万册,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一切都崩溃了,价值已难持守,世界上...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电影改编需要重新建构适合其美学特质的诗性传统.而艺术诗性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美的艺术形式,如电影中生动美丽的艺术形象、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清新的构图和细腻真挚的情感呈现.儿童电影以朴真唯美、灵动自然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
现代科学技术随着时代的不断革新与发展,愈发的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高科技,大制作,高投入,电影创作上跨国或跨地区合作,已成为欧美电影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特色标签。但在这些光影背后,欧美国家的电影无论在历史背景、本体的艺术表达、观众的...
一、介绍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故事发生在1953-1954年期间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影片讲述了一位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艺术史女教师凯瑟琳和女学生们,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如何通过摆脱男性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身份天使和魔鬼,...
摘要盘点新世纪以来大陆青春校园电影,电影创作者跨越了特殊时期意识形态思想倾向的约束,以传播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为己任,传承延伸大陆电影艺术精华为责任,将镜头对准当下流行文化与娱乐元素,以不同与往时的青春回忆为主线、隐含观众,通过拍...
电影《霸王别姬》和《梅兰芳》拍摄的时间整整相隔了十六年,十六年时光流转,物是人非:陈凯歌的导演梦在《霸王别姬》之后起起伏伏,甚难出彩;哥哥张国荣斯人已逝,百转千回的程蝶衣只能在银幕上反复品咂;2008年《梅兰芳》的上映让影界认为陈凯歌想要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