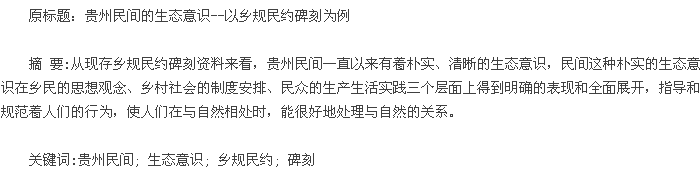
人类的生计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自然环境,这决定了人类只有在所处的自然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着生点,选择有利于生计的利用对象,进行经济活动,以维系生存。贵州山多地少,民众的生产生活与山林关系密切,因此民间很早就有“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生计方式和爱林护林传统,虽然这种爱林护林的生态养护实践是原始、朴素的,但民间这种“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生计方式却表现清晰的生态意识,具备了一定的生态向度。
这种朴实的生态意识在乡民的思想观念、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三个层面上得到明确的表现和全面展开,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在与自然相处时能很好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
一、思想观念层面
( 一) 人天和谐的生态认识观
人天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看待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上,贵州民间非常重视养护生态,维护好生态环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民间碑刻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俯拾皆是。同治八年( 1869 年) 黎平县长春村所立禁碑言: “吾村后有青龙山,山林葱茏,四季常青,乃天工造就福地也。”为保护好村后山良好的植被,村民聚集在一起饮生鸡血酒,发下盟誓: “凡我后龙山与笔架山上一草一木,妄不得砍,违者,与血同红、与酒同尽。”[1]清咸丰四年( 1854 年) 贞丰县《长贡村护林碑》载: “众议前后左右山林,禁蓄以培风水。”并规定“不准砍伐,亦不准放牛马践踏入内。”又如清咸丰十年( 1860 年) 仁怀县薛家岩士民公立的护林碑文云: “县属礼博里薛家岩一带,林深箐密,洵属一隅,钟毓之秀,实为士民风水攸关,理应护蓄栽培。”故而禁止“戕伐延烧”,违者“许即扭禀赴县,以凭究治”[2]。从以上几则材料可以看出,乡民往往是从风水的角度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及维护好村寨周边的良好生态。然而,这同样体现了民间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在民众传统观念中,能否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关系风水好坏的重要因素,而林木茂密葱郁、环境宜人则是好的风水环境的具体表现,正如风水理论认为: “草木郁茂,吉气相随。”[3]因此,民众常希望通过植树造林或护好植被获得好风水,“盖闻黎山蓄禁古木,以配风水”[4],培植和护好风水林木便成为乡民的神圣职责与普遍行为。在一些乡规民约碑刻中,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述和规定。兴义县绿荫村“永垂不朽”碑载: “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赖乎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两山放牧牲畜,草木因之濯濯。
掀开石厂,巍石遂成磷磷,举目四顾,不思叹息……于是齐集陈姓面议……于后龙培植树木,禁止开挖。庶几龙脉丰满,人物咸宁。”[5]碑文充分反映了乡民在风水观念的影响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 二) 敬畏天物的生态伦理观
贵州民间,尤其是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普遍有自然神观念和“敬畏天物”观念,他们“崇奉天地、山林、水泽的神鬼精灵和自然物,重祭祀、跳神与禳解等”[6]。对天地万物保持着崇拜与敬畏,尊重生命,这使乡民不敢去触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从江县芭莎苗族就认为树和人一样都有灵性和生命,因此“寨中敬奉的古树和风景树,要以神相待,不准亵渎或砍伐”[7]。“敬畏天物”,在民间不仅表现为一种信仰,而且表现为人们对待生命万物的一种尊重态度。受此影响,乡民往往将村寨周围的大树、林木人格化并加以崇拜,奉其为护寨神树,严禁砍伐。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现存乡规民约碑刻常有记述。例如“民族环保第一村”的锦屏县文斗村的鎸刻于 1876 年的一块环保碑,明确规定: “此为本寨护寨木,蓄禁,不许后代砍伐。”从碑刻内容看出,寨民对古树有崇敬心理,视其为本寨的保护神,十分敬畏,因而禁止砍伐。又如清咸丰七年( 1857 年) 贞丰县《长贡护林碑》载,该村因“有不识之子孙”,砍伐护寨之古树“惊动龙神”,于是“合族老幼子孙合同公议”,并“立碑以示后世子孙,不得妄砍树木”,对古树要细心守护。
对有些动物,民间同样加以崇拜与敬畏,奉其为神灵之物,对它们存有一种仁爱和敬生之情,从不捕杀。梵净山地区的土家族最尊重白虎,视白虎为其远祖廪君死后化身的白虎神。因此,当地乡民从不狩猎老虎。鱼是水族的吉祥物和最为重要的崇尚之物,在婚俗中常作为信物、圣物出现。因而,受到乡民严格保护。都匀市基长水族乡翁降村中有一大池塘,村民称“保寨塘”,塘中鲤鱼大的重达几十公斤,被村民视为“护寨神鱼”,加以崇敬和保护,对塘中鲤鱼村民规定只许投食喂之,不准捕食之。这种“敬畏生命”“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情怀,在贵州民间普遍存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 福泉市谷汪乡诸浒村的《严禁毒鱼告示碑》: “严禁毒鱼,以全生灵。”[8]另宣统三年( 1911年) 瓮安县银盏乡瓮安河上的《禁渔石刻》规定禁止打鱼;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都匀与独山交界处遇仙桥段的《护鱼条款》明示永禁捕鱼,这些碑刻文献资料也都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民间敬畏天物,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观。
( 三) 合理取用万物的生态价值观
现代环境理论认为,人类应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反对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从现存乡规民约碑刻来看,乡民早就认识到这点,他们懂得合理取用万物,珍视资源的重要性。首先,反对杀鸡取卵式的掠夺资源的行为。清末贵州过度捕鱼和用药毒鱼现象非常严重。如“贵阳、安顺、镇远所属乡民,多有毒鱼之事……缘黔中多产茶树,民将子榨油,即以渣饼投置水中,鱼无大小,靡有孑遗,到处皆然。而安顺所属九溪一带,系北桑梓,此习为尤是焉”[9]。针对这种只顾眼前小利,过度捕食的毒鱼现象,安顺九溪附近的鲍屯乡民公议立碑规定:
“禁止毒鱼挖坝,不准鱼鹰打鱼、洗澡,不准赶罾、赶鱼,违者罚银一两二钱。”[10]乡规严禁挖坝毒鱼、鱼鹰打鱼等过度捕食的不良行为,并作出罚款规定,反映了乡民对保护渔业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视。清咸丰年间的《金沙公议“十禁”碑》则明确禁止人们毁堰毒鱼以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多样性。对过度捕食现象见而不报者,乡约也作了相应的处罚规定。清咸丰八年( 1858 年) 贵阳《石板哨十寨乡禁碑》规定: “毒鱼打鸟者,拿获罚银一万口千文,倘见者不说,口亦罚钱五百文。”[11]其次,注重资源保护。贵州境内山多河少,旱灾频发,“十日无雨则亢旱可虞”[12]。因此,民间对水资源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其保护的意识很强。清道光十二年( 1832 年) 安龙县阿能寨岑、韦二姓公议后,立下《谨白碑》告诫寨民: “凡不( 准) 洗菜、布衣,污秽水井。”贵定县苗族聚居地菜苗附近无河流,水资源十分珍贵,为保护生产和生活用水,村民于咸丰二年( 1852 年) 特勒石树碑云: “妇人随到随背,不准洗衣裙井内。”
明确禁止污染生活水源,并对不遵者,作出“罚银一两二钱”的处罚规定。此外,清咸丰年间的《黔西修月城水池碑》,民国佟铭的《迁建火神庙碑记》等碑刻都有保护生活水源的内容。从以上这些碑刻中,可以看出民间对水资源的保护意识。最后,具有“时禁”观念。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民众认识到,万物有其生长规律,因此,取用万物时要做到“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清咸丰五年( 1855 年)安顺水塘寨《安良除贼碑》碑文规定: “不许寨内三四月搜巡蕨菜。”原因是三四月正是蕨菜生长的关键时期,若在此时期采摘会“夭其生,绝其长”。可见,乡民知道适时取用万物,懂得“树木以时伐焉”这个古老的道理。
基于对生态环境的上述认知,为保护环境,维护生态,乡民制定了具有民间法和习惯法功能的乡规民约,形成了具有乡土社会特色的生态保护机制,这就是接下要谈到的制度安排。
二、制度安排层面
在制度设施层面上,民众订立了乡规民约并立禁碑昭众,明确规定了禁止性事项和严格的惩罚措施,利用民间智慧有效处理地方生态问题。
( 一) 规定了禁止性事项
禁止性规定是碑刻乡规民约的主体性内容。乡规民约中禁止性事项主要涉及砍伐树木、破坏植被、污染水源、过度捕食、放火烧林等方面。例如,为保护全寨墓地及附近自然环境,贵阳花溪区高坡乡杉坪寨全村制定了公约,并于清嘉庆十六年( 1811 年) 立下《龙村锁阴碑》规定“不准砍伐林木”; 而清同治六年( 1867 年) 册亨县《秧佑乡规碑》则规定“不准纵火烧林”。以上两则碑刻乡规民约共同的特点是内容简单,禁止性事项单一,而多数乡规民约规定的禁止性事项较多,也比较具体。例如,为保护坡、屯、水,普定县田官乡乡民于民国十一年( 1922 年) 特立《田官乡规民约碑》规定: “屯、坡内不准打石、放牛、割草、砍伐; 水井内不准车水、洗菜……违者处以罚款,见而不报者,与犯同罪。”[4]860碑文明确规定了不准打石、割草、砍伐、井内洗菜等多项禁止性事项,并对违反规定者和知情不报者予以同等处罚的规定。又如,清咸丰元年( 1851 年) ,贵阳下铺村民为保护村周边山坡植被,规定了多项禁止性事项和严厉的处罚措施: “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以上五条若不遵,罚银四六钱是矣。”[13]再如,前文中提到的鲍屯乡民为禁止过度捕食鱼类,公议规定: “禁止毒鱼挖坝,不准鱼鹰打鱼、洗澡,不准赶罾、赶鱼。”这些禁止性事项,是乡民保护自然生态的具体表达。
( 二) 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
乡规民约中的惩罚措施是乡民生态意识显性的文字表达,是乡民为保证订立的禁止性规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而制定的。一旦有人违犯了规定,均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不论亲疏。如贵阳市布依族聚居地瓦窑村订立的公约特别强调“嗣后倘有无知之徒,再开此山,众议罚银十两。从此之后,言出罚随,勿论亲疏,决不徇情”[11]100。体现了乡规民约处罚的严厉性、公平性。乡规民约对违犯条款而制定的处罚形式多种多样。罚款,是最普遍的处罚方式。如清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榕江县冷里“禁条碑记”就有对乱砍伐者处以罚款的内容,碑文载: “不准砍伐生柴,若有乱砍破坏,日后查出,罚钱一千二百文。”[14]清同治八年( 1869年) 立于镇远县全坡村的乡规民约碑则对盗砍不同树种处以不同的罚款规定,“偷窃桐茶盗砍木植,一经拿获,罚钱五百文”若“偷窃杉料材木”,须“加倍处罚”,不论内外亲及贫老幼人等。对明知禁止性事项而故犯者,则予以重罚。普定火田寨熊姓于清道光三年( 1823 年) 制定的护林乡规民约规定,“禁水火、禁砍伐、禁开挖”,并重申“明知而故犯者,罚银十二两”。其次是禀官究治,对乱砍坟地周边林木的严重违禁行为,多鸣官究治。
如咸丰七年( 1857 年) 贞丰县《长贡护林碑》规定“如有妄砍树木者”,必“严拿赴公治罪”。黎平府城乡绅民于清道光八年( 1828 年) 立“公议禁止”碑,严明“三庵上下左右坟墓,其有一切大小树木,日后子孙并众人、山僧,不许砍伐。违者送官究治”[13]293。对那些蛮横、不遵处罚者,同样送官处置。麻江县《小鸡场护林石碑》碑文载: “小鸡场对门之山……周围一例大小竹木、毛茨、生干土石,不准伤残。倘若犯者,要罚银六两……罚不起者,每户灌屎一筒,罕( 喊) 寨。倘若横性者,众同送官究治。”[15]除了罚款、禀官究治这两种常见的惩罚方式外,乡规民约中还有一些民间特有的处罚方式,吃榔规酒、游寨示众等,以警戒寨民严守乡规。
如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年) ,凯里流水寨一寨民偷砍一棵杉树,全寨罚其出钱、出酒于六月六日请全村人吃榔规酒,处罚之严厉可见一斑。有些地方的处罚则更具民间色彩,如天柱县门堂村的乡约规定,若有人偷砍了树木,除罚款 500 元外,还规定这人以后家里死了人,别人不准给这家抬棺、拉牛[16]。这种孤立违规者的处罚方式,在乡村社会警戒作用很大。
客观地说,虽然民间订立的环保型乡规民约,其主要目的或直接目的并不一定就是今天意义的环境保护,但不能就此否认这些乡规民约在客观效果上起到的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的积极作用。
三、生产生活实践层面
在上述生态认知和乡规民约作用下,贵州民间进行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活动。如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立于锦屏县九南乡的《水口植树护林碑》载,“我境水口,放荡无阻”,被人盗砍乱罚,致使其地“古木凋残,财爻有缺”。于是当地村民捐买地界,复种植树木。碑文中记载 20 多人捐买一片山地植树造林,并规定: “禁周围水口树木,一栽之后,不许砍伐,如有犯者,罚银五钱。”[1]101又如锦屏县章山村的“万古碑记”载: “盖闻黎山蓄禁古木,以配风水……前人相心相议论,买此禁山蓄禁古木……至道光年间,立定章程,收存契约捐钱人名,昭彰可考。蓄禁古木成林,被人唆害,概将此木砍净……至光绪七八年间,合村又于同心商议,又将此木栽植成林。不料有不法之徒 ……私将此栽之秧木扯脱,成林高大之苑砍伐枝丫,剥皮暗用,弄叶杀树。合村众人见目睹心伤,殊属痛憾。自今勒石刊碑之后,断不拉坏。若再有等私起嫉妒歹心之人故意犯者,合团一齐鸣锣公罚赔禁栽植章程,另外罚钱拾三千文,违者禀官究治。”[4]857从碑文可知,章山村村民为蓄禁古木作出了不懈努力,道光年间曾“立定章程”,予以保护。后因“被人唆害”,毁林现象严重。光绪初年间,合村又将古木蓄栽成林,不料又遭不法之徒蓄意毁坏。于是,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该村特勒石刻碑,以儆效尤。
应该说,上述两例对保护森林,维护自然生态起到了一定作用。从现存乡约碑刻史料看,民间类似的生态保护行为很多,并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如清咸丰四年( 1854 年) ,道真县思里七甲槐坪花甲老人梅奇冠在从槐坪至旧城必经之路的火烧关路两旁植树,因“其地石多土少,便由山下背土培 植,寒 暑 不 断,坚 持 10 余 年,成 活 千 余株”[4]856。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 ,名叫郑代兴的乡人失火烧了 2 棵树,于是,由“郑子香出首公议”,罚其钱二千,并树碑护林。此后,该处树木茂密,浓荫数里。又如为禁止违禁捕鱼,保护渔业资源,湄潭县高台乡陶泥河下游合江段立有放生碑,放生区域长 10 华里,从 1886 年起,便一直由白瑞廷、白光霞、白明昌三代人管理。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民间的生态保护行为有持续性,并不是零散和不稳定的,效果也不错。
四、结语
生态意识是人们在处理自身活动与所处环境关系时所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及人们为保护环境而不断调整自身的活动与行为,反映了人们对保护环境、养护生态的认知程度,体现了人们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从这点来看,贵州民间的生态意识是清晰的,在乡民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乡村社会环保型乡规民约、民众保护生态的实践活动等层面上得到具体体现。应该说,民间的这种朴实的生态意识,对保护地方环境,养护生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蕴含着一定的利用价值。虽然在现代科学知识面前,乡土知识已处于边缘,但乡土知识与现代知识一样都具有合理性。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认识并有效利用民间朴素的生态知识和智慧处理生态问题,使其转化为全社会和每一个公民保护环境、养护生态的实际行动,也许是构建现代环境理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编幕委员会. 黔东南州志·林业志[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146.
[2]仁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 仁怀县志·附录[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246.
[3]关传友. 徽州宗谱家法资料中的植树护林行为.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J]. 2003. 04
[4]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省地方志·环境保护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857.
[5]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编幕委员会. 黔西南州志·文物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6]成卫东. 转神山———冈仁波齐亲历记[J]. 地理知识,2000( 7) .
[7]杨大昌. 贵州少数民族生态及其现代化建构[C]/ /吴大华,杨大昌. 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专论.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频发对我国司法审判活动的正常运行、法律的权威以及社会秩序稳定均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
严复是我国近代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大师,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大的影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都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对严复的评价及其具体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不但没有统一的认识,就是互相对立...
从研究范畴上分析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还有选择与责任、主观与客观、自在与自为、内容与形式、认知与行为、情感与理性等其他范畴可以考量。...
近来,刘清平、邓晓芒和郭齐勇、丁为祥等人围绕着孔子的父子相隐与现代法治的关联度展开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孔子的观点导致腐败,是现代法治的大敌,后者则认为孔子的观点是现代法治的源头,如此强烈、鲜明的一贬一褒,正犯了孔子强调的过犹不及的方法论错误。...
一、环境权之争环境权本是民法学上的相邻权,近年来,经过环境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各领域学者的研究,将这一民事实体权利发展成了一种具有综合特征的法律权利,现今已经成为各方面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环境权是仅存在于理论上的一项权利,其概...
在国人眼中,柏拉图一词意味着追求一种高尚纯粹的精神理想,不掺杂任何俗世之欲念,最脍炙人口的一句短语便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然而在希腊历史上,柏拉图的确曾经就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向他的导师苏格拉底提问,两人的对话流芳百世,被后人奉为对此最具有哲理的...
坚定不移地推进法治改革,有效突破法治实践中存在的制度难题,努力破除影响法治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法治社会要遵循法制办事,但现实中一些事实性的社会习惯规范才能真正化解纠纷,让民众心服口服的接受认可。在民族地区,由于宗教等习惯的影响依然很大,许多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基于此现实,重视民间法的作用,在法律可接受的范围内...
庞德不仅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也是社会学法学创始人,其在法学研究道路上贡献卓越。作为二十世纪法学界领军人物,他的法学思想以深厚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表述了社会文明、社会控制、法律价值等诸多法律要素的内在关系,司法实践可操作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