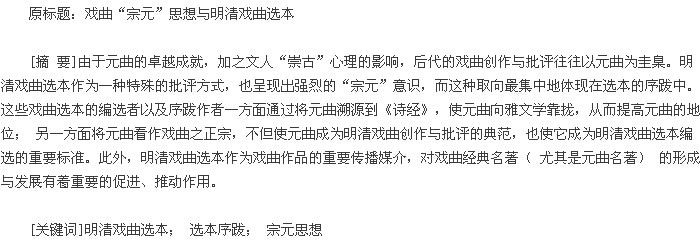
与诗在唐、词在宋一样,戏曲发展到元代也进入了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包括杂剧、南戏在内的戏曲形式日臻完善,既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高明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也出现了《西厢记》、《琵琶记》这样耳熟能详的文学名著。由于元曲的卓越成就,加之文人“崇古”心理的影响,后代的戏曲创作与批评往往以元曲为圭臬。在众多戏曲批评中,明清戏曲选本①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也呈现出强烈的“宗元”意识,这种取向最集中地体现在选本的序跋②中。依笔者目前所见,现确定为明清戏曲选本者约有 64 种。其中,剧选本 28 种,出选本 36 种,这些戏曲选本集中产生于万历、崇祯、乾隆三个时期。约有半数的选本原刻、重刻或重印时都有序跋附于正文之前。初步统计,现有序跋 71 篇,除去王国维、吴梅等近现代学者所作 13 篇外,可作为研究之用的明清人之序跋共 58 篇。本文即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明清戏曲选本情况,探讨编选者及序跋作者论述中所体现出来的宗元思想。选本的发生与以雅为本的观念诉求戏曲从它产生之初就被正统文学拒之门外,往往被斥之以“余技”、“末流”,戏曲的创作更是正统文人所不愿涉足的领域。虽然经历了元代的发展,戏曲在明清时期呈现出比较成熟的状态,但它受排斥、被歧视的情况依然存在。在戏曲选本的序跋中,作者刻意提高元曲地位,往往将之置于与唐诗、宋词相等同的地位上,如息机子《杂剧选·自序》开篇即言: “一代之兴,必有鸣乎其间者。汉以文,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以词曲。其鸣有大小,其发于灵窍一也。”
目的就是为之争取与汉文、唐诗、宋理学同等的地位,以彰显元曲的重要性。但是,仔细研究这些序跋,又不难发现,作者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此。
受儒家“崇古”、“好古”思想的影响,大多数文人都有根深蒂固的复古倾向。在序跋的论述中,作者就非常注重从文体发展演变的角度来寻求元曲的根源,玉阳仙史《古杂剧·序》中言: “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六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
于若瀛《阳春奏·序》也说: “降至《三百篇》,率皆采闾巷歌谣而播之声诗,宜尼父所谓可兴、可观,良有旨矣。《离骚》则楚之变也,五言则汉之变也,律则唐之变也,至宋词、元曲,又其变也。时代既殊,风气亦异。元曲兴而其变极矣。”
邹式金《杂剧三集·自作小引》亦言: “《诗》亡而后有《骚》,《骚》亡而后有乐府,乐府亡而后有词,词亡而后有曲,其体虽变,其音则一也。”
在这些论述中,作者特别强调文体的延续性与传承关系,将元曲的源头直接上溯到《诗经》。元曲作为俗文学的一种,想要发展壮大,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就必须向雅文学靠拢。而《诗经》作为文学的源头,向来被文人视为正统,将《诗经》与元曲联系起来即为戏曲寻找雅文学的来源,化俗为雅,进而提高元曲的地位。黄正位为其编选的戏曲选本命名时,即考虑到戏曲的雅化问题,于是“乃以杂剧之名为未雅也,而显之曰《阳春奏》。《阳春白雪》,和者素寡。黄叔以是命名,岂不为元时诸君子吐气乎”.《改定元贤传奇》的定名亦是此理: “又谓之行家及杂剧、升平乐,今舍是三者,而独名以传奇,以其字面稍雅致云。”
明清戏曲选本在编选过程中往往也遵循雅文学传统,时时比附《诗经》,《醉怡情》就是“撮录其近《风》、《雅》者百余出”结集而成,《杂剧三集》的编选也有“倘亦《小雅》之志,风人之遗乎”的目的。正如有学者所言: “他们努力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比附戏曲与诗歌的关系,极力将戏曲纳入到正统文学观念认可的诗词系统,借着确立戏曲与传统诗词文同源同质同构的亲缘关系来提升戏曲的地位。”
序跋作者不仅将戏曲文体划归于雅文学范畴,其功能也在不断向雅文学靠拢,以求全面地转换戏曲俗文学的面貌,完成其对《诗经》传统的复归。孔子对《诗》的功能有过经典论述,《论语·阳货》中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后来的文人也以“兴”、“观”、“群”、“怨”作为文学创作的至高目标。为了向雅文学靠拢,戏曲的选本也非常重视诗歌的这些功能。程羽文《盛明杂剧·序》中言戏曲之“可兴、可观、可惩、可劝,此皆才人韵士,以游戏作佛事,现身而为说法者也”,《杂剧三集·序》中认为戏曲是“殆真所谓有其文则传其文,可以为鉴,可以为劝者也”.《诗经》之所以得到后代文人的广泛认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将文学创作与社会和政治联系起来,也因此形成了诗歌“美刺”与“言志”的传统,尤其是社会黑暗、民族衰亡的危急时刻,诗歌都能最及时、最有效地表现出来。元曲就特别吸收了诗歌的这种传统。在元代,科举被长期废止,大量优秀文人从事戏曲创作,以抒发其心中不平之气,故而有“一时名士如马东篱辈,咸富有才情,兼善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要而言之,实所以宣其牢骚不平之气也者”,又加之诗文诸多忌讳,因而元曲更多地承担着抒发情怀、尤其是那种抑郁于心的不平之情的重任。明清戏曲选本就特别注重收集这种抒发情感、反映现实的作品。徐翙在《盛明杂剧·序》中就说: “文长之晓峡猿声,暨不佞之夕阳影语,此何等心事,宁漫付之李龟年及阿蛮辈,草草演习,供绮宴酒阑所憨跳! 他若康对山、汪南溟、梁伯龙、王辰玉诸君子,胸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长啸以发舒其不平,应自不可磨灭。”
程羽文序中也言: “盖才人韵士,其牢骚抑郁、唬号愤激之情,与夫慷慨流连,谈谐笑谑之态,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笔底,不能直写而曲摹之,不能庄语而戏喻之者也。”
事实上,《盛明杂剧》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表达个人情感的,《杂剧三集》的编选也就透露出作者的故国之思,表达了遗民作家的激愤情怀。“诗”的另外一个功能被《诗大序》具体阐释为: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其中就特别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这也是诗歌作为雅文学重要的表现之一。戏曲选本在编选过程中也特别以教化功能作为其重要宗旨。《改定元贤传奇》的编选目的即为“激劝人心,感移风化”,《阳春奏》选取作品的原则即为“洎有关风教、神仙拯脱者”,《六十种曲》也是在“几令纯忠孝、真节义黯然不现本来面目”之时,“拈出风化之本原”,《审音鉴古录》非常重视“其能承先志,其辅翌名教”的作用,《缀白裘》九集序亦言: “今举贤奸忠佞,理乱兴亡,汇而成编,其功不在《三百篇》下。”
事实上,从《杂剧十段锦》始,至《元曲选》、《六十种曲》、《今乐府选》中的很多作品都体现着作家或编选者的这一目的。当然,编选者们( 包括序跋作者) 所提倡的教化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宣扬忠孝节义,以此来教化人民,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其文学传统的复归,强调戏曲继承诗词等雅文学的“兴、观、群、怨”,目的是使戏曲由俗化雅,并以此来提高元曲的地位。在明清戏曲选本的序跋中几乎都涉及了选本的教化宗旨,可见序跋的作者对戏曲宣扬教化功能的重视以及借此达到向雅文学进一步靠拢的目的。
明清戏曲选本的编选者及序跋的作者即通过对元曲的溯源,使元曲向雅文学靠拢,从而提高元曲的地位,而明清戏曲选本中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类似《诗经》的社会功用,这无疑也促进了元曲的雅化。
以元曲为宗的选本批评策略明清戏曲选本的编选者与序跋的作者多将元曲看作戏曲之正宗,这不但使其成为明清戏曲创作与批评的典范,也使它成为明清戏曲选本编选的重要标准。孟称舜曾言明代戏曲“间有一二才人偶为游戏,而终不足尽曲之妙,故美逊于元也”,他将元曲视为戏曲创作之圭臬,将尽元曲之“妙”视为戏曲之最高标准,并在与元曲的比较中完成对明清戏曲优劣之判断。所以,明清戏曲创作者“盖自谱者固每掇取元人旧作; 考正声律,藻饰词句,间亦有之”.文人在创作之前每每要参考“元人旧作”,并“考正声律”抑或“藻饰词句”,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接近元人戏曲的真谛,才能真正“得元人三昧”,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达到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邹绮在《杂剧三集·跋》中说: “余既有《百名家诗选》,力追盛唐之响,兹复有三十种杂剧,可夺元人之席,庶几诗乐合一,或有当于吾夫子目( 自) 卫反鲁之意乎。”
不仅将元曲与唐诗相提并论,而且为了进一步说明《杂剧三集》的重要性,作者不惜用“可夺元人之席”这样的评价来提高其本身的地位。那么“元人之席”无疑就成为有识之士挑战的高峰,具有了相当大的号召力。序跋的作者在提及元曲时,也首先言及他们的文学地位,这不仅是一种论述方式,更是一种思维的表达。在他们的思维中,元曲是戏曲的精华,言及戏曲,首推的是元代,宗元思想正是根植在这样的土壤上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戏曲选本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除了序跋之外,编选者的思想与价值取向不是通过文字直接地表达出来,而是渗透于选本所收集的内容以及编选方式之中。由于这种对元人的高度崇尚,戏曲选本的编选者“欲世之人得见元词,并知元词之所以得名也”,并且使元曲“藏之名山,而传之通邑大都”,戏曲选本的编选者往往将大量元代作品收入选本中。《阳春奏·凡例》中即云: “是编也,俱选金元名家,镌之梨枣。盖元时善曲藻者,不下数百家,而所称绝伦,独马东篱、白仁甫、关汉卿、乔梦符、李寿卿、罗贯中诸君而已。”
《阳春奏》现只存 3 种,但据《汇刻书目》,原有元杂剧 20 种,而明代杂剧收录 19 种。虽然元明作品在数量上相差不大,但黄正位却是力言元曲的重要性,“卷内俱是元曲,末以明曲附之,亦见我明作者一斑”.的确,在明清戏曲选本中,《阳春奏》中元明作品的比例确属较均衡的情况,但他却用编排的顺序及方式彰显了元曲的重要地位。以剧选本为例,除去《盛明杂剧》、《杂剧三集》、《六十种曲》( 除《西厢记》外) 这样只收录一个朝代作品或仅收录戏文、传奇的选本外,元代作品所占比例往往较大。从《古名家杂剧》现存的 65 种作品来看,其中有 41 种是元人作品,占总数的 63%.《息机子元人杂剧选》中的 30 种作品,有 24 种是元代作品。《古杂剧》元明作品比例是 17∶3,《元明杂剧》为 18∶ 9,《古今杂剧合选》中的《柳枝集》为 16∶ 10、《酹江集》为 17∶ 13,《今乐府选》所收杂剧中元代作品为 92 种,明代作品为 29 种,清代作品为 40 种,明清两代作品相加的总数也没有超过元代作品的数量,可见戏曲编选者对元代作品的重视。所以,就连选取明代杂剧的《盛明杂剧》徐翙序中也不能不承认“大约元人传十之七,明人传十之三”.可见元曲在当时所占比例之大,这也足以说明元代作品在明清戏曲选本中的地位。
序跋作者评论的兴奋点也集中在元代作家与作品上。吴伟业《杂剧三集·序》中言: “盖金、元之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接。一时才子,如关、郑、马、白辈,更创为新声以媚之。”邹绮也说: “或清商迭奏,传轶韵于金、元,或锦绣纷披,踵妍思于关、董; 或以笔代指,如月明沧海之声,或翻谱为新,有木落洞庭之怨。洵元龟之非宝,知大贝之无奇,而天地元音,亦藉此复振矣。”
阅世道人在《六十种曲·演剧首套弁语》中亦言: “适按《琵琶》,《荆钗》善本,暨‘八义'’三元‘名部,卓然绝调。”
序跋的作者不仅兴奋于对元曲的点评,甚至还引起了争论,如臧懋循《元曲选·序一》就针对当时《西厢记》与《琵琶记》的高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观《西厢》二十一折,则白少可见,尤不欲多骈偶。如《琵琶》《黄门》诸篇,业且厌之。”
肯定了《西厢记》,并指出《琵琶记》宾白过多,且多骈偶的缺点。他还参与了何良俊与王世贞的《幽闺记》与《琵琶记》高下之争: “何元朗评施君美《幽闺》远出《琵琶》上,而王元美目为好奇之过。夫《幽闺》大半已杂赝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美千秋士也。予尝于酒次论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娇序】二曲,不类永嘉口吻,当是后人窜入,元美尚津津称许不置,又恶知所谓《幽闺》者哉。”
臧懋循没有从两剧本身入手来谈及两者高下,而是从以两者真伪的角度评判高下。在这些评论与论争中,作者与读者都在不断加深对元曲的认识,更进一步巩固了元曲的地位。
由于明清人对元曲的崇尚,继承与模仿元曲的作品越来越多,单就《西厢记》来说就陆续有多部《南西厢》出现,在情节关目、表现手法、思想主旨以及细节处模仿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牡丹亭》在主旨上对《西厢记》重情反礼的继承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在清代,《牡丹亭》对戏曲的影响往往比《西厢记》更直接。当然,也有一些人为了达到元人的标准,盗用或翻改元人作品,经常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独怪夫今世之人,云翻雨覆,厌旧喜新,趋利者往往盗袭元、明词曲,改作新剧,惟务荒诞不经,怪异无伦”.可见当时人们对元曲的崇尚程度,只有当元曲成为戏曲的榜样、典范时,人们才有可能对之进行翻抄。
明清戏曲选本与戏曲名著的形成名著之所以为名著首先是其自身的艺术成就使然,但明清戏曲选本作为戏曲作品的重要传播媒介,对戏曲经典名著( 尤其是元曲名著) 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推动作用。
首先,明清戏曲选本所具有的“选”的意义是名著形成的重要前提。在浩如烟海的戏曲作品中,优秀著作如何能脱颖而出是名著形成至关重要的一步。正如纪振伦《校乐府红珊·序》所言: “彼连篇累疏,虽兀兀穷年者,何能茹其英,咀其华哉?”
明清戏曲选本的编选者即承担了“茹其英,咀其华”的重任,他们或“遴选其诸曲词藻伟丽,情节周贯,演之可以欣悦人之视听,起发人之兴趣者”,或取其“辞足达逢情为最,而协律者次之,可演之台上,亦可置之案头赏观者”,或“特取情思深远,词语精工,洎有关风教、神仙拯脱者”.总之,是编选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审美原则,将从众多戏曲作品中所挑选出的优秀者呈现给大众,而在这众多的选本中,反复被认可,不断被传播者,即大浪之中淘出的金子,最终闪现出璀璨耀眼的光芒。以《西厢记》为例,在目前笔者所见的 64 种可查到目录的选本中,出现 29 种之多。其中剧选本 5 种①,出选本 24 种②.现存最早的收录《西厢记》的选本为《风月( 全家) 锦囊》,它所收录的从“惊艳”到“报捷”几乎是整本《西厢记》。之后,从万历年间一直到清末都有选录《西厢记》的选本相继出现,其中以万历年间的选本最为集中,目前可确定为万历年间的选本就有 12 种,并且这些选本都是出选本,这就使得《西厢记》中的一些经典段落,如“听琴”、“佳期”、“寄柬”等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经过万历的强势宣传,到明末又出现了如《大明春》、《赛征歌集》、《万壑清音》、《怡春锦》、《尧天乐》、《乐府遏云编》、《时调青昆》等一批选本,强化了《西厢记》在民众间的地位,明末的《六十种曲》及清代的几种具有代表性与总结性的选本如《缀白裘合选》、《缀白裘全集》等也将《西厢记》收入其中,这样不但延续了《西厢记》的传播,更扩大了《西厢记》的影响。这样连续不间断的传播,使《西厢记》一直活跃于人们的视线中,并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也是《西厢记》成为名著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编选者在选择作品时,并非毫无目的与章法,他们是在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主旨、艺术特征以及编选者与接受者双方的审美取向、心态等等,才能使所选真正为大众所接受,才能符合时代与读者的审美要求,而元曲以及元曲的继承者、摹仿者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其次,戏曲选本的编选者在收录作品时并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会“删繁去冗”、“参伍校订”,使其日臻成熟、完美,进而达到“以广其传”的目的。李开先在《改定元贤传奇·序》中就坦言其选本中作品均为“改定”,其“删繁归约,改韵正音,调有不协,句有不稳,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订正之,且有代作者,因名其刻为《改定元贤传奇》”.《元曲选》亦是典型一例。从它诞生起就受到了戏曲批评家的广泛关注,虽然历来对臧懋循编选《元曲选》学界褒贬不一,但它在戏曲选本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在它产生后的几百年中,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元杂剧选本被人们广泛接受与传播。孟称舜就非常推崇臧懋循及《元曲选》,他在《古今名剧合选·自序》中不但极力赞同臧懋循所言的作曲“三难”,而且也称《古今名剧合选》所收元曲是“元曲自吴兴本外,所见百余十种,共选得十之七”,可见其选曲之时也是以《元曲选》为标准的。在《盛明杂剧》及《杂剧三集》的序跋中,更多次提及《元曲选》,认为“顾诸臧先生向为大盟主,未迨于兹”,如果选本可以“与《元人百种》并传,此亦骚雅鼓吹,风流胜事矣”.“其传于世者,《元人百种》鸣盛于前,明代两集继媺于后,类皆脍炙人口,鼓吹词坛,所谓情之所种( 钟) ,盖在是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屡屡提到《元曲选》①而未及其他选本也可以充分说明,明末清初时,《元曲选》作为元杂剧选本的杰出代表已经一枝独秀,称霸曲坛了。现存唯一一部元代戏曲选本《元刊杂剧三十种》在这些序跋中并没有被涉及,在笔者所见的其他古代相关文献中也未见过相关记载,但明代臧懋循所编选的《元曲选》却缕缕被言说,并成为元代戏曲的代表。这其中除了传播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臧懋循( 或是元明两代文人集体成果的呈现) 对总题与题目的修正、科范形式的统一、宾白的增加、角色的规划等形式体制方面甚至是主题思想方面的较大改进,使元曲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统一、规范的样貌,更符合时代、读者对于戏曲的要求,也因此更有利于戏曲的传播与接受。事实上,《元曲选》的“选刻之富”、“搜选之勤”确是有杂剧以来最为完备者,体现了元杂剧完备与成熟的状态,《元曲选》也已经成为元曲的代表选本,受到广泛关注。
其三,戏曲选本中的序跋、评点以及戏曲的演出也促进戏曲选本的传播,推动戏曲名著的产生。不可否认的是,一直活跃在大众视野之内的作品,终将保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而不被岁月所湮没。序跋与评点就是很好的载体。除去上面所论的序跋中对戏曲作品的点评以外,评点作为戏曲选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戏曲选本的传播以及作品认识的深化也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玄雪谱·凡例》中云: “传奇接《三百篇》之余,虽俗笔附会不少,而要文人感托者居多,非细细拈出,则幽深隽冷之味不见,故不揣固陋,僭加评点,歌咏者幸谅我于知罪之外。”
而评点就是将作品中的“幽深隽冷之味”“细细拈出”,使作者不明传之言、读者不易悟之意,皆呈于纸上。戏曲选本的评点多集中于剧选本中,如陈继儒评点的《六合同春》、多人评点的《盛明杂剧》、孟称舜评点的《古今名剧合选》、邹式金评点的《杂剧三集》、冯梦龙评点的《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石韫玉评点的《六十种曲》等,在评点中多是对戏曲主旨、艺术以及社会文化的批评,我们也可以从中考察作者与评点者的艺术旨趣与思想倾向。当然,评点的大量出现也说明戏曲选本的阅读人群在不断增加,这也推动着选本及其中优秀作品的传播。与阅读相对,演出是更直观、更乐于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戏曲呈现方式。《缀白裘》就是很好的供演出的选本,其七集序中言:“其间节奏高下,斗笱缓急,脚色劳逸,诚有深得乎场上之痛痒者; 故每一集出,梨园中无不奉为指南,诚风骚之余事也。”
即是明证。现存的其他出选本大多也是供演出所用的,从名称看,大多选本中都带有“青阳时调”、“滚调”、“南北新调”、“青昆合选”等说明选本所演唱的声腔,所以这样的选本亦可视为演出的脚本,或是供大众休闲时赏玩的选本,如《词林一枝》( 全名《新刻京版青阳时调词林一枝》) 即为弋阳腔中的青阳腔选本,《乐府歌舞台》( 全名《新镌南北时尚青昆合选乐府歌舞台》) 是弋阳腔与昆山腔的合选本。此外,一些选本亦有点板标识,如《大明春》( 全名《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或《新锲徽池雅调官腔海盐青阳点板万曲明春》) 、《万壑清音》( 全称《新镌出像点板北调万壑清音》) 等,这也说明这些选本往往是用于演出或者演唱的。
总之,戏曲选本对产生名著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促进了优秀作品的传播。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序》中曾言: “王实甫在元人,非其至者,《西厢记》在其平生所作,亦非首出者,今虽妇人女子,皆能举其辞,非人生有幸不幸耶?”
我们尚且不论《西厢记》本身的价值,单说其传于今,而其他的作品为何至今湮没不闻? 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传播问题,正如李开先自己解释的一样,“宋刻已古,抄册渐讹,再过百年,俱失传矣,必须题请之,后有京板,以及各书坊有镂板,始可遍行天下,不然,则以拘拘背朱为嫌,而经术不幸,不减秦火矣”.名著的形成,不仅是其本身艺术价值的呈现与认可,还有至关重要的传播问题,而选本即是很好的传播媒介,为其成为名著提供了可能。经过岁月的淘洗,一些优秀作品只停留在历史的某处,而幸运的另一些则经过反复的传播终成为“传奇”、成为“经典”.
[参 考 文 献]
[1]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一)[M].济南:齐鲁书社,1989.
[2]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9.
[3] 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71-172.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1980: 185.
[5]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0.
[6]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 明代编第二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9.
一、陶渊明的出仕思想千百年来,人们囿于先贤的成见,而难以透过历史迷漫的烟尘,一睹陶渊明的庐山真面目,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单纯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高大隐士。其实不然,陶渊明并非自始至终地离群索居,他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大济于苍生和猛志也曾是他生...
在“万艳同悲”的《红楼梦》中,女儿形象特征鲜明且具有现实意义,贾迎春形象反映出的是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主要论述文学基本原则,阐述各种文体的渊源和流变,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理论,而神思篇为创作论的首篇,也是创作总论。在《神思》篇中,刘勰开门见山,给神思作了一个描述性的界定:形在江海之上,心存...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传奇从明末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开始,经过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作家群的大批时政之作,直到清初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此时的戏曲创作艺术更加成熟,迎来了康熙朝的两大传奇力作《长生殿》与《桃花扇》的问世。初读两部剧本,不难发现,它们...
在中国这个诗歌国度,女诗人寥若星辰,而李清照可谓是首屈一指,她在诗词创作方面的深厚造诣和突出成就,显示出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聪明和才华。李清照生活在两宋交际之时,经历了由繁华到衰落的转变,这样的巨变造就了她一颗百回千折的心。她才情惊人,既婉...
明末清初出生于如皋的文化巨人李渔, 首先是一位各体兼擅的作家, 其小说、戏曲创作在清代风格独特, 成就首屈一指。文艺来源于生活, 作家创作离不开孕育其成长的土壤, 李渔出生于江苏如皋, 自幼随其父母在如皋生活, 直到二十多岁才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
文学史分期是考察文学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性特征的必要前提,其具体划分往往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文学观念的影响,文体演变、政治变革、人性发展都可能成为分期依据,由此造成文学史分期的不确定性,给准确把握时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客观评价具体阶段的文学成就造...
引言自大、小传统理论兴起后,学术界对二者的关系颇为关注.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相当复杂,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不会是单一的,难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大、小传统的关系有若干层面,如对立关系,依存关系,互补关系,等等.在诸种关系中,我们更为重视二者的互补关系....
笔记小说始于汉代,经魏晋隋唐五代发展,至宋日渐成熟。明中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品经济发展、启蒙主义思潮涌动与印刷技术进步,促使明代笔记小说发展迅速,数量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