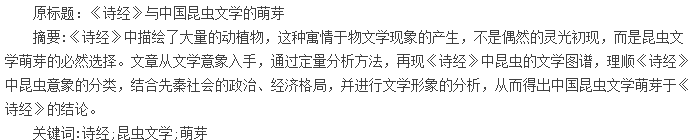 、
、《诗经》是中国文学少年时代的骄傲,文学自觉意识在此阶段已然显现。先民的生命意识逐步从混沌中走向清晰,因而,《诗经》作品中对生命存在的思索与追问日趋增多。这种生命自觉的意识首先源自当时生存环境的残酷现实,借作者身边熟悉的场景、物候而抒发,其中尤以对动物、植物的文学书写最为出色。
昆虫文学,顾名思义是指以昆虫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抒发由昆虫而产生的文学情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反思,并涉及昆虫与周边环境生态联系的文学。就其内涵而言,它包括昆虫进入文学各时期的发展演变规律、盛衰之状况;各类昆虫的意象表现、文化意蕴的差异;不同作家写作的思想倾向,以及凡与昆虫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思想、经济、教化等。
一、《诗经》作为昆虫文学萌芽的科学依据
中国昆虫文学萌芽于《诗经》,是有科学依据的。数据统计是还原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数据的整理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可以给我们直观的印象,尽管数据本身不一定能完全揭示它的文学意义,却能够给人最真实的原貌,对研究工作和文本分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作品数量上看,结合统计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诗经》单独使用了“虫”字的地方不多,例如《召南·草虫》的“喓喓草虫”、《齐风·鸡鸣》的“虫飞薨薨”、《大雅·桑柔》的“如彼飞虫”、《大雅·云汉》的“蕴隆虫虫”、《周颂·小毖》的“肇允彼桃虫”。这中间仅有“草虫”为昆虫,其他几个如“虫虫”、“虫飞薨薨”泛指鸟和虫,“飞虫”、“桃虫”指鸟。
按《风》、《雅》、《颂》分别进行人工统计,其次,从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来看,《诗经》中昆虫文学影响深远。《诗经》中的昆虫形象对后世昆虫的文学性格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例如害虫多象征小人;斯螽、阜螽、蟋蟀与物候相关;螓、蛾、蝤蛴等象征美人;螽斯象征子孙后代众多;蜉蝣象征短暂的虚华不实;蜩螗象征乱象等。表现的主题既有反映国家之象,又有反映社会之貌的,不仅有一般人民的生活,还有位高权重者的生活,并涉及女子、贤与不肖、美貌等多方面、立体的图景。
昆虫意象透露当时政治之现状,展现古人浸润于自然的体察。《诗经》向世人展示了先秦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兴、观、群、怨、事父、事君”是《诗经》留给后世的大道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用来增长见识的小事情。《诗经》中多用比、兴,而这类诗句大多是由鸟兽草木虫鱼构成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大道理就寄寓在鸟兽草木虫鱼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这些“小事情”往往是了解“大道理”的重要途径,昆虫意象是名副其实的“小事情”。
二、《诗经》中昆虫意象的分类与分析
昆虫的分类阶元与其他动植物相同,包括界、门、纲、目、科、属、种,按照蔡邦华氏2亚纲34目系统,本文将《诗经》中出现的昆虫文学形象归入以下七目:
1.以蜉蝣为代表的蜉蝣目昆虫。蜉蝣组成一个小目,已描述约3000种,在温带地区种类最多。通称蜉蝣,它们“体细长,软弱,口器为退化的咀嚼式,已丧失功能,触角刚毛状,前翅大,后翅小或缺,尾须长,常有1根中尾丝。原变态,即稚虫发育至成虫,有一个很短的亚成虫期,此期足较短,翅较不透明,较不活跃,经脱皮羽化为成虫。稚虫捕食小型水生动物,捕食范围很广,是淡水植物链中重要的一环。成虫寿命极短,‘朝生暮死’,飞翔力弱,部分种类有趋光性。在飞翔中交配。”
蜉蝣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曹风·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於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於我归说。
借美丽而短暂的蜉蝣(又叫渠略),讽喻时事,因其羽翅薄而鲜洁,休息时双翅张开,直立背面,非常漂亮却不能久存。《毛诗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无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郑玄《笺》亦认为“喻昭公之朝,其群臣皆小人也。徒整饰其衣裳,不知国之将迫胁,君臣死亡无日,如渠略然。”朱熹在《诗集传》说:“此诗盖以时人有玩细娱而忘远虑者,故以蜉蝣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犹衣裳之楚楚可爱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忧之,而欲其于我归处耳。”这首诗中就是借蜉蝣的自然生长规律来讽喻君臣只重视华饰而轻朝政的做法,是不会长久的。
2.以蟋蟀为代表的直翅目昆虫。《诗经》中属于直翅目的昆虫有螽斯、草虫、阜螽、斯螽、莎鸡、蟋蟀六种。“该目昆虫为头下口式,口器咀嚼式,触角丝状,复眼发达,多数单眼3个,前翅为覆翅,后足跳跃足或前足开掘足。渐变态。部分种类的雄虫能以声求偶、示敌,雌虫则无声。”《诗经》中,直翅目昆虫象征着两种意义,一为象征子孙众多,二为象征时令。先看象征子孙众多的《周南·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中国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螽斯产卵孵化的幼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真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草虫、阜螽言夏秋均可象征时令,《召南·草虫》中的“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小雅·出车》的“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皆言昆虫的声、貌、状,以它们的自然生物习性和出现时间来象征夏秋之交的时令。斯螽、莎鸡分别象征五月、六月,《豳风·七月》言:“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斯螽、莎鸡二虫五、六月始有,因此诗中乃应时之态。
二虫接连出现,言季节之流转,“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象征天寒到来。诗中从蟋蟀在野、在宇、在户、入床下,由外而内,由远而近,象征天气逐渐寒冷,蟋蟀都从外面躲进屋内避寒了,古人观其习性,就能总结规律。《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则象征岁暮将至,蟋蟀已不在户外活动,点出这个时间段以后,劝人及时行乐,不然日月将舍之而去。古人常将昆虫活动与季节月份相连,从而总结候虫纪时之规律,昆虫虽然微小,却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以上即是最初的文学印证。
3.以蝉为代表的同翅目昆虫。《诗经》中的蝉类计螓、蜩、螗三种,“头后口式,口器刺吸式,雌雄异形现象常见,渐变态。产于美洲的十七年蝉是生活历期最长的一种昆虫。昆虫界中叫得最响的是某些种类的雄蝉。植食性、陆生,不少是农林作物的重要害虫,除直接危害外,还传播植物病毒,尤以蚜虫最为重要。有的叶蝉和飞虱在黄昏或昏暗的灯光下会刺人吸血。”
多栖于植物枝干,五月到九月最为常见。《诗经》中“螓首”为拟态,以物比之,象征额之宽广。见《卫风·硕人》: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写美人之美,多以物象比之,以蝉的美丽形态作比。《诗经》中,蜩、螗则多言声,以声之到来或象征月份,或象征和谐之声、混乱之声。
《豳风·七月》“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这里的蝉就不是秋蝉,而是比较早出现的蝉,象征月份。再看《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嚖嚖。有漼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有柳树多的地方就多蝉,蝉虽微小,却也群聚,和谐相处,有伴可依,象征人也应该求友合群。诗中体现无友群之苦,就像舟流,不知所往,有这样的愿景,却事与愿违。蝉在这里是象征和谐之声的。在《大雅·荡》中,则表现出混乱之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蜩、螗之音杂沓,足以乱人视听,当时国事不定,无所适从,就像沸腾的羹汤,胡乱无理。这里的蝉一指乱声,二指乱象。
4.以萤火虫为代表的鞘翅目昆虫。鞘翅目通称甲虫,系昆虫纲第一大目,已知有35万种,占昆虫总数的三分之一。《诗经》的蝤蛴、熠耀、螣、蟊、贼均属此目。鞘翅目昆虫食性复杂,许多种类为农林害虫,有趋光性和假死性。蝤蛴,天牛红虫,色白身长,在《卫风·硕人》中以“领如蝤蛴”来象征美人庄姜之颈白而长,此后文学作品中多有沿袭。熠耀指萤火虫,腹部有发光器,多为夜行发光者。幼虫肉食性,以螺类为生,成虫较少进食,仅以露水、花粉、花蜜度日。萤分水生、陆生两种,喜欢在潮湿、杂草丛生的地方出现,《礼记》腐草为萤的说法虽然不科学,但是也能够反映出萤的习性。“熠耀宵行”在诗中象征荒凉景象,见《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这首诗说东征之士归来后,述其归途所见及归来之情,结果却是苍凉一片,本该干净整洁的家里,却杂草丛生,萤火虫乱飞,处处呈现荒凉的景象。
螣、蟊、贼皆是害虫,《小雅·大田》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大雅·桑柔》有“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在农业社会中,虫害轻则减产,重则饥荒,从帝王到百姓皆不敢轻视。螟是蛀食稻心的害虫,螣是食苗叶的害虫,蟊是食稻根的害虫,贼是食稻茎的害虫,螟、螣、蟊、贼指代了一切害虫。蟊贼还经常用来象征小人,《大雅·召旻》有“天降罪罟,蟊贼内讧”,《大雅·瞻卬》里有: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毛诗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小人为恶,残害生灵,民不聊生,以蟊贼比喻众多残酷之人,恶人,即邪僻之小人。小人作恶,犹如蟊贼残害禾苗,由此做比。
5.以蚕蛾为代表的鳞翅目昆虫。《诗经》中蛾、蚕、蠋、螟蛉、螟属鳞翅目,其中,螟蛉、螟象征害虫和小人的意义和上节螟、螣、蟊、贼的意义重复,不再赘述。蛾,在“螓首蛾眉”中主要用来表示女子之美,其眉细长如蛾,蚕则有另外两层含义,一指蚕事忙碌时节,二指男耕女织社会体系中的养蚕织布女红之事。先看《豳风·七月》: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这里指的就是蚕事忙碌之际的景象,蚕月的说法不一,有指蚕事既毕之月,有指蚕长之月。《大雅·瞻卬》中则表达妇女的分内之事:鞫人忮忒,谮始竟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在中国古代,养蚕为衣是妇人之事,诗中写妇人不用参政,即公事,只要做好本分之女红,如果妇女一旦休其蚕织,社会就会乱套。蠋在诗经中只出现一次,象征独宿之征夫,“蜎蜎者蠋”一句,以蠋的孤独形象作比,形容征夫的形单影只,茕茕孑立。
6.以蝇为代表的双翅目昆虫。《诗经》里苍蝇、青蝇属双翅目,这一目的种类已知九万种,多喜吸食动物血液或昆虫体液,常传播人畜共通的疾病,站在人类的立场,这是妨害人类环境卫生的害虫。《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蝇不夜飞,这是它的生理习性,天未亮的时候听见的声音肯定不会是苍蝇之声,此乃国君妄称之词,明明是鸡叫声,因为不肯起床,就以苍蝇为托词。这是贤夫人警君之诗,如喻人,则苍蝇为谗人,以这种谗人做挡箭牌,找个不起床,不做正事的理由。《小雅·青蝇》: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这是《小雅》中一首著名的谴责诗。它的鲜明特色是借物取喻形象生动,劝说斥责感情痛切。《毛诗序》说“《青蝇》,大夫刺幽王也。”朱熹《诗集传》说“诗人以王好听谗言,故以青蝇比之,而戒王勿听也。”诗歌以青蝇比喻小人,营营往来,拨弄是非,危害善良甚巨,君王应远之,故引以为喻。
7.以蜂为代表的膜翅目昆虫。蜾蠃、蜂属于膜翅目,在《诗经》中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蜾蠃在现代生物学的解释上和古人所看到的表象是不同的,《小雅·小宛》中“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
蜾蠃即细腰蜂,它捉螟蛾的幼虫作为它自己幼虫的食物。古人不察,错认为细腰蜂领养螟蛉为己子。古人还误以为细腰蜂用善使螟蛉像它。因此,在诗中蜾蠃不辞辛劳,乃勤勉之虫,象征着勤于修德者。诗人见螟蛉子为蜾蠃负去之象,言王若不勤政以固位,必将有勤于修德者取而代之。蜂是《颂》中唯一出现的昆虫,来看《周颂·小毖》: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肇允彼桃虫,拼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蜂在这里象征着小人,说的是不要自己扰乱群蜂,招致棘刺,喻咎由自取。作为自警之诗,近蜂则被螫,近小人则受其惑。
三、昆虫文学与《诗经》的相互选择
《诗经》是农业社会的时代产物,既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反映,也是人类感情的流露。昆虫由此成为那个时期社会生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对象,这是先民朴素的自然观与文学的天生联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二者相互选择的几点共识。
1.《诗经》中昆虫多为常见之类。即便时代久远,环境变迁,在今天依然能够准确区分它们各自的生物学特征。
2.昆虫意象反映农业社会特征。具有明显时节指向性的昆虫如斯螽、阜螽、蟋蟀等,有的细致到了特定的月份、季节,有的粗略象征着岁暮、天寒的不同物候。
3.昆虫意象与古人的好恶观已经进入文学视野。螽斯象征子孙后代众多,符合古人希望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景;蜉蝣朝生暮死,有对短暂生命的惋惜,也有认为它虚华不实的体会;螓、蛾、蝤蛴等多以美好的外表象征女性容貌;蜩螗声音的混杂象征社会政治乱象;害虫多象征小人等。
4.昆虫意象出现在《风》中最多,《雅》次之,《颂》最少,仅一例,说明昆虫与当时农业社会普通百姓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与上层社会政治、祭祀、神灵的正面关系尚未建立起来。
5.《诗经》无蝶,此为特例。我国昆虫文学溯源几乎全部始于《诗经》,唯独蝴蝶源于《庄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诗经》的内容。《诗经》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的诗歌总集,也是世界最早、最灿烂的诗集之一。与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巴比伦的《吉佳美士》,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大多描写英雄人物且笼罩着宗教的神秘色彩的长篇史诗相比,《诗经》几乎描写了世间万物,“141篇492次提到动物,144篇505次提到植物,89篇235次提到各种自然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百科全书。在一字千金的古代文字中,诗人为何写了那么多草木鸟兽虫鱼?为什么在后世文学发展中大行其道的蝴蝶,在《诗经》中间竟然一字未提?原因就在于《诗经》记载的昆虫几乎都与农事有关,而蝴蝶对原始农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先秦农耕经济的独特结构,使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农业生产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并认为昆虫正常的存在和繁殖并不会影响到农业的丰歉,除非是像蝗虫非正常地、大量地出现危及到庄稼,才会破坏这种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古代农业中所面临的害虫不少,人们也基本上可以找到相应对的防治办法,多数情况下,古人“防虫”胜于“治虫”,因而《诗经》对农业害虫是描述得比较多的。蝴蝶不属于先秦农业里人们要面对的昆虫,既无益也无害,也没有将其作为欣赏的对象来进入诗的文学意识。蝴蝶在春天出现,飞舞于花间,不像蜜蜂那样带来副产品供人类食用,在物质条件极为简陋的先秦时代,它就是无用的。由此可见,因为与农业生产的疏离才是导致《诗经》中没有蝴蝶原因。除《诗经》以外,《说文》、《尔雅》、《史记》也都鲜有蝴蝶的记载,连汉赋这类善于比兴的作品中都没有蝴蝶,先秦时代仅“庄周梦蝶”这一个典故流传。直到《乐府诗集》中的《虫疌蝶行》才又有了蝶的身影,然后是南朝梁萧纲的《咏蛱蝶诗》、刘孝绰的《咏素蝶》、李镜远的《虫疌蝶行》、北魏温子昇的《咏花蝶诗》等,直到唐宋时期蝴蝶才真正迎来了诗词里的春天。
四、结语
《诗经》的昆虫形象反映了国家之象、社会之貌的主题,涵盖了上达君王众臣下至平民百姓,涉及女子、贤与不肖、美貌等多方面的立体生活图景。把昆虫的形态、习性、声音糅合到诗中,展现出古人浸润于自然的体察能力,成功地开创了后世昆虫情感体验的“微”模式。虽然自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后,有人做过《诗经》鸟兽、草木的专门研究,但让人完全清晰的并不多,而研究昆虫这类更“微小”的事物更是鲜有人问津。这中间有两个难点:一是从生物学层面上来说,《诗经》中的实物难知,现代生物学中,同一种类别的昆虫有不同的名称,例如蟋蟀的别称就有促织、莎鸡等,斯螽和阜螽究竟是什么?
前人研究众说纷纭;二是从文学层面上说意象不明确,究竟是要表达什么内涵,这些昆虫身上所承载的意义尚不明确。如何将生物学和文学融而为一?重视昆虫的形态、习性、功能,探究《诗经》的昆虫意蕴及情致是有重要意义的,将《诗经》作为中国昆虫文学的萌芽,并由此而引发对昆虫文学进行整体的、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思考,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拓展行动。
参考文献:
[1][6][13]陈振耀.昆虫世界与人类社会(第2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2][3][4][5][7][8][9][10][11][12][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周振甫.诗经译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1]胡淼.《诗经》的科学解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诗经》作为原典,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往学者们多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恰恰打开了读者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沟通的大门.本文将从情感角度对《周颂闵予小子》组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能了解其中更为深层的文化意蕴及《诗经》时代...
《诗经》中以《关雎》为代表的许多诗篇在具体叙事抒情以前大都会先摹写一些与所叙情事无直接关联的额外场景,营造某种氛围铺垫一定的前设情绪,然后展开具体的叙写抒情,这种艺术手法就是后世人们饶有兴趣反复谈论的兴。当然《诗经》的艺术手法是...
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六略艺诗》的小序中写到: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历来注家多注意孔子删诗,对凡三百五篇进行解释,然而《诗经》里的诗歌并不全是周诗,而上采殷和纯取周诗相矛盾...
女子伤春文学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里是传达情感的一个重要方式与媒介,在春天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古代文学家却常常喜欢将自己悲伤情绪隐藏其中,在《淮南子谬称训》中曾有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的说法,这说明,中国历来就有伤春悲秋的传统.而作家将这个传统...
本文简要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 其中主要包含九尾狐、玄狐、天狐三种, 并论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形象的演变历程及狐形象演变的内在动因...
橄榄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别称,如:橄榄子、忠果、青果、青橄榄等。其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左思的《吴都赋》:龙眼橄榄,棎榴御霜,《文...
通过分析《诗经》的内在价值,能够更好地展示《诗经》中女性的外在美、内在美与情感美。...
意象选择方面他侧重于对冷色调意象的选用,使得诗歌整体色调偏冷,营造出了清冷,清幽或是清旷的意境,意象的运用和意境的营造为谢灵运诗歌中意蕴的表达奠定了基础,对表现他本人坚持本心的人格之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竹意象是后人鉴赏和解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媒介之一。“竹”本身的自然属性就能够引申出君子之象, 使其成为君子品质的重要象征。...
风、花、雪、月、雨、露、冰、霜是历代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我国古代是农耕社会,春雨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风调雨顺则丰收有望,相反则将面临饥馑甚至灾荒。自古以来,人们对春雨都极为重视。春雨与古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文人也极其关注。因此,春雨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