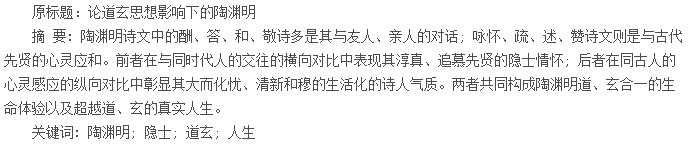
历来对陶渊明的研究,学者们偏重对其总体文学作品中的哲学思想阐释,并以写意田园总括其诗文特征,在这一基础上,重点对其某类作品的分析更能发现他思想中的突出特征。陶渊明的总体诗文包涵其栖田园之心、抒归隐之志,但是作品中的酬、答、和、敬诗以及咏怀、疏、述、赞诗文似乎更能直观体现其受道家思想和玄学思想影响后领悟生命真谛和感受生活的方式。
1 隐士情怀: 现实人生的体验者
陶渊明是一位生活于东晋后期的隐士。东晋后期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黑暗都已经处于极端的状态,归隐就成了士人们保身全生的重要途径。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士人,远离祸患的意识更加强烈,陶渊明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中,玄学思想的发展进入后期,而玄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合流的产物,道家思想在整个魏晋时期呈现繁盛的局面。这与汉代儒家思想独尊的状态是不同的。道家思想和玄学思想均含有归隐的人生处世方式。同时,隐逸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理想的追求①。陶渊明生活在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下,也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变得彻底“遗世”。归隐后生存的方式有多种,“渔隐”、“樵隐”、“医隐”、“吏隐”等等[1],而陶渊明选择了田园。
不同于其他魏晋诗人对隐士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描摹,同时也不入超凡进仙的彼岸世界,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中充满了人间交往的真情,这种真情表现在他与友人、亲人的话语中,如“有客有客,爰来爰止”[2]。友人的到来实给他独居的生活带来了发自内心的欢欣。“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答庞参军》)②。友人相聚的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老友即将分别。“负痾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表达终日想着友人何时才能再来的殷切期盼。陶渊明对待人间真挚的友情出自内心的淳真,念着“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答庞参军》) 的温情。他的隐居的落脚点是“人境”,“人境”中含情,亲情在其中是无法回避的,道家思想和玄学思想对人情多以超脱的心境看待,人情多归于一种对得道的羁绊。陶渊明却以人情为立足点,对友人的相邀避世山林,他直言“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酬刘柴桑》) 。对待亲情上,当他看到自己拮据的生活状况,流露出难以排遣的伤感,“汝辈稚小家贫,毎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与子俨等疏》) 。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位慈父因家贫对幼子生存的担忧,拳拳之心分明可见。这就是陶渊明,其情出自对人性自然状态的直观表现,无矫揉,无做作; 其心淳然,生活的落魄与捉襟见肘都难以是他割舍下人间的挚友与温情。
无怪清温汝能评价“其心盖真且淡,故其诗亦真且淡也; 惟其真且淡,是以评之也难。”[3]这样的评价可谓得其人其诗之旨。因为有情,使得他的隐居生活充满了乐趣,这是他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难以体会到的,所以于他而言弥足珍贵。
陶渊明的酬、答、和、敬诗文是将自己的人生见解与感受诉诸同时人,诗文内容答客赞友实有,事实上却是自我心灵的宣读。他的咏怀、疏、述、赞诗文则是以古代先贤为镜,映射出的是与自我心灵的契合。这两种诗文意向构成了他感受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在恬淡的自然环境中寻求心灵的解脱,在静谧的田园中固穷守拙,在追慕先贤的期望中寄托超越苦难的人生理想。
陶渊明善于用心捕捉蕴藏在现实自然景物中的意趣,这种意趣一经展开便具有浑然天成的效果。
“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酬刘柴桑》)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 。“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巳腓”(《于王抚军座送客》) 。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巳洁”(《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这种对四时季节的描摹中含有对自我生存状况的摹写,春之萌发、夏之繁盛以及秋之雍容、冬之凛冽在陶渊明的笔下染上了生活的真切感受,由于生存的困境带来的种种不便都掩藏在这四时的变化中,或悲或喜,或畅达或郁结,总能在景物中找到对应的感情。渊明独爱菊,而菊开在秋季,因此对秋着笔甚多,秋季在他生活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季节,更是其超越生存苦难的场所。自然景物带给他的是心灵的畅达,以此消解生命中的种种不顺利。“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和郭主簿》) 。和风迎面而来,吹入衣襟,身与物浑然一体。正是由于这种物与人心灵的契合才使得他在田园中找到了适合自己性情的归属。在经历了几番仕途之后,他更加向往回归悠游自得的田园生活中,理想和志趣都能在这里实现,甘心在其中固穷守拙。这是他的“人生理想深受玄学崇尚自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抛却仕进之心,归耕肆勤,以实现他抱朴含真,与‘道’合一的夙愿”[4]。他直言“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岂无他好? 乐是幽居”(《答庞参军》) 。“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答庞参军》)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 。对于不得不出仕的违心之举,眷恋家园的心情贯穿羁旅的始终,“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此时更加怀念田园生活的美好,“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 。“孟夏草木长,遶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 。与亲人同游,在这游驾四方的期望中寄托超越苦难的人生理想。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不是因为田园生活的富足,相反,他常常感受到的是饥寒交迫,他说: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咏贫士》) 。但是他在意的不是这些生存上的困窘,“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 赖古多此贤”;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 。而一时的富贵也不能撼动他的心志,“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咏贫士》) 。不可否认,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是贫寒的,但他并不寂寞,在与同时代人的应答赠和中体会友情的真挚、亲情的温暖; 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找到心灵的契合,追慕先人以达己怀,使得他能真正体会“丘山”生活的苦中之乐,感受现实的温情人生。
2 大而化忧、清新和穆的生活化的诗人气质
陶渊明既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又有对道家以及玄学思想的认同。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 ,他的家族渊源中也包含这样的思想,他的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仕人,尽管当时玄学盛极一时,儒家思想因是其接受的开蒙教育而深深植根在他的人生选择中,而他后期的人生观逐渐偏向于道、玄思想,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一个方面,他性本自然的人生态度却是最主要的因素。
这一点前人学者早有论述。那么,陶渊明何以表现这种受道、玄思想影响的人生态度呢? 又是怎么样将这种人生态度表现出来的呢? 他通过大而化忧的“万化”之道,消解人生“命”、“名”的牵累,以“心期”的内在感受构建冲盈的胸怀与心境。陶渊明的追忆古贤的诗文中,常用“化”字,如“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于王抚军座送客》) 。
“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已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 。西晋郭象《庄子注》中“化”为主要概念,“化”指“变化”,进而有“独化”之意。”与“独化”概念相关的概念则有“有”、“无先”、“性分”、“不为而相因”等[5]。陶诗文中的“化”含义沿袭了郭象注,承认事物万化而归一的性质,但是,其中的“化”又具有由内而外的动力性和普遍感召力,由此即引发出涵容万物的内蕴。这种内蕴暗含了顺随自然的理趣,能够消解现实世界中的“名”、贫的牵累。“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和郭主簿》)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 “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咏贫士》)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着! ”(《咏二疏》) 这种大而化忧的自我超脱,来自与人生的苦闷、生存中的种种不顺意的抗争。陶氏将自己恪守的理想心性作为一种力量和武器来应对它们,而苦闷的生成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期望与现实不符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自身的思想力量,所以在陶诗中出现超脱后又表现出苦闷并不稀奇。
他的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不断消解这种苦闷,达到生存状态的适性而乐。
在对待人生中的生死问题上,他认为“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 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赤泉给我饮,员邱足我粮。方与三辰游,寿考岂渠央”(《读山海经》) 。陶渊明不惧死,对生的谨慎态度成就其对死的超然,即大而化忧。他关注生死,自觉思索,是其独立人格的显现,而生死问题是常解常新的话题,以一种精神信仰来让自己解脱体现其砥砺不灭的力量,具有了哲学思辨的意味,所以撼动人心。至此,“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概念了,更具有了某种人格力量,不但能化己、化人,推而广之则,具有化天、化地的指向功能,它超越了道、玄思想,而具有某种人类生命存在价值的永恒意义。
袁行霈先生认为: “他( 陶渊明) 既熟谙老、庄、孔子,又不限于重复老、庄、孔子的思想; 他既未违背魏晋时期思想界的主流,又不随波逐流; 他有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这才是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的地方。”[6: 2]他的诗写的是自己切切实实的生活,却“常常是从生活里得到一点启示,忽然悟出一种道理”[6: 8],这道理充满了哲学理性的意味。这种道理在人格上的表现就是以“心期”的内在感受构建冲盈的胸怀与心境。“心期”就是内心的认同,不仅包括对人、物的情感上的归属感倾向,更包括对生命存在价值上的理性思索的认同。前面说到陶渊明的酬、答、和、敬诗文是将自己的人生见解与感受诉诸同时人,咏怀、疏、述、赞诗文是以古代先贤为镜,那么,他的《自祭文》则是作者与自我的对话,“茫茫大块,悠悠高旻。
是生万物,余得为人……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 文章的言辞是沉静、凝重的,自然造化万物,顺而成人,然而人生艰难,身在其中,感触至深,生命的存在只能付之天道运行,又怎么能考虑到死后会怎么样呢? 陶氏想到古代先贤生不逢时、零落成泥,终成烟土,为他们感到惋惜、愤慨。他自身的苦是生活的真苦,切切实实。他最终选择了遗世独立,接受了道家思想和玄学思想,继而走向通达。
由此之后,他的生存困境得到解脱。解脱表现于乐,可以说,陶渊明受苦之透彻,享乐之至极乐。
将这种苦发挥到极致,经过诗人自身的锤炼,结出别样的清新和穆的果实,写出独特的抒情表意诗。在清 新和穆的诗风背后,承载的是诗人洗练尘世的厚重灵魂。其心寓于诗,其思表于字,其情驰骋于天地之间,简洁的文字下面是陶氏百转千回的至性之情,这些也是他诗人气质的生活化表现。
魏晋时代是玄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期,陶渊明无意于绝隐而完全与世隔绝,同时也并不有意成为任何社会思想的代言,他就是一个生活在田间的诗人,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发现隐居生活的美好,感受静谧的生活带给自己的无限乐趣,这就是陶渊明,一位本真生活的追慕者。
参考文献:
[1] 李生龙. 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3.
[2]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2003:23.
[3]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 陶渊明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221.
[4] 李文初. 汉魏六朝文学研究[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83.
[5]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65.
[6]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 18.
一、陶渊明的出仕思想千百年来,人们囿于先贤的成见,而难以透过历史迷漫的烟尘,一睹陶渊明的庐山真面目,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单纯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高大隐士。其实不然,陶渊明并非自始至终地离群索居,他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大济于苍生和猛志也曾是他生...
李白诗文集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北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它距离李白去世已逾三百多年。其间李白诗文的编集与流传,因为时间久远,载籍零落,原本无存,均言之不详。本文试图钩稽各种史料,对李白诗歌在唐五代的流传略作探析,以便考察李诗在...
文徵明是明代书画界的领军人物。他居于文化、艺术发达的江南长洲(今苏州),具有那个地区文人的典型气质和艺术风格。文徵明初名璧,别号衡山居士,字徵明,以字行。文徵明书画兼工,为吴中四才子之一,对当时苏州一带的书画影响深远。文徵明不但书画造诣极高,诗文...
对于明代遗民而言,华夏大地的山河胜迹是时时萦绕在他们心头的。从用世的角度来看,对故国山水的凭吊与游览是意图复明者经营的重要内容,无论是顾炎武的往来海上、出入塞外,还是顾祖禹奋力着书以求民族光复,他们心中的故国山水,与时代风云紧紧结合在一起...
法式善(1753~1813),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诗龛、小西涯居士,蒙古族人,隶内务府正黄旗。洪亮吉(1746~1809),初名礼吉,字君直,又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汉族,籍贯江苏常州府阳湖县。法式善是清代乾嘉时期北方诗坛...
陶渊明留存于世的诗歌仅百余首,但不可否认他是文学长河中璀璨夺目的明珠,钟嵘《诗品》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295,苏轼《与苏辙书》也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
陶渊明是古今文人喜爱的诗人,其历久弥新的醇厚魅力在哪里?其实并不复杂。昭明太子在《陶渊明传》中曾评价陶渊明: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脱颖不群,任真自得。任真是陶渊明人生的本质凸显。一、真实劳动,尊重劳动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甚至达官贵人...
钟嵘《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为后人所重视,然而历代诗论家对《诗品》所评诗人的品第问题多有微词,如所谓品陶不公,第谢不允的指责.《诗品》中被历代评论家所非议者,大约有魏武帝、魏文帝、宋征士陶潜、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梁左光禄沈约等几条,其...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重要开创者,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评价建安文学的审美特征时曾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①梗概多气被刘勰视为建安文学最主要的审美特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