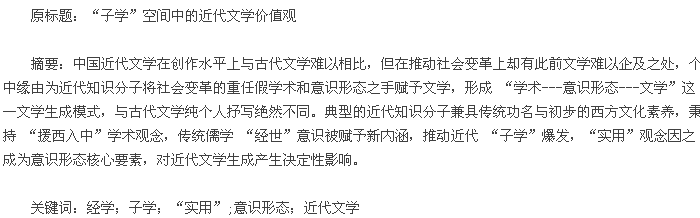
作为文化的顶级形态,文学是一定文化空间诸要素合力的结果。文化空间的核心要素是意识形态,这是国家推行的观念体系,对文学艺术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官方提倡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方法,既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又以不同途径和方式证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于是,“学术---意识形态---文学”成为一定时代文学生成的基本模式。中国历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存在两种情形。一方面,在大多数朝代儒学独享“国学”地位,宋代以来更是如此,国家推广儒家经典,士大夫终生研习儒家经典,流风所及,整个社会依据国家提供,士大夫示范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有条不紊地运转。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找到纯粹由儒学主导的朝代,思想倾向某种非儒观念的朝代或人物则比比皆是。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如汉代 “诗大序”在诗歌的性质、作用、内容、体裁、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体现了先秦儒家对诗乐的重要认识,“抒情言志”、六义、美刺、兴观群怨、“经成厚美移”等观念就是标准的儒家诗论。但汉代绝非儒学一统的朝代,大致产生于同一时期的 《淮南子》便呈现矛盾色彩,思想以道家为主,杂以儒、墨、申、韩之说,同时又困惑于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维护秩序之间。上述两方面的结合组成传统中国文学生成的基本文化空间,传统文学主要建立在儒家思想提供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同时各种非儒学说从未退出文化舞台,个别时代甚至与儒学双峰并峙,共同刻画文化空间,成为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的基础,推动文学形成大异于前的风貌,比如近代。
一
“子学”始于先秦,是历史相当悠久的学问。按 《隋书·经籍志》, “子部”涵盖儒、道、法、名、纵横、杂、小说、兵、天文、历数、医等多种 “家”,《四库全书》中,“子部”不仅包括先秦诸子,而且涵盖秦汉以后诸家著作,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道家类、释家类等。后代所谓 “子学”一般遵循司马谈的说法:“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西汉刘向增补纵横、杂、农、小说扩充为十家。
这份目录单显示诸子百家地位原本是平等的,都是 “(诸)子学”.“独尊儒术”之后,各学派经过一番博弈,儒家思想逐渐上升为具有支配意义的思想,对这个学派典籍的研究也上升为 “经学”,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基础与核心,在思想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非儒学派 “降格”为 “子学”,与蔚为大观的经学研究相比,“子学”彻底沦为附庸,鲜有问津,直至近代。
近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学术对社会的干预程度远胜于前,学者的思想不再囿于纯学术研究,他们突破传统儒家学说和国家意识形态,援引各种非儒学派思想为推动国家富强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近代文学迥异于传统的生成模式是知识阶层出于社会和政治目的从外部推动生成,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文学直接为表现政治主张服务,这是政治宣传;二是学术为政治思想提供理论支撑,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思想趁虚而入,国家意识形态遭到空前压制,民间意识形态如荒野蔓草般疯长,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左右着文化空间性质与走向。这样,文学生成模式不再取决于清政府倡导的国家意识形态,近代文学在这一点上至为清晰。近代文学既然在民间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化空间中生成,那么学术界的主流价值取向便至关重要了,而近代学术背景有三,一是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二是儒学走向今文学,三是 “子学”兴起。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已有太多成果,此不赘。儒学走向今文学是一种内部调整与转向,仍然是 “经学”,而子学兴起造就中国学术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景观,那就是一改此前 “经强子弱”,出现 “经、子并峙”格局。这不是清代官方推动的结果,而是在外敌入侵、国势衰微的局面下自发形成的 “民间意识形态”.
近代现实处境把与国家、民族相关的一切硕大无朋的问题都推向了必须要在不长的时期内做出选择的尴尬境地,异常活跃的思想界则为这种选择提供多种可能性。后来的历史事实显示,最终胜出的是实用的、通俗的、西化的观念,清代官方默许的 “儒 (朴)学”虽未彻底退出,却不再具有支配地位,这意味着传统 “经学”及其连带的 “国家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同时丧失。于是传统儒学内部产生矛盾,汉学 (朴学)被认为是无关致用的空疏学问,知识界需要更有用的学问和研究方法。对 “用”的一贯追求是中国思想界的共识,形成一个专用词汇:实学。由于 “用”的含义处于流变之中,实学的含义也因时、因地、因人不同,对某种 “空虚无用”的学问的批判成了学者标榜自身“实学”的基本路数,经过多次破与立,“实学”的含义在清代形成三次转向[2].第二次转向矛头便指向汉学,古老的 “汉宋之争”又一次被摆上台面,注重阐发义理的宋学攻击执着于训诂考据的汉学对个人知识有所帮助,但无助于提升人格修养和道德建构,是空疏无用的学问。时值清代晚期,一种迥异于前的学术理念呼之欲出。当中国传统经学、富国强兵的现实需求与似是而非的西方文化知识在康有为身上结合起来的时候,今文经学也就顺理成章了。
康有为继承久已断绝的今文经学传统,将 “义理”的方法用于儒家经典的研究,重新振兴今文经学,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投机也好,钻营也罢,在当时整个知识界掀起的波澜的确如梁启超所言不亚于 “火山”“飓风”.康有为将传统经典与西方文化简单附会,进而与晚清乱局相关联,几乎完全抛弃了朴学的科学性,如日本学者佐藤慎一所言:“将外来的事物与中国固有的事物联结起来,以此使输入外来事物正当化的逻辑。”[3]
这种武断、附会的逻辑在康有为学术著作中极为常见,兹举一例:撰于1901年的《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挥 《孟子》一书微言大义的汇总,书中显示康有为以西方知识解释孔、孟思想的基本思路,是他武断附会逻辑的集中展示。《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康解释说:“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日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顾问官也;诸大夫,上议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议院为与民共之,以国者,国人公共之物,当与民公任之也。”
在其他著作中,康亦有此观点:“孟子言治天下,皆曰 ‘与民同之',此真非常异义,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可见这并非康“一时性起”之言。
康有为煞费苦心想要证明的是西方民主政体并非西方原创,而是来自中国的儒家经典,因此改革变法不需要学习西方,只要回归经典即可,这样,他的今文经学不但具有合理性,而且简直是拯救苍生不可或缺的灵丹妙药了。
康有为用这种错误的观点和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今文经学汉代之后再次崛起,他的高足梁启超也不遑多让,一方面是今文经学的狂热鼓吹者,另一方面又祭起 “子学”大旗,将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的 “子学”推向前台,基本方法与其师如出一辙。
二
梁启超是近代 “子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煌煌巨著 《饮冰室合集》就有大量篇幅涉及这个问题,《墨子》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与魏源、苏时学、俞樾、孙诒让等近代“子学”巨子不同,梁启超作为身兼社会活动家的学者,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 “子学”大爆发。
与此前的 “实学”不同,近代 “子学”的 “经世致用”基本内涵是 “救世”,是富国强兵,而非成就个人德行,甚至不是境界更高远的 “三不朽”.近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他们需要直接而迅速见效的救国方略。
于是从自身知识结构出发,用转手贩卖到国内的西方文化解读传统文化成了知识界唯一的选项,这是今文经学在近代兴起的文化语境,又何尝不是 “子学”复兴的原因呢!
1904年,梁启超在 《新民丛报》连载 《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 (后来合为 《墨子微》出版)。梁启超对“墨学”的阐释以全新的 “义理”之学取代了传统的 “考据”之学,把今文学 “经世”风格发挥到极致。
1920年以后,整理出版 《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和 《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书,对墨学多有讨论。梁启超之所以对 “墨学”表现出如此热情 (集中于 《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七至四十),原因是在他看来墨学具有挽救民族危亡的 “奇特功效”,他说:“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
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显然与康有为的 “附会”逻辑不同,不是佐藤慎一所谓士大夫借墨学 “断定 ’西学‘之源流存在于中国”,更非出于证明 “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或机械技术,这绝不是模仿西方,而是拿回自己本来就具有的东西”这样的目的,[8]而是企图从墨学的 “兼爱观”和杨朱的 “利己观”出发辨明存亡之道。他对墨学的基本认识也着眼于社会改造,他说:“革除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就是墨子思想的总根源。”
另外,墨学非常契合梁启超的 “新民”思想,这实际上是近代社会下层启蒙运动。在塑造“新民”的方法上,梁启超十分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说:“好 《墨子》,诵说其 ’兼爱‘、’非攻‘诸论。”从下文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等说法来看,[10]梁启超 “好墨子”是由来已久的事。而 “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我族能继继绳绳与天地长久,未始不赖是也。”?梁启超 “新民”逻辑并不深奥,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把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的错误,于是转而寄希望于普通国民,在 《新民说》
中任公将理由阐述为 “内治”和 “外交”两方面:从 “内治”来说,有什么样的国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因而只有国民 “新”,政府才能 “新”,国家才能 “强”;从 “外交”说,当时民族帝国主义盛行,只有国民团结,方能抵御外侮。这就产生了塑造 “新民”的现实需求。在这样的现实需求刺激下,梁启超大力发掘墨学思想,而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有一个根本观念,就是 “兼爱”.梁启超试图以墨学的 “兼爱”观照亮国人蒙昧的心灵,完成他的“新民”之梦。既然目的如此,那么阐发墨学 “义理”自然是梁启超的主要任务了。
虽然起点一样,但与魏源、苏时学、孙诒让等清代“子学”前辈们固守书斋,纯然依靠透过一丝缝隙渗入的社会思潮,结合自身传统学术素养,想象着西方文化的前世今生不同,梁启超们走上中国现实社会,借助处于形成期的近代大众传媒,宣扬与魏源们没有本质区别的 “子学”观念,不同之处是梁启超们利用 “子学”致力于时代赋予他们的 “启蒙”使命,仅此一点即使其具有鲜明的近代性,所属的传统士人队伍也成长为典型的 “近代知识分子”.正是这批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塑造了典型的近代文化空间,其灵魂不再是传承千年的儒学,而是糅入西方文化,被赋予 “致用”内涵的 “子学”,其使命亦不再是传统的 “教化”,而是近代 “启蒙”.“致用”的 “子学”赋予以其为核心的文化空间的东西当然只能是 “致用”,在 “致用”文化空间中生成的文学必然也是 “致用”的,于是近代文学生成呈现出前述线索:学术---意识形态---文学,不清楚这一线索就无法解释近代文学。
近代文化空间借助西方文化之力打破的一是儒学对意识形态的统治,这一趋势体现在学术和文化空间层面上是子学的兴起,形成 “经、子并峙”格局,体现在文学上一方面是语言的西化趋势;另一方面是文学屈从现实压力的实用趋向,既成全了近代文学,因为它扭转了传统文学专注于内心世界的局面,开创了全新的创作领域和审美范式,为后代文学所继承,以低水平创作占据重要文学史地位,大概无出其右者了;同时又毁了近代文学,因为文学本应以其独特的美学特质和作用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不能全然委身于现实,否则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一如近代子学面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本能反应,既成全了近代学术,又毁了近代学术。无论对与错,“实用”精神一经形成,便处于近代文化空间的核心位置,进而推动倾向 “实用”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
在此文化逻辑支配下,近代文学如学术一样,将 “实用”摆在第一位,如典型体裁小说创作完全颠覆传统文学观念,至少呈现两方面突破,一是语言之俗,二是启蒙之用[11],无论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都有大量例证,前者如黄遵宪 “我手写我口”,裘廷梁 “废文言而崇白话”,尤其是梁启超,从多方面提出语言文字通俗化主张,“言文分而人智局也”,“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以致白话或浅近文言小说成为时代最畅销作品,时人惊叹 “十年前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日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
后者仍以梁启超主张为核心,“译著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其他如康有为、傅兰雅、徐念慈等人都大力鼓吹小说在开启民智上的巨大作用。梁启超所谓 “小说”包括戏曲,虽然这类政治目的明确的小说数量并非最多,在当时却有着最大的影响力。
在文化名人的大力倡导下,兼有近代大众传媒提供的商业化创作实践平台,一种迥异于传统文学的近代 “新文学”迅速崛起,从体裁、题材、创作手法,到创作目的、审美范式、流通模式等各方面都出现本质不同。一时间,政治、狭邪、公案、言情、艳情、科幻、翻译等各类作品风起云涌,在客观效果上形成多方面启蒙价值,最核心的当属现代政治与 “人情 (性)”启蒙,或者概言之为 “开启民智”,如梁启超所谓 “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15]借助梁启超在言论界的巨大影响力,小说中传达的近代政治、社会等理念渗透进其他题材中,在其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推动中国近代文学形成,成为促进近代社会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结语
近代文学研究长期不被重视,在传统研究者看来,这个时代的文学因创作水平低下而不具研究价值。这是受狭义文学观念主导所致,很大程度上将文学从其所属的文化空间中剥离出来研究,即便能意识到文学与文化空间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批评实践中却往往大而化之,由大的时代背景直接过渡到文学,二者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各种纠结在一起的复杂因素,以及与文学关系更密切的意识形态及推动其形成诸要素却被忽略。作为文化的顶级形态,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空间诸要素合力的结果,是作家处理文化空间诸要素之间关系后流淌笔端的结果。近代的特殊性在于社会现实对文学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在那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便沦为工具文学也必须做出回应,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也是传统文学难以企及的社会作用,如果说传统文学是书斋文学的话,那么近代文学就是社会文学,近代文学的价值在于实用性,而非艺术性。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88-3289.
[2]白红兵·学术、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学变革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3.15-22.
[3](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M].刘岳兵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11.
[4](南宋)朱熹·孟子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
[5]康有为·孟子微[M].北京:中华书局,1987.20.
[6]楼宇烈·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C].北京:中华书局,1988:184
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走向衰亡,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改造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臣民观的瓦解和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诞生.严复所引进的天赋人权、契约立国、进化论等学说以及梁启超宣扬的民族国家学说都深刻影响了世人.20世纪初的人们已经开始...
绪论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中国近代文学在八十年的时间里非常困难而又快速地走完了它的全程,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迈出了第一步。中国近代文学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继续发展和光辉终结,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阶段和先声先导,并指引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们不仅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更迭中留下矫健的身影,也给湖南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改变了湖南的社会结构、民间风俗。...
近年来,普通民众通过舆论渠道,表达扞卫国家利益和主权以及重新厘定文化身份的渴求.而官方和民间双重推动下的国学回潮,以及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宣传等,亦可看作为这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浪潮的一种显现.从某种程度上,它是长久以来西化追求之后的精神返乡[1]...
《点石斋画报》1884年5月8日(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创刊于上海,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采用连史纸石印,每期刊载图画新闻八幅,每月上中下旬各出印一次,随《申报》附送,也单独发售。因由点石斋石印书局印刷,故得名《点石斋画报》。1898年8月停刊(...
当前对近代至民国旧体诗词社团研究的成果不多,仅有袁志成、查紫阳、万柳、马大勇以及笔者的相关论著。①又钟振振教授与笔者所从事的民国时期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项目,因限于篇幅、体例等问题,仅专门收录了南社、如社、须社、沤社、国风社、变风社、...
李光洙(1892-1950)是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一生创作了60余部长篇小说,30余部短篇小说和300余篇(首)诗歌、散文、杂文等其他作品,被公认为是自20世纪10年代韩国启蒙主义起,在韩国文坛最具行动,最彷徨的作家,在新文学50年历史上拥有读者最多,给予感动和...
陈洵(1870-1942),字述叔,别号海绡,广东新会潮莲乡(今广东江门市潮莲芝山)人。陈洵少有才思,爱好填词。少时随父亲至佛山经商,拜吴道镕门下,补南海县学生员。后欲随叔父陈昭常仕宦关外未果,辗转至江西瑞昌知县黄元直家当了十多年塾师。客居江西...
《三四郎》是日本近代大作家夏目漱石的一部经典作品。学术界对《三四郎》的研究一般是将《三四郎》视为教养小说,表现了文明开化问题。随着20世纪西方文论的层出不穷,为我们阐释经典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方法,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有的研究者就从女性...
一、吕碧城的生平简述吕碧城(18831943),原名贤锡,一名若苏,字圣因,号曼智,法号宝莲。别名较多,有晓珠、信芳词侣、兰清、清扬、遁天等。安徽族德人。吕碧城生于光绪九年(1883年),自幼慧秀多才,除工于诗文,亦擅长书画,五岁知诗,七岁能绘巨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