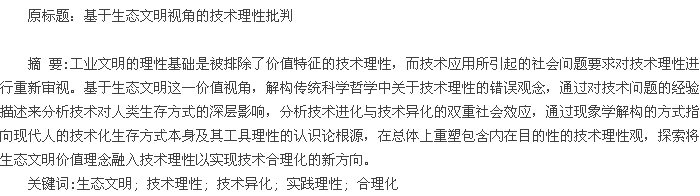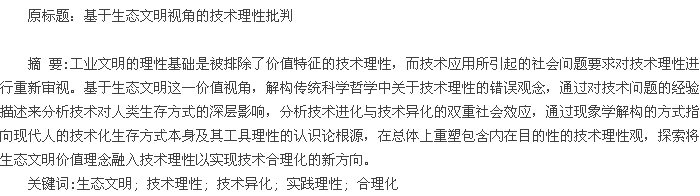
作为一种文明生物,人类总是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从而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人能够认识自己,在对错误的反思中成长,在对问题的弥补中进步。伴随工业文明的脚步,人类的自我膨胀与争功近利使得生态问题从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演化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是人类在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矛盾尖锐对立、凸显出生态危机的严重后果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性的审视与反思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把“生态学”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领域的研究结果。
生态文明问题从本体论上说是一个自然观的问题,从认识论上来说,则是一个技术理性问题。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现实生存的环境要素正在被全面技术化,人的生活经验正在接受深层次的技术转换,技术理性如何在生态文明视角下为自己找到一种合理化的价值实践模式是哲学研究与生态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无论是出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思还是出于对技术本身的社会功能的反思,人们都需要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维度上重新看待技术理性的社会影响,解构技术问题的“自明性”,把被人们无意识地接受的技术现象进行社会重建,并由此引导人们反思当前的生活,展示出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以及不同的看待问题的视角。
一、作为一种现代经验的技术问题
现代人类是技术化的人类。现代社会因对规范和高效的追求全方位地向技术敞开,而在技术理性的裁制下,自然、社会甚至人本身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技术化的改造,进入到严格的技术程序系统之中,成为可量度、可控制、可预测的抽象化与匿名化的存在。人本身的精神生活已经在生命整体的意义上被排除,现代人越是以自身的理性与生命意志推动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就越是使人自身的生命和自我走向知性和欲望。每一事物都外在于其他事物,而作为主体的人则外在于作为其对象的世界,这是一个孤寂的物的世界和众多弥散的个体的世界。
首先,人们经常在由一些数字和抽象观念所构成的世界中活动,以致日益脱离具体的生活,从而丧失了许多具体的经验,也逐渐丧失了人的个性丰富性。人们在技术化的世界里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世界,没有属于本己的时间存在和空间存在,就像计算机中虚拟的字符,随时可以被剪切、被复制、被重新组合。人本身就是一些过渡性的、短暂的、偶然的经验碎片,似乎每一个碎片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但又都不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因而,作为现代世界中的碎片之一,人们常常会惶恐不安地关注自己的存在,为了提升自己的存在感,人们会千方百计把它“炒”出来,把它“刷”出来,因为人们那破碎的自我正在远离给它以生命整合力量的生活,难以维系一种自足的存在感。
其次,快速的技术变革使得现代人对新奇性具有强烈的渴求,这种渴求趋向于感官经验的表层开发,寻求直接的冲击性的效果,从而创造出技术化的感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反思、领悟等深层的思想精神交流常因审美距离和社会距离的压缩而统统被消解。从表面上看,现代人获得了一种对“现在”的普遍分享,一种“经验的民主化”,实则获得的只是碎片化的经验感受,“它阻碍了能够有意识地自我判断和决定的自主和独立个体的发展”,超验的价值体系已然崩溃。
最后,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现代科技的发展打破了人们传统的经验结构,人的感觉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无不受到技术理性和商业逻辑的规制,世界的经验呈现以及人们经验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信息时代的新技术能否成功,取决于人们对新技术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反应,取决于新技术能否同人的知觉、情感与思维达到平衡。而从目前来看,主体已经越来越成为人工经验的产物,直接经验的丧失使主体与真实环境疏离,很可能使主体沦为技术的附庸,失去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关注的兴趣。此外,媒体的变化会直接引发主体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变化。在电子媒介时代,人的意识获得了延伸,这种延伸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生存体验,但也造成人们最核心的内在自我同现实生活环境的技术性隔离。在现代技术操控下,整体的、综合的、时间性的经验方式已经不存在,破碎的体验时代开始———这种体验是一种破碎的、异化的经验,是一种现代人无法把握周围世界时出现的经验状况。
二、技术进化与技术异化
人们对技术产生了深刻的依赖性,倾向于通过建构可能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而社会的技术化降低了人的因素对技术系统的直接干预,也降低了人本身在社会技术系统中的地位。
首先,就社会机制层面而言,工具和机器同生活在工具和机器环境中的人们被现代技术融为一体。这些技术正在变成人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惯常的生活方式,它们使人类外部感官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同时,也使机械的习惯同生物的、社会的节律混合到一起。米德在 1954 年 9 月 4 日的《时代周刊》中撰文说: “对社会前进不得不保持过高的速度,方能跟上机器的速率,人们的怨言实在是太多。
如果你的前进完全彻底,如果社会、教育和娱乐的变化并驾齐驱,那么迅速前进是大有好处的。你必须同时改变整个模式,同时改变所有的人———而且人民必须自己下决心向前推进。”迈克尔·扬认为:“任何复杂的工具都是一种物质性的习惯,要经历反复地否弃或修改,这些习惯把无数先辈的过往经验封存在现在,并在其以修改过的形式得到传递以前不断地精致化( further elaborated) 。”
人类的全面技术化带来了诸多社会机制方面的异化问题,如物理自然环境技术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人类社会自然环境技术化造成的个体对官僚机构的无力感。
其次,就人类精神层面而言,人的心理自然环境被技术化普遍引发了生命的无意义感。人们倾心于技术、投身于技术,但对技术又常怀着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总体上说,高度发达的环境给人的参与机会很少,而对专业化分工的要求却很高。这导致了人类总体的进化和个体的异化。“潜意识抑制保护我们的核心价值系统,它借助一种简单的机制,大大缓解经验的冲击,从而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样。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冷处理系统导致终身的心理僵化或梦游症。”
一方面,没有异化,就没有进化。而另一方面,通过异化而达到的进化总是不断需要纠偏才能完成真正的进化。那么,人们通过何种途径来完成这种纠偏呢? 很多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赞成技术是一种运行着的人性的观点,他们试图通过将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进行批判性的比对来揭露现代技术的反人性,如果说前现代技术是体现了人性、服务于人类的,而现代技术是压抑了人性甚至威胁社会民主秩序的,那么,从前现代到现代,技术中的人性是如何丧失的呢? 显然,按照现象学观点,对象总是关联着对象视域,技术问题也不可能仅仅是技术问题。
“与其说我们需要对技术进行人性批判,毋宁说需要对人性 - 社会 - 技术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按照中国学者赵建军的观点,技术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的建构过程。技术建构的对象是问题,技术问题的生成背景包含各类相互制动的社会力量,具有理性探究的成分,也离不开判断、权衡、直觉、猜度和抉择等过程; 技术问题的解决部分依靠技术发明和工程设计,但技术结构与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与科学中的“理论之于事实的不定性”类似,在技术中存在着“设计之于功能需求的不定性”; 最后,技术产品的接受也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计算过程,而是包含着建构、磋商和冲突的过程。
三、技术理性异化的根源是伦理维度的缺失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来由宗教所整合的价值体系逐步被世俗化的浪潮所吞没,新的价值体系的支撑点不再是具有超越性的神,而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现代工业化的价值体系中,理性的工具意义———计算获得了非理性的突显,自由的功利意义———权利获得了技术性的规制。
科学、技术和工业已经在经验上成为进步观念可变现的基础。支撑进步信念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自由主义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价值理念。在进步的教条里,价值的创造被简化为人造物的快速增长,价值的实现被等同于物欲的满足,而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这样一种进步事业。社会生活的总体背景急剧地变动,一方面是物质和精神的传统联系的断裂,另一方面是世界本身的分裂以及人的主体意识的分裂、人的经验空间的分裂。随着对世界总体的研究转变为一种分工的、职业化的技术操作,人逐渐丧失了对其自身行为的最终负责。
在工具取向的理性视野中,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按照人的文化、欲望和目的重新理解的自然,是人类主宰自然的理念的产物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自然不是一个伦理对象,而是一种纯粹的资源。以这种技术理性为指导的工业生产实践是以打碎、分割、割裂自然生态秩序为前提的,当人类的实践行为对自然所造成的破坏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之后,生态自然的秩序就会遭到毁坏,人类则要面对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因而,要克服生态危机,就要弘扬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并且要把这种价值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目的渗透到技术理性之中。生态文明价值观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根本,把自然作为伦理价值的对象,把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作为实践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权力和利益的同时,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是人类群体性或社会性的产物,责任源自人际间的社会依存性,是特定社会之于个体思想、行为的规定性,责任主体通过与群体、社会以及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将这种规定性内化,并最终体现于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实践之中。传统的责任伦理大体上是以行为动机和实际效果来确认责任的,然而在科技主导的现代社会,很多风险都是事前无法预知其后果的,尤其是那些以科学 - 技术为主导的人类行为,很多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事物存在的自然属性的行为,如转基因的后果、克隆人的后果等,行为动机本是善意的,但人们并不清楚这种善意的动机是否一定能带来善良的结果,因为很多后果都需要跨越一段漫长的时空之后才能具体显现出来。换言之,人们的行为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无法预先确知自己行为的影响。无法确知影响,当然也就无法确定责任,无法确定责任,也就无法建立相应的责任约束机制来限定那些明知是很大风险却又无法定义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迷失了责任的主题,也无法做出责任的评价。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人们总以为自己也可以成为上帝,并努力做出了许多以上帝的权能才有资格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却发现,自己并非全知全能。从特定个体或特定群体的角度来说,随着社会分工与个人主义的膨胀,人们的利益分化日趋严重,他们追求自由、追求发展、追求成就、追求利益最大化,但特定时空与社会资源的限制势必造成这些不同主体间利益的分裂,以致每个人都希望财富个人化而成本社会化,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不想负责任或一心只想转嫁责任,造成主体的社会责任缺失。
四、技术理性的合理化探究
当今世界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告诉人们,科学技术越发展,越需要与自然、与人类的生活经验相适应。“现代社会构建了一个技术统治社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的力量遍布整个社会,不仅是对自然,而且深入到人们的交往———这导致技术对人们头脑的控制,并进而导致实践堕落为技术,堕落为社会非理性。”
在技术实践论的语境下,理论和应用的关系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样一来,技术理性被片面化为工具理性,而这种工具理性又进一步使得实践概念的内涵片面化,使得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片面化为以对象控制为核心的技术活动,技术的失控自然而然会导致生态危机甚至社会和文化的危机。这要求人们在理论理性之外发展一种实践智慧,用以指引人的生活与人类的生存,在把人类作为自然生命整体的一部分的意义上,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说法,实践智慧应“通天、地、人”,且“参赞化育”。技术并非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过程,技术理性也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工具理性。技术首先是一种人类的有目的的设计活动,技术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就是“设计”。
这种设计不仅是理性的设计,也是理想的设计。根据中国学者陈凡和王桂山的看法,“设计思维形成人的实践活动的观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实践理性。这里的实践理性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实践观念,是一种绘制蓝图、刻画意想之中的应然状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以追求对象在实践活动中达到预期效果和目标为价值取向的”。
那么,如此说来,前文所说的技术理性就是建立在技术实践基础之上的技术实践观念,技术理性是一种特殊的实践理性,是不断发展着的具有综合性、整合性的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与经验个体,它的理想就是通过技术设计将文化、道德与科学和谐地融会到技术之中,在观念中建构出理想的客体。此外,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设计也是从理性到感性、从理论到实践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要求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关系经验思维,理论理性在这个过程中要合理地转变为实践理性,过渡才能理想而顺利地完成。如哈贝马斯所说,“实践理性不仅追求可能性和合目的性,而且也追求善”,但当前,“技术生活被置于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之上,以创制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越来越缺失了伦理的维度”,所以,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迫切地要求技术理性展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意蕴,归还技术活动的人性本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的统一、价值属性和工具属性的统一。在技术设计中,如果技术的合目的性、主体尺度与价值属性能够得到有意识的凸显,人的感性经验中的丰富个体内涵与超越性的价值信念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人文精神将在科学的社会应用中得到彰显。
总之,生态文明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合人性的文明形态。基于这一文明视角,人们应该在对技术的合理化探究过程中更深入地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在人类伦理观变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科学技术显然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人对自身的看法,那么,科学技术是否也根本改变了人性呢? 当然,如果科学技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人们就有要求科学技术必须人性化的充分理由。
参考文献:
[1] 赖章盛. 关于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的哲学思考[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5) : 38—40.
[2] Theodor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J]. New Ger-man Critique,1975( 6) : 18—19.
[3]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53—58.
[4]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88: 163.
[5] 王大洲,关士续. 技术哲学、技术实践与技术理性[J]. 哲学研究,2004( 11) : 55—60.
[6] 赵建军. 超越技术理性批判[J]. 哲学研究,2006( 5) :107—113.
[7] 丁力群.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本真涵义与变质形态———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说起[J]. 哲学动态,2012( 1) : 31—37.
[8] 陈凡,王桂山. 从认识论看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划界[J]. 哲学研究,2006( 3) : 94—100.
[9] 哈贝马斯. 对话伦理学与真理问题[M]. 沈清楷,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7.
[10] 吴彤. 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J]. 哲学研究,2012( 2) : 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