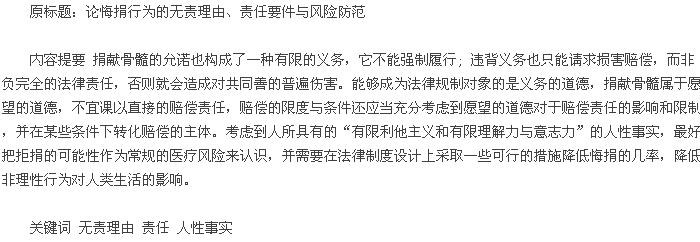
最近几年媒体报道了许多捐献骨髓( 造血干细胞) 者最后反悔而置受捐者处于危险境地的实例。
像白血病这样的疾病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只能通过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来治愈,而造血干细胞只能通过捐献的方式来获得。骨髓移植手术的一个必要程序是清髓,就是把不健康的造血系统全部摧毁,以移植进去健康的干细胞。进入清髓程序之后,病人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身体已没有免疫能力了。这时如果供体突然不愿再捐献了,那么病人只具有非常有限的生命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由患者亲属来捐献,据报道,患者亲属与患者的骨髓配型大多属于“半相合”型,过去这种情形一般不适宜做移植。与“全相合”相比,“半相合”的骨髓和造血干细胞移植存在排斥反应大、恢复周期长、后期治疗费用高等问题。
①诸如此类的反悔行为在国内外都不鲜见,有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骨髓捐献志愿者最终“临阵脱逃”的概率非常高,美国媒体报道全美的拒捐率高达近 50%,而日本学者统计亚洲志愿者中则有约60%最终拒绝捐献。而在我国,拒捐率在 20% 左右。由于联系方式变更,志愿者年龄以及身体状况已不适合捐献条件等原因,山东、广东、北京等地骨髓库的志愿者流失率达到 30%。
②有的因拒捐产生纠纷而告上法庭,有的甚至还导致了患者死亡的情形。从这样的疑难案件( hard cases) 中,我们看到了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它跨越了医学伦理学与法律; 深入地思考这个复杂的问题,也为我们在理论上解释与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透过一些情绪化的批评与指责,我们更应当看到这些案例所涉及到的深层次法律与道德哲学难题,因此必须详尽地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关系的性质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它们包括: 自愿捐献的行为( 允诺) 在道德上与法律上的性质是什么? 这种类型的允诺能否产生强制执行的义务? 如果不能,应负的道德与法律责任( 如果有的话) 是什么? 在弄清全部的理论问题之后,怎样在制度建设和实际操作中有效预防此类极端情形? 这些都是本文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允诺与义务的一般关系的分析入手,然后切入关于捐献允诺之义务性质的更为复杂的分析,最后分析责任承担的限度和风险防范措施问题。因此在论证的结构上,本文第一部分重点讨论悔捐行为对允诺、义务与责任的一般关系理论的挑战,即悔捐行为只应承担极为有限的法律责任,而非一般关系理论所展现的要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借助于规范义务、美德义务以及义务的道德、愿望的道德两组区分来更为详尽地分析捐献义务的性质以及对于责任的限制,并尝试提出责任要件与承担主体移转的方案; 第三部分继续分析公益捐献脆弱性的人性基础并以此为根据给出制度上可行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总结悔捐行为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悔捐行为的无责理由
关于拒捐行为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公益事业捐赠法、献血法对骨髓( 造血干细胞) 捐献无明确规定,《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指向的是财产而非具有人身性质的物,2007 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把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的移植排除在外。
③因此关于拒捐责任( 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 的探讨需要在一般理论层面上进行,而不能简单地类推适用相关的规定④,因为不同的捐献对象所涉及到的外在行为存在性质上的重大差异。虽然关于捐献行为的分析不能简单套用合同法的规定,但它首先类似于契约法上的一种允诺( promise) 行为,或者说它是一般意义上的允诺行为。下文就从分析允诺的一般性质开始,探讨围绕允诺所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关系,重点在于指出捐献骨髓的允诺所具有的特定性质。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下文分析所使用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概念既是道德意义上的,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因为二者共享着一套词汇。⑤
( 一) 以规则为基础的自愿性义务:
一种无条件的理由( a categorical reason)假设 A 对 B 做出了一个允诺,承诺在周五之前归还借 A 的一本书,这一允诺本身改变了 A 的道德地位,使得其相关特定的行为不再是任意的( optional) ,而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强制性( oblig-atory) 。
⑥这种强制性会表现为一种义务,如果能够产生义务,那么义务的性质是什么,即它对 A的行动有多强的约束力? 关于允诺与义务的分析成为了本文讨论的起点,因为整个骨髓捐献制度的设计以及争点都源于一个自我施加的义务,即自愿捐献的行为,接下来关于捐献的道德与法律困境的分析与解决都要基于我们对这个“义务”的性质的认识,而分析的重点就是拥有义务在规范性力量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Joseph Raz 认为,允诺并不是在表达做某事的一种强烈的意愿,而是在表达承担义务,二者在实践推理的重要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他指出: “允诺是自愿性义务,并不是因为允诺做某事是一种有意图的行动( an intentional act) ,而是因为它是沟通一种承担义务的意图,或者说,无论如何是在为他自己创造一个行动理由。”
⑦允诺的意图观认为,遵守允诺的理由本质上在于它能产生一个最好的结果,意图本身并不拥有独立的力量。而义务是以规则为基础的,义务所产生的理由的效力也来自于规则。因此,规则和义务都具有一种无条件的性质,即规则和义务的效力都独立于行动者本身的目标和欲望。用 Raz 一以贯之的理由论来概括就是,允诺一旦做出,基于某些规则,它自身就产生了一种独立的力量,在性质上表现为一种排他性理由或无条件理由( 绝对的理由) ,即排除行动者个人在做出允诺时所能依据的他自己关于理由的判断与权衡。
对于任何一个理由来说,如果它要具有义务性就必须具有这种无条件的性质,即独立于行动者的主观目的与偏好,否则就不成其为一种义务。作为一个结论,允诺在允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规范关系是:允诺就是“在允诺人和受诺人之间创造一种关系———它是从相冲突理由的一般性竞争中得出的。
这种关系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联结,即约束允诺人偏向于受诺人。它强制允诺人要把受诺人的主张不仅作为每一个人就对他的尊重和帮助而言都会拥有的诸多主张中的一种,而且还要作为拥有强制性力量的主张。”
⑧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允诺与其他的行动理由相比在实践推理中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它们是基于规则的,并强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义务———自愿性义务。
⑨按照允诺的一般理论,做出允诺就会产生一个独立的义务,独立于行动者自身的目标和欲望,除非得到受诺人的豁免,否则违背义务就要继续强制履行或者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原理也适用于本文关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讨论,但是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形,我们需要对其中的相关关系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
( 二) 骨髓捐献中的允诺与义务
捐献骨髓具有阶段性特征,并不是通过一个行为来完成的,而且从有捐献的意愿到真正实施捐献行为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永远都不会遇到匹配者。当我们通观整个捐赠过程时,可以发现捐献之允诺在允诺的对象、内容和性质等方面并不具有典型允诺行为的特征。
1.公益捐赠的阶段性以及相关关系的分析为了保障骨髓捐献的公益性,所有的捐献对象都必须是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机构,而不能是直接的个人,否则很难保证不存在变相的市场交易行为的发生。根据我国骨髓捐献的流程,整个捐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一般协议阶段。
适龄、身体健康( 符合无偿献血条件) 、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与各地红十字会( 或者中华骨髓库分库) 的热线电话联系报名,填写《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表》及相关资料,并抽取 6~8 毫升血液。组织配型实验室将会对抽取的血液进行 HLA 分型等检验,并把该个人所有相关资料录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计算机数据库中。这样他( 她) 就成为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⑩第二,当出现捐献相对应的特定患者即受益人时,为特殊协议阶段。当中华骨髓库捐献者资料库检索到某位志愿捐献者与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患者的 HLA 配型相合时,则要进行血型高分辨检测并对志愿者进行健康体检; 进一步确认合格后,经询问若志愿者愿意继续履行捐献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承诺,中华骨髓库将要求其签署捐献同意书及捐献协议书。
此后,志愿者和患者将分别被安排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和移植前的准备工作。
第一个协议是捐献人和受捐赠机构之间的双方关系,内容是关于骨髓捐献进程中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性工作,但同时也在表达一种捐献的意图( 也许是强有力的,也许是不成熟的) ,否则单纯进行 HLA 分型检验就没有了实际意义,但这一意图本身并不是关于捐献的允诺,因此可以称之为一种初步的允诺( prima facie promise) 。这种允诺不产生新的义务,而只是从情感上加强了人们本来具有的对于他人的人道与仁慈的道德义务。从义务的分类上看,这一阶段的行为可以视为不完全的义务( imperfect duty)———比如慈善的义务( duties of charity) ———的进一步延续,即有了捐献的意图而不是单纯宣告“我们负有捐献的道德义务”。这一类义务意指要去做一般性的行为,并不存在特定的人能够向义务人提出具体的主张。
不完全义务并不回应权利,它也并不指向特定的权利人或受益人。
第二个协议旨在表达捐赠人承担义务的意图,允诺的内容是真正捐献的承诺; 而在此之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血型高分辨率检测等)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据采集,而是有着特定的目的,即是否符合特定受益人的捐献要求。从表面上看,这一义务可以称之为完全的义务( perfect duty) ,存在特定的权利人或受益人,若违犯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一允诺已涉及三方关系,即捐献人、受捐赠机构和受益人,类似于第三方受益人协议。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捐献人和受益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捐献人是对受捐赠机构还是受益人承担义务? 受益人的加入对我们理解义务的性质会产生影响吗?
根据边沁的观点,拥有权利就是成为一个义务的被意图的受益人( beneficiary of a duty) 。针对这一观点,Hart 提出了着名的第三方受益人( the third-party beneficiary) 理论。Kamm 曾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 A 和 B 签订一个协议由 B来照顾 A 的母亲,这样 A 就有权要求 B 照顾其母亲,母亲是被意图的受益人。但是对 B 享有权利的是 A( 权利的主体) ,B 负有义务( 义务的对象是A 的母亲) 。在哈特看来,A 享有权利的标志就是,A 的选择是确定 B 是否应该帮助其母亲的有效基础,例如 A 可以放弃这项权利从而免除 B 的义务。A 享有权利的标志并不是 A 将会因为它的实现而从中受益,而是拥有这种选择。
因此,根据 Hart 的理论,权利的标志是选择而非利益,权利人与受益人是可以分离的。骨髓捐赠类似于这种第三方受益人情形,但是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权利的选择论。在我们所讨论的允诺中,捐献的义务直接指向受捐赠机构,根据骨髓捐献领域通行的双向匿名原则,捐献人不能直接面对受益人。但是公益机构作为一方当事人,只具有有限的权利,比如要求捐赠人要履行相应的检查手续且只能在公益机构指定的医院捐献等等。但是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具有改变自身或他人规范性地位的力量,它理论上并没有选择权,因此无法放弃这个权利而免除捐赠人的义务,否则与其作为公益机构的性质以及在这个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不相符。允诺所产生的义务的对象是受益人,但是受益人并不是权利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享有其他权利,受益人可以基于对允诺的信赖而享有某种意义上的请求权。因此,捐赠机构基于允诺而享有权利,受益人基于信赖而享有权利。
无论是捐赠者还是公益组织都清楚,捐赠本身最终指向的是受捐者,而不是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在其中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直接利益可言。受益人的加入只是使得我们对其中的道德或法律关系的定性更为复杂化,但是应当说,这个制度设置对于允诺产生的义务的性质来说不产生根本的影响,义务依然还是独立于捐赠者本人之欲望与目的的排他性理由。同时受益人的加入也使得义务的履行有了特定的人而成为一种完全的义务,当然从根本上讲,这一完全义务的形成是由关于捐献的允诺本身造成的。义务( 尤其是法律义务)一般都具有上述这个性质,Leslie Green 又称之为内容独立的理由( content-independent reasons) ,“内容独立”的标志是理由的力量并不依赖于这些义务所要求的行动的性质与优点,而有其他的独立来源,比如“信守诺言”这样一个法律与道德规则。具体来说,内容独立的理由包含两个方面,即这样的理由在效力上既是绝对的又是优先性的( both categorical and pre-emptive in force) 。
优先性意味着义务人要把自己关于行为价值的看法放在一边而去履行义务; 绝对性意味着义务的主张并不取决于义务人自己的目标与利益。
“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作为一个法律规定( 同时也是道德规定) 本身即强加了一个义务,而不取决于行动者是否认为吸烟有害健康或者是否能够满足其个人特有的欲望与爱好。这些都是关于义务的一般性分析,或者说只是在表达一般情形下的一种分析性的主张,即义务应当具有这种力量并应当以这种方式而被遵守。但是在本文所讨论的语境中我们就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理由冲突,义务的规范性力量也许独立于并优先于捐赠者本人的欲望与目的,但是这一规范性力量却有可能被欲望与目的所压倒。
2.理由冲突的复杂性与责任的难题在签署捐献同意书且受益人已经进入清髓程序之后捐献人是不能或不应反悔或停止捐献的,但现实中可能会因为多种原因导致允诺并不能实现。其中存在比较复杂的理由冲突,概括起来有两种: 一是捐献人可能因为一个更强的权利或利益而“侵犯”受益人的权利; 二是基于捐献人个人的某种( 或某些) 欲望、目的、认识、怨恨或压力而反悔。这都表明允诺所产生的义务与受益人所享有的权利并不具有绝对性,权利的严格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需要考察各种相冲突理由的强度,并把责任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悔捐行为上。下面分别讨论这两种理由冲突的情形。
允诺的接受者与受益人无疑都有相关权利,捐献者与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霍菲尔德意义上的狭义的权利,即请求权( claim-right) 。Ka-mm 指出了在霍菲尔德的请求权体系中有着更为复杂的权利冲突,有时在权利的冲突中,权利具有一种性质,即义务人可以为了更重要的权利而侵犯( infringe) 这个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权利就是可侵犯性的( infringeable) ,但是并没有违反( violate) 相对应的权利。权利的可侵犯性与违反性是 Judith Thomson 对权利做出的一个区分,这一区分表明了相冲突理由的性质差异。
Thomson 认为,我们也许侵害了某人的权利却没有不当侵犯它这是可能的,只有违反了一项权利,我们才不当侵害了某人。而“侵犯”与“违反”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在权利之外存在一个更为重大的权利或正当利益导致它们存在的重要性压倒了义务相对应的权利的重要性。
此处受益人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也具有类似的可侵犯的性质,比如捐献人的身体健康条件已经不再允许捐献,或者说继续捐献会损害其健康,因为根据公益捐献的性质,保证捐赠人的健康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尽管受益人的权利也具有很强的严格性。第二种理由的冲突可以称之为对受益人权利的不当违反。其中的情形多种多样,有的是基于家庭的压力( 这是多数情况) ,有的是因自身的意志软弱而无法坚持下去,有的是因为捐献过程中机器故障或一次捐献数量不够而要求再捐导致的捐献人中途退出。
这些都可统称为悔捐行为,也就是并不具有正当理由或压倒性正当理由的拒捐。此类拒捐行为使得基于这一允诺而做出相关行为的受益人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而不仅仅是物质的损失。一般来说,其中相冲突的理由在所影响的利益的重要性上并不对等,对于捐献人来说所能影响到的利益是比较小的,也许只是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而对于受益人来说,则可能会影响到生命。但是利益的重大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法律上或道德上要强制捐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承认并“保护”这种拒捐行为。拒捐行为存在一种所谓的“证立的独立性( justification-independence) ”的特征,即对这种行为的承认甚或保护的根据并不来自于对个人的欲望与目的的道德与法律评价,而是来自于一个独立的理由,即允诺本身不仅具有公益性( 自我施加义务) ,而且允诺的内容具有很强的人身性,它本身不可以强制执行,否则就违反了“人是目的,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的这个康德式人性公式。这就是骨髓捐献最重要的原则———自愿原则———的最终根据,美国国家骨髓捐献者资料库一再申明,骨髓捐献永远是自愿的,志愿者应该被告知在实施骨髓移植手术前的最后一分钟都可以撤销同意,世界骨髓捐献组织也声称捐献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
而且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保障捐献的完全自愿原则对于整个捐赠制度来说是具有根本性的,因为强制执行只会赶跑潜在的捐献者,导致捐赠体制的受损,从而造成普遍的功利伤害。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能够与受益人的权利相抗衡的是这些具有独立性的证立理由,面对这些理由,受益人的利益就不再具有当然的优先性。
在第二种理由冲突中,除了证立的独立性,我们还可以发现权利的另一个特征,即权利保护的强度与其所体现的利益的重要性并不是成正比的。对权利存在的这一困惑 Raz 曾指出,“一方面,通常对于权利持有人来说,权利指向的是或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相当普遍的是,一个权利的价值,即它所被给予的分量或者遵守它的严格性,并不与权利持有者的价值相符合。”
上述那些独立的证立理由可以被称之为公共善( common good) ,即一些普遍的或衍生的具有公共性的价值。权利的严格性与权利人利益的重要性是分离的,或者说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这取决于更重要的权利或公共善的保护。因此,捐赠人的允诺并不是一种可以强制执行的排他性理由,从理论上说,捐赠人可以随时并基于任何理由撤销捐赠,在道德上或法律上还要保护这种撤销的效力。
于是难题就转到关于责任的讨论。在签署捐献同意书及捐献协议书之前,捐献者可以随时反悔,因为相关的协议并非关于义务的允诺,而是在表达一种允诺的意向。HLA 分型等检验与血型高分辨检测所引发的相关费用,不应当由捐献者个人承担,而应当由公益机构和受益人分别承担,因为这一阶段属于前允诺时期,还没有涉及责任问题。基于保护捐赠人的健康等正当理由而对权利的侵犯( 而非违反) 已阻却了责任的产生,责任( 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 的产生只能始于严格意义上的悔捐行为,即没有压倒性正当理由的拒捐行为。此类拒捐行为不能强制履行,法律上还要保护这种拒捐的效力,因此捐赠人并不对拒捐行为可能导致的受益人救助机会的丧失、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承当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尽管不排除道德意义上的否定评价,比如网络上对拒捐行为是“变相杀人”的评价更多就是道德评价上的激愤之词。即使如此,这并不影响承担其他责任的可能性,比如基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 相关医疗费用的支出等) 和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上文关于允诺的一般理论的论述可以看出,违背允诺所产生的义务要么取得受诺人的谅解,要么承担赔偿责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1) 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以及( 2) 如果要承担的话,那么条件是什么、由谁来承担。
二、悔捐行为的责任要件
对损害赔偿原则适用与否的讨论通常基于后果论的考量,即违背允诺也许应该负有道德或法律责任,但是如果执行,则在目前捐献成功率很低的情况下会使得捐赠制度的存在更加举步维艰,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个制度不再能够维持下去,因此应当免除捐献人的责任。这是一个直观而有效的理由,许多文献已对这个论据进行过比较详细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有力地限制了“人应该信守诺言”这一具有很强义务论( deontol-ogy) 色彩的道德与法律原则在这个具体情形中的适用。但是这一后果主义( consequentialism) 的进路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作为一种外部限制的理据,后果论的考量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析和把握略显粗糙,它无法深入争议本身并把复杂的关系和核心的问题揭示出来; 第二,由此又导致后果论无法提供一个融贯的论证和实践上可接受的方案,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因此,本文摒弃这一论证方案,并继续沿着分析义务的进路,通过对自愿性义务的更为复杂面向的梳理,力求揭示出我们在直觉上所面对的道德和法律困境的核心所在,最后以此为基础分析认定责任的条件以及承担责任方式的可接受方案,在“应当”与“结果”之间寻求一种可以接受的平衡。
( 一) 捐献允诺的双重性:规范论的与美德论的关于义务有两个基本维度的考量,一是规范论的,二是美德论的。所谓“规范论的”是指义务来自于某种职责规范的规定,是外在因素要求主体的,而不是主体内在生成的。所谓“美德论的”是指义务来自于行动者的信念与良知,出于成为道德卓越的人的动机而自我施加的义务。这里责任的基础不是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正义原则,而是自我付出与牺牲的美德伦理。John Rawls 曾经区分了人的三种道德行为,即自然责任( natural duty) 、职责义务和份外行为( supererogatory actions) 。自然责任是针对一般人而言的,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责任。根据 Rawls 的论述,它们是一些普遍的、直觉上明显的道德原则,它们并不来自于政治与法律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性安排。比如帮助处于需要或危难之中的另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他自己无需冒太大风险或承担过多损失) ,不伤害或损害其他人的责任等; 与此相比较,职责义务则来自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性安排,和行动者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与职责相关; 份外行为远远超出了自然责任的要求,对于一些份外行为———如善行、仁慈、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尽管这样做是好的,但“它并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或义务”。“尽管我们有一个自然责任去产生极大的善( 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够相对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但是当我们自己要付出很大成本时,就被解除了这一责任。”
根据上述“规范论的”和“美德论的”义务的区分,可以把自然责任与职责义务视为规范论的,而份外行为并不是一个人的义务或责任。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去实施一个份外行为、履行一个自我施加的美德义务是追求道德崇高或道德卓越的行为,比如前面提到当捐献行为会损害到捐献人的健康时就解除了这一责任,但是如果捐献人还是决定继续捐献就是一种份外行为。
从上文关于捐献允诺的分析来看,它首先是一种规范论的义务,其效力来自于外在于行动者的某种规则,正式的捐献与允诺协议以及受益人基于信赖所做出的一系列后续行动更强化了这种允诺的义务性质。正是允诺本身赋予了捐献意愿最终具有义务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在表达一种可有可无的意向。但同时也应看到,捐献行为本身( 或者说它的内容) 已经超出了人的自然责任,也并非一种职责义务。实际上根据 Rawls 所做的上述区分,自愿捐赠的行为本身更多属于份外行为,是一种美德,本身不是一种法律或道德义务,只是这种美德通过一定的程序可以为自身设定了一个规范性的义务。单纯分析自愿性义务的性质以及它在效力上的独立性不应模糊掉这一行为本身属于份外行为的性质; 而且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其履行允诺的动机更多是基于自身对于这一行为性质的认识,即这是一种救人于危难之中的美德,履行义务的力量主要来自于自身的这种道德信念与道德良知。由此可以看出,捐献的允诺具有比较复杂的面相,从表象来看它是一种规范性的义务,而支撑这一义务履行的是一种基于道德良知而自我施加的美德义务,从这一点我们既能够看出所谓的自愿性义务之“自愿性”的来源,同时也能从中洞悉我们直观上道德困境的根源。
应当说,所谓的美德“义务”只是一种修辞性的用法,本身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或法律义务,而是通过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自我立法所进行的行为上的一种心理强制。上述两种义务的区分是道德哲学上的一种常见的分法,尽管用语也许不同,比如 Lon Fuller 的“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区分。对于本文的目的来说关键是探讨这些区分对于法律规制的意义,而后者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Lon Fuller 曾经把规范性义务所包含的内容概括为义务的道德( the mo-rality of duty) ,它确立了一些基本的规则,以保障一个有序社会的存在或使其得以达致其特定的目标。如果说义务的道德确定了有序社会得以存在的最低标准,那么愿望的道德( the morality of aspi-ration) 就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卓越成就作为出发点的,它是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人之力量最完满实现的道德( the morality of the GoodLife,of excellence,of the fullest realization of hu-man powers) 。
前者规定了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后者设置了社会生活所追求的完美标准。前者是法律直接规制的对象,从中也可以比较容易找到一些可行的行动标准与裁判标准; 而后者与法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法律没有办法强迫一个人达致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卓越程度”,但是间接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法律上也有许多的制度设计( 比如合同法关于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合同的效力规定、机动车的强制保险等等) 都是旨在降低人的非理性行为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 二) 义务的刻度与责任的认定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捐献允诺的效力来自一个自愿施加的义务,“允诺禁反言”体现了义务的道德; 但是这一义务的内容( 即无偿捐献) 、性质( 即公益性) 和保障履行的力量( 即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内在良知) 都体现了一种愿望的道德。两种道德集中在一个事物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我们能够设想在这样一个事物的道德标尺上,最低端是关于义务的刻度,最高端是人的生活所能达致的最卓越标准。其中比较困难的是确立道德标尺上义务的刻度,就像赌博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从人类行为卓越性上说,任何赌博行为都是一种拜物主义,非人的目的所应努力为之的。但是法律并不禁止所有的赌博行为,广义上说赌博也是一种游戏( 公共善之一) ,所谓“小赌怡情”; 只有达到一定条件的( 人数、数额、有无固定场所、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否为赌博活动的组织者等等) 赌博行为才属于法律规制的对象。寻找这种刻度是法律哲学永恒的难题之一,刻度过窄就无法维持一个有序社会的存续,而义务的范围过大又会导致道德义务的泛化并进而强制推行一种生活方式、或强制让人们接受一种善观念。应当说,这种刻度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它的确立也是一个主观论证的结果。
上文在自愿性义务之性质分析的框架中关于捐献允诺之责任的讨论已经排除了“强制履行”这一承担责任的方式,最后集中到是否要使拒捐人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问题。不考虑限度问题,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可以总结为: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拒绝捐献者都要承担道德与法律责任,承担责任者只限于严格的没有正当理由或压倒性理由的拒捐者。第二,拒捐者即使承担责任也不能使其履行强制捐献的义务,而只能考虑拒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是否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第三,有观点认为,根据契约法中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的原则,受益人可以对捐赠人请求损害赔偿。前文已经述及,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并不能直接套用合同法既有的规定,合同损害中的信赖利益赔偿有一个前提,即合同要有对价( consideration) ,这是允诺的期待理论,在这里似乎并不能直接适用,因为公益捐赠并没有对价。但是在理论上确实可以借鉴信赖利益作为一个理由,即作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基础,而且这还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一般而言,允诺的义务可以使得受益人获得一种权利,在悔捐的情形中实际上就是基于信赖允诺而享有对所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损失在道德直觉上和法理上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从道德上说不伤害他人也是一种自然责任。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上,赔偿的限度与条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愿望的道德对于赔偿义务( 责任) 的影响和限制,而不是基于义务的道德来承担完全的责任。这里所强调的只是限制和影响,而不是要取消或免除所有情形的赔偿义务。这种影响与限制可以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讨论捐献允诺之责任时,义务刻度的范围不宜过大,否则就是在执行一种愿望的道德,在心理或其他方面变相强制人们成为一个卓越的人,这不是由法律来执行的范围; 第二,如果执行一种愿望的道德,即使只是赔偿,对于实际或潜在的捐献人来说都构成了一种心理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所做出的决定就不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决定,就违背了公益捐献的完全自愿性质,而完全自愿原则是世界各国骨髓捐献的通则; 第三,愿望的道德并非完全拒斥责任的承担,而只是会限制责任的认定、范围和强度。认识到捐献允诺的双重性能够使我们更加注意行为本身的公益性质、行动者的内在动机和主观心理,而不仅仅只是分析允诺之中所包含的关于承担义务的意图这个层面。注意到这一点能够影响我们关于责任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它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此外,愿望的道德的这种限制和影响还体现在承担责任的主体上,这一点更应引起注意。任何责任的承担都要考虑到行动者的主观方面和行为本身的性质,法律可以执行义务的道德,而执行愿望的道德( 即使只是赔偿金钱) 要有更为强大的理由和严格的论证与限制。执行愿望的道德应当设立更为严格的主观过错要求,这在许多法律制度中都有表现,比如“见义勇为”中过当行为的责任、不当无因管理对本人的损害赔偿等,不但要求具有明显的过错,而且在责任承担上还要从轻、减轻或免除相关赔偿或处罚。因此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拒捐行为的赔偿责任,除非是故意的拒捐行为或者说一开始就持有一种蓄意的拒捐意图,否则基于其他原因的拒捐行为———家庭的压力、由恐惧导致的临阵脱逃等等,在法律上最好不要直接规定由捐献人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物质损失的赔偿或精神损害赔偿) ,受益人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进行保护。
因此,责任继续承担,主体可以转化。赔偿的义务是继续存在的,但不必然由捐献人来承担; 履行义务的主体可以转化,即赔偿义务可以基于某些公共善的考虑而由法律直接规定某些机构代为承担,也就是把个人的赔偿义务转化为一种职责义务。结合上文的论述,这些公共善的考虑包括:( 1) 公益捐献要保障完全自愿的原则,赔偿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变相强制捐赠之虞; ( 2) 愿望的道德只能提倡,而不应作为法律规制的对象;( 3) 要留住潜在的捐献者,捐赠制度存在下去才能使更多人受益。作为一种制度上可行的设计,法律可以规定,因反悔造成的受益人直接损失或可能的精神损失由红十字会等负责捐献流程的公益机构来补偿,而不是由捐赠者( 拒捐者) 以法律责任的形式来承担。这一措施也有其他的制度可以参考,在见义勇为的过当行为中,因不当造成其他人损失的,根据过错程度由相关基金会承担部分或全部的赔偿责任。
三、悔捐行为的风险防范
上文讨论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之关系一方面是要确立一个合理的义务标尺,确定法律上的行为标准与裁判依据; 另一方面是要看到愿望的道德与法律的间接关系,采取措施降低人的非理性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对于践行捐献的允诺来说,其保障力量不仅仅来自于信守有诺必践的道德与法律准则,更来自于成为一个道德上卓越的人的内在驱动力,这主要依靠捐献人内在道德良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实践自己允诺的内在道德力量。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这对人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才成为愿望的道德。对于捐献行为来说,除了探究相关义务的复杂性质,还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即这种善行的脆弱性,以及这种脆弱性所根源的一些人性事实,这些都是法律必须要面对并要着力预防和事后解决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其在法律上设计一些精巧的责任承担问题,不如去采取切实有效的制度性措施降低人的非理性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这似乎对于受益人、对于整个捐献制度的存在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是降低居高不下的悔捐率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措施。
( 一) 关于捐献行为性质的另一种认识: 法律要直面的人性事实
只规定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或应当能够做到的行为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之一,对于过高的行为要求只能由道德来提倡并给予荣誉上的嘉奖,而不能由法律来直接或间接强制执行,这也是我们认识法律现象和制定法律规则的客观基础。因为对于人的行为我们面临如下两个直接的人性事实,Hart 称之为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内容( The Mini-mum Content of Natural Law) ,这些自然事实与法律和道德规则之间具有一些特有的理性联系。虽然 Hart 都是从规则的必要性角度进行解读的,但我们同样可以就同一自然事实进行反向解读。
第一,人所具有的只是有限的利他主义( limit-ed altruism) 和有限的理性。利他主义几乎是伦理学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利他主义’意味着,不是‘因责任的缘故对其他人行善’,而是‘因行为自身的缘故而对其他人行善’或‘为了对他人行善而行善’”。因此利他主义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促进其福利,与自我利益的利己主义相对。虽然道德准则普遍提倡利他主义,但是人的利他主义的范围是有限的,如果存在普遍的利他主义则规则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所以,一方面需要规则来限制人的损人利己和侵犯的倾向,但另一方面规则也不能强制人成为完全的利他主义者。
第二,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 limited 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 of will) 。这是一个具有双面性的人性事实,我们同样可以进行两方面的解读。一方面,对于人身、财产和允诺规则的尊重需要一些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力量和善良的动机来服从规则。如果没有一定的“制裁”措施,自愿服从的人就会牺牲给那些不服从的人,因此“理性所要求的是在一个强制体系中的自愿合作( voluntary co-opera-tion in a coercive system) ”。
另一方面,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表明人存在意志薄弱( weakness ofwill) 的问题,人并非总是按照自己的较佳判断来行动。这几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尽管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 “一个人要是既了解又相信有另一个可能的行动过程比他现在所遵循的更好,他就不会继续目前的过程”。
捐献允诺之义务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还签有正式的捐献同意书和允诺书,不能说在这一时刻捐献人还没有形成较佳的判断,但是悔捐却是大多数人的行为。
综合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有限的利他主义和有限的意志力都是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统一在一个行为上的客观人性基础,即,既需要规则的存在,又不能强制执行过高的道德要求。当法律( 或道德) 面对人的普遍的有限利他主义和有限意志力时,要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来确定义务的标尺与责任的范围,对人的侵犯的倾向和对服从规则的强制都要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 二) 法律制度的完善途径
讨论客观人性基础是要表明,拒捐行为本质上源于人的意志软弱这样一个人性事实的存在。
承认这一事实,更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各种非理性行为、意志软弱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并使得人们把那些即使是有限的利他主义也要发挥出来。除了转化赔偿的主体,在法律上更应当做的———而且也能够做到的———是从各个方面去加强捐献人履行自己行动的意志力。
意志( will) 指的是“人类意欲某物、选择并决定行动过程并根据其选择或决定来采取行动的能力”,它既包括认知的要素( cognitive elements) ,也包括意动的要素( conative elements) 。意志与理性的一致是一种美德,没有遵循理性则是意志薄弱。在法律上或者实践上所应当做的就是加强认知的要素和意动的要素的充分实现:
第一,建立专业的捐赠制度,完善相关流程,回归公益本身。不专业的捐赠制度更是在变相杀人,尤其在宣传和稳定志愿者方面,要使捐献行为与任何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脱钩,避免物质的诱惑和假大空的思想工作,这些都会导致捐赠意愿的不稳定,只有纯粹的公益性才能留住坚定的志愿者。建立完善和专业的捐赠制度是我国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领域亟需要完成的一件工作,制度建设对于这项事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不能只凭忽悠的水平和志愿者的一时冲动。
第二,充分的知情同意。要以制度化的措施保障捐献者能够了解并理解所有的信息,使之经过充分的、理性的反思平衡之后做出选择,包括与亲属、朋友的充分交流。这样做是为了确保选择的稳定性,否则出现反复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要把人设想为能够具有一定利他主义倾向的道德人,具有理性的反思能力以及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行动的道德责任感。其中的关键是要披露所有的信息并使志愿者知情同意,这里有一个可以借鉴的实例。美国国家骨髓捐赠计划在 2014 年 5 月 1 日生效的最新一版中规定,预期的骨髓或机采捐赠者将至少被告知如下信息: ( 1) 捐献流程及其与捐献者相关的风险; ( 2) 受捐者的移植过程; ( 3) 志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退出的权利,但在捐献不能完成而使得受捐者处于丧失生命的极端危险情况下,不能拒绝捐献; ( 4) 他/她也许被要求为同一受捐者提供其他细胞治疗产品的可能性。
第三,完善充分、持续、制度化和人性化的关怀和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志愿者的意愿,增加捐献的成功率和可能性。毕竟这一类公益行为要达到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靠捐赠者履行允诺的内在驱动力,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拒捐的损害赔偿上。以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移植中心为例,义工组织细致周到的服务和追踪是建立信任的重要途径。沟通细节在于动员已捐赠者分享捐赠经验,在捐赠的每一个环节都反复确认捐赠者的意向并明确告知其有权拒绝,捐赠者的任何请求都会有专人解说。
第四,为避免最坏的结果,在实践上应当准备多套移植方案,以防拒捐行为可能导致的不可逆后果。在治疗实践上也基本是这样做的,即所有的捐献渠道都堵死之后,一般由直系亲属来捐赠,尽管这样做的成功率可能有所降低。但是在法律上所能做到的也只有如此,它无法预知最后的结果,也无法消除运气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结语
绝对自愿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捐献人“有权”———尽管这在道德上要受到否定的评价———随时( 即使是最后阶段) 违背自己的诺言而置受益人于危险境地,对这一行为既不能强制执行,也不适宜课以直接的赔偿责任。法律要直面这一现实并承受相应的代价,因为这是法律自身无法解决的。虽然上引美国的最新规定表明,志愿者在受捐者处于丧失生命的极端危险情况下不能拒绝捐献,但是这个规定只是在用更为严厉的措辞来表达一种强烈的主张而已,并非要强制履行。因此,最好把拒捐的可能性作为常规医疗风险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认识,因为这是一个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人性上都必须面对的事实,不能预见且无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在法律上以制度化的方式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降低悔捐的几率,相比于对承担责任的范围和方式的精雕细琢,这也许是法律更应当做、而且也能够做好的。
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简称新《商标法》)自201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简化了注册程序、加入声音商标等诸多亮点在此不过多赘述,笔者仅将视角落于新《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述关于商品及商标相同或近似的...
我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领域之立法目的是一致的,即保护合法的物权关系,促进形成和谐住宅小区,但在一些具体规定中,四地立法亦存在一些差异。另外,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毕竟是制定法的产物,要掌握其原理,有必要厘清四地关于...
一、我国新《消法》施行前有关明星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定2014年2月妈先生购买xx鱼油软胶囊并一直服用,冯先生于五月份将北京百姓xx大药房有限公司及xx产品代言人以虚假宣传为由告上法庭.这是在新《消法》施行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例明星涉嫌虚假广告宣传的案件....
2013年一起骨髓捐献者临阵反悔,白血病大学生生命告急的事件经微博传播得到了社会的多方关注。22岁的吴某不幸患上了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在与中华骨髓库中的两例骨髓采样配型成功后吴某摧毁了自身免疫造血系统,为骨髓移植手术做好了准备,不想此时两位捐献者竟都...
《民法总则》强调“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同时也十分重视尊重被监护人的意志。...
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采用专章的形式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自此,医疗损害责任的认定统一以《侵权责任法》为准,2002年通过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侵权责任法》规定不一致的,以后者为准,这既确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也改善了之前...
立法者在接下来的民法典编撰过程中应采取合理的立法方式为将相应商事规范分离出法典,从而让司法实践者,甚至让广大民众能更好地区分其与相应民事规范的区别。...
一、商品房预售及其法律规制概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由此可知,商品房销售可分为商品房现售与商品房预售两种方式。在商品房预售中,合同订立之时,标...
国际组织和众多国家 (地区) 纷纷制定法律加以应对, 其中个人信息的合法收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是指抵押人在抵押权存续期间未经抵押权人的同意,将抵押财产以买卖、赠与、互易等方式转让给第三人的处分行为。传统民法认为,抵押人有权就其已设立抵押权的财产处分给第三人,原抵押权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我国立法对于抵押人的该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