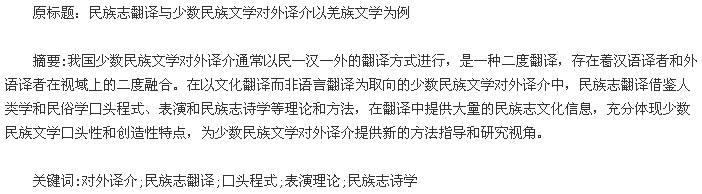
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指的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外国语,如英语等,它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略有差异,后者一范围更广,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汉译以及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研究,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相对于汉民族文化典籍和文学经典的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这导致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研究也缺乏应有的关注。长期以来,懂民族语言和外语的双语人才医乏。在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译者一直接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外语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的翻译还是先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再将汉语翻译成外语,即民一汉-外的翻译过程。这实际上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分为了两个部分,首先是懂民汉语言的译者一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然后再由懂汉外语言的译者一将汉语本翻译成外语。通常这两部分译者一分属于中文和外文两个领域,由于各自的关注点和目的不同,两个领域的译者一也甚少交流,客观上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被隔离成两个阶段。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实际上是一种二度翻译,也是汉语译者一和外语译者一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而这种二度翻译因民译汉和汉译外两个环节互不相涉而显得相互脱节。在这种情形下,外语译本如何能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意义,减少汉语文本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归化翻译”所带来的影响就成为译者一和翻译研究者一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少数民族文学广泛存在于民间,同一部作品有多种版本存在,且不断变化和发展,翻译中的原文本很难确定;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也使得意义的删减和增添成为常态。传统和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学通常是以口头化形态的形式而存在,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民译汉还是汉译外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意义的流失或增加,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由于其二度翻译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目的是,在外语译本中保留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特点和艺术审美特征,即少数民族文学有别于汉语文学和外国文学异质的东西,向外国读者一展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独特的魅力。如何在外语翻译时一和少数民族文学“直接见面”,仅仅延续民一汉一外的语言路径显然是不行的,需要我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有一个新的思考,即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不仅仅是民一汉一外之间的语言转换,而且是一种将少数民族独特优美的文学审美和文化意蕴传达再现给外国文化的文化翻译。在这种文化翻译中,是沿用传统的以忠实和对等为取向的文学文本翻译策略,还是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学的产生语境、性质特征和接受形式,从一种跨学科和他学科的视角去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并确定其相应的翻译策略,这是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所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将人类学和民俗学领域中的民族志翻译,以及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相关理论应用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研究中,将会给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带来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一、民族志翻译与表现他族文化民族志翻译源于民族志的实践。在文化人类学中,民族志的撰写是文化表述的重要方式,包含着民族志学者一对待他族文化、再现文化他者一的立场和方法。民族志的跨文化特性决定着民族志实践就是一个对他族文化阐释的过程,或称翻译的过程。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一Pritchard)在1951年的一次报告中,把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任务描述为“文化翻译’,1973年,另一位人类学家利奇( Edmund Leach)也提出,他所从事学科的“根本问题是翻译问题”,并得出“社会人类学家从事的是创立文化语言翻译的方法学”的结论。民族志的实践涉及对他族语言的转写和翻译,他族语言的形式通常是口语的,所以民族志翻译的过程是从口语到笔头,即将他族口头语言文本化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语符之间的转换仍然是民族志实践的一个基本任务。这一点和我们所熟知的翻译,即文学或非文学的翻译并无不同,语言对比和差异分析是这个层面上翻译的主要土作。但民族志翻译的内容却不仅限于此,民族志翻译的根本任务还要去表现他族文化。所以,民族志翻译的另一层意义和任务是将整个他族文化作为文本进行翻译以表现他族文化,在这个层面上的民族志翻译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原文本存在。民族志翻译基于他族语言文本,又远远超越他族语言文本,其阐释、修辞和写作的特点远远大于忠实于原文和等效于原文意义的翻译标准。民族志翻译赋子了翻译者一很大的权利,有时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原文本的对他族文化的理解与书写;但同时一也给子了翻译者一很大的伦理责任,即译者一的职业操守和译者一通过翻译所表现出的对他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与翻译学领域所研究的从书面文本到书面文本不同,民族志翻译的对象主要是活形态的口头文本,即在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高度地方化的特定口头文本,如史诗、歌谣、祭祀文、布道词等具有强烈文化色彩的口头文本。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广泛的口头文学特性,其特有的动态性、即时-性、语境化和地方性都使得口头文学的对外译介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书面文本的翻译。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固定在民一汉一外的语言翻译模式上,除了语言障碍而不得己而为之以外,这也反映了我们习惯于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汉民族主流文学中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忽略了不同民族文学所拥有的审美特性和族群文化异质性。少数民族语言的口头文本,甚至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的美学取向和文化诉求,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解决的只是语符转换的问题。将翻译置于源语和译语双重文化的语境下,将文化而非语言作为翻译单位,并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这是民族志文化番羽译观的主要内容。
如何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美国学者-本德尔(Mark Bender)认为有三种方式。一是基于第二种语言的翻译,如前面所提到的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然后再将汉语翻译成外语,其中汉语就成为第二种语言。这种翻译着重语言层面上的转换,缺乏源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相关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在第一种方式的基础上,附加上大量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信息,包括口头文学讲述者-的信息和场景信息,以及在第二语言文本中提供相对照的原文本,这为将第二语言翻译成外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信息。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外语,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民族志翻译方式,可以最直接地体现所要翻译和表现的少数民族文化,但这种翻译的操作性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很难实现。现实且具操作性的方式是第二种翻译方式,这要求汉语译者一和外语译者一之间的通力合作,汉语译者一在汉语文本中尽可能地提供口头文本的历史社会信息,讲述人的在场表演信息,以及提供原始记录转写文本等丰富的民族志资料,使得外语翻译者一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对于外语译者一来讲,需要有一种“介入”的积极态度,即采用民族志的田野土作方法,如参与观察、细读、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再阐释(rinterpretation)等等,对文本及文本之外的材料进行仔细梳理,并通过与汉语译者一的合作,将民一汉一外三种语言贯穿起来,打破语言的隔阂,跨越语言的界限,将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生动地呈现在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化面前。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国内最早开始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成英语。1957年,戴乃迭翻译并出版了云南撒尼族叙事长诗《阿诗玛》( Ashi-ma) X37;1962年,戴乃迭又同杨宪益一起将壮族歌舞剧(刘三姐) (Third Sister Liu)翻译成英语出版。
这两本译著对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本译著的前言中,两位译者一都表示英译本是基于当地文化局和歌舞团收集、整理的汉语本而译成的。将汉语本与英译本两相比较后发现,在汉语本中己经缺失了《阿诗玛》和《刘三姐》作为撒尼族和壮族的民族诗歌所具有的大量的民族志信息。对于英译者一而言,拘泥于语言层面上的翻译也就在所难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也说明在少数民族对外译介中,采取民族志翻译的观念和策略所具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就翻译策略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宜更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具体而言,可更多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深度翻译方式。这样既能满足目标语读者一对异域文化的阅读期待,又能使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与艺术之美得以表现。从跨文化交际学的意义来讲,也可以使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得以彰显,使它们的文化身份诉求得以传达。民族志翻译特别强调翻译具有表现他族文化的功能,强调将他族文化作为文本来细读和阐释的必要性。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是一个具体的民族志实践过程,少数民族文学的译者一首先应是一个民族志学者一,需要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尊重文化多儿的情怀以及具有文化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二、程式、表演、民族志诗学与羌族文学对外译介2008年5月的汉川大地震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将羌民族推显在世界面前。羌族所居住的阿坝、平武和北川等地遭受重创,其中北川羌族民族自治县,中国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更是遭受灭顶之灾,羌族同胞损失惨重,羌族文化哑待抢救。世界人民为为、方这样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所遭受的厄运扼腕叹息,但同时一也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中,羌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对这样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重振,对羌族文化的认知以及羌族文化身份的确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一样,羌族也以其丰富的口头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大家庭的一员。羌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恶劣的环境,生存的挑战不断洗礼着这个民族,使传统羌族文学,如羌族史诗充满了沧桑和厚重感。羌族口头文学分为古代神话史诗和民间歌谣两大部分,前者-以《羌戈大战》和《木姐珠和斗安珠》为代表,后者一则散落在民间,和羌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联系,不计其数。
将羌族口头文学译介到国外,理解是译介土作的基础“口头诗歌是与文人诗歌有着极大的差异的作品形式,不可以简单套用研究文人书面作品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口头创作、口头传播的作品。由美国民俗学家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Lord)所创立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认为,口头文学由于其口耳相传的特点,其内在的文学语言结构形式具有稳定性,以此保证在千百年能长期的流传;口传文学能保持其在程式、主题和叙事方式上的相对稳定性。深入文本之中,梳理文本之中具有规律性的特征,既关注口头文本普遍性的特征,如中西方史诗中的主题、叙事演进的相似性,也关注某一特定民族独有的表述程式,后者一往往成为理解和表现这一特定民族独有的审美和文化特质的关键。
以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为佰生《羌戈大战》描述的是羌族的祖先从西部迁徙到眠江上游定居的历史,由长途跋涉,遭遇戈兵,与戈大战,神灵暗助,最终获胜,兴建家园,繁衍后代,民族延续等部分组成。
《羌戈大战》篇幅不长,但具有西方英雄史诗的雏形,其英雄落难,恶魔肆虐,神明高照,悲喜结局等主题和叙事模式与西方史诗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另一首羌族史诗《木姐珠与斗安珠》则描写了一对彼此忠贞的男女青年,奋力抗争,冲破阻拦,终成眷属的故事。史诗由倔强公主,牧羊少年,龙池巧遇,赠发定情,大胆求婚,三破难题,火后余生,再次求婚,险遭毒计和创造幸福等部分组成。同样,《木姐珠与斗安珠》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主题以及叙事顺序,与西方史诗形态的爱情抒情长诗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具有相似性。口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高度程式化的观点对羌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尤为重要,它从理论上解决了羌族文学的可译性问题,以及在另外一个相距甚远的文化中被接受的可能性问题。
同样,口头程式理论还为我们提供了在羌族口头文学中发现其固有的,带有区别性特征的结构程式。羌族文化中保留着不少淳朴厚重的古代遗风,羌族人能歌善舞,民歌在羌族民间有着巨大影响,传承着不少优秀作品。羌族的男女老幼都会唱民歌,其民歌有山歌、情歌、酒歌、风俗歌、劳动歌、时政歌等等。羌族民歌的艺术特色包括唱词结构和调式独特。羌族民歌歌词多为4或7个音节一句,类似于汉语中的四言诗与七言诗。采用调式多为羽、徽调式为主,多用五声、六声音节,偶尔也用四音音列或七声音阶的。羌族民歌语言丰富,通过巧妙运用,表达含蓄、深沉、生动、形象、幽默、风趣、朴素、华丽、抒情、伤感等情绪,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羌族民歌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比兴、烘托、委婉、白描、铺陈等都是常用的修辞方法。如使用比兴的手法:
“一颗树儿九枝娅,又结葡萄又结瓜。又结南山更豆子,又结四川牡丹花。”此民歌用树来比喻人家,言此家人多,用南山更豆子和四川牡丹花来言此家人好。
“远看贤妹身穿花,于人看到九人夸,观音看到J陀下马,和尚看到不出家”。此民歌赞姑娘之美,但通篇只用了“看”字,便把姑娘之美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帕里一洛德口头程式理论提供了一个文本分析方法。羌族文学,尤其是羌族史诗,在主题、程式、叙事等方面,都有着与世界上其它民族文学共享的结构性特征。这说明文学是一门人学,世同此心,心同此理,羌族文学与其它民族文学共享着许多相通的为、西,这些相通的特征为羌族口头文学的翻译,在异域文化中被理解和接受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口传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是在具体的民族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其独有的语言艺术表达方式成为共性中的个性,普遍性中的差异性。所以,通过具体的田野研究方法,发现羌族文学的差异性特征,这对羌族文学的对外译介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羌族文学和文化区别于其它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异质部分,也是最具有羌族独特民族性的部分。
当代美国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对外译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表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鲍曼(Richard Bau-man)认为,表演是一种言说的方式,口头艺术就是表演。表演理论所关注的是正在发生中、正在活动中的民间口头艺术文本,所研究的是它们的交流形式和交流过程。表演理论改变了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从文本到文本,研究抽象的、往往被剥离了语境关系的口头艺术文本的做法,将文本还原给语境,以表演为中心,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对于译者一而言,口头文学的讲述过程应该是一个表演的过程,作为演员的讲述者一在演出当下的即时一发挥,表演场景等非语言因素,都应被译者一纳入对于口头文学的整体理解之中。而后,当译者一将他所理解和阐释的口头文学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的时一候,译者一的翻译行为也是一种表演。在羌族古老文化的传承中,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释比。释比,汉族称为端公,羌族又称为许、比、释古、释比等。释比是古老的羌民族遗留至今的一大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现象。释比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一。羌族的许多民俗能够存留到今天,除了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诸多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释比对释比经典的讲述和演绎。以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为例,《羌戈大战》既是羌族的民族史诗,也是一部著名的释比经典。释比在(姜戈大战》的程式结构下,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观众,口头演绎着这部经典。不同地方的释比对《羌戈大战》的不同演绎也会形成不同的口头版本。释比在口头讲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语境所表现出来的即时一性和突出性来表示口头文学的讲述,其讲述具有非常突出的表演性质,讲述者一所显示的对口头文本的操控和创造意图非常明显,但同时一又必须遵守着口头文学讲述中的规定模式。当译者一要将羌族文学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一,他就成了目标语和目标文化眼中的“释比”。翻译成为一种表演,表示任何翻译都是一定场合和时一间的产物,都是译者一的创造性成果。在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尤其讲究“译创”,即“翻译加创作”,这是由于口头文学原文本的不确定性和译者一在翻译过程的创造性所决定的。传统译论中的“忠实于原文”在口头文学的翻译中基本不适用,译者同时也作为一名表演者,在将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学译介到另一个文化时,译者会根据翻译的目的,源语文化的规范,译语文化的期待等等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同时,译者尤其注意口头文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的讲述语境,以及讲述人和观众等等非文本的因素,尽可能地表现出口头文学所产生的时一代文化背景。
如何在翻译中去表现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民族志诗学所开展的翻译实验同样给我们带来启示。民族志诗学(Ethnopoet-1CS)和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一样,令门研究少数民族口头文本,代表人物有鲁森伯格(JeromeRothenherg)和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民族志诗学学者一认为,部落口头艺术具有其独特的语言和审美特征,以及其独有的讲述表演方式。部落口头艺术表演中的每一个声响,每一个修辞形式,都具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需要我们去体验它们,尊重它们,并打破惯常的书写方式,利用多种手段,将它们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在不同文化的人们面前。
民族志诗学的学者一们在研究美国印第安部落的口头文本被翻译成英语的情况后,对以往的翻译加以否定,认为以往的翻译泯灭掉了印第安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语言特征和审美特征。他们希望通过深入部落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族志调查方式,对部落口头文本重新进行转写和翻译;通过具体的、具备操作性的翻译模式,开展对部落口头文本的翻译实验,以张显部落口头文本中独特、本质的艺术魅力。
部落口头文本的讲述是一个表演的过程,语言只是构成表演诸多要素中的一种。翻译是要完整地再现这种表演的过程(实际上翻译也是一种表演),一切与表演相关的要素都要尽可能地被再现出来。其中,口头文本诵读、吟唱所用的声音的大小、高低、急速、缓慢、停顿、轻重等等,都需要再现出来。再现的方式可以采取打破通常的文字印刷方式,通过大小写、黑体字、上下划线、连线、破折线、断行等再现上述的表演要素,以唤起我们阅读文本时一的声响感。
翻译文本是一个综合性的立体文本,印刷符号的视觉冲击力唤起我们在阅读时一的吟唱,在吟唱中体验到的是部落诗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及所传达出的文化魅力。
羌族情歌在实际演唱时一,每首歌几乎都加有语气词,如啊、啦、喂、呢、咳、哟、哦"p},-"A}、嗬、娓等词。如《耕地歌》中主要表现劳作的艰辛和对牛的怜悯:。
瓦依拿啦,我年轻的偏牛俩,你俩跑得多快啊,象插翅腾飞呀。转弯了,我的偏牛俩,你俩多辛苦啊,我也心痛你们,看到地头边啊,已快耕拢了。
又如《割麦歌》中表现人们丰收时一欢乐,喜悦的心情:
呀呀拉呀米子,这块地的麦子长得好,也很饱米。快收割吧,快收割吧,都象这块地,收成该多好。
还如《挖窝子歌》表现挖窝子时一人们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的情形:
挖啊挖,快快挖,我已经挖起走了,你赶快跟起来。
如何将羌族民歌中这些具有生命力的语气词、重复词在译文中反映出来,是采取异化的策略,努力在译文中再现少数民族民歌的声响之美,还是采取一种归化的策略将其消隐在译文中,通过译文的诗歌步韵来表现,以达到功能对等的效果,这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译者一而言需要做个选择。译者-清楚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是一种民族志翻译,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翻译,这一点非常重要。民族志诗学学者一所做的翻译实验,例如改变译文的文字印刷方式来表现口头文本所独有的音响特征在实际的翻译中难以行得通,但我们可以采取音译的方式将这些辅助词保留在译文中,并通过注释的方式解释说明这些辅助词的作用,这样在译文中这些辅助词将成为羌族民歌的标志。作为民歌这种具有特别民族性和文化性的文学类型,异化的翻译策略更能满足译入语文化渴望了解一个异域文化的期待。
三、结语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学从被“忽视”和“遮掩”到“显现”和“表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族群身份和文化身份被确认和被尊重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载体从“母语书写”到“汉语书写”,再到up卜语翻译”,正进入一个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的发展空间。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翻译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民族志翻译通过强调在翻译中采取直译,并尽可能多地提供民族志背景信息便于译语读者一理解,在跨越差异的同时一更注重展示差异,这一点特别适合少数民族文化差异性的表达诉求和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文本的传承需要,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具有特别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峡}马克·本德尔著,吴珊译,巴莫曲比模审校.略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翻译[M].民族文学研究,2005 (2).
[3]Gladys Yang.A.shima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7.
[4]Yang llsien一Yi and Gladys Yang. Third Sister Liu山].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2.
[5]迈克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蒲新竹,李娜.羌族民歌的历史与现状[M].教育教学论坛,2010 (8).
[7]杨碧嫦,陈远贵.浅析羌族民歌的艺术特色[M].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21(1).
[8]Kicbard Bauman.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M].1'bilip Aus-lander.feCrnaarrce:Critical Concepts irr Literary arrd Cultural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3.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各类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时代的到来。史传文学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成果最着的一个题材领域,这方面的作品数量多,取得的成就也高,更是出现了像《尘埃落...
一、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情怀概述民族情怀是在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特征,少数民族情怀是少数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民族自豪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情怀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文学家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
一、文学人类学的视野: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互动如果要谈文学人类学对重新审视和建构少数民族文学观的作用,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渊源。文学人类学的产生离不开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融合互动。作为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转型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全球化时代和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入研究,以混杂性理论作为核心命题的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得以凸显。混杂性一语,赛义德探讨后殖民时代文化主体身份时分析: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所有的都是混合的,多样的...
文学理论是人类文学活动规律的总结,到目前,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是都能够阐释说明所有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理论是普世、也是普适的。但是,理论在运用时总是表明或流露出使用者主体选择某一理论的动机,不管是出于社会性的功利要求,还...
引言根据文化多样性观点,每种文化都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因此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保持文化本身的面貌极为重要,特别是处于文化弱势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其有限的跨语言传播和推广中更需要保持民族文化真实的模样,以此来使少数民族文化独特而珍贵的价值得以...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独特的少数民族气息和女性特征,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地区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下,将写作要点放在对传统社会男权文化的反思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层面,积极倡导将女性视作时代的主人、社会的主人甚至是自己的主人。...
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58年,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开始真正纳入研究视野。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及其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运用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当然这种批评实...
引言当代汉族作家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促进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而且向我们展示了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人情。比如王蒙在新疆学习生活了16年,向我们展示了伊犁草原纯朴的民族风情。陕西作家红柯在西域流浪10年...
《布洛陀经诗》作为壮族的创世史诗与宗教文学,是一部传唱不衰的卷轶浩繁的巨着。虽然《布洛陀经诗》在发展中也逐渐以文字的形式以保存下来,但口头传唱仍然是经诗在民间得以存活与传承的主要方式。《布洛陀经诗》内容丰富、规模与篇幅都较大,为何却能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