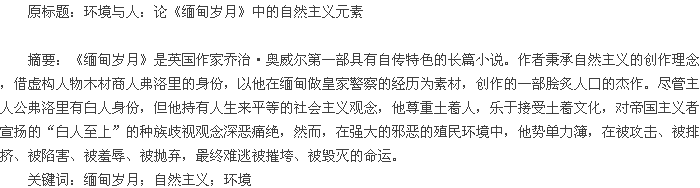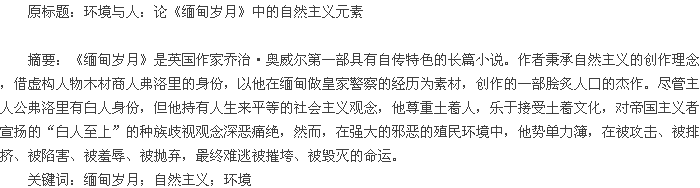
1 引言
《缅甸岁月》(BurmeseDays,1934)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继吉卜林(RudyardKipling,1865-1936)的《吉姆》(Kim,1901) 和 福 斯 特 (E. M. Forster,(1879-1970) 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之后,以英印殖民地为背景的上乘之作。
1922年,伊顿公学毕业的奥威尔,怀着为帝国效劳的梦想,前往印度殖民地做皇家警察,1927 年,在目睹英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犯下的种种罪行之后,他愤然辞掉了待遇优厚的工作,立志用写作揭露谎言,寻求真相。
奥威尔在《缅甸岁月》借木材商人弗洛里的身份,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以在缅甸的经历和体验为素材,创作脍炙人口的佳作。国内研究者多从后殖民批判视角或历史和政治视角解读该作品;但是,鉴于奥威尔在后来回忆他写《缅甸岁月》的初衷时说:“我当时想要撰写宏大的自然主义小说,带有悲惨的结局。”本文回归奥威尔创作本意,试图用自然主义视角走近文本。
文学自然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作家左拉倡导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并逐渐扩展到欧洲以及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自然主义是对浪漫主义公开的挑战和反击,它继承了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受进化论、遗传学、决定论、和实践论等科学思想的影响,主张小说家“用科学家在实验室做科学实验的方式,制定实验内容,以人为研究对象,观察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发展和变化。”
就人物塑造而言,自然主义文学强调人的生物属性,认为人并非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而是与野兽别无二致:他无法控制自己暴虐的冲动,受本能和情欲驱使,被遗传和环境制约;毁灭是他的宿命,偶然的因素也会导致他的失败。他本人的毁灭也会如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给与他相关的人带来厄运。
正如左拉所言:“人是能思想的动物,是大自然组成部分,处于它所生长和生活的土壤的种种影响之下,这就是何以某种气候、某个国家,某个环境,某种生活条件,往往都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 欧洲人俱乐部
英国于十九世纪先后三次发动对缅甸的侵略战争,逐步吞并了缅甸,建立了英印殖民地(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缅甸在内地区),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英帝国在国内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文化传播等渠道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和“白人至上”等帝国主义思想。用殖民话语对白人潜移默化:对被殖民者“妖魔化”- 有色人种总是无知、野蛮、肮脏、愚昧、落后的,是“白人的负担”,期待白人的拯救,对殖民地的统治是白人的责任 - 欧洲殖民者认为他们的优越感是理所当然地的,并期待被殖民者将殖民话语内在化,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被奴役的命运。
小说《缅甸岁月》的背景是缅甸。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英帝国殖民统治已经日薄西山的缅甸,故事发生地—奥克拉达镇是上缅甸的偏僻的小镇,全仅有七个欧洲人,却统治着四千居民 - 除了大多数缅甸人以外,还包括两百个印度人、几十个中国人和两个欧亚混血儿。镇上驻扎宪兵队,设立法庭、监狱、教堂、学校、医院等机构,英帝国除了军事占领和掠夺资源,还对当地人奴性和愚民教化。白人们虽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土着人打交道,但在娱乐和社交方面必须呆在一个小圈子里,即欧洲人俱乐部。俱乐部文化起源于英国,传统的绅士俱乐部实行封闭管理,严格限制会员人数,以体现其不同寻常,因此,它不仅仅是社交和娱乐场所,更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在英属印度殖民地,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更是白人的专属权利,更能体现白人与土着居民之间的身份区别。
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印度的每一个城镇,欧洲人俱乐部都是其精神堡垒,是不列颠权力的真实所在,是土着官员和百万富翁徒然向往的极乐世界。”凯奥克拉达俱乐部成员严格遵守“白人绅士准则”,具体包括以下五条:1、维护我们的声誉;2、手段要强硬(不必外柔内刚);3、我们白人必须团结在一起;4、他们会得寸进尺;5、我们要保持团队精神。
这五条规则反映了殖民统治者的殖民话语,其核心是强调殖民者要极力维护欧洲中心主义的权威,一旦面临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就会团结一心,一致对外,对当地人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走一个。埃利斯是典型的白人至上的沙文主义者,他“痛恨东方人—简直可以说是厌恶至极,仿佛他们是什么邪恶和不洁的东西似的。谁要是对东方人表现出一点儿友善,他都感觉是可怕的变态。”他讲话中带有“恶狠狠的伦敦东区的口音”,埃利斯满口脏话,出言不逊,在缅甸人面前,更是一副白人老爷的派头,横蛮霸道,作威作福。作者以第三者的口吻评价道:“常常有那么一些英国人,决不该让他们踏上东方的土地,不幸的是,他就是其中一员。”
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埃利斯问管家还剩多少冰块,管家用英语回答:“我发现如今保持冰块低温可真够困难的。(Ifinditquitedifficulttokeepicecoolnow)”他立刻恼羞成怒,让他生气的并非是降温的冰块短缺,而是管家说的英语太标准:“你他妈的少这么讲话—还什么‘我发现真够困难的!’难道你刚才吞了一本字典不成?‘对不起,主人,冰块冷不了!(Please,master!Can’tkeepingicecool’这才是你应该说的话。哪个家伙英语开始讲得太好了,我们就得让他走人,我可受不了会讲英语的佣人。”。他高傲狂妄的作态,撕破了英帝国在缅甸的推行以英语为主的殖民教育制度的虚伪面目:他们以救世主自居,宣扬给落后的东方带来先进的西方文明,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培养不过是能使用英语对英国人服务的奴仆。
正是长期的殖民教育潜移默化使被殖民人民忘记了屈辱,竭力以标准的英语讨好主人,然而,在英国人心目中,一口文法严谨、措辞高雅的“标准英语”(King’s English)代表良好的教养和显赫的地位,是白人老爷的专属权利,一旦土着人也变得同他们一样文雅而有教养,必将威胁到他们天然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同样的情形也体现对待宗教信仰方面。
小说中的欧洲人几乎没有一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甚至没有遵循基督教要求的每周去教堂做礼拜的教义,但他们将信仰基督教和在教堂做礼拜当做白人的专属权利。埃斯利在谈到教堂里六个礼拜举行的一次“圣会”时说:
“我就是哭着唱圣歌,就算是帮牧师了。但是我可受不了他妈的土着基督徒挤进咱们的教堂。一帮马德拉斯佣人和克伦人教师,还有那俩个黄肚皮,弗朗西斯和塞缪尔 - 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牧师上一回来这儿的时候,他们俩居然胆敢跑到前排跟白人坐在一起。
应该有人出来给牧师说说才。我们对在缅甸的传教士听之任之,真他妈傻到家了!居然去教那些集市上扫大街的,说他们跟咱们没有什么分别。‘抱歉,先生,我是跟主人一样的基督徒啊!’真他吗的厚颜无耻。”
当得知俱乐部不得不吸纳当地官员为新会员,他坚决反对,发誓:“(我)宁肯死在水沟里也不要看到这儿有个黑鬼;”并声称俱乐部是白人们行乐的地方,受不了“肚皮大、个头小的黑鬼隔着桥牌桌直往你脸上呼大蒜的臭气”。他煽动其他会员“:这个俱乐部不要土着!就是因为这样的小事我们一再地让步,我们已经毁了大英帝国。这个国家暴乱横行,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太手软。唯一有效的手段,是把他们当成臭泥。这可是个关键时刻,能得到威望,我们一点也不要放过。大家必须合起伙来,一起说:‘我们是主人,你们是臭要饭的 - 你们这些要饭的要安分守己。”当他听说一个白人会员被当地人所杀,他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在遇到一个学生面露不敬时,他用木棍向其中一位的眼睛砸去,导致学生一只眼睛失明,引起了当地人的骚乱。
3 “白人老爷”中的另类
木材商人弗洛里在俱乐部中是一个另类,他同情缅甸人,痛恨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因此,他成了埃利斯们的眼中钉。弗洛里小时候在英国接受正统教育,怀着对东方殖民世界生活的向往和对帝国事业的热忱,未满二十岁就来到印度缅甸的木材公司工作。一开始他过得如鱼得水:酗酒、打猎、招妓、纵欲,也很快“适应了缅甸的水土”,连“身体也跟着热带季节和上了拍。”:但 25 岁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从头到脚全是可怕的疮,“八年的东方生活,热病、孤独、酗酒,都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
他开始意识到缅甸生活使他堕落,渴望回到英国去过文明的生活。谁知在归途中,接替他工作的同伴突然暴病死亡,木材公司发电报要他返回。他受到当地人的热情迎接,他发现自己心头涌动着喜悦之情,十几年的生活已经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沾染着缅甸的泥土”,缅甸的景色也“比英国来得亲切;”曾经让他“无比痛恨的”缅甸“变成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他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而且是最深的根。”
于是,他走出封闭的俱乐部,与当地人接触,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艺术。他逐渐认识到俱乐部的白人成天炫耀西方文明,抱怨土着人野蛮,其实他们虚伪自私、腐化堕落、缺乏人性;也识破了从小接受的诸如土着人是“白人的负担”、英国人是“完美无缺的白人老爷”“、殖民地白人勤劳和能干”等谎言。在缅甸,所有工作都是本地下属官员做的,英国官员是地地道道的寄生虫。对于他效忠的大英帝国,他无比痛恨地称她是“年老的女性病人;”并揭露她的邪恶本质是“一种专制主义 - 仁慈到不必否认 - 但仍然是以偷窃为最终目的专制主义;”
缅甸殖民地是“一个令人窒息、使人愚昧的世界,这里的句话,每种思想都要受到审查……一旦每个白人都成为转动专制主义的齿轮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友谊便荡然无存。自由言论是不可想象的,这里有各种其他的自由。
你可以自由地成为醉鬼、懒鬼、胆小鬼,做诽谤和通奸的勾当,但你没有思考的自由。你对于任何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想法都是由‘白人绅士准则’左右。”在这种专制体制下,白人“一辈子生活在谎言中。”每当殖民者叫嚣“那些血腥的民族主义分子应该放在油锅里煮,”以及你的东方朋友被唤着“油腔滑调的小人”的时候,你不得不点头附和。这时,你会“点燃对你同胞的怒火,渴望当地人起来反抗,将帝国主义淹没在血泊里。”
弗洛里作为白人老爷的身份和内心叛逆的想法使他在俱乐部格格不入,也使他矛盾和痛苦,他“学会活在内在的、隐秘的生活,活在书本里,活在不可言传的内心世界里。”他向他唯一的朋友,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倾诉,然而,对于一把俱乐部会员资格看成是莫大殊荣的东方人来说,弗洛里的推心置腹的倾诉无疑是话不投机。殖民教育中毒很深的医生认为自己属于“低劣、堕落的种族,”那些“创建大英帝国的白人老爷”是“世上的精英”;大英帝国给缅甸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始终不渝的英国公正,以及英国统治下的永久和平。”
弗洛里讥讽说英国带给缅甸的是疾病、监狱、经济垄断和剥削。后来他遇到刚欧洲来的白人女孩伊丽莎白,立刻把她当成知己,并迫不及待地她吐露心声:“当我有足够的勇气,我会尝试不去做一名白人绅士。”。然而伊丽莎白欣赏的正是白人男人的冒险精神、征服欲望和男人气概,因此弗洛里在她那里屡屡碰壁,他们的关系的发展也跌宕起伏:每当弗洛里表现出白人男性的英雄气质,伊丽莎白就会对他无比崇拜,流露出柔情蜜意;一旦弗洛里做出有辱“白人老爷”身份的事,伊丽莎白就会对其冷若冰霜,形同陌路。
4 向环境屈服
置身于殖民环境,深受殖民思想的约束和影响,尽管弗洛里意识到殖民统治的罪恶和荒谬,但他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中,因为他自己“本人就是专制统治的产物,是个白人老爷,被一套牢不可破的禁忌束缚了手脚,捆得比和尚和野人还要紧。”
他对英帝国的专制统治的挑战也是有局限的。在是否支持他的医生朋友加入俱乐部时,他犹豫了,为了安全,他选择了“完全置身事外”,认为:“对于印度人,绝不能有什么忠诚和真正的友谊。感情,甚至喜爱,都不行……医生的确是个好人,但为了他就对抗整个白人老爷的传统 - 唉,不行,绝不行!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失去整个世界,这能有什么好处呢?”
麦克斯威尔打死了一个缅甸人,被死者的亲戚碎尸万段。为此,埃利斯盛怒之下,暴打面露不逊的缅甸学生,把一个儿童的眼睛刺瞎,引发当地人骚乱。弗洛里为了讨好伊丽莎白和俱乐部其他成员,冒险渡河,搬来救兵,化解了这场危机。在殖民地环境中,良心未泯的弗洛里时常处于殖民话语和反殖民话语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最后选择自杀也是其必然归宿。
参考文献:
[1]奥威尔·乔治.缅甸岁月[M].李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毕修勺 洪丕柱译. 西方文艺理论名着选编.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87-223.
[3]刘利民.试论英国殖民统治对缅甸教育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4):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