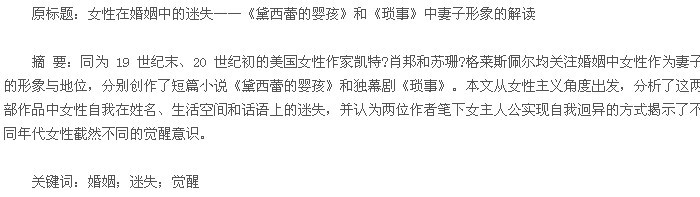
引言
1848 年至 1920 年期间,美国女权运动者们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并非‘天生的’,而是社会造成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该时代的女性作家开始探索女性的社会形象,揭示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凯特·肖邦就是其中的一位。其长篇小说《觉醒》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女权主义的力作’”,而其短篇小说《黛西蕾的婴孩》,堪与之媲美。
《黛西蕾的婴孩》主要讲述的是弃婴黛西蕾嫁给了地位显赫的阿尔芒后,生得一子。当儿子表现出黑人血统特征时,阿尔芒将原因归结于妻子。不堪忍受猜疑,黛西蕾抱着儿子投河自尽。阿尔芒最后得知,孩子肤色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的母亲有着黑人的血统。而 20 世纪初美国戏剧界代表人物苏珊·格莱斯佩尔,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坚强而独立,表现出一定的女性觉醒意识。1916 年发表的独幕剧《琐事》讲述了农场主约翰深夜被人勒死,其妻子米妮被认定为最大的嫌疑人。三位男性角色调查一无所获,而两位妻子却通过“琐事”看出了蹊跷。
同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美国女性作家凯特·肖邦和苏珊·格莱斯佩尔,通过对少数裔妇女黛西蕾和米妮相似人生的描写:婚姻中的从属地位和精神上的压抑,给她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一位最终走向了死亡,一位成为了杀夫罪犯。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大多从写作技巧、叙事手法、精神分析等方面对这两篇作品进行解读,并没有学者对这两篇同时期作品刻画的妻子形象加以对比研究。本文试图分析这两篇文章中女性自我在姓名、生活空间和话语上的迷失,以探究女性在婚姻中的迷失,并通过分析两位女主人公不同的结局,进一步探讨两位女作家不同的女性觉醒意识。
一、迷失在姓名之中
在《女性主义文体学》一书中,米尔斯指出,作品人物的命名对作品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名字不仅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也隐含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这两篇作品中,凯特·肖邦和苏珊·格莱斯佩尔都借助人名,尤其是借助女主人公的姓名,来讽刺本应该是幸福美满的婚姻,体现女性在婚姻中的迷失。
在《黛西蕾的婴孩》中,女主人公被命名为黛西蕾(Désirée)。在法语中,Désirée 的意思为“向往的,渴望的”。一方面,黛西蕾是追求者们眼中的“女神”,美丽优雅、温柔娴熟。另一方面,黛西蕾是弃婴,从小渴望被爱。当她嫁给阿尔芒·
奥比尼后,渴望在婚姻中得到爱。但这个曾在向她求婚时,对她不明身世毫不在乎,并认为能够给她“一个路易斯安娜最古老、最荣耀的姓氏”的丈夫,却在发现小孩呈黑人特征时,态度变得冷漠。
黛西蕾尝试着与丈夫沟通,但这种“渴望”始终没有被满足。虽然凯特·肖邦笔下的黛西蕾嫁给了奥比尼,但文章没有一处将其称为奥尔尼夫人。黛西蕾一直处于“渴望”被爱的状态。而这些“渴望”的未满足正是黛西蕾感到迷失的导火索,导致黛西蕾走向死亡。肖邦将黛西蕾婚后的住所命名为 L’Abri。L’Abri 的法语意思是“躲避处”。“躲避处”这一词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馨的地方。但事实上,“这房子的屋顶坡面陡峭,黑得像个蒙头大斗篷,一直伸到宽大的走廊外面”、“旁边生长着几棵硕大的深黑色橡树,枝叶繁茂,向外延展,树荫就像一片棺材布罩,盖在房子的上方”,就连年长的瓦尔蒙德太太“到了拉贝种植园,就跟每次一样,见到它便觉得毛骨悚然”。肖邦将这样一个阴森恐怖的场所称之为“躲避所”,实际上是对当时的婚姻进行讽刺。从女性的角度来看,阴森恐怖的“躲避所”,就像男权主义下的婚姻和家庭,使女性角色感到畏惧,象征着妇女在婚姻中的迷失。在《琐事》中,米妮·赖特(Minnie Wright)体现了作者对女性地位的思考。首先,“Minnie”,与“mini”同音,译为“微型的、袖珍的”,表明女性在婚姻、社会中的微不足道。在婚姻中,米妮·赖特是微不足道的“局外人”:丈夫约翰·赖特从不关心她,周边的朋友不探望她。正是这种在婚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导致了她们的迷失。其次,“Wright”是米妮嫁 给了 约翰· 赖 特 (John Wright)之 后的 姓氏 。
“Wright”与“right”同音,具有双关的意味。“right”可以理解为 “正确的”,表明米妮找到了一位“Mr.Right”(如意郎君)。但事实上,这位“如意郎君”却并非“如意”,在婚后对米妮实行压迫。禁锢着的米妮困在了婚姻的牢笼中,失去了原本的自我。
“right”还有“权利”之意。米妮嫁给了拥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丈夫,丧失了自我的权利,永远处于被支配、被压迫的地位。而在出嫁前,米妮是米妮·福斯特(Minnie Foster)。“foster”意为抱有(希望等),体现出米妮对于婚姻的渴望,对婚后生活充满希望。“foster”也可译为“寄养的”,这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妇女身份的思考,即未出嫁的妇女只是被寄养在家中,没有任何的自我身份;结婚后,妇女改随丈夫姓,妇女的身份由丈夫所赐予。因此,通过这三个具有双关意味的姓名,苏珊·格莱斯佩尔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一个对爱情充满希望,却在婚姻中被压迫、被禁锢的妇女形象。我们可以看出,两位女主人的姓名都反映出两位女主人公对于丈夫关爱的渴望,但这份关爱始终没有得到满足,婚姻给予她们的只有冷漠与压迫。
二、迷失在空间之内
女性主义认为空间就像语言一样,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建构。空间中隐含了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的定义,男性与公共的、经济的生产相联系,女性的空间则更多地局限在私人的、再生产的场所,形成了男性公共空间与女性私人空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两性空间的隔离。在这两篇作品中,两位作者通过对女主人公婚后活动空间的描写,反映出女性在婚姻中所受的压迫,并通过设计不同的“走出”空间的情节,打破女性被束缚的状态,解构父权社会中男女空间的隔离。
在《黛西蕾的婴孩》中,作者将婚前、婚后以及走向死亡时黛西蕾所处的空间设计的完全不同。
黛西蕾首次登场是“躺在瓦尔蒙德先生家门口大石柱后面的阴影里”;婚后的黛西蕾一直在拉贝种植园的房间里,要么“平躺在沙发床上”,要么“坐在自己的房里,无精打采地用手指捋着几绺丝绸般的棕色披肩长发”;而在文章结尾处,黛西蕾决定自杀,她穿过走廊,走下台阶,向着屋外的长沼湖走去。通过这三处场地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婚前,黛西蕾出现的场地是家门口,这属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交汇处,并没有与男性公共空间相隔离;“大石柱后面的阴影里”侧面反映出黛西蕾处于某种压制下。而婚后,黛西蕾的活动场所全在屋子里,黛西蕾此时已完全被束缚于私人领地,与男性公共空间完全隔离。为打破这种固有的僵局、隔离的状态,黛西蕾最终选择“出走”,走出家门,最终选择死亡。
而在《琐事》中,米妮·赖特的厨房是这场独幕剧的主要场景。米妮自婚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所的厨房干活。这就使米妮不仅被束缚在家中,而且是被局限在更为边缘、更为狭小和孤立的空间——厨房。米妮和丈夫虽在同一屋檐下,但并不在同一个横向平面内,体现出两性空间的隔离。而在这样一个物理空间中,作者把丈夫设定于在高高在上的二楼卧室中,象征着男性在婚姻中所具有的权利与优势,而米妮则处于家里的一角,仅做饭才会需使用的厨房,体现女性处于较为边缘的空间位置,表现出婚姻中的被压迫和被束缚。在整部剧中,彼得斯太太和黑尔太太所有的行动也只在厨房,而三位男性角色则在房屋内和房屋外的院子里到处走动,这也体现出男性对于空间的支配力和女性的边缘化。正是由于这种在空间资源分配上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导致在婚姻中,女性被困在她们的领地——卧室或厨房,一步一步迷失了原来的自我,并被男权的制度所压制。
在设计两位女主人公的命运时,两位作家是这样处理的:黛西蕾抱着其婴孩走出了那栋“庇护所”,走向了长沼湖。这就意味着黛西蕾走出了婚姻带来的压迫,走出了婚姻带来的迷失感。而米妮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被捕入狱。虽然被捕入狱,进入了现实社会真实的“牢笼”, 但米妮却从那个一直压抑她,令她窒息的婚姻“枷锁”中走了出来。
对两位女主人公空间活动的描写,体现出两位作家都对父权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有一定的认识。两位作家设计这样的“走出”情节,实际上是在解构男女空间的隔离,打破女性被私人领域束缚的状态,表达了女性要从不幸婚姻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
三、迷失在话语之上
女性主义者伊里加蕾也认为,“话语是有性别的。”相比之下,女性却没有一个“属于女性性别的语言。她们无法得到语言,只能重述‘男性’的再现体系,而这一体系侵害了她同自己以及其他女性的关系”。女性主义者们注意到了女性话语受到男性文化压制的现象,认为父权体制剥夺了女性表达欲望和思想的能力和权利。在这两篇作品中,男女角色的对话也反映出两性交流中的不平等,体现了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与压制。
在《黛西蕾的婴孩》中,黛西蕾发现小孩肤色呈黑人特征后,她与阿尔芒的对话把故事推向了高潮。黛西蕾三次呼喊阿尔芒,却没有得到阿尔芒的理会。随后,她紧紧抓住阿尔芒的胳膊说,“看看我们的孩子。快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而阿尔芒却“掰开抓着他胳膊的手指,神情冷漠,动作很轻,然后用力把手甩到一边”。当黛西蕾再次绝望地询问时,阿尔芒只是“轻声应道”,“这意味着这个孩子不是白人,也就意味着你不是白人”。首先,在这一系列动作中,女主人发现小孩肤色问题时,不加思索,马上祈求男性帮助,以获得答案。通过这一细节,作者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女性的地位:
女性被剥夺了思想的能力,凡事只能求助男性得到答案和帮助。其次,女主人公惊恐地询问,得到的确是男主人公“轻声”的“应道”。这一“轻声”的作答,流露出男主人公对于女主人公谈话内容的不屑,凸显出父权社会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渺小。
在《琐事》中,男性的权威感更是被描写的淋漓尽致。当剧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进行交流时,男性人物的话语总是流露出对女性的嘲笑和忽略。例如,律师亨德森在巡查厨房时,彼得斯太太提起,米妮担心果酱会被冻住,果酱瓶会裂开。顿时,彼得斯警长评论道:“真搞不懂女人啊 ! 都已经被控谋杀了 ,收押期间还在担心她的果酱。”亨德森则嘲笑道:“在结束调查以前 ,她可能有比果酱更需要担心的事儿。”最后,黑尔总结说:“女人就爱关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三位男性角色不仅表露出对于女性关心家务事的鄙视,也通过强调判案的重要性来突显男性的地位和自信。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只关心“鸡毛蒜皮”的琐事的女人们,最终找到了杀人动机。作者这样的处理,正是对男性权威地位的颠覆,以及对男性过于自信心理的批判。在两篇作品中,男性人物都对女性人物话语进行忽略和嘲笑,这充分反应出在当时社会中,男性对于女性话语的歧视。正是这种歧视造成了女性婚姻中没有话语权,最终导致女性心理的压抑和她们的迷失感。
四、结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女权运动发展迅速。女性作家纷纷以小说、戏剧等形式对女性的生存现状进行描述,以争取女性的解放和两性的平等。处在这一时代的凯特·肖邦和苏珊·格莱斯佩尔,运用女性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女性在名字、生存空间、以及话语上所受到的压抑与歧视,共同体现了当时女性在婚姻中的迷失。
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对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社会背景、女性地位、婚姻观念等有深入的理解。这两部作品不同的是:在婚姻中受到压抑而迷失自我后,黛西蕾选择以死亡来实现自我,而米妮则是选择根除使其受压抑的根源。通过这一点,不难看出,相比在凯特·肖邦所生活的十九世纪末,女性反抗的方式大部分是消极和被动的,而身处二十世纪初的苏珊·格莱斯佩尔对反抗压抑的方式更为彻底。但不论是在十九世纪末还是在二十世纪初,两位作家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认识,都对当时在婚姻中迷失了方向的妇女唤醒自我意识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韩贺南,张健.新编女性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2]杨任敬.20 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3]钱满素选编.我,生为女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4]凯特·肖邦,着.德西蕾的孩子[J].陈亚丽,译.北京:外国文学,2010.
结语李彦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围绕着女性群体,发散出各有特色的女性声音。纵观李彦的文学创作历程,其小说轻松出入加拿大及中国的文化视域,以局内人的视角勾连历史与现实情境中的两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具有十分独特的亲历性、在场性,同时也有作为局内人的自...
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1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尤以北美新移民文学为重。在众多的新移民作家中,李彦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大胆以英文创作进军加拿大主流文坛,并以中文译写的方式重返中国,演绎着从边缘走向中心...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著名短片小说,主要讲述了出生在南方没落贵族的艾米丽小姐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而杀死自己情人的悲惨人生经历。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不再仅仅突显南北方的冲突或追忆南方辉煌的过往,而是着力刻画一个浑身散...
一、引言每次阅读蒲宁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一个古典的蒲宁,在古典中呈现清新隽永的韵味。究其原因,我想这种清新和隽永多来自于他笔下的乡村和原野。蒲宁深爱着有着白桦林和卡秋莎的俄罗斯乡村,他在心中的乡村和原野上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甚至整个生命...
叙事学家申丹在其论着《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指出:任何一位作家创作小说并出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听众并传递其意识以至建立影响,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作品所争取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
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入手解读这些自然意象所蕴含的丰富意义。...
当代着名的华裔女作家任碧莲的处女作《典型美国人》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美国文坛乃至学术界的关注.与关注华裔美国的历史、文化、性别等的华裔美国前辈作家(如汤婷婷、赵健秀)不同,任碧莲不再执着于文化冲突、华裔美国历史、性别政治等问题,她更加注重个人的...
一、介绍莫里森为《宠儿》一书所选取的场景是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凶宅。虽然奴隶制已被废除10年了,但被杀婴儿---宠儿的冤魂一直在家中肆虐,家人中死的死,精神崩溃的精神奔溃。最后,是成长起来的另一个女儿丹芙和黑人民众一起帮助她摆脱了宠儿...
一、故事梗概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社会学家、作家,她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女权主义者。在她所在的时代,她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吉尔曼非正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为后代的女权主义者树立了榜样。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她在产后抑郁症后写下的半...
探讨夏洛蒂·勃朗特“为何要”使用月亮意象的心理价值原因,以及“为何能”使用月亮意象的文化传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