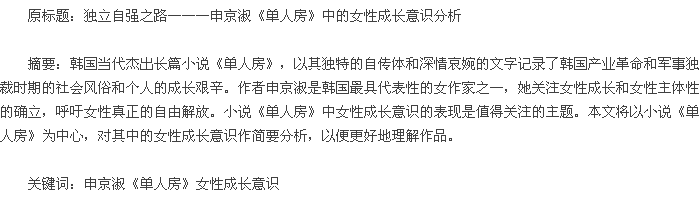
申京淑,韩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韩国上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神话。 1963 年生于全罗北道井邑郡, 毕业于汉城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 1985年,申京淑凭借中篇小说《冬天的寓言》入选《文艺中央》新人文学奖。 1993 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风琴声起的地方》,引起了韩国文学界的关注,在韩国文坛崭露头角。 1995 年出版的《单人房》是申京淑最为重要的长篇代表作,被誉为 90 年代韩国文坛的重要收获。着有长篇小说十多部,作品多次获奖。她极具写作才气,作品感情细腻、真实委婉,弥漫着淡淡的乡愁。她以切己体察的方式表达出人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精神迷失和灵魂自救。
《单人房》带有作者早年自传的影子。风云动荡的时代,少女申京淑离别农村,来到城市,租住在偏僻的单人房,奔波于车间和课堂之间,一心追逐心中的梦想。 同学希斋姐姐的死给她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周围的人们为反抗军事独裁奋不顾身的精神加速了她的成长。 《单人房》承载着作者的成长历程,可谓一部“成长小说”,同时也是韩国社会动荡、急剧向现代奔突的历史进程的缩影,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传记。 下面我们将从女性成长小说层面,对作品中流露出的女性成长意识作具体的解读。
通过上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变革,在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韩国社会中自我本体性丧失的问题逐渐变得具体起来。 尤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的主体性丧失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作家通过文学活动具体确立了女性的本体问题。 他们首先开始了一种告白题的“为了探讨自我本体性的苦斗”。 作家所着力表现的女性角色是个体生存意义上“人”的“自我”,而不是宏观世界的“女性”,并通过文学创作把女性还原成“个体生存的”切实人物。作品集中表现韩国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自我”形象,强调被遮蔽在男尊女卑社会体制下, 男权家族利益的女性主体性自觉意识,着力表现人物如何通过“选择”找到真正的“存在感”。 这种普遍的人性的揭示与现代人精神实质的开掘,构成其作品深厚的社会现实意义,也成为女性“自我”主体性觉醒的主要思想内涵。
作家申京淑关注女性成长和女性主体性的确立。
长篇小说《单人房》描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韩国社会政治体制发生变革的背景下,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女孩从青春期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集中深入地表达了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呼吁和关注。
一、成长之路
《单人房》里主人公“我”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成长,从离开家乡踏进那间狭窄的单人房开始。 十六岁的“我”走过艰难而又漫长的成长之路,不断等待理想的实现。 首先是成长之路的艰辛。 “我”每日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沉重的心情,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枯燥无味的日子。“不管怎么节省,生活费总是捉襟见肘”,总是累得疲惫不堪。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成长的过程中往往要体会比男性更多的艰辛与苦涩。十六岁的“我”以及工厂中众多的“她”,在城市中的生存位置被一再剥夺,特别在经历了女工被搜身、女工怀孕等事件,“我”更体会到女性成长中不可言说的曲折与痛楚。 亲历生存艰辛的一点一滴后,“我”懂得了这一份成长的来之不易,更加珍惜成长的经历和机会。
其次是成长中的梦想之殇。对于每一个走进城市的人来说,大多是怀抱着梦想与希望的,而现实的残酷将理想与梦想击得支离破碎。表姐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而我也举步维艰地一点一点地守护着最初的梦想(成为作家)。 “作家那些人好像天生就是与众不同的”,“我”坚信这一点,为了继续守护这份与众不同,“我”加倍努力,顽强地与生活进行抗争,因为“我”知道梦想的实现是需要付出血泪的代价。
爱情也是“我”成长路上必经的元素。那时的“我”十六岁,唯一令“我”开心的是给喜欢的男生昌写信,在乡村与城市之间,通过书信传递与分享着成长中那份辛酸和欢乐。同时这份感情也成为“我”艰难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 而邻屋希才姐姐穿着上的改变,也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一名女性的不同。还有成长中的死亡之重。对于十六岁的“我”来说,生活的苦难、梦想实现的艰辛以及爱情的苦涩都是成长中的必经之路。但沉重的死亡之痛,对于“我”来说,却成为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仿佛刻于心间,永远无法忘记。希才姐姐的死以及时代政变下发生的一次次流血事件及惨案,变成了我生命中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即使“我”长大成人拥有家庭后,这些依然使“我”感到无法抑制的忧伤。
二、父亲角色缺失
父亲角色的缺失是《单人房》女性成长意识的重要表现。父亲角色缺失的问题和“我”的主体性确立的问题密切相关。父亲一般被认为是家庭的供养者和对家庭负有责任的家长。父亲角色的缺失会导致家庭的生存危机。而且,父亲作为家庭秩序的维护者,他的缺失也会导致家庭的无秩序和混乱。在《单人房》中几乎看不到父亲这一角色的身影,原本应该被父亲守护和供养的我们———“我”和哥哥、姐姐们独自来到城市打拼,努力生活,克服在城市工作和上学的困难,不断走向独立自强之路。 尤其是主人公 “我”在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生活的艰辛以及希才姐姐的死亡之后,精神上受到洗礼,“我”克服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所造成的阴影,怀揣着成为作家的梦想,努力向前,不断写作,完成了精神上的巨大成长。 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主体性形成的过程。 作为女性的“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三、姐妹情谊
同时,姐妹情谊也是《单人房》女性成长意识的另一重要表现。与其他女性小说注重在男性他者的注视与压制中展现女性主体成长命运的方式不同, 小说《单人房》 则更为关注女性独立个体的发展与自我价值的获得。 申京淑细致入微地探索个体女性心理,并且深入地将女性个人生活与时代背景相联系,是女性向社会证明自身价值和存在的可贵探索。 近代以来,随着以人性觉醒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的兴起,女性得以迈出封建家庭的围栏,走进学校,甚至走到社会上进行自由的社交。 与此同时,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也随之浮出历史表面。
姐妹情谊伴随着每一个女性的成长始终,成为女性成长小说中较常出现的主题之一。女性成长中的共有经验被相互分享与保存,成为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精神慰藉,更为在成长道路上处于生存困境和性别困境的女性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援助。这些播撒在女性成长叙事深层的姐妹情谊,阐发了女性在灵魂沟通基础上相互给予的温情与关怀,成为女性心灵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庇护所,并因此更加注重自我的独立和发展,从而走上更为健康的女性成长之路。 《单人房》中“我”与表姐、希才姐姐在艰难生活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正是我成长道路上的避风港,在缺少了父亲的守护和母亲关爱的情况下,姐妹情谊显得尤为重要甚至不可或缺。表姐和希才姐姐作为“我”成长道路上的伴随者、影响者,甚至是引导者,也是主人公自我形象的投影,在姐妹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也说明了“我”个体精神的不成熟状态。 因此,与姐妹暂时或者永久的别离,成为主人公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直到勇于穿过这片黑暗的影子,才能完成蜕变,收获成长。但我相信个体生命的成长必定将主人公引向独立的成长道路。正如希才姐姐的死亡让“我”久久不能忘记,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但也正是这痛苦而艰难的经历使“我”不断成熟,最终完成蜕变,走上独立自强之路。
四、写作
《单人房》中“我”的主体性确立或者成长的完成最终是通过写作(文学)实现的。 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作者自己认为的写作(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关于写作的梦想,“我”把它描述成为“面向星空,站在高处优雅入睡的鸟”。 这是非常浪漫和具体的形象。 而被现实压抑的“我”只描述了在笔记本上抄写《矮子射出的小球》的事情和“我”对文学(梦想)的热情。换言之,小说并没有描写“我”在阅读或抄写《矮子射出的小球》时有什么想法,以及这部作品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小说重点强调了“我”那被囚禁在自我和家庭共同体藩篱内的梦想。“我之所以从事文学并不是想用文学改变什么。 只是因为喜欢而已。 只有通过文学,我才能梦想那些在现实中不可能的东西、被禁止的东西。 ”
“那些梦想究竟来自何方? 我认为我是社会的一员。 如果说我之所以能够做梦是因为有文学,那么社会不正是让人做梦的地方吗? ”主人公认为写作能够带给自己梦想的力量,写作能够使自己冲出灰暗现实的泥沼,寻求自己心灵的乌托邦。 最终通过写作(文学),主人公完成主体性的确立和自我的成长,获得了自我认同。 而对于作家自身,写作则无疑是心灵深处的赎罪和灵魂的拯救。这也反映了后工业化时代的精神迷失和灵魂自救这一深刻主题。
本文从成长之路的艰辛、爱情的体验、父亲角色的缺失以及姐妹情谊等方面对《单人房》中的女性成长意识作出分析,最终落脚到写作(文学)这一梦想之翼上。 主人公在经历了成长的艰辛之后,最终通过写作(文学)完成了自我成长和主体性的确立,在实现了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完成了心灵的救赎。主人公完成了自己的独立自强之路。《单人房》细腻地记录了女性成长之路,深刻地反映了女性的成长意识,对于反思现代社会女性的成长现状、促进女性实现真正的自由解放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 高 印焕.申 京淑小说中 “家庭 ”的意义———以 《单 人房 》和《寻找母亲》为中心[J].当代韩国,2011(12).
[2] 黄 洸希.申 京淑 《单人房 》中的成长主题研究[D]. 云 南大学,2011.
[3] 薛舟.从少年到白头,没有一天不忧伤———关 于韩国作家申京淑和她的《单人房》[J].外国文学动态,2006(10).
摘要《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文体优美、情感充沛的诗一样的小说。它属于一部抒情性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诗意特征。其诗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部小说既有着诗一样准确、精致的语言,作者以诗人的敏感和准确去描写世界,捕捉周围的细节,也将人物...
结语李彦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围绕着女性群体,发散出各有特色的女性声音。纵观李彦的文学创作历程,其小说轻松出入加拿大及中国的文化视域,以局内人的视角勾连历史与现实情境中的两代中国女性的命运,具有十分独特的亲历性、在场性,同时也有作为局内人的自...
《藻海无边》是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的代表作,被称为《简爱》的前传。简里斯把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没有详细讲述的疯女人的故事再现,把疯女人的形象丰富化。自问世以来,此小说引发了研究者们浓厚的兴趣。他们或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或从叙事策略方面、...
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1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尤以北美新移民文学为重。在众多的新移民作家中,李彦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大胆以英文创作进军加拿大主流文坛,并以中文译写的方式重返中国,演绎着从边缘走向中心...
小说《永无长久》是法国年轻的女作家洛朗斯塔迪厄于200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这也是她个人的第三部小说,出版当年即获得法国阿兰傅里叶文学奖,她的前两部小说《如父亲一般》(2002)和《蕾阿的审判》(2004)也获得了相当的好评.这部小说并不长,记叙的故事情节...
一、引言每次阅读蒲宁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一个古典的蒲宁,在古典中呈现清新隽永的韵味。究其原因,我想这种清新和隽永多来自于他笔下的乡村和原野。蒲宁深爱着有着白桦林和卡秋莎的俄罗斯乡村,他在心中的乡村和原野上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甚至整个生命...
第三章艾丽丝门罗小说重视表现心理的成因当艾丽丝门罗用她绵密深邃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日常生活中平凡普通人深邃独特的内心世界之后,我们忍不住要问:门罗作品中的人物为什么会拥有这么真切丰富的内心波澜?小说人物的心理世界与作家的创作主体有什么关系...
德拉梅尔在小说《杏仁树》中,没有通过他所擅长的心理描写来传达令人窒息的婚姻状态,更没有令人惊悚的灵异氛围、令人心寒的猜忌、撕心裂肺的争吵。悲剧婚姻主题在《杏仁树》中凭借的是涓涓细流般的对话,一桩濒临死亡的婚姻缓缓侵入读者心田,柔和却冰凉,冒着...
小说《纯真博物馆》是帕慕克近年来的一部力作。从表面上看,主人公这座为了纪念逝去的爱情而建立的博物馆承载了作者对一段刻骨铭心爱情的记忆,实质上这里面同样交缠着一座城市的过往,而这座城市的记忆中积淀的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过往。小说中,贵族青...
约翰班维尔(JohnBanville)的小说通常弥漫着一种嘲讽意味的绝望及想象的慰藉,因为他觉得语言是感知的障碍,语言并不能充分描述或者理解人的经历。因此,班维尔的小说都是由一个自我中心的男主角来叙述人生中发生的悲剧。少年时期学习绘画的经历让班维尔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