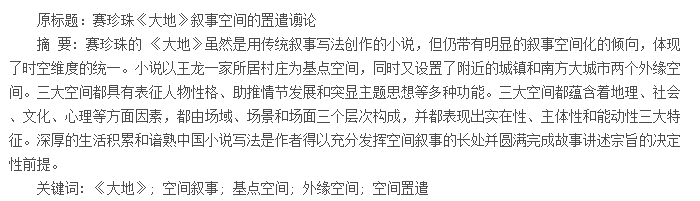
赛珍珠的 《大地》虽不像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那样表现出自觉的空间化意识、体验和摆脱任何时间因素制约的书写方式,但若透过其文本的外在形式层面,仍可感觉到时间化的情节被化解为众多零散的、片段的空间板块彼此衔接,如 “草蛇灰线”隐伏其间。《大地》在叙事方面的空间化追求,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和运作前提。正由于此,本文乃试图另辟蹊径,借鉴空间理论的某些观点来探讨、发掘小说叙事艺术成就。完全可以说,用空间叙事理论去阐释这部小说的艺术特征并不是削足适履。打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学理蔽障,使用空间叙事理论对这部作品进行考察,当会有不少新的收获。
一
空间叙事是现代、后现代小说的艺术追求。赛珍珠的 《大地》当然不属于现代、后现代小说,采用的是典型的传统小说 “性格———情节”叙事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借助事件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构成情节链条,在情节的进展过程中刻画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物 (性格) ,同时配备以环境氛围的渲染描绘,即在事件基础上建立一个三元构架。小说的作者运用传统的 “情节———性格”的思维定势和操作规程、依据时序的叙事模式来表现主题,采用线型延伸推进的写法,重视事件的序列性、逻辑性和因果律,追求情节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小说的时空体验主要反映在事件转承、性格发展、因果逻辑等历时性因素方面,结构虽不乏起伏但较单一。以往人们研究这部小说的写作艺术时自然都以时间维度为逻辑起点和阐述思路。
然而,这部小说虽然依循传统的 “以时间为主导和本质”的创作理念和结撰原则,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叙事空间化的倾向和色彩。准确地说,《大地》的叙事宗旨及其厚重的思想底蕴是通过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表现出来的。赛珍珠在追求叙事空间化方面有着相当的自觉意识,在时间艺术作品中较充分地利用、发挥了空间叙事的长处,圆满地完成了故事讲述宗旨。迄今所有 《大地》叙事艺术的研究成果虽都从时间维度切入,但在阐释过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触及空间方面的因素。这说明在叙事艺术中时间和空间总是始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事件是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统一体,“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
《大地》以王龙一家所居村庄为基点空间,并由此渐行渐远,又设置了两个外缘空间,从王龙脚下可耕作的土地,逐步推及近在迟尺的城镇和百里之遥的都市,把所有主要人物的活动镶嵌入一个完整的、层次井然的空间体系之中,其行为指向性也完全为这一复杂的空间所规定。这三个空间都兼有表征人物性格、助推情节发展和突显主题思想等多种功能。小说在叙事中用 “土地”这一核心要素使三个由一系列社会行为所界定的行动场域发生关联、互动,将主人公的恋土情结得以充分地展示,出色地完成了全部情节的讲述宗旨。主人公王龙的经历是以具有时间性特征的语言为媒介叙说的,但表达出来的是一系列充满空间感的形象,作品的叙事结构是在时间序列和空间流程两种维度的坐标中建构起来的。小说对空间的安排、驱遣体现出作者巧妙、高超的艺术匠心。
赛珍珠从文学空间与地理学空间的关系着眼,以一个旧中国农民家族的历史流程为脉络,将所述故事与行旅和家园意识联系在一起,旨在通过叙事文本构建一种 “家园感”。 “家园感”本为中西文学创作史上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 “母题”,但在赛珍珠笔下被赋予了新的意蕴。赛珍珠从文学空间与地理学空间的关系着眼,将故事与行旅和家园意识绾系在一起。小说全部故事的空间流转迁徙实际上都在回扣、呼应着这一主题,随着故事进程的展开和收束,不断强化着作者期待、思慕的 “家园”,渗透着对人类出路的理性思考。从家园的营构、失落,经过探寻回家的旅程,到最终还在极力寻找回本原的那一支点,作品由一系列社会行为所界定的空间组构而成,表达了旧中国农民安土重迁、以土地为命根的理念。伴随着主人公生存、活动空间的变化、转换,故事的终点流露出欲与起点———本原的失落点交合的倾向,“离乡”和 “回乡”的焦虑始终贯穿于文本之中。王龙那块故土实际上成了“家园”的喻体。环绕着王龙院落的土地不仅是地理版图上的定点,也是赛珍珠生态之梦的理想支点。她在通过 “原乡”这一象征性符号表达着自己的价值观。王龙 “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之语是对这一貌似十分简单和浅显其实有着极为复杂而深刻寓意的过程的文化阐释。由此可见,作者在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创作中别具慧眼,匠心独运,充分利用、发挥空间的叙事作用和长处,取得了可圈可点、引人瞩目的成就。
二
正如论者所指出,小说的叙事空间是以 20 世纪初安徽北部宿县 (今宿州市) 县城和郊外农村以及江苏南京的生活为现实基础构思出来的。《大地》的情节不算繁复,故事发展呈主副式。王龙为主线,其他所有人的活动都只能构成副线,依附于主线而存在,整个故事顺着主人公王龙的经历单线推进,所有人物和时间都围绕王龙的行动展开,毫无蔓枝,情节连贯,主题单一。作者根据叙事的需要设置、驱遣空间。小说由 34 章组成,故事集中发生在皖北农村地带的两大场域———即王龙的村庄和附近的城镇,其间只是由于故事发展的需要穿插进了一个逃荒的落脚点——— “南方大城市”。这三个空间可分别被称为 “乡村空间”、“城镇空间”和 “都市空间”。三者的交织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一幅尚未完全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脱胎出来但又显露与现代社会接轨之端倪的近代中国的画卷。从空间对主题的显现和阐解功能来看,乡村空间为基点空间,城镇空间和都市空间是外缘空间。在这里,我们对 “基点”一词的理解不应过于狭窄、机械。
根据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基点”有二义:一为 “作为开展某种活动的基础的地方”,一为“基础”。因此,这一基点空间不但在小说的空间维度中具有核心部位和叙事焦点的意义,而且在时间维度中也具有全部故事情节的起点和结穴的意义。“外缘”本佛家语,意谓外在的助缘,即 “自外与力,而助物之生起之缘”,此处用来表示与基点空间相对应、联系并辅之以阐释、生发主题的各个空间的性质。
乡村空间包括王家宅院、王家田地、打谷场、地里的水塘、土地庙、家坟和通往城里的田间小道等场景。各个场景中都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它们构成了故事的一个个具体的片段———展现各种事件的场面,反映了以宗法制度和观念规范、限定人的行为的中国传统乡土世界的本质特征,以及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结构和地主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中农民的土地观念和恋土心态,表现了主人公王龙性格的变化和发展,准确、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皖北地域文化的身份特征。土地情结与宗法意识构成了乡村空间的主要思想内蕴。
城镇空间含纳着这样几个从方方面面阐发主题的场景群: 城墙、城门洞、护城河、护城河旁黄家的土地,城门里的剃头街和展销各种商品的市场,街面上的饭馆、大小茶馆、水果店、蜡烛店、点心糖果店等林林总总的各类商铺,佛教古迹西塔、娱乐场所说书摊和王龙两个儿子念书的学校,还有那个在小说后半部才出现但在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石桥街的粮店,尤其是对情节发展产生了决定性意义的黄家大院和名叫 “花房”的新开大茶馆,发生于其中的诸多故事段落是乡村空间叙事的延伸和补足,与乡村一道演绎着 20 世纪初的乡土中国,其功能主要体现在辅佐乡村空间完成主题的阐释。
都市空间也包含着一系列场景,一墙之隔的富豪院落和难民席棚区、居民点和建筑物、大道和胡同、路边和野外、出售各种食品和用品的商场以及那个南方大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夫子庙,这些静止的地点与人物的活动有机结合为一个个流动起来的 “行动着的地点”,成为阐释主题、讲述故事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作品所设置的三个空间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相紧密关联的结构,整个故事被囊括、镶嵌、编织在这一视野较开阔的宏观框架里。王龙之父的晚年、王龙从结婚到暮年、王龙三个孩子的青少年生活大体上都在这一空间内展开。王龙屡次往返其间的村庄和附近的城镇构成这一空间系统的两大支撑点。小说所叙故事主要集中在 “乡村空间”和“城镇空间”两大场域,仅于第十———十四章涉及那个 “南方的大城市”,而这一片段在小说的 34章中只占七分之一弱的篇幅。所以说,“乡村空间”和“城镇空间”是作者在本部小说中所设置的两大主体空间 (此处的 “主体”乃取其 “事物的主要部分”之意) ,贯穿故事始终,而 “南方的大城市”则为辅佐空间,是阶段性的,仅为完成叙事的目的而存在于叙事过程的某一环节。三个空间都有其特定的形式、内涵和功能,既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彼此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又互相依赖、补充,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小说以绝大部分篇幅描写的乡村和城镇两个空间都属于乡土世界。乡村和城镇的空间虽然不算宏大、开阔,却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叙事密度远远大于 “都市空间”,而乡村和城镇两相比较,前者的叙事密度又明显高于后者。
三
小说所设置的三个空间虽从表面看来主要是从地理学的视角划分的,地域性的特征十分明显、突出,但都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内容,实质上是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体,是作家所感受和创造出来的 “人化空间”,体现了个性化的审美观照意义。赛珍珠不仅把空间当做文学书写的对象,而且赋予其主题化意义。三个空间的内涵不仅反映在自然、地理、物质方面,而且反映在人文、社会、文化方面,都同时兼备行动的地点和行动着的地点两方面的元素,都是静态的结构空间和动态的主题化空间在时间流程中的有机结合。这一完整的空间体系较成功地再现了近代中国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展示了主人公王龙由一个贫苦的农民转变为富裕地主、凭借土地发家致富后离开土地而又归心愈烈的真实过程,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乡土性的”中国社会血缘、地缘、家庭三位一体的特征和本色,饱含厚重的中国社会历史积淀,灌注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底蕴,凸显了旧中国农民的社会品格、心理结构和生活追求。《大地》叙事空间的功能主要体现为表征人物性格和推进情节发展两个方面。三大空间三位一体,共同为完成叙事的需要发挥着作用。就这一点来说,赛珍珠在构思上显示了极强的特色。正是由于她在空间叙事方面匠心独运,别出心裁,融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于一炉,才得以通过空间凸显作品所特有的思想底蕴和文化内涵。
《大地》中每个大的空间都由若干层次构成。
要言之,乡村空间、城镇空间和都市空间都是范围较大的场域,每一场域又容纳不少场景,发生在每一场景中的诸多细碎的场面构成一个又一个彼此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其流迁、接承、转换和联缀愈来愈深刻地演绎着作品的主题。被置于各个空间中的人物、事件和情感也不断丰富着小说的思想蕴涵,演绎着故事的文化意义。场域、场景、场面构成了小说空间结构系统的三个层面,环环相扣,不同层面的空间 (地点) 共同演绎了以王龙为主角的故事,凸显了故事的题旨指向。在这一空间体系中,每一层次的空间不仅包纳、衔含着自身完整、清晰的内涵,而且其外延也呈开漾、拓宽之势,并逐渐与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接近、叠压和交汇,产生了极大的艺术张力。作家凭借着具有空前超越力度的创作视角和笔触,翱翔在跨越时空的广阔的艺术天地,将大千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对主人公的“土地情结”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探索,对受宗法制度和意识影响的清末民初中国农村的社会状态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末代的人际关系及其演变做了淋漓尽致的剖析。
四
小说中乡村、城镇和都市三大叙事空间都表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实在性。小说所设置的空间都不是空空如也的容器,而具有丰富、深邃的人文内涵,体现了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人际关系和矛盾以及激发起抗衡和冲突的 “规定情境”。乡村,作为基点空间,集中体现了以宗法规范、限定人的行为的中国传统乡土世界的本质特征,以及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结构和地主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中农民的土地观念和恋土心态。城镇,作为基点向外延伸的第一个层面上的空间,其作用主要是强化处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的主人公性格的再度建构和补足,拓展和深化在乡村空间中未能充分展开的家庭、社会矛盾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相态,完整、典型地反映中国乡土世界的社会结构及其中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精神面貌,并着重通过王龙与原乡的田地藕断丝连表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切思考。作为第二个外缘空间的都市,也包含着许多展示各种事件、具有象征性符号意义的场景,是极富意蕴和主题化的行动场域。身处这个比王家庄附近的城镇远得多的大都市的主人公更表现了内心的矛盾和对乡土、田地的一往情深。
其二,主体性。由于被赋予了社会内容, 《大地》中的所有空间就都具备了表征人物形象特征、推动情节发展变化的功能,因此,它在讲述故事、表现主题方面不仅仅是性格和事件的附属品或静态的 “环境”,而是负有主动承担叙事使命的重要因素。此处拈取王龙的土地这一景点为例证表述之。
在作者的笔下,土地成为了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象征物,它不是静止、单纯的、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而是一种有生命、有灵性的文学形象,被赋予了主体的身分以及社会性质和人文意蕴,它和主人公一道共同阐释着主题思想,它既是背景,也是角色,是最富有精神指归意向的动态意义上的物质,既孕育五谷滋养众生,又象征 “轮回”和 “新生”,同时又成为贯穿整个故事的主干经络和思想脉息,与人物共同构成故事自身完整的主体大厦,具有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赛珍珠小说里的土地犹如哈代笔下的威赛克斯地区和海明威笔下的大海,是构成小说整体意象的 “灵魂”。土地这一空间意象不仅仅是营造环境、刻画人物性格、烘托心理活动的陪衬,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物心理活动过程中 “移情”的对象,而是具有主体意义的因素。小说是把主人公和土地作为一个完整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来表现的,作为自然景物的土地已成为了人的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人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王龙始终与土地相依为命,土地就是他的命根子,两者相互依存,相互生发,故事自始至终都在书写着王龙和土地之间 “心”与 “物”“思”与 “境”的纠缠、扭结和交汇。
其三,能动性。在小说中,空间不是单纯的事件发生或人物活动的地点,而是行动着的地点,具有很强的活力和驱动力。它不仅是完成叙事任务的重要前提,也是达到叙事目的的根本手段。现代空间叙事理论认为,空间如只单纯具备行动地点的意义和价值是根本无法履行叙事功能、完成叙事任务的,只有当它超越了自身地理、物态概念的藩篱,成为了促使事件发展的动因,并在运动状况下发挥作用,变成行动着的地点 (动态空间) ,才能在叙事中发挥作用。《大地》的作者在构思、设置空间时,千方百计地寻找、激活能促使空间运动的因素。她努力赋予空间丰富的社会内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导致冲突的动力,令人物性格和情节事件在空间的助推下和运动中向前发展。小说在这方面多有可称,此处隅举一例。王龙从妓院接回荷花后,自己的宅院里便不安宁了,阿兰和荷花之间、王父和荷花之间、荷花和王龙两个儿子之间、王龙和荷花的侍女杜鹃之间、王龙和叔婶之间,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皆矛盾重重,出现了许多棘手的事情,其间夹杂了王龙兴土木扩建宅院、儿子在学堂逃学挨打、王龙为儿子提亲引出城里粮行刘掌柜、儿子在堂兄教唆下进城嫖妓、王龙愤怒之下与当了红胡子的叔父发生争吵等一系列事件,随着空间在时间序列中的流动、转换,各色人物行动充分展开、各种矛盾逾趋激化,空间的动态性特征便不断强化,以一个行动着的地点的身份完成了叙事结构的建构和叙事宗旨的实现。
五
《大地》在空间叙事方面能达到如此高的艺术境界,是与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分不开的。赛珍珠早年曾长期生活在三个空间的地理原型———土质贫瘠、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皖北宿县和社会高度发达的商业化大都市江苏南京,目击了农民的艰辛困厄,与各阶层居民同呼吸共命运,也感受了城市的贫富对立。她曾回忆说,在宿县 “那些年我走遍了穷乡僻壤”,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到的地方越来越多,新朋友也越来越多”,并一往情深地表露心迹: “在南徐州 (即宿县———引者注) 居住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了解那些住在城外村庄里的穷苦农民,而不是那些富人。穷人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钱挣得最少,活干得最多。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走访农家成了我自己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在农民当中,我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5]154 -156
张子清称 “她对中国农村熟悉的程度,甚至远比同时代的生活在大城市而脱离工农大众的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深得多”, 《大地》里的 “种种生动场面,如不十分熟悉当时中国农村的情形,任何天才的作家也杜撰不出来的”。她在南京时也广泛接触各阶层的人们,细致入微地观察现实生活,曾竭尽所能“为蜷缩在城墙上的成千上万的难民募集衣食”,也常站在城墙上 “眺望广阔乡村和叠嶂峰峦”,这里的着名景点如紫金山等使她终生眷恋[5]164 -165。
这些都使她对皖北苏南一带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风土民情和广大居民的心理状态有了完整而深刻的洞悉。小说家的创作心理尤其是创作时的记忆和想象活动是完成叙事宗旨的前提,记忆和现象堪称能让形象飞动起来的两大翅膀,在写作中的重要意义是众所周知、不言而喻的。文学叙事的客体是事件,但 “叙述的对象并不是原生事件,而是意识事件”,也就是 “叙事行为即将开始之际出现在叙述者意识当中的事件”, “叙述者必须从意识中选择出一系列事件并把这些事件根据某种关系组织起来,才能最终达到叙事的目的”, “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并最终进入叙述过程的事件,是经过 ‘选择性记忆’处理之后的结果”,所以记忆对叙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 “记忆不仅和时间有关,它的空间特性也非常明显,而这种空间特性必然会给虚构叙事带来深刻的影响”, “我们生活中重要的记忆总是和一些具体的空间 (地方) 联系在一起……那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方很容易成为我们记忆的承载物”,因此叙事作品 “也就必然会具有某种空间性的特征”。正是由于对皖苏一带城乡人们生活及其生活环境的深刻了解,才使赛珍珠能够在叙事文本中再现诸多栩栩如生的空间以及空间中各色人物的具体活动,把记忆中的 “空间形式”转化为意识中的 “空间形式”,并通过想象和有关艺术表现手段再转化为文本中的 “空间形式”,圆满地完成叙事的目的。有人描绘这一转化、飞跃的过程时说: “写作者敏感的感觉使他的大脑提示的现实过于丰富,于是过剩的现实变成了想象,而这一形成过程把他本人及周围所有人的生活,包括他想到的梦到的都卷入这一内部开始的活动过程中,结果是演绎出了艺术。”
有人劝她修改 《大地》时,赛珍珠以不能把书中的人物 “强制放在外国房子里”的理由予以拒绝,这充分说明了自己十分重视记忆中的空间对于叙事的价值以及文学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意义,以及对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生活基础是作品成功的关键这一原理的深切感悟。这是这位天才的小说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艺术经验。
赛珍珠在空间叙事上的特点,受中国文学影响很深。她 “小时候,在中国,她和中国儿童一样,听周游四方的说书人讲故事,这些江湖艺人的演出使她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这对她日后继承中国说书人的传统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有裨益。”
中国叙事文学的空间化倾向很突出。着名的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认为 “在中国小说的主流中,空间感往往优先于时间感。从上古神话到明清的章回小说,大都如此”。赛珍珠特别推崇中国传统小说创作以 “自然”为至境的美学宗尚,并将它与空间叙事联系起来。她说“‘自然’就是丝毫不矫揉造作,非常灵活多变,完全听凭流过他头脑的素材的支配。他的全部责任只是把他想到的生活加以整理,在时间、空间和事件的片段中,找出本质的和内在的顺序、节奏和形式”。由此可知,赛珍珠在 《大地》的创作中自觉地强化空间叙事功能,这绝不是偶然的,是她深谙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手法并有意识地从中国文学中吸取艺术养分的结果。
本文的宗旨不在于将 《大地》作为典范和例证从整体上诠解、演绎空间理论的内涵,因此,不把注意力放在追求空间理论的自洽性上,而是借鉴、运用空间叙事理论的有关基本观点、研究成果和学术命题解析、探索并揭示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撰方法、叙事特点和艺术经验。作为用现代文学理论阐释传统小说写法的一个尝试,笔者尽可能在接近“绝对真理”的探索中寻找更多的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杨星映. 中西小说文体形态 [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13.
[2] 保尔. 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 时间与叙事 (第 2 卷) [M]. 王文融,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3: 224.
[3] 丁福保. 佛学大词典 (上册) [M]. 上海: 上海书店,1991: 937.
[4] 赛珍珠. 大地三部曲 [M]. 王逢振,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00.
[5] 赛珍珠. 我的中国世界 [M]. 尚营林,张志强,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6] 张子清. 赛珍珠与中国———纪念赛珍珠诞辰一百周年 [M] ∥郭英剑. 赛珍珠评论集. 桂林: 漓江出版社,1999: 178.
[7] 龙迪勇. 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 [J]. 江西社会科学,2009 (9) : 49 -56.
[8] 鲁新轩. 赛珍珠的文艺观 [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7 (3) : 37.
[9] 希拉里. 赛珍珠在中国 [M]. 张秀旭,靳晓莲,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1: 149 -150.
[10] 姚君伟. 归来兮,赛珍珠———试谈赛珍珠及其作品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 [M]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30.
[11] 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7.
[12] 赛珍珠. 中国小说———1938 年 12 月 12 日在瑞典学院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M] ∥姚君伟. 赛珍珠论中国小说.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4.
叙事学家申丹在其论着《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指出:任何一位作家创作小说并出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听众并传递其意识以至建立影响,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作品所争取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
英美文学作品通常是作者源于现实,将所知所想通过艺术手段凝练为文学作品。因此,英美文学作品带有作者生活的气息,在语言的使用上明显具有地方性语言特点。...
探讨夏洛蒂·勃朗特“为何要”使用月亮意象的心理价值原因,以及“为何能”使用月亮意象的文化传统因素。...
一、引言安吉拉卡特(19401992)以独特的写作风格驰名英语文坛,其写作风格混杂了魔幻写实、哥特式与女性主义。2006年众多女性读者在英国掀起一股卡特作品回顾热潮。在两年后的《泰晤士报》战后50位英国最伟大作家评选中,安吉拉卡特位居第十。《马戏团...
一、前言纳撒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主要描写单纯善良的青年布朗到魔鬼那里去赴约,但是当他走入黑暗的森林中,却发现许许多多他平时最尊重的人威严的执事、德高望重的教长、虔诚的老妇人、贞洁的少女,都跟他一样与魔鬼有约。最后他竟然...
叙事视角在当代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作为一种研究角度, 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将作品的分析带入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本文以叙事视角的方式对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的《白噪音》进行的分析呈现出该作品的艺术特征与表达效果。...
叙事视角是把叙述者对故事的感知经验局限于某一个局部主体意识,从而把整个叙述置于这个局部主体意识的能力范围之内。从宏观意义上,叙述视角可以分为两大类:全知视角和有限叙述视角。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创造性地将两者相结合,用多种叙述手法,在不...
现代性主体建构于个体在现代社会追寻与确认自身身份的过程之中。从空间理论的角度来看,城市人身份感的模糊缺失与城市空间密不可分,城市空间的设计、规划与布局对人的身份会产生同化与异化作用。两种作用相互抗争,使人的身份成为矛盾体,从而引发城市人的...
一、叙事角色的颠倒《刀疤》收录于1944出版的博尔赫斯小说集《虚构录》集中,它不是博氏创作中玄之又玄的迷宫建筑。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简单,故事本身也并不惊心动魄,但颠覆性的叙事方式却令读者耳目一新。小说出现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先由我(博...
本文试图藉由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印象主义技法进行深入探析,深入解读作者在文本中对于光与色的艺术化处理及娴熟的感观化叙事应用,为该经典文本的解读提供崭新的视野与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