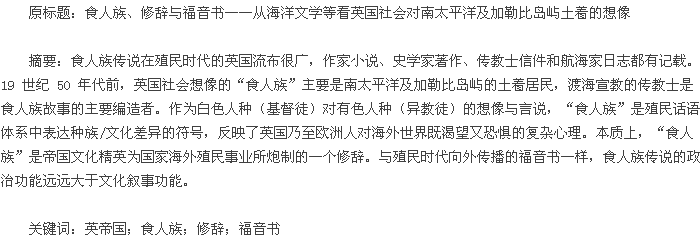
西方社会关于食人族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①只是,《奥德修纪》中的“食人族”还仅与希腊语 anthropophagy 一词相对应,并不具有伦理学、种族学和政治学含义。近代史上,真正令“食人族”词义发生本质变化的是着名航海家哥伦布。1493 年,哥伦布在给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总管路易斯·德·桑塔戈尔(Luis De Santangel)的信中宣称,“一个名叫加勒比(Carib)的岛屿……居住在该岛上的居民被所有其他岛屿视为十分残忍的民族;他们以人肉为食;他们有很多独木舟,出入于印度的所有岛屿,将他们能够到手的东西虏掠一空……”。
尽管哥伦布只是转述了他在阿来瓦克岛(Arawak)上听到的传闻,他本人从未真正接触过食人族部落,但哥伦布将食人族(Cannibals)和加勒比人( Caribbean ) 联 系 起 来 , 使 得 “ 食 人 族 ”(Cannibals)一词在欧美世界广泛传播,导致西方人普遍产生了“食人族=加勒比人”的错觉。
自哥伦布以降,西方社会想像和描述“食人族”的文字日益增多。法国学者蒙田、作家凡尔纳、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和作家麦尔维尔等人都在作品中提到过食人族。
比较而言,英国大概是世界上拥有食人族传说最多的国家。18 世纪,英国着名航海家兼地理学家詹姆斯·库克率领船队在南太平洋海域航行,绘制过美拉尼西亚岛(Melanesia)、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等岛屿地图。库克船队在与当地土着发生冲突过程中,有十多名船员被毛利人杀死或“吃掉”。库克在当天航海日志中这样评价毛利人:“尽管他们是食人族,但他们生性不坏。”
库克后来在发现斐济一些岛屿时,又将斐济岛上的土着居民描述成食人族:“据说,他们是野蛮凶残的食人族,这恐怕他们自己都不会否认。”
在库克等航海家影响下,英国社会关于海外食人族的传说越来越多,甚至形成了独树一帜、蔚为大观的海洋文化现象。英国作家作品、史学家着作和传教士日记与信件等,都以不同形式记述过“食人族”或食人现象。当然,在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英国社会对“食人族”的想像主要集中在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屿地区。
随着后来欧洲各国对非洲殖民探险逐渐展开,特别是英国殖民势力在非洲大陆逐渐渗透以后,英国社会对食人族的想像才相应地从南太平洋及加勒比海岛转向非洲大陆。
一、英国食人族传说
从文学上看,笛福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第一部描写“食人族”故事的作品。1704年 9 月,英国船员塞尔柯克与船长发生冲突而被遗弃在拉丁美洲荒岛,四年以后,经过的船只才将他救回英国。笛福根据塞尔柯克的经历创作了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作品叙述主人公鲁滨孙漂流到“绝望岛”以后,将一个荒岛经营成繁荣富庶的“独立王国”的故事。鲁滨孙从食人族手里救下野人土着“星期五”,教他说英语并让他皈依基督教。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章节即是关于吃人场景的描写:“我……看到他们所干的惨绝人寰的残杀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更令人可怕!那血迹,那人骨,那一块块人肉!”
作品接着描述“野人”吃人具体细节:“两三个野人一拥而上,动手把他开膛破腹,准备煮了来吃。另一个俘虏被撂在一边,到时他们再动手拿他开刀。”[5]
笛福在小说中的描绘形象而又具体,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惊肉跳的恐怖感。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出版之前,莎士比亚《暴风雨》(TheTempest)中野人卡利班形象已进入西方人的意识世界。尽管莎士比亚并未明言卡利班是食人族,英国人乃至欧洲人仍然普遍相信食人族真的存在。笛福小说进一步强化了食人族在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其后,维多利亚时代作家巴兰坦(Ballantyne)在《珊瑚岛》(1858)中再次描述食人族的野蛮行径。小说叙述拉尔夫等三个年轻人漂流到一座孤岛,亲眼目睹了岛上居民举行的杀人仪式:“用石刀从死者大腿上切下一大块肉片”,“他的身体刚刚停止抽搐,那些土人就从尸体上割下肉来,稍微在火上烤了烤就吃下去”。
英国传教士的日记和信件是食人族传说又一来源。1796 年伦敦传道会首次决定向南太平地区派出传教士。1809 年,一群英国传教士在南太平洋地区斐济岛的海滩上搁浅。牧师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在并未见到食人族的情况下仍然这样写道:“斐济人可能是现存的最着名的食人族。所有岛屿都由一些穷兵黩武的酋长们统治着。无论何时,敌人一旦遭到杀害就会被人吃掉。有时,人肉会被切成几百个小块一起放在炉火上烧烤,然后举行盛大的食人宴会。他们烧烤人肉的方式与塔希提人烤猪肉的方式一样。”
1839 年秋,英国传教士嘉吉(Cargill)到达斐济群岛宣教。他在给卫斯理传教士协会的信中谈及他在斐济见闻,其中关于斐济土着食人场景的描写同样令人毛骨悚然:“今晨,我亲眼目睹令人震惊的一幕……二十具男女和孩子尸体被当作礼物送给塔诺亚王(Tanoa),然后又被分给众人煮着吃了。孩子们也以残害一个女孩尸体为乐……人体内脏在我们驻地的河上顺流漂下,那些被切断的手指、头颅、躯干在水面漂浮。我们到处看到这样令人作呕的骇人听闻的景象。”
南太平洋传教史上着名的传教士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认为,食人是一种极其残忍的习俗,反映了斐济文化中堕落、野蛮和恐怖的一面。他在《南太平洋岛屿传教事业叙述》中这样描述部落酋长塔诺阿的吃人动作:
“吻了他的亲戚以后,塔诺阿从肘部割下他的胳膊,喝着他静脉流出的温热的血,颤动的胳膊被他扔到火上,在充分烧烤后,他当着死者主人的面将这些肉吃掉。此时,主人已被割断手足,肢体不全。野蛮的杀人者却在观察这些将死之人的痛苦表情。”
威廉姆斯宣称这种谋杀在斐济岛司空见惯。1939 年,约翰·威廉姆斯及同伴詹姆斯·哈里在与土着冲突中被打死,许多英国民众认为他在遇害后被斐济人“吃掉”了,威廉姆斯也因此像在非洲宣教的传教士李文斯通一样,在英国国内成为受人敬仰的圣徒式英雄。
一些史学家着作也记录了食人族传说。18世纪末,西印度群岛的食人族故事出现了新的版本,即食人族不再是当地土着居民而是流散而来的非洲人和黑皮肤的克利奥尔人(Creole,欧美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后裔)。在相关的历史着作中,爱德华·龙(Edward Long)的《牙买加历史》和布莱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的《英国在新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历史、内政和商务》影响最大。龙在考察当地土着居民的饮食习惯时记录了食人情况:“当地吞噬人肉的旧俗违反人性和理性,令人作呕。如果不是经过许多航海家证实,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不仅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所证实……也为我们殖民地里的非洲黑人自己的报告所证实。当我们想起他们血腥、残忍的脾性和其他方面恶行时,也就不难理解了。大家知道,殖民地的黑人热衷于吮吸他们敌人身上的血;在贝宁、安哥拉和其他国家,人们至今还爱吃猿猴、狗肉、爬行动物和其他东西……”
比较而言,爱德华兹对待黑人的立场显得比较理性,但他关于食人族的描述同样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爱德华兹指出西印度群岛一些非洲移民,如考罗曼帝人(Koromanty)和伊布人(Ibo)等是食人族部落。
他在作品中这样叙述杀人和喝人血的情况:“在巴拉德山谷,他们在早上四点就包围监工的房子,房子里七八个白人还在梦中,却全部遭到野蛮杀害,他们甚至还把人血和朗姆酒掺在一起喝下,他们在伊舍和其他地方制造了同样的悲剧。
他们还纵火烧毁了房子和藤条。仅一个早上,他们就屠杀三四十个白种人,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
上述关于食人族的描述可谓恐怖至极。然而“世界上是否存在食人族”,至今仍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自 1979 年威廉·阿伦斯(William Arens)发表《吃人的神话》开始,西方学者对“食人族”及“食人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布雷迪(Brady1982)、李驰(Leach1979)、布朗与图金(Brown &Tuzin 1983)、奥斯本(Osborne1997)、休姆(Hulme1998)、戈德曼(Goldman1999)、普尔(Poole1999)和康克林(Conklin2001)、林登鲍姆(Lindenbaum2004)、加 纳 纳 什 · 奥 贝 赛 克 拉 ( GananathObeyesekere2005)等人,甚至为“世界上是否存在食人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争。②实际上,与其争论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食人族部落,还不如讨论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屿土着是如何变成食人族的。也许,分析食人族传说与大英帝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关联,比寻找食人族的蛛丝马迹的物质证据更有意义。
二、“食人族”的修辞表征
日本学者石川荣吉认为,欧洲人在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终于走出过去比较“闭塞”的生活,开始从欧亚大陆的西端向其他地区流散和移动。他们常常将非洲人、新大陆人、大洋州人和东南亚人看作“野蛮人”,并把他们所见到的与他们自身社会极不相同的社会称为“野蛮社会”。
石川荣吉这番言论道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食人族(Cannibal)一词进入欧洲语言系统以后,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前见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形成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从英国社会对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地区的想像来看,他们将这些岛屿土着想像为茹毛饮血的食人族,而想像者“我”或“我们”却是举止文雅的欧美白人,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等级秩序,即土着居民—有色人种—异教徒—野蛮落后—未受教化/欧美白人—基督徒—文明高雅—文质彬彬。由此,“食人族”作为欧美白人对海岛有色人种的想像和言说,是欧美白人从本体论上对本土以外的他者身份的一个界定,无论在人种学、宗教学或社会学意义上,形象制作者和将被制作者都不在一个对等位置。
在“制作者——食人族——被制作者”镜像关系中,“食人族”作为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屿土着的指涉符号,不仅体现了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还反映了形象制作者的欲望、心理和意识。正如形象学理论所言:“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被制作出来的‘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某种补充和延长。‘我出于种种原因言说‘他者’,但在言说的同时,‘我’却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否定了‘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
上述爱德华兹在《英国在新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历史、内政和商务》中描述的“食人族”杀人场景,其实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1760 年,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发生一场奴隶反抗斗争。黑人后裔在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起义的奴隶并不满足获得人身解放,还想“吞噬”那些奴役他们劳动的压迫者,的确也有一些白人在这场起义中失去了生命。爱德华兹描述这次令人惊悚的食人盛宴,从侧面反映了英国民众对海外异教徒的恐惧心理。豪维特在《殖民地和基督教》中对此有着深刻认识:“长期以来,我们用虚假的论调来讨好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文明的、信奉基督的民族。我们谈到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民族时,认为他们是野蛮的和不文明的。我们对印第安人裸体战斗时发出的呐喊,以及食人族可怕的宴会感到颤栗,祈祷自己避开这些灾难。”
这样,在帝国海外扩张和征服过程中,凡是不愿臣服于帝国统治的异教徒都被视为“邪恶的”,“食人族”便成为对帝国事业具有潜在威胁力的象征性符号。学者凯·斯卡弗在论述澳大利亚历史时分析过当地“食人族”的由来:“在殖民地时代的最初二三十年里,澳大利亚当地报纸很难发现土着食人的描述,然而白人殖民者大规模侵入澳大利亚时,由于受到当地土着的持续反抗,19 世纪二十年代晚期,悉尼报纸开始登载白人目击土着吃人的一些事件。”也就是说,“食人族”传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根据帝国的实际需要被制造出来的。
传教士热衷于描述食人族故事也并非偶然现象。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就打着传播基督教的旗号,第二次驶往美洲的船队带有十多位西方传教士。此后,欧洲人在宗教情绪感染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和拓殖行动,其中许多人兼有传教士和殖民探险者双重身份。由于“食人族”具有野蛮、凶狠、不开化等特点,传教士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拯救”他们的灵魂。学者指出:“对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文化而言,‘食人族’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他者形象。1890年,爱丁堡杂志的一个作者在查阅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文献后承认:他们大脑中的食人族与其想象的野蛮和粗俗行径相联系,与比畜生更低劣的习惯和容貌相联系,与最堕落的迷信相联系。这些无法形容的野蛮行径成为这一时期欧洲传教提供了强有力证据。”
一些到达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屿的传教士在日记、游记、信件和着作中描述食人族,其深层原因在于通过渲染当地的恶劣条件和食人族的野蛮恐怖,表明他们海外宣教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取得国内政治、经济和宗教力量的支持。正因如此,从 18 世纪 90年代到 19 世纪 50 年代,许多传教士曾亲身经历波利尼西亚食人族,传教士成为虚构的食人族故事的主要编造者。
另一方面,传教士关于食人族的生动描绘又进一步激发英国民众的“拯救”意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纷纷走出国门,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基督教传播和帝国海外扩张事业。针对传教士日志和信件中关于“食人族”的夸张描述,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在南太平洋岛屿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曾在小说《泰比》中描述过食人族部落——泰比人。他却严厉斥责传教士编造食人族故事的险恶用心:“传教士倾向将异教徒描写成野蛮不堪;即便对最无害的迷信仪式也极尽诋毁之能事。事实上,食人风俗并不普遍。但传教士竭力渲染此事,以至于有人将传教(missionary)与吃人(cannibal)联系在一起。传教士的实际作为让人以为,‘相较于异教徒对原罪的无知’,欺压原住民的残暴行为是可以赦宥的小恶。传教结果与其理想背道而驰。”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清楚地反映了“食人族”符号的制作过程。主人公鲁滨孙在并未看到食人族的情况下,就认为自己要离开绝望岛、回归正常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弄到一个野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一个被其他野人带来准备吃掉的俘虏”。
果不其然,鲁滨孙真的从食人族手里救下了“星期五”,梦的真实性最终被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然而生活常识告诉人们,一个人是无法准确预知将来发生的事情的,鲁滨孙的梦越真实就表明故事的内容越虚假。张德明教授这样分析食人族与鲁滨孙做梦的关系:“对鲁滨逊这个西方殖民者来说,梦先于现实,文本先于经验;对他者的想像先于与他者的实际接触。小说中写到的食人部落其实不存在于现实中,只是存在于作家的梦境、想像和‘前见’中。”
进一步说,笛福在作品中塑造的食人族形象植根于欧美白人的经验中,是西方殖民者心理潜意识的产物。由于西方语境中的非西方人常被西方人用某种修辞来表达。神话、象征、隐喻和修辞手段便成为殖民话语表达目的重要方式,[20]“食人族”作为一种指称“他者”的象征性符号,是英国公众对待他者的思想与情感的混杂物,也是帝国文化精英为国家海外事业精心炮制的一个修辞性表达。不管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民的心理感受如何,“食人族”的帽子还是牢牢戴在他们头上。他们试图拿掉这样一顶名不副实的帽子时,才会发现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三、食人族与福音书
在帝国的知识结构中,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屿土着是令人恐怖的“食人族”,是亟待他们前去拯救的对象。有趣的是,当地土着也一度怀疑踏上他们岛屿的白人传教士会吃人,以至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跟他们交往。经过多次接触以后,斐济土着才逐渐改变原来对待传教士的敌视态度。当地酋长将传教士留在自己身边视为一种荣耀。按照传教士的说法,他们也只有留在酋长身边才不会被人杀死或“吃掉”。那么,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屿土着果真是食人族?英国传教士在这些地区传播的又是怎样的“福音”?
斐济酋长塔克姆布(Thakombau)是南太平地区着名的“食人族”首领。在英国传教士着述中,他与当地其他酋长一样野蛮残忍,都将杀死、吃掉敌人视为自己至高无上的特权。传教士瓦尔特·劳瑞(Walter Lawry)如此评价这位斐济酋长:“塔克姆布拥有绝对王权,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从总体上看,他对我们在当地传教比较支持,但他坦承自己讨厌引进教皇制度,更喜欢战争和食用那些战死者身上的肉。”
塔克姆布是一个聪明、固执而又讲究实际的酋长。十五年来,英国传教士威廉姆斯(Willianms)和亨特(Hunt)千方百计劝他皈依基督教,不断向他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一些船长和商人也希望他放弃落后的生活方式而做一名基督徒,可塔克姆布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1854 年,塔克姆布在基督教精神的长期影响下,特别是在经济上获得传教士的帮助以后,他终于宣布斐济从此皈依基督教。塔克姆布还遵从传教士的劝告,不再杀死、吃掉俘虏和绞死寡妇。1874 年,斐济因此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海外殖民地。显而易见,不是所谓的“食人族”吃掉了西方传教士,而是以“食人族”闻名的斐济最终被大英帝国所吞噬。
加勒比岛屿居民原来信奉原始宗教和自然宗教,但随着英国及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入,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巴巴多斯为例,“1624 年英国人宣布占有该岛,1626 年,第一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其中伴随着为这些移民服务和传教的英国圣公会牧师。1637 年建成了 6 座教堂和 10 座小教堂。1824 年成立了巴巴多斯主教区,是英国圣公会西印度群岛教省的组成部分”。
英国殖民者用利剑打开加勒比地区的大门,传教士则通过基督教从精神上驯化加勒比人。“南太平洋是传教士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在此地区,传教士是最受争议的人物……传教士坚持原住民信仰仪式必须连根拔除。”
在殖民者的威逼利诱和传教士的影响与驯化下,南太平洋和加勒比岛屿土着逐渐改信基督教。反过来,基督教在南太平洋及印第安岛屿的广泛传播,又使得大英帝国在这些地区的贸易和殖民得以顺利展开。基督教宣扬的“容忍”“宽恕”和“爱仇敌”等伦理观念,特别是《马太福音》“山上宝训”中宣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等论调,客观上缓和了岛屿土着与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英帝国占有和统治这些地区起到了润滑剂作用。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入侵,加勒比地区土着居民的原始宗教和自然宗教消亡殆尽。然而这种文化输入并非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而是强势的现代文化对弱势的土着文化的清除和蚕食。土着居民在认同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也即认同了大英帝国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和统治。从此意义看,西方传教士在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地区传播的所谓“福音”,其实是一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殖民运动。
从本质上看,食人族传说与殖民时代的基督教传播有着相似的政治功能。按照霍米巴巴的理论,“食人族”这种“固定性概念”是殖民话语在他者文化意识建构中的一个显着符码。“食人族”一词作为殖民话语中文化/历史/种族差异的符号,是表征的一种矛盾形态:既表示混乱无序、堕落和恶性循环,又表示不变的秩序。同样的,作为推论的主要策略,其文化认同方式变成了刻板的模式。
也即是说,英国社会通过对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地区岛民的“食人族”想像与言说,试图通过刻板符号将土着居民的社会身份永久地固定下来,通过强调他们的野蛮残忍、愚昧落后以及令人不齿的恐怖行径,塑造和强化这些地区土着居民的自卑心理,促使他们意识到罪恶而憎恶自己身份,从而在精神上向帝国的殖民者屈服。从这个角度看,食人族传说其实是殖民者强加在被殖民者身上的话语暴力。
一些英国作家并未亲身从事海外殖民和征服活动,但正如传教士的宣教所起到的作用一样,他们也从意识形态层面参与了大英帝国的话语建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手法叙述自己亲眼看到“食人族”吃人过程,使食人族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笛福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急遽扩张的时代,此时英帝国的民众都对未来和海外世界充满自信,笛福的小说激发了英国民众向外殖民的欲望。正如马丁·格林所言:“《鲁滨孙漂流记》这类冒险故事的作用不容轻视,它们一遍又一遍地通过主人公的海外历险标榜英国人的‘勇气’‘力量’,令许多年轻的读者感到热血沸腾。这类故事既是英国海外殖民的真实写照,又反过来刺激了英国人统治世界的欲望。”
许多像鲁滨孙一样胸怀激情和梦想的青年人,毅然投身于帝国主义的海外冒险事业。作品结尾,鲁滨孙带着他用基督教文化加工的产品——“星期五”返回大英帝国,向世界展示他对“未开化”民族驯化和改造的成果。在布兰坦的小说《珊瑚岛》中,作者通过儿童彼特金之口赤裸裸地公开了占有企图,“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岛。我们将要以国王的名义占领该岛”。
同时,作品还强调基督教文化对于海岛土着的拯救功能。作品中信奉基督的虔诚的印第安妇女,长期处在部落酋长的残酷压迫下。作品结尾,这位“食人族”酋长也由于被“福音书”驯化而信奉上帝,与当地居民一起烧毁海岛上所有木雕偶像。作品以历险故事的形式倡导岛屿土着居民要崇信基督、服从大英帝国的管理与统治。由此,文学作品描述的“食人族”故事也实现了从文化叙事向政治功能的转化,正如赛义德(Said)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与小说相互扶持,阅读其一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涉及其二”。
希腊语的食人族 anthropophagy 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 Cannibal 却有着鲜明的种族和意识形态色彩,Cannibal 替代 anthropophagy 一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词义替补或淘汰。这个词语更迭与西方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联系在一起,是西方国家对不同文化圈中他者身份的一个界定,反映了西方殖民者对未知世界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复杂心理。“食人族”传说在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最为丰富,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食人族”传说与帝国的海外扩张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与殖民时代向外传播的基督教及其他文化产品一样,都以隐晦的方式为国家的海外殖民事业服务,因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能。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帝国在统治过程经常运用文化霸权的形式,通过知识精英等推广帝国的政治、伦理及文化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式”。
英国作家、传教士和史学家等将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屿土着想象成低等野蛮的形象,“这样,殖民征服和殖民侵略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存在的同时,被殖民者实际也就被作为不可更改的‘他者’形象而固定下来”。相对于“食人”土着的野蛮和残忍,帝国对南太平洋及加勒比岛屿的侵略与统治不仅显得天经地义,还会被赋予“正义”“拯救”等伦理和政治含义。
参考文献
[1] ARNOLD A. A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Caribbean[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3.
[2] LONELY P. 新西兰[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4.
[3] COOK J. Journals: 3vols[M]. Beagle Hole J C, New York: BoydellPress, 1999: 163.
[4] BRANTLINGER P. Missionaries and cannibals in nineteen-century Fiji[J].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006, 17(1): 24-25.
[5] 丹尼尔·笛福. 鲁滨孙飘流记[M]. 郭建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62-177
.16、17世纪,罗马教廷为阻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大陆发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除组织宗教战争外,教皇重用耶稣会发动宗教论战。在这种宗教改革的大语境下,戏剧渲染新教与罗马教廷的对峙,介入到宗教改革运动之中。①当时...
道德说教是18世纪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奥斯丁生于18世纪末,深受18世纪道德小说的影响,是一位公认的道德家.ThomasRodham认为,她小说中的每位人物都具有道德说教的作用.然而,奥斯丁作品中的道德观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模仿,因此,不像理查逊的《帕梅拉...
《藻海无边》是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的代表作,被称为《简爱》的前传。简里斯把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没有详细讲述的疯女人的故事再现,把疯女人的形象丰富化。自问世以来,此小说引发了研究者们浓厚的兴趣。他们或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或从叙事策略方面、...
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干将特里伊格尔顿对美国文学批评家耶鲁四人帮之一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向来持有很大的意见。早在1983年,伊格尔顿在其以论为立、轰动一时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就对诸多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家作了史论结合而且针锋相对的批评...
比较文学具有跨越性、可比性和文学性, 那么我们研究的范围就可以扩展到两国或多国, 两民族或多民族。...
英国着名作家约翰厄斯金汉金斯从意象学的角度把威廉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的花园概括为三种类型:大地花园人体花园和大宇宙花园。大地花园即现实花园,是一种宇宙秩序的缩影。人体犹如有灵魂的花园,创造这种人体花园的造物主是令人惊异的。汉金斯还...
乔治奥威尔是英国着名小说家,其代表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影响久盛不衰,但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却少人问津,尤其是他1935年发表的第二部小说《牧师的女儿》,国内外真正阅读和研究过原着的人少之又少。这部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主人公...
幽默是一种文化、是一门艺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看似寻常、无所不在,却又抽象、难以用精确的语言给出最恰当的定义。林语堂先生曾这样解释幽默,幽默是一种能激发起人类心理某种情感的智慧,某种在对逻辑性进行适当调控后对现实进行某种形式的加...
英国着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出版于1814年,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女主人公范妮普莱斯因家庭贫困且人口众多,在十岁时被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姨父姨妈托马斯伯特伦爵士夫妇收养,和表哥表姐一起长大.在庄园里,只有埃德蒙表哥对她关心照顾,众人对她除...
中文摘要李彦是加拿大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都以女性作为关注对象,描写她们在历史政治困境或移民现实生活中的挣扎与反省,从迷失到成长的心灵蜕变。本论文以李彦的中文小说(包括英文改译为中文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反思、婚恋关系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