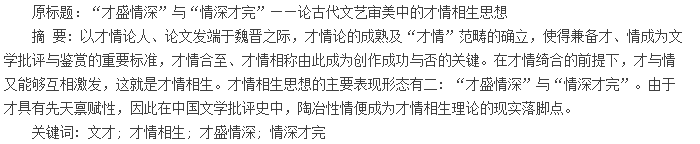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才、情是同源的。才本自个人体性,《荀子·正名》云: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为天赋,即是才性,其本然的蕴育和运用便衍生出才能之意。情同样与性相关,《礼记·乐记》论情欲之所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依据朱熹的阐释: 人之初始心性平静,得乎中和。及其感于物而心摇动,性中本有的欲望便逐渐显露,善恶由此而分。其中的性之欲就是所谓情; 于物感知且心生好恶,也同样是情。
可见情本来也源自性,所以《荀子·天论》中提出了人有“天情”,杨倞注曰: “天情,所受于天之情。”陆机《演连珠》中便有“情生于性”之说。情出于性,也是具有天赋性的,正如《礼记·礼运》所云: “何为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生而为人,备此人性,便有此天情。因此古人言情,或曰情性,乃是从末及本而言; 或曰性情,乃是从本及末来说。二者意指没有区别。若论及才、情、性的关系,朱熹说: “问情与才何别? 曰: 情只是所发之路陌,才是会恁地去做底。”又云: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恁地者。情与才绝相近,但情是遇物而发,路陌曲折恁地去底; 才是那会如此底。要之,千头万绪,皆是从心上来。正如黄宗羲的解释: “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广言之曰气、情、才,岂有二哉? 由性之流露而言谓之情,由性之运用而言谓之才。”
才情皆从心上来,才情皆出乎性,情是心动及如何运动,才是情如何呈现与表达。三者的同源性以及体用之表现形态从哲学上已经确立了。才与情之间关系密切,呈为一体,互相影响。
从文学理论认知考察才情的关系,班固早就从“感物造耑”论“材智深美”,以能感而生情者即为具备文才,情直接关系到才; 借物引情之兴必须要通过托物寓意、随机成咏之才转化为艺术,才与情之间又有着彼此的需要。以才、情论文在魏晋时期实现了彼此的融合,从此才与情在审美理论中以一种密不可分的姿态出现,且形成了后世普遍应用的“才情”范畴。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而言,后世所谓的才情论,仅仅是一种泛而言之,它实则包括同时以才和情从各自维度论文和以“才情”范畴本身论文。
才情论的成熟及“才情”范畴的确立,使得兼备才、情成为文学主体素养与文学批评赏鉴的重要标准,才情融美、格意朗畅、才情澜翻或者极才情之变化等成为批评中的常调。即使汤显祖所谓的“神情合至”,虽然有着殷璠“神来气来情来”的痕迹,但神为神思,出乎性灵,本来就与才相关,因此所谓“神情合至”实则就是才情相合之意。
才情之合在以上所论融合之意以外,还有一个和谐、相称的要求: 各自呈现的分量相称,各自表现的形态相称,各自在作品之中互不压盖等等。朱晞颜《跋周氏埙箎乐府引》云:余谓才情韵三事惟长短之制尤费称停,大抵才胜者失于矜持,情胜者失于刻薄,韵胜者失于虚浮。故前辈有曲中缚不住之诮。信哉言乎,杜子美诗云: “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减尽针线迹。”
才情偏胜皆为诗文之病,所以要如杜甫所云之“细意熨帖”,才情韵致各得其适,不至于偏失。明代文人论诗,往往如此提倡,有时批评诗歌之病,也以才情二者不能协调为口实,如王世贞批评岑参“才甚丽而情不足”; 黄汝亨盛赞屈原“郁结于气,宣畅于声,皆化工也”,随后称“宋玉而下,有其才而非其情,贾谊有其情而非其才”。以宋玉、贾谊于才或者情上的欠缺,凸显了才情兼备又相称合的屈原之贡献与成就。毛先舒论词也持这个观点,有人以为词要本色,“才藻所极宜归诗体; 词流载笔,白描称隽”。
但毛先舒以为: “大抵词多绮语,必清丽相须,但避痴肥,无妨金粉。唐宋以来,作者多情不掩才。譬则肌理之与衣裳,钿翘之与鬟髻,互相映发,万媚斯生。何必裸露,翻称独立?”只要不成痴肥,粉妆玉砌、艳辞丽藻并不为病。唐宋以来之作,多不以重情为由掩饰文才,所以情才相称。而一意白描,就如同美人裸露肌理而不着衣裳、仅挽鬟髻而不施钿翘,没有互相映发之美。
在才情绮合、才情相称的前提下,才与情又能够互相激发,这就是才情相生。即天赋之才深厚,其唤醒心灵、激发情怀的禀赋往往异乎常人,其对情思的描摹必然深厚感人; 具有深情者,方能全面展现本然的文才。从美学观照而言,才与情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世说新语·文学》中已经获得了初步总结: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 “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其中“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或作“文于情生,情于文生”。所谓“文生于情”,意思是情为诗文发生的源泉。这一论断包含两个指向: 其一,情并非直接生发文章,因此其中含有情感深厚则引发文才现身之意; 其二,文才现身,与情绮合,则诞生动人心旌的文章。“情生于文”,本意是讲文人所创作的作品能够包纳众情,且能诱发读者深情,“文”之中包纳了成文的才能,因此“情生于文”已经隐约表达了才对情的激发。当然,这个论断也有两个指向: 其一是由作者自身而言,其文才创造了如此深情的作品; 其二是由读者而言,在对作品的赏鉴之中,激发了其同情。
但无论如何,都有文才与情怀生息关系的表达。古人才情相生之论中,多兼容以上指向,即主体之才之情,既能够激活主体之情之才,同时又能够将其赋显于诗文,进而感染读者。以此为基础,后人论才情相生的关系集中在两点上: “才盛情深”与“情深才完”。
一
才情相生首先体现为天赋之才深厚,其唤醒心灵激发情怀的禀赋往往异乎常人,其对情思的描摹必然深厚感人,此为“才盛情深”。后世相关表述不一,但归趣一致:或曰才盛则情赡。屠隆《冯咸甫诗草序》云:夫声诗之道,其思欲沉,其调欲响,其骨欲苍,其味欲隽,而总已归于高华秀朗。其丰神之增减,大都视其材矣。材多则情赡而思溢,光景无尽; 材少则境迫而气窘,精芒易穷。此其大较也。
“赡”为丰富广泛,才多则主体神思洋溢多姿,作品情感也丰厚富赡; 才少则无论人、文,左支右绌,神气易尽。袁枚延续此论,明确提出了“才盛情深”:才者情之发,才盛则情深; 风者韵之传,风高则韵远。意思是说: 才为情发动与表现的资源,且才之大小与情的深浅密切相关; 风( 相当于主体的气骨) 是韵传播塑造的力量,所以风高而韵能悠远。
明清之际一些文人径直标榜: 文人之情生于才。钟惺评卓文君《白头吟》“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文君此时为此语,若其初奔,止爱相如之才,非必以其为一心人也。然有才人亦自有情。”谭元春从本诗整体而论曰: “有如此妙口妙笔,真长卿快偶也。不奔何待?”又云: “有一种极难为长卿语,长卿不得不止。文君之奔与妒,生于才耳。”奔为情,妒忌也是情,两情之浓烈,熔铸为《白头吟》,深情、丽文皆生于才,所以叫做“有才人亦自有情”。丁澎评《摄闲词》则云:慎庵词如芙蓉出水,秀色天然,晓黛横秋,苍翠欲滴。时而慷慨悲歌,穿云裂石; 时而柔情纷绮,触絮粘香。偶携一册于西湖夜月,倚声而歌,不觉驱温韦于腕内,掉周柳于毫端。文人之情生于才,有如是乎?
作者之才,可以焕发自我性情,也能使得作品中情意盎然,从而引发读者兴会,这就是“文人之情生于才”。近代何炳麟论《红楼梦》称,“情生于才,才大则情挚”,“无才则无情,无情者不可与读天地间妙文”,必有才情者方能赏才情之作。笤溪生论女子也认为“长以才者必有情”,二人可算是谭元春隔代的知音。
或曰各极本量则不失性情。本量是禀赋、天赋、天分的意思,与性情相对而言则指向个人的才性。此论出于沈德符《马仲良诗集序》,文中他批判了明清之际两种不依自我本量创作的倾向,其一为以七子为代表的拟古诗派,其二当为晚明娄东诗派之余脉。他认为七子等人依循前人有偏,娄东诗派习为靡丽也有其偏,二者对比,当为五十步笑百步:明兴以来,称诗至弘正之际而李何出,范永徽开元之貌而俎豆之。由是贤愚争奋,巧拙共赴。盖摄持世界者近百年而渐有腹诽者。至近日则反唇甚口,欲尽扫而空之,以返于性情。夫倦游京洛,乃贵林丘; 饱饫牲牢,必珍蔬笋: 理势然也。然讳江笔之暮年,贪薛笺之小样,盎盆堆景,猿鸟哀鸣,可永永作耳目供乎? 盖前之为庄语者,多易京楼上妇人,即习大声闻数里,而听者嗤其非质。今为微言之人,又多江东伧父,学王谢侬音细唾,有识者肯遂以风流相许乎?
后者对前者的反拨,仅仅是口味上的喜新厌旧。二者一徇于唐人一维,造作而成高声大气;一拘于习气,刻意塑造与风尚的不同。沈德符以为二者均没有极其本量,而是以不同的形式落入格调规限,从而将才情规范化了。他赞赏马仲良的作品: “恣意匠之所经营,恣情景笔墨之所称惬。举百年中人心慕手追者,并其阳诋而阴事者一一罗之纸上。词能达意,肉足罥骨,大抵眼有镜,腕有力。以故曲折变幻,于此道庶几无遗憾。”这种创作之所以值得称道,因为它没有模式化,而是“即有相羡妒者亦安能效罗什而饭针”的才情所寄。由此沈德符推出了他的“各极本量”而“不失性情”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核心在于各尽各才则各见各情:
首先以唐人论,其成就源自各极本量: “燕许簪裳于观阙,李杜亢壮于江湖,以至钱刘之流连光景,温李之描画闺奁,总能自以全副精神,开拓阵势,胸无伏匿之物,喉无嗫嚅之音。譬之群饮,然深浅不同,各极本量而止,夫是之谓不失性情。”各极本量便是不失性情,也就是尽我之才而不羡他人之才便能展现我的性情,唐人之所以成功,根源在此。
其次论明人之出路: “耳食之徒,每深文于唐中叶,若赵宋则交喙詈之。夫唐宋者人也,性情亦何唐宋之有! 倘以万历之人发抒万历之性情,试按其语,乃得唐人之未曾有与宋人之不能有。是亦诗之跻巅造极,观于是乎止矣。”
马仲良便由此入手,加以其人“具异性兼有深情”,因此但能尽自我异性之量,而深情自显。或曰笃于根柢而后可以言情。翁方纲《月山诗稿序》云: “传曰: 诗发乎情; 又曰: 感于物而动。夫感发之际,情与物均职之,而情与物之间有节度焉,有原委焉。溺而弗衷者非情也,散而弗纪者非物也。”诗虽然由情而生,但对诗而言,审美意义的情与物又皆有一定的要求: 物应该是为情摄取的意象,不当是自然状态下散漫无纪的物象,这样诗人无从下笔; 而情则当真挚由衷,伪饰而成者非情,同时还要避免耽溺其中,如此的话便是物欲而非源乎本心的审美之情。因此,论情不得不追溯于天性、本性这个才与情共同的源头,要求诗人禀性能够承担对情的这种保障,同时还要具备将物色、物象升华为意象的能力,所以翁方纲借月山之诗论道:
寻常景色悉为诗作萌拆,凡有触于目者皆深具底蕴焉,非物自物,而情自情也。故谓诗者实由天性忠孝,笃其根柢,而后可以言情,可以观物耳。所谓“笃其根柢”实则是说“笃其才性”,只有具备此才,方可总持物象,使得散而弗纪者建立艺术的逻辑; 而后可以言情,可以观物。翁方纲如此论诗,便包含了创作之中才对情的统摄与引领。以上所言皆表达了“才者情之所由茁”的涵义,以才为情萌发的根源; 与此相反,对创作主体而言,“无才则情滞”。可见,顾贞观所说“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绝非文人的自饰与倨傲,正是“才盛情深”之意的具体表达。
二
在才情绮合的前提下,才情相生又表现为情可以直接影响到才的生发运使,此为“情深才完”,才完即才可尽其本然之意。相关论述较早见于《文心雕龙·神思》: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虽然刘勰这里强调的是创作之前的兴会,并与实际创作之际“半始心折”的状态形成对比,但仍然是对艺术创作情态的逼真描述,尤其激情充盈、兴会空前之际才思来会的概括,颇得文家三昧。这种状态与才气关系中“气全才放”的理路甚至内涵都是一致的,如刘勰所提倡的“入兴贵闲”说与其他兴会手段,实则皆属于激情的培养,一旦修养饱满而机键开启,则才自然现身。
这种因情的激荡促使本然才华洋溢而出的现象被独孤及称之为“才钟于情”,其《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论诗,先道其有赖于天资:“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泳风骚,宪章颜谢。至若丽曲感动,逸思奔发,则天机独得,非师资所奖。”又由其才之发挥而论: “每舞雩咏归,或金谷文会,曲水修禊,南浦怆别,新意秀句,辄加于常时一等。”作者将这种特定情境下的兴会淋漓、才思横溢现象归之为“才钟于情”。“才钟于情”的含义是: 才凝聚于情,才因情而焕发洋溢,有激发主体情致勃勃的机缘就会有这种新意秀句加于常时的景象。
到了明代,谭元春将这种现象名之为“才触情自生”。他自道其诗学追求,首先必须真挚自然,不徇于人亦不徇乎己: “幸而有不徇名之意,若不幸而有必黜名之意,则难矣; 幸而有不畏博之力,若不幸而有必胜博之力,又难矣; 幸而有不隔灵之眼,若不幸而有必骛灵之眼,又难矣。”能有此心态,然后可以驰骋: “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 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 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 才不由天,以念所冥为才。”
“念所冥”为神思所至; “才不由天,以念所冥为才”则神思所至、神情关合之处,其才驰骛; 而不是不顾及情思之质地,一任其才之放肆。这个论述体现的才情关系便是情至则才至。《汪子戊己诗序》中谭元春对这个思想有更明晰的表达:诗随人皆现,才触情自生。……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 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而因以候于造化之毫厘,而或相遇于风水之来去,诗安往哉?才因与情遭遇而激发,情为才提供资源与机缘,才则由此具有了一种自我生发的机制。而才的运使最终要“听我胸中之所流”,情至,才则现身; 至于所谓“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则是强调此情书写又受到才思的自然引导与限制。
至清代,张际亮则将才情之间的这种关系概括为“情深者才完”。其《答姚石甫明府书》云:凡为诗,须知道神骨、才情、气韵。夫无神则骨轻,无骨则神漓; 无才则情滞,无情则才浮; 无气则韵薄,无韵则气粗也。诗之至者曰入神,其骨重,则神愈永也。曰雄才,其情深,则才始完也; 曰真气,其韵高,则气乃固也。六者具备,此盛唐大家之诗也。骨、才、气有余,而神、情、韵不足,此宋大家之诗也。
才气、情韵、气骨皆不可缺,而其中才情之间的关系是: 无才,于主体素养而言则情思情绪便凝滞不活,溺于俗常功利得失,不可能转化为刻骨铭心的幽情微绪; 于创作而言,便难以传递心绪之幽眇。无情,于主体素养而言则气质轻浮而不凝重,于作品而言便浮华矫饰而不周密。所以才有“其情深,则才始完”的说法。“情深才完”还体现为下面一种价值取向:文学创作必先有真情然后方谈得上才华的施展。凡是论文首论情者,往往都是从这一点立论。《文心雕龙·情采》云: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
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 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文章以“述志为本”,真情真意是首先要表彰的,因此刘勰称“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所有诗文之文采,必有待于情性,才有价值,此所谓“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于情性”。此先言情真情深。继而言文: 能“文”者赖乎才,有此才方可实现文章的“辨丽”,但所有这一切必须本于情性,“为情而造文”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千载不易的准则; 而“为文造情”则由于采滥忽真,成为历代警惕的弊症。
又如谭元春批评李攀龙等人之作,缺的是情,不乏的是抑扬铿锵之格调声韵,诗作如同土鼓,可观而不可击。出路在哪里?夫诗道最为情韵,情之所至乃能日新而不可穷。然惟绝有情人,为于音影之外,别具英变,以转未坠之线。故情不能至,诗亦不至焉。要超越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情至,随后再合以“别具英变”之才,则能日新不穷。
三
才是禀赋,不可改变; 具体到个体之情,则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杭世骏说: 人有性、有情、有才,性与情生人所同,而才则为其所独。就情而言,虽然古代哲学追根溯源至乎性,人从本质上具有七情之禀赋; 但无论现实人生还是文学创作,主体之情与文学表现之情都是一个建立在七情基础上的可变量,因境遇而异,因修养而变,所以章学诚说: “情本于性,天也; 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
如此天人之合,于是千丝万缕、千头万绪、千形万状,甚至千奇百怪、千回百转,所谓心有千千结皆不足以尽情之万一,所以文人才子本身并不乏情,但创作之中却经常表现以下三种弊端: 或者寡情,或者滥情,或者矫情。寡情者即应酬羔雁之作,文学创作成为礼尚往来或者谋于稻粱的工具; 滥情者即放而不收、纵而不回、荡而不返的率意与粗粝; 矫情者即是虚浮应接之中的虚情假意。从纠偏的意义而言,寡情者需要矫之以深情,矫之以深情者,意在激活才的灵动,尽主体文才之本然,从而规避机械、可复制的艺术生产。
而滥情矫情者则需要养之以性情,使之复归真诚。于是,才情相生之论中,无论“才盛情深”还是“情深才完”,对于才子文人这些并不缺乏文才的主体对象而言,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最终往往归结于情( 或者性情) 。而这种情的归结不只是对情思敏锐、情怀幽微、情感多兴之禀赋的提倡与张扬,更主要的指向还有自我之情的修养。因此,一如才不可易而气养自我,自我之情或者性情修养成为才情相生关系理论教化于人的现实落脚点。这种取向,既有才不能易而择取人工着力点的需要,也有儒家发情止礼思想熏陶之下的集体就范。
历代文人多论性情,着眼点便在于此。屠隆在密集论述才的同时,就明确提出过“诗不论才而论性情”的观点,《李山人诗集序》自道其由: “故诗不论才而论性情,亦存乎养已。”诗歌论性情,因为性情可以通过人工培养、锻炼,也能够在作品之中体现这种涵养所得,属于可把控的范畴。
屠隆的文学批评中论性情者极多,《唐诗品汇选释断序》云: “夫诗,由性情生者也。”《论诗文》亦云: “造物有元气,亦有元声,钟为性情,畅为音吐,苟不本之性情而欲强作假设,如楚学齐语,燕操南音,梵作华言,鸦为鹊鸣,其何能肖乎?”又认为所谓诗文传世实际上“匪其文传,其性情传也”; 以唐诗为例,之所以可以万代传诵,“匪独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则其生平性情者也”。屠隆论性情主要集中在情感的真实上,《唐诗品汇选释断序》云: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乐,和声能使人欢然而忘愁,哀声能使人凄怆恻恻而不宁。人不独好和声,亦好哀声。哀声至于今不废也,其所不废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华绮丽、优游清旷,盛矣; 其言边塞征戍、离别穷愁,率感慨沉抑,顿挫深长,足动人者,即悲壮可喜也。
唐诗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主要是由于诗歌真切传递了诗人的悲喜。陈仁锡论文章,同样主张以性情为贵: “文以性情贵,得百才士不如得一性情之士。何以知性情之士? 其文不违于性情者是。”有如此性情,便可以体现在文章之中,由此决定作品的身价,并与作者形成对应,使人瞻顾而得其真精神:凡人一生作文,有一语与性情相近者,此一语必不朽; 一生行事,有一事与性情相得者,此一事必不朽。又当锁闱拈题构思苦索之候,如有一股一句快舞性情,必快主司观览。何也? 有性情斯有奇正,有步骤,有起伏,有位置,有开阖,有结构。大都其人面目正,脉理正,文体自正矣。
此文也,孔子思狂狷,狂者常简,狷者有所不为。简也,有所不为也,皆情性之极便,而乡愿有大大不便者矣。乡愿痛仇狂狷,无他焉,衣冠易绘,精神难貌也。当其时既过我门,将入我室,有一士焉,神严气立,挺血性以寒之五步之内,嗟乎! 性情足恃哉。今乡愿伪种,尽浸淫于文章……以经术反对之,莫如先以性情正之。
文章但凡论其意义,首先必论其性情之真伪有无,因此宁狂狷其性也不可为乡愿。陈仁锡明论文以得性情为贵,包含以下考量: 性情可以修为、可以约束,得性情的文章因此可以正人心术。翁方纲也由这一理路论徐桢卿。他从《迪功集》所达到的造诣说起,以为其作披沙多而拣金少,所以然者,其所师资者李攀龙不能辞其咎:“徐子知少作之非,悟学古之是,此时若有真实学古之人,必将引而伸之,由性情而学问,此事遂超轶今古矣。李子本具蹈袭之能事,以其能事贶其良友,以如此清才而所造仅仅如此,为可惜也; 以如此能改之毅力而所改仅仅如此为可惜也。”
徐桢卿受李攀龙等影响,虽以学古为名目,但最终走入拟古蹈袭,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性情入手。要由性情入手则不是习古人格调,以古人之性情为性情,而是从学问入手,在对古人的学习研磨中磨砺自我性情、发现自我性情、揣摩自我性情,由此才能从性情出发为诗,而非蹈袭。在同样具备才华的条件下,文人之间的优劣以情胜者为优,因为情胜可以见人性情之涵养。
所谓情胜,不是就某一文人而言,其情多于才,才与情不可能有这样的量化标尺; 而是指其情感之细腻、敏锐,或者一定语境下指其温厚和平较于他人更为突出,而在其人身上也成为主要的标志性素养。《修竹庐谈诗问答》对比朱彝尊与王士祯的诗歌创作:大率竹垞才胜于情,渔洋情胜于才。才胜者多外心,情胜者有余旨。朱虽广博,终逊一筹。二人比较,才胜者“多外心”,即指言不由衷的运才使气,掉弄机锋。而情胜者运情入诗,意旨有余。这种比量也是从情养而能正、才主放纵必有节制而言的。在文学尚才抑或尚情的问题上,本无多少歧见,多以才情兼美为最高标准,但文人们的通病恰恰在于纵才而乏情,情少之根在于荣利纷于外而天机铄于内,缺乏性情陶养,才既不能灵动,情也由此钝滞。性情之养与修身进德之养没有区分,又皆可纳入养气说的范围。由于处于立身的发端,加之随后附丽上道义等大话题,因而在一些文人的论说里,才情论中情或性情便因此成为首先考量的对象。于是有了后人以下论断:天下惟有真性情者乃能为大文章。昔左文襄有言: “世人统称才情,若人而无情,才于何有?”此语可谓千古名言……世之讲修身者不可不知此言,讲文学者尤不可不知此言。
孟子云: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又云: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情居才之先,情之挚者乃能善用其才。结合左宗棠之论,就本身不乏才华之文人论才情两端,则以情为主,以情为先; 既论文学,又及修身。由此反思文学史上性灵、性情之辨,便不难看出其中的用意,鲍鸿起曾论: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泽之以风骚、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辞意兼至,以求其合。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粪秽轻薄,流弊将不可胜言矣。正统文学理论承儒家诗学大义,以中和蕴藉、温柔敦厚为极致,自然格外强调情的修为与陶冶,以性治情而论性情。情本于性,才率于气,才情不离乎主体血气。如章学诚所云,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一任阴阳运使则人纵其情欲而无归,“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如此任心任情者即为性灵。
发乎情为人之所通,但能否止乎礼义则必有待于修为,持其情,约其欲,着眼点在于教化,这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主体素养理论强力干预的产物。此外,不主张一任才情鼓吹性灵,还有一个雅的门槛,意在防范粗疏甚至鄙俗。
参考文献:
[1]吴澄. 礼记纂言[G]/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陆机. 演连珠[G]/ /萧统. 文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379.
[3]朱彬. 礼记训纂[M]. 北京: 中华书局,1996: 345.
[4]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1994: 79.
[5]黄宗羲. 陈乾初先生墓志铭[M]/ /沈善洪,等. 黄宗羲全集: 第 10 册.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362.
[6]朱晞颜. 瓢泉吟稿[G]/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
[7]王世贞. 艺苑卮言[G]/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1007.
[8]黄汝亨. 楚辞序[M]/ /寓林集(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天启刻本)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毛先舒. 与沈去矜论填词书[M]/ /邹祇谟,王士祯.倚声初集(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屠隆. 冯咸甫诗草序[M]/ /白榆集(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龚尧惠刻本)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第三章陆九渊文艺思想的理论构成通过前文的叙述,已经对于陆九渊的主体思想有了大致的把握,也对其文艺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对于陆九渊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向来缺乏较为系统的整理。我们知道陆九渊的理论成就以心学为主要依托,对文、道、气都有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艺发展的转型时期。这可以从艺术类型与审美特征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说,秦汉艺术的主要类型是宫殿建筑、陵墓雕塑、汉画像石以及汉赋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艺术的主要类型则是音乐、绘画(人物与山水)、园林、书法、诗歌等;如果...
“文如其人”作为文艺欣赏的一种方法,古今中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有过思考,但其作为在中国有着千年历史的重大命题,古人有着非常思辨的看法。...
第一章陆九渊文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任何重要的哲学、文学以及文艺思想的诞生都不是偶然发生的结果,任何伟大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与整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陆九渊作为南宋重要的思想家,其独具一格的思想主张也一定与其生活的时代有着重要的联系。陆九...
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中的艺术思想与审美理想是当时背景下民族理想、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处于明中后期的中国在艺术上与思想上也正经历着艺术革新、思想解放的碰撞、荡涤与变革。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的自我批判总是在其自身尚未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的...
从文艺美学提出之时,作为跨学科、边缘学科的文艺美学,成为文学理论界争论的一大焦点问题之一。文艺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性学科,学科的归属是否妥帖,学科的研究范畴如何定义,诸如此类的学术问题至今仍无确切定论,而其探讨争论的过程却有助于我们对此门...
西蜀园林作为四川平原地区的地方性古典园林, 蕴含着丰富的蜀文化内涵, 同时又具有西蜀地域特色的文艺美学特征。...
方东美,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之一,作为现代新儒学代表,方东美学贯中西、自成体系,尤其在文艺美学思想方面,方东美更是成绩卓然。虽然我们看到的阐释方东美哲学思想的专着论文不少,但是,专门论述方东美文艺美学特色的论着并不多。方...
物感说是我国文艺创作理论的基础,是我国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的理论,后来的神思论、意境论是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张晶通过与西方文艺创作的神赐论、天才论、灵感论的对比指出:中国古代关于艺术思维或者说神思的来源、动因的论述则不然。它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
一、作为学科定位的争论文艺美学自诞生起,围绕它是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一直受到争论。在《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综述》中,龙辛总结了文艺美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四种观点:一是文艺美学是一般美学的分支;二是文艺美学是在审美关系中确立其对象与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