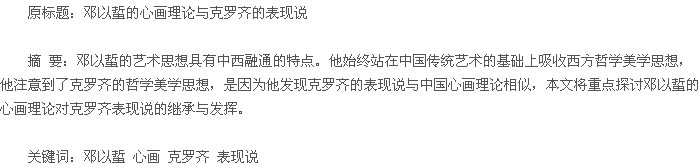
邓以蛰学贯中西,在其诠释与分析中国传统艺术审美活动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美学家的思想。在《〈艺术家的难关〉的回顾》一文中,邓以蛰明确承认其美学思想曾受到了柏拉图、康德、柏尔、叔本华、柏格森、克罗齐、莱辛等人的美学思想的影响。①但从总体而言,除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与历史辩证法对他影响较大外,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是显着的。这尤其表现在克罗齐“表现论”美学观对他的影响上。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
邓以蛰受克罗齐“艺术即直觉”的影响,将表现论的美学思想引入到中国书画理论研究中。直觉在克罗齐的精神哲学里,体现为关于个体的认识活动,并不出现在知觉层面上,在这里直觉也就与概念、逻辑框架、一切外在的物质世界脱离了干系。克罗齐强调艺术是“没有谓词的主词”,他认为:“这是没有理智关系的直觉。这是一首诗歌传达给我们的情感;它令我们广开眼界来看实在。我们永远不能用理智的词句把实在表达出来;只有把实在反复吟咏,即是说,把实在创造出来,才能把它据为己有。”
②克罗齐指出,直觉以无需依傍的表现方式表现所直觉的形象,并掌握这些形象,它凭着自己的特性就足以应付所承担的任务。他说:“没有在表现中对象化了的东西就不是直觉或表象,就还只是感受和自然的事实。”③要从个人的感受和自然的事实层面上升到直觉或表象,因此直觉的活动就是完成了表现的活动。克罗齐说:“直觉必须以某一种形式表现出现,表现其实就是直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里,克罗齐将表现视作直觉。
邓以蜇对克罗齐表现说的继承与发挥直接体现在其对中国心画理论的诠释与分析上。例如邓以蛰在《书法之欣赏》一文中指出:宇宙之内,不外自我与外界。自我者,感于物而动者也;外界之所以有,以其能给自我以形体之对立。形体之有,有在自我之感得。其感得之初,原不假于知识联想而为直觉。
④邓以蜇指出了外在事物形体感的获得并不在于外在事物的实际存在,而在于自我感的获得。这种自我感的获得起初是源于人心之直觉对外在事物的赋形。如果把这种心灵的赋形能力纳入到艺术审美视野中来看的话,那就是克罗齐所言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受此影响,邓以蛰也认为直觉或表现是一种心灵活动,一种超功利欲望、超知识概念的精神妙得或美感的擒获。换言之人心之直觉或表现就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邓以蜇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其《画理探微》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山水画作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最高形态的心画,其实就是人心的直觉或表现。他说:胸有成竹或寓丘壑为灵机所鼓动,一寤即发之于笔墨,由内而外,有莫或能止之势,此之谓心画也,表现也。
若象后模写卷界而为之,或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后也,非表现之事也。画至表现,非复拘挛用功之时可比,而正是解衣盘礴,入心不能丝毫之际,其敏捷如风驰电疾者正所以求其逼近心中所寓之意,不使丝毫差错,岂营营世念,偃伛趋于庭者所能耶?
⑤邓以蛰认为中国画论中所谓“心画”的表现,就是一种直觉表现。邓以蜇的心画理论以体现宇宙精神、人格本体为宗旨,以笔墨、胸襟的结合,即意与法的结合为创作结构,以“以大观小”为具体的创作手法,以形成气韵生动、诗情画意相融合的审美效果为最终目的。
邓以蜇的“心画说”与克罗齐提出的“诗为心声说”有着共通的哲理基础,但落实到具体的艺术中,二者又有实质性的差异。在吸收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上,邓以蜇还是结合中国书画艺术的实际,做了理论上的发挥。
他创造性的开拓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形而上的语言诠释体系。在《六法通诠》一文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和明显。克氏之说,以为美为人类精神活动之一,精神活动者乃一动必有其始条理、终条理而自为一整个之结果与价值焉。美既出于一寤之感动,则其必与抽象演绎之知识不同,而为一种具体、直接而价值自在自足、由内而外之主观活动也;因其既为美感,则又与感觉或刺戟不同,故凡由刺戟或感觉而来之动作或颜色皆非美之资料,于是由颜色而成之绘画,根本不在美之域内也。然则如何为美乎?克氏曰:既具体而直接,自内而外,又能有感动之自在价值所谓美者,而非感觉或刺戟可比,此岂非言语诗歌之表现乎?盖表现者,美之活动也;言语诗歌者,具体而直接,有自在之感情价值自内发出者也。
⑥在这里,邓以蜇批评克罗齐未能将表现论思想用于书画,未能进一步研究得出表现之结果和价值,即未能见出中国气韵生动的义理。但他高度推崇克罗齐的表现论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相形之下,两者在方法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克罗齐是哲学家的分析,邓以蛰则是艺术家的分析。⑦
二
在哲学上,克罗齐发展了黑格尔的观点,消除了心物二元对立,认为心灵得到感受,并赋予此感受以形式。在艺术上,克罗齐的核心概念是“艺术即是直觉”“艺术就是表现”,指出心灵的直觉活动为艺术提供了材料和形式,是人的心灵成就了艺术。他提出了“诗为心声说”。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心”即主体之情感意绪,情感决定了诗的材料和形式;二是此“心”指天地之心、宇宙之心,是未被心灵束以形式的“道”。朱光潜先生以“心灵”(“心”)来译克罗齐的spirit,他解释说:“克罗齐spirit并不单指一般心理学家所谓的mind,不只是你的‘心’或我的‘心’,而是全体真实界的大用流行,不仅是‘人心’,而也是‘宇宙心’”⑧。
邓以蜇接受了克罗齐的这一观点,但是他以老庄哲学为依归,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诠释与分析。老庄哲学认为天地万物以道为本体,道贯穿于万物以及具体的艺术创作及欣赏中,人们所能体悟到的“道”就是流荡、生动的气韵。而克罗齐最初使用的指代万物本源的词“spirit”本意也是“气”。这两种“气”在解释万物成因、本义及存在方式上,有着共同的美学内涵。
⑨邓以蜇当然敏锐地感知到了克罗齐的“心声说”与中国传统画论的“心画说”有着相通的哲学依据,它们都认为不存在人与外界的二元对立,“心”在艺术形象的生成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此主体之气既可以是审美主体之心绪情感,也可以是充塞天地间的大“道”。于是,克罗齐以诗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直觉表现说,演变成了邓以蛰以书画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直觉表现说。但是经过邓以蜇的发挥与进一步的诠释,中国的“心画论”比克罗齐的“心声论”更完整、更深刻地诠释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或“艺术即表现”认为“艺术”是spirit获得“感受”这一自然的、非真实存在的材料,继而再由spirit赋予此材料以形式。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都是spirit一己作用的结果,并且克罗齐所谓的“传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表现含义,他认为达到心灵中的“表现”,艺术就彻底完成了,与运用何种媒介、何种技法完全无关,这种艺术创造理论是空想性的,是漂浮于空中难以掌握的。
⑩虽然,邓以蛰与克罗齐都认为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正是自己的内在精神,但邓以蛰将这种内在精神具象化了,变得可以进行实践与操作。而克罗齐则把它心灵化及抽象化了,变得虚无而空洞。邓以蜇的“心画说”最基本的创作原则是以表“意”为主旨、以“法”为手段。
此“意”就是心,是个体之心,也是宇宙之精神;此“法”具体于山水画中,则指用笔的骨力、运笔的迟缓、破法的擦染,又指用墨的浓淡、燥润,还指用色的渲淡、素雅。以传达出心之“意”为原则,以创作技法的高度成熟为保障,艺术作品才能达到“齐物我”,沟通“道”与“技”的关系,形成气韵生动、意法结合的审美效果。正因为中国的艺术精神是落于现实生活中的,使得“心画说”并非抽象、悬浮的思想,而是将深刻的哲学观念融于具体的艺术形式的美学结晶。
也正是因为此原因,邓以蜇批评克罗齐无法把握艺术创作的效果。他引用传统文论中扬雄所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以及米友仁之“画之为说,亦画也”的观点指出中国的“心画说”较克罗齐之理论更加完备、深刻和周详。进而批评克罗齐表现说的简单化,且不足以表述与概括中国艺术的全部特征及价值。他说:克氏未能将表现推之于书画,盖彼不知用笔作书作画之能表现耳。气韵生动可谓美之活动的结果,而为美之至极之价值焉。言语之表现为美之活动,此克氏之独到也,然未及此表现之结果,之价值,换言之,犹不知有气韵生动之事也,言表现而不及于气韵生动,犹之乎言思想不及于名理也。
三
前文已经论述邓以蜇在中国心画理论的诠释与分析中受到了克罗齐表现论的启发。但是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两者还是有鲜明的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对克氏的表现论进行了具体的生发与诠释,明确地区分了“表现”与“非表现”的界限。他所谓的表现只是类同于克罗齐的表现说,他认为:只有形象已经在心中浑然一体即“心画”已经形成,才能称作“表现”。这吸收了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观点,直觉的表现若不是在流出心中之前已经完整浑融,就不能成为艺术。在这一点上比克罗齐的表现说更加的明确和具体。除外,克罗齐并不赞同艺术表现之后传达一定的手法与技法,同样,邓以蛰也反对胸中无画意对所画着意加工,他认为模写、对照、分析等对心画的形成没有直接联系。但是邓以蜇也强调了笔法与胸襟的关系以及艺术义理的掌握,当艺术技艺达至与道合一的时候,完全有助于心画形象的表现。
其次,邓以蜇认为克罗齐就艺术表现出来的是“美”这个词,并不足以表述与概括中国艺术的全部特征及价值。克罗齐强调艺术是表现,固然是对的,用美来说明表现,也是对的,但是显得简单,没有涉及美在艺术中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这正是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与之相反,邓以蜇认为,中国传统的心画理论强调表现的结果即气韵生动,这是邓以蛰对克罗齐论美的一大补充。不仅肯定了绘画创作是一种审美活动,而且还以气韵生动来落实这一审美活动,使得绘画的特征更明确。这一看法使得艺术表现的对象———心灵、性灵与艺术表现的结果———气韵生动能够统一起来,性灵所显现的艺术独特性融合在气韵生动所显现的艺术整一性中从而得到充分反映。
艺术家的直觉、性灵既得到了深刻的表现,同时所创造出的气韵生动的意境,又给予欣赏者与批评者可以判断的对象,艺术作品的气韵生动不仅成为艺术家的直觉与性灵走向表现的处所,也成为走向读者的中介与平台。这样一来,邓以蛰就弥补了克罗齐理论中的断裂,即“美”因为空泛抽象而无法与艺术家的直觉相联系,也无法与欣赏者和批评者相联系的尴尬、孤立。
邓以蜇正是运用中国传统智慧,有效而全面地发展了克罗齐的艺术表现说的理论,建立了有中国独特审美价值的心画理论。他的心画理论回答了几个问题:
艺术家审美的直观是什么?审美主体如何才能产生直觉?审美直觉的结果是什么?而这些问题,在克罗齐那里没有提出来,甚至被他视为是不必提的。而正是因为这些根本问题的无法解答使得克罗齐的艺术表现说使人有琢磨不定的感觉。他的表现说无法连接艺术家的内在精神活动与外在世界,只能将创造与欣赏艺术的活动局限于直觉领域中来加以认识。
但是,邓以蛰不仅强调内外的交流、互动、融合与创造,并且描述了这一过程:开始时“自外而内”,是外物对主体的感动,调动了主体,这时候艺术家只能做到“应物象形”是“求象得其形”,“随类赋彩”“传摩移写”是依自然与旧本为其形象,此“三法皆主于外界”,求“形似”“,但画愈形似则愈无画家”,就像照相一样,非纯艺术也。接着展开“自内而外”的活动,主体被调动后,是我为主,物为客,“画家若欲有个人之表现,舍艺与意莫由也。故将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二法归之于画家焉”。到此时,才能真正地在移情状态中创造气韵生动的意象。
邓以蛰对这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详实地论述,从而全面回答了问题:直觉是什么,是玄解;如何才会有直觉,靠人品;直觉对物的作用,是发掘物的精神;直觉的结果是气韵生动等。如果说,克罗齐在研究直觉时,仅仅在精神的层面上界定它,邓以蛰则已经在精神的、创造过程的、与客体关系的、创造结果等不同层面上界定了它,显得极其深入,丰富了“直觉说”,这是邓以蜇对中国美学与艺术学理论的独特贡献。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与研究的价值所在。
因此邓以蜇对克罗齐表现说的吸取是基于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深刻领悟与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他参照克罗齐表现说的视角与方法,更加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书画艺术的义理与精髓。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挖掘与研究做出了极其可观的贡献。他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价值阐释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书法、绘画(尤其是山水画)是个体情感观念的外现,成就了国画中的“逸品”;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书法和山水画艺术的品评等级中以表达宇宙精神者为最高品,即“神品”。邓先生指出国画虽不似西画写实,但“心画”思想表明国画有最根本的两层价值,他说:国画之价值,可分两等,一等出于画家之笔墨自身……士气、逸格等价值,多属于此类也。又有一等价值,则为画之表现,此之所谓画乃离于画家之画,其表现乃为笔墨之外,尤有一种宇宙本体之客观的实在存焉。
此实在为何?即董广川所谓“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之一气,所谓自然者是也……所谓神品庶品足当之……可见中国书画艺术中,心画是主体精神活动或美感的具体直接表现,它是超越逻辑概念的主观情感的直观表现。邓以蛰的“心画”表现论并不是对克罗齐的表现论的完全复制,而是对其作了选择性的吸取和创化。
一、崇高与优美的美学起源关于崇高与优美的论述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过,但这一时期还并未将崇高与优美分而论之。崇高的概念形成在古代的修辞学之中,在希腊文中崇高也被称之为高度庄重雄浑,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十分流行的术语。但是在这一时期,崇高...
绪论第一节研究目的及意义黄药眠先生是当代着名的美学家、文艺学家和作家。解放后他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一级教授,曾任中文系主任,博士生指导教师,长期从事美学、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文学创作和译着,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学的建...
克罗齐在《美学》的开篇就谈到:“人类的知识总是分为两种:要么是直观的知识,要么是逻辑的知识;通过想象获得的知识或者通过智力获得的知识;个人的知识或者宇宙的知识;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或者关于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
文化传播能把美的思辨更好展现在大众眼前。关于美的阐释,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本质,意志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欲求冲动,显着特征就是生存,这就是唯意志论。...
近年来草原文化成为我们身边研究的主题,也表现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纯自然、自由、淳朴、博大的美学观。游牧民族文艺美学成为人们研究、欣赏的科学作品。但欣赏的多、研究的少,谈论的多、钻研的少,理论与实践脱节,主题文化思想与作品脱节,故此笔者从游牧...
莱辛在《拉奥孔》中明确提出诗与画的界限问题.认为诗叙述的是时间上先后承续的动作,而画描绘的则是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1,并指出了诗与画应该如何在各自的技巧领域内努力臻于完美,并获得成功.莱辛认为诗是动态的,在时间的进行中用语言描述一系列动作的发生,它...
目录第一章孟子美学思想的研巧现状第二章孟子美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因素第一节家庭影响第二节师承因素第三节对学生的人格品评第四节周游列国的阅历第三章孟子美学思想的基本观点第一节人性美;孟子美学思想的基石...
第二章孟子美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因素孟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华夏大地的深厚主壤中,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博大境界中。其美学思想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强调人格美,可W说对人格美的追求是孟子美学思想的核屯、。这固然根源于孔子对个人修养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