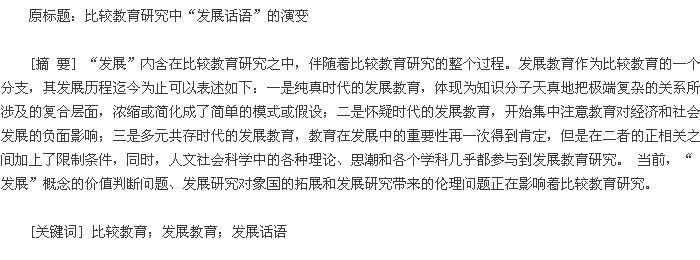
“发展”一直贯穿在比较教育研究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是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较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进教育和促进教育的发展,进而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比较教育的历史,不管是贝雷迪(George Bereday)所言的“借鉴时期”、“预测时期”还是当前的“分析时期”或者说“反思建构时期”,“发展”的概念和发展研究影响了比较教育提出问题的方式、研究的方法论、研究程序、研究对象的选择,同时也规范了民族国家的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政策、国际教育组织的教育研究的策略、教育援助的路径和方法、教育援助中援助主体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等。
本文将概要地考察“发展话语”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历程和方式。
一、“发展”概念的发展与比较教育
发展作为哲学术语,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 但不同时期的发展概念受其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其含义也在演变中变化。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深受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进化论影响,在阐释社会发展过程中运用生物学的比喻, 形成了社会学的普遍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进化”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哲学概念,人类社会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样,都受进化律的支配,从而推翻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主张社会是普遍进化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社会有机体”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超有机体,其分工类似于动物机体各个器官的分工,动物机体的各种器官的机能是相互配合、均衡的,而“社会有机体如同单个有机体一样,机能的均衡引起结构的均衡”.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19 世纪“发展”概念的含义和进化没有什么差别,“适者生存”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了社会普遍进化、发展的原则。这种普遍进化论“发展”概念包含着人类的进步与福祉的普遍主义精神,以此为指导,教育体制必须要为这个终极完善的人类理想服务,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是发展概念的内在要求。 比较教育是社会改良与道德改善的工具,需要从别国的发达和繁荣中发现可使本国兴旺发达的办法。 与这种人类普遍进步的理想主义相随的解释是教育竞争体现了背后的国家之间经济、军事、国际地位、意识形态等的竞争。 埃德蒙·金(Edmund King)在对比较教育的演化的总结中说到,“19 世纪,法国、日本、纽约州等已经建立了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完整系统,但是如英国等其他一些工业国家却还没有。 然而,不管是否由国家运作,大多数教育系统不时复制或者被其他地方的成果或者实践所影响。 经济和商业竞争,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竞争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要求在教育成功的各个方面也不被邻国超越。 另外还有对某些比如共产主义等政治信条的恐惧,还有对国家杰出的技术或管理的焦虑。 ”
进化论的发展观也从全球的角度把国家分为工业国家和非工业国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前者处于复杂的文明阶段,是后者的未来发展阶段,后者则被贴上落后和不发达的标签。 后者应该全盘借鉴和复制前者的教育制度,在前者的帮助下发展。 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弱国内的开明人士主动提出的学习与借鉴,更彻底的表现则是作为宗主国的欧洲列强如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忙于在印度、非洲等殖民地推行自己的教育制度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披着生物学、社会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普遍性的外衣,一方面被解释为进步、进化等;另一方面,“发展假设”事实上使欧洲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成了发展的标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战争的借口,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说 19 世纪比较教育家对民族主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抱乐观、积极的态度的话,两次世界大战的酝酿过程和战争的经历则使比较教育学家重新思考“民族主义”的内涵。 当民族主义与集权主义相结合,再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时,社会的进步则会受阻。 发展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质疑。 欧洲列强之间的敌对关系而非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成为国际局势的主流。 发展的标准处于重新探索之中,比较教育研究转向对民族主义、民族性、影响教育的因素与力量的研究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比较教育更多地转向理解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使国家更强盛、更具竞争力中的的角色。 发展、进化的普遍性被民族因素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特殊性所代替,但“适者生存”的进化律却依然在社会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发展的含义由普遍走向了特殊,19 世纪所持的人类的共同发展道路转向了对民族国家的自己发展现状的解释而非预测,因为未来的方向是不明晰的。
二战后,民族国家积极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教育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实证主义社会学初创时就孕育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完善,达到了顶峰。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被保留下来,“不论是否采用’生物的‘这个形容词,进化原理都牢固地确立下来了,可以适用于任何由生命体构成的世界……有机进化或变异、选择、调适、分化和整合这样的基础概念。 如果适当地加以调整,用到某种社会和文化主题上,就是我们关注的核心。 ”
美国社会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也称:“无论是自然进化,还是社会进化,都是自我维续、自我转变和自我超越的进程,有着时间上的方向性,因此也是不可逆转的。 这一进程在其发展历程中总是日新月异,不断产生出更多的变异,更为复杂的组织,更高程度的观察能力,以及日益增长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 ”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迅速复苏和繁荣,19 世纪萌芽的现代化理论在这一阶段成型, 经济学家在总结的过程中也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 在这种乐观主义精神的鼓励下,发展的内涵由现代化、科学化和经济增长等因素构成,而西方国家再度成为发展的样板和标准。 这些理论体系都被比较教育用来分析教育与经济增长、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人的生活质量与基本的人类需求等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比较教育的发展与“发展”概念及其理论紧密相连,发展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内在逻辑假设。
二、发展教育中的“发展话语”
虽然发展假设内在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历史中,但是作为比较教育一个独立分支的发展教育则是始于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和去殖民化而兴起的。 从这个时候起,在教育和比较教育中,与发展研究相关的问题汇聚并凸显出来。 自此,发展教育发展迅速,成为了比较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其强劲势头一直延续至今。 从对发展概念的界定、发展研究的命题构成形式、研究对象等方面可以将其发展进程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汉斯·韦勒(Hans Weiler)将其称之为纯真时代(the age of innocence)。 第二个阶段为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汉斯·韦勒称其为怀疑时代(the age of scepticism)。 第三个阶段从20 世纪 90 年代起至今,可以称之为多元共存时代。
(一)纯真时代的发展教育
华德(Frederick Ward)在《重新思考教育与发展》一文中认为,纯真时代的发展教育体现为知识分子天真地把极端复杂的关系所涉及的复合层面,浓缩或简化成了简单的模式或假设。托达罗(Michael Todaro)解释了这一时期的发展研究。 他认为发展,尤其是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期间,其传统含义是指一国的经济实力,也即该国的经济状况或多或少地保持一段长时间的静止后进而驱动并维持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年均 5%-7%或更快的增长速度。当国家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后,在决定国家经济、社会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变得有影响力。 国家寻求“现代化”和取代移居国外的高技术人才,教育变成了后殖民社会政策的中心支柱。 而这一时期的发展又主要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黎安琪(Angela Little)对这一阶段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做了深刻的概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家(虽然常常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制定描述的,是伴随着发展政策产生的。 从其开端来看,经济目标构成了’发展目标‘的根本特点。 ”
在比较教育方面,二战后,比较教育立即集中于教育成就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从教育对发展的作用的理论假设来看,其宏大命题对教育增长与社会经济效果之间关系的假设是笼统和涵盖一切的,其结论是充满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 诺亚和埃克斯坦提出的假说是:“教育发展水平相对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经济将出现高速增长;而教育发展水平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将是缓慢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论述道:我们需要把教育看做是人力资本而非仅仅是财政消费支出。尽管时隔二三十年后,这些假设被认为很幼稚,但是战后关于教育是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思想,却指导了各大洲的各国政府的教育政策,人人受教育成为教育的目的,教育也被理解为是向现代化迈进的基石,教育开支在财政开支中占了绝对的优先地位。 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积极为教育扩张提供资金和项目。 采用结构-功能研究范式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发展了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使教育被看做一种投资,其利润可以用应用于工资结构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计算。 同时,人力资源发展规划也被认为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合并到教育、就业和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政策的制定中。 教育财政支出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被理解为是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下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最初的定义是“对促进国家发展的目标具有最适合价值的学校教育或训练”.
由此可见,纯真时代的发展教育是隶属于社会学、经济学的分支,从事研究的主体也主要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研究问题集中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如社会招聘和遴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教育和社会的关系等。
(二)怀疑时代的发展教育
事实上,认为前一个阶段幼稚的观点就是怀疑时代提出来的。 这一阶段的发展教育从上一阶段大一统理论的失败中总结出了很多教训。 库姆斯(Philip Coombs)就指出,“教育事业的扩展并不一定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倒不合理的教育结构与维系教育发展的巨大成本却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从一段时间看来,上一个阶段所提倡并大规模实施的教育扩张,没有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繁荣,却造成了更多人失业,国家的公共支出负担不断加重。 另外,批评还认为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扩张主要体现在量的线性增长上,而真正需要的变革却没有发生。 怀疑论者认为,需要用一种更具区分性的、 谨慎的观点去对待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偶然性特征。重大政策决策的选择受到很多标准的制约,国与国之间是不同的,特定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会影响政策制定。 很多标准在本质上是规范性的,来源于对最向往的未来生活的假定,这种假定被转化成对这种社会中的教育的形式和实质的假定。
与前一阶段乐观地认为教育增长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国家的现代化相反,这一时期的发展教育开始集中注意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汉斯·韦勒质疑了教育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公平性问题、学习中的平等问题以及学习与工作、就业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孰先孰后发展的问题等。 他认为,教育政策的选择标准要考虑“平等问题”、“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和“教育改革问题”,而“决策制定的透明和参与问题”、“政策选择的知识和信息基础”和“政策选择的自力更生和独立性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的教育发展政策的讨论和形成。 德博伟斯(Michael Debeauvais) 也对前一阶段的发展教育的研究和教育实践做出了类似的批评和怀疑。
汉斯·韦勒认为,前一阶段的教育发展假设在实践中遭到了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后殖民时期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这种前所未有的依赖已经或多或少使关于“民族国家的发展”的隐式假设无效,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教育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 发展不仅仅被看作是社会内部平等的关系,而且是社会之间、特别是北方的宗主国和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 ”而对经济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研究不够。
怀疑产生的另一原因是世界的二级分化、三级分化格局没有改变,反而有增强的趋势。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二极对立,滋生了依附论的解释框架,中心-半边缘-边缘国家的三级划分进一步丰富了依附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学者给了它新的名词---世界体系分析。 这些理论体系不仅用来解释经济上的依附,也被用来阐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依附,以及依附关系的再生产。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分析是在20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在比较教育中流行的, 教育被认为是全球系统中再生产了不平等,恶化了失业问题,并帮助发达国家推进了文化帝国主义。
上述批判意见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教育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便宣告结束了,从那时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影响社会变革不仅仅是教育,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维度,还包括社会/文化和政治。布劳格(MarkBlaug)认为,经济学家们在寻找导致教育扩展并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应当关注一下“网眼假设”、“不完整的雇佣合同”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问题。 他认为,教育与发展之间的本质关联除经济因素之外,还应当包括制度与社会等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的发展模式无法移植,国际教育援助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失去了乐善好施的名声。
(三)多元共存时代的发展教育
多元共存时代与怀疑时代之间的年限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怀疑的同时也伴随新的理论体系的出现或原有理论体系的修正和发展。 怀疑时代的发展研究和发展教育研究,对“纯真时代”发展教育的评价只是基于 10-15 年的实践基础上,而教育产生效果的周期较长,且对效果的评定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也难以达成一致的评价标准。 因此,其怀疑甚至否定的结论本身也是令人怀疑的。 萨哈和费格林德(Lawrence Saha & Ingemar Fagerlind)通过对五十多年的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指出,教育对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足以消除人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此件事情上所持有的怀疑态度。 一刀切的判断方式无疑是存在问题的,要对任何一项教育投入都可取得预期的结果下定论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非是同质世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知识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培养出合格的受教育者才能实施其发展政策,参与国际竞争。 “只有在教育可以满足某一国家所提出的特定的发展需求并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得到有效的应用时,它才能够成为促进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 ”
教育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肯定,但是在二者的正相关之间加上了限制条件。同时,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了延续,并形成了系列分支理论,但是其核心范式却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
人文主义者批评其忽略了个人,激进功能主义者批判其致力于维护现行社会秩序,不注重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冲突理论把重点放在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内部冲突的后果上等。 这些理论从某一层面批评了传统的功能主义,同时又从另一方面发展了功能主义,并赋予其新的元素和解释、运用框架。 人文主义范式也与功能主义并存,一改过去由某一派独领风骚的趋势。 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实用主义、人种志、现象学等异彩纷呈,以不同的概念、理论范式进入发展教育领域。
三、当前的“发展话语”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
发展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发展研究的期刊、发展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很多大学里也设置发展研究专业,这些机构方面的变化和人员的汇集使发展研究越来越系统和制度化。 如果说前面主要是从理论构成方面对发展教育的大致分期的话,当前的比较教育的其他三个领域---外国教育、比较研究、国际教育①,也同样被发展研究所影响,发展内在于整个比较教育领域之中,是比较教育存在的基本逻辑起点。 当前,这些研究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给比较教育研究带来了变化。
(一)“发展”概念的价值判断问题
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社会各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负面问题,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贫穷问题、性别与发展问题等。 “发展”概念从价值无涉的“一种改变的过程”到价值有涉的“好的改变”.但是,什么是“好的”,如何鉴定“好的”? 古利特(Dennis Goulet)提出通过消除贫穷、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来衡量发展,把读写能力和教育看作是发展的基本成分和发展的标准之一。爱泼斯坦则认为,发展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观念,发展绝不完全根据客观的、理性的和无可争辩的前提,也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纯客观的目标。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则明确指出,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现代化等观点,是狭隘的发展观,在他看来,发展是扩展人民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人们拥有的自由的增进是评判进步的首要标准。
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也都在对“好的改变”进行界定,在界定的过程中就必然伴随着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 比如,在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2015 年后的教育总目标---“全民享受公平、优质的终生教育和学习”就是其价值有涉的“好的改变”的判断。 当前比较教育由注重理论生成的发展研究转向问题研究,如教育公平问题、女性教育问题、终身教育和学习问题、儿童早期教育问题、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教育质量问题等的研究都必然伴随着对“好的改变”的价值选择。正如阿诺夫所说,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的功能不仅仅是我们能从别的社会中学到什么来改进国内教育政策与实践, 而且是我们的这个领域能够为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公平的社会贡献什么,这无疑是一种对比较教育的“发展”功能的一种新的价值判断。
(二)发展的对象国问题
当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发展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国家内部的贫穷和不公平问题。 发展研究的对象不再囿于发展中国家,而是转向全球发展研究。 因此,发展研究也开始研究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自身的情况也不再被视为是发展的模板,发达国家的发展教育学家已经把他们的发展批评扩大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同时,发展和比较教育理论家也在研究能从建立在传统价值观基础上的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学到什么。此外,一些全球性问题涌现出来,关系到全球所有国家的未来发展,如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到的“气候-土地-能源-水-发展关系”问题等,这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耕耘其中。而在联合国的《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强调教育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各种国际性的和跨国的教育问题也随之产生。
(三)发展研究的目的或目标带来的问题
发展研究可以分为较少工具目的的从事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和具有较强工具性的政策研究、行动研究等,还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研究。而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研究,都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干预功能,也正是这一点使发展研究备受批评。 批评者认为,发展的标准和理念都来自发达国家,要求受援国接受其条件而很少考虑受援国自身的发展要求和文化背景,而正是这些成为了发展中国家问题之源。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也批评道,“这也导致了文化新帝国主义,一种倾向是认为在主要的英语国家的状况就是评价其他地方的实践的标准。 ”
由于发展研究不可避免对“他者”产生干预,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存在于研究者与政策决定者之间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而这在国际比较中由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因而比较教育学尤为需要在发展伦理学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Parkyn,G. W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ducation [J]. ComparativeEducation,1977,13(2):87-94.
[2]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69.
[3]Edmund King. A century of evolution in comparative studies [J].Comparative Education,2000,36(3):267-277.
[4]Talcott Parsons.Societies,Evolutionary,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M].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66.2.
[5]Julian Huxley.Evolution,Culture and Biological [A].William C. Thomas. Current Anthropology[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3.
[6]Ward F. C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reconsidered:the Bellagio Conference Papers [M].New York:Praegr (for the Ford and Rockfeller Foundations),1974.XV.
[7]Todaro M. P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4thedn [M]. London:Longman,1989.86.
[8]Angela W. Litt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Context,content,compari-son and contributors[J]. Comparative Education,2000,36(3):279-296.
[9] Robert F. Arnove.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J]. Compare: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0,40(6):827-830.
[10]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13,189.
当今社会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热,中国的家长似乎觉得出国留学已经成为培养孩子和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孩子成绩好坏,家长都希望孩子出去镀金。好的学生出国留学再有工作经历,回来提高不少身价。成绩一般的学生可能感受到中国教育的压力,怎么也想到国外...
比较教育学理论研究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基点和成熟的标志,而比较教育学理论选择是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更是比较教育学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性环节。比较教育学诞生以来,比较教育学理论选择问题一直受到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重视...
师从王承绪先生三十年来,恩师始终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感召着我,以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精神激励着我。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恩师常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给我以人生的启迪。他与人为善、积极向上、乐观豁达、荣辱不惊的处世态度时时感染着我,帮助...
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21世纪理想学校的愿景,中美教育决策者以及改革家们都在热切地宣传和实施各种学校改革的方案和措施。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有效学校研究中,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校长在学校改革中的关键作用(Edmonds,1979)。他们将模范校长的作用定义...
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过程创造现代文明。只有正确的劳动方向、劳动方法和劳动理念,才能提升个人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劳动教育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
1.引言研究生课程设置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而言,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同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培养高层次高水平英语学术型人才的主要载体。而课程的开设量...
教育督导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现代教育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对于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西点军校的课程设置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现在开设的课程反映了西点两百多年来军事教育和高等文化教育指导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反映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出现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在军事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语言类通识课程分为母...
教师在进行比较阅读教学时,要做好课前准备,不仅仅要收集某一作家的某一时期的作品,而是要详细地对其作品的内涵进行剖析总结。...
尽管家庭不是专门的教育机构,却蕴涵着天然的教育优势,中西方家庭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都对其下一代的成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的家庭应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国家庭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