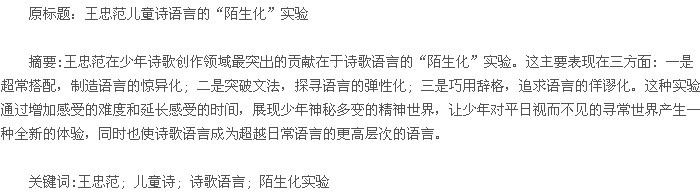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 1916 年在《作为艺术的手法》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 “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 остранеие) 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 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
这里的“反常化”即“陌生化”,就是通过对常规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陌生化是各种艺术的一个基本法则,尤其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更是如此。儿童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在语言上呈现“优美、精粹、平易、晓畅、富有音乐性等基本特点”。从一般意义来讲,成人诗歌追求的虚幻缥缈和朦胧晦涩,在儿童诗这里是不大有“市场”的。
然而,从上世纪 80 年代少年诗兴盛以来,为了展现少年神秘多变的精神世界,很多诗人亦开始踏上诗歌语言的实验之路,王忠范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超常搭配,制造语言的惊异化
词语搭配的惊异化,是指在通常意义下不能搭配的词语在特殊的诗歌语境中临时组合在一起。这种超乎寻常的搭配,是一种对于词语的“暴力”行为,其直接结果就是使语言变形、扭曲,从而达到特定的美学效果。在王忠范的儿童诗中就普遍地存在着这种词语魔变的现象,一般意义上的词语“不搭配”成为一种耀眼的标志嵌合在诗句中。比如,“打开英语课本翻出阳光”( 《对话》) ,“天空很充足\阳光很宽广”( 《燕子》) ,“因为一排活跃的姿势”( 《1234567》) ,等等。当然,最常见的要数词类活用,以及具象词和抽象词嵌合于同一语境这两种语言现象了。
其一,词类活用。词类活用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表达的需要,把甲类词临时当做乙类词使用。王忠范在诗歌创作中多有尝试: 第一,经常把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词。例如“蒙古包燃烧成火红的歌谣”( 《旅行》) ,“鸟群飞成灰云了”( 《春鸟》)等。第二,形容词临时用做动词。从现代汉语的造句规则来看,形容词的后面是不能带宾语的,然而王忠范的儿童诗中却大量地存在着“形容词 + 宾语”的形式: 有的直接嵌合,如“枝蓬勃云朵 \叶响亮大山\以粗壮饱满姿势 \饱满梦”( 《红柳》) ,“朝霞灿烂所有的梦”( 《珍惜天空》) 等; 有的借助虚词“着”来粘连,如“角纹坚硬着道路”( 《红羊角》) ,“红红火火着日与夜”( 《山梅》) ,“哗哗啦啦的声音洁净着天空”,“姿势笔直着天空”( 《我是一棵白桦》)等。本来是主语或宾语的中心语的修饰语,被变更为谓语动词,强化了修饰语的特质,同时又给读者以新奇的感觉。第三,把名词活用为形容词。例如“老师的脸比红芍花还红芍花”( 《红芍花》) ,“同学们说我比林黛玉还林黛玉”( 《眼泪》) ,“我们这些比小河还小河的孩子”( 《浪花》) 。这样活用之后,形象更为直观可感,而且因着读者对于“红芍花”、“林黛玉”、“小河”的不同理解,人物形象变得多元繁复,别有一番情趣。
其二,具象词和抽象词嵌合于同一语境。诗歌语言之所以具有美感,是因为其讲究诗句的意合、流动、气韵以及延伸自身内涵的文化特征。诗人通过具象词和抽象词的嵌合,把语言从单解中释放出来。
因为具象词的理性化和抽象词的感性化相反相生,而使诗歌生发出无限的“张力”和“弹性”,使诗歌体物得神、气活灵通。王忠范的儿童诗中这种语言现象屡见不鲜,例如“身躯挺立着纯洁\挺立着向上的道路”( 《我是一棵白桦》) 。在这种具体物象与抽象概念的嵌合中,“身躯”有了情感,“纯洁”有了形态,表层的感官形象中同时蕴含了深层的情感和哲理,虚实结合产生了弹性的美感效果。这样的组合还有很多,如“十四岁都有健壮的腿\在我面前走动着自由与羡慕”( 《十四岁》) ,“红绸悬起欢乐与吉祥”( 《丰收节之夜》) ,“从草地上升起\又落进草地\洋溢着眷恋与鲜红”( 《贝朗花落了》) ,“手心还在喷吐力 量”( 《打 草》) ,“意 志 和 理 想 不 怕 风 雪”( 《雪》) ,“队日里升起的队旗 \哗啦啦地把梦抖开了”( 《想象》) ,等等。它们或虚者实之,将表示智性内容的抽象词为具象词所修饰、所过滤,获得一种形象感性的外观; 或实者虚之,将直观可感的具象词为抽象词所规范、所引领,延展一种形象暗示的深度。
人们对外界的刺激有“趋新”、“好奇”的特点,只有新奇的东西才能唤起人们的兴趣,才能在新的视角、新的层面上发掘出自我本质力量的新的层次并进而保持它。在诗歌创作中,词语搭配的“惊异化”正是化熟悉为新奇的利器。在王忠范的儿童诗里,那种被逻辑思维和实用态度所赋予词语的限制涵义,被诗人放逐了。放逐带来的并非是语意的丢失和错乱,相反,它打开了一条通往超越的道路,词语在互相变更、互相位移、互相应和、互相吞噬、互相失落“限制”的过程中却意外地达到了彼此的溶解,并且呈现出一种完全开放式的语言结构。这种结构使语言获得了自由。
二、突破文法,探寻语言的弹性化
美国着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曾对语言的弹性化做过这样的比喻: “可以把语言看成一架乐器,能奏出不同高度的心灵活动。语言的流动不只和意识的内在内容相平行,并且是在不同的水平面上和它平行的,这水平面可以低到为个别印象所占据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高到注意焦点里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的心理状态”,语言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强度,随着注意或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
也就是说,心灵的价值和自由度决定了语言的弹性,诗人的智慧和热情可以让语言开始炫美的“智力的舞蹈”。当然这种智力的舞蹈,一般要通过对语言要素的重组来实现。王忠范便深得其妙。宋人的诗歌“伸缩离合”法被他灵活地运用在现代诗句的组合中,几个句子可以浓缩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拆分成几个诗行,此外还可以“切割文法”,语断意连。在王忠范的诗里,语言的“魔法”尽情地得以舒张,语言变得忽而熟悉忽而又陌生,语意变得忽而简单忽而又繁复。
其一,几个句子浓缩成一个句子。随着现代诗歌对“散文化”的追求,长句较多地出现在诗人的创作中。这种长句表意繁复,更适合于传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情绪。王忠范在创作儿童诗时就很喜欢使用长句,尤其是这种将几个句子浓缩在一起的句子,如“她想用目光拴住我不许东奔西闯/可她扶我练骑她吃风尘她只有汗”( 《阿妈是我们永远的晴空》) 。这样的写法,很有些类似于小说的细节表现法,又像是电影镜头的定格法,我们眼前会分别浮现出: 妈妈扶着我、妈妈迎着风尘、妈妈的汗珠。这明明是一幅整体的图景,却被换做三个意象的叠加,完全呈现出发散性和跳跃性的思维特质,闪烁着令人目迷五色的光芒迎面走来,时而分离,时而合一。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然而你从来不忌恨妈妈/就是批评你你也喜欢妈妈”( 《你为什么最喜欢妈妈》,“也要一起去逛星期天的公园/你笑了笑得跳起来笑出了泪花”( 《心思》) 等。
其二,一个句子拆分成几个诗行。中国传统诗歌多是一诗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五四以后,借鉴西方诗歌的创作方法,中国现代诗歌也开始出现了将一句话分行排列的诗歌创作形式。这种形式摆脱了日常语言的直叙化、机械化、程式化,引发出象征性、唤起性乃至神秘性的思维,有效地利用语言自身的“膨胀系数”延伸了诗歌的内涵。在《早晨,八点钟……》的开头,王忠范便采用了这种语言排列方式:这是早晨八点钟红领巾浪漫成朝霞前两行为一句,合起来显然应该强调的是“八点钟”,分开来却将“早晨”一并突出出来。后两行为一句,效果亦然。四个融合于一体的意象被独立地呈现,各自唤起读者不同的情感体验,同时朗读起来又充满顿挫感。再如《血路》中的第三节:树呼喊着撤退冰的声音特别尖刻尽管血路弯弯曲曲表情冰冷而我却没有离开我知道血路的尽头是什么“尽管血路弯弯曲曲”本应是一句话,却被拆分成三个诗行,甚至词语“弯弯曲曲”又再次拆分,路的曲折之感可见一斑。
其三,切割文法,合成句子。中国传统诗歌中有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即切断语法串联语素,造成“惊乱”的意象复叠,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温庭筠)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孟浩然)等。清代文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称之为“蹊径绝而风云通”、“语不接而意接”的组词造句模式。
自我国诗歌进入现代以来,众多诗人对诗歌通俗化、贫民化、散文化的追求使诗歌贴近了“白话”,但远离了诗意,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不满。如何融合西方现代诗和中国古典诗歌之精华创造出全新的现代诗成为戴望舒、穆旦等诗人孜孜以求的终极理想。当然,语言实验也在探索范畴,包括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这种切断语法串联语素的方法的迁移。在王忠范的儿童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这种语言实验的痕迹,如在《姐妹》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呼伦池和贝尔湖在草原上痛苦与闪亮两只眼睛两滴泪这样的诗句应该怎样解读呢? 我们可以试着通过补足省略成分以及调整句子顺序的方法来“还原”: 呼伦池和贝尔湖像两只眼睛,又像两滴泪一样在草原上痛苦与闪亮。“还原”了诗句,清楚是清楚了,“逻辑”也“逻辑”了,但诗意已经荡然无存了。
诗句本身的跳跃性、流动性和偏重于心理感受的语言策略,其实是指向一种细致的暗示性的美感经验,同时也是指向某种唤起读者瞬间感受的气氛和境界。这种“切断”和“重组”提高了意象的独立性、视觉性和玩味空间,增加了诗意的顿挫、曲折和回旋,当然,也扩展了诗句之外的天地,增强了语言自身的弹性。同样,《眼睛》中也有类似的诗句:马灯一只眼睛长在我的手上当抽取了“马灯”和“一只眼睛”之间的连接词以后,两者就独立开来,那么“长在我的手上”的到底是“马灯”还是“一只眼睛”呢? 似真似幻,灵动惬意,瞬间的感受被凝固下来。
很多诗人都会产生“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的感慨,“言语”与“人意”在诗歌创作中如此这般的纠结,语言的呈现形式直接关涉着情感内蕴的表达。
美国的苏珊·朗格在《谈诗的创造》一文中曾说: 优秀的诗篇必然是一种表现性形式,“这种表现性形式借助于构成成分之间作用力的紧张与松弛,借助于这些成分之间的平衡与非平衡,就产生出一种有机性的幻觉,亦即被艺术家称之为‘生命的形式’的幻觉。”
这段话将语言的弹性实验与诗人的生命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暗示出弹性语言的精神性、隐喻性和参与性。从表面看来,王忠范儿童诗中,这些突破文法的句子似乎是指向一种“表现性的形式”,然而这种形式是一种以人的自由精神为主旨的抒唱方式。在这种形式中,语言以自由灵动的舞蹈传示着诗人时而流动时而凝固、时而爆发时而消逝的生命幻觉,语言所呈示出的弹性力量极大地拓展了诗性空间,深化了诗意内蕴。
三、巧用辞格,追求语言的佯谬化
佯谬就是指看上去是一个错误,但实际上是正确的,而且可能更正确。它是一种伪错误的语言形式,通过采用特殊的手段,布下一个“迷魂阵”,在客观上延长了读者欣赏的时间。但佯谬化指向的绝非荒谬,而是诗意的朦胧,甚或是穿越朦胧的真实。使诗歌呈现出佯谬化的特质可以采用很多手段,在王忠范的儿童诗中,主要表现为通感和矛盾修辞的运用。
其一,通感。诗歌借助于通感作用,一方面可以积极推动欣赏者的审美再创造,把欣赏者从一种美的境界带入另一种美的境界,而这两种境界的融合,便使欣赏者获得更强烈的美感愉快; 另一方面由于通感所表现的不是有限时空中有限感觉的美,而是突破了有限时空的无限时空的美,它使每一种感觉都能够将该种感觉所不能直接表现的其他感觉间接地表现出来,将诗中直接的感觉形象与间接的感觉形象相互交融,使艺术形象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得到很好的统一。王忠范的儿童诗《小河》中有这样的诗句: “野玫瑰的声音是朵暖和的芬芳”,其中“声音”是听觉类词语,“暖和”是触觉类词语,“芬芳”是嗅觉类词语,因此“暖和的芬芳”看起来很不搭调,“声音是朵暖和的芬芳”就更不可思议。打乱各种感觉系统固有的秩序进行的交错性搭配,带给我们的感觉首先是荒谬的、非逻辑的,然而细细品咂,这样的语言别有一番滋味,形象地传示了诗人瞬间的体验,“野玫瑰”在听觉、触觉和嗅觉的彼此交错中变得丰盈饱满。又如,“笛孔里放飞的七只小鸟飞遍山谷”( 《幼林与路》) 。这句话乍一看来只涉及视觉感知,似乎与通感无关,可是仔细看来却存在着荒谬之处,细细的笛孔里怎能放飞小鸟呢? 显然小鸟是通过听觉作用产生的视觉联想,诗人是被笛子奏出的音乐迷住了啊! 再如,“领我们追百灵抓一把把鸟声”( 《你是一颗幼松》) 。这里,鸟的声音叫人迷醉,少年多想将它捧在手心,在我们的眼前分明可以看到手捧着阵阵百灵鸟鸣叫声的少年的迷醉的眼睛,诗句由此为我们打开了视觉和听觉的无限想象空间。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句子: “一弯了像把镰刀割净了声音”( 《心思》) ,“又一曲马头琴漫过草原”( 《丰收节之夜》) ,“好听的日子纷纷扬扬”( 《春鸟》) ,“奶雨甜得无边无际”( 《奶雨》) 等等。这些句子的修辞效果与前面的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颜色、芳香、味道、声音、温度的密切契合“将我们从那近乎醉与梦的神游物表底境界达到一个更大的光明———一个欢乐与智慧做成的光明”。
其二,矛盾修辞。矛盾修辞法( Oxymoron) 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是用两种不相调和,甚至截然相反的词语来形容一件事物,起到一种强烈的修辞效果,使得所表达的语义更强烈。如“真实的谎言”和“甜美的忧愁”便是矛盾修辞法的具体表现。在王忠范的儿童诗里,这样的矛盾修辞也有不少,如: “欢乐与烦恼都不戴面具/因广阔而逃避/因简单而复杂”( 《珍惜天空》) ; “回音在根须里锋锐与死去”( 《红羊角》) ; “光芒里的笑和哭都好看都好听”( 《妈妈像一盏灯》) ; “太阳躲在妈妈的故事里发冷”( 《在雨里》) ; “学校数学竞赛我拿了第一/因为什么也不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 “这些日子是我的决不借给别人/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无忧无虑”( 《这些日子》) ; “我的雪。一切都存在一切都不存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怀念》) 等等。这里,我们以“欢乐与烦恼都不戴面具/因广阔而逃避/因简单而复杂”为例具体地分析一下: 在这个诗句中,“欢乐”与“烦恼”,“简单”与“复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而“广阔”与“逃避”之间虽然并未存在明显对立,但结合在一起显然存在某种悖论。因为会让人产生“逃避”的欲望的原则上应该是束缚和压抑的空间,而广阔和自由的氛围,人怎又会想要逃离呢?
这种对立的并置结构,让诗句表达的含义复杂而矛盾。但是,在特定的情景中,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可能存在的。对立的含义中往往包含着人生的辩证法,正所谓越简单越复杂,喜极而泣,过渡的自由也是一种负担。这是怎样的充满悖谬又真实的人生体验?!
在相反的方向上寻求“和而不同”,在矛盾的情境中寻求更深刻的“真”。这样看来,这看似矛盾的矛盾,并非“真矛盾”,而是“类矛盾”,这个包含在大而深的理性之中的“小小悖理”,赋予诗歌极为特殊的魅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王忠范作为一位儿童诗诗人,在遵循儿童诗创作规律的同时,为了恢复少年对生活的新鲜体验,使少年感觉到事物的活的存在,大胆地进行了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实验。这种实验通过增加感受的难度和延长感受的时间,让少年对平日视而不见的寻常世界产生一个全新的体验。17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曾指出: “诗是一门学问,在文字的韵律方面大部分有限制,但在其他方面极端自由……可以随意把自然界里分开的东西联合,联合的东西分开。这就在事物间造成不合法的配偶和离异”。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实现,使诗真正进入到隐喻的世界,诗歌语言也因此成为超越日常语言的更高层次的语言。
[参考文献]
[1]什克洛夫斯基. 作为艺术的手法[G]/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方珊,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6.
[2]陈辉. 通向儿童文学之路[M].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2005: 21.
[3]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13.
[4]苏珊·朗格. 谈诗的创造[M]/ / 艺术问题. 滕守尧,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43.
[5]梁宗岱. 象征主义[M]/ /诗与真二集.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76.
[6]杨匡汉. 中国新诗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 142.
[7]培根. 学问的推进[G]/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辑委员会.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3.
作为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着名诗人,阮章竞有两重身份引人注目:其一,他是民歌体叙事诗的大家,《漳河水》是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探索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成功之作...
晚清民初的学堂乐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儿童诗歌的创作之门,从晚清到五四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儿童诗歌显示出较鲜明的阶段性艺术特点。选取以老鸦为内容的几首儿歌作为线索,能够以点带面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儿童诗歌从风格到意境的流变轨迹,揭示出...
(二)亲子之间的相处在青少年时期,子女往往与父母战火不断.青少年开始具有了比较独立的主体思维,他们对成人世界充满向往,渴望独当一面,不再对父母言听计从,有了逆反心理。如果说父母心中总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那么每个孩子心里也有一个理想的父母;由...
诗歌能够帮助人们找回童年,诗歌和童年关系密切,女诗人夏吟在诗歌中始终保持对儿童的热诚关注,她写了许多儿童诗,也写了许多以儿童为书写对象的诗,还写了大量的和童年、游戏有关的诗歌,表现童真、童趣和童话,这些诗充满了温情和想象力,格调健康,激情...
一、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追溯到古代,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创作的民间文学中就有很多被广大少年儿童接受和喜爱的作品,如《茉莉花》、《外婆的澎湖湾》、《幼儿画报》、《摇篮歌》等等.小耗子,上灯台的儿歌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受到广大少...
古今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的成长认知过程中担当着塑造健全人格和培养审美情感的重要角色,应当成为各民族少年儿童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由于语言文字的限制,新疆的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尤其是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地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年儿童)很...
茅盾的《少年印刷工》是唯一一部关于“印刷”主题的文学作品,并在很多方面都占据了重要地位。首先,这是茅盾唯一一部涉及到商业的作品。其次,《少年印刷工》与《走上岗位》(1943)和《锻炼》(1948)一样,是茅盾极少的连载作品。...
少年强则国家强。在国人生活水平日益增加的今天,阅读是需要引导和关注的。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很多国家已意识到阅读对人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将阅读从儿童抓起。在国家和出版业的推动下,我国少儿...
儿童诗歌以其语言天真活泼、柔软,结构简便灵活明显区别于为成年人创作的诗歌。其中的审美特征也其独特的气息和风格来进行表达,扣孩子们的心弦,反复激起他们对自然的见识、对生命的感情、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儿童的情趣特殊,许多现象,景观、色彩款式、闪...
就如同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样: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1]在这一年,我国儿童文学领域里发生了批判陈伯吹童心论的运动。这场批判运动缘起于陈伯吹在1956年和1958年先后发表的《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