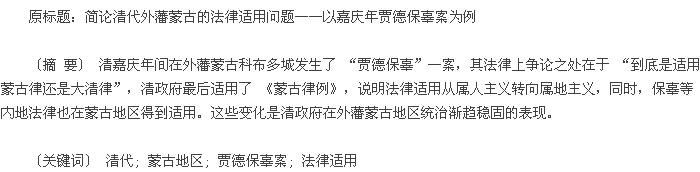
在清代的历史档案中,有关贾德保辜案①的材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此案发生在嘉庆年间的外藩蒙古科布多城,城中的贾德与邵廉舒同为晋商,均为汉人,因索债事宜发生争执,贾德用刀扎伤邵廉舒致其身亡。案情本不复杂,但是审理一波三折,长达一年半之久,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适用蒙古律还是大清律”,因为适用不同的法律,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甚至关系人命,对此,从科布多参赞大臣的初审,到报理藩院,再到三法司会审,对此案的处理都非常谨慎,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的世袭骑都尉董诰在上奏的题本中诚惶诚恐地表示: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阅后,嘉庆帝朱批: “贾德依拟应绞着监候,秋后处决。”最后嘉庆帝亲自定夺为绞监候,正是适用的《蒙古律例》。本文通过对此案的分析,借此对清代外藩蒙古地区在法律适用特点略抒浅见。
一
邵廉舒与贾德同为山西汉人,在科布多地方开小铺为生。嘉庆十四年 ( 1809 年) 十二月,邵廉舒向贾德赊取麻花,价银三两八钱,约定十五年正月内奉还。正月十三日早晨,贾德来要赊欠麻花银两,邵廉舒央恳到二十日还他,贾德不依。邵廉舒负气说: “你要这样逼我,我不还了。”贾德一时情急,拿起炕上放的小刀在邵廉舒左腿上扎了一下,邵廉舒随即将他按倒,夺过小刀,随后上报了官厅。48 天之后,即三月初一,邵廉舒因伤离世。
在 《清会典事例》中乾隆四十五年议定:“科布多地方命案,毋庸解送刑部,即由该参赞大臣审明定案后,将该犯解送乌里雅苏台将军处,由该将军复核,入于秋审汇奏”。[1]( P. 1280)从题本中显示的案件审理经过来看,邵廉舒与贾德发生争执,被扎伤报官后,首先也是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策拔克进行处理的。策拔克认为: “查刑律载,刃伤人杖八十、徒二年,又保辜刃伤限三十日平后,又例载,辜限内不平复,延至限外刃伤,十日内身死,奏请定夺,又正限后余限外身死者,止科伤罪各等语。此案邵廉舒于嘉庆十五年正月十三日被贾德刃伤左腿,延至三月初一日身死,计期四十八日,已在正限三十日余限十日之外,自应按律定,拟贾德应依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褫回原籍山西延抚定地充徒至配折责安置。”由此可见,策拔克是按照 《大清律例》进行判决。
策拔克将此案上报到刑部,刑部 “查例载,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照蒙古例办理,又蒙古例载,斗殴伤重,五十日内身死者,下手之人绞监候”,因此,刑部认为贾德犯事系在蒙古地方,自应照蒙古例办理。此外,在查阅邵廉舒尸体时,格刃伤仅止填横长及宽,并未声明深入几分,是否筋断骨损,“验伤既未明确,引例亦未妥协,罪名生死攸关,臣部未便率议,应令该大臣详晰查审,按律妥拟报部,再行核办。”很显然,刑部认为策拔克适用法律错误,故返给其重新审理。
策拔克重审此案,验明邵廉舒确因伤致死,刀深入七分,并未断筋骨,且按 “刑部指示”,适用了 《蒙古律例》,即 “贾德合依蒙古斗殴伤重五十日内身死者,下手之人绞监候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最后理藩院会同 “三法司”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刑部主稿,由董诰上奏嘉庆帝。
此案正是因为不同罪名生死攸关,所以各相关部门都相当谨慎重视,从联合上奏的 23 名大臣及其职务①便可窥见一斑,如董诰、瑚图礼、金光悌、佛尔卿额等都是朝中重臣。嘉庆帝最终认可了董诰题本中的判决——— “贾德依拟应绞着监候,秋后处决”,此案画上句号。
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笔者一直在思考,科布多参赞大臣策拔克在最初审理时为何会直接适用 《大清律例》? 而刑部在复核时又为何认定要适用 《蒙古律例》? 最后适用 《蒙古律例》说明了什么? 正是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看相关的律例规定,发现里面涉及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清代蒙古地区在法律适用原则上,发生了由属人主义向属地主义的变化,二是保辜等内地法律制度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适用。下面笔者试着从这两方面来做一分析与说明。
二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面对广博深远的汉文化,清代统治者既不是拒绝,也不是破坏,而是积极主动地学习、接受汉文化,在其267 年的王朝统治期间,不仅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法律制度也获得了显着成就。在立法上,清统治者建立了 “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参考以明朝法制为主的汉族君权王朝法制; “酌金”,就是斟酌吸收满族固有的习惯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是《大清律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大清律例》是以 《大明律》为蓝本完成,是中国传统君权王朝法典的集大成者,汉唐以来确立的皇权社会法律的基本精神、主要制度在 《大清律例》中都得到充分体现。
清朝还是中国多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多民族共存的状况是清朝多元一体法律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现实基础。清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统治,根据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经济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历史传统等实际情况,建立了一系列与内地有别的特别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蒙古律例》。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大前提下,将边疆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有机统一起来。如 《清会典事例》记载: “国初定: 边内人在边外犯罪,依刑部律,边外人在边内犯罪,依蒙古律。”[2]( P. 1254)这说明,清朝在建国之初,对于少数民族之间的案件,采取属人主义原则,以蒙古地区为例,如在蒙古地区民人犯罪,适用 《大清律例》,如果蒙古人在内地犯罪,仍然适用 《蒙古律例》。到了清中期,据 《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年九月,原任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归化城应行事宜:“凡会审之件,民人照内地律治罪,蒙古照蒙古律治罪。如蒙古无正律,援引刑部律例定拟,倘有偏执己见者,即行题参。从之。”①。由此可以看出,此时仍然贯彻属人主义的原则,蒙古律与刑律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
在属人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可能导致在适用中存在同罪异罚,处罚倚轻倚重的情况,这让清统治者开始反思这一问题。据 《清实录》记载,理藩院奏请改定民人蒙古等偷窃牲畜例: “现今蒙古偷窃民人牲畜,治以重罪,而民人偷窃蒙古牲畜,止从轻杖责发落,殊未平允……凡在蒙古地方行窃之民人,理应照蒙古律治罪,如谓新定例不无过重,则蒙古之窃蒙古,照蒙古例,蒙古之窃汉人,照汉人例,始为允当。但蒙古地方辽阔,部落蕃孳,俱赖牲畜度日,不严加治罪,何所底止,今将汉人之窃汉人,仍照汉人例,汉人之窃蒙古,照蒙古律,则窃盗自必渐少,而立法亦属平允。着照理藩院所奏,将律文更定。”②《清会典事例》也对此有记载: “乾隆十四年奏准: 蒙古地方均系游牧,并无墙垣,易于偷窃,是以定例綦严。但蒙古一切衣食等物,大半买之内地,内地人持货赴边,日积月累,迄今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余万。今蒙古偷窃内地人牲畜,皆照蒙古律拟绞,内地人偷窃蒙古牲畜,仍依内地窃盗计赃治罪,蒙古内地人相聚一处,未免情同罪异。嗣后内地人如在边外地方偷窃蒙古牲畜者,照蒙古例为首拟绞监候,为从议罚三九。”[2]内地民人在边外蒙古偷盗,不再适用 《大清律例》,而是照 《蒙古律例》处理, 《清实录》里的表述更为明晰,民人在蒙古地方偷窃民人,仍依大清律,但是偷盗蒙古人,则依蒙古律,这说明严格的属人主义渐渐转向以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 《大清会典》所记载来看,乾隆十四年,此时适用的属地主义,即 “蒙古地方”是指 “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等内扎萨克蒙古地带,而非外扎萨克蒙古,这在乾隆二十六年,山西按察使索琳的奏折中也得到了印证,③现将索琳所奏摘录如下:
窃照律例一书,原系因地制宜、随时损益。我圣朝钦定刑律节目详明,条分缕晰,实为薄海共守之宪章,万事遵行之良法。而惟蒙古所用律例则与内地不同,缘蒙古生长边隅住居,游牧牲畜之外别无,生计事务不烦,故所定律法亦多简易。今则内外一家,渐被日久,沿边察哈尔、喀喇沁、土默特各部落蒙古咸知营治房室、垦种地亩,其安居乐业之情形,实与内地无殊。且民人出口营活者多,命盗事件,往往互相交涉。遇有交涉之案,有照蒙古律办理者,亦有参用刑律办理者,原未拘泥。惟是蒙古律无明文,方准引用刑律,若蒙古律内本有专条,自又不便混行引用。而蒙古专条之内或语涉疑似,或义属笼统,则拟断易致歧互,似应酌为变通,免轻重出入之虞……因沿边察哈尔等处蒙古与民人杂处,易于交涉事件,故敢冒昧敷陈,其外藩蒙古,仍应照蒙古定律遵行。
在索琳所奏中,明确指出,所需要变通的是沿边察哈尔、喀喇沁、土默特等内属蒙古地带,因为此处蒙古与民人杂处,纠纷之多,亟须统一规定,而对于外藩蒙古仍应照蒙古律执行。据《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的注释所言,此次索琳所奏,馆修入律④: “蒙古与民人交涉之案,凡遇斗殴、拒捕等事,该地方官与旗员会讯明确,如蒙古在内地犯事者,照刑律办理; 如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者,即照蒙古律办理。”⑤《蒙古律例》卷十二也有此规定: “蒙古人在内地犯事,照内地律治罪,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照蒙古律治罪。”[3]同样也是乾隆二十六年刑部会同理藩院议复山西按察使索琳所奏之定例。由此可知,此时 《大清律例》和 《蒙古律例》中所说的在“蒙古地方”犯事,尚不包括外藩蒙古。
回到贾德保辜案,本案发生在我国西北边陲的科布多城,据 《清实录》记载,在雍正九年三月,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言: “北路军营遵上筑城。查科布多地方,按连布娄尔与库里野图相近,系进 兵 大 道,请 于 此 处 筑 城。” 上 “从之”。①由此可见,科布多的军事战略的重要性。
乾隆二十六年 ( 1761 年) ,清政府在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在此设参赞大臣。据 《科布多政务总册》富俊所言: “科布多,乾隆三十二年建筑,径方四百步,周围约二里,东西南三门,东西无关厢,东名迎祥门,西名延庆门,南名福汇门,外有关厢长里许,俱系商铺”。[4]随着大量军政人员的到来,大量的旅蒙商②瞅准商机,来此经营各种买卖,建立商铺,频繁来往于科布多与内地之间。
五方杂居,民人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繁荣了科布多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存在纠纷冲突。此时,对于蒙古与民人之间的纷争如何处理,并无明文规定,更何况贾德与邵廉舒同为内地民人,到底是适用蒙古律还是大清律,显然无先例可循。按照策拔克对此案的处理来看,策拔克适用了普通法大清律,即沿用了属人主义的处理原则。
从策拔克的处理来推论,之所以会适用大清律,可能存在以下两种可能性: 一是根据 “蒙古地方,汉人之窃汉人,仍照汉人例,汉人之窃蒙古,照蒙古律”来看,因贾德与邵廉舒同为汉人,因此,应该适用属人主义原则,即大清律; 二是策拔克对可适用的 “蒙古地方”理解上有偏差。
策拔克作为清政府派出的参赞大臣,处理各种政务要事,不可能不知道 《大清律例》 “化外人有犯”第三条所述内容, “蒙古与民人交涉之案,凡遇斗殴、拒捕等事,该地方官与旗员会讯明确,如蒙古在内地犯事者,照刑律办理; 如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者,即照蒙古律办理”,只是他也认为此条只适用内属蒙古,并不适用处于外藩蒙古的科布多。因此,对于在科布多犯事的汉人贾德与邵廉舒按照刑律进行了审理。
可是案件报到刑部之后,刑部却认为 “查例载,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照蒙古例办理”。到了乾隆五十四年, 《蒙古律例》③几经修改添补,已经臻于完善,十二卷的内容基本固定,其中,十二卷明确规定: “蒙古人在内地犯事,照内地律治罪,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照蒙古律治罪。”[3]显然,和 《大清律例》中 “蒙古与民人交涉之案,凡遇斗殴、拒捕等事,该地方官与旗员会讯明确,如蒙古在内地犯事者,照刑律办理; 如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者,即照蒙古律办理”的规定相比较,不再局限于斗殴、拒捕等恶性事件。
此外,在贾德案中,刑部认为科布多地区民人犯事,也应适用 《蒙古律例》,由此可见,此时蒙古律已实行了严格的属地主义,且 “蒙古地方”早已不再局限于内属蒙古,而是广泛包括了外藩蒙古。此条规定适用范围和地域的变化,充分说明了清政府对外藩蒙古管辖范围的扩大及掌控力的增强。
三
贾德用刀刃扎伤邵廉舒,邵廉舒逾 48 天后因伤身亡,其中还涉及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就是保辜。保辜制度源远流长,早在唐律中就有非常详细周到的规定,它是我国古代在长期的刑事法律活动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经验,非常有价值。④正是基于保辜制度的积极意义,清朝统治者沿用了此制度,不仅写入《大清律例》,而且在蒙古地区也开始适用,在《蒙古律例》中予以确认。
《大清律例通考》对保辜这样解释: “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 以 保 之。保 人 之 伤,正 所 以 保 己 之 罪也。”[5]( P. 822)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保辜是古代刑法处理伤害案件的一种特殊制度,其基本内容是殴人致伤后,规定一定的期限,视期限届满时的伤情,再行定罪量刑。[6]也就是说,如果殴伤人,伤者在保辜期内死亡,理论上被认为殴伤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对殴者应以斗殴杀人论; 如果在保辜期限外死亡,则认为殴伤与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对殴者各从其殴伤论。《大清律例》保辜限期规定,以刃及汤火伤人者限30 日。另外保辜期限第三条例文规定,斗殴伤人,辜限内不平复延至限外,若手足、他物、金刃及汤火伤限外 10 日之内,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限外 20 日之内,果因本伤身死、情正事实者,方拟死罪,奏请定夺。贾德用小刀扎伤邵廉舒,按照刃伤规定的保辜期限为正限 30 日加余限 10日,共 40 日,邵廉舒 48 天后去世,已过保辜期限,因此,理应将贾德以殴伤论。而根据 《大清律例》“斗殴”例规定: “折人筋,眇人两目,堕人胎及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5]( P. 816)。
由此,策拔克最初作出了 “杖八十,徒二年”的判决。这是完全依据 《大清律例》所裁决的结果。《蒙古律例》卷七 “人命”中有 “斗殴杀人”的规定: “因斗殴伤重五十日内死者,下手之人绞监候。”这正是对保辜的相关规定。据《清会典事例》“理藩院”记载: “顺治十五年题准: 斗殴伤重五十日内死者,将殴人之犯拟绞监候。”[1]( P. 1276)《清顺治实录》里也有记载: “斗殴伤重五十日内死者,行殴之人处绞。”同时,笔者又查阅了 《阿勒坦汗法典》、《卫拉特法典》等有代表性的地方立法,有关斗殴身死,处以罚牲或是其他物品,并无保辜之规定,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在对蒙古地区的立法中,有改变地吸收了中原立法的相关规定,出现了蒙古法律内地化的趋势。当然,按照 《蒙古律例》的规定,保辜期限未像 《大清律例》根据伤害程度以及伤害手段作具体划分,统一规定为 50 日。对此,索林曾特别提出应予区别对待,题本内容如下:“蒙古斗殴杀人应照刑律分别保辜治罪也。
查蒙古律载,斗殴伤重于五十日内身死者,将殴打致人拟绞监候等语,其斗殴伤轻于何日内身死作何拟罪之处,蒙古律内并无明文。即以伤重而论,有手足他物金刃汤火致伤之不同,复有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之各异,刑律俱系分别保辜,蒙古律内亦无区别。是以蒙古遇有斗殴杀人之案,但于五十日限内身死者,多照律拟绞。伏思杀人者死,法令昭然,既因斗殴而杀人之命即不论其日远近,拟以抵偿,亦属理所当然。惟是我圣朝大德好生,凡是关人命,苟有一线可原,无不曲为矜恤。故民人命案于刑律所定辜限之外,复定有限外十日、二十日之内,果因本伤身死情正事实,方拟死罪,奏请定夺,此外不许一概滥拟渎奏之条,无非欲生者不致含冤,死者亦无遗憾。
乃独于蒙古斗殴杀人,则于五十日内身死,概行拟绞,似觉偏枯。且遇有蒙古殴死民人及民人殴死蒙古之案,承审之员未免执持两议,意为高下,亦非一定不易之良规。请嗣后蒙古斗殴事件均照刑律开载,手足及他物伤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者,无论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如限内因伤身死,依律拟绞,其有手足、他物、金刃及汤火伤,限外十日之内,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限外二十日之日,果因本伤身死,亦依刑律拟以死罪,奏请定夺。”①从所奏内容看来,索琳认为对于蒙古地区保辜应完全依照大清律予以分类裁决,但从乾隆五十四年 《蒙古律例》的修订,以及嘉庆 《理藩院则例》中来看都没有体现,可得知该建议并未被采纳。虽然索琳的提议未被施行,但从中可以推断出蒙古律对斗殴伤害案的重处。蒙古律中不论伤害程度与伤害手段,一律规定保辜期限为50 日,与大清律中最短保辜期限 30 日相比,足足长了 20 天,这让殴打之人的法律责任更重。
如贾德一案,按照大清律,保辜期限为 40 日,邵廉舒逾 48 天身亡,贾德只需依殴伤罪定拟,然而依照蒙古律,贾德就需拟绞监候。蒙古律之所以作出此项规定,这与蒙古民族的好斗性格密不可分,斗殴在蒙古地方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因此对其予以重处。
通过保辜,可以看出,一方面蒙古本身社会的发展,很自然地吸收了中原的一些先进的法律制度,如中原的留养承嗣,②在司法实践中也频频适用,在此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也是有意识地将一些有适用价值的法律融入到蒙古立法中,保辜制度是蒙古立法内地化的一个缩影。在刑罚方面,蒙古原有主要是罚牲刑,然而到了清中后期,如枷号、鞭刑、流放、刺字等在蒙古地区也开始得到广泛使用,此外,五服制罪①等儒家文化也渗透到蒙古立法中。
结 语
嘉庆年间贾德保辜一案,双方均为汉人在蒙古地区犯事,对汉人到底适用何种法律,虽然一度有争议,但从清廷最后的处理来看,适用了《蒙古律例》的相关规定,这充分说明了到嘉庆年间,在法律适用原则上已过渡到绝对的属地主义。在蒙汉交往问题上,从清初绝对的属人主义到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最后到绝对的属地主义,不仅仅反映了蒙汉杂居与相互往来日益加强的时代特点,更揭示出 《蒙古律例》作为清廷治理蒙古地区的特别法,拥有优先权,且随着清廷对外藩蒙古统治的渐趋稳固,逐步加以推行与实施,是清廷强化对蒙古控制的必然反映。
清廷在强调 《蒙古律例》、 《理藩院则例》等特别法优先权的同时,却在 《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中逐渐渗透更多的内地立法原则与精神,如保辜、留养承嗣等。又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二十二年定: “凡办理蒙古案件,如 蒙 古 例 所 未 备 者, 准 照 刑 例 办理。”[2]( P. 1257)可见, 《大清律例》仍然是适用蒙古地区的一般法。从立法上来说,清朝统治者高瞻远瞩、因俗制宜,灵活制定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特别法,然而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适用法律时,注意将中央一般法和民族地方特别法有效协调,积极渗透,可谓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立法与司法的集大成者。
〔参 考 文 献〕
〔1 〕清会典事例 ( 卷九百九十六) ·理藩院·刑法[Z]. 北京: 中华书局,1991 ( 影印本) .
〔2 〕清会典事例 ( 卷九百九十四) ·理藩院·刑法[Z]. 北京: 中华书局,1991 ( 影印本) .
〔3 〕蒙古律例·回疆则例[Z]. 台北: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 236.
〔4 〕富俊等. 科布多事宜 [Z]. 台北: 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 ( 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
〔5 〕马建石,杨育棠.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 [Z].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6 〕高绍先. 中国刑法史精要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226.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夏,河南夏邑等州县雨水过多,导致严重的洪涝灾害出现。次年二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上奏乾隆帝,称夏邑受灾土地上高粱收成很好,只有谷、豆等有所减收,灾情并不严重。乾隆帝下令对夏邑和与之相邻的商邱、永城、虞城四县提供赈济一...
清代官府日常的理讼必须对当事人及相关证人当堂审讯.差役凭官府签发的信票(差票)将当事人等从居住地带至县城歇家,等官府悬牌示审,再由差役于审讯当日将当事人等带到官衙进行审讯.这种传讯的过程在传统的行政运作中属于催勾事务的一部分.所谓催勾,催即催科、...
从法律社会学的视阈出发,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唯一的行为规范,国家法之外还广泛存在着类型多样的其他社会规范,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整体法秩序。中国传统社会的法秩序在总体上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伴随着皇权专制自上而下建构的国家法...
汪辉祖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代名幕。在他三十多年从幕生涯中,不仅协助十多位幕主办了不少疑案,在当时取得了很大名声,而且尤其善于引经决狱。本文所写的几个判案小故事,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在无锡处理浦四童养妻与未婚夫叔通奸案乾隆二十一年(1756),...
自唐代起,历代封建王朝都建立了成体系的法律制度,经过近千年沉淀、发展和完善,至清代,封建法律制度已经比较成熟。清代婚姻制度反映了清代的专制主义与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折射出诸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婚姻故事。一、择偶...
清代书吏问题是清史学界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不过,囿于材料,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州县书吏身上,并以此扩展到对整个清代地方政府的研究。对于部吏,从晚清起,无论政治家还是学者,都对其在王朝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予以高度认可,但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多。现有研...
一、清末司法改革的肇因(一)清末司法改革的思想基础在经历了西方列强的摧残和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之后,维新派即改良派应运而生,他们对清末的形势和局势进行了分析和考量。于是他们,文化上主张兴办西学,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其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
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要求它的调整工具法律,无论在调整方式还是在调整范围上,都要作相应的变革[1]。清入关后,统治者为了维护新政权的良性运转,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统治秩序,允许暂行明律。这在当时是非常可取的办法,对于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起到了一定...
一、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现状及不足死刑复核权下放至省高院的这段时间,出现了诸如赵作海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等冤假错案,极大刺激社会公众原本就敏感的神经,公众甚至对我国司法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担忧,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鉴于此,最高法决定从2007年1...
传统中国,民商事纠纷的解决存在司法审判和民间调解两条路径,这已是学界共识。二者共同构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法律制度。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广义的清代法律制度在其运作之中,同时包含着官方正式的司法制度和民间非正式的纠纷处理制度,前者以审判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