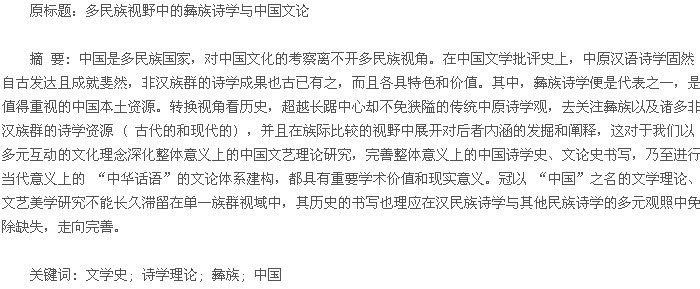
中国是 56 个民族共居的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考察离不开多民族视野。就文论及美学而言,从多民族视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群诗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时间维度讲,“彝族诗学与中国文论”这一话题应包含古代和现代两个层面,但本文把着眼点仅仅放在彝族传统诗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对读上。之所以做此选择,一是古代诗学和现代诗学有较大的分野,就二者做比较研究是个很大的话题; 二是彝族传统诗学与中国古代文论已是既定形态,加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迄今仍可谓是“显学”,论述起来对象容易把握且有现实意义; 三是在传统与古代的范围中,以 “中国”冠名的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迄今对彝族传统诗学仍关注不够,其中有不少问题值得学术界反思。
①不必讳言,在汉学主位的中原传统诗学或文论视域中,作为族别 “他者”的非汉族群诗学长期被边缘化,人们对之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原汉语诗学固然自古发达且成就斐然,非汉族群的诗学成果也古已有之,而且各具特色和价值。其中,彝族诗学便是代表之一,是值得重视的中国本土资源。聚居中国西南部的彝族是有文字的民族,也是诗学智慧发达的民族,不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而且留下了凝结思想成就的诸多文献典籍。彝族民间叙事长诗 《卖花人歌》即云: “彝家的故事能填满山谷,彝家的古经就象那瀑布,三天唱满一面坡,九天唱满一个湖。”
①种类多样的彝文古籍中不乏诗学方面的精彩论着,犹如举娄布佗在 《诗歌写作谈》里所言: “从那古时起,彝地人世间,着书藏书多,诗文论着多。”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有 《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等。
《彝族诗文论》作者举奢哲是古代大毕摩、大作家,他知识渊博,着述宏富,着有 《祭天大经书》、《祭龙大经书》、《做斋大经书》等系列经书,以及 《黑娄阿菊的爱情与战争》、《侯塞与武佐》、《降妖捉怪》等文艺作品,被彝人世代敬奉,彝文古籍即云: “古时的人间,知识大无边。有知识的的人,他来安天门。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天门他来开,地门他来管,有知识的人,宇宙他来管,……先贤举奢哲,他来传知识。他是什么人,至尊的大师。”
②根据彝族 “盐仓”家谱记载,举奢哲生活的时代为清康熙三年 ( 1664) 往上推 66 代,大致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语诗学系统的《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诗品》作者钟嵘等的时代相近。举奢哲的 《彝族诗文论》是彝族古代文论奠基之作,用五言诗写成,共包括 “论历史和诗的写作”、“诗歌和故事的写作”、“谈工艺制作”等五个部分,从立足文艺创作的实际出发,就想象和虚构、作品的内容及作用、文艺的审美和教化功能等问题展开讨论,触及诗文理论中若干根本问题,不乏真知灼见。比如,对诗的作用,他的概括是:
既可 “唱来颂君长,唱来赞君长”,又可 “唱来骂君长,唱来恨君长”,是表达人们对统治者爱与憎的社会情绪的风向标; 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把它当作 “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情感、表达爱意的媒介与工具。又如,说到 “诗”与 “史”的异同,人们往往会想到欧洲文艺美学史上赫赫有名的 《诗学》,想到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亚里斯多德对此的精彩论述。其实,在东方诗学领域,被族人尊称 “先师”的举奢哲也以其经验之谈,谆谆提醒从事写作的人: 叙述历史务必事事求真,创作诗歌需要驰骋想象,二者遵循着不同的写作规律。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写诗歌,不像写故事。诗歌和故事,可以是这样: 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相像,就可做文章。可以有想象,夸饰也不妨。”为此,他针对故事创作的真实与虚构问题提出 “须有六成真,可有四成虚”,或者有 “七成真实,三成想象”,认为如此方可 “把人写活,把事写真”。
这位彝族学者尽管生活年代晚于古希腊哲人,但由于地域和语言的巨大界隔,若是简单套用比较文学中的 “影响研究”来观照二者恐怕很难。在笔者看来,从尊重言说者的 “主位” ( emic) 立场出发,二位诗论家观点接近实际上是各有其文化发生土壤的 “英雄所见”。换言之,东方世界的举奢哲和西方世界的亚里斯多德,他们作为诗学家在对各自民族文化的深刻体验和感悟中,阐发了有关 “诗”、“史”异同的重要观念。
“诗歌叙天文,诗歌叙地理”,③这是彝族先民自古就有的诗学认识。彝族文化史上,传授知识、论诗写书的伟大先哲除了举奢哲外,还有着名的女经师和女诗人阿买妮。追溯历史,文字、农耕乃至医药的发明在彝民心目中跟女性相关,彝族经籍 《物始纪略》、《西南彝志》便记载彝文创制于远古女性中心时代,并且极力称赞 “女性有知识,女性有智慧”。时代近于举奢哲的阿买妮甚至被彝民尊奉为传播知识、文化的 “女神”,称为 “恒也阿买妮” ( 恒也在彝语中有 “天上”之意) 。她不仅有《独脚野人》、《猿猴做斋记》、《横眼人和竖眼人》等作品传世,其中 《彝语诗律论》尤其是她在彝族诗学方面的杰出成果,大而言之,也是她对整个中华文艺美学的重要贡献。翻开 《彝语诗律论》,我们看到,既写诗又论诗的文艺理论家阿买妮从创作美学入手,阐述诗歌的体式和声韵,探讨作者的学识和修养。凡此种种,堪称论述到位,见解精辟,而且从头至尾都是一边举诗歌创作例子一边讲诗歌创作理论,既有实践针对性又有理论提升性,由此体现出理论和实践联系的论诗原则,相当可贵。
今有研究者指出,无论从理论内容还是从理论形态的精湛程度看,《彝语诗律论》 “都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彝族古代诗学着作”。
①此外,立足当代,从 “性别” ( gender) 和 “民族” ( ethnic) 这两大学术热点切入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艺美学史,以冷静、客观的目光透视多年来学界对此历史的传统表述和惯性书写,就会发现一种 “缺席/在场”的怪异现象。所谓 “缺席”,是说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史的书写中,女性批评和少数民族批评大多是在视域之外并且缺少席位和话语权的; 所谓 “在场”,是说女性批评和少数民族批评尽管常常被遗失在主流书写的史着之外,但自古以来二者的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抹不去的。长期以来,思维定势使然,在历史形成的男性本位和汉族中心的话语框架中,作为性别 “他者”的女性批评和作为族别 “他者”的少数民族批评在传统中国文论体系中同处边缘地位,造成了中国文论史在书写上的某种偏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及理论研究史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是 1927 年陈钟凡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问世,1997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 《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便是以此为学科起点。后者分别从资料整理、史的编撰、专题与范畴研究以及大陆和港台、古代与现代等方面为读者梳理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所涉及的本土古代文论信息不可谓不广,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并不见有关于女性文论的专门章节。
②明乎此,再来看彝族女性作者阿买妮的诗学,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成就和价值绝不可低估。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影响深远,“风骨”作为其中名篇是刘勰 “把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风骨’概念,取其精神,加以改造,移用于文学”③的成果,而 “骨”亦是贯穿华夏古典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两汉人物品鉴重骨法”,④诗歌、绘画等也时时讲 “骨格”、“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原传统美学之外的彝族阿买妮的诗学论着中,也屡屡有见 “骨”范畴的使用,不但表述自成系统,其美学含义亦别具特色,如: “举奢哲说过: ‘每个写作者,在写诗歌时,声韵要讲究,人物要写活。诗文要出众,必须有诗骨,骨硬诗便好,题妙出佳作。”又如: “文章讲音美,诗贵有硬骨; 无骨不成诗,无音不成文。”在她看来,“诗骨从旨来”,“写诗抓主干,主干就是骨”,创作者要根据不同内容确立不同的诗 “骨”,所谓 “诗骨如种子,种子有各样,各样种不同”,同理,“诗骨各有异”,“因诗而不一”,切忌笼统划一。作品是有机的整体, “骨”与 “肉”相对, “骨肉紧相连,整体不能分”,诗人务必处理好二者关系,否则, “只有骨头在,没有血肉身,写出的诗文,骨立就差矣”。按照彝族诗学的观点,这 “骨”是关系作品能否传世的命脉所在,它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生命力,“诗若无骨力,任你写得多,再多也无用,后传没有根”。因此,这位女性诗学家再三强调诗歌要有 “骨力”。放宽视野,对 “骨”的看重又是彝族文化的极重要特征之一,非惟体现在其传统诗论里,也投射在其民间艺术中。以出自毕摩之手的民间美术为例,⑤他们在仪式活动中绘制的神图、鬼板就是以线条 “画骨”作为其构图的主要方式。2012 年 4 月,笔者参加四川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评审会,读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文化馆编写的毕摩绘画传承人刷日拉都的推荐材料,其中介绍其技艺特点时即指出,“抓住 ‘骨’的本质特征,以 ‘线条’为主要造型,舍其外形轮廓,画物之 ‘骨’像。体现出拙稚古雅、浑然天成的韵味,又富有力感”。
⑥在彝族同胞的审美意识中,“‘骨’凝聚了对象的灵性与血脉,只要抓住了 ‘骨’便切中并概括了对象的根本; ‘骨’连带着对象的 ‘血亲’与 ‘近亲’,只要画出了 ‘骨’,便把握并超越了对象以及与对象发生关的‘类群’之全部和整体”。
①尊重 “地方性知识”的当代人类学提醒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族群,对于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尽可能尊重当地人的 “主位”立场,结合其 “在地性”语境,关注其 “在地性”生成,才能把握其 “在地性”特征,认识其 “在地性”价值。在族群意识上注重血脉根基的彝族文化中,“骨”以及 “根”作为彝族传统诗学范畴,有其族群文化及习俗的特有积淀和本位内涵,因此,研究者对其特性应予分辨,不可简单套用汉语诗学去识读。
“天地有万物,万物都有根”,②凉山彝族克智的说辞中有此语句。对万事万物之根脉的看重是彝族文化一大特征,如 《彝族创世志》云: “白雁迎土根,青鸿迎地根,兹吐迎女根,凤凰迎男根。胆肺人的根,身躯人的根。舅家的住地,所有根源到。”
③翻开彝文古籍 《物始纪略》第一卷,我们看到,紧接在 “天地的产生”之后,便是 “风的根源”、 “雾霭的根源”、 “万物的根源”、 “种植的根源”、 “医药的根源”、 “女权的根源”等重要篇章,关于 “根源”的叙事占了其中相当大的篇幅。
“寻根”成为彝族诗学传统,盖在彝族文化本身有强烈的 “寻根”意识。“彝族是一个崇拜知识,喜欢思考,用诗思维的民族,对一切事物都要寻根问底,探索其渊源,寻究其来历,这种寻根思维,正是彝族古代文学的指归。”
④他们深信,“万物有根源”,“有根枝叶茂”,“有源水才深”,并且再三告诫 “叙根别错乱”。
⑤反映在彝族诗学中, “根”这范畴屡屡出现,如 “文根”、 “诗根”、 “音根”、“书根”等,佚名 《彝诗史话》讲 “彝诗书之根,书根要讲音,音要讲音根”、 “写诗要抓根,根要诗中有; 有根诗有体,无根诗不生”,举娄布佗 《诗歌写作谈》称 “谈诗要寻根,有根方为上。彝诗无根底,不算好诗章”。彝族诗学中这 “根”,又是与 “骨”范畴密切关联的、基于其族群生活及文化中特有的血统观念。至于阿买妮 《彝语诗律论》讲的 “诗有多种角,诗角分短长”、“韵协声调和,诗角更明朗”,这 “角”就更是有关彝族格律诗的又一独特诗学范畴,其涵义有待学界深入阐发。在多民族中国,在民族与民族之间长期文化互动的语境中,少数民族诗文论确实有跟汉民族诗文论相通的地方,与此同时,也不乏其自我文化积淀和族群特色的话语系统,对此异质性特征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切忌作简单化的 “大一统”式对待,更不可戴着有色眼镜视而不见。
“以诗论诗”是本土诗学传统。说起中国诗歌美学史上的 “以诗论诗”,人们首先会想到唐代司空图的 《二十四诗品》( 该论着的作者归属迄今仍未全然定论,此处暂从传统的说法) ,视之为该体式诗论的开先河者。其实,在非汉族群中,诗性智慧本是他们天然所擅长,对于这种当今学术界有人称之为 “后设诗歌”( metapoem) 的以诗歌评论诗歌的形式,在他们当中并非鲜见。如五言诗体就是彝族诗歌的主流,举奢哲在 《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讲: “彝族的语文,多是五字句,七言却很少,三言也如此,九言同样是,也是少有的,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举奢哲、阿买妮等用彝族五言诗体写就的诗学着作,无疑属于该类型,但跟通常认为是生活在晚唐的司空图相比,他们的时代更早。以诗论诗在其他彝族诗学家笔下亦见,如生活年代大约为南宋时期的布麦阿钮,其着 《论彝诗体例》曰: “诗文有各种,各种体不同,各有各的风,各有各的骨,骨肉各有体,血肉各有分。诗歌有多样,各样与差别。”“诗中各有主,主体各不同,题由主所出,骨肉紧相连。” “万类诗中出,各各显圣灵。性质各不同,四季乃分明。”不同的文艺作品有不同的骨,犹如彝人内部有 “黑骨头”和“白骨头”之分,彼此是混淆不得的,这是诗文创作和诗文审美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彝族以诗论诗也很有特点,例如佚名的 《论彝族诗歌》云: “对于诗歌呀,诗歌体又多,文体各有类,类在诗美妙。谈到诗美妙,美妙在哪里,怎样才美妙? 我来说一说。妙在有文根,根在扎得深,深在知识富。知识靠积累,积累靠钻功。钻攻在刻苦,刻苦在勤奋。”从修辞方式看,由于上下句之间使用了连珠体,让人读起来琅琅上口,不但有奇妙的形式美,而且便于诵读和记忆。
彝族传统诗学中,有名有姓的作家理应重视,佚名论着也不可忽略。如今被定名为 《彝诗史话》的篇章,出自古籍 《实勺家谱》( 实勺乃古时彝族最显赫的部族之一) ,其篇幅不算短,其中论述了彝族诗学开山祖师举奢哲、阿买妮的业绩,是不可多得的彝族古代文论史料。类似篇章还有上述佚名的 《论彝族诗歌》,其中对彝诗之 “体”的分析以及对如何写好这些 “体”的论说,对于创作者甚有参考价值。除了专篇,彝族的诗文论也不时闪烁在其传世文献的字里行间,如水西土语区的 《西南彝志》中有 “论歌舞的起源”、 “论尼伦的歌场”、 “论天地的歌场”等篇章,涉及远古彝家 “哎哺”( 天地、阴阳、男女) 社会也就是原始时期的文艺起源及仪式呈现,其中 《哎哺歌师找对手》记述: “我俩是慕施,以歌诗相会,……读诗文也可,歌雅颂也行……广阔斋场里,平坦舞场上,歌诗又论文,论文又读史。”
①所谓 “慕施”,指歌师、歌手,他们能说擅唱,是彝族民俗活动中的重要人物。乌撒土语区的 《彝族创世志》里亦有 “没有引歌笙,歌师难开口”、 “但无引歌灯,歌师难开口”以及歌师请东南西北中五方 “歌神”的仪式过程的记述: “你若是歌神,请下歌场来,下来设歌场。”“你若是歌神,请下歌场来,下来执歌事。”
②克智 ( 又译 “克哲”) 是凉山彝族民间文学瑰宝,常见于婚娶场合,带有论辩色彩,男女两家参加婚礼者各自选出思维敏捷、知识丰富、能说会道的人作为代表,对坐饮酒舌战,其论辩内容包罗万象,或叙事或抒情,或讲史诗或引谚语,通俗易懂,脍炙人口,富有音乐感。作为彝族社会流传广泛的诗体口传文学,克智说辞中谈到这种二人竞赛式的民间文艺对听众有巨大吸引力时云: “大地的人们,个个来听词,七天不放牧,七天不吃饭。”
③如此谈论文艺的审美感染力,堪与汉语诗学中讲的孔子闻 《韶》乐 “三月不知肉味”相媲美。云南楚雄彝族谚语中的 “访故事如深山里寻菌,编戏如金沙江里淘金”、“山上没有千姿百态的杂木,春天就没有万紫千红的花朵; 世上没有形形色色的人,台上就没有各色各样的戏”,则是对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透露出朴实的美学观念。
彝族诗学发达,跟他们自古有本民族文字并且世世代代重视知识、重视文化的优良传统不无关系。尽管彝族社会重根骨意识讲阶层区分,但在他们看来,天地间万事万物,地位没有高过 “知识”的,哪怕是掌管天下的君权: “世间谁为大,世间知识大,君是第二名,臣是第三名。”因为,“有了知识后,知识代代传。用知识祭祖,用知识祭天,用知识祭祀,用知识诊病,知识收妖魔。有了知识后,君用它掌权,臣用它司令,工用它造物,子用它孝父,女用它敬母,探索大小路,条条通大道”。在彝民看来,“世上无知识,一切都没有”,“有了知识后,人间很繁荣”。知识不但指引着为君为政之道,而且成就着百工技艺,规范着礼仪风俗,协调着人类生活,繁荣着人类社会,创造着人类文明。总而言之, “人有知识后,用来管宇宙,用来造树林,用它来种地。知识传开后,人人靠知识。世上的人们,代代都聪明。知识是金门,知识是银门,知识是铜门,知识是铁门,四门都有了,世间永流传”。正因为如此,诗学鼻祖举奢哲、阿买妮成为彝族人民 “传知识”的 “大先贤”; 被定名为 《物始纪略》的彝文古籍中有题为 《传知识》的专篇,这绝非偶然。今天,世人都非常熟悉近代西方学者讲的 “知识就是力量”,却不知在中华本土,古老的彝文典籍中老早就说过 “学呀学文化,知识出力量,脑筋变聪明,人人都心灵”。
④这种尊知识重文化的理念,千百年来成为彝人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族群意识,无疑推助着彝族文明史上本民族诗学系统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转换视角看历史,超越长踞中心却不免狭隘的传统中原诗学观,从非汉族群的 “主位”立场出发关注彝族以及诸多非汉族群的诗学资源 ( 古代的和现代的) ,并且在族际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对后者内涵的发掘和阐释,这对于我们以多元互动的文化理念深化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完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诗学史、文论史书写,乃至进行当代意义上的 “中华话语”的文论体系建构,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诚然,过去长期由于语言和地域的距离,“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同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相距甚远,在地理位置上具有 ‘边疆性’; 而在文化上,汉文化是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汉族文学占主导地位,进入中原地区的文学作品必须是汉文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不了中原地区,在文化上具有 ‘边缘性’”。
①迄今有关中国古代诗学史的撰述基本上以汉语为表达媒介,而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诗学典籍被译成汉语甚晚,从而使众多研究者难以顾及。然而,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 《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等译为汉文出版到经历了世纪转换的今天,已经 20 多年过去了,如此局面再延续下去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诸多族群的血缘维系着中华民族大家庭,诸多族群文化的激荡交流融铸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冠以 “中国”之名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研究就不能长久滞留在单一族群视域中,其历史的书写也理应在汉民族诗学与其他民族诗学的多元观照中免除缺失,走向完善。
引言与西方的史诗研究传统相比,我国的史诗研究,尤其是南方史诗,仍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的状况。先天不足是指与西方两千年从未间断的史诗研究传统相比,中国的史诗研究历史不足百年;后天失养是指从20世纪中叶到80年代初期,国内史诗研究基本上为...
当今世界,生态危机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和现象愈来愈突出和频发,生态问题已然成为一个全球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界探讨的热点,于是应运而生了化解生态危机的生态建设。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强调要把生态建设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更突出了生态文...
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指的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外国语,如英语等,它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略有差异,后者一范围更广,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汉译以及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研究,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
博葩在凉山彝族民间文学中属较被忽视的文化意象,在民间和学术上没有过多的人了解与研究,一直以来彝族博葩都处于将被边沿化的尴尬境地,而作为彝族母语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而言,博葩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它来源于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的婚嫁喜事或节日集...
《姿子妮乍》是一首古老的彝族诗歌,早在魏晋时期,就已载入彝族祭司毕摩的经籍。[1](P.108)历经千载,《姿子妮乍》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仍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广泛流传。《姿子妮乍》是一首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彝族古诗,从中不仅能了解彝民族的...
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是一部主要流传于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的古典长诗。《勒俄特依》的出版是凉山彝族文学的一件盛事,随后被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纳入到彝族四大创世史诗之列,在彝族文学史上给予了诺苏彝族这一古老的文学传承以应有的地位。〔1〕这部史...
云南巍山,史称蒙化,是彝族文治武功兴盛之地。巍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唐代时有雄霸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南诏国,明清时期有传承512年的蒙化彝族左氏土司。...
广西文学桂军崛起和广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密不可分,民族作家团队及其民族文学构成文学桂军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学存在、生存、发展具有鲜明的地缘优势与地域特征,在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对于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
在传统文化中,月亮多与女性相关同为阴性,表征内守、寒冷以及阴暗。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反复出现的新月意象与主人公新月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其明净、清秀和凄楚与新月的聪慧、美丽与不幸异质同构。喻体、喻指浑然一体,成为联结人与物、感性和理性的桥...
《姿子妮乍》是一首古老的彝族诗歌,早在魏晋时期,就已载入彝族祭司毕摩的经籍。[1](P.108)历经千载,《姿子妮乍》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仍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广泛流传。《姿子妮乍》是一首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彝族古诗,从中不仅能了解彝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