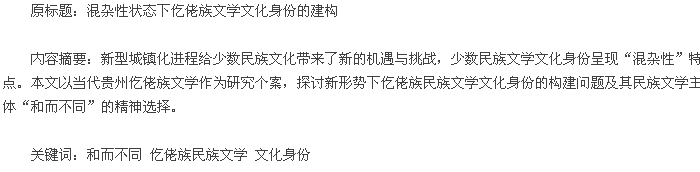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逐步突破传统民族文化羁绊,创新地将民族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熔铸到中国多样性文化建设中,积极地完成民族文化的当代构建,使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新主题呈现鲜明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色彩。在社会学家鲍曼看来,在一个充满“他者”的个体社会里,宽容“他性”的存在,承认相互间的相异性,在差异中谋求一致,才是个体自由、保障的前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家纷纷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突破对原有民族生活的局限,以人性的反思、人性关怀走向每一个生命个体,对人类生命状态进行真实的剖析,不仅展望本民族的未来,也关切人类的集体命运,这是对狭隘民族文化的拓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民族作家在经历了文化混杂化的痛楚后的无奈选择,其实却可以从此“混杂化”中看到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选择,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实现在混杂性状态下民族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
传统文化的反思、女性意识的觉醒等主题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总体走向,这样的思考是在继承民族文化之根与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羁绊的双向抉择中走出的创新之路,是混杂性状态下民族文学文化身份转换与重构的结果.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属于典型的以“自我”与“他者”混杂视.
80年代回族作家霍达在《穆斯林葬礼》 中以混杂视域揭示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路历程。2005 年第1期 《当代》 刊登了仡佬族当代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 《桥溪庄》,讲述了一个由于水泥厂的污染导致桥溪庄男人死精、女人气胎的乡村苦难寓言。桥溪庄的人们默默承受苦难的人生,没有反思,更没有去抗争以获得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选择在愚昧中自救,或者渴望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这里似乎模糊了这群人的民族性,但这样的行为选择带有深深的民族历史痕迹.作者在此深刻反省民族曾经的历史,道德主体是民族,仡佬族人在曾经的历史中正是以包容甚至退让以保全着这个苦难的民族,保住自己的生息之地.妻子的背叛、外人的夺妻之恨本是刻骨铭心的痛楚,但在对孩子的极度渴望中陈小路释然了,他对兰香的理解,一方面展示了仡佬族人懦弱的负面精神与性格,另一方面却是族人宽容本性的释放,回归了他们骨子里对生命繁衍的渴望。同样的思考在 《傩赐》 中也能看到,“一女多夫”荒谬的婚姻现象在远离平原的高山上存在着,那里的太阳是白色的,那里被漫天的白雾包裹着.在此,关于人性、道德等命题,作家的思索是极其痛苦的。高山、贫穷一直是仡佬民族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如斯生存境况所带来的痛苦在族人的心里已经深深扎下根。伦理道德在此似乎失去了审判的力度,因为生存成为第一要务,贫穷面前的道德失去了它的约束力。在强势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强烈对比中,作为民族文化精英的作家们对文化弱势状态感受颇深,只有回归传统文化并以宽容的态度接纳自己的民族根性,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回归母文化,不得不主动反省母文化并吸收新文化,以所构造的“他者”的眼光来认识自身,完成在“和”之下的自我观照,成为创作主体的主动选择。
对女性的关注是仡佬族当代文学的又一突出特点,同样呈现出民族文学主体“和而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构。根据肖瓦尔特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
“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发展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写男性的模式”.以女性自身角度关怀女性的生存状态,摆脱男性角度的束缚,才是女权主义的要旨.当代仡佬族文学中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的影响,肖勤 《暖》、《云上》、 《我叫玛丽莲》 等作品刻意以女性作为表现对象,用她特有的细腻心理体验在逼仄生活中苦苦挣扎生存的女性的心理,并用“花”去进行比喻,有时甚至直接用花来进行指代,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个有意味的符号,表达了她对底层生活女性的人文关怀与悲悯.仡佬族作家除去对女性的关怀外,更将对民族之根的眷恋寄予女性身上。 《寻找丹砂》 就是寻找民族文化 之根 ,“我”对丹砂先天的依恋,祖母于丹砂的痴迷,堂祖公“存丹砂在心”等,其实是对祖祖辈辈开掘丹砂的仡佬族人的根脉延续.传统仡佬族中女性承担的使命远远重于男性,与男性一样劳作同时承担养儿育女的重担,但是在民族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尊重,当代作家在对传统文化反思中深情地关注其生存状况,更关注其精神灵魂状态,追求人类存在的普遍本真性意义,明显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仡佬族作家并未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关怀仅停留在1性与儿童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更深层次的人性反思。在仡佬族的民族历程中,生存问题是最能触动人心弦的那个话题,在生活的磨砺中形成的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是支撑族人走下去的精神动力,为了活着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的价值由此变得虚无,每个个体被永远束缚在生命的链条上,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失去了生命本应具有的许多东西.当代仡佬族文学希望用如斯生存困境与精神磨难提醒族人永远铭记曾经的历史与顽强的民族精神.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凸显族人生存状态的同时,突破了种族的局限,淡化了单纯族人与人类一般性之间的差异性,从关怀民族个体生存状态,民族命运走向上升到人类集体命运的层面.赵剑平《獭祭》、 《困豹》,王华《家园》 都展示出人类家园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破坏的痛苦,用《困豹》 中的话来描述:“我们的天空烟雾弥漫,已经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我们的土地越来越窄,越来越老化,我们的长江水再不是清亮纯净的。而是又浑浊又恶臭.”[2]作家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撕裂的担忧拓展到对整个族类、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恶化的痛苦思索。张承志(回族)、孙健忠(土家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朱春雨(满族)、扎西达娃(藏族)、阿来 (藏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都在思索类似的主题,为了追逐生存的利益,人类失去了与大自然的和谐,曾经相亲相近的自然会对我们反扑。我们未来的路在哪里?
这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共同发出的心灵质疑之声。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的作家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时,不约而同地将解决问题的期盼投向民族文化,温情地缅怀传统文化曾给予人们挽救生存处境的智慧,释放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显现超强的生命力以及积极的精神动力作用,以此来实现民族文化自身的当代转换与重构。 《家园》 中描绘的那个人人友爱共处,山川水木、花鸟虫鱼和谐共生的“安沙”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没有纷争,没有杀戮,有的只是蓝蓝的天,碧碧的河,翠翠的山和淳朴的人。作者描绘的图景,正是仡佬族本着“和合”精神所创造的美好家园。从字里行间投射出的对“安沙”的怀念,何尝不是对“和合”精神的留恋。
混杂性状态是当下民族文化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走向了“文化同化”或者“文化一体化”,而是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有意识地保留了与本民族文化观念相近的观念,改造原有的民族文化观念,弥补了文化间的嫌隙,在“第三空间”催生新的民族文化。
“和而不同”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混杂化状态下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独特方式,“和”指的是混杂性状态下多种文化彼此间的交融渗透,“不同”强调的是在文化外壳相似的情况下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就仡佬族文学而言,走向“和”是以包容并蓄的心态接受汉民族与其它民族文化因子的渗入,坚守“不同”是对本民族“和合”精神、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固守与传承,“和而不同”成为新时期仡佬族民族文化续存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出,仡佬族文学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一部分表征着民族文学文化身份混杂性特点,同时也显现了民族文学主体在混杂性状态下构建文化身份“和而不同”的方式。新时代、新境遇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混杂性是时代文学不可回避的特性,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民族风情、民族服饰的渲染等方面对“民族特色”作表面的、浅层次的描绘,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反思民族文化根性,以包容并蓄的态度批判地接受它民族文化,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把民族化和现代化、把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民族文化续存的新型方式。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着名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幕克因其创作中“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织的新象征”而获得赞许,他还明确表示自己创作的理想就是追求文化的混杂性 :
“我相信混杂化是新生 活 的模式”.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由于生存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中,于矛盾和冲突的文化碰撞中创造、构建着自己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身份兼具“既是此又是彼”和“既非纯粹此又非绝然彼”的特性,同时身陷于文化转换动荡而痛苦的过程中,但正是在这种弥漫性的文化转换,为民族作家获得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宝贵视角,将他们置于“混杂性”空间中,为他们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从而实现了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这是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混杂性理论对文化身份的认识,也是后殖民文化身份理论对当今世界文化批评的意义所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各类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时代的到来。史传文学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中成果最着的一个题材领域,这方面的作品数量多,取得的成就也高,更是出现了像《尘埃落...
一、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情怀概述民族情怀是在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特征,少数民族情怀是少数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民族自豪感。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情怀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文学家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
一、文学人类学的视野: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互动如果要谈文学人类学对重新审视和建构少数民族文学观的作用,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渊源。文学人类学的产生离不开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融合互动。作为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转型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全球化时代和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入研究,以混杂性理论作为核心命题的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得以凸显。混杂性一语,赛义德探讨后殖民时代文化主体身份时分析: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所有的都是混合的,多样的...
文学理论是人类文学活动规律的总结,到目前,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是都能够阐释说明所有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理论是普世、也是普适的。但是,理论在运用时总是表明或流露出使用者主体选择某一理论的动机,不管是出于社会性的功利要求,还...
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指的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成外国语,如英语等,它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略有差异,后者一范围更广,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汉译以及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研究,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
引言根据文化多样性观点,每种文化都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因此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保持文化本身的面貌极为重要,特别是处于文化弱势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其有限的跨语言传播和推广中更需要保持民族文化真实的模样,以此来使少数民族文化独特而珍贵的价值得以...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独特的少数民族气息和女性特征,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地区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下,将写作要点放在对传统社会男权文化的反思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层面,积极倡导将女性视作时代的主人、社会的主人甚至是自己的主人。...
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58年,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开始真正纳入研究视野。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及其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界运用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当然这种批评实...
引言当代汉族作家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促进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而且向我们展示了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人情。比如王蒙在新疆学习生活了16年,向我们展示了伊犁草原纯朴的民族风情。陕西作家红柯在西域流浪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