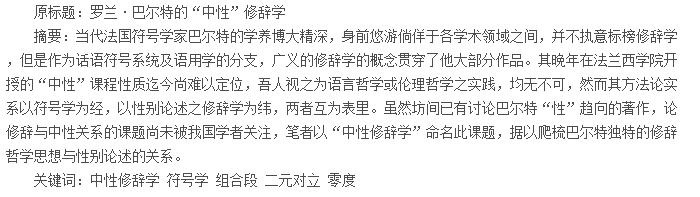
一、前 言
20世纪中叶的修辞学复兴原因驳杂,涉及的思想史和学科史的议题太多,影响的层面极为广泛,即使专业的修辞史家亦很难整理出头绪。笔者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他们皆为欧美振兴修辞学的学界重镇,然而师承有异、路数不一,殊难以修辞学的框架纳入同一阵营,大体以编年为序: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1897-1993)、佩雷曼(Cha觙m Perelman,1912-1984)、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韦恩·布斯(Wayne Booth,1921-2005)、杰哈尔·热内特(Gérard Genette,1930-)、史坦利·费希 (Stanley Fish,1938-)以及列日学派(le Groupe μ,1967-)成员。无论他们是否健在,其学术地位大致已被认定,一般参考书资料多有引述,易于检索,此处不再辞费介绍。在“族繁不及备载”的修辞学队伍中,也许我们可以再加上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Cohen 1994)。
当代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的学养博大精深,身前悠游倘佯于各学术领域之间,并不执意标榜修辞学,但是作为话语符号系统及语用学的分支,广义的修辞学的概念贯穿了他大部分作品。其晚年在法兰西学院开授的“中性”课程性质迄今尚难以定位,吾人视之为语言哲学或伦理哲学之实践,均无不可,然而其方法论实系以符号学为经,以性别论述之修辞学为纬,两者互为表里。虽然有学者讨论过巴尔特的“性”趋向,甚至以虚构的方式要求他出柜(Miller1992),本文第一作者亦曾在台湾大学指导过相关博士论文(Chang Chih-wei 2001),但是论修辞与中性关系的课题尚未被学者关注。笔者不揣冒昧,以“中性修辞学”命名,爬梳巴尔特独特的修辞哲学思想与性别论述的关系。由于这个命题涉及到比较敏感的同性恋论述,某些话题只能淡化处理,或点到为止。
本文探讨的主要语料如下:巴尔特前后所开授的课程纲要经整理后出版的两部作品:第一部是1964-1965年他在法国高等社科院所讲授的“旧(‘古代’)修辞学”(L謘ancienne rhétorique)(见《全集》卷二,1966-1973年, 1994:111), 1970年12月在《交流》16期修辞学专号出版,后收入《全集》卷二901-959页;第二部是1978年2月18日到6月3日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性”(le neuter)的讲座,2002年出版。具现性别修辞或爱欲修辞的第三部作品则是巴尔特的《爱的言谈---片段集》(Fragments d謘un discours amoureux[1977],中译为《恋人絮语》有待商榷)。这三部作品在素材上都可上溯到古典思想史文献。除此之外,本文将旁及巴尔特其他著作中关于修辞的论述,希望呈现巴氏中性修辞学一幅较完整的面貌.首先简述巴尔特的修辞学实践。
二、巴尔特论“旧”修辞学
1964-1965年间,巴尔特在巴黎高等研究院开设了一门修辞学课程,宣称研究“旧修辞学”,事后授课记录整理成文,1970年发表于《交流》杂志第16期,命名为《旧修辞学(记忆术)》(“L謘ancienne rhétorique(aide-mémoire)”)。“旧修辞学”一词,乍听之下,显得怪异,为何不称“古代修辞学”呢?巴尔特给“旧修辞学”所下的定义和所划定的时空范围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9世纪统治西方(仅包括雅典、罗马和法国)的后设语言(其对象语言是话语)”(Barthes1970a:173;1985:86)。作者的定义言简意赅,可得而言者有二。
第一,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9世纪这漫长的两千四百年不可能属于“古”代或“古典”时期,因此这个断代不具传统编年史的意义,而系指称它们作为语料,亦即“对象语言”的资料库(inventory)。传统修辞学处理这部西方修辞史用的是“旧”方法,故以“旧修辞学”名之。为何是“旧”方法?道理很简单,因为学者没有一套现代意义的“后设语言”(métalangage)。笔者认为“后设语言”一语双关,要么作为方法论的隐喻,要么作为反讽,暗示“旧”修辞学欠缺后设语言。这一对关键词“后设语言”和“对象语言”的推出,无疑把修辞学突然拉近到20世纪语言学方法论的语境。众所周知,首先援用这概念到诗学研究的是1950年代末期的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1896-1982),其素材来源是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和数理逻辑学家塔斯基(Alfred Tarski,1901-1983)1933年或1934年的文献。虽然雅各布森未曾交代其用语出处,但这套1930年代的逻辑语言已经属于公共智慧财产,任人挪用。巴尔特私淑雅各布森,他借用了这对术语,把修辞学纳入语言符号科学之下;至于他和索绪尔的差别,主要在于巴尔特的对象语言为实践性的“话语”(la parole或le discours),而非“语言系统”(la langue)。处理话语的是“二阶语言学”,或“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亦即修辞学。巴尔特说这套后设语言是“话语的话语”(discours sur le discours),并非玩弄文字游戏或提出悖论,而系指话语(对象语言)的论述(后设语言),分属两个层次,但最终他希望能师法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建立一门跨符号系统的“一般修辞学”.此处插播一句:后来规模索绪尔的论述,并提出“rhétorique générale”(“一般修辞学”)这个学科,正式缴卷的是列日学派,即著名的“M研究群”,他们追认巴尔特对此新学科的贡献,并尊称(或戏称)他为“法国的新修辞家”(néo-rhéteurfran觭ais)(le groupe μ 1970:15)。
第二,既然有“旧”修辞学,那肯定该有“新”修辞学,在逻辑上前者预设了后者的存在,因为“旧”是“新”的相对概念。巴尔特说,这个“新”文本还没有现身,需要我们把它挖掘出来,挖掘的工具就是符号学,换言之,用符号学来重读“旧”修辞学。巴尔特显然有感而发,也颇有针对性。1958年佩雷曼和露西·欧尔布雷希特-提特卡(Lucie Olbrechts-Tyteca)的《新修辞学:“议论”论文》(La Nouvelle Rhétorique:Traité d謘Argumentation)在法国出版,轰动学界,一时洛阳纸贵。这本书虽然标榜“新”修辞学,但是在方法论上未见新意,主要是作者讨论逻辑推理和价值哲学议题,却没有处理到巴尔特意识到的修辞学的核心---语言符号问题。1977年佩雷曼续作《修辞帝国:修辞学与议论》(L謘Empire rhétorique:rhétorique et argumentation),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回应巴尔特的《旧修辞学》,略谓要更好地了解修辞学我们还是得回归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和辩证法(即逻辑)的区分上去(Perelman 1997:16)。这两位大师有意无意之间的回应、看似冷淡的交锋,其实隐然流露出哲学(纵然属于后形式逻辑的哲学)和符号学在攻略修辞学疆域时的敌对立场。有趣的是,佩雷曼仅提到巴尔特一次,作为负面的开场白,但他的书名“修辞帝国”却出自巴尔特1970年《旧修辞学(记忆术)》的第二节,在该节中巴尔特为其尚未诞生的新修辞学开疆辟土,划下舆地志。才气纵横的巴尔特岂是省油的灯,1970年出版的《符号帝国》(L謘Empire des signes)索性不提修辞学,直接从事修辞学舆地志的日本文本实践,当然包括同性恋的语言、话语和视象修辞,遥指后来的“中性”修辞学(Barthes 2002c)。
巴尔特如何挪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架构来处理旧修辞学呢?他请出索绪尔论语言结构的发现工具,共时轴和历时轴,和一个修辞学的古典隐喻“场合”和“题目”的双重外延义(topos= place = topics,按英语的“commonplace”(陈套语)词源上“场合”、“地点”的意义已丧失),把它们结合,进而发展出一个描绘地形图的解释工具。《旧修辞学》以“修辞学实践”开篇,别有意味,因为巴尔特的共时策略下的历时分析,所涉及到的是各个历时时期关于“修辞学”的对于话语的话语实践。这样的话语实践之广泛,证明了一个“修辞帝国”的存在,其幅员与时延都比任何现实帝国强大。巴尔特所谓的“修辞帝国”建立在“修辞学建立了一种文明之上的文明”这一认知的基础上,认为修辞的帝国是西方唯一的文化实践。这一文化实践确立了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绝对主权,因为这样的话语实践所赋予人类的分类法,不仅体现了历史上各个历史集团的意识形态,也发展出了整体社会的、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的意识形态(Barthes1970a:174-175)。因此,巴尔特对旧修辞的研究也是对西方文化的话语的分析,也是对其整体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回视与结构分析。
巴尔特所谓的“在结构主义视域中研究旧修辞”,其核心在于重建旧修辞的研究对象,并且在重建中表现这一对象发挥作用的规律(或发挥的各种功能),也就是说,要有指向性地模拟出这一对象的“假象”.此中有一个极为深刻的辩证法悖论,在重建旧修辞学的对象语言过程中,巴尔特逐步地写出了、催生出了“新”修辞学。作者选择勾勒历时性的西方旧修辞学的七个阶段,然而对每一阶段的解读都在共时的、系统的面向上进行。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巴尔特的这种“历时”性勾勒与共时性读解结合的研究策略?我们发现,巴尔特以“旅行”(Le voyage)与“网络”(le réseau)这一对隐喻为题,对其研究策略做了说明,我们综合如下:(a)不重建修辞学史;(b)在修辞学两千年历史中隔离出几个时段作为其“旅途”上的“日程”;(c)对每一时段修辞家所操用的分类法进行搜集整理。以上的三项工作,旨在将旧修辞学重建为一种用以进行话语生产的“纲领”(Barthes 1970a:175)。巴尔特使用了两个比喻辞格:“旅行(航行)”与“网络”.用“旅行”隐喻“历时”性的追溯,在这一部分,巴尔特对他在课程说明中提出的七个阶段中修辞家所生产的话语进行了概述;用“网络”隐喻“共时”研究,说明修辞学的历史并非仅仅是历时的。巴尔特提示我们,对于语言赋予文化的修辞学代码的认知,将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和解释其文化,并且修辞学代码所具有的共时性的特质,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与贯穿西方的文化法则和当时之大众文化之间内在的一致性那里,得到了证明。因此,可以说巴尔特重建旧修辞,目的在于重建过去西方文化的言说方式与言说背后的意识形态;修辞学的目的在于解析这种言说,因此,超越了语言的句法层面,不仅将语言的语义分析包括在内,也容纳了语言的语用分析,人类话语的表意与交际都成为修辞学的考察对象。从这一视域出发,我们再看巴尔特为这篇《旧修辞学》添加的副标题“记忆术”,作者承袭了耶米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 的内涵和外延逻辑二分法,继续发挥他在《符号学原理》中的推论,视记忆术为无穷演绎的内涵符号学,与修辞学实为一体之两面(关于“第三人”逻辑和修辞学作为符号学的关系,参见Eco 1988:255)。
三、巴尔特的中性概念与修辞学实践
“中性”(le neutre)概念是巴尔特与“零度”概念同时提出的,但是直至他1978年集中地讨论了这个概念,它才获得了读者和批评者的重视。一方面,它诚然未得到系统、统一、清晰的界定,另一方面,它显得过于具有包纳性因此不够澄明。巴尔特在接受美国《法语评论》(TheFrench Review)杂志萨瓦奇(Nadine Dormoy-Savage)采访时指出:“中性”并不是系统性的概念,系统性的概念不可能为“中性”(Barthes 2002b:737)。我们只能把这句话当作一个讨论的起点,而不得就字面上多作解读,正如我们不宜把巴尔特的宣告“作者之死”就字面义来理解,并据之否定巴尔特在不同场合的任何发言一样。我们尝试做两部分工作:第一,整理巴尔特的“中性”概念;第二,在前一工作的基础上,反思巴尔特书写中“中性”的成分与性质。在第一部分工作里,我们将要梳理各个时期巴尔特对“中性”的界定,探视“中性”概念/思想的呈现及其内涵指向;此外我们也将尝试应用修辞学的辞格术语,一并涉猎巴尔特自己特殊的修辞学实践。事实上,“中性”由音位、形容词、句子直至话语的各个层级发展而来,必然会遭遇修辞学的问题。在句子以下的层面,“中性”只是语言学的现象,在句子之上,“中性”是特殊的修辞策略,而在更为广义的意指系统中,“中性”不仅是特殊的语言实践,也是特殊的文化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巴尔特的“中性”概念、书写、思想的研究,必将反馈于我们对其话语符号学的思考。
“中性”概念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至巴尔特的第一本专著,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第一部分“什么是写作”.巴尔特用“中性的”(neutre)这个形容词修饰一个隐喻的喻依“:任何写作的痕迹都沉淀于一种初见是透明、单纯与中性的化学成分中,(写作的)简单持续逐渐在一种悬停状态中,揭示出越来越厚重的一整个过去,就如同一部密码”.(Barthes 1965:19)“化学物质”这个喻依的喻旨究竟是什么呢?在化学学科中,“中性”表示既不成酸性,也不成碱性的性质,比如纯水。这个来自于拉丁语“neuter”的形容词,表示在两个对立项之间的“非此非彼”(nil謘un nil謘autre)。而在巴尔特的语境中,写作中彼此对立的“此”与“彼”分别是什么呢?是自由与记忆。写作的痕迹最终呈现出有记忆的自由,溶解双方的是否是书写行为?
在“写作与沉默”这一节中,巴尔特讨论到语言学上“中性”,即在两个极项之间建立的中性项,也是零项,并由之引申出“中性写作”,后者这个概念被视作是一种从语言的规约中解放出来的“白色写作”,也称“零度写作”.加缪在《局外人》(L謘魪tranger)中尝试的一种否定写作的风格,可视为是“中性写作”的形式表征,在写作中,思想并不拘囿于语言的社会/神话属性,即不负累历史的承诺。巴尔特认为,这种写作重现了古典艺术(古典写作)的基础:工具性。但是,写作的形式作为一种工具,却不为意识形态服务;形式成为了作家的特殊境遇。作家竭力地创造清新的语言,还要抵抗,以防被社会和历史塑造为他自己语言风格的囚徒(Barthes 1965:66-68)。
综合《写作的零度》对“中性”的思考,我们可以认为,巴尔特在1953年的这部作品中提出的“中性”是对一种特殊书写·行·为的描述,与其说有一种“中性”的书写形式,不如说存在一种“中性”的书写行为。这种书写行为是一种假设存在(或以缺席的方式存在)的对语言的创新,在这一创新中,作家努力使得自己的创造一方面在清新语言,另一方面不至于成为新的限制。
在1964年的论文《符号学基础》中,巴尔特特别辟出一节讨论了“中性化”(neutralisation)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指“语言学上的一种现象,相对应的对立组失去了其相关性,也就是说,这组对立不再有所意指。在一般情况下,在系统关系中的对立组的中性化现象发生于语境的效应之中,因此可以说,‘中性化’现象是‘消除’系统关系的句段关系”(Barthes 1964:127)。举例而言,在音位学上,法语中的é与è处于词尾时,中性化现象就发生了,它们二者之间的替换不会导致意义的改变。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某些语义单位在特定组合中的替换上。巴尔特把这种“中性化”现象从语言学延伸应用至符号学,他提出,当一个符旨(高名凯误译为“所指”)可能存在两个对应符征时,这两个符征(高名凯误译为“能指”)之间就可能产生“中性化”现象。总而言之,“中性化现象体现了句段关系施加于系统关系上的压力。句段关系近乎言语,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意义的一个因素。在一个符号系统中,系统关系为主导则意味着句段关系的匮乏,反之,句段关系为主导则趋向于导致意义的含混。”(Barthes 1964:129)在1975年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中,在“语言学的寓言”这一片段中,除了“中性”在语言学层面的呈现之外,巴尔特还论述了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中性”.语言学上的“中性”用以解释在某些对立之中的意义的损失,而伦理学范畴的“中性”用以消除压制性的意义之令人无法忍受的标识(Barthes 1975:127-128),也即是说,表征聚合关系的冲突之外的话语。可以说,前者是语言结构层面上的中性,后者是话语层面上的中性。因此,话语中性超越在句子层面的中性操作。相比于对初级意指过程中因二元对立而产生的意义的延宕,巴尔特更为关注在第二级意指活动中悬置话语冲突性,比如,避免某一(甚至任何)意识形态对话语的主导作用。
此外,《自述》中特别设置了题为“中性”(“Leneutre”)的一个片段,在该片段中,巴尔特的话语中性思想表露无疑。他将“中性”界定为“二律背反的反对物”(1975:135),“是对炫耀、掌控以及威吓的一切回避、破坏甚或嘲讽”(1975:136)。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片段中作者首次区分了“零度”与“中性”,而在之前的写作中,巴尔特总是将“零度”与“中性”合并谈之。他认为,“零度”是一种第三项,是一种在语义和冲突两个方面都对立的中间项,而“中性”则是“言语活动的无限链条上的其他一个缺口,是一种新的聚合关系中的第二项,相对应的,暴力(斗争、胜利、戏剧、傲慢)是其饱和项”(1975:136)。
此外,《自述》中性也表露了作者对意义方面的“中性”的重视。比如,“排除意义”这个片段里,他阐述了在“大众意见”与知识分子不懈努力要引入社会的“意义”之间产生的一种张力,主张要排除“大众意见”的同时,梦想对“意义”的排除(1975:90)。在“意义的波动”这个片段中,巴尔特延续了“排除意义”的主题,同时指出,文本、意指活动以及中性都是意义波动的形式(1975:101-102)。“中性”操作对于意义来说,即是避免固定的意义(比如大众意见的意义),同时避免无意义。
在1973年的《文本的愉悦》中,巴尔特用“中性”来表述“文(文本)”(Texte)的性质。巴尔特写道,他之所以热爱“文”,是因为在“文”中绝少话语上的冲突。“文”不是一种“对话”,“没有虚假、挑衅、敲诈,也没有个人私语的斗争”,“它在人类关系的内部,建立了一座环岛,彰显出悦的非社会的天性”,以及“使人隐约瞧见欢的诱人至极的真实”,“文”“将十分可能是言语已然摈弃了的所有的想象界的内容,中性”(2002a:227)。
在1977年的《爱之言谈的片段》,“滴酒不沾的醉态”(Sobria Ebrietas)这则片段中,巴尔特通过一个东方的概念“清心寡欲”(无占有欲),间接地讨论了“中性”的问题。“清心寡欲”不是一个或此/或彼的选择,“占有欲”应该被节制,然而“无占有欲”也不应该显示出来,而是要在其缺席的陈列中,主体从自己的“意象库”(Image-repertoire)中脱离出来,“不主动寻求清心寡欲,让来者来,去者去,无意存留,无意拒绝,接受而不保有,创造不为适存。是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Barthes 1977:277)。巴尔特在《中性》课程中亦利用道家原理讨论“中性”问题。在他看来,道家的启示是先有“不判断、不言语”,再有内心深处的“不判断、不言语”(巴尔特 2010b:48),外部的言语行为要转换为内部的言语行为,直至彻底的沉默,或者说“飘落于语言之外,沉于惰性之中”(Barthes 1977:277)。
1978年2月至6月期间,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特别开设了一门研究“中性”的课程。在课程说明中,巴尔特指出,该课程不再研究语言系统中的中性事实,而是研究话语实践中的中性现象,“中性这个词可应用于一切分节言说的有意义的句段,比如文学的、哲学的以及宗教的文本,也包括经过社会编码的姿态、行为、品行,以及主体的内心活动”(Barthes 2002b:531;2002c:261)。在该课程的讲义中,巴尔特对伦理学范畴的话语“中性”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我把中性定义为破除聚合关系(paradigme)之物,或者不如说,我把凡是破除聚合关系的东西都叫做中性……什么是聚合关系?它是指两个潜在的项次之间的对立,我为了说话,为了产生意义而显现二者之一。”(巴尔特 2010b:10)这一界定贯穿了整个“中性”课程,在1978年2月,巴尔特在摩洛哥菲斯和拉巴特的文学院进行授课时,这一界定也被再度重申:“一切曲折变化,只要避开或打破意义的聚合性和对立性结构,以便搁置话语的冲突性现象,我们都认为属于中性。”(巴尔特 2010b:335) 聚合的本质即在两个项次A与B之间选择其中之一,A与B之间的差异即为意义,对聚合关系的破除自然也就关涉于如何处理差异性。话语的中性则体现为:既不选择A也不选择B,同时拒绝对这两个项次的逻辑对立面非A与非B的选择。
此外,与《中性》课程同期,巴尔特也在其他采访与小文章中谈到了“中性”的问题。在一篇发表于1978年2月6日摩洛哥《意见报》的采访稿中,巴尔特将“中性”与“对断定的悬宕”联系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写作姿态(Barthes 2002b:539-540)。另外,在前文已经引述过的访谈《与巴尔特面对面》中,巴尔特否认“中性”是系统化的概念/思想。
在此,我们稍微回视上述界定,我们基本可以罗列出三类“中性”:语言学“中性”;中性的书写行为,这里涉及到伦理学上的中性话语实践;意义上的“中性”.前面二者可与“零度”概念互通,可视为对二律背反二元关系的中介,但是最后这一类“中性”则是破坏了二律背反,在这一规则之外,建立了新的聚合关系,这即是巴尔特所谓“可写的文”以及“清心寡欲”所意味的“中性”.或者说,我们可以将“中性”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属于回避或破坏了冲突性的话语,第二属于这种回避/破坏的行为,它们可能包括悬宕意义、回避断定等。《中性》课程中,就是巴尔特对二十余项在他看来可能属于上述两类“中性”范畴的熟语进行的分析。
在上述对“中性”概念的历时性界定之外,我们尝试调用修辞学术语对巴尔特所论述的“中性”对聚合关系的破坏进行重述。在巴尔特看来,中性,也体现为一种新的辩证法:“两项的矛盾正通过发现第三项而消失,这第三项不属于综合,而属于延续:任何事物都在返归,但却是以虚构的形式返归,即以螺旋的新的回环形式返归。”(巴尔特 2010a:20;Barthes 1975:73)从修辞学的视域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中性对聚合关系的改造相当于辞格“悖论”(paradoxism)对辞格“对照”(antithesis)的中介。“对照”的两项,并不是根据某一特征的有无来区分的,而是由于这两项均被标识出来(marqués)来区分,并且这两个项次之间存在一种既定的且永固的对立;“悖论”却试图调和这种对立,在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建立一种中介关系。在巴尔特的话语概念这里来看“悖论”,它对于“对照”两项的调和,之所以不是综合而是一种延续,是因为“悖论”产生了第三种言语活动。第三种言语活动的永续出现,是“中性”对聚合关系所体现出来的话语冲突性的消解。巴尔特在《旧修辞学》一文中曾隐蔽地指出,中世纪的修辞学训练中,对三段论的操演,以逼迫辩手一方承认自相矛盾为手段,事实上是对在话语支配活动失利的一方进行精神阉割(castration)。然而,在言语能力的场域,并没有任何一种言语活动能够对其他言语行使永久的支配,一方的胜利,随时可能会被第三种言语活动推翻。因此,在修辞学的对立中,胜利总是属于第三种言语活动。“这种言语活动的任务是解救俘虏:分散符旨,分散教条。
……
言语活动之上又有言语活动,无休无止,这便是驱动话语的领域(ogosphère)的法则。”
(Barthes 1975:54)在这一视角下,话语中性是话语所固存的本质,它体现了言谈中话语支配的胜利甚或意识形态的操纵的暂时性。话语中性存在于交际往复中,也存在于任何一次单独的话语使用之无休止的内涵意指活动中,它的任务是解救在话语中被“捉住”的人。这也正是巴尔特试图通过对三十种中性辞格/形象(figures)的论述从而使读者理解的内容:“中性未必如定见所认为的那样,只反映一个平庸的、毫无内在价值的意象,相反地,它可以有重要的和积极的意义。”(巴尔特2010b:335)在以上认知的基础上,我们得以将中性话语与任何断言、外延(discours denoté)以及大众意见(doxa)区分开来,然而并非对立起来。从语言学(而非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语言的天然的论断性来自于语言的代码总是与一种符旨联系在一起。这一符旨既指向存在(être)也指向外延---“言语活动的一种‘真实’状态”(Barthes 1975:71)。从根本上来说,断言、外延、大众意见都是生产固定意义的话语。在《就职演讲》中,巴尔特如此论道:“言语活动是一种立法,语言系统则是一套代码。我们看不到语言系统中的权力,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任何语言系统都是一种分类系统,而任何分类系统都是带有压迫性的。”(Barthes 2002b:431)断言从语言系统进入了话语,这是因为话语由本是断言的命题/场合(Topiques)构成,中性要避开话语,就要反话语的独断论(dogmatisme),悬置存在与语言的关系,这也正是布朗肖的主张。布朗肖认为:“中性的要求不外乎将言语行为的表征性结构(例如‘这是此物、彼物’)悬置起来,即那种与存在有关的时显时隐的关系;在我们的语言里,一旦说出一个东西,这种关系就立即提出来了。”
(巴尔特2010b:75)从巴尔特的修辞学视野来看,中性对于断言的超越,也是“无定所”(atopos)对“地点/命题”(topos / Topique)的超越。“无定所”的话语正是中性的话语,没有被固定在一个阶级、一种固定话语模式的场所中“.大众意见”(doxa),或“公共舆论”正是“命题”的典型体现,是某种重复的、固定的、多数人的精神,是“偏见之暴力”(Barthes 1975:51)。
四“、中性”作为“符号间性”的批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巴尔特的“中性”作一个比较严格的检验。首先我们同意在语音系统中,音位的对立并非绝对。巴尔特以/s/和/z/两个音位既同且异的二元对立为基础,把它投射到人名上,如其名著S/Z中的角色Sarrasine名字中两次出现的书写字母s,由于所处身的场所不同而有/s/和/z/两种发音,并赋予了它们性别的语义值,继续往象征层次发展(Barthes 1970b)。这个例子也显示出“文元”(grapheme)和“音位(元)”(phoneme)的冲突,此虽为题外话,但未尝不能引发关于巴尔特话语/书写符号学更深一层的探索。音位上的对立作了结构语言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础,但是在表面上听来是对立的,更下一个层次却有一些不稳定的、“无以名状的”(“underspecified”)灰色地带,它“中和”了、“中性”化了音位的对立,它可以被称为“原音位”(archiphonemes),布拉格语言学派对此多有发挥。我们不妨说巴尔特企图寻找更原初的存在状态,正如他在《爱之言谈的片段》中召唤出柏拉图的《会饮》篇119DE作为互文本的情况一样。在更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引述会饮者喜剧作家亚里斯多芬里尼斯的一段叙述:“最初,世上有三种人,不像今天只有男女两性。那第三种人具有两性的特质,今天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女/男’(ɑνδρóγυνον[androgynous])。他/她的形象和名字一样,是一个双性的统一体,可惜如今只剩下一个被贬责的名字了(oνεíδει 觟νομα κεíμενον)。”
除了语音上存在的中性现象,中性主要属于语法范畴中的名词类别,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语法上的“性别”(gender)不得与自然性别,即生物的性别雌雄、男女混淆。在法语和希伯莱语中,每一个名词都具有性别,或阴或阳,其代词亦随之区分;德语和俄语则有三性,阳性、阴性和中性。名词是人为的非生物,其性别是附加上去的,是任意性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性别范畴只能被视为高度聚合的分布型态,没有语义基础。不幸的是,用语言的人类,一旦碰到名词的性别(gender)就难免抓狂,会作人称性别(sex)的联结(Taylor 1989:246-247)。许多性别研究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中性论述听来动人,但我们得保持清醒。鉴于性别的差异主导着西方文化,巴尔特竟跨越范畴,反对结构语义成分的聚合体(paradigme)内外的替换关系,然而没有此关系运作原理就没有符号演绎(semiosis),也没有机制让不同范畴的符号系统从事转换,从(名词的)性别过渡到语法、到伦理、到意识型态,符号间性的内涵符号学无法成立,修辞学也就宣告死亡。如果修辞学是舆地志(topology) 和喻词学(tropology)“,无定所”、“无所”、“不在场”或“无所适从”(atopos)意味着中止旅行、去除舆地志“、无修辞学”.此外,巴尔特推崇希腊怀疑论者乐道的“中止判断”(epoche),一再引述伪迪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和胡塞尔的搁置主观性论调,以免陷入武断论的窠臼,但是这一切负面性的、否定论的、甘地主义式的、道家的、禅宗的、所谓没有立场的立场正是另一种武断论(关于身体语义学可能和“中性”否定论的关系,可参见Ruthrof1997:123ff)。归根究底,让我们回到身体(soma)即符号(sema)亦即坟墓(sema)的原初场所,一切都来自生物基因的排序,一切显意识和潜意识的意象数据库都肇因于一个始原性的、遗传性的偶然事件,即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遗传指令赋予了巴尔特未来的性趋向(无妨戏称为“历时轴”吧!),加上后天巴尔特的生长环境(不妨视之为“共时轴”),两种因素的互动使得巴尔特面临了说“出柜/不出柜”与不说“出柜/不出柜”的两难式修辞困境,导致了他反讽地选择了“中性”和不得不说“中性”.
参考文献:
罗兰·巴尔特 2010a 《罗兰·巴尔特自述》,张智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兰·巴尔特 2010b 《中性》,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引言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其他的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单一性,日益成为我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因此语义表达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各种多模态话语中,广告语篇最能体现时代特征,也是最显着地运用多种符号建构...
隐喻和转喻作为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被理论学家研究并且广泛使用。纵观以往人们对这对概念的理解,基本是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的:修辞学领域、认知方式、词汇学领域。但是,通过对雅各布逊的阅读和理解进行新的考察,会发现这一对概念的使用远远不限于此。雅各...
复杂结构隐喻的认知过程区别于传统的二元结构隐喻,要求至少三个或三个以上语义体参与隐喻映射过程。复杂结构隐喻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隐喻现象,其最主要特点在于将三个或三个以上事物建立认知关联,该类型隐喻是汉语和英语中常用的语言表达和修辞结构,如语...
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完善, 必然引起修辞学学科的改造与重建, 正如技巧论与归纳法构建了狭义修辞学;互动论与多范式整合、多参数分析、多视角观照等方法, 则扩建或重建了广义修辞学。...
隐喻研究正逐渐成为一门独立且成熟的学科。认知语言学家GeorgeLakoff等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的产物,是人类利用某一特定领域的经验来理解另一领域的认知活动。GeorgeLakoff等人提出的概念隐喻更强调了隐喻是认知的重要方式,隐喻的思维性和概念性已得到普遍...
一、引言关于韵律特征的定义,国内外众多语言学家都曾提出各自观点。从广义上来说它指的是音高、音响、语速和节奏的变化,狭义上则指超音段特征。[1]张家騄认为:传统上,韵律特征(美国常称之为超音段特征)主要包含音高、音强和时长等三个方面。[2]14...
对某一课题的专门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对研究的课题做出界定,用古人的话来说叫作正名,名正则言顺.对陌生化语言的研究首先要对陌生化语言的概念做出界定,揭示其内涵.要对陌生化语言有比较清晰的理解和认识,首先要明确与此相关的陌生化和语言陌生化这两个...
结语从本文的分析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结合中国具体的政治体制与社会语境,在内容上灵活变通地采用逻辑诉诸、情感诉诸、人格诉诸、同情认同、对立认同、无意识认同等修辞策略,为实现政治目的劝说行为争取了听众的同一,不仅清晰地阐述了新一届中央...
一、前言巴赫金是当今最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俄罗斯学者之一、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早在他1929年问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就提出言语体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他着手对言语体裁进行专门研究,写出了《言语体裁问题》一文,此后又...
厘清修辞能力的概念,在理论上可对加强外语能力与国家修辞能力研究作有益的补充,在实践上可对提高大学生的修辞能力与支撑国家修辞能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