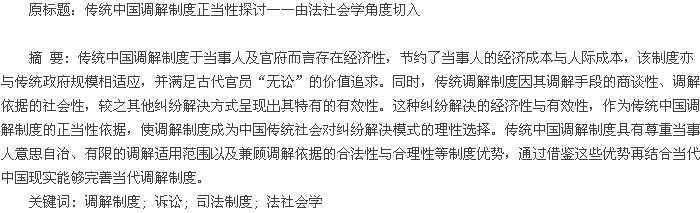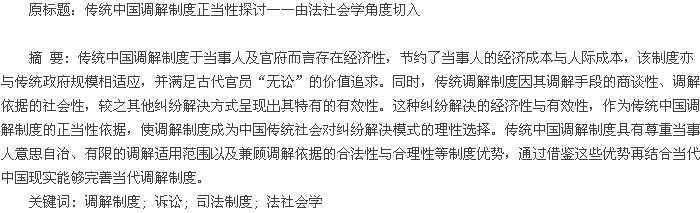
一、引言
调解,指的是纠纷发生后,由第三方主持,依据一定的共识观念和社会规范,进行劝解、调停、斡旋等行为,以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合意,消解冲突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调解是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尽管古代中国的法律条文极少提及调解,但调解构成了传统中国法律生活中最经常、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近年来,立法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越来越注重从传统中国调解制度中吸取有益因素,以矫正现有纠纷解决制度的不足。但由于人们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正当性和借鉴意义缺乏深入思考和探究,致使在纠纷解决实践中广泛存在不调不判、名调实判、以调代判等不合理现象。调解在纠纷解决上的经济性与有效性,使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对纠纷解决模式的理性选择。考虑到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行动逻辑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不难发现,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对当代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有着显着的借鉴意义。
二、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经济性分析
( 一) 对当事人的经济性
有学者认为,当事人究竟选择什么调整方式,诉讼还是调解,依赖于利益的计算,依赖于哪种方式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这体现了人们在纠纷解决方式选择上的经济性考量。具体就传统中国而言,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生产与生活模式,意味着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影响的大小,成为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首要考虑。由此,调解流程的简单快捷、调解过程的协商性特色,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社会生产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与破坏,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与人际成本。
一方面,相对于诉讼审判而言,纠纷调解更有助于当事人经济成本的节约。在传统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农务对于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进而成为人们选择社会交往、文化娱乐乃至纠纷解决的首要考量因素。一般而言,作为官府主持的强调举证与质证的正式化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审判过程需要当事人花费大量知识、时间和金钱成本,才能获得判决结果上的胜利。一旦进入严肃的诉讼审判程序,家庭一般会派出最主要的成员去应诉,而这个人选通常是在农业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成年男性。由于审判程序复杂,耗时长久,农业生产活动被突如其来甚至频繁的应诉活动所耽误。再从行为要求而言,诉讼审判过程的形式主义特征,意味着当事人需要支付相当数量的金钱,以负担其间产生的花费。以诉状呈递为例,西周时起,法律规定,除轻微案件当事人可口诉之外,重要案件均须提交书面诉状。唐宋两朝,法律对诉状已有明确要求; 元代开始,法律对诉状撰写有了统一规范的格式; 明清时期,法律甚至对诉状的用语做出严格的规定。
可见,随着诉讼审判制度的演进,传统中国对于诉状递交的要求愈加严格。这意味着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前,需要亲自或者聘请代书讼师来书写诉状。于民众而言又是一种精力与物质的成本消耗。在节约成本的层面,民众更需要一种用时快捷、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审判而言,调解的经济性便凸显出来。如果选择调解解决纠纷,当事人就可以相对自由地安排调解和农业生产的时间,将纠纷解决过程对农业生产活动的冲突尽力降低。当事人亦可就近选择调解的场所,宗族的祠堂、宗长的家中乃至日常生活的院落均无不可。另外,参与方式灵活自由,民众以自身精力与金钱所能负担的最具经济性的方式来参与调解。
例如,当事人可自由选择口头或文本方式来陈述观点。口头陈诉过程是各自观点的集中阐述,抑或是你来我往的对辩,并无限制,而即使文本陈述,也无需递交审判诉讼所需的规范文本诉状。
从调解的参与人员角度而言,不同于公堂应诉的严肃性与正式性,调解的当事人不拘泥于最主要的男性家庭成员来担任,调解的中间人也不限定于具体某个权威人士担任。而且调解一旦达成合意,即时告结,用时较少,方便快捷。显然,自主的时间安排、就近的场地选择、灵活的参与方式、多元的参与人员、快捷的结案程序显示出调解耗时较少、成本低廉、程序便捷、方式灵活、节约当事人经济成本的特质。
另一方面,调解对于人际成本的节约与保护,也充分展现了其在纠纷解决上的经济性。如果说时间成本与金钱成本的节约是一种显性的经济性,那人际成本的节约与保护则是一种隐性的经济性。在小农社会中,民众的活动区域受到很大限制,人际关系呈现熟人化。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属于格鲁克曼( M. Gluckman) 所谓的复杂关系,即目的复杂、接触面广、存续时间长,是一种长期的不断发生的关系,不适用于用法律分清是非、权利与义务。
人际之间的亲属朋友关系,同时也附带较强的经济、文化等关系。破坏任何一种关系都可能意味着相关关系的断裂,正如《金翼》中所谓的“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人际交易不限于一次,人们通常希望以诚实守信维持交往,尽力持有宽容忍让的态度以促成纠纷解决。尽管一方当事人的诚实守信与宽容忍让并不一定能带来纠纷的解决,但从社会交往的持续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角度考察,寻求一种对人际关系破坏最小、人际成本耗损最少的纠纷解决方式,仍是最优选择。社会的发展要求并促成了这样一种经济人的思维方式。相对于诉讼审判非此即彼的判决思路、败诉人可能招致的笞杖拷掠以及审判之后可能带来的“一到讼庭,终身仇敌”( 真德秀: 《再守泉州劝谕文》) 的不和谐局面,调解显现出明显的经济性优势。因为调解并非依靠官府在公堂之上严格程序的审判和裁决,也无需进行正式形式的陈述和对辩,可以预防矛盾激化,有助于大事化小。对于当事人而言,不至于因为当时的纠纷结下宿怨; 从长远角度而言,也便于纠纷解决之后,再进行当事人关系的再修复。这无疑有助于维护人际关系和节约交往成本。
( 二) 对官府的经济性
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和环节,纠纷解决是中国古代官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内容。基于传统政府规模和古代官员对诉讼价值追求的考察,调解较之诉讼审判,更能满足官府在纠纷解决经济上的要求。
从秦至清,县政衙门始终是封建司法体系的初级法院。地方发生的各种诉讼案件,一般都由县官直接审理; 户婚田土及轻微刑事案件,县级官府还可进行判决。但由于传统官府是身兼司法与行政职责的机构,尤其是没有现代意义上职权明确、职责分明的机构设置,各级官府长官尤其是县级长官总揽本地赋税、兵役、文化、工商、宗教、司法等事务。具体就司法审判而言,长官不仅主持庭审和做出判决,还主持勘查和讯问及缉捕罪犯,承担现代社会中的法官,检察官,警长,验尸官等职能。而其他幕吏扮演着辅助长官的角色。很明显,这种“一人制官府”不仅造就了地方政府运行中的集权特色,更使地方长官不堪重负。再加上“大多数州县官并不熟悉法律,也无能力写批词”,地方官府实际上并无充足的资源用于民间细故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因而,为了缓解政务压力及积案滞囚情况,官府希望减少诉讼案件尤其是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的受理,让这些纠纷转由乡绅耆老通过调解手段进行解决。由此调解就成为官府推崇的纠纷解决方法。
尽管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但是“无讼”的理想却是儒家官僚士大夫的普遍追求。在官员自身的价值判断中,词讼之兴有损封建伦理道德,伤风败俗,实为“风俗日薄,人心不古”( 《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 之征兆。于地方官员而言,讼息则晋升,讼起则降免。
总之,无论是基于从政理想的追求,还是基于现实为官利益的考量,这种“无讼”的地方治理效果,都成为地方尤其是基层司法官员孜孜以求的最佳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调解制度的运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无讼”理想的实现: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有助于确保地方民心和谐,社会安定; 不仅有利于满足士大夫无讼是求的心理追求,亦可彰显地方安定的为官政绩。
三、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有效性分析
法的有效性问题是法学和司法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在法学理论层面,法的有效性主要是指社会主体的实际行为与法律所规定或认可的标准相一致,那么,在司法实践层面上,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则可以解释成当事人的实际行为与诉讼决定所提出要求之间的一致性。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观察,人们“对法律制度的遵守是基于共同的法律确信,而这种共同确信根据的是得到认可的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
那么,同样在司法过程中,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亦与人们的文化认同密切关联。而正是在这一方面,传统中国的调解活动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具备的有效性。从调解过程的角度分析,调解结果的有效性主要源于其调解依据与手段的独特品质。也恰恰是这种过程的有效性才有利于保障调解结果即调解协议被认可和执行。
( 一) 调解手段的商谈性
较之于诉讼审判,调解的程序性约束较少,这使调解过程中采用的方式与手段更为灵活。调解的过程通常表现为调解人两方劝和,各陈利弊,即调解过程中的“训导”行为。所谓“训”为训诫之意,以中间人的权威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强制教育。
费孝通所着的《乡土中国》中写道: “差不多每次都有一位很会说服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 ‘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
而“导”为因势利导之意,以分析争端中暗含的利弊因素来帮助当事人尽快达成协商的合意。可见,“训”只是手段,是用以强化调解人的权威,其真实目的则在于“导”,将纠纷解决的主动权交给当事人自己。在无形中凸显当事人对协议达成与否的自愿性与履行协议责任的自主性。
或者说,调解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维护权威象征与道德情理的教化活动。因为担任调教中间人的往往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个人或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权威的象征者,由他们主导调解,当事人更容易信服,也更容易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度。而“导”的行为则表明,只要稍加训诫,民众愿意认可这种权威的影响力; 而只要因势利导,民众也大多愿意忍让协商。调解以当事人自己的让步和协商来达成纠纷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地接受官府程序化的判决和裁定,更能保障当事人的自尊,也更能保障当事人对于解决方案的认可程度。尽管在某些调解案例中,当事人的让步,可能受到调解中间人的训诫,迫于权威的压力; 也可能出于经济性考量和利益的引导。但是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里,当事人认可适度的训诫和利诱,当事人出于自治的意思,愿意在权衡利弊之下忍让和协商,以保证纠纷解决方案带来的效益最大化。因而调解中的训导能从心理动力机制上确保调解结果的有效性。
( 二) 调解依据的社会性
作为一种权威性纠纷解决方式,调解或审判都必须以一定的规则或法理作为判断依据。与审判主要以国家法为裁判依据不同,调解对判断依据的要求则灵活得多。由于传统社会的调解主要针对户婚田土及轻微刑事案件,情理道德、乡土人情作为调解依据比之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有其优势所在。尤其在传统中国注重道德教化的执政理念和熟人关系的交往氛围中,以国家法之外的温情脉脉的道德情理作为判断依据,更符合地方官员和乡土社会的法律心理。知礼、温良、谦让、自省方能称得上有教养。因此,反映在普通民众心里,合作协商、宽容忍让成为基本的道德情操与行为准则,自然也成为调解的主要依据之一。另外,诸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亦可成为调解依据。
从其产生的效果来说,相比较源于传统礼教的法律规范,情理显然柔和性更强,民众的接受程度也更高。因为情理源自传统文化,更受一时一地的现实生活的熏陶。此情理早已不纯粹是儒学中的天理人情而更多的是普通意义的道理和人际关系中的那种人情。将现实生活中诸如借贷的欠债还钱、契约的诚实信用、家庭的友爱互助等情理作为主要依据的调解制度,容易在实质上获得比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强烈的认同感。
四、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当代镜鉴
由上可知,传统中国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有限地采用调解方式结案,更多的是出于纠纷解决的经济性和有效性的考虑,是古代社会在纠纷解决方式上理性选择的结果。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这种理性选择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或弱化; 相反,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化即为合理化的判断,就不难发现,在现代社会,包括纠纷解决在内的社会生活方式选择上的理性化,更具有正当性与必然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对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有着鲜明的借鉴意义。
一是调解应当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正当性。日本学者滋贺秀三以“教谕式调停”来涵盖传统中国纠纷解决模式的特质。尽管人们对这一表述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在我看来,“教谕式调停”至少凸显了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当事人自主性的倚重———尽管这种自主性常常为“教谕”或“训导”所掩盖。反观当代司法实践,不调不判、名调实判、以调代判等违法现象,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从本质上看,更是对当事人的处分权和意思自治的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某些调解协议难以得到有效执行的根本性原因。因此,借鉴中国古代调解制度运行的经验,当代中国的调解尤其是诉讼调解应当以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和自愿性为正当性依归。
二是调解的适用范围应当有限度。在“明刑弼教”的法律治理思维指导下,传统中国的调解解纷模式主要适用于户婚田土及轻微刑事案件,这体现了传统中国对调解适用范围的理性思考。但当代社会的调解却存在适用范围不清的现象。例如法院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提倡调解民事部分,对做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这类“赔钱减刑”现象虽有其存在土壤和积极意义,却极易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结合当代法律关系的分析,应注重调解适用范围的限度。
例如: 传统中国民众重视维护与人身关系紧密的民事关系。当代社会同样如此,诸如涉及婚姻继承、赡养扶助、亲友借贷等民事关系,调解最能充分体现经济性与有效性。除此之外的民事关系,适用调解应当谨慎。同时,尽管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更应考虑当事人实质地位的平等性。诸如涉及劳动争议或环境侵权问题,应当限制调解的适用。民事关系保护的利益一旦涉及公共性,应限制调解的适用,以保护公共利益。例如国家机关作为民事关系当事人的案件。
三是调解的依据应当兼顾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刑事司法主要以国家律典或单行法规为判决依据,而民事或轻微刑事案件则更多适用儒家教条或地方习俗解纷尤其是作为调解依据。在当代中国,出于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人民调解或诉讼调解均突出解纷依据的合法性。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过于强调国法权威的调解思路和实践,常常陷于“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中国古代调解制度建设的经验,放宽调解依据合法性的限制,承认地方习惯、道德观念等在调解依据上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胡旭晟. 狱与讼: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朱景文. 解决争端方式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05) .
[3]林耀华. 金翼: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 庄孔韶,林宗成,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8.
[4]曾宪义. 关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J]. 中国法学,2009,( 04) .
[5]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M]. 范忠信,何鹏,晏锋,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1.
[6]徐胜萍. 中国传统民间调解溯源究因[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01) .
[7]魏德士. 法理学[M]. 丁晓春,吴越,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
[8]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 邓正来,姬敬武,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
[9]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5.
[10]黄宗智.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1]徐昕. 司法: 第五辑. 调解的中国经验专号[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12]张伟仁. 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J]. 现代法学,2006,(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