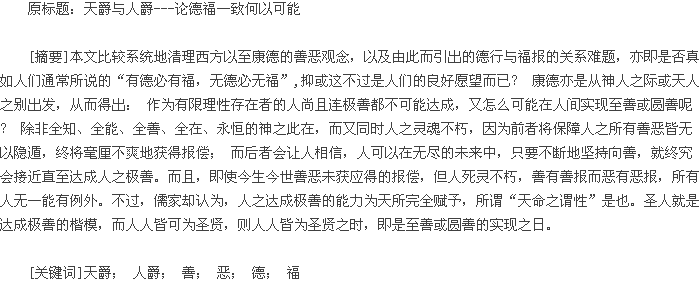
本文比较系统地清理西方以至康德的善恶观念,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德行与福报的关系难题,亦即是否真如人们通常所说的“有德必有福,无德必无福”,抑或这不过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 康德亦是从神人之际或天人之别出发,从而得出: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尚且连极善都不可能达成,又怎么可能在人间实现至善或圆善呢? 除非全知、全能、全善、全在、永恒的神之此在,而又同时人之灵魂不朽,因为前者将保障人之所有善恶皆无以隐遁,终将毫厘不爽地获得报偿;而后者会让人相信,人可以在无尽的未来中,只要不断地坚持向善,就终究会接近直至达成人之极善。而且,即使今生今世善恶未获应得的报偿,但人死灵不朽,善有善报而恶有恶报,所有人无一能有例外。不过,儒家却认为,人之达成极善的能力为天所完全赋予,所谓“天命之谓性”是也。圣人就是达成极善的楷模,而人人皆可为圣贤,则人人皆为圣贤之时,即是至善或圆善的实现之日。
一、善恶与德福
康德认为一般人理解的善与恶,其实多半是福与祸或苦,而实际上这两对概念完全不同,善与恶依凭于理性的原则,而福与祸却仅仅出自于经验。“于是,善或恶本身就关联于人的行为,而并不关联于人的感受状态;倘若某物应当是,或者应当被认为是绝对地(在一切方面都再无条件地)善的或恶的,那么,它就只会是行为的方式,意志的准则,因而是作为善人或恶人的行为者本人,而不会是可以如此称谓的一件事情。”进一步讲,“人按照这种一度对他的自然安排而当然需要理性,以便随时考虑他的福与苦,但除此之外,他还将理性用于一个更高的目的,也就是不只用于思考系自在善或自在恶的东西,亦即纯粹的、绝无感性兴趣的理性才仅仅能独自作出判断的东西,而且要把这种评断与前一种评断完全区分开来,使它成为前一种评断的无上条件。”因此,“善与恶的概念必定不是先于道德法则(哪怕表面看来前者甚至似乎必定为后者提供基础),而仅仅(一如这里所发生的那样) 必定后于并经由道德法则来规定的。”[1](P. 61 -73)[2](P. 31 -72)[3](P. 78 -92)于是在康德这里,只有服从或反对义务命令的自由意志,才是所有善或所有恶之所在或根源。世间的万物或者具有一种市场价格,或者具有一种情意价格,但只有超越一切价格、从而不容有任何等价物的东西,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尊严! 这也就是纯粹的善人及善行[4]( P. 87)[5]( P. 443)[6]( P. 60)。
孔子讲:“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所谓“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
而仁者也就是本心之全德者,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亦即莫不以道德法则为依准,评断自己及他人之善恶。时时处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至成贤成圣。反之,“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也就是说“不 仁 之 人,失 其 本 心,久 约 必 滥,久 乐 必淫”[7](P. 69)。仅以一己之私欲私利评断福祸而不顾道德法则地趋福避祸,终将成为不仁之人! 所以对善恶的判定不能以福祸、乐苦、利害、有用无用等等为标准,而必以道德法则为其根本规定,也就是以“道心惟微”之微,人兽之别的“几希”,亦即人之良知良能为根本标准。
康德指出:“作为纯粹实践理性,它同样为实践上有条件者(基于喜好和自然需要的东西)寻求无条件者,虽然不是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而是当该根据(在道德法则中)也被给予时,寻求在至善名下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之无条件的全体。”这个至善或者说圆善的全体也就包括了作为极善之德行及其所配享的幸福[1](P. 119 -122)[2](P. 115 -118)。理想的方式应当是幸福总伴随德行而有,有德必有福,无德必无福。可古往今来的事实却常常是:有德未必有福而无德未必无福。所谓福或幸福当然包括财产一类东西,孟子讲:“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尽管如此,不过亦可能“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①。然而此足已表明,对所有人尤其对大众而言,德福一致之重要! 就这个问题,西方历史上有两派观点,他们的典型代表就是伊壁鸠鲁派的“幸福即德行”和斯多亚派的“德行即幸福”.前者主张,德行是整个至善,而幸福仅仅是拥有德行的意识。后者主张,幸福是整个至善,而德行仅仅是谋求幸福的准则形式。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德行与幸福同属于至善,然而它们二者却属于至善的两种在类型上完全相异的要素,从而它们的联合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即使德行也只能是配享幸福的资格,而不能是现实中获得幸福的直接原因,因为幸福亦取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以及将其运用于达到自己意图的身体能力,而并不仅仅取决于意志的道德意向。于是至善或者说德福一致尽管于人类是必需的,却似乎对于现实的人类又总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又将怎么办、何以为呢[1]( P. 122 - 126)[2]( P. 118 - 121)?
正如康德在解决纯粹思辨理性之自由与自然的二律背反时指出,作为自在之物或本体的存在者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作为现象或现相的存在者则必须完全服从自然之因果性法则,决无任何自由可言。与此类似,在纯粹实践理性之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上,“两个命题中的第一个:追求幸福产生有德行的意向的根据,是绝对虚妄的;但是,第二个命题:德行意向必然产生幸福,则并非是绝对虚妄的,而是只要就德行意向被视作感官世界中的因果性形式而言,从而当我把感官世界中的此在当做理性存在者惟一实存的方式时,才是虚妄的,因而它仅仅是有条件地虚妄的。
但是因为我不仅有权把我的此在思想为一个知性世界中的本体,而且甚至在道德法则上具有我的(感官世界里的)因果性的一个纯粹智性的规定根据,所以,意向的德性作为原因与作为感官世界中的结果的幸福,就拥有一种若非直接也系间接(借助于一位理知的自然创造者)而必然的关联,这并非是不可能的;这种联结在系单纯感官客体的自然里面无非是偶然地发生的,而不能够达到至善。”于是,康德在道德哲学上否定伊壁鸠鲁派,而有条件地肯定斯多亚派。当然康德也并不否认就伴随纯粹德行而有的一种“至福”(或者亦可称之为“极福”,亦与所谓“极善”相对),他将其称之为“自足”或者“智性的满足”,它在源头上就是对自己人格的满足,只是他不承认那可以叫做幸福,幸福就得是在感官世界中的享受,而至福仅仅是智性世界里的“享受”.他也不把它称作至上存在者的“洪福”或“永福”,而仅仅认为是与之类似而已。至于德行与幸福的关系则必然是:“极善(作为至善的首要条件)构成德性,反之,幸福虽然构成了至善的次要要素,却不外乎是仅以道德为条件的、是德性的必然的后果。只有在这种隶属次序中,至善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整个客体,纯粹实践理性必须把至善必然地表象为可能的,因为竭尽所能地促成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信条。”因为幸福隶属于自然,是思辨理性的对象,而德行必由纯粹实践理性所决定。当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联结成一个必然性认识时,则纯粹实践理性就占据优先地位。因为一切关切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就连思辨理性的关切也仅仅是有条 件 的 而 只 有 在 实 践 的 运 用 中 才 是 完 整的。
[1]( P. 125 - 133)其中康德所谓自足也就是儒家所说的“自慊”,它是通过诚意、毋自欺、慎独或者说自主、自律而达成的至高的道德境界,而最能体现这个境界的莫过于《论语》中大量的看似平实的陈述,譬如像,“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 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当仁不让于师。”“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乃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等等②。
二、不朽与神在
通常西文“不朽”(Unsterblichkeit/immortality)一辞源自拉丁语 in(不)和 mort(死)③。表达一种永久的或超时间的存在状态,尤指人的不朽,即在肉体死后的灵魂存留。而“灵魂”古希腊语为 psy-che,拉丁语为 anima,原本的意思指生命的气息。
灵魂赋予躯体以生命、认知力、思想以及自我运动的 力 量。 躯 体 有 朽 坏 而 灵 魂 却 不朽[8](P. 477 -478,942 -943)。这也就是人的终极问题,亦即人的生死问题以及生前死后的问题。西方哲学思 想 传 统 主 流 是 始 终 坚 持 这 一 主 张的[9](P. 168 -169,343 -344),因而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夏自古虽也有帝天、鬼神、魂灵等等一类的观念,乃至至今也不乏鬼神、魂灵一类的传说,不过,华夏文化的主流却始终依从圣人孔子的教诲“敬鬼神而远之”.西方文化相对于天竺与华夏而言实属彻底入世的文明④,不过依我看,他们的今世却必然以来世做定位。于是,他们在执着乃至执迷于今生今世的同时,还把这种入世的执迷延伸到了对来世的关注当中,以入世的态度及方法面对神在、灵魂存在及不朽等等问题,因而于今世人生之根本似至今都摸不到门却也浑然不觉。
西方在灵魂与不朽等问题的探讨上可谓五花八门,灵魂一方面与生命、心灵相联系,另一方面也与有生命的或有机的物体相联系,于是人们就主要在争论:以某种方式与身体结合的灵魂是作为一个非物质的实体或原理存在吗? 是以身体和灵魂组合在一起构成两个不同的实体或实在的方式,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相关部分结合在身体中吗?
或者,灵魂是一个有机体的实体形式,因此,形式和质料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有生命的复合实体吗? 灵魂是否在它与人类身体的结合之前或之后独立存在? 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持存? 以什么样的方式与身体结合以及分离,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再度与或者别的身体或者如耶教所谓复活的身体结合? 于是天堂地狱、来生来世、轮回 转 世 等 等 一 系 列 的 难 题 就 都 呈 现 了 出来110](P. 613 -624、789 -798,979 -989、1464 -1472)。原本确定人之当下的灵魂,或许不是问题,我常常举的例证是:
凡深深为自己华夏文化所化者,聆听西洋莫扎特、贝多芬等等的交响乐,必会为之心灵感动;但惟有《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梁祝》等才能够震撼我的灵魂! 但若硬要如西方那般言说以至落实心灵为何,灵魂又为何等等,恐怕通常不太可能,或许也不值得! 宁可说心灵如何,灵魂如何,如中国理学家之言心[11](P. 105 - 110),或许更为有益一些。在我看来,康德近于这个思路。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之“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中明确指出,那些妄图在思辨理论上肯定心灵或灵魂在人之生前死后的实存的学说,无论叫合理的灵魂学说,还是叫合理的心理学都不外乎是伪科学而已。因为它们将纯粹思维主体或者说我们思维之纯粹先验的条件或者说先验自我当成了经验实在的对象,而使之实在化、实体化了。从而它们所得出的心灵或灵魂之实体性、不朽性、人格性、精神性等等结论皆属于十足的谬误推理。
“所以,并不存在作为教理而对我们自身认识有所增益的合理的心理学,而只存在作为训练在这一领域为思辨理性设置不可逾越的界限的合理的心理学。以使我们一方面不至于投入无灵魂的唯物论之怀抱,另一方面不至于成群地陷入于我们此生没有根据的唯灵论之中,而毋宁在提醒我们,把我们的理性拒绝给予那些好奇的、超出此生的问题以满意的答复,视之为对我们理性的一种暗示,即将我们浮夸无益之思辨的自身认识转到富有成果的实践的运用上来,这种运用即使也始终只针对经验对象,但却自更高处取得其原则,并如此规定行为,仿佛我们的使命无限远地超越了经验,因而超越了此生似的。”康德由此而提出了属于理性自己特有的领域---“目的秩序”.人的自然禀赋,尤其他心中的道德法则是远远超出他能在此生获得的全部利益与好处的,以至于道德法则甚至教人即使在缺乏所有好处,甚至连死后荣誉的任何征兆都没有的情况下,也要把纯粹正直意向的意识推崇至一切事物之上,他感受到内心的召唤,通过他现世的行为,放弃诸多好处,而令自己适合于成为其理念中拥有的一个更好世界的公民⑤。
于是由此康德的论述转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灵魂不朽上来了。所谓公设,也就是康德所谓事之未必然而理之必然且因此而必认为事之亦然的命题。德福一致之至善或圆善于我们的道德实践与善良生活是必要的,此谓理之必然。
但其达成却取决于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与道德法则的完全切合,而这种完满性在康德看来只有神圣意志那里才可能,不会有哪个感官世界的理性存在者在其此生的某个时刻能够达到,此谓事之未必然。于是依康德,有限理性的德行者就只有在无穷的进步与努力当中,来终究达成自己的意志与道德法则的完全切合,而这又必然会要求德行者的生命之无限。但是人固有一死,于是人们就必须设定:人的灵魂可以不朽,以便人类最终能够达成至善或圆善! 让有德者终究有福而无德者终究无福,善良者终受报偿而罪恶者必受惩罚! 这即是由于理之必然而必认为事之亦然⑥。其实耶教所说的人死后或上天堂或入地狱乃至末日审判,佛教所说的成佛之无量劫的修行以及六道轮回、西天净土等等,无不想达成的也就是这个终极的理。他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无限地推远了来说。康德尽管也是无限地推远了来说,但他不是由宗教而是由道德上来说的,只不过康德终究也会走向宗教,尽管那只是道德的宗教。
终究实现至善或圆善,在康德看来,除了灵魂不朽的公设外,还必须有肯定神在,尤其是肯定神之此在的公设。据说,神是世界中各种形形色色存有物以及一切存有物的根源。它是第一主动因;它们被它所吸引,因为它是它们的最后目的;万物都分享它的圆满,因此显示出神的光芒或痕迹来。根源本身不以任何其他事物为基础,而仅以自己为基础;万物的第一和最后原因本身必须是无原因的,因为它是藉着它自己的本质之绝对的必然存在,是因己而在,因此神的本质和存在是完全同一的;它并不以存在物身份“具有”存有,而是有位格的存有本身---它是自立存有。这就是神的形上本质---它构成了神最内在的本性,藉着它神才与其他一切决然有别⑦。总之,神被说成是万物的最终源头,即是世界之全能、全知、全善、至爱的创造者,它维护世界的自然秩序并维持其道德秩序。但即便如此,在西方关于神的争论也还是始终不绝于耳,所以,在西方文明中,无神论者否认神在,就意味着他们否认的是超自然实体的存在,是犹太教、耶教和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对象。他们否认从无中创造世界的单一、人格的神,这个神超越于这个被造的宇宙,用它的固有力量维持着它,神立法管理所有事物,以它的神佑眷顾每一个个体,它按照它自己的形象造人,向人启示它自己和它的意志,给亚当的后代施以永恒的赏罚,它也以它的恩典救助他们。于是泛神论也被视同为无神论,而自然神论因为拒绝超自然的启示和信仰同样遭致耶教传统的反对。据说,对神在的论证,构成了人类心智超越可感的或现 象 的 经 验 世 界 的 最 伟 大 的 努 力 之一[10](P. 437 - 456)。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论证不能强迫理智同意;我们无法使神在的信念成为非同意不可的信念,这种信念始终有赖于整个人的自由决定。---因此,这种证明的实际目标并不在于使不信者相信,而是给予信仰以一种理智上稳妥的基础和明证,这信仰对许多人来说原先是建立在权威或宗教经验上的[9](P. 177)。
况且依康德,就人类心智而言,无论证实还是否定神之此在,都是不可能的。神在仅为纯粹理性的最高理念以至至上理想,不允许思辨理性对之做出任何实在化、实体化以至物化、人格化的考虑! 我们可以承认由世间所有存在者之偶然性推论出作为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之神在⑧,而不可以承认由此而进一步推论出的一个神之此在。后者正是康德称作的神之此在的宇宙论证明,除此之外,还有所谓自然神学证明,亦即将某种一定的经验、因而对当前这个世界的诸物的经验,它的性状和秩序,用来充当一个能够可靠地帮助我们去确信一个至上存在者之此在的证明的根据。不过遗憾的是,据康德分析,无论自然神学证明,还是宇宙论证明都远不是自身完备的证明,实际上,自然神学证明必须依赖于宇宙论证明,而宇宙论证明亦必须依赖于本体论证明。因此本体论证明才是关于神之此在的惟一可能的证明,然而这个惟一可能的证明却不外是把一个单纯的神的至极完满的概念实在化、实体化以至物化、人格化而已,亦即将单纯的“神是”或“神在”,凭空变作了“神之在此”或“神之此在”.这就好比硬将头脑中想象的纸币拿到现实中来购买商品一般,他人是不可能应许的。于是康德的最终结论是:
“这个至上存在者对于理性之单纯思辨运用来说,依然是一个单纯的、但毕竟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是一个终止整个人类知识并使之获得圆满完成的概念,它的客观实在性尽管不能以这种方式获得证明,但亦不能被否认,并且,如果应当有一种道德神学(Moraltheologie/moral theology)的话,就可以弥补这种缺陷,这样一来,以前只是悬拟的先验神学就通过对自己概念的规定,通过不断地检查一个经常被感性蒙骗得够呛并同其自己的理念不总是一致的理性,而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或缺性。必然性、无限性、统一性、世界之外的此在(不是作为世界灵魂)、没有时间条件的永恒性、没有空间条件的全在性、以及全能等等,十足都是些先验的谓词,因而它们的那个被纯粹化了的、任何一门神学都必不可少的概念,也只能从先验神学中引出。”[12](P. 450 -496)也就是说,康德最终肯定的只是道德神学,其对一个至上存在者之此在的确信仅仅依据于德性的法则[13](P. 455 -505)。
单凭这点我就敢断定,康德超越了西方所有关于神在的神学理论论证。所有神学关于神之此在的理论论证或证明都达不到它们的目的,而与之对立的反驳亦不能成立,因为它们都同样是对人类理性的僭妄! 把仅仅入世此岸有效的态度方法未经任何批判反思地直接套用在了出世彼岸之观念上,这是始终执着以至执迷于入世此岸态度的一种最为典型的表现。康德虽亦未能完全自外于这种态度,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康德的道德神学是企图转变这种态度的开始。所谓道德神学,进一步讲,也就是:“当我们从德性统一性的观点从一条必然的世界法则来考虑那惟一能给这条法则提供出相应的效果、从而也提供出对我们有约束性的力量的原因时,则其必定是一个惟一无上的意志,它自身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法则。因为我们想怎样在各种意志中找到诸目的的完满统一呢? 这个意志必须是全能的,以便整个自然及其与世间德性的关系都服从于它;它必须是全知的,以便它知悉诸意向最核心的内容及其道德价值;它必须是全在的,以便它直接贴近世间至善所提出的一切需要;它必须是永恒的,以便任何时刻都不会 缺 少 自 然 与 自 由 之 协 调 一 致,如 此 等等。”
[12]( P. 598)我们知道,所谓至善或圆善也就是德行与幸福的完全契合一致,这之中首要的就是德行的完满,据康德,这是理性存在者仅仅在一个永恒里面才能够充分完成的,由此我们有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公设:灵魂不朽。进一步,我们践履了完满德行,就获得了配享幸福以至洪福的资格。但德行以至完满德行自身并不直接导致事实的幸福,因为后者属于自然的领域,那么,谁能够将配享的幸福以至洪福完全契合一致而毫厘不爽地赋予德行以至完满德行者呢? 于是,我们由此又有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另一个公设:神之此在⑨。诚如康德所言:“于是,只有在自然的一个具备合乎道德意向因果性之无上的原因被认定的情形下,世间的至善才是可能的。一个其行为能够依照法则的表象而行的存在者就正是一个理智存在者(理性存在者),而且这样一个依照法则表象的存在者之因果性就正是他的意志。因而自然之无上的原因,只要它必须为了至善而被预设,则就是一个通过知性和意志而为自然之原因的存在者(从而为自然的原创者),亦即神。因此,派生的至善(极善世界)可能性的公设同时就是一个本源的至善的现实性的公设,亦即神之实存的公设。既然促进至善原本是我们的义务,那么预设这种至善的可能性就不仅是我们的权限,而且也是与作为需求的义务联结在一起的必然性,因为至善只有在神之此在的条件下才发生,所以这就将神之此在的预设与义务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亦即认定神之此在,在道德上是必然的。”这虽然在理论理性上只是假设,但在实践方面却必定是纯粹理性的公设和信仰。正是因此康德才断定:“道德法则通过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和终极目的之至善概念而导致了宗教,也就是导致了一切义务乃神之诫命而非神之惩罚的知识,”因此,道德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谋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配享幸福的学说。惟有在宗教参与进来,也才出现有朝一日依我们曾关注并非不配享幸福的程度来分享幸福的希望。康德正是据此判定所谓耶教的道德原则自身并不是神学的(从而不是他律的),而是自为的纯粹实践理性自身之自律的[1](P. 136 -144)。
三、极善与至善
至善或圆善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到此该是我们回应康德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康德明知道道德无须宗教而自给自足,比如他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就曾指出过:“道德为了自身起见绝对不需要宗教。相反,借助于纯粹实践理性,道德是自给自足的。”[14]( P. 4)可是他却由于至善问题而终将道德引向了宗教与神(以及灵魂不朽)。
康德的这种做法在耶教文化圈子中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所以我说康德受惠于他所背靠的耶教文明,此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康德是否同时也因此受制于或受限于这个文明呢? 这正是我们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牟宗三就不止一次地批评康德在此“是情识决定,而非理性决定”,而且“情识地需要并信仰一个人格神之存在并不能说明自然与道德品质相谐和;以之为这谐和之根据,说他含有这谐和之原则,这并不能使人坦然明白”[15](P. 254)。
若依康德,孔子所能达到的也就不外乎“极善”,终归是实现不了“圆善”或“至善”的。因为一般而言,“幸福”是要取决于现实经验的条件的,是属于“自然”中的事情。这就好比一幢别墅,不是我想要就可以要得来的。不过在我看来,幸福该是可以分出层次的,大致说来不外乎以下四类,即享乐层面的幸福;荣誉利益层面的幸福;精神层面(比如审美活动)的幸福;纯粹精神层面的幸福1之中除了纯粹精神层面的幸福仅仅依凭极善的德行,也就是说可以始终伴随后者而来,因而我愿意称它为“至福”外,其他三类,从精神层面的幸福到荣誉利益层面的幸福直至享乐层面的幸福,所必须依恃的外在条件会依次地递增或逐渐地增多。
所有这些条件大多位于自然的而不在自由的领域,因而要想它们也实际地成为德行所配享的幸福,就不仅仅是德行自身的事情了。于是我们看到自由与自然的分离,终于酿成了德行与幸福难成一致,这就是至善或圆善问题。
或者我们可以问:当我忠实地践履了我的道德义务之时,我可以希望什么? 应当说,我所希望的幸福并非一切幸福,而仅仅是圆善中的幸福,亦即德行所配享的幸福。因此,幸福在此是有所限定的,它必须受到德行的限定。那么,凡是以幸福为动机的行为,就不是单纯出于义务的行为,因而也就不是德行,其结果无论怎样都谈不上德行所配享的幸福;反之,凡不是德行所配享的幸福,譬如孔子所说的“损者三乐”:“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等等,就更不是圆善中的幸福,而必须毫无保留地清除出去。因此我首先可以希望的惟有“至福”,它是仅仅以德行,尤其仅仅以极善的德行为先决条件的,并且必然伴随德行,尤其伴随极善的德行而来的。所谓“孔颜乐处”就不仅仅是体现了而且是非常充分地体现了这德行与至福的和谐一致。正是因此我才说:德行即至福!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希望什么呢? 至少,作为一位德行者,他决不会为企求世俗的幸福而践履德行,即便这种幸福也是他的德行所配享的幸福,否则,他还能称得上是德行者吗?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是否获得了幸福,而在于他是否配享幸福。一位德行者倘若享受了不是德行所配享的幸福,或者享受了他的德行还不配享的幸福,我都以为是必然会玷污或者至少有损于他的德行。这就是所谓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孟子讲:“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所谓天爵,依朱子,那就是“德义可尊,自然之贵也”,亦即这里论述的人之德行。而所谓人爵,从广义上讲,也就是这里所论述的幸福。而“修其天爵,以为吾分之所当然者耳。人爵从之,盖不待求之而自至也”.看来我们的古圣贤对此是有坚定的信念的,而《中庸》亦载有孔子之言,即:“舜其大孝也与! 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 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必受命。”所以,一位德行者不但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格,而且应该始终以自己的德行、善行去影响他人,甚至“德化”一方,让更多的人成为善良的人。而且他还应该积极地谋求建立一种使人人在其中都能够“有耻且格”的社会制度,从而尽可能地让每一位德行者与善良者都能够获得他们的德行所配享的幸福,总归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也就是朱子所盛赞的“天地气象”、“圣贤气象”.而钱穆先生则更强调“孔门之学,言即其所行,行即其所言,未尝以空言为学”.而且,“盖工夫即在效验上,有此工夫,同时即有此效验。人我皆入于化境,不仅在我心中有人我一体之仁,即在人心中,亦更与我无隔阂。同此仁道,同此化境,圣人仁德之化,至是而可无憾”.这才是圆善的真义! 一般而言,即便“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孔子看来,就是圣王“尧舜其犹病诸”,不过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自化化他,自立立他,自达达他,尽其所能,兼善天下。圣人不道吾治已足,“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然而,“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
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飨帝。”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似犹有进者,他受天台判教而显圆教的启发,承接孔子以来的儒学的发展思路,最终以儒家的“圆教”以至“圆圣”来希图真实地成就“圆善”之可能。所谓圆教即圆实之教,圆者满也,实践上的圆满;实者无虚也,实践上的无虚。而圆教之所以可能,端就有赖于牟宗三所谓无限智心。或许这就是康德所谓神之无限理性或智慧,但依牟宗三此实是康德将无限智心人格化而为一无限性的个体此在,是康德秉承耶教之情识的结果。而中国儒释道三教都有无限的智心之肯定(实践的肯定),但却都未把它人格化。
因而三教皆可以通过各自的无限智心成为圆教而令圆善真实地可能。儒家的无限智心,依牟宗三,乃由孔子之“仁”而开示。孔子之言仁主要的是由不安、不忍、愤悱不容已之指点来开启人之真实的德性生命。中间经过孟子之即心说性,《中庸》《易传》之神光透发---主观面的德性生命与客观面的天命不已之道体之合一,下届宋明儒之识仁与一本等等,由此无限智心之概念遂完全确立而不摇动,而且完全由实践理性而悟入,绝不涉及思辨理性之辩证。有此无限而普遍的理性的智心,故能立道德之必然且能觉润而创生万物使之有存在。只此一无限的智心之大本之确立即足以保住“德之纯亦不已”之纯净性与夫“天地万物之存在以及其存在之谐和于德”之必然性。此即开德福一致所以可能之机[15](P. 243 -265)。
由此,牟先生进一步地论述道:儒家的无限智心之本,除释家解心无染(自性清净心)与道家无为无执外,还有一竖立的宗骨,此即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所表达的道德的创造,即仁心之不容已。于是自我、他人以及一切存在都可涵泳在仁心底润泽中,此即是德行之“纯亦不已”,以至《中庸》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或孔子所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有此浑全不容已之仁心或无限智心者即为圣人或大人或仁者。一般人亦有之,但惟仁者能无丧耳,能通过道德实践而体现之耳。一般人虽不能完全体现之,然总能体现一点,因为它随时可以呈现。只要理性作主,不是感性作主,由其随时可以呈现,吾人即可用当下指点之法令一般人通过操存涵养而时时体现之,终至于完全体现之。此完全体现是可能的,此即函圆顿体现之可能。儒家圆教必须从此圆顿体现之可能处说。所以,牟先生的最后结论是:
圆教必透至无限智心始可能。无限智心能落实而为人所体现,体现之至于圆极,则为圆圣。在圆圣理境中,其实义完全得见: 既可依其自律而定吾人之天理,又可依其创生遍润之作用而使万物( 自然) 有存在,因而德福一致之实践( 真实可能)亦可得见: 圆圣依无限智心之自律天理而行即是德,此为目的王国; 无限智心于神感神应中润物、生物,使物之存在随心转,此即是福,此为自然王国( 此自然是物自身层之自然,非现象层之自然,康德亦说上帝创造自然是创造物自身之自然,不创造现象义的自然) .两王国‘同体相即’即为圆善。圆教使圆善为可能; 圆圣体现之使圆善为真实的可能。至圣神位,则圆教成。圆教成则圆善明。圆圣者体现圆善于天下者也。此为人极之极则矣[15]( P. 305 - 335)。
以上牟先生大体上是顺着阳明学来回应康德的圆善问题的,或许从康德学者的立场会以为有失康德的本意而难以构成对康德的真正应对。若是我们尝试顺着朱子学来回应的话,则可能是:“康德意味上的德福一致,在儒家,当每个人都实现自己的人之所以为人后,便会成为实境。这看起来虽然竟似只比康德所说好上那么一点,但已迥然有别的是,倘若一定还要用助成这个词,则天地之助成力量,已毫无保留地全然贯注于人,这个实境,每个人之德行,皆在亲手打造它,将它带到地面上来,虽然系于所有人其实意味着在己惟成德之一事。这才是本于儒家之规模基址,对康德意味下的德福一致的究极回应。”康德尽管也说过,德福一致之实现有赖于世间所有人的德行圆满,不过他却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绝对不敢相信与承认“天地之助成力量,已毫无保留地全然贯注于人”了。于是,康德以及整个西方都是除了把圆善交给神,此外,就不好再有其他的可能了。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会与人性之无上美好及其可以达成的至上境界失之交臂,而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特出之处亦于此见焉。
参考文献:
[1][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韩水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A]/ /康德着作全集(第 5 卷)[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德]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德]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A]/ /康德着作全集(第4 卷)[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德]康德。 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M]. 李明辉译。 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2003. 年
[7](宋)朱子。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8][英]布宁、(中)余纪元。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德]布鲁格。 西洋哲学辞典[M]. 项退结译。 台北:国立编译馆,1976.
[10]陈嘉映等译。 西方大观念(第一、二卷)[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杜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像其他传统哲学家那样从哲学的思辨出发,而是从非哲学领域中---尤其是心理学、生物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得到启示并发展为一个自己的系统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杜威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知识的定义并非是普通哲学家的真理---它贬低感觉...
存在概念一直是西方哲学研究的终极概念。黑格尔(Hegel)认为,只有当巴门尼德(Parmenides)提出being概念时,西方哲学史才真正开始。其实在巴门尼德提出存在(being)概念之前的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有了很多基础性的存在思想,海德格尔(Heidegger)早年也...
一、康德时间学说的内容康德在其着作《纯粹理性批判》中系统阐述了时间的时间学说。下面从时间是先天综合知识何以可能的必要条件、时间为经验知识划定范围和时间作为先验图型的构造三个方面来理清康德的时间学说。1.时间是先天综合知识何以可能问题的必要...
源于印度文明的佛教哲学通过对认识过程的考察提出了阿赖耶识这一概念;源于欧洲文明的近代西方哲学也是通过对于认识论的考察至康德得出了一个别具特色的主体认识模式,此种主体认识模式在认识论上所带来的变化更是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本文意在考察阿赖耶...
基于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哈贝马斯将社会共同体区分为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层结构。哈氏的生活世界理论是综合了近现代西方生活世界现象学、社会学、结构主义等理论的结果,其中对其影响最深的首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点,其次是许茨的主体间际社会学理论。此外,...
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NorthWhitehead)所认为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只是对柏拉图思想的一系列脚注。柏拉图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其哲学之中,而且这种理念不可能在人世间得以充分实现,理念是永恒存在的。对于柏拉图来说,对理念的任何...
共通感 (sensus communis) 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 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 人们为共通感注入了认知、实践等多重内涵, 这一思想在20世纪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得到了集成和复兴。...
1795年, 康德的学术事业进入了最后总结期, 他发表了《论永久和平》一文。其行文并不如年富力强时那样深邃、论证严密, 而是更加平实、舒缓, 省去了繁琐的论证。...
在康德伦理学中,“神圣存在者”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或许因为人们过于关注“意志自律”,而让这一概念受到了轻视,有关它的研究相对少见。...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般被认为构成了连接《纯粹理性批判》所界定的现象世界与《实践理性批判》所界定的道德本体世界的中间环节。但只需看看这部批判的主题---目的与合目的性---便不难明白,它考察的不再是和现象、道德本体两个世界并列的第三个世界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