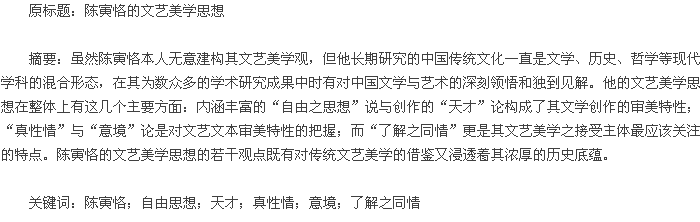
陈寅恪一生着述颇丰、研究领域宽泛。在传统文学研究领域里,陈寅恪以其深厚的文史积淀、精湛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各异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解读。先后撰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读哀江南赋》《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文学研究着述。通过对陈寅恪的文学研究实践进行深入的挖掘与梳理,可以大致总结出其颇具特色的文艺美学思想。
一、“自由”与“天才”--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
所谓“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自由思想”是陈寅恪对文学作品评析的最重要标准。“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章亦臻上乘,其骈骊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陈寅恪以南宋汪藻《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证,认为此文“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撤,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焉之”[1].在这里陈寅恪提到的“思想自由灵活”系指作者不受外在形式束缚与限制,把自己的情感与意蕴能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
地表达出来,是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论再生缘》一文中,陈寅恪把在此种“自由思想”支配下的表达能力又进行了阐释。如陈寅恪将陈端生《再生缘》第一十七卷中自序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相比较后认为,“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之所以如此,在陈寅恪看来是因为陈端生的思想自由之故。“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1]
对陈端生自由思想的强调仍是着眼于作者卓越的文章表现能力和技巧,这是陈寅恪有关自由思想的第一层意蕴。
陈寅恪所谓“自由思想”的第二层意蕴系指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之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如在《论再生缘》一文中,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反传统、反礼教的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籍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这也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是陈寅恪学术研究一直秉持的理念,且将此一理念融入到对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感悟与解读之中。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以何种态度及立场与传统文化进行对话是陈寅恪学术研究的最根本的出发点。陈寅恪自谓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2].学界对此论述颇多,但有一点共识即陈寅恪坚守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基本立场与认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立场的再现。职是之故,陈先生对当时文学界缺乏此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之状况深表不满,“国文则全国大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3].所谓“不求通解及剖析”,如果联系当时时代状况就不难发现,陈寅恪此一论断似有所指。
当时在胡适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口号鼓荡之下,一些趋新人士无不以西方理论为准绳来衡量中国语言文学。在陈寅恪看来,如果不对传统文化进行通解与剖析,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框架解读包括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不但使文学丧失了独立的品格,更是对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理念的忽视。所以从这个意义出发,以何种态度与方法对待包括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在陈寅恪看来“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
关于陈寅恪的这一论断,学界普遍认为他之所以对有宋一代文化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原因在于宋代思想文化的自由。而宋代新儒家的产生便是思想自由的表现,新儒家产生的途径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故陈寅恪将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演进概括为:“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2]
由此可知,在陈寅恪的人文世界中,“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不仅关乎为人与为学,更关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发展。故笔者认为“自由思想”不但是陈寅恪文艺美学的核心,更是理解其文化观的关键。
此外在陈寅恪的文学批评中,他特别重视文学创作主体自身所具备的禀赋和素养,“天才”更成为他解释评判文学成就高下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准绳。有关文学创作中“天才”说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结构经营之工、文章造语之妙、体情摹物之能、文体革新之巧。
就文章布局、结构经营而言,在《论再生缘》一文中,陈寅恪对作者陈端生评价颇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文章布局之精、结构经营之妙,“如今观再生缘为续玉钏缘之书,而玉钏缘之文冗长支蔓殊无系统结构,与再生缘之结构精密,系统分明者,实有天渊之别。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1]
此外对于白居易《长恨歌》开篇之“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陈寅恪认为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且以汉武帝李夫人事明言此诗上半段以描写人世为主,但有关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结构其实“已暗启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文思贯澈钩结如是精妙”[5].故陈寅恪对白居易《长恨歌》之天才构思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5].
另外在述及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结构布局时,陈寅恪认为:“不支蔓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而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的结构布局就在陈寅恪的称赏之列,“乐天新乐府结构严密,条理分明。总序所列作诗之旨,一一俱能实践。洵非浮诞文士所可及也。”[5]
在文章的遣词用语上,陈寅恪对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用语是非常欣赏的,如他在评价《连昌宫词》“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两句时,通过考证唐代宫廷的格局,辨明了《唐诗纪事》中的“玄武楼前花萼废”的“前”字为谬,因为花萼楼的地理位置不在玄武楼前。而从这两种建筑建成的先后顺序上,花萼楼建成于玄宗之世,玄武楼则建成于德宗之世,陈寅恪认为此句妙在“一成一废,对举并陈。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着一字,即已在其中。若非文学天才,焉能如是”[5].此外在分析白居易《长恨歌》之“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时,陈寅恪认为“句中特取一‘破’字者,盖‘破’字不仅含有‘破散’或‘破坏’之意,且又为乐舞术语,用之更觉混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时',本奏以缓歌柔声之丝竹。今以惊天动地急迫之鼙鼓,与之对举。相映成趣,乃愈见造语之妙矣。”[5]对于那些既无元微之“不着一字”之巧,又无白乐天一词两用之妙的创作者来说,即便吸取前人语句只要能做到灵活运用从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意境,在陈寅恪看来也是天才的表现。如对柳如是“约个梅魂”一句的解读,陈寅恪认为此句之微旨,“复由玉茗还魂记中’柳梦‘之名启悟而。然则河东君之作品袭取昔人语句,皆能灵巧运用,绝无生吞活剥之病,其天才超越,学问渊博。”
创作者在表达情感与描摹事物方面表现出的杰出的技巧与能力,陈寅恪亦以为是天才之表现。如虽然明言元稹人品不足取,其人为了能够在仕宦一帆风顺,抛弃寒门之莺莺,另娶高门大姓之韦氏。就元稹艳诗创作而言,于一时一地在诗作中所表达“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怨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其巨”[5],就其悼亡诗创作而言,陈寅恪也对元稹诗作中不时流露的夫妻生活的真实深表赞赏,认为“凡微之关于韦氏悼亡之诗,皆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而不旁涉其他。转就贫贱夫妻实写,而无溢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之名着。非微之天才卓越,断难臻于此也”[5].虽然一再陈述其人品不足取,但陈寅恪对元稹非凡的情感表达能力与技巧是赞赏有加。此外在对事物的描摹上,陈寅恪对元稹在表达能力方面的概况是“微之之文繁”,而“长于用繁琐之词,描写某一时代人物装饰,正是小说能手。后世小说,凡叙一重要人物出现时,比详述其服装,亦犹斯义也”[5].
天才的最后一个表现体现在对文体的开拓与题材的驾驭上。陈寅恪对元微之之《连昌宫词》,一再感叹,认为此诗:“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题材,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所致。”
此外,对于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就其题材而言,首先开启了“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陈寅恪认为“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对于元稹驾驭不同题材的能力,陈寅恪也是高度赞赏,认为:“微之天才也,文章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5]
陈寅恪在文学批评中屡屡提及的文学创作中的“天才”论,不论是文章结构布局、语言技巧还是表达能力与文体开拓,其核心所指就是作者推陈出新能力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体现。
二、真性情与意境--文艺文本之审美特性
“意境”一词在陈寅恪的文学评析中经常出现。
而对于何谓“意境”,他也没有明确言说,不过在其《读哀江南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供我们参考,“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7]
陈寅恪所谓“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与“意境”似有关联,只不过这一“幻觉”的生成是创作者将“古典”与“今事”结合起来,与诗人将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陈寅恪称其为“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评价不可谓不高。因此我们说,虽然此种“幻觉”与“意境”并不尽然相符,但就其一般意义而言,陈寅恪所言及的“幻觉”大致就是古今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意象或场景。此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陈寅恪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出发列举了何以用对对子的形式作为考题的诸多理由,也对理解其“意境”不无启发。他认为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若正及反前后二阶段之词类声调,不但能相当对,而且所表现之意义,复能互相贯通,因得综合组织,别产生一新意义。此新意义,虽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意义,显着于字句之上,但确可以想象而得之,所谓言外之意是也。此类对子,即能备具第三阶段之合,即对子中最上等者”[8].从陈寅恪所谓上等对子所必具的“言外之意”而言,这是“意境”又一特征。从上述两段与“意境”有关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还是能引起读者联想的“言外之意”都有一个共同的存在基础,即创作者的造境与抒情的创造能力,此外它还须具备感染读者、引起读者联想、共鸣之效果。这点我们从其文学鉴赏与批评中不难窥见其端倪。
如在论及《再生缘》第一十七卷第六八回末节“向阳为趁三年日,入夜频挑一盏灯”时,陈寅恪认为“此句法与第一卷第四回末节之’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正同,而意境则大异也”.前后二者句法一致,但“意境”大异其趣。究其原因,陈寅恪通过考察陈端生创作《再生缘》先后不同的创作阶段后认为:“端生自谓前此写成十六卷,起于乾隆三十三年秋晚,讫于三十五年春暮,首尾三年,昼夜不辍。”今则“殊非是,拈毫弄墨旧时心”,“其绸缪恩纪,感伤身世之意溢于言表,此岂今日通常读再生缘之人所能尽喻者哉?今观第一七卷之文字,其风趣不减于前此之十六卷,而凄凉感慨,反似过之。”[1]
从这段关于“意境”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陈寅恪所提到的“意境大异”所指的是与前期创作相比由于作者自身独特的经历所带来的“凄凉感慨”所致。由此可知陈寅恪的“意境”说则更倾向于作者主观的“意”,侧重的是由于创作者情感内涵发生的变化从而带来的不同的鉴赏效果,这种由内而外的感发作用亦正是陈寅恪所强调的。
此外,陈寅恪也从“意境”的角度对元稹与白居易相同题材之作品进行比较,“长恨歌及传之作成在莺莺歌及传作成之后。其传文即相当于莺莺传文,歌词即相当于莺莺歌词及会真等诗,是其因袭相同之点也。
至其不同之点,不仅文句殊异,乃特在一为人世,一为仙山。一为生离,一为死别。一为生而负情,一为死而长恨。其意境宗旨,迥然分别,俱可称为超妙之文。”[5]
陈寅恪把“意境”与“宗旨”联系起来来理解两位诗人的作品,两首诗作俱为讴歌情感之作,从意境的角度去分析,“一为生离,一为死别”显然指的是“意”,而“一为人世,一为仙山”则指的是“境”,“一为生而负情,一为死而长恨”则指两首诗创作宗旨之不同。但在这里陈寅恪并未从道德层面去非议“负情”和“长恨”,纯然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出发评论两位天才诗人的倾情之作。
陈寅恪在对比李公垂《悲善才》一诗与元稹《琵琶歌》与白居易《琵琶引》时,认为虽然三者性质类似,都是歌咏歌伎之作。李诗“诗中叙述国事己身变迁之故。抚今追昔不胜惆怅。取与微之所作相较,自为优越。但若与乐天之作参互并读,则李诗未能人我双亡,其意境似嫌稍逊”[5].在这里陈寅恪再次以“意境”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下。李公垂《悲善才》之所以比元稹《琵琶歌》“自为优越”之处就在于在叙述国事之际融入了己身变迁之故,从而达到了一种“抚今追昔、不生惆怅”的审美效果。李公垂的《悲善才》与白居易《琵琶引》相较则“似嫌稍逊”,而之所以“稍逊”就在于未能在“意境”上达到所谓“人我双亡”的境界。虽然在创作的先后顺序上,元稹创作在前,白居易受到元稹启发创作在后。但白居易“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陈寅恪所谓“人我双亡”的意境与静安先生“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颇有暗合之处。在《人间词话》里静安先生指出,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9].就其遣词用语来看,陈寅恪所谓的“人我双亡”与静安先生的“无我之境”颇相似,因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达到了物我相忘的程度,这与陈寅恪的“人我双亡”所指大体一致。白居易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人我双亡”的意境,在陈寅恪看来是因为“乐天此诗自述其迁谪之怀,乃有真实情感之作。与微之之仅践宿诺,偿文债者,大不同耳”[5].真情实感是形成意境的基础,情感是否真实则是陈寅恪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如在解读元稹悼亡诗之所以名垂千古的原因在于“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5].如果联系真情实感在营造“意境”所起到的作用就不难体会这一点。与陈寅恪相较,静安先生也是高度重视创作中的“真”,如他认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我们很难考证,陈寅恪有关“人我双亡”的意境是不是受到静安先生有感境界说的启发,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则是不争的事实。从真实这个概念出发,在一篇作品中,作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倾注其中,那么诗作就是失败的,如陈寅恪提到:“唐诗纪事之郑嵎《津们诗》,虽托之旅邸主翁之口,为道承平故实,书写今昔盛衰之感,然不过填砌旧闻,祝愿颐养而已。才劣而识陋,……以文学意境衡之,诚无足取。”[5]
由此可知陈寅恪运用“意境”这一美学概念来品读文学作品时,侧重的是作者在其作品倾注的真挚的情感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染读者的艺术效果,而“人我双亡”则是其“意境”的最高层面也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对陈寅恪“意境”的使用来考察也可发现,除了强调真情实感之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对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家国兴衰变迁及个体坎坷历程带来的深沉的“抚今追昔”的“凄凉感慨”之情是情有独钟的。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个人的诗歌创作中体会出来。如在叙述其晚年撰述《柳如是别传》之状况时,曾赋诗一首:“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终难裁。”
这首诗不但描摹出作者“暮齿着书之难”,更将古今“孤怀遗恨”之情、书中奇女与作者暮年之状浓缩于诗作之中,真正达到了陈寅恪自谓“人我两亡”的艺术意境。
三、了解之同情--文艺美学之接受主体
陈寅恪在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谈及对古人着书立说的解读与接收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着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了解之同情,始有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0]
陈寅恪所论是就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撰述而言,但如果我们从文艺美学的接受主体的视角去解读的话,则更能窥见其方法论意味。陈寅恪所言及的“了解之同情”是文艺美学的接受主体应具备的基本的能力与素养。对于接受主体如何方能达到“了解之同情”的审美效果,首先从创作者的立意出发,陈寅恪认为“古人着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欲探讨作者的着书立说之主旨,则不能不从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出发。此点颇与传统文学批评之知人论世之旨趣相似,而陈寅恪则从知人论世出发更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考论赏析传统诗文欲探究具体语境之出处,不但要阐释古典更须对作者作文之时的境遇及时代特征及“今典”进行了解。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他提到:“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
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
一般来说解释古典诗词之“辞句”属文学研究的范畴,而考证古典诗词之“本事”则属于史学考证的领域,两者的结合是“文史互证”最好的注脚。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对“古典”的解读固然重要,但如仅停留在对“古典”的解读而忽略了“今典”的考证,其最终所解亦不能趋近于诗作之原旨。故相较于“古典”,陈先生对“今典”的考证用心最多、考证最勤、创获亦颇丰。可以说对“古典”与“今典”尤其是“今典”的考证,不但使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与考证的才情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亦真正做到了对创作者“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了解之同情”①.如陈寅恪考察陈端生的“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与“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重写再生缘”两组诗,认为:“自再生缘十六卷写完,至第一七卷续写,其间已历十二年之久,天道如此,人事亦然。此端生之所以于第一七卷之首,开宗明义即云:’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古典今情合而为一语,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于子山之文,深有解会,即此可见。”陈寅恪对通过古典今情的考释进而深入了解作者创作这一方法颇为自信,如其所言,“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1]
不论是接受主体具备的“欣赏之眼光与精神”还是“神游冥想”均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在介绍静安先生作品时,陈寅恪再次以诗人之心郑重提出“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陈寅恪特别拈出“神理相接”“心喻”这两个词汇,所谓“神理相接”与“神游冥想”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强调阅读者以自己的情感体会出发越过语言文字的表面而深入创作者的本心,不但对作者的创作思想有洞彻之见,更能对其精神世界有了解之同情。这不但与传统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鉴赏方式有内在关联,更与先生一直倡导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具有史学通识的态度是相通的。
这种强调阅读者以自己的情感体会出发越过语言文字的表面而深入创作者本心的认知态度在陈寅恪的文学鉴赏及批评实践中有更直观的体现。如他在品读《再生缘》的过程中对陈端生创作《再生缘》的曲折历程产生了高度共鸣,“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璧,遗憾无穷。至若禅机早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1]
在考证《再生缘》作者始终后,陈寅恪有感于陈端生“岂是早为今日谶”之语,联想到己身“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玄之瞽女”,虽然解读的是“异代春闺梦里词”,感慨系之遂有“怅惘千秋泪湿巾”之感动。[1]
在解说自己撰述《柳如是别传》的初衷时,陈寅恪提及到了由一枚红豆而兴起的缠绵之思。“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箧,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从这段颇富文学意蕴的自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陈寅恪对钱柳姻缘之考释既有温旧梦之愿,更系其源自其丰富而有深邃的精神世界的”寄遐思“之作。对于读者而言,《柳如是别传》故系史学考证之列,但如果我们忽略了该着述的文学精神与品位,则实有负于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的谆谆教诲。
陈寅恪的文艺美学思想虽无系统阐释与解说,但通过考察其文学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其在文学创作、文艺审美与文艺接受美学等方面确有独到的见解。
此种独到见解与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如他在文艺鉴赏中经常使用的”意境“这一词汇,该词汇除了具有一般文艺美学的内涵之外,还包涵着陈寅恪对历史人物、事迹变迁的叹赏与感悟。尤其是”自由之思想“与”了解之同情“虽然是陈寅恪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与方法,但作为一位颇具文史通识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文史领域精深的造诣及传统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陈寅恪的文艺美学思想浸透着深沉的历史底蕴。
注释:
① 此处参考拙作《陈寅恪的文学研究范式探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 论再生缘[C]// 寒柳堂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C]//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3] 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任[C]// 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4] 陈寅恪。 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C]//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5]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7] 陈寅恪。 读哀江南赋[C]// 金明馆丛稿初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8] 陈寅恪。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C]//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9] 王国维。 人间词话[C]// 王国维集第一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0]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C]//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1] 陈寅恪。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C]//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绪论第一节研究目的及意义黄药眠先生是当代着名的美学家、文艺学家和作家。解放后他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一级教授,曾任中文系主任,博士生指导教师,长期从事美学、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文学创作和译着,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学的建...
摘要文艺美学是一门研究文学和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的学科。黄药眠先生是我国现代着名的文学理论家、作家、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首批两个文艺学博士点之一的创建者(另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蔡仪先生)。曾担...
第三章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的实践维度黄药眠先生不仅是一位着名的理论家,也是一位着名的作家。据童庆炳先生回忆,黄药眠先生要求自己的学生进行一定的文学创作,以期在实践中更深刻领略文学批评技巧、内涵等。黄药眠先生自己在这方面也确实是亲身力...
我一生从事文艺美学研究,耄耋之年得青年女教师王虹的新着《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民族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一书,因其开拓创新,吸引我思考研究,看到书中融通古今中外的艺术哲学和文艺审美学的创造经验,有言人之所未言者,使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
余论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和价值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性概括,主要阐述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和价值,包括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思想的学术贡献、理论的意义和历史地位。第一节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的影响一、对文艺美...
第二章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本章节将介绍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从黄药眠大量的美学文艺学论文中,总结、分析、概括出其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主要的观点,并把握其中的理论内涵和特质。黄药眠先生文艺美学思想十分丰富...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面向个体和心灵世界,追寻生命的意义,并且帮助人找到最适合的存在方式,也便建构了最基本的人学实践品质。细读宗白华先生的美学着作,他是在梳理、诊脉、开新方的审美实践中建构其独特的人学实践品质的。宗先生认为,文艺站在道德和哲...
第四章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色本章主要分析黄药眠生活实践论文艺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色,根据对其主要内容和实践分析来总结、概括出其理论特质,分析其理论特色之间的异同之处和内在联系,并将此特色与其他形态的文艺美学进行比较,突出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