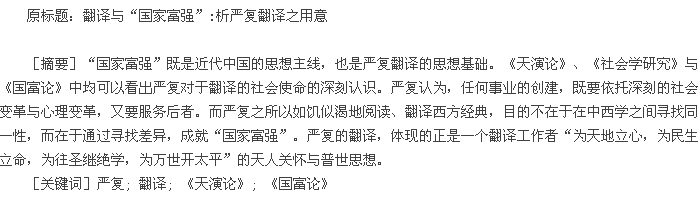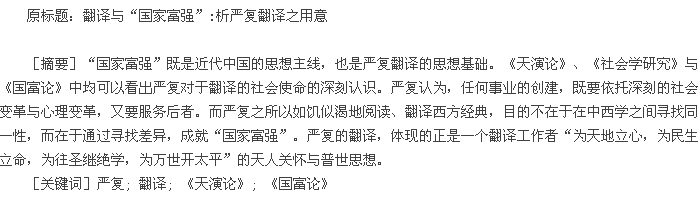
一、导言
“国家富强”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思想主线,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不同。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文祥与左宗棠等发起改革运动,鼓吹经世致用思想,虽然初衷不坏,本质上却同顾炎武与黄宗羲鼓吹的没有两样,即都是以正统的儒家政治 - 经济哲学为基础。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同文馆与总理衙门先后建立,但也都没有动摇儒家学说的正统框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确实有一部分政治家,如张之洞与李鸿章等,以及士大夫与洋务专家,如薛福成、郑观应与马建忠等,经历了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军事技术同整个西方工业体系之间的关系。例如,李鸿章曾经置办工商业,认为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然而,这种对于西方的以识缺陷非常明显: 无论是李鸿章与张之洞,还是薛福成、郑观应与马建忠,抑或是更早时期的曾国藩与奕 ,他们无一例外都赞成“保教”。所谓“中学为体”即是要维护儒家政治 - 经济哲学基础,上至作为国家基础的君主政体,下至个人与家庭伦理道德。如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所说的: “盖道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甚至更有徐桐叫喊“亡国比变法强”。( 王栻,1986: 63; 李定一,1956: 128。) 因此,尽管李鸿章等人身上已经有了工商业意识,其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通过军事上的“自强`”,扞卫正统的儒家政治-经济哲学基础,他们对于西方的有限反应并没有跳出贺长龄文编中的“治国之道”。( 史华兹,2010: 6)
二、“国家富强”: 严译的思想基础
洋务运动之后,严复等从传统的变易思想中,引出自强意识与变革精神,以此赋予翻译相应的社会使命。例如,严复依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指出: “进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之疾,放在其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至亦不过二百年,近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 王栻,1986: 27) 《孟德斯鸠传》中,严复又指出,孟德斯鸠关于政体所作的区分源于亚里士多德,其学说合乎情理,并说道: “三制精神,若其出于吾人,则必云:太上之民主以德,其说有道之君主以礼,其说无道之专制以刑。”( 同上: 935—1027) 只不过,那时的中国国民,无论缙绅乡民,因为“三分学说”本为我国所无,又有违古之法制,所以都不欲谈论。
众所周知,严复出洋,以及日后得以进入船政学堂,乃是因为得到了沈葆桢的赏识。留洋期间,严复结交郭嵩焘,并与后者兴趣相投,常常一起研习中西学术的异同。然而,当1879 年严复学成回国后,却没能得到重用。1890 年,因为才学出众,严复被李鸿章擢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被擢升为总办。表面看,其地位在平稳上升,然而正如陈宝琛所说,这种提升不过是徒有虚名,因为严复只能“总办学堂”,却是“不预机要”,所以充其量只是“奉职而已”。( 王栻,1975: 15) 严复后来吸食鸦片,似乎同他事业上的不顺心不无关系。当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以下方面: 一、严复留学期间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印象深刻,常与郭嵩焘一起考察其制度,认为英国的富强不在于军事,而在于制度,这一思想大大超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的“自强”范畴。二、严复虽然也是洋务运动期间改革派的重要成员,他对于“自强”的理解却明显不同于李鸿章等。在李鸿章看来,国家的根本与出路在于儒学,所谓“富强”主要在于军事,目的正是为了维护晚清既有的政治与经济秩序。而严复认为,任何事业的创建,必须依托深刻的社会与心理变革,洋务派关于创建现代海军的思想也不例外。由于这些原因,李鸿章既没有给与严复创办学堂的全权,更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果敢的实业家。事业上的这种壮志未酬,在 1895 年后的几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与《辟韩》中,严复反复表达了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这些文章一方面洋溢着久所欲言而终于一吐为快的情绪,另一方面又毫无意外地构成了其日后翻译的思想基础。
三、《社会学研究》中的“国家富强”思想
以《社会学研究》为例。这是一本影响严复终生思想的作品,书中论述的进化论观点如此让他着迷,若干年后,严复在《译群学肆言·自序》中谈到阅读此书的感受时指出,《社会学研究》的某些观点,同《大学》与《中庸》等中国古籍精义相互印证,既纠正了他“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的错误,又恢复了他对于中国古籍的信念。《大学》有云: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熹,1985: 4) 在这段话里,道德的完善在于“知”,而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同样强调“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 王栻,1986: 126) 后来,当严复创作《原强》时,再次说到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 同上: 16)当然,严复对于斯宾塞的不少理解其实并不正确。例如《社会学研究》中,斯宾塞对于英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其实并不满意,尤其不满英国政府对于社会内部事务的干涉,以及日益发展的帝国主义,认为它们是文明的倒退。( Herbert Spencer,1844: 600-607) 然而,严复从对斯宾塞的阅读中,看到的不是斯宾塞的沮丧与失落,而是出于他对于“富强”的过分关注表现出来的某种功能关系。就这样,斯宾塞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通过严复对于“富强”的关注,竟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史华兹,2010:46-50) 又比如《社会学原理》中,斯宾塞详细阐述了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的相似性,并将脑的进化看作整个生物进化过程的终极目标,认为有机体的进化从趋势上看应当是局部服从集体的利益。然而在本书的结尾处,斯宾塞又回避了这一结论,反而认为“排除成员的利益而考虑群体的利益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国家的要求本身没有什么,只有当它们包含了其成员的要求时才有意义。”( Herbert Spencer,1844:47-48) 可是,由于受到斯宾塞原有生物进化学影响太深,加之自己对于国家“富强”的渴望,严复并没有意识到斯宾塞结论同其前文之间的差异,而坚持认为国家是整个进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
类似的情况在严复的翻译中不在少数,其中就包括了《天演论》。众所周知,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本是为了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讲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出于维护人类伦理观念的目的,赫胥黎反对创立所谓“进化伦理”,也明确提出反对斯宾塞,以及“进化伦理”的其他鼓吹者,尤其不能忍受斯宾塞的宇宙乐观主义,因为这在他看来是极其残忍的。赫胥黎认为,“社会进步意味着控制宇宙进程的每一步,并以其它伦理进程代替宇宙进程,……社会的伦理进步不是依赖模仿宇宙进程,更不是回避宇宙进程,而是同它斗争”( T. H. Huxley,1925: 81) 。很明显,严复想要在达尔文主义体系中,为人类行为寻找应变方法,这一点同赫胥黎的反宇宙进化伦理的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同样的道理,严复对于国家富强的关注,同赫胥黎的关注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即便如此,严复仍然翻译此书,并利用赫胥黎的思想资源,破除中国旧式文人的“夷夏之辨”,同时也利用翻译更好地维护斯宾塞体系。严复的翻译客观上无疑传播了赫胥黎的声名。然而,有一点却是赫胥黎始料未及的,那就是,他的思想居然会因为严复自己的考量而被“利用”。严复为了实现他对于国家富强的构想,附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于国家出路的主观诉求,不惜刻意曲解赫胥黎,维护斯宾塞。然而需要指出,严复在理解与维护斯宾塞的过程中,同样犯下了不少错误。比如,斯宾塞认为,社会科学描述的乃是社会进化的过程与规律,具有客观自律性,因此不应受到外部干扰。而在严复看来,情况并非如此。从对斯宾塞的阅读中,严复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即一方面,社会科学很好地提供了关于社会发展的解释;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提供了关于社会改造的方案。这一方案,同他自己关于中国富强的构想并无二致。事实上,早在接触斯宾塞之前,严复就一直在思考有关进化动力的问题。既然达尔文与斯宾塞所说的进化动力无所不在,那么何以西方日益强盛,而中国却逐步衰微呢? 严复以为,其中缘由在于西方的智者清楚地懂得进化过程,而中国的圣人却从未了解进化的作用。这一点当我们阅读《论世变之亟》时可以清楚地看出。严复认为,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莫过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而“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又说: “《物种探源》,自其出书,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婓变。”( 王栻,1986:16) 严复的意思是,进化学说在西方,不仅贤达人士深谙其律,而且平民百姓也多少了解。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共同抬升了西方的学术与政教水平。严复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不仅描述了现实,而且规定了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乃是进化的力量来源。而斯宾塞将达尔文的思想,运用于社会事务解释,既妥当又具有启发作用。对于严复这样在传统文化中生活太久的中国文人来说,达尔文与斯宾塞思想的吸引力自然无法抗拒。然而,严复在解释西方的学术概念时,仍不时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说法,比如他在解释逻辑学与物理学的基本范畴时,就从《易》与《春秋》中找到了解释,指出西方的“名数质力”早已包含在《易经》中,是名副其实的发端于古人,只不过后来者“莫能竟其绪”罢了。( 同上: 320) 但是,严复对于西学的态度之虔诚与热情之高涨,同李鸿章等人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四、《国富论》中的“国家富强”思想
在《国富论》的翻译上,严复格外用心,因为它是西方计学的代表。严复说: “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故计学欲窥全豹,于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尔、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移译。”( 同上: 97) 正如以前的做法一样,严复在这本书的译本中同样增加了不少按语。这些按语虽然也有提及李嘉图、穆勒与罗杰斯等其他经济学家对于斯密学说的修改与补充,但是严复认为,自斯密以来的西方社会经历的经济变化,总体上仍然印证了斯密学说的合理性。《国富论》原本中,斯密论述的问题很多,比如政治经济学的目的问题,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个人利益、普遍利益和公众幸福的关系问题,公债同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富的关系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斯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乃是一种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怀,因为经济学传统中,斯密并不是重商主义者。所谓“重商主义”,用埃利·赫克谢尔的话说,就是指“经济活动从属于国家政权的利益”。( 埃利·赫克谢尔,1935: 15-17) 既然斯密不属于重商主义者,那么又怎么能服务于严复的政治目的呢? 这是因为: 一方面,斯密虽然反对重商主义,但他反对的只是重商主义的措施,而不是反对重商主义的目的。与马克斯·施蒂纳不同,斯密并不认为个体与社会势不两立。相反,他认为个体与团体利益相关,准确地说,团体利益乃是个体利益的一种补充。斯密大概从边沁那里找到了灵感,他用“无形监督”来理解二者间的协调与关联。《国富论》中,斯密不仅经常使用“普遍利益”与“公众幸福”之类的表达方式,甚至使用“社会”一词表示经济活动的最终受益人。斯密认为,“社会”虽然由个体构成,但又可与“民族”和“国家”相互替换。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的最终受益人是“社会”,同说最终受益人是“个人”其实是相通的。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斯密也就自然地同严复的“国家富强”联系在了一起。从对斯密的阅读中,严复看到了维多利亚英国的自由经济主义体系,认为是它促成了英国的国家富强。另一方面,严复又从斯密的着作中,看到了爱国主义的情绪释放。如在《国富论》的“论公债”中,斯密批评了英国的公债政策,认为它是一种“毁灭性的权宜之计”。( AdamSmith,1904: 737) 严复认为,正是因为斯密对于英国政府的警告与规劝,英国才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自由经济主义体系。
严复说: “……英国自斯密所处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于是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天诅之通商。”( 王栻,1986: 920) 又说:
“英人无释负之一日矣,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 同上: 103) 在严复看来,“公债”政策之所以没有导致英国的万劫不复,不是因为“公债”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因为英国政府鼓励的自由经济补偿了其不利影响。而在中国,民众的经济活动长期受到压制,因而国债的增加只能是抽取整个社会的财富。所以,尽管严复对于《国富论》的某些理解不同于斯密的原初用意,但他显然在爱国主义的话题上,找到了与后者的情感契合。严复对斯密的翻译尽管有些不近如人意,但这样的情况并非随意为之,问题不在于严复的语言能力,而在于其所关注的对象。( 史华兹,2010: 123)近现代中国中,虽然翻译选材和译家态度各有不同,却都是为了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事翻译,自然要考虑翻译的功能指向。对于严复来说,翻译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实践政治诉求。在给好友张元济的信中,严复写道:
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 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复今者勤苦译书,羌为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见所译者,乃亚丹斯密理财书,为之一年有余,中间多以它事间之,故尚未尽其半,若不如此,则一年可以事,近立限年内必要完工,不知能天从人愿否?
此书卒后,当取篇幅稍短而有大关系,如柏捷《格致治平相关论》、斯宾塞《劝学篇》等为之; 然后再取大书,如《穆勒名学》、斯宾塞《天演第一义海》诸书为译。极知力微道远,生事夺其时日; 然使前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 ( 王栻,1986: 524-557)就这样,严复在随后十几年中倾尽心力,逐一译介计划中所列书籍,并借用书中学说或自己的按语“闵同国人”,荡涤蒙昧,实现社会救赎。毫无疑问,严复的理念不仅迎合了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同时迎合了维新志士,乃至“五四”一代的渴望与追求。如《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中》
指出的那样,天下各国,无论中外,不分古今,无不贯穿变易之道。因此,面对当今形势,“我”若不图自强变法,又“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而哉! ”( 王蹈,1959: 161)王韬既是洋务大吏,又是翻译名家,他的上述表态,以及他在翻译事业上的以身作则自然有其示范作用。
五、“国家富强”的实现途径: “差异”而非“同一”
需要指出,严复之所以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翻译西方经典,并非为了在西学中寻找同一性的东西,其着眼点乃是为了寻找差异。就对斯宾塞的阅读而言,严复所得到的不仅有后者的“社会有机体”概念,更有关于“社会群体之质量有赖于各个单位”的认识。通过这些理论,严复不仅明白了中国的历史循环论,同西方的无休止的历史进步论之间的差别,而且明白了国家的出路同个体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所谓“社会群体之质量有赖于各个单位”,代表的是斯宾塞对于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解。斯宾塞将个体的潜在活动概括为体力、智力与道德的结合体,认为只有通过追求个人幸福,才能实现个体活力。对于严复来说,斯宾塞的这种理解有别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消费式利己主义,更不同于享乐主义。在西方,人们强调的是个人能力的充分释放,以及这种能力的建设性作用,既利己,又利它。西方社会之所以能成就富强,关键在于人在驾驭文明的过程中,实现了蕴藏于个体的巨大能力。而中国的伦理中,强调的是消解个人能力,限制和禁锢个人能力,以使个体能力服从于社会有机体。
反之,一旦个体的能力和自我利益得以实现,便会削弱社会有机体的利益。所以严复说,中西“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 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 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王栻,1986: 3) 正因为这样,严复在《辟韩》中强烈抨击了韩愈的所谓“圣人之说”,指出政府的出现无赖于圣人,正如文化的缘起无赖于圣人一样,它们只不过是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政府的建立不是创造了文化,而是保卫社会,所谓民“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 同上: 33) 所以史华兹指出,严复的工作无论是翻译也好,还是伪译也罢,其着眼点很少体现在语言使用上,而是体现在个人的主观成见上。比如严复的译文风格典雅,既不同于六朝时期的华而不实,浮艳巧辩,又不同于清代考据学派的文采暗淡,章法缺失,目的是要回到先秦哲学家那里,找到一种适合表达的文体典范。这一点体现的正是一种诗学上的考虑。事出同理,严复翻译《天演论》时颇费心思,创造了不少新名词,而没有套用日文里的既有表达,体现的则是他在“东方岛夷”面前的高傲与不满,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比如《社会学研究》中,斯宾塞站在人民幸福的角度,批评立法对于进化的干预,而严复的翻译却集中在国家的兴衰。斯宾塞不认为人民的幸福可以通过国家作用获得,认为只有当进化过程不受国家干预时,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可是,严复在译文里并未提及幸福话题,而是转而谈论起国家的富强。毫无疑问,这种焦点话题的转移乃严复刻意为之,出发点仍然是为了吻合译者对于国家富强的整体构想。
六、结论
严复的翻译发生在中国思想界面临变化的年代,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思潮发生变化的时候。众所周知,十九世纪的世界思潮变化,整体上都强调对于传统思想、政治和经济的反抗。这种反抗既有浪漫主义的,也有理性主义的,而严复所受影响主要来自边沁、穆勒父子、达尔文、斯宾塞等理性主义中的急进派,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自身独特的知识结构。
如严复翻译《天演论》,主张以进化论思想分析社会的更迭与演进,正是这一知识结构调整所致。1896 年,严复写信给梁启超,说道: “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 王栻,1986: 514) 1902 年,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主张以“愈愚为最急”,认为只要是会致人民愚昧的东西,不管它“父祖之亲,君师之严”,都要抛弃。而与此相反,只要能疗贫起弱,不论中西,又或是出自“夷狄禽兽”,则也要学习。
严复认为,拘泥于中国文化的固有性,排除异族的因素,并不具有建设性。为了不使“时局愈益坠坏”,国家“如居火屋,如坐漏舟”,他呼吁国人认清时势,“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就是说,要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机立断,改弦易辙,方能挽狂澜于既倒。严复深知了解“西学”的重要性与急迫性,认为它有助于我们获得自我反省的契机,因此“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同上: 5)对于严复而言,“君民共治”也好,孟德斯鸠的法制观念也罢,但凡有助于中国开启民主与自由之风的东西皆可翻译。《社会通诠》中,严复不吝笔墨,详细论述西方的政党制度,并借题发挥,增加了许多原文本无的东西,如“其争于外者无论已”、“宜乎古之无从众也。盖从众之制行,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畛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古宗法之社会,不平等之社会也。不平等,故其决异议也,在朝则尚爵,在乡则尚齿,或亲亲,或长长,皆其所以折中取决之具也。”( 同上: 128-129) 而在论述“政党实用”中,同样增加了大段内容,如“今夫门户之分,古之人以为大贼”,“此所以救人道过、不及之偏,国家得以察两用中而无弊者也”,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从翻译的正统讲,如此取便之举当然不值得提倡。然而,严复以其双语专才却偏在这些问题上大费周张,其中考量的确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1] 李定一. 中国近代史[M]. 台北: 台湾中华书局,1956.
[2] 史华兹.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 王栻. 严复集( 第 1 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4] 王栻. 严复传[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 王蹈. 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中[C]. 上海: 中华书局,1959.
[6] 严复. 天演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7] 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 岳麓书社,1985.
[8] Spencer,Herbert.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 Vol. 1)[M]. New York: Appleton,1844:.
[9] Huxley,T. H. Evolution and Ethics[M]. New York:McGraw-Hill,1925.
[10] Cannan Edwin.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the Wealth of Nations[C]. Smith,Adam. ed. London:Methuen and Co. ,Ltd. ,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