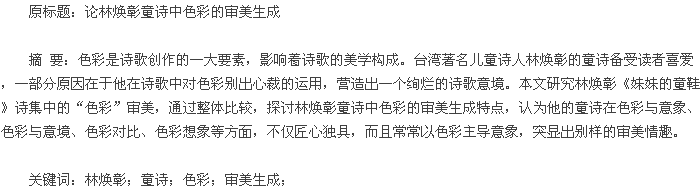
引言
“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成辞章,神理之数也。”①我国古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刘勰将“五色”至于“立文”之首,由此,色彩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在古代诗歌写作实践中,无论画意,无论传情,色彩这一要素已被运用得炉火纯青。“碧云天,红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苏幕遮》范仲淹),“莲粉飘红,菱花掩碧”(《鹊桥仙》纳兰性德),这里的碧穹红叶,花红叶绿,尽是写实,嚼字咬文之间,头脑中便形成了一幅幅色彩绚烂的如画美景,在这些诗句中,色彩营造意境,可谓功不可没;“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留”(《江城子》秦观),“花褪残红青杏小”(《蝶恋花》苏轼),而这些诗句中的色彩,除营造意境而外,诗人更是借之传情达意,似乎所有愁绪都集中于那一个红字,一个绿字,非其不可;在修辞方面,色彩的运用也相当纯熟,如“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八声甘州》李清照),“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蝶恋花》欧阳修)都运用以色代物的借代手法;又如“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剪梅》蒋捷)一句将流光拟人化,妙趣横生;“红叶满寒溪,一路空山万木齐”(《南乡子》纳兰性德),一处实写一处虚写,将两大色块巧妙结合,引人联想无限;这样的色彩处理方式都让原本平淡无奇的诗句焕发别样的光彩,令人眼前一亮,读来饶有趣味,颇值得反复咀嚼。现代诗歌色彩运用更是站在巨人肩膀上,锐意创新,不断发展。
然而在诗歌色彩理论方面,色彩作为绘画的要素之一,其介入诗歌、对诗歌审美产生影响的作用一直以来被集复杂性与丰富性于一身的“画”所掩盖。提到诗歌,人们往往将“诗”与“画”并提,例如王维之诗画,历来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称道,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也曾给诗歌一个明细的定义:“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情绪中的意境。”②朱光潜在《诗论》中写道:“诗的姊妹艺术,一是图画,一是音乐。”③诗歌绘画美理论研究成果颇为显著。对诗歌中色彩的关注,来源于诗画比较。1926 年,王独清在诗歌研究领域明确提出“色彩”这一概念,他认为“纯诗”是由“音”与“色”构成的,“(情 + 力)+(音 + 色)= 诗”是其为诗歌写的公式④;穆木天在给郭沫若的信《谈诗》中极力肯定并主张写“纯诗”,著名诗论家梁宗岱在前人基础上重新定义“纯诗”,他认为所谓“纯诗”便是“摒弃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构成它形体的元素---音韵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的感应,超度灵魂到极乐的境域。”⑤胡适提出“具体的做法”,要求诗要有鲜明的视觉“影像”、听觉“影像”及其他感觉“影像”,视觉“影像”包括形状、线条、色彩等⑥;艾青也在《诗论》中提到“一首诗里面,没有新鲜,没有色调,没有光采,没有形象,---艺术的生命在哪里呢?”⑦这些理论的提出表明“色彩”参与诗歌审美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也表明“色彩”逐渐脱下“绘画”这重重的外壳而独立存在。
正如上文对古代诗歌中色彩的审美分析,色彩能介入和影响诗歌审美,画意传情。林焕彰童诗中不乏色彩的描写,但“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⑧,林诗并非色彩词的堆砌,而是对其精心设计,去芜存菁,色彩的运用增强了林焕彰童诗的艺术表现力。本文主要研究台湾第二代著名儿童诗人林焕彰的代表作《妹妹的童鞋》,探讨其童诗色彩的审美生成问题。
不同于绘画中色彩给人以直接的视觉冲击,诗歌中的色彩是依托于文字,通过文字来唤醒读者记忆中的色彩累积,刺激读者的生理和心理反映,从而触发其想象,激活其情感,以此来完成色彩介入诗歌审美的。这一过程体现了诗歌中色彩的审美生成具有间接性与想象性,具体表现为在诗歌中色彩依靠“意象”与“意境”进行运作,色彩首先依附于意象或本身成为意象,或细致刻画,或表达情感,意象的细腻、传神是意境生动的铺垫,多个附着色彩的意象互相汇聚、碰撞,继而形成富有色彩的意境,因诗变色。色彩融入诗歌,使得意象与意境从含苞到怒放,变得绝妙而鲜活,诗歌也因此极富诗味与诗蕴。
一、色彩与意象生成
如上所述,色彩参与意象构建主要依靠依附于意象或色彩本身成为意象两种方式,即“意象色彩化”和“色彩意象化”.简而言之,“意象色彩化”指色彩依附于意象,使单一的意象着色,诗歌离不开意象,意象是构成诗歌审美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文字首先作用于视觉,对视觉形成一定的冲击,诗人多爱给意象上色,因此“意象色彩化”
在诗歌中十分常见;“色彩意象化”指色彩并不依附于意象,而是其本身作为意象直接出现,担负意象的功能,这种手法比较特殊,给诗歌理解造成一定难度,因此相比“色彩意象化”较为少见,尤其是在以儿童为主体接受对象的童诗中,“色彩意象化”更是罕见。
意象色彩化
古往今来,相当多的诗人选择通过给诗歌意象着色使之更加细腻、传神,从而使诗歌入味,例如被我们熟知的“诗鬼”李贺、近代诗人郭沫若、现代诗人戴望舒、艾青等均是用色高手。对色彩的关注同样出现在孩童的视角,孩子的世界干净而澄澈,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们眼中的世界五彩缤纷。
1960 年林焕彰开始写作、画画,70 年代起致力于参加与推动儿童文学工作,笔耕不辍,但他并没有因此彻底放弃绘画,而是成功地将自己的绘画才能与童诗创作结合在一起,两者相得益彰。色彩词在其诗歌中的运用,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读林诗,仿佛跟着孩子一起欣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儿童大半喜欢极鲜明的颜色,红、黄两色是一般儿童的偏好。”⑨林焕彰先生笔下的孩子也不例外。
妹妹的红雨鞋,
是新买的。
下雨天,
她最喜欢穿着,
到屋外去游戏,
我喜欢躲在屋子里,
隔着玻璃窗看它们
游来游去,
像鱼缸里的一对
红金鱼。
《妹妹的红雨鞋》是林焕彰同名诗集《妹妹的红雨鞋》的第一首,雨鞋和金鱼是诗歌唯一两个意象,除了都是红色以外,这两种事物基本上没有联系。但在诗人眼中,雨天屋外的世界就像一个大大的玻璃鱼缸,而妹妹穿着红雨鞋在雨中游戏就像鱼缸里的一对红金鱼游来游去。这个比喻贴切、生动、鲜活,完全符合孩子的思维方式,而这个比喻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红”字,彼时,屋外的世界瞬间浓缩成了一个鱼缸,原本躲在屋子里的“我”从暗处走出,观察着鱼缸里的一切,穿着红雨鞋的妹妹游来游去变成了红金鱼,化腐朽为神奇。细细品读,仿佛还能咂摸出一丝追寻自由的况味,穿着红雨鞋在雨地里玩耍的妹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其儿童天性得到了极致释放,而在“我”眼中,那两只穿着红雨鞋、踩着水洼、活蹦乱跳的小脚丫像极了鱼缸里的红金鱼,金鱼看似悠游自在,却只拥有那一方小天地,或许那对红金鱼不是妹妹的红雨鞋,而是“我”---喜欢躲在屋子里的“我”.
色彩意象化
如果说“意象色彩化”使林焕彰先生的童诗得以完美地向读者展示儿童视角的五彩缤纷,“色彩意象化”则使他的童诗更加鲜活,更加贴近儿童的心理。林焕彰先生说过:“诗要有意味,但诗的意味不存在于华丽的辞藻,而是看你所使用的文字是否准确以及有无新鲜的感觉。”⑩其中一部分新鲜感则来源于色彩词的以色代物手法,即“色彩意象化”.比喻的目的是使抽象的变成具体的---借比喻把你所要比的东西更鲜活地显示在人们的眼前。“使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使原来感觉不到的东西感觉到、看得见、闻得着、知道它的温度和硬度。”而林焕彰先生的以色喻物似乎反其道而行之,把原本具象的事物代之以抽象的色彩,独树一帜,别具风格,新鲜感便产生了。
我们,情绪起伏不定
我们,用分析、用解剖、用透视
我们,用黑白、用褐与灰
用眼睛和鼻子……
探索这个世界,
只是,不用嘴巴
我们的嘴巴,常常
紧闭,不说一句话
---一句话也不说
这首《一句话也不说》中的“黑与白”、“褐与灰”作为抽象的意象,已不是单纯修饰意象的色彩,在这里色彩本身成为意象,与“分析”、“解剖”、“透视”;“眼睛”、“鼻子”相呼应,用偏灰暗的冷色诠释青春期少年性格中的孤僻、冷静、自尊、迷茫,“我们,情绪起伏不定”,但“我们的嘴巴,常常 / 紧闭,不说一句话”,不同于孩童的年少无知、无忧无虑,也不同于成年人的饱经风雨、成熟稳重,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处于人生重要的转折期,一切都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他们的性格逐渐养成,常常缄口不语,更多的是观察、思考与沉淀。林焕彰先生仅用黑、白、褐、灰四色,便将青春期孩子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胜似万语千言。同时,色彩意象细腻、传神,使得整首小诗透着浓浓的诗味,虽为暗色调,整首诗却因之亮堂堂的。不妨再一起品读小诗《我的鸽子》:
我的鸽子我养在心中,
我的鸽子会哭会叫;
我的鸽子高兴时,是一只白色的鸽子,
我的鸽子不高兴时,是一只灰色的。
我在我心中养着鸽子,
我的鸽子有喜怒哀乐;
它快乐时,就从我的笑声中飞出来,
它不快乐时,羽毛就一根根脱落死在我心中。
这只有着喜怒哀乐的鸽子真的是只鸽子吗?
明显不是。它更像是“我”自己。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不做任何掩饰,这是孩子的天性。这首诗的新奇之处就在于林焕彰先生把孩子这种爱哭爱笑的天性比喻为一只养在心中的鸽子,而且它还能随心情变幻羽毛的颜色:高兴,它是白色的;不高兴,它就变成灰色的;破涕为笑时,它又变成白色的,多么神奇的一只鸽子啊!我们还可以想象白色的鸽子胖嘟嘟的,笨拙地走来走去,煞是可爱;而灰色的鸽子精瘦精瘦,耷拉着小脑袋,羽毛在一根根脱落,它转过脑袋,用硬硬的喙梳理稀疏的羽毛,怪可怜的,就如孩子高兴时蹦蹦跳跳,而不高兴时就像霜打的茄子一般。在这里,白色和灰色不再只是两种颜色这么简单了,它们分别与两种情绪建立了联系,成为意象。当你读到白色,耳中似乎飘来孩子咯咯咯咯的笑声,心情随之明朗起来;当你读到灰色,脑海中浮现一个伤心哭泣的孩子的形象,心中亦是铅云沉沉。在这首小诗里,林先生又一次成功诠释了“色彩意象化”.
二、色彩与意境营造
色彩构筑意象,不同的色彩意象又以不同的形式组合生成意境,色彩在营造诗歌意境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同一种色彩在诗歌中反复出现可以渲染环境、烘托背景气氛,形成诗歌主要色调,主导诗歌意境”;两种色彩的对比组合会产生特殊的审美效果;多种色彩在同一首诗中互相融合,产生强烈的带入效果。
作为以绘画才能见长的林焕彰,在创作童诗时充分利用色彩的造境功能,选取应时应景的色彩,对不同色彩组合的驾驭可谓得心应手。
单色渲染
孩子的世界是纯粹的,他们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没有丝毫掩饰;孩子眼里的世界同样不参杂任何杂质,或欢快明朗,或充满生机,或静谧温暖,有时也带点儿令人不解的灰色调。林焕彰像画家一样在诗里自如泼洒油彩,如果说他用儿童化的语言淡淡勾勒出孩子天真活泼的形象,这浓郁的纯色无疑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孩子纯粹的内心世界。天是水蓝的草是翠绿的,山是青的海是蓝的,小蘑菇是白色的,太阳公公是金黄的,连早晨和年龄都是绿色的,而岸上的那条死去的鱼是黑色的,火车的大烟圈是黑色的,秋天飘落的树叶黄黄的。这些色彩在林焕彰笔下不再单纯是颜色,而更像是诗人为读者精心准备的带不同颜色镜片的眼镜,仿佛戴上,就能去领略孩子眼里单纯的世界。
比如《在岸上的那条鱼》:
在岸上的那条鱼,
如果它还活着,它也不敢想
会有我们这么多人
来看它,对它指指点点
在岸上的那条鱼,
有好多女生,都不敢接近它
它已经开始发黑、发臭了
如果它还活着
它会愿意这样吗?
在岸上的那条鱼
已经没有了眼睛
只有一个黑洞洞
如果它还活着
它会用这样的方式看着天空吗?
在岸上的那条鱼
有人说它是自己跳上来的
如果它还活着
它一定会张开嘴巴,大声说:
“NO!”
林先生的这首小诗明显是无言听话人式的独白,从“我”的自白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恻隐之心以及对死亡充满不解的小男孩形象。全诗只用了一种颜色词,黑色,使全诗笼罩着浓厚的死亡气息。黑色共出现两次,第一个“黑”描写在岸上那条鱼的外部显性特征,“它已经开始发黑、发臭了”,离开了水的鱼,生命如何不走向终结?第二个“黑”描写岸上那条鱼的眼睛,失去生命之水润泽的眼睛空洞而无光亮,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当“我”和岸上那条鱼无法用眼睛沟通时,索性说“已经没有了眼睛 / 只有一个黑洞洞”,这完全是孩子的思维方式,包括每一段中排比出现的“如果他还活着”,都是孩子对死亡的不理解,同时也折射出孩子对岸上那条鱼的恻隐之心,当大家对它指指点点、好多女生都不敢接近它,“我”,一个小男孩,却能站在鱼的立场,和它感同身受。诗人从孩子的眼光出发,把死鱼的眼睛比喻为洞洞,而且是黑色的洞洞,黑色给人以心理上的压抑感,并且黑色的洞深不可测,对死亡的不可知带给“我”深深的恐惧感。黑色而外,诗人还巧妙地运用了蓝色作为黑色的对比,那是天空的颜色。活着的人可以尽情享受天空蓝,而岸上的那条鱼,只能用一个黑洞洞看着纯蓝的天空。在“我”的心里,死去的鱼还是可以看天空的,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真是天真可爱!
对比色造境
单色对诗歌有渲染效果,主导诗歌意境,使整首诗氛围和谐统一。对比色造境则完全不同,不同色彩会打破诗歌基调的整体性,使诗歌意境富有张力。林焕彰童诗中的色彩对比以色相对比(补色对比、邻近色对比)、明度对比、冷暖对比、色块对比为主,不同色彩对比所营造的意境也不尽相同。补色对比显得明快;邻近色对比显得温和;冷暖对比调动人的生理感受;明度对比则可以营造出带有过渡感或层次感的诗歌意境。
(1)补色对比
对比手法的运用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混合后呈灰黑色的两种颜色互为补色,在诗歌色彩对比中,补色对比最能体现对比带来的冲突,同时,补色对比也能避免单调,使诗歌意境显得明快、活跃。林焕彰先生利用色彩词之间的强烈对比来塑造形象、营造意境的功力可谓炉火纯青。
邮筒有两个兄弟,
他们喜欢站在一起,
而且个子都一样高;
只是一个爱穿红衣服,
一个爱穿绿衣服。
穿红衣服的,性子比较急,
他叫邮差送信,
要骑摩托车去;
穿绿衣服的,喜欢慢慢来,
他告诉邮差,
骑脚踏车就可以。
单句诗歌运用补色对比的十分常见,但是像林焕彰先生的《邮筒》这样将色彩附着于意象使得色彩对比贯穿全诗的却少见,真是独树一帜。“对于那些普通的生活场景,如果你能以儿童的方式去观察它,感受它,你就会赋予它一种崭新的生命力。”
诗人用孩子的视角观察,用孩子的口吻讲述,讲故事般娓娓道来,一笔一划勾勒出邮筒两兄弟,一个爱穿红衣服,一个爱穿绿衣服,一个性子比较急,一个喜欢慢慢来,穿红衣服的急性子送信骑摩托车,穿绿衣服的慢性子骑脚踏车就可以。全诗无一处华丽的辞藻,邮筒两兄弟的形象在我们脑海中却历久弥新,一红一绿,一急一慢,煞是有趣,孩子们去寄邮件,恐怕再也不会弄错哪个是快递,这便是童诗的魅力。林焕彰在这里选择红绿两色作为对比色是有讲究的,诗歌中最常见的补色为红和绿、黄和紫、蓝和紫,其中以红和绿最为常见。同时,色彩存在一般性的色彩通感经验,见下表:

分析色彩通感意义的研究结果,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急性子的邮筒爱穿红衣服,而慢性子的邮筒爱穿绿衣服。
(2)明度对比
明度,顾名思义是指色彩的明暗程度,色彩的明暗对比往往可以营造出带有过渡感或层次感的诗歌意境。
有时候色彩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隐藏在词语背后的,但是这些词很容易刺激大脑生成一个个色彩浓郁的场景,营造诗人表达所需的环境,如《那年》:
那年,
冬至后,
一个黄昏;
我跟隔壁阿吉仔玩捉迷藏,
躲在他家屋后的墙边。
已经数过一百了,
阿吉仔还未找到我,
而夜像一个家伙躺过来,
将我遮住;
于是,我们玩得更久,
阿吉仔一直找不到我,
妈妈也找不到我。
那晚,
我不敢回家。
这首小诗对于小读者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有趣的、可能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躲猫猫的故事,但是它却写进了许许多多大读者的记忆深处,不是因为诗中的“我”,而是因为曾经的“我”而忍俊不禁。确实,小时我们都玩过躲猫猫的游戏,有的时候因为躲得太过隐秘,游戏变成了“悲剧”.《那年》中的“我”就是这样,他不是因为躲到了柜子里、床底下、或者其他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而被放弃寻找,而是因为夜将他遮住了,一个看似幼稚的理由,却让我们觉得如此感同身受,仿佛再一次经历那由兴奋到忐忑最后害怕的等待过程。“那年 / 冬至后 / 一个黄昏;夜像一个家伙躺过来/ 将我遮住”,虽无一个色彩词,但是黄昏的温暖渐渐褪去,夜色越来越深,如露沉重,暖黄过渡到冷黑的这一过程,是通过“黄昏”、“夜”这两个词来描绘的。“我”的情绪也和“黄昏”与“夜”步调一致,一开始玩得开心,但是隔壁阿吉仔找不到我,天都黑了还没有找到我,“那晚 / 我不敢回家”,真令人怜之、笑之。
(3)色块对比
如果用数学用语来解释,色块对比与其他类型的色彩对比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可以是补色对比,也可以是邻近色对比,区别在于色块对比往往适用于较大的场景,它侧重于大的色彩面积。在意境营造上,色块对比的效果甚佳。
一群白鹭鸶,低低飞
柔软的翅膀
鼓动着,静止的风
它们,低低地飞过了田埂
犁过的稻田,已经注满春水
秧苗在秧房中
伸展嫩绿的小手
开始试探早春的冷暖
自强号列车,穿过家乡
速度把静止的空气
拉响,也拉响了我的心事
外婆的家,还在铁道旁
后院那颗老杨树上
挂满了黄黄绿绿的小星星
好像还挂着小时候的我
在杨桃树下巴巴张望的,眼神
林焕彰先生的这首《车过我家乡》,除了和其他童诗同样充满童稚童趣之外,还带着一股淡淡的乡愁。林焕彰先生曾说:“‘儿童’是儿童诗的作者。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自己的意识形态,写诗就应该让他们尽情地自然流露或表白他们自己的意思。”然而在《车过我家乡》中,诗人好像写着写着便情不自禁,不管不顾地从“儿童”的身份跳脱而出,成为自己,眼前大片大片那嫩绿的初春的稻田以及不远处低低地飞着觅食、嬉戏的白鹭鸶,都没办法将他拉回,原来是那列车的轰鸣将诗人拉回了外婆的家,于是所有的小朋友跟着一位年迈的“林叔叔”一起回到了后院那颗老杨树上,小朋友们看到了枝繁叶茂的老杨树上“挂满了黄黄绿绿的小星星”,而“林叔叔”还看到小时的自己,像星星一样眨巴的眼睛。列车一瞬而过,诗人又回到了儿童的世界,当他站在原地,眼前除了一大片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的嫩绿,铁轨的那头,还挂着一树黄黄绿绿的小星星眨巴眼睛,白色的鹭鸶还在低低地飞来飞去,点缀着这满眼的绿。为什么坚持为儿童写诗的林焕彰跳脱了儿童的身份?因为他要求自己“用最好的语言,最愉快的心境,最纯真的意念,最丰富的情感,最灵活的想象,最新的思想……来为他们写诗。”林焕彰先生正是这样实践着他创作童诗的理念,情到深处,自然流露。也是因为如此,两个时空的场景才完美融合在一首诗中,完成了“邻近色的色块对比”,独一无二,读来过瘾。
多色想象
多种色彩在同一首诗中互相融合,产生强烈的带入效果,引人入胜。“语言丰富的人,能以准确而调和的色彩描画生活”,看似简单的多色组合,却最见诗人的用色功力,只有和谐的色彩搭配才能产生色彩美,才能营造出美的诗歌意境;反之,不和谐的色彩搭配给人以杂乱无章感,很容易令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当然,有些现代诗人刻意利用色彩丑来营造诗歌主旨传达所需的意境,但在林焕彰先生的童诗中,几乎没有这样的刻意为之,他选取的色彩都是符合儿童心理的,阳光而积极向上。“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多年的绘画经验让他在色彩搭配方面游刃有余,熟稔如何搭配色彩才最有利于诗歌意境的营造。
《鹅妈妈的宝宝》是一首长诗,全诗选取了五种色彩,共十六处出现色彩词,读起来自然、清新、趣味盎然,丝毫不觉杂乱无章之感。开篇第一句“鹅妈妈在池塘里捡到一片红叶,/ 她说:/ 冬天来了。”透明的池水中静静地飘着一片火红的树叶,穿着白色丝绸大衣的鹅妈妈笨拙地游向它,将它摭拾,红与白形成强烈的对比,瞬间将读者带入那个唯美的童话世界。冬天来了,鹅妈妈回到它的窝里造宝宝,窝外的世界一片雪白,窝里同样一片白色,鹅妈妈还是穿着她那件珍贵的白色丝绸大衣,一个一个地,生了五个白白胖胖的大鹅蛋。过了一个月,从白白胖胖的大鹅蛋中钻出了五只小鹅,“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淡黄色的衣服。”“五只小鹅像五朵小黄花,/ 会走路、会唱歌、会跳舞的 / 黄色的小菊花。”这里一口气从纯白转换到纯黄,转换自然,丝毫不露痕迹,独独被这五朵活泼可爱的小黄花所感染,仿佛春天来了,我们走在踏青的田野间,闻到花香,听到鸟语。果然,五朵小黄花跟着鹅妈妈走出小窝,探索这个“好新好新”的世界,天清气朗,鲜花盛开,鹅妈妈和鹅宝宝们一路看到了:和小鹅衣服同样颜色的小黄花,和鹅妈妈衣服一样颜色的小白花,和嘴巴一样颜色的小红花,和眼睛一样颜色的小蓝花,还有一朵不知道跟什么一样的小紫花,所有春天的色彩都与可爱的鹅宝宝一家融为一体,我们也沉浸在这种融融的气氛中,笑开了花。不禁感叹,林焕彰先生用色之出神入化,非“天然去雕饰”不能形容。
结语
色彩介入林焕彰童诗,使林焕彰童诗融合绘画艺术的技法和审美特征,丰富其诗表现力,影响诗歌的审美构成,使诗歌富有韵味。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色彩只是作为影响诗歌审美的其中一个因素,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对林焕彰童诗色彩的审美分析包括色彩在林焕彰童诗中的审美生成和色彩在林焕彰童诗中的表现方式,都是置于整个诗歌语境大背景之下进行的。通过个案分析、整体比较,我们从林焕彰先生每一首小诗的字里行间看到一位在纸页上用心灵写作、童心未泯的老人形象,这位老人诗画兼善,色彩在他的笔下,能“画意”,能“传情”,他说:“为儿童写诗,就像每一个父母对待他们的子女一样。”怀揣着这样一颗殷殷之心,何愁写不出动人的诗章呢?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一直以来,林焕彰先生都怀着一颗为儿童作诗的爱心,在语言的汪洋中悠游,他用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贴近儿童心理的语言,为儿童描绘出一个缤纷绚烂、真实美好的世界。
当代儿童诗人王立春出生于满,汉,蒙三族杂居的辽宁省阜新,六岁那年,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在位于乌兰木图山脚下的阜蒙县哈达户稍乡生活了五年。虽然时间短暂,却影响了诗人一生,我一辈子离不开乡村的哺育,离不开我儿时所感受的教益。正因为从这个小山...
晚清民初的学堂乐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儿童诗歌的创作之门,从晚清到五四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儿童诗歌显示出较鲜明的阶段性艺术特点。选取以老鸦为内容的几首儿歌作为线索,能够以点带面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儿童诗歌从风格到意境的流变轨迹,揭示出...
童诗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以儿童为对象的,最富于感情、最凝练、用有韵律、分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童诗历史悠久,可追溯到骆宾王的《咏鹅》,取材自然,意境优美,寓意深远。但是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与儿童本位观的缺失,使中国古...
儿童文学是文学体系中比较特殊的存在,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创作者与读者的身份不同,此二者之间的差异指向我们对“儿童”追问与反思。...
诗歌能够帮助人们找回童年,诗歌和童年关系密切,女诗人夏吟在诗歌中始终保持对儿童的热诚关注,她写了许多儿童诗,也写了许多以儿童为书写对象的诗,还写了大量的和童年、游戏有关的诗歌,表现童真、童趣和童话,这些诗充满了温情和想象力,格调健康,激情...
林良是台湾知名的童诗创作者,他笔下的童诗处处闪现着质朴本色的真美。质朴是一种美学品格,在形式上语言平实不雕琢,内容上扎根于自然与生活,表现的是一种简约、自然、朴素的风格,体现了事物真与善的本质特征。林良的童诗精简短小,不事雕琢,...
儿童诗歌以其语言天真活泼、柔软,结构简便灵活明显区别于为成年人创作的诗歌。其中的审美特征也其独特的气息和风格来进行表达,扣孩子们的心弦,反复激起他们对自然的见识、对生命的感情、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儿童的情趣特殊,许多现象,景观、色彩款式、闪...
新世纪以来, 在中国儿童诗歌的版图上北京、上海和重庆呈现三足鼎立之势。而重庆市巴南区、永川区又成为西南直辖市重庆儿童诗歌的重镇。戚万凯为巴南区儿童诗坛的领袖, 永川区的领军人物则为钟代华。...
一、引言在当今华语诗坛,有一位诗人的作品渐渐引起了人们阅读、研究的兴趣,他,无师自通,童心未泯,他就是享有国宝级的儿童文学家美誉的台湾诗人林焕彰。在台湾当代诗坛上,林焕彰是个异数.[1]1939年出生于台湾宜兰礁溪乡的林焕彰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
1研究背景。(1)童年消逝的忧虑与扞卫童年的需要。童年时代应该是纯真的、无忧的、甜美的,童年生活的绚丽美好应该植入于每个人永远的记忆中。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孩子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童年却过早地打上了成熟或者说是迷惘灰色的色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