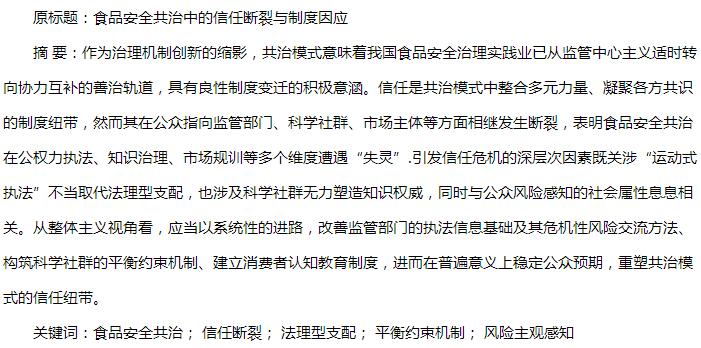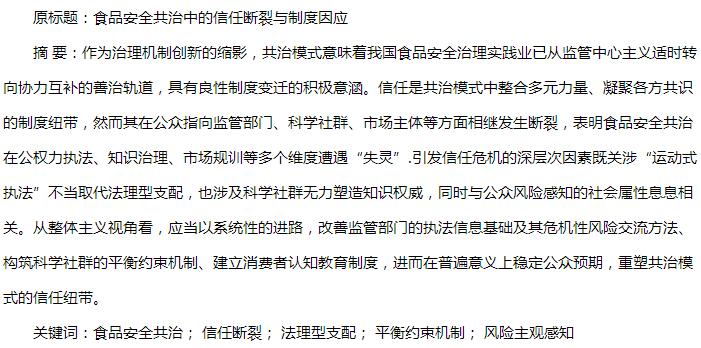 一、问题的缘起: 食品安全共治何以可能
一、问题的缘起: 食品安全共治何以可能
食品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机制设计必须予以有效因应的重要民生法治议题。作为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治理优化的投影,近年来我国先后从制度、组织、技术等多个层面切入,力图全面构筑食品安全风险防治体系: 及时废止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在2009年出台并于2015年修订通过了系统性更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 ; 设置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从科层权威角度增强全国食品安全治理的统一协调性;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进一步整合优化执法资源; 组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推动风险评估技术优化升级等。然而,上述治理优化的种种努力却在当下遭遇严峻的现实壁垒:从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到双汇“瘦肉精”猪肉,再到跨国肉制品巨头福喜公司改装上市的过期劣质产品,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不少着名品牌异化成制售假冒伪劣的“避风港”,严重损及消费者的安全预期; 在日常的媒体报道披露中,“塑化剂”白酒、“苏丹红”鸭蛋、地沟油、毒豆芽等有毒有害食品始终不绝其踪,“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成为公众心中挥之不去的安全阴影,并逐层累积、日渐放大成无处不在的集体焦虑。
在现实的危机挑战下,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进程同步,开始积极探索多元治理之道。2015年4月24日修订通过、同年10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将“社会共治”给予基本法律层面的确认,将之规定为今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制度之一。从《食品安全法》的法律效力以及随后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多层次食品安全协同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当前的食品安全治理业已转向共治机制,其力图改变既往拘泥于监管中心主义的窠臼,全面吸纳一切可能的治理力量,建构增益互补的安全控制体系,这是食品安全领域福柯意义上治理技术[1]的深刻变革。共治的制度化,意味着食品安全治理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挑战业已纳入协同互补的处理机制,而不再由公权力主体垄断治理。这一体系化的制度思路,既需要以国家强制为核心的监管权威,需要以专业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等为代表的科学社群①的智力支持,需要广大公众基于“用脚投票”的弥散化的市场制裁,更需要借助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2].只有有机整合这些不同源泉、不同形式、不同适用机理的多元力量,才能彼此取长补短,发挥体系化治理效力。
食品安全共治,究其实质,在于借“共”而达“治”,非“共”则无以为“治”.在“共”的治理体系中,讲求的是多元力量信任互助、同心戮力,是各方主体围绕“治”的共识性目标而形成和谐均衡格局,其间他们以积极能动的自觉性加入治理的行列,在协力共进的治理实践中最大程度地展现主人翁的立场。以“共”达“治”,以主体间性取代主客二分,在这一根本性变革的背面,究竟以何种深层次因素作为制度基础方能成就各方主体之间协力共进的均衡格局呢? 易言之,是何种因素改变了各方主体原本原子化的分布状态,将之有效地粘合成互补增益的治理有机体,进而顺利实现以“共”达“治”的制度目标?
二、通过信任的食品安全共治之道
从共治模式的运行机理看,其得以聚合各方的制度纽带在于信任。人类的任何社会合作行动,都需要一个基础性前提: 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约束性条件下,行动主体之间能够实现彼此期待的行为选择预期,建立起对于相对方行动之恒常性认知,在此基础上产生人际信任。舍此,合作将无从发生,也难以为继。“人际之间若无普遍的信任,社会就会解组,因为很少有关系建立在对他人行动全面、彻底确知的基础上。”[3]信任附着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按起源划分,社会关系分为先赋性关系、准先赋性关系、获致性关系[4]; 按照功能划分,可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5]; 按照交往的亲疏距离分,则分为家人连带关系、熟人连带关系、弱连带关系、无连带关系[6].尽管视角不同,但上述分类分享了一个隐含的共同标准,即依据主体之间熟悉/陌生的差异程度进行界分。以社会关系为主轴,可以构建出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 (1) 社会互动以行动者自我为起始原点; (2) 与该中心原点的距离越近,情感性关系越强,越值得信任; (3)从中心原点外推开来,情感性关系逐渐减弱,工具性关系逐渐增强,信任也随着成员之间的离散化程度加深而淡化[3]283 -284.循此逻辑,在以工具性关系、无连带关系等为代表的陌生化关系中,倘若缺乏特定的制度安排以保证行动者对于彼此行动的稳定预期,则其中的信任最为淡薄,也最难在这类关系覆盖的群体当中建立合作。正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人们尤其需要借助科学的机制设计、借助法制手段[7]建立普遍信任即制度信任[8],借助这一基于制度威慑的信任(deterrence - based trust)[9]弥补特殊信任即情感/血缘信任之失。进一步分析表明,信任的指向和分布是由信息决定的。究其实质,信任是对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应对机制---在无法确知相对方的具体行动选择时,仍然对其选择保有稳定预期,主观认定其仍将选择信任者所预期的行动。由此可以推知,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各方的行动选择都是可观测、可验证的[8]198,那么在这一确知的状态下就无需信任,各方主体可以根据完全信息进行决策; 如果一方相对于其他主体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那么此时的人际信任则是由信息劣势方指向信息优势方,是前者对于后者在互动过程中的稳定预期。对于信息对称状态或者信息优势者,信任没有适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