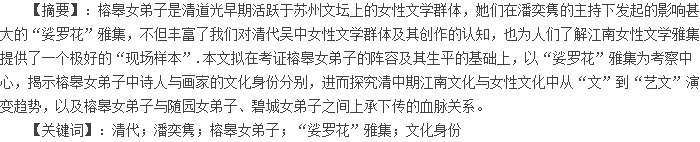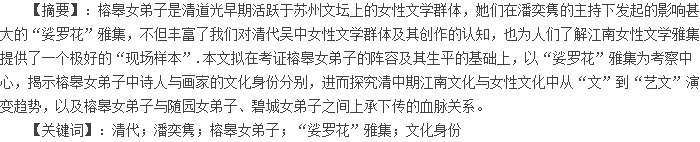
在清代嘉道间的江南诗坛上,女性文学创作处于彬彬郁郁、斐然称盛的“黄金时期”,其中随园女弟子与碧城女弟子这两个会聚一时灵襟的女性文学群体堪称杰出代表。不过,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榕皋女弟子却极少被当下的研究者提及。事实上,这个在宗主潘奕隽的奖掖倡导之下颇为活跃的女性文学群体,不唯为江南女性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过贡献,更在随园女弟子与碧城女弟子这两个女性文学群体之间具有承前续后的血脉联系,因而深具女性文化史、文学史的考察意义。
一、榕皋女弟子丛考
潘奕隽(1740-1830),字守拙,号榕皋,又号水云漫士、三松居士,吴县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协办、侍读、户部贵州司主事、贵州乡试副考官等职。潘奕隽“嗜吟咏,以诗文名世”,“论诗原本风雅,得于性灵为多”,有《三松堂集》传世。潘奕隽京华碌碌十余年后,即“早辞粉署挂帆远”,其后“林居四十余年,读画评诗,游心物外,怡然乐也”.潘奕隽生当承平,天佑耆寿,文采风流,照耀吴下。作为吴中文坛领袖的他,特别乐于奖掖后进,尤其是对待女性文学创作的态度,更显出通达的宗主气概。潘奕隽致仕后,他一面与骆绮兰、汪端等女诗人往来唱和,一面又为这些“扫眉才人”张扬鼓吹。如题骆绮兰《听秋轩集》有云:“今观佩香诸体,冲和大雅,独得正声,故当追步曩哲,非徒压倒名媛而已。”其序《吴中女子诗钞》有云:“诗固女子之所事也。《周南》,女子诗居其八;如《召南》十四篇,女子之诗居其十二。里闾能诗之彦,往往出于闺闼之间。”
嘉兴沈毂诗画并妙,刻成诗集《画理斋诗稿》后索序潘氏,潘奕隽以“耳目几近废”的八十六高龄,仍推誉其诗:“沨沨乎清微和雅之音,鲍妹、谢女之余韵也。”作为这些闺秀的诗道知音与揄扬者,潘奕隽一直以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肯定她们的创作,鼓励她们交游与出版作品,更主动召集她们拈韵联吟,分笺酬酢,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争诵三松侪五桂,珠林雏凤彩衣斑”的女性文学群体--榕皋女弟子。
榕皋女弟子以群体性面貌公开亮相,是在道光甲申年(1824)潘奕隽所主持的“娑罗花”雅集上,其具体的活动细节见之于苏州贵潘所刻的《佛香酬唱集》一书中。这本刊录了潘氏家族与苏州文士雅集唱和的主题诗集共分三集,《佛香酬唱集·初集》卷首潘奕隽撰有小序以记此雅集缘起与活动梗概:
道光甲申四月五日,撷芳亭娑罗花盛开,花出天台山华顶,钱唐王松泉司马文鳌所赠也。招女弟子陈友菊秀生、吴香轮规臣、顾畹芳蕙、陈灵箫筠湘并赏之,诗以纪事。望后三日,属外侄孙女李定之慧生为花写影,定之,乃黄尧圃孙妇也。由序可知,参加潘奕隽道光甲申四月的“娑罗花”雅集的女弟子有陈友菊(秀生)、吴香轮(规臣)、顾畹芳(蕙)、陈灵箫(筠湘)四人。为花写影的李慧生虽未曾参与唱和,但据江标《黄荛圃先生年谱》所载:“饮鱼(按黄丕烈孙黄美镐)室为李氏,名慧生,字定之,工诗画,为子仙孝廉福之女,潘榕皋先生之诗弟子也。”由此可知,李慧生也是潘奕隽女弟子。《佛香酬唱集·初集》中还列有其他闺秀和作,她们分别是李珍(浣霞)、叶苞(九仪)、归懋仪(佩珊)、管筠(湘玉)、汪端(允庄)、张襄(云裳)六人。六人中归懋仪一人独和七首之多,她对“娑罗花”唱和的积极响应,自然让人觉得她与潘奕隽之间有着更紧密的关系。事实上,潘奕隽在黄丕烈所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一书的跋语中道明了他与归氏的师生情谊:
荛圃得《幼微道人集》,倩秋室学士图像于前。复索拙句,自惭荒劣,不称是题。代索女弟子归佩珊填《壶中天》一阙,置之《濑玉集》中,盖不能辨也。由此可知,归懋仪为榕皋女弟子无疑矣。至于榕皋女弟子的具体组成,除了《佛香酬唱集·初集》外,清人别集与总集中罕见提及。笔者搜检清代女性别集,唯有汪端的《自然好学斋诗钞》与骆绮兰的《听秋轩诗集》中多有与潘奕隽及其女弟子的唱和之篇,综合这三种集子中的榕皋女弟子名单,我们大致可以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榕皋女弟子阵容。首先,汪端《题陈无逸〈三松七子图〉》一诗不仅在诗题上点出“图中七人,皆榕皋先生女弟子也”
这一重要信息,而且在诗中注出七子姓名,她们分别是:顾畹芳、吴香轮、陈灵箫、陈友菊、孟咏琴、李慧生、陈无逸。以此为凭据,榕皋女弟子的名单比之《佛香酬唱集·初集》上所载又增孟咏琴、陈无逸两人,加上归懋仪,榕皋女弟子已至八人。再者,骆绮兰《寓邗上,承潘榕皋先生过访,率呈一首》中“此时可忆诗人否,怅望先生倚夕阳”句下有注云:“谓先生弟子周素芳”,由此可知,周素芳亦为榕皋女弟子无疑也。
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确定,围绕在潘奕隽周围的榕皋女弟子有归懋仪、陈秀生、吴规臣、顾蕙、陈筠湘、李慧生、孟咏琴、陈无逸、周素芳等九位才媛。爬梳抉剔相关资料,我们始能勾勒出其中的七位闺秀(孟咏琴、陈无逸暂无考)的生平轮廓,现分述如下。归懋仪(1762-1832),字佩珊,常熟人。巡道归朝煦女,上海监生李学璜室。有《绣馀吟草》。
归懋仪不唯是榕皋女弟子中引人瞩目的人物,亦是其时巾帼才人下风拜倒的诗坛领袖。归懋仪之诗于清婉绵丽中有发扬纵达之气,一洗闺阁纤秾之习,实是闺音中杰出者。陈文述赠诗赞曰:“绝代青莲笔,名媛此大家。”归氏在问字榕皋之前,曾为随园女弟子,其题《虢国早朝图》“马驮香梦入宫门”之句为袁枚所激赏,赞其诗“雄伟绝不似闺阁语”,并以“领袖人间士大夫”的期许相赠。
归懋仪在拜入榕皋门下的同时,又与赵翼、洪亮吉、王文治、汪启淑、陈文述等名家相唱和,一时之间,诗名隆于东南。广泛的诗学交游与旺盛的创作才能,使得她的诗学内容相较于同时期的闺秀更为丰富。褚华题其诗稿:“扫眉才子才如海,搴取闺房姑蔑旗。”盖实录矣。
李慧生,既是榕皋女弟子中画技出众的才女,更与潘奕隽有着多重亲近关系。潘奕隽在“娑罗花”雅集小序中已交代过李慧生是他“外侄孙女”及“黄尧圃孙妇”这两层姻亲关系。其实,李慧生父李福亦是潘奕隽过从甚密的诗友,由长辈至亲加好友的姻亲关系延伸而成的潘、李之间的师徒情谊显得格外自然与亲切。李慧生,字定之,苏州人。诗人李福女,黄丕烈孙黄美镐妻。李氏精能绘事,尤擅花卉。“娑罗花”雅集中引发众人唱和的《娑罗花图》就是出自她的手笔。此外,据江标《黄丕烈年谱》载,苏州问梅诗社召开第十五次雅集时,黄丕烈亦命李慧生作画,并请同社诗友题之。显然,李慧生的妙手丹青不仅是闺秀画家中之翘楚,亦得到了吴中文士的认可与肯定。
顾蕙是榕皋女弟子中声名颇着的才媛。顾蕙生于名门艺族,“父纯熙字湘筠,善绘事”,外家更是一门风雅,外祖翟云屏、舅翟琴峰“俱精六法,负盛名”.她“幼聪颖,六岁即喜读书,能见大概。秉庭训兼得外家三昧,写花鸟,丰神骨力兼擅其胜”.得天独厚的家族艺文氛围与天资颖异的兰心蕙质奠定了她不寻常的诗画人生,而出嫁才士毛庆善与请贽于名师潘奕隽则又成为其艺文生涯的新起点。顾蕙不唯画笔动人,亦擅吟咏,并着有《酿花庵小草》,《国朝闺秀正始集》中亦选其篇什。对于顾蕙来说,咏絮名族,结缡名士,亲炙名师,似乎能造就艺文才名的各种因素都集其一身,也无怪乎她的成就与影响能超过同侪了。
陈筠湘与顾蕙齐名,据潘曾莹所撰《施室陈孺人传》可知,陈筠湘原为吴郡名诸生张野樵先生女,早失怙,恃表姑育为己女,遂冒姓陈。陈筠湘,字仲芳,又字灵箫。陈幼年早慧,通五经及唐宋诗文,工韵语。嗜读书,晨夕不释卷,裙钗问字,粲然成行。书临钟绍京,画师夏茞谷,茞谷为昆山唐和春高弟,孺人尽得其渲染之法,尝作梅花便面,神似杨补之。又作小楷数帧,秀逸工整,顾南雅先生见之,极为心折,于是遐迩索书画者无虚日。善鼓琴,作《停琴小影》,石琢堂、郭频迦、齐梅麓诸名宿俱有题咏,诗学剑南,着有《九华仙馆集》四卷,《西泠渔唱》一卷,诗作亦散见于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陈文述《碧城女弟子诗》等选集中。汪端有《赠吴门陈灵箫夫人》云:“郁嫔仙范今重见,高咏青山静掩扉。
吴苑名家陆卿子,唐宫学士鲍君徽。露华涤笔香生纸,花影横琴月上衣。佳句应追李秋雁,一行湘水带霜飞。”亦实录也。榕皋女弟子吴规臣则是以诗、画、医、剑术无所不通的面貌出现在时人评价中:“吴规臣,字香轮,一字飞卿。长洲顾小云大令室。小云远宦,飞卿常往来金陵、维扬间,鬻书画自给,奇情倜傥。工诗词,精医理,通剑术。画无不擅,而尤妙写生,赋色妍淡,神夺瓯香。”
曾作扇面《九秋图》以贻友人,改七芗、倪小迂等写生妙手见之,皆叹赏不置。应当说,吴规臣在博通诸艺的同时,她“画无不擅”与“神夺瓯香”的画技尤为引人注目,无怪乎陈文述赠诗云:“闺中自有鸥香馆,绝代佳人老画师。”上元闺秀陈秀生为榕皋女弟子中精能书法者。陈氏字友菊,参军徐垣室,有《望云楼诗集》。陈氏工书法,尤擅晋人小楷。陈文述曾赠以“石城烟雨写冰纨,珍重吾宗有采鸾。咏絮诗情清胜雪,簮花书格静于兰”的诗句,以唐代女书家吴采鸾比之陈秀生,可见书格高雅,诗情清净。
周澧兰,字素芳,江苏长洲人,知县周兆熊女,李大桢妻。周氏为其时诗书画并能的才媛,有《浣云楼诗草》传世。书画一道,骆绮兰《题周素芳松泉小影》“开图惊见卫夫人”句,当为推服其八法者。又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云:周氏“白描士女最工,矜惜殊甚,非闺阁素心友不能得也”.
可见周氏亦擅丹青。与此同时,周曾参加袁枚在苏州召开的阊门绣谷园诗会,故曾为随园女弟子无疑也。考察榕皋女弟子的阵容及个人生平后,我们发现,榕皋女弟子这一女性文学集群虽不及随园女弟子与碧城女弟子那样光熹耀眼,但将其置身于群星闪耀的清代江南女性文学星空中,仍有其特殊的考察价值。究其原由有三:其一,就地缘而言,与随园、碧城广招门生,以至于弟子遍布江浙地区的宽泛甚至松散人员构成相比,榕皋女弟子以苏州本地人居多,其中陈秀生与吴规臣是随夫家定居苏州,亦可以苏州人视之。所以,密切的地缘性使得潘奕隽与其女弟子之间诗画交往比随园与碧城要更为直接与频繁,并对她们文学艺术活动及智识生活施加更深刻的影响。其二,从艺文结合的层面上看,榕皋女弟子所追求的才学内涵更为宽泛。归懋仪、周澧兰皆能诗、书、画,李慧生、顾蕙、陈无逸精于诗、画,陈秀生能诗工书,陈筠湘诗、画、琴俱能,吴规臣更是诗、画、医、武术并能,显然,具有综合的艺文能力是榕皋女弟子突出之处。其三,就女性文学群体的关系而言,榕皋女弟子与随园女弟子、碧城女弟子之间有着前后衔接的血脉关系。归懋仪、周澧兰皆名列随园女弟子之位,从时间上看,她们转投潘奕隽门下,显然是在随园离世之后。而榕皋女弟子的中坚陈筠湘、吴规臣、陈秀生则在潘奕隽逝后,转师碧城,其中吴规臣更被梁乙真称为“陈碧城门下才华之美者”.这一关系的揭示,既丰富了我们对清代吴中女性文学群体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认识,亦有助于推进清代女性文学的深层研究。
二、“娑罗花”雅集中的身份认同
对于榕皋女弟子来说,“娑罗花”雅集是她们集群互动,联翩吟唱而演出的一场女性艺文的盛宴。这场艺文盛宴的出演,既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师生间心灵碰撞、同声交契的艺文雅集的“现场样本”,也因为弟子间诗人与画家的文化身份差别而引发认同之异调,可以深化我们对清代江南女性文会活动中“诗画风流”的认知。
道光甲申(1824)四月,潘奕隽招女弟子陈秀生、吴规臣、顾蕙、陈筠湘等人群集于三松堂下的娑罗花旁,延伫赏花,品香啸歌。这次雅集既保存了榕皋女弟子最生动的群体文学活动,也为后人留下了这些闺秀文化生存状态的一段记忆。
就雅集而言,潘奕隽既是活动的发起人,又是整个过程的推动者与主持者。他首倡在先:
浙东佛地树娑罗,开到幽斋客肯过。
华顶一株分荫远,撷芳今岁着花多。
檐前日暖能延伫,亭角香清可啸歌。
那得双瞳翦秋水,名篇北海手重摩。
参加雅集的榕皋女弟子顾蕙、陈友生、陈筠湘、归懋仪等人联袂出场,依韵奉和,她们的诗作可用陈友生的“拈得瓣香还窃喜,撷芳亭畔拜维摩”两句来概述之。从活动过程可知,雅集开端于赏花,在潘奕隽与女弟子当堂赋诗之后的“望后三日”,潘奕隽“属外侄孙女李慧生为花写影叠前韵”,并由此将以榕皋女弟子为主要参与者的“娑罗花”雅集扩大为一场包括吴门名士、贵潘弟子与吴门闺秀等三十五人参与的“和者甚众”的地域风雅联唱。
当我们较深地进入《佛香酬唱集·初集》这一风雅联唱的文本空间时,会发现在文人雅士用联吟的方式表达对三松堂下、撷芳亭旁佛缘天香的向往与艳羡的同时,几乎都对女弟子李慧生为花写影的《娑罗花摹本》不吝颂词:凭将湘管试兜罗,落墨徐熙不汝过(潘奕隽),更倩眉娘粉本摩(宋熔),凭他妙手一描摩(尤兴诗),更倩边鸾与细摩(吴信中),画工何处着临摩(尤崧镇),定知画本费描摩(黄美镐),兜罗绵手写娑罗(陈文述),临摹粉本兜绵手(张吉安),读画留题取次过粉本优昙佐啸歌(孙学诗)。欣从画里识娑罗(毛翔鳞),灵葩写照还调粉(毛庆善),粉本何妨一再摩(顾蕙),读画人徵宛转歌(叶苞)。
不论诸人将李慧生比作大画家徐熙与边鸾的说法是否有过誉的溢美之嫌,只从“欣从画里识娑罗”与“粉本优昙佐啸歌”的表达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李慧生的丹青妙笔既是这些诗人对“娑罗花”及女弟子雅集直观了解的凭借,也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头。所以说,对于“娑罗花”雅集后的更大规模的风雅联唱,李慧生的绘画是重要的引导物,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图引”.李慧生作为“图引”的“娑罗花”图所激发的不仅仅是众人文学创作的激情,还有对其绘画艺术的赞赏。顾蕙即以“粉本何妨一再摩”表明画家身份,而她这一身份既得到潘奕隽“粉本重烦妙手摩”的肯定,也得到潘奕隽“畹芳女史亦以所画见贻”的证实。
显而易见,李慧生与顾蕙,在这一场榕皋女弟子集群性文化出演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她们作为丹青妙手的画家身份。在师妹们争妍竞演与吴中雅士们同台喝彩时,归懋仪亦是吟兴不减,她幽汩涌动的闺音在显扬其诗笔之时,多少让人感受到她与其他榕皋女弟子之间文化身份之分别。“娑罗花”雅集伊始,身处异地的归懋仪虽是“偏我无缘未得过”,可这并不妨碍她以诗句来想象“天花开到曼陀罗”的撷芳美景。特别是潘奕隽将李慧生“娑罗花”图与“珠字满眼、妙香纸上”众人唱和之作远示于她,“碧天如水夜闻歌”的归氏“尘劳一扫挑灯读”,在“几度含毫费揣摩”的沉吟中,如“佛香缥缈采云罗,玉河照影几经过”般的清词丽藻联翩而至,“夜深瑶鹤搏风至,月好骊龙出水歌”般的奇思异想缤纷而出,归氏操觚摅臆,一泻而下竟成诗七首,其诗力之盛不唯是榕皋女弟子中的冠冕,就是置于《佛香酬唱集·初集》的众多唱和诗中也堪称夺目。当我们再检对《佛香酬唱集·初集》的诗作时,可以看到除了雅集主持人潘奕隽前后赋诗三首,毛庆善为了配合其妻顾蕙的一诗一画而赋两首外,所有唱和者都是一人一首,而归氏如此诗兴大作而到喧宾夺主的地步,是她不可遏止的诗情在喷薄,还是别具怀抱、另有隐情呢?
带着这一问题,我们查对归氏的《绣馀小草》《绣馀续草》《绣馀续草再》《绣馀续草三》等诗集,归氏唱和酬答的篇什极富,但如在《佛香酬唱集·初集》中数倍于其他酬唱者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显然,在众声喧哗中炫才示雅不是她的习惯与风格。那么,归氏一反常态的诗兴大作则应是另有意旨的。事实上,归懋仪不但是榕皋女弟子中重要的一员,也是她们中声名最盛、影响最大者。可以说,从诗艺与才情而言,归懋仪的师妹们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既然没有必要与师妹们比赛诗艺,那么最有可能是李慧生的“娑罗花”的图引与潘奕隽对李慧生、顾蕙“画家”身份的定位,以及随之而来对李、顾绘画众口一词的颂美,才使得作为“诗人”的归懋仪以七首诗作与作为画家的师妹们进行一种文化身份的宣示。对归懋仪而言,这一反常的唱和举止既可以理解成她对诗人身份的执着与坚守,也暗示着她对乾嘉以来愈演愈炽的“艺文”潮流的本能抵制。
如果说“娑罗花”雅集还有着某种才智竞赛的倾向,那么归懋仪在与潘奕隽的个别往来中,她对诗人本位的执着与坚守更为确实。在榕皋女弟子中,归懋仪与潘奕隽的笔砚往来时间最长,内容也最丰富。在他们前后长达十五年的诗歌唱和中可注意两点。一是潘奕隽自始至终对归懋仪的文学才华极为嘉许。由于欣赏归懋仪的才华,潘奕隽不但请其代为酬唱,甚至认为她可比李清照,可以说,归懋仪是榕皋女弟子中唯一能得到老师如此赞誉的闺秀。二是潘归唱和涉及书画内容极少,就是有潘奕隽题《兰皋觅句图》一诗,也还是在颂扬归懋仪的诗歌创作。而如归懋仪在与潘奕隽的唱和中亦有“至三松堂适王绮思夫人来,先生命即席赋诗为赠。仪素不习八法,先生偏誉以工书。诸夫人兼为磨墨抻纸,爰赋小诗二章以志愧”
这样的自白。从归懋仪在《唐女郎鱼玄机诗》后题词来看,归氏绝非不谙八法之人,之所以自云“素不习八法”乃在表明,书画在归氏世界中只是诗之余事耳,诗才是她生命活动的重心,诗艺的讲究与创作才是她作为诗人本位最重要的实践之道。相较于归懋仪执着于诗艺,一味涵濡发扬其诗人定位,顾蕙、吴规臣、陈筠湘、李慧生等人无一不是以画家的形象出现在潘奕隽的诗文之中。蒋宝龄曾评价顾蕙:
幼禀庭训,善写生神,明矩矱,下笔便工。畹芳既工花鸟,自归叔美,益临摹古迹,兼长山水,二十年来粉墨远播,凡钜公名卿以逮山野之士,靡不知重畹芳画者。榕皋农部髦年爱才,见之尤加击赏,题其《红豆书楼图》云:咏絮才名属谢家,湘帘斐几擅清华。
何须更说相思子,此是西天称意花。不难看出潘奕隽对顾蕙“尤加击赏”的乃是她翰墨远扬的画才。李慧生为娑罗花写影后,潘奕隽首先赠诗“凭将湘管试兜罗,落墨徐熙不汝过”.老师对学生绘画才能的推赏之意,溢于言表。又如潘奕隽与陈筠湘的个人交往,则是以一首《题陈灵箫春风鬓影图》的题画诗而存于《三松堂集》里的。再如女弟子吴规臣,在诸多文献中都写着“榕皋画弟子”的画学师承。此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年岁远小于归懋仪的女弟子并非不通诗道,她们均有诗集存世,顾蕙有《酿花庵小草》,陈筠湘有《九华仙馆诗》,吴规臣有《晓仙楼诗》,陈秀生有《望云楼集》。那么,她们在与潘奕隽的往来中为什么会给人一种画家身份的定位呢?很显然,这是师生两者互动的结果。一是潘奕隽诗书画兼擅而具备综合艺文倾向,尤其是对画道热衷,他的这一倾向会很自然地影响到他的女弟子;再者,是这些诗画兼擅的女弟子在“艺文”的潮流中的自我身份认定,这其中以郭频伽对吴规臣“飞卿画花卉,风枝露叶,雅秀天然,然诗词皆娴,而不多见”的评说最为典型。在吴规臣等榕皋女弟子的“艺文”的世界里,虽诗词书画皆娴,但她们对绘画的热爱是要多于诗歌的,也就是说,她们更愿意以画家而不是以诗人的身份来示人,有了这样一种定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画家身份会成为她们之间的一种声气标榜,她们也正借此自立于江南的艺文天地中。
三、榕皋女弟子的文化史与文学史意义
潘奕隽与榕皋女弟子成为清道光年间吴中文坛上的特殊文化景观,潘奕隽所建立的女性文化团体以及提供给这些女弟子受教与活动的空间,加上他对女性才华的欣赏与包容,对于推动那个时代的女性艺文可以说是颇有贡献的。尽管榕皋女弟子的人员阵容、文化声名及其创作成就与随园女弟子、碧城女弟子相比都有所不及,但是,由于这一群体主要阵容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身份,更重要的是,她们在随园女弟子及碧城女弟子之间具有传接的作用,使得她们无论是在文化史还是在文学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考察意义。
从文化史视域来看,榕皋女弟子中诗人与画家文化身份之分别较为典型地体现出清代江南文化存在着由“文”向“艺文”的演变趋向。归懋仪的文学和集群活动是考察这一演变的参照。众所周知,归懋仪曾有过瓣香袁枚,列名随园女弟子的诗学经历。这一经历无疑对她的诗歌创作与诗人身份的自我认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师生间的唱和来看,她对袁枚诗学既有过“高山仰止久依依”的敬仰,又有过“床头自诵小仓诗,六千三百披来遍”的狂热追摹。而袁枚对这位诗名早着的女弟子亦有着“闺阁如卿世所无,枝枝笔架女珊瑚”的激赏与“将侬诗独争先和,领袖人间士大夫”的期许。
师徒二人在诗学上合证一心的夙契使得归懋仪深得袁枚诗学真传,尤其是袁枚以毕生心力集注于诗,以诗为其唯一文学文化事业的执着精神。所以说,“随园女弟子”这一称谓对归懋仪既是一种诗学身份,更是一种对诗的痴迷与执着的根性之证。袁枚身后,归懋仪带着袁枚诗学理想与成熟的诗学造诣拜在潘奕隽门下,在潘奕隽与归懋仪的师生关系中,作为诗书画兼擅且有着“艺文”倾向的老师对以坚守诗道为己任的学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潘奕隽之于归懋仪的师道,既然与传道、授业、解惑无关,那么绝大多数只是对归懋仪的诗名揄扬与褒赏。由此推之,归懋仪对潘奕隽的师道的认可,虽不无潘奕隽大力提携而产生的感念所至,客观地看,恐怕还是有依赖潘奕隽的文化地位与资源来扩大其才名及交往空间的企盼。
所以说,归氏本质上尚不属于潘奕隽的“艺文”时代,她自始至终仍属于袁枚那个以诗为城、以诗为家的“文”的时代。相对来说,潘奕隽的诗书画兼擅及以画家面貌而群集出现的榕皋女弟子则是清中期“艺文”潮流高涨的力证。明清江南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股“艺文”潜流,对于文学艺术的深刻崇拜和不断潜于学、游于艺的实践则使得这一潮流渐显。其具体表现为他们对山水的眷慕、园林的钟情、市隐的向往、藏书的执着、古玩的雅好、金石的精鉴、书画的擅场、饮茶的讲究凡此种种,说明了清代江南文化渐显的“艺文”化禀性。
由于潘奕隽文化趣味甚广,以及个性上的包容性,所以归懋仪以特立独行的诗人形象与风格归于其门,潘氏持有开放的姿态。其实,归懋仪与画家身份的师妹们的分别既是榕皋女弟子内部组成的分别,一定程度上也是随园女弟子与榕皋女弟子的分别,更是袁枚与潘奕隽的分别。说到底,是“文”与“艺文”的分别。这一分别体现在江南文化史上,则是由“文”向“艺文”的演变历程。
榕皋女弟子的文学活动既体现出文化史上波澜绚丽的衍变历程,又在清代女性文学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传接作用。我们知道,在当下的清代女性文学论述中,女性群集相习、延师而拜的风气在随园女弟子与碧城女弟子之间有过一段“寂寞开无主”的空白期,难道这些风华倾人的才媛在袁枚之后只能在孤芳自赏中等待另外一个“广大教化主”陈文述的降临吗?当我们了解了榕皋女弟子的活动周期后,就会知道关于“空白期”的假设并不成立。
19世纪初,虽然袁枚(1716-1798)去世了,王文治(1730-1802)去世了,王昶(1725-1806)也去世了,但是,女性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停止,褒扬与奖掖女性文学才华的火种更没有熄灭,而是由像榕皋女弟子这样的女性文学群体保存下来。当我们仔细考察榕皋女弟子的人员构成时,更会明显地看到这种血脉传接的前后关系。
随园女弟子归懋仪、周澧兰转师潘奕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园女弟子与榕皋女弟子之间的血脉关联;而部分榕皋女弟子在潘奕隽身后又转师陈文述,进而成为碧城女弟子中的一员,特别是名列《碧城女弟子诗》的陈筠湘、吴规臣、陈秀生等人,则更说明榕皋女弟子与碧城女弟子的血脉关联。通过对榕皋女弟子所处时间段及其人员构成两方面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清中期以降,女性文学史上愈演愈炽的群集相习、延师而拜的风气在随园女弟子、榕皋女弟子与碧城女弟子之间生生不息地传接着,并由此构成了一幅前后相连的全景式女性文学版图。
在审视这一幅全景式女性文学版图时,我们发现,无论是作为随园弟子与榕皋弟子,还是碧城诗友,一直有作为诗人的归懋仪自在穿行的身影。那么,她在这一幅女性文学版图中究竟有什么独特意义?仅仅是一个“春风长遍随园草,留得琴川一瓣香”的随园的追随者与守护者,抑或是榕皋女弟子中踽踽独行的歌者或是“艺文”时代的逆流者吗?
要了解归懋仪的意义还是要回到她的诗中,回到那个记录了她清苦而憔悴的悲剧人生,给予她生存意义、安慰与尊严的诗学空间中去。翻开《绣馀草》诸集,扑面而来的是她欢喜、哀怨、叹息、恸哭的种种声音,是她紊乱、颤动、挣扎、疼痛的种种心绪。可以说,诗既是她的歌哭之寄,更是她的心灵掩体与精神家园。总而言之,归懋仪诗中所表达女性心灵的窈渺与丰富在榕皋女弟子与碧城女弟子中少有可匹者,她的诗学创作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化史上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并不能取代文学史上的深度与高度。
归懋仪的深度与高度不但有袁枚、潘奕隽与陈文述等人一贯的赞赏为证,就是在归懋仪贫病而终以后,潘奕隽长孙潘遵祈再次举行“娑罗花”雅集,苏州知府吴云在拜观《佛香酬唱集·初集》时还说:“册中常熟女史归懋仪和章最多,警句亦不少。中有‘尘世得来原觉少,灵山虽种亦无多’二语,奉去素纸,请兄书成楹帖。”很明显,即使是在“娑罗花”雅集曲终人散之后,归懋仪的吟咏之声依旧余音袅袅,绕梁不绝。作为一名诗人,其生命虽如泡影水花,但她的诗魂还是那样摇曳生姿,一直没有被人遗忘,这就是她的价值,而这一价值恰恰说明了江南这一“艺文天地”,本质上是诗性的,在“文”向“艺文”的演变历程中,无论你是何种文化身份,总是无法脱离“诗”的根蒂的。
【参考文献】
[1]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G]//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2]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M].光绪十年(1884)如皋冒氏刊本年刻本。
[3]潘景郑。着砚楼书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4]潘奕隽。三松堂文集[M].道光刻本。
[5]沈毂。画理斋诗稿[M].道光刻本。
[6]苏州潘氏辑。佛香酬唱集·初集[M].民国七年(1918)刻本。
[7]江标。黄荛圃先生年谱[M].光绪二十三年(1897)长沙使院刻本。
[8]鱼玄机。鱼玄机诗[M].建德周氏影印。民国印本。
[9]骆绮兰。听秋轩诗集[M].嘉庆刻本。
[10]潘曾莹。小鸥波馆文钞[M].光绪三年(1876)刻本。
[11]蒋宝龄。墨林今话[M].中华书局。民国十一年(1923)铅印本。
[12]陈文述。西泠闺咏[M].道光刻本。
[13]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M].光绪八年(1882)扫叶山房刻本。
[14]李濬之。清画家诗史[M].台湾:明文书局,1986.
[15]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钞[M].宣统元年(1908)南陵徐氏刻本。
[16]归懋仪。绣馀续草[.M].胡晓明。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17]
[17]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8]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9]陈文述。碧城仙馆女弟子诗选[M].道光二十二(1842)年听香阁刻本。
[20]吴云。两罍轩尺牍[G]//近代史料丛刊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