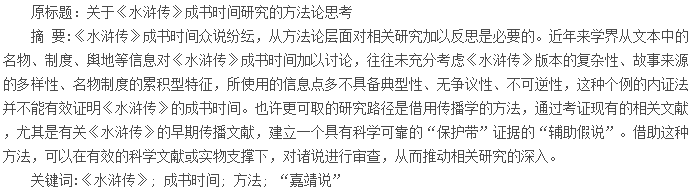
近百年来,对《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探讨一直是水浒研究的热点话题,亦是一大难题。自胡适、鲁迅建立《水浒传》研究的现代范式以来,学界对此主要有“元末说”、“元末明初说”、“明初说”、“成化弘治说”及“嘉靖说”等多种观点。其中,持“元末明初说”者最多,代表者有鲁迅、袁世硕、欧阳健、萧相恺、苗怀明等; “成化弘治说”的提倡者主要有李伟实等,持“嘉靖说”者有胡适、戴不凡、林庚、张国光等。近年来,石昌渝通过挖掘《水浒传》文本的名物信息以断《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王齐洲、王丽娟等则借用传播学理论以现存相关文献记载为基础,重提《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的观点,引发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近百年的《水浒传》研究进程中,由于《水浒传》版本情形、成书过程及作者研究的复杂性,导致研究过程中的分歧颇多。在现存资料匮乏的情况下,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主要突破口,除了对《水浒传》版本、作者及成书过程作尽可能细致的讨论,充分利用现有文献的信息价值外,更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对近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予以反思,全面总结研究过程中的得失,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 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所提出的某些理论或假说得到了事实的客观支持或反对; 科学研究的方法则是通过提供能够有效证明某种理论或假说的事实或文献的正面启发法,以建立保护其说的“硬核”证据链; 或者通过提出某种具有反面意义的“辅助假说”以建立使其“硬核”得到有效巩固的“保护带”证据。当某种“辅助假说”经过文献记载或经验式的事理推导的证明或证伪的严密论证后,其将从“辅助假说”上升为一种具有“硬核”证据的、业已证明的科学结论; 即使这些“辅助假说”最终被证明不可信,它们也是有价值的———排除了“辅助假说”的多种可能性,使得研究在事实的客观支持或反对中进一步靠向真理之一面。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可供讨论的、具有科学合理特性的研究平台内,否则科学研究的证明或证伪将任由研究者的主观阐释随意夸大。这种方法论对赞成或反对此说的研究者而言,都可以在有效的科学的文献证据的支撑下,对某种观点重新进行调整或替代。
这一思想对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讨论极富启发性,是本文展开方法论反思的理论指导。
在《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论争中,多数学者持成书于“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然而,“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并不能提供能够有效证明其论点的证据,既缺乏保护其说的“硬核”,也缺乏辅助其说、使其“硬核”得到有效巩固的“保护带”证据。换句话说,著录《水浒传》作者的早期文献,即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卷二五: “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能抗……罗贯中演为小说”; 高儒《百川书志》卷六: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 “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 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翻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七: “《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等等。这些记载缺乏有效连接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关键点,所言《水浒传》编者多是罗贯中,而罗则一说为“南宋时人”,或说为“元人武林施某”之“门人”,诸说相互矛盾。同时,在现存《水浒传》的明刊本中有三种题署,即二十五卷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辑”、万历袁无涯刊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容与堂本同) 、崇祯末年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合刊的《英雄谱》本题“东原罗贯中编辑”,亦多言为罗氏所编。有关罗氏的文献,1931 年郑振铎等赴天一阁访书时发现蓝格抄本《录鬼簿续编》中有关于他的记载,其有云: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所言罗氏为太原人,与田汝成、王圻等所言钱塘人有异; 其创作“乐府、隐语”及所作《风云会》、《蜚虎子》、《连环谏》等作品,并未提及《水浒传》,不能证明此罗氏与编撰《水浒传》者为同一人。至于《赵宝峰先生文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载罗本,《戴九龄集·书画舫宴集诗序》说他字彦直,并不字贯中。这反而证明历史上同姓名者大量存在,《录鬼簿续编》所载戏曲家罗贯中与写小说《水浒传》的罗贯中可能毫无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之关系及其编纂《水浒传》的情形,则是另外一种传说,现已无法有效追踪。另外,主张“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者不仅不能有效提供《水浒传》于元末明初的传抄本或刊刻本等实物,亦找不到记载《水浒传》于此时期成书或传抄、刊刻以及评论的任何文献记录,仅以明中后期的某种传说就确定《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在方法上是不科学的,何况这些传说还是相互矛盾的。至于说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等,不仅文献来源不明,且在格式、年号、传主履历、著述等方面都存在争议; 《施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施奉桥地券》等文献虽然可信,但文献中并未提供与施耐庵生平及其创作《水浒传》相关的任何材料;《施氏长门谱》( 即国贻堂《施氏家簿谱》) 施满家抄本中的“字耐庵”三字,是从旁边添加的,不仅名和字缺少关联,“元朝辛未科进士”的身份也是子虚乌有。更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未发现元末或元末明初文献中有关于施耐庵或《水浒传》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 同时,以《水浒传》的文本信息所作的论证,其信息点亦缺乏典型性与不可逆性。
也就是说,“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不仅缺乏有效支撑并保护此说的“硬核”文献,亦缺乏能够辅助此说的“保护带”文献。因而,持此观点的学者在面对其他学者的质疑时,所采取的反驳策略仅仅是: 以现今未发现相关的文献记载或版本实物,并不能否定《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或元末明初的可能,即有关文献可能暂没被发现,可能已经散佚。这种解题手法仅是提供一种不可被证明真伪的“可能”,而事实的存在情形却只有一种状态———是与否。“可能”不是“事实”,何况还有相反的“可能”;除非持此观点的学者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可被证伪的判断,否则在“可能”性上绕圈子,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论,这也不是“科学研究”的方法。科学的研究唯有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就“事实”而言,能有效支持“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的记载实在有限,直接相关的可靠文献和版本实物几乎没有,故持“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的证据链,应该说还没有建立起来。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采用新的方法研究《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不约而同地得出《水浒传》成书于“明代中叶”的结论。从方法论角度反思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推进这一研究的深入、促进中国通俗小说研究的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它能够启发我们对类似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提高研究水平。
这也是本文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原因。
二
虽说持“明代中叶说”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但这种研究的过程及结论可被科学证伪,仍是一种有助于接近事实真相的有意义的讨论。因为此说有《水浒传》的嘉靖刊本和文献记载为依据,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事实”证据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是能够被证伪的。即是说,只要有人发现了元末或元末明初《水浒传》实物或传播的任何第一手资料,成书于“明代中叶说”的结论就会被推翻。
不过,持“明代中叶说”者其论证过程、论证方法,亦有不少问题需要总结和反思。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张国光于 1980 年代所发表《〈水浒〉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等文极具启发意义。《祖本探考》主要从“小说地名有明代建制”、“没有反映宋元时期的民族矛盾”、“嘉靖前文献没有提到《水浒传》”、“《水浒传》受《三国演义》影响”等方面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十一二年左右。所采取的方法包括内证法、外证法,将事证与理证相结合,有文献学的考证,亦采用了传播学的方法。 这些方法是后来论证《水浒传》成书于“明代中叶”的学者所惯用的。如持“成化弘治说”的李伟实发表《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持“嘉靖说”的石昌渝的《明初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与〈水浒传〉成书》,王齐洲、王丽娟的《从〈菽园杂记〉、〈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看〈水浒传〉成书时间》,诸文所采取的方法即是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石昌渝的《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等文所采取的方法即是内证法的典型。王齐洲、王丽娟的《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等文则是对“嘉靖前文献没有提到《水浒传》”之细化与深入,属于事证与理证、内证与外证及文献学与传播学相结合的典型。
从方法论上看,内证法研究引起的争论最大。比如,石昌渝《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从朴刀杆棒、子母炮、土兵、白银使用等《水浒传》文本所记载的名物加以论证,虽是新采用的信息点,但是支持其说的“内核”证据并不牢靠; 其对朴刀进行解读后,认为“《水浒传》对朴刀的认识,较上引的元杂剧《争报恩三虎下山》和明初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有明显偏差,就这一点说,它的写作时间要晚于它们”、“腰刀产生在环刀之后,是明朝才有的兵器”,以此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朴刀流行的时代相去甚远”、“不在元代,甚至不在明初,而在靠近戚继光的时代”。 萧相恺、苗怀明等人就不同意石氏的论证,他们以宋《宝庆四明志·四明续志》、《景定建康志》所载辨明宋时腰刀使用的普遍化,又以今黑龙江金源博物馆所藏腰刀实物、元杂剧《冯玉兰夜月泣江舟》及《翠屏集》为例以证金代就已广泛使用腰刀,以为宋金使用腰刀的情形与《水浒传》所写并无本质之别,以驳石氏之谬。尤其是,支撑石氏之说最重要的核心证据,即子母炮的流传情形,遭到釜底抽薪式的剥离。石氏以为子母炮出现于正德末,是西方传入的“佛朗机”,以断《水浒传》不可能产生于嘉靖以前。但萧、苗二人指出,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三及《元明事类钞》等文献载有唐顺之语“佛朗机、子母炮、快枪、鸟嘴铳皆出于嘉靖间”或有误: 首先,唐顺之《武编》有“子母炮”条,未见“佛朗机”记载; 其次,据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四载“佛朗机夷人,差人送回广东听候”语、黄 《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 《名臣经济录》卷四十三) 载“臣前此曾将原获佛朗机铳四管”语,前者指葡萄牙国,后者指葡萄牙所造的武器; 又据林俊《见素集》“附录上”所载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公首仁讨贼,制佛朗机铳”,可知正德年间国人就已可仿造佛朗机,则唐顺之所言必有误; 再次,据戚继光《纪效新书》卷十五、《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四引茅元仪《武备志》、何良臣《陈纪》卷二、《筹海图编》卷十三等相关文献,可知“子母炮与佛朗机完全不同,它不过是一种相当简单的火器”。
上述文献将子母炮与佛朗机并列,表明二者显非一物。同时,二者在形制、制造方法、使用方法、功效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石氏从土兵、白银的使用判断《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亦引来不少研究者的反驳,如张培锋《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再质疑》、张宁《从货币信息看〈水浒传〉成书的两个阶段》等文就此有详细的分析。邵敏《明代通俗小说货币描写研究》曾指出明代的货币政策及民间实际流通的货币并非同步,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含有前朝货币信息的明通俗小说之货币描写情形与前朝的货币政策、当时的货币政策及民间实际流通的货币情形亦不同步,甚至相矛盾。⑨ 面对支撑“嘉靖说”的“硬核”文献遭到全面且证据确凿的质疑,石氏起初试图通过“答客难”的形式为自己做辩解,但这种辩解最终拘囿于对文本名物的不同解读,依旧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这里的最大问题在于,从文本的名物考察是否能够达到证明《水浒传》成书时间之目的?
近今据此视角所作的诸多研究都只是通过有限的个例进行论证。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任何建立在有限的实例的基础上的假说或理论,都是十分危险的。只要研究者发现与此相反或不支持此类假说或理论的文献证据,其论证必遭质疑。石氏最初对《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论证体系首先选用的是现存《水浒传》所有版本中均存在的文本信息点,但其所使用的诸多个例的不典型、有歧义及可逆性,导致以此建立的任何假说或理论都不牢靠。这也是从文本视域论证《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广受质疑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内证法的角度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必须注意证据的唯一性及论证的严密性。所使用的文本信息须首先注意采用什么样的版本为判断依据,其是否保留了较早的版本信息。所使用的文本信息必须是唯一性的、无歧义的、在各版本中均存在的。
同时,还须确定所使用的文本信息并非出自对先于研究对象的经过世代累积的故事或材料的加工。因而,尽管讨论者均使用百回本《水浒传》作为讨论的平台,但《水浒传》版本的复杂性、故事来源的多样性、名物制度及成书形式的世代累积性特征,这些因素导致单纯从文本信息进行成书时间的判断存在巨大风险。确切地说,《水浒传》对土兵、白银、腰刀等的描写或带有写定者个人的生活体验或经验,也可能是对以前传流的“小本水浒故事”的抄缀。除非此类名物信息具有鲜明的时间坐标信息或独一无二的特征( 且只能出现于某一特定的历史年代) ,否则对此类名物作不可被证伪的主观解释就可能贯穿于结论完全不同的相关研究中( 即是说这种阐释存在两种结论完全相反且概率相同的“可能”) ,何况这样的研究也只能确定名物出现时代的上限而不能确定其下限。因此,对《水浒传》的文本信息作经验式推导是不可取的。这与根植于文献记载的经验式推导,有本质之别。
研究者采用基于文本信息的内证法时,除了采用名物现象的考证外,亦有学者从地理职官制度方面加以解读。如周维衍撰《〈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从历史地理方面考证》一文,指出《水浒传》文本所称“江西信州”、“淮西临淮州”、“太原府指挥使司”、“济宁”等地理职官制度均是明洪武年间及以后的情况,其又以“高唐州”的描写为例,云: “书中在出现众多的明代政区的同时,偶有一二处宋代并不存在,明代也不曾见过,而只是元代才有的政区,这就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应在元亡后不久,作者对元代的政区地理观念尚未完全消失,因而习惯地用上了元代的名称”,从而确定《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初期( 周氏确定其说的另一证据则是施耐庵作《水浒》) 。这种解说就是未充分考虑《水浒传》版本、故事来源、名物制度及成书形式的世代累积性特征。因为若《水浒传》成书于明代中叶,则保留着元代或明初的地理政区职官制度等信息的其他文本,写定者完全有可能将其抄缀杂入文中。
《水浒传》在刊刻过程中所产生的文繁事简及文简事繁的两大系统,经过书贾尤其是明建阳书坊主的多次随意增删,致使文本信息点更加复杂,而许多信息点只能定作品成书上限而不能定其下限,故所做结论常不具有唯一性。冯保善《从白秀英说唱诸宫调谈〈水浒传〉成书的下限》、刘铭《从林冲的“折叠纸西川扇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王平《〈水浒传〉“灵官殿”小考———兼及〈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颜廷亮《两位英雄结局对〈水浒传〉成书时代的有限界定》等文均存在此类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此类讨论只是在论争一种“可能”( 正、反“可能”的概率相同) ,而非“事实”的确凿考证,即使结论成立也只能确定《水浒》成书的上限。
可见,单纯基于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名物制度描写之论证,是无法成为有效支撑“嘉靖说”或“元末说”、“元末明初说”的“硬核”证据的,因为内证讨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可逆性。故而,对这种论证方法的采用应保持相当的警惕,切记过分夸大此类证据的有效价值。研究者可以进行必要的研究,但它的使用须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相结合,不能只靠推论。
三
前文已述及单纯从现存《水浒传》文本信息来取得作品成书时代的确凿依据的内证法是不太可行的,“科学”的研究应避免这些研究方法的过分使用,以寻求新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从科学研究方法论层面所揭示的两种方法———反面启发法与正面启发法之研究思路的本质意义。
就《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考证而言,反面启发法就是启示研究者从文本信息加以研究的路子不仅不适合“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亦不适合“明代中叶说”。它与这两类观点的建构,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石昌渝与周维衍的研究就是个中典型。因而,不管是持“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者,抑或持“明代中叶说”者,基于《水浒传》文本信息的解读尚不能成为建构其说的“硬核”证据。即是说,能够有效推动《水浒传》成书时间探讨深入的证据链并不是基于文本信息而建的“硬核”证据,而是避开此类论证思路的一些“辅助假说”,以在围绕某种观点周围所形成的核心“保护带”。换句话说,持“元末说”或“元末明初说”者,抑或持“明代中叶说”者,均可通过这样的“保护带”来建构自身的理论。这种研究的科学性在于围绕“硬核”或“辅助假说”周围的“保护带”可以在文献记载或版本实物证据的检验中,不断进行调整、甚或被全部替代或否定。举个例子,持“明代中叶说”者通过《词谑》、《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菽园杂记》等文献记载,借用传播学理论方法,讨论《水浒传》在嘉靖年间的传播情形。这种视角的科学合理性在于: 所持的“嘉靖说”是一个可以被证伪的“辅助假说”,证明此“辅助假说”的一系列文献证据亦可被证伪,其论证过程是可被不断纠正的科学研究。因而,反对此说的学者若能够从现存或新发现的文献证据及事理逻辑层面驳倒“嘉靖说”,就可以增加保护自身观点的“保护带”; 相反,若反对者不能推倒“嘉靖说”的“辅助假说”,则事先作为一种“辅助假说”在经过自身的文献证据的建构后,将从“辅助假说”上升为一种具有“硬核”证据、业已证明的科学观点。
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讲,提出“辅助假说”的正面启发法可以通过被证明或证伪的过程以明确在某种研究的进程中,所可能存在的某些可被反驳的“变体”,以更好保护自身的“保护带”证据。比如,建构“嘉靖说”过程中所存在的“变体”则如万历二十年( 1592)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之类的文献,以示研究者确保其所建之学说在不违背现有文献记载的前提下得以有效确立。可见,从传世的文献记载探讨《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不仅具有相对科学可靠的证据链,而且可以通过论证逐步排除多种“辅助假说”的存在。
因此,检讨支撑“嘉靖说”的相关证据链是否可被证伪及其信息点的可靠程度,是十分必要的。
这方面的研究以王齐洲、王丽娟用力最勤。从传播学及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一部作品问世之后紧接着就是流传过程,是作品的传播和接受使其价值及意义得以体现。探讨作品的意义只有在其成书并流布、以及在流传过程中的影响范围内进行; 即使某作品已经成书却并未流传开来( 注意: 这是一个假说,并非“事实”证据) ,从中蠡测该作品的成书情形,所有讨论都将属于推论而无法被证实或被证伪,此类研究在拉卡托斯看来是“不科学”的。新作品成书和流传( 借阅、传抄、刻印等) 后,就有了信息传播或相关记录,存在被谈论或被引用等情况,这是作品被承认存在的前提。因而,以相关文献记载为基点,借用传播学的方法讨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是符合逻辑及学理规范的。当这些文献记载的相关信息———诸如记载这类文献的作品及其作者、记录的版本及记录的真伪、文献信息点的可靠度、文献记载所提到的人或事及与时代背景的关联性等方面———可被确定或大致确定时,就可据此为参照物以讨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比如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据李开先《词谑》所载“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 《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等语,云: 《词谑》系李开先( 1502—1568) 晚年之作,但李开先、陈束、王慎中、唐顺之、熊过在一起讨论《水浒传》的时间只可能在嘉靖八年( 1529) 至嘉靖十三年之间; 在这期间,李开先与崔铣只在嘉靖九年见过面; 此年李开先在户部任事,熊过、唐顺之、王慎中、陈束也都在京任职,他们聚在一起应是易事,李开先集子中也确有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记载,故李开先等人在一起讨论《水浒传》的确切时间应为嘉靖九年。
又如,王齐洲、王丽娟《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一文,通过对钱希言《戏瑕》所载“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等语的考察,以为: “犹及与闻”的“功父”即明末著名画家、藏书家钱谷之子钱允治,他与文征明等一起“听人说宋江”的时间不能早于其出生的嘉靖二十年,实际时间应该更晚,正值文征明的晚年,这时《水浒传》在社会上已得到广泛传播。② 再如,王丽娟、王齐洲《〈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以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例,通过对熊过生平、《墓表》撰写目的、材料来源、成文时间的考察分析,结合熊过与杨慎的交往以及他们与《水浒传》的关系,大致确定《墓表》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至隆庆元年( 1559—1567) 之间,熊过所言并非采自嘉靖之前的原始材料,而是其自己对刘七事件的理解或说明; 因此,这则材料并不能成为正德七年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证据,更非“铁证”。③ 王齐洲、王丽娟又通过对陆容《菽园杂记》与潘之恒《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的比较: 两书所记一脉相承,前者据《宣和遗事》设计“叶子戏”,而后者据《水浒传》; 陆容所记为《水浒传》成书前的情形,其人主要活动于成化至弘治初年,结合其生平、为人、交游及著述,尤其是其与文征明有交往: 《明史·文征明传》: “征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劘,名日益著。”文征明父辈如吴宽、李应祯等,都和陆容关系密切; 文征明同辈如祝允明、徐祯卿等,也和陆容之子陆伸相识友好( 陆伸请祝允明、徐祯卿为《式斋藏书目录》作序) 。更何况,文征明本人就和陆容相识交好。文征明曾撰《先友诗》,其序曰: “征明生晚且贱,弗获承事海内先达,然以先君之故,窃尝接识一二,比来相次沦谢,追思兴慨,各赋一诗,命曰先友,不敢自托于诸公也。”先友包括李应祯、陆容、庄超、吴宽、谢铎、沈周、王徽、吕常八人,其中陆容排在第二位。因父亲文林,文征明结识了陆容,且十分敬重他。在这样一个文人圈、文化圈里面,如果文征明成化间抄过《水浒传》,陆容又岂能不知道? 如果陆容知道,又如何解释《菽园杂记》关于“叶子戏”的记载? 从陆容与文林、吴宽、李应祯等的关系来看,从陆容与文征明的关系来看,文征明成化间抄录《水浒传》是不可能的,“成化间已有古本《水浒传》”也无可能。这也说明材料之间的相互联系,融会贯通十分重要,依据单则材料的记载来判断,很容易造成偏差。
由此得出明弘治初年以前《水浒传》并未成书的结论。通过王齐洲、王丽娟的考证,李开先《词谑》、熊过《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陆容《菽园杂记》、潘之恒《叶子谱》、张丑《清河书画舫》及《真迹日录》、钱希言《戏瑕》等文献的可靠性和其内涵可被确定。如果说据其中的某条证据导出的结论还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词谑》、《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菽园杂记》等一系列史料文献所组成的证据链均导向《水浒传》传播始于明代中叶之一面,从这些确凿的事实归纳得出的结论,足以震撼学界。可见,同样是经验式的事理推导,根植于文献记载的推导要比据《水浒传》文本信息所作的推导来得可靠。至少前者的推导可以通过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来不断进行修正: 若未有与此结论相反的文献记载,那么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层面讲,此类观点应该成为一种被认可的、可资引用的研究结论。甚至,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大概可确知《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是从当时社会上层开始的,经历由上至下的传播历程。周弘祖《古今书刻》录有《水浒传》“都察院”本、“武定侯”郭勋曾于嘉靖十六年仿《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并家刻《水浒传》等资料,可作佐证。通过王齐洲等人的考证,上述文献均是可靠的,其所记载的信息点亦可被证伪,故以这些文献记载作为“辅助假说”之“保护带”证据而建构的《水浒传》成书的“嘉靖说”,其论证过程具备严密性,结论亦相对可信。
从这种外在证据法的视角看,若是相关研究可信,“嘉靖说”将从辅助假说上升为一种具有“硬核”证据的、业已证明的科学结论。
不过,既然有学者鄙薄相关研究只能从“今传其他文献中寻求所谓的大致旁证”,那么如何在相关文献记载之外证法的科学性得到有效论证的情况下,将其与基于《水浒传》文本名物描写之内证视角相结合,以进行更为客观的科学研究? 对此,石昌渝、王齐洲等人的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石氏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的早期,主要是基于文本名物信息的解读,当面对诘难而选择的解题手法又不能说服反对者时,其对持说的论证则转向将相关的文献记载与基于文本信息的解读相结合的内外互证法,试图重建保护其说的“保护带”证据。以《明初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与〈水浒传〉成书》为典型,此文根据朱有燉所存世的两种“偷儿传奇”所提到的“水浒”人物名单与《水浒传》有别,加以比较: 两种“偷儿传奇”的两位主角鲁智深和李逵: “无论出身经历,还是气质性格,都与《水浒传》的鲁智深、李逵大相径庭,差距不能以道里计”,由此石氏认为朱氏创作的材料依据“只能是《宣和遗事》、元杂剧和元末明初的宋江一伙传说,其人物故事比《水浒传》要原始粗糙得多”。石氏又分析作为藩王的朱氏爱好诗文书画戏曲,与钱塘瞿祐和江西李昌祺等小说家有交游,因而若是朱氏见到过《水浒传》,则其创作应以后者为参考。同时,石氏采用换位思考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也是在前人所提供的资料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水浒传》吸纳了朱有燉“偷儿传奇”之“仗义疏财”模式,以证明《水浒传》成书是在朱有燉创作二种“偷儿传奇”的宣德八年( 1433) 之后。 石氏虽在讨论过程中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仗义疏财”模式的借用。从小说母题的角度看,“仗义疏财”模式大量存在于表现英雄气节的侠义公案类的说唱文学及通俗小说中,并形成一套已为大家所认可的情节模式或套路,故认为《水浒传》的“仗义疏财”模式吸纳了朱有燉的“偷儿传奇”,还缺乏有效链接二者的关键点。同时,从创作与阅读之关系的角度看,既然《水浒传》所写故事主要是流传于民间经久不衰的题材,那么就很难清晰地确定作品所写话题所曾参考或抄录过某某具体作品; 从读者阅读的角度看,某种具有母题性质的题材在不同的文学体裁或若干具体作品中,读者既可以阅读到其中的相同性,亦会有不同的审美差异体验。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所写是流传于民间的典型题材,朱氏进行创作时加入与自己学识、才情及时代背景相匹配的成分,则作品的相关描写与《水浒传》并不相同是合理存在的,亦会与元杂剧所写同类题材之剧作有别。石文所论虽结论欠妥,但其研究思路仍应值得肯定。相比而言,王齐洲、王丽娟《从〈菽园杂记〉、〈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看〈水浒传〉成书时间》一文的讨论,其证据的典型性、论证的逻辑性及结论的可靠性,似更有说服力。但是,李伟实先生从传播学角度,通过对陆容《菽园杂记》和杜堇《水浒人物全图》等材料的分析,提出“成化弘治说”,与王齐洲、王丽娟等结论有别。李氏《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一文以《菽园杂记》为例证,认为“成化年间流行的水浒叶子依据《宣和遗事》绘画梁山英雄图像,断定当时《水浒传》小说尚未产生”,并以明末陈洪绶“水浒叶子”、清人笔记所载当时流行的水浒叶子等为反例,以“水浒叶子的图像依据小说《水浒传》而不依据《宣和遗事》”进一步证明其论断正确可靠。
此文最大问题在于《菽园杂记》所载为昆山地区的水浒叶子,而陈洪绶及清人笔记所载当时流行的水浒叶子等并非昆山地区的,导致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和说服力。王齐洲等将同属昆山地区的陆容《菽园杂记》与潘之恒《叶子谱》所载相比较,其方法要比李氏来得科学,结论亦较为可靠。李氏又据杜堇《水浒人物全图》,认为其有天罡地煞当为《水浒传》流传之后,“杜堇着手绘画《水浒人物全图》,至多不过正德六、七年”,以断“《水浒传》产生于明弘治初到正德初这二十年间”。 但据相关研究,杜堇绘画及其他活动早在天顺八年( 1464) ,晚至正德七年( 1512) ,主要集中于成化、弘治时期。杜堇大约生于正统九年( 1444) 前后,卒于正德末年( 1521) 前后。杜堇若画 108 人的《水浒全图》,也应是《水浒传》流传较广时才会发生的事情,而迄今为止并未发现嘉靖以前《水浒传》流传的文献资料。从李开先、郎瑛等与杜堇的交游情形及现存文献看,均未提及杜堇曾作《水浒全图》; 最早提及杜堇作《水浒全图》者为晚清刘晚荣,刘氏并未交待此图收藏之来龙去脉,疑点重重。据此,杜堇是否绘《水浒人物全图》尚须存疑,现存《水浒人物全图》极可能是伪作的,故以此作为讨论《水浒传》成书时间及传播情形的文献材料,并不可行。可见,采用传播学研究法必须对有关传播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辨伪,才能有效使用这些资料。以有关传播资料论证《水浒传》成书时间虽说其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但这种研究方法是可被证伪的、所使用的文献亦可加以反复讨论,故而此种研究方法是“科学”的,虽然“科学”并不必然“正确”。
要之,近年来学界从文本中的名物制度舆地等信息对《水浒传》成书时间加以讨论,往往未充分考虑《水浒传》版本的复杂性、故事来源的多样性、名物制度的累积型特征,所使用的信息点多不具备典型、无争议、不可逆性,这种个例的内证法并不能有效证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以现存记载《水浒传》早期传播的文献为依据,将内证与外证、事证与理证相结合,综合考察相关文献及文献记录者的行状、交游等背景,借用传播学的方法,以形成一个合理的、科学的且为学界所认可的讨论平台,从而提出具有“硬核”证据的观点或具有“保护带”证据的“辅助假说”。借助这种方法,可以在有效的科学的文献或实物支撑下,对诸说进行审查,从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就学界目前的研究情形看,通过《水浒传》文本中的名物、制度、舆地等信息点以考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做法,难以有效建立其立论之“硬核”证据,虽然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和实际帮助的。借用传播学的方法,通过考证现有的相关文献,尤其是有关《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文献,建立一个诸如成书于“嘉靖说”等具有科学可靠的“保护带”证据的“辅助假说”,这种研究对于确定《水浒传》成书时间可能更有价值。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
中国尺牍文学源远流长。关于尺牍的起源,最早的说法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所称的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后来,姚鼐在《古文类辞纂序目》又称: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当时尺牍都只是作为国与国之间...
吴武陵,字不详,中唐元和时人,以名儒、文章、史学、气节着称,韩柳皆与之游。其集今佚,存诗文数篇。《旧唐书》卷一七三、《新唐书》卷二○三有传(以下简称《旧传》、《新传》),然多有脱误,其生平事迹迄今学界极少有关注者。兹钩稽史乘、方志、金石、文集...
诗坛誉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着名诗人、西域人辛文房,又是位卓越的文艺评论家,他以非凡的气魄,历经多年的广搜博彩、排比考订,于元成宗大德甲辰写出唐才子传。从隋大业初年至五代末年约三百五十年间浩瀚诗海中,精选出出类拔萃者二百七十八人,为之立传,附...
秦观(1049-1100),张文潜说他: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祭秦少游文》)可以说,秦观的一生充满了磕磕绊绊。而由于他诗词创作总体数量与个体性格的原因,秦观咏茶诗的数量非常少,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学人们的忽视。可以说:研究秦观,不能只研究其词...
对于《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期的判断,以古诗产生于桓灵时代的观点最为集中,梁启超、罗根泽、袁行霈、李炳海均持这一观点,而木斋先生的著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经过详尽考证,明确地将《古诗十九首》归入建安时期作品,并进而提出其为曹植甄后作...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涌现了大批学者、研究组织和研究机构,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也形成一定的研究理路与方法,有些是实证性的研究,如注释、校勘、考据等,有些是赏析性研究,如论评、诗文品评、批点、杂论等。近年来,随着文...
谣谚作为一种考察社会风俗的重要载体,早为人们所重视,在《尚书》、《左传》、《论语》等先秦典籍中,就记录了相当数量的谣谚,这也为后世研究谣谚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后来的历代典籍中,谣谚的记载也从不缺乏。但是,这种零散分布的特点给人们全面认识和研...
《游侠列传》一篇于《史记》各传中超拔醒目,被称为太史公最有斟酌用意文字。本文特别拈出侠情一词以分析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游侠所赋予的情感及其意义向度。此处的侠情非为现代武侠小说中所谓的侠者的个人私情,而是指激越而又往复跌宕的情感样式...
据《新唐书》[1]载:高适,字达夫,沧州(今衡水景县)人.初仕封丘尉,历任左拾遗、监察御史、侍御史、谏议大夫、蜀彭二州刺史、西川节度使、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封渤海县侯.卒,赠礼部尚书,谥号忠.难怪《全唐诗》[2]编者评价道:开、宝以来,诗人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