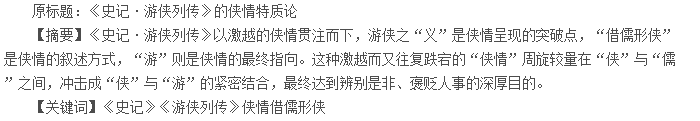
《游侠列传》一篇于《史记》各传中超拔醒目,被称为“太史公最有斟酌用意文字”。本文特别拈出“侠情”一词以分析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游侠所赋予的情感及其意义向度。此处的“侠情”非为现代武侠小说中所谓的侠者的个人私情,而是指激越而又往复跌宕的情感样式周旋较量在“侠”与“儒”之间,冲击成“侠”与“游”的紧密结合,最终达到太史公辨别是非、褒贬人事的深厚目的。
从侠情角度分析《游侠列传》,对于理解《史记》的游侠精神和中国侠文化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游侠之“义”———侠情呈现的突破点
《史记》不是帝王将相的功劳簿,而是由无数面形各异、身份地位迥然不同的人共同演绎而成的中华历史画卷。《史记·游侠列传》一开始就明确表达出游侠于以往历史记述中被缺漏的憾恨:“古布衣之下,靡得而闻已”,“儒墨皆排摒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不仅如此,游侠在现实语境中还遭到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因此,司马迁要为游侠“正名”。自韩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论出,“侠”似乎就被定了性———以武犯禁,与“暴豪之徒”的仗势欺人、倚强凌弱混为一谈,被认为仅有匹夫之勇。司马迁为正游侠之名便从儒家的根本二字“仁义”讲起,以“义”作为呈现侠情的突破点。
检阅《游侠列传》全篇,一个“义”字反复出现,前后共有9次。何为“义”?《论语·阳货》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认为君子小人皆有勇,唯有“义”是衡量他们是否作乱为盗的标准。孔孟儒学推崇仁义礼智信,将“义”放在与“仁”同等的地位,那种不屈服于强权的威逼,为弱小者、为贫穷者、为无助者作抗争的行为就是“义”,其内里也符合儒家所说的伟大的同情之心,即“仁爱”。与暴豪之徒的勇武相比,侠是感念他人不幸遭遇并给予行动上的扶持。朱家本身“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车句牛”,却愿意鼎力助人脱离困境,急人之难,赴士之厄,“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救人之后,功成而弗居,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另一位以任侠闻名的剧孟,其行为也“大类”朱家,死后竟然“家无余十金之财”。如此有情有义之“侠”怎能等同于比周的“朋党宗强”、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呢?正如《太史公自序》中谈到的作《游侠列传》的主旨:“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游侠列传》中的“义”此时可等同于原始儒家所讲的“仁义”,那就是对他人抱有的深刻同情,是在他人危难时施以救助的援手。“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伊尹、孔子等圣贤仁人尚且不能躲避,更何况才智平凡之人。再加上遭逢乱世,其悲惨境遇又待与何人去说?人生中的困境是即便圣人也会遇到的必然,能有于此时赴汤蹈火、解人于危难者就是侠。侠之“义”如同“己饥己溺”的儒家情怀,道出了司马迁对人遭逢现实困境时的那种热切期盼。《史记评林》引陈仁子曰:“游侠之名,盖起于后之世无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侠者,持也。
轻生高气,排难解纷,较诸古者道德之士,不动声色,消天下之大变者,相去固万万。而君子谅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为,虽未必尽合于义,然使当时而无斯人,则袖手于焚溺之冲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谓杀身成仁者也。迁之传此,其亦感于蚕室之祸乎?”
侠的出现给冰冷的现实送来了温暖,在一定程度上解脱了无所逃于天地间的苦难之痛切,拯救了天道不公时的人心倾颓,给世间带来了正义和公平的希望。可以说,侠情中的“义”负载着司马迁惨遭蚕室之祸、隐忍就辱时的低回悲叹,是司马迁对苦苦追索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现实回答。
《游侠列传》为“犯禁之侠”正名,侠情激荡,但司马迁笔下的游侠之“义”已然超越了儒家的“仁义”,其“义”的维度已被设置在一个更加雄浑壮观的历史长河中。在《游侠列传》开篇,司马迁就大胆地质疑甚至消解了儒家“仁义”观念所依靠的背景。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司马迁巧借“鄙人有言”和庄子之言大胆地挑战传统的道德价值判断。所谓“仁义”,在司马迁看来,是“久孤于世”的“咫尺之见”,含有窃国大盗就为侯、就存有仁义的虚假性。他所寻找的“义”是一种原本存蓄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最可宝贵的大无畏精神,“游侠”则是当日时下这种精神的承担者和践行者。司马迁通过《游侠列传》的书写达到以此冲破各种束缚、完成对民族心灵培育的目的。
二、借儒形侠———侠情的叙述方式
司马迁没有将“游侠”之“义”局限在儒家的定义框架之下,而是跳脱出来,采用了独特的呈现侠情的叙述方式———“借儒形侠”。的确,司马迁在书写《游侠列传》时,笔墨出入于儒和侠之间,并且在儒侠相提时常常“比权量力”,斟酌下语。列传伊始就引韩非子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以明儒、侠于其时都受到指斥;但在汉代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二者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学士多称于世云”,儒者可以通过缘饰儒术求取功名;而侠者却为儒家、墨家等排摈不载,地位卑下、声名不显。司马迁提出的恂恂儒者原宪、季次等,一方面具有令人肯定和同情的“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行为,另一方面也赢得了“死后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的身后名。两相对比,反衬出游侠生前修行砥名、死后却寂寞无闻的处境。“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此处司马迁毫不隐晦地表达出对游侠的偏爱,对儒、侠予以衡量的天平自然有了倾斜。南宋的刘辰翁认为:“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宪等,盖言其有何功业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说游侠之所为,有过之者而不见称,特其语厚而意深也。”
已然察觉到了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在《游侠列传》的儒家队伍中,不仅有拘学“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的自保者,更有“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者。后一类一旦与“布衣之徒”、“闾巷之侠”、“匹夫之侠”的专趋人之急、赴人厄困相逢、与侠者的不矜攻伐廉洁退让相比,则“不同日而论矣”。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写出这类儒者的虚伪丑态,但从最后导致郭解之死的公孙弘朝议便可看出司马迁对他们的不满。当“吏奏解无罪”时,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正是这番貌似堂皇的议论,导致郭解丧命及遭灭族的悲惨结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无疑是充当了庞大统治机器的维护者和发言人,其进言深合皇帝之意。郭解虽未直接杀人,但统治者认定他已经发展到借声名威望就能一呼百应、应者影从、甘愿献身的地步,这种强大而无形的民间力量已直接威胁到了专制集权政体对百姓的统治。“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柄,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在传统的史家眼中,匹夫小民般的游侠无论如何也不能握有生杀之权,一旦他们成长为立于皇权统治之旁的势力,成为可能威胁政权的存在时,则必定要除之而后快,只有“杀无赦”才能斩断这种逸出于政体之外的力量。
《游侠列传》对郭解人生经历和悲惨结局的大书特书正是“借儒形侠”的明显表现。《游侠列传》总共2400多字,真正开始进入人物传写的有1500多字,其中除去对朱家、田仲、剧孟等的片段式记述,对郭解的记叙就达1000多字。很明显,郭解是理解《游侠列传》的关键性人物。他“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少年时的郭解不是在儒家谦恭卑微、温文尔雅的礼教训导中成长的,对此司马迁也没有为尊者讳,如实叙写而已,但其背后藏有深意。长大后的郭解突然收心改性、重新为人了。箕踞者对他傲慢无礼,郭释之为“吾德之不修也,彼何罪”,而且为其免去“践更”,以德报怨;自己姐姐的儿子在与他人冲突时被杀,郭解竟没有像少时那样“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地快意恩仇,而是调查了解事情经过、明白是非曲直后承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并且“去其贼,罪其姊子”,主持公平与公正,大义灭亲。郭解居间调停洛阳两家相仇者,功成后却于深夜悄然离去,不使人知,不矜功自傲。郭解行为举止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郭解在他乡“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郭解种种行为几乎达到了“为人谋”要“忠”、“与朋友交”要“信”的儒家为人原则。即使郭解在被追杀的流亡途中,也是“所过辄告主人家”,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以上种种,如果放在儒家礼教范围内去要求一个“君子”、“贤人”,我们不会觉得诧异;但“忠”、“信”、“勇”、“义”、“直”却在一个从未接受过儒家思想规训的郭解身上得到了体现,这就不禁令人深思了。究其因,在于司马迁对郭解———“游侠”身份的价值确定上。班固曾不满地说司马迁是在“退处士而进奸雄”。司马迁的确在“进”和“退”,但“退”的是儒之不堪、或独善其身仅抱咫尺之义,“进”的是侠之高蹈、古直纯朴。儒之种种不堪表达的是司马迁对现实虚伪的反思,而侠之高蹈则是司马迁对激昂侠风的向往,推而广之就是对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游侠”品质的塑造。而这种精神也是渊源有自,我们可以回到“儒”、“侠”文化的分蘖处来看。
关于“侠”的来源,各家观点不太一致。有认为“侠”出于儒者。也有说“侠”发源于战国时期的墨家,如鲁迅言“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闻一多说“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还有如郭沫若认为的游侠源于商贾:所谓任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贾,商贾而唯利是图的便成为市侩奸猾,商贾而富有正义感的便成为任侠。
比较融通的看法是余英时的“侠”与“士”的谱系说: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而武士则又由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分化而来。漆雕氏之儒和“赴火蹈刃”的墨者都不过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之蜕化未纯者,因此和侠有几分表面上的相似。
余英时先生在此认为,春秋时期“士”的阶层进行着文武分化。有的“士”闲时耕田,忙时则参与作战,保留原有的习武身份,最终发展为具有尚武、尚勇行为特征的武士,如孔门弟子中非常英勇的子路。“侠”也就在“士”阶层文武分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具有最高的武士道德水准。同时,“士”阶层的文武分化所形成的另一支则专门从文,“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他们打破了贵族阶层垄断知识的局面,掌握知识,学习“王官之学”(礼乐文化),以恢复三代之学为己任,“儒”便是其中一类。“侠”和“儒”在后世的发展中也就逐渐成为具有不同文化特征和价值追求的两类人。
战国至汉,“侠”已成为令统治者不可小觑的力量。韩非子的《五蠹》曾说“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班固说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东汉荀悦则认为“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他们虽然承认游侠这类人冲州撞府、救人危难的节操品质,但更担心在各修其业的四民之外骈生出的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成为扰乱社会统治秩序的“德之贼”。
汉初高惠文帝之时,统治者对势力强大的游侠尚未采取强大的打击措施,多半因为刘邦本身就是提三尺剑、以布衣之身取得的天下,他所依靠的是一些游民、游士等身份的人:“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割有齐、楚,跨制淮、梁。”
这些人后来就成了为他出谋划策的智囊、斩将搴旗的武将。至汉景帝时,统治者任用郅都等一批酷吏,对豪侠开始了大规模的诛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馀皆股栗”。郭解的父亲也“以任侠,孝文时诛死”。
汉武帝朝任用酷吏充当耳目和爪牙。这些人应和上意,行见知故纵之法,致使大臣们噤声不敢言,人人惶恐自危。郭解之被杀正是武帝禁网严密的表现。同时,武帝听从主父偃的建议,迁徙富人豪强于茂陵,茂陵成为豪强的又一生长地。茂陵秦氏杀原涉季父,谷口豪杰又为原涉杀茂陵秦氏,“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游侠的活动延续到武帝时,基本上一直是沸腾不安的。
随着皇权的集中,禁网的严密,对游侠的管制和打击也逐渐强硬起来。
相较于侠一路而来的被管制、被打击,儒的发展历程就平顺得多。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礼教经孔子集成传至汉代已近千年,先前百家腾涌、活跃鲜明的思想环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统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叔孙通为汉高祖立朝仪,使原本“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群臣知晓了臣卑君尊的等级秩序,使布衣天子惊呼“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武帝重臣公孙弘从不敢面折廷争,丧失了先秦儒家“谏诤”的传统。汉代的儒家服务于大一统帝国,依附于皇权,失去了原有活泼独立的个体意识。而言行果断勇敢,赴人厄困不爱其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与专制集权之间形成了一种力量上的无形角逐。对这种矛盾的紧张较量状态司马迁不但没有进行纾解,反而以述作本身进行了颂赞,他肯定“侠”这类人的存在,凸显他们的个体价值,从而寄予自己的理想。《游侠列传》在黑夜如磐的天幕下,彷如一盏反抗专制、批判黑暗现实的明灯。
三、“游”———侠情的最终指向
《游侠列传》“侠情”之最终指向就是“游侠”中的“游”,表达了司马迁对游侠作为个体与天下大势发生矛盾冲突后的思考。
“游”字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架构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气息。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语,要求学生立志在道,根据在德,凭依于仁,能“游”于艺,即娴熟地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最终得到学习的自由和愉快。庄子“逍遥游”,讲的是个体精神冲破各种客观的限制,游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些“游”的思想源泉,都处在中华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构件都是生动活泼的。孔孟庄子时代他们很愿意“游”,很在乎“游”的状态。在专制的文化态势形成前,“游”有实践的空间。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游士在动荡中寻求活法,凭借口才之厉、驰骋辩辞、游说天下,此时的“侠”常接受有权有钱者的招致,周游各国,如孟尝君招六万多家任侠者,蓄养死士。至秦孝公时不喜欢人们游,他启用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连逃亡中的商鞅也被挡在“商君之法,无验者坐之”的规定之下。到了汉代,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严密的王朝出现了。在严酷的专制统治中,“游”俨然成为司马迁心头的一种理想。他期盼着严苛的政治体制中有一种力量出现,能在社会的夹缝和专制的刀光剑影中左冲右杀。《史记·索隐》对“游侠”这样解释:“游侠,谓轻死重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游,从也,行也。侠,挟也,持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
从游士到游侠,从游走于诸侯国到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独立生存,“游”的主体身份、行走方式都发生了转换,不再唯统治权势的马首是瞻。游侠阶层的存在,构造出不同于现行体制的另外一种社会格局。朱家、剧孟、郭解等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以个体的身份穿梭游走在底层社会,构成了一个非儒非墨非商、亦非主流非官方的一类人。在他们身上,种种品德令人叹赏,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赴人厄困、存亡死生、功成而弗居。他们的声名传播四方,在当时当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他们交游的人越来越多。
与高祖同时的朱家是鲁人,“鲁人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景帝时的剧孟住在洛阳,“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得一剧孟则“得一敌国”,其母亲去世时,从远方来送葬的人有千乘之多;郭解势力影响更大,那些敬仰他的里中少年可为他以躯报仇,为他效劳,还“不使知也”。这些游侠及其带动起来凝聚在他们周围的人已经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力量。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司马迁深知“游”之“侠”、“侠”之“游”,必定因为游离于现行社会秩序之外而遭到制度的压榨和摧残,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政体中,如何能允许他们的存在?《游侠列传》篇尾“吁戏,惜哉”四字上就凝结着对郭解的无限痛惜之情,因为“游侠”是司马迁被压抑着的理想及希望的闪耀。
“游”作为侠情的最终指向,其思想来源可以归结到司马迁的“平民”精神。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曾说:“司马迁虽因为儒家的教育之故,讲缙绅先生的趣味,讲雅,可是他骨子里的精神是平民的。”
唯具有“平民”精神的人才可以对皇帝尽嘲讽之能事,对惺惺作态的官僚行揶揄之言。
侠的精神之所以能在民间扎根,因为民间是其精神的沃土。一旦自由、正义受到了限制和戕害,侠的反抗精神就会委曲在民间大众的心灵上生存,他们所生活的空间就是“民间”,即后人常说的“江湖”。
民间秩序的维护不同于儒家礼教的文化秩序,二者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央专制集权的大背景下,“游侠”和“士人”成为两种文化秩序的代表,一个游离于传统的文化秩序之外,救人之难,不爱其躯;一个因依附王权而进退皆忧。《史记》中有好游侠的汲黯、有“为气任侠”的季布和栾布,他们都没有被写进《游侠列传》,就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统治阶层。所以司马迁的“游侠”的“游”不仅是陈仁子所说的“游者,行也”在地理空间上的游走,更包含了作为一种力量游离于儒家伦理秩序以外的意思。
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对游侠与刺客的情感趋向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就司马迁而言,既然将游侠与刺客分列二传,游侠与其所养之客不能是二而一的概念应该是清楚的。”
侠以暴易暴,行的是正义之举,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刺客主要是感知遇之恩。《刺客列传》中写了五个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除了荆轲刺秦王外,其他几人如曹沫劫持了齐桓公、专诸刺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等,主要纠结在个人恩怨上,在境界、眼光、气魄、产生的社会效应上与游侠都有不同。侠重的是正义,刺客是受人之恩,一诺千金。游侠与刺客在义的大小高下上有所区别,在用情上亦也不同。侠情有社会担当,带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理想追求;刺客亦有情,但更多的是感恩图报。游侠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体现的是崇高、伟岸、壮烈,有普适性、开放性;而刺客铤而走险、意气用事,将自己沦为他人实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其行为和后果取决于施动者的动机,成功与否不得而知,其情有偏狭性、封闭性、保守性。刺客是勇敢的,富有冒险精神。荆轲刺秦壮怀激烈,令百代后世都为荆轲掬同情之泪;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荆柯刺秦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为华夏民族不能再像战国时候那样混乱割据,数千年的文明需要在统一中求得发展,因而司马迁对荆轲等既怀深情又有节制和保留。
《游侠列传》是中国史书上的空谷绝响,后代史家没有再写出类似的游侠传了。虽然后有班固的《汉书·游侠传》,美其名曰“游侠”,但实际上已是游侠的变质———豪侠了,万章、楼户、陈遵、原涉等与司马迁所推崇的“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的游侠已不可同日而语,属于“向者朱家之羞”的“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豪侠之伦,是封建诸侯和地方豪强壮大自己所借助的一股力量。钱穆先生说:“太史公又写了《游侠列传》,为什么后来人不写了,这也因在后代社会上游侠不成为一个特殊力量,却不能怪史家不写。”
其实,在后代社会中,依然存在“游侠”,不过其精神本质与品格已经不为专制皇权下的正统史家所肯定了,但这种“特殊力量”并未隐匿消失,它顽强执着地扎根于民间社会,维护和追求着人间的公道。如《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们,他们与太史公笔下的游侠渐行渐远,一方面宣传“替天行道”,一方面又要“忠义双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最后只能在逼上梁山之后又走上被朝廷招安的道路,他们的悲剧结局正是民间游侠之气与儒家品格结合后的产物。而在后世文人笔下多出现的“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实际上是对“游侠”本身所具有的自由无畏精神的文学观照。
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最主要的着作形式,但它并不只限于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范围,好的诗话在此基础之上还反映出作者的文化意识、审美情趣和人格精神。王夫之的《姜斋诗话》正是如此耐人解读并令人青睐。它是一部着名的文学理论着作,是清代...
《红楼梦》是我国着名的经典章回体长篇小说.作品主要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基础突出描写了贾家荣,宁二府家族由旺盛而衰落的过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人物四百多,作者十分善于刻画人物,在作品中采用人物性格多种对照方式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
《五代史》和《五代史记》均未设《艺文志》或《经籍志》,清人补五代史《艺文(经籍)志》中,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以下简称顾《志》)搜罗广,刻本多,影响大,享负盛名.就小说类而言,顾《志》共着录小说63部,其数量居各种补五代志之首.不过,数量虽大,舛误也...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
结语张祜乐府诗是乐府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弥补了前人之于张祜乐府研究的不足。从张祜乐府诗文献留存情况谈起,继而论述张祜乐府诗的创作背景、张祜乐府诗之复与变、张祜乐府诗的文学特点。明晰张祜乐府诗在文学史、诗歌史和乐府诗史的意义和地位...
、《诗经》是中国文学少年时代的骄傲,文学自觉意识在此阶段已然显现。先民的生命意识逐步从混沌中走向清晰,因而,《诗经》作品中对生命存在的思索与追问日趋增多。这种生命自觉的意识首先源自当时生存环境的残酷现实,借作者身边熟悉的场景、物候而抒发,...
中国尺牍文学源远流长。关于尺牍的起源,最早的说法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所称的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后来,姚鼐在《古文类辞纂序目》又称: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当时尺牍都只是作为国与国之间...
唐代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文化措施,促使文学与艺术全面发展与繁荣。统一的唐朝有利于西域与中原的交流。西域歌舞传播流行,促成了唐十部乐①的形成,西域乐舞、乐器、乐师遍布朝野,备受唐人的喜爱,这不仅给唐文学注入新的内容,而且成为唐代艺术和...
管仲作为齐国历史上的名相,《史记管晏列传》给予其很高的评价: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
在学术界一直没有超越基于农业文化传统而产生的重实尚用观念,以及由此决定的传统文学批评的经世致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