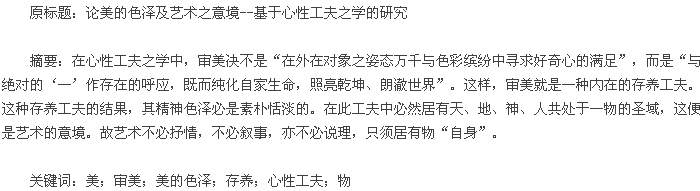
美是否有一定的色泽呢?这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一般的美学家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一般的美学家看来,美之所以为美,正乃在于色泽的多样与变化,一定的色泽总是令人审美疲劳而不美。但是这种所谓的鉴赏的审美只不过是在外在对象之姿态万千与色彩缤纷中寻求好奇心的满足,进而获得一时的激动与愉悦。这种一时的激动与愉悦不唯不能使精神得到教化与提撕,亦可能恰恰是人类狂欢乃至堕落的开始。柏拉图把艺术家及诗人排斥在理想国之外,康德把魅力刺激(色彩)排除在审美之外而标举素描,这都是对审美保持一种警惕态度。欲通过鉴赏这种美获得审美教育,不但不可能,可能还适得其反。如果要获得真正的审美教化,那么审美就决不是在外在对象之姿态万千与色彩缤纷中寻求好奇心的满足,而是与绝对的“一”作存在的呼应,既而纯化自家生命,照亮乾坤、朗澈世界。既如此,则美之色泽就不会是多样与变化的,因为直通大道的朗朗乾坤、明澈世界之圣域不是靠形式的多样与色彩的缤纷而为美,乃是依道而行而为美。如果吾人承认美学就是心性学,则美一定有个固定的色泽。那么,这种美当是什么色泽呢?这种色泽与心性修养有什么关系呢?
一、素朴恬淡与精神存养
《论语》有两条语录以表征孔子的生活。“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1](120)“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161)从生活自身来看是安和娴静的,但从其色泽来看,则一定是素朴恬淡温和的,决不显示色彩的华丽与缤纷。因此,从色泽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德行与生活。《论语》有下面三条记载:
子曰:“巧言令色, 鲜矣仁!”[1](70)(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1](31)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1](227)第一句说,一个在言语上巧佞、颜色华丽的人,决不是一个仁者。这意味着,一个决不在色泽上表现绚丽。第二句须与第三句合起来看,“动容貌”就是要“望之俨然”,“正颜色”就是要“即之也温”。“望之俨然”乃指“貌之庄”,“即之也温”乃指“色之和”,都与色泽相关,且这种色泽不是华丽浓郁的颜色,乃是指素朴恬淡的颜色。何以见得?《论语》尚有下面一条语录: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1](215)一个人内心柔弱空虚,于是只有外表上装出一派威严之容貌与浓郁之色泽,以掩饰其根基之缺失,这正是小人之所为。作为君子决不是这种色泽与容貌,故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129),“坦荡荡”是指和融舒泰、平淡自然,“长戚戚”是指患得患失,忧乐形于色。另外,《荀子》里有如下一条记载,尽管未必是历史事实,但一定表现了圣人的生活态度与色泽容仪:
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汝矣!
由!”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犹若也。子曰:“志之,吾语女。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2](532)孔子之所以批评子路“盛服裾裾”“颜色充盈”,乃因为这种容仪色泽在人与人之间无形间建立了一道屏障,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精神提撕与德性润泽,从而无法生成舒泰安乐的生活美境。子路听到乃师的批评以后,立即换了一套服装。“犹若”是指舒和平淡之色泽容仪。孔子见了以后,再次告诫子路,在能力上夸饰、在色泽上华丽的人,都是小人,吾人切不可如此。
因此,子思在《中庸》总结曰:《诗》曰:衣锦尚絧。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1](62)“锦”上面之所以要披一层淡雅的轻纱,乃是避免颜色太着,而这种色泽是根本违背君子之道的。君子之道在色泽上是“淡”“简”“温”,若在精神上表现出如此之色泽,就可以入德悟道了。“淡”“简”“温”
是人尽了性分之德后的容仪。刘劭《人物志》云:
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叡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3]
一个真正能纯化自家生命而尽性之德的人,该“勇强”“刚正”时一定“勇强”“刚正”,然在色泽上一定是简淡和融、自然娴静的。不唯孔子如是,有存养修持之贤达皆如是: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4]。明道先生坐如泥塑,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5](426)。
游定夫访龟山,龟山曰:“公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龟山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处来也。试涵泳“春风和气”之言,则仁义礼智之人,其发达于声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6]上面几条史料都说明了理学家存养修持后人之精神境界在色泽上的表现。大体来说,皆具平淡素朴之色,和乐安静之颜。这是存养后自然而至的结果,决非外在光景之虚映。朱子曾语陈同甫曰:
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窃恐此正是病根。[7]“沂水舞雩”是孔子与弟子游乐之故事,“躬耕陇亩”是诸葛亮闲居隆中耕读吟咏之故事,此皆精神修为之事,可刻意以外物装饰打点出来,以为“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即是此等气象,则非也。人间之生活美境正是通过存养,以这种色泽之遍润世间之结果。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1](447)“霸者之民”,喜怒哀乐形于色,“王者之民”,则淡然自处,不露神色于外。故王阳明以为这种生活图景是“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8]。也就是说,如果“王道”真正实现在人间了,在色泽上一定淡然素朴而无文采之景象,但这并非民生凋敝之惨淡,而是真正的人间美境之灵现。
这当如何理解?为了便于厘清个中之问题,我们暂且回到老子的一段话中来: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9](334)这里呈现出一派荒远、萧疏,甚至是贫瘠之景象,没有大都市物质的竞奢、车马之喧嚣、灯火之辉映、色彩之绚丽,但人们安居其间,“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10],这种素朴恬淡而有灵性之生活,远甚于在物质的丰饶中放纵、器物之便利中享乐与色彩之绚丽中沉醉。这是老子的“理想国”。
十八世纪的卢梭亦沉迷于这种“理想国”,他说:我们对风尚加以思考时,就不能不高兴地追怀太古时代纯朴的景象。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我们不断地向它回顾,并且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那时候,人们清白而有德,并愿意有神祗能够明鉴他们的行为,和他们一起都住在同一个茅屋里。
但历来人们对这种“理想国”诟病甚着,以为这是倒退的历史观、反科学与进步。如果我们只是从物质的丰饶、器物的便利与色彩的绚丽来看进步,那老子的理想诚然是反动的。但问题,进步就是意味着物质的丰饶、器物的便利与色彩的绚丽吗?这种进步观含有怎样的危险?它在怎样的意义上褫夺了人间真正美境的到来?这些问题解答清楚以后,我们便可知道,真正的美为何一定是素朴恬淡的。
尼采曾说:“一切伟大之物,总是远离了市场与荣誉才能发生;新价值之发明者总住在市场与荣誉很远的地方。”[12]
一切认为老子的上述思想乃反科学、反进步的人,一定是基于市场原则,以功利思维为主导。
海德格尔把这种功利思维称之为计算性思维,而与沉思之思相对,后者海德格尔以一个很诗意的词——“泰然任之”——表示之。二者的区别对于我们理解老子的话有何意义呢?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
二、泰然任之与素朴恬淡
我们要理解“泰然任之”的意义,先必须认知计算性思维的特征及其后果。对于计算性思维,海德格尔说:当我们进行规划、研究和建议一家工厂时,我们始终是在计算已给定的情况。为了特定的目标,出于精打细算,我们来考虑这些情况。我们预先就估算到一定的成果。这种计算是所有计划和研究思维的特征。
这种思维即使不用数来运行,不启用计算器和大型计算设备,也仍然是一种计算。计算性思维权衡利弊。
它权衡进一步的新的可能性,权衡前途更为远大而同时更为廉价的多种可能性。计算性思维唆使人不停地投机。[13](1233)居常以为,科学反映客观事物之真理,但科学亦不过是一种计算性思维,科学在原因-结果之间计算与预测。海德格尔说:
现代科学作为在观察意义上的理论是对现实之物的一种极端干预性的加工。……科学调节着现实之物。
它使现实之物自身在各种情况下各自展示为受作用物,即展示在被设定的原因所造成的各种可预测的结果之中的受作用物。现实之物在其对置性中被确定了。[13](965?966)说到底,科学所面对的现实之物乃是一种原因—结果之关系,科学就是要处理这种关系,尽管科学的处理相当成功与有效,但这依然是一种计算。故海德格尔说:“所有现实之物的理论所进行的追踪-确定的过程都是一种测算。”[12](976)在科学面前,现实之物确实是一种成功之物,其之所以“成功”乃是由一个原因“带来”的。所以,科学就是这样一副座架,不但把世界促逼于其中,人亦随之被促逼于其中。海德格尔说:
人类如此明确地处身于座架之促逼的后果中,以至于他没有把座架当作一种要求来觉知,以至于他忽视了作为被要求者的自己,从而也不去理会他何以从其本质而来在一种呼声领域中绽出地生存,因为决不可能仅仅与自身照面。[13](945)在科学的促逼之下,人不再安居在自身之中,亦成为了一种成功的“关系”。比如,护林为纤维素所订造,纤维素为纸张所订造,纸张为报纸或画刊所订造,报纸则为公众意见所订造。同样,空气为氮料所订造,土地为矿产所订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海德格尔进一步说:每个钟点,每一天里,他们都为广播电视所迷住。
每周里,电影都把他们带到陌生的,通常只是习以为常的想象区域,那里伪装出一个世界,此世界其实不是世界。到处唾手可得“画报”。现代技术的通讯工具时刻挑动着人,搅扰和折腾人。[13](1235)就这样,人的根基便在物质的丰饶、器物的便利与色彩的绚丽中被连根拔起。就连耕作也成为了摆置着自然的订造。而原先,“耕作”——海德格尔说——意味着:“关心与照料。农民的所作所为并非促逼耕地。
在播种时,它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且守护着种子的发育。”[13](933)这就是“泰然任之”。如果人类要找回自己的根基,不再在技术的促逼中漂浮,那么,唯有在“泰然任之”中安居于世界。海德格尔曾借用约翰·彼德·海贝尔之言曰:“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13](1241)吾人应像植物那样,安居在故乡,守护着大地。
应该说,在老子的时代,科学并不发达,海德格尔所见之情形在老子那里并未出现,但人类以欲望之心、享乐之能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依此方向而走,以老子的智慧必然有所预见,故他写下了“小国寡民”那段话,其精神主旨为二千年之后的海德格尔所默契,这并不是一种过度诠释,因为这不是文字训诂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精神问题,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1](361)。老子之所以呼唤什伯之器不用,安居乐俗,就是让人回到“泰然任之”之中,在这里,天、地、神、人共处一域,而科学之计算性思维则以人之欲望宰制天地万物,从而驱赶了神灵。吾人以为老子之所说是一种美,且是一种大美,即是就“天、地、神、人共处一域”言。这是真正的至德之世。庄子亦曰: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14](334)这种美乃依“见素抱朴,少思寡欲”[9]134之工夫而来,其色泽必是素朴恬淡的,其境界必是空灵幽静的,而且真正的大美必如此。这种人间大美,在工业化社会之前的农耕社会是常有的,辛稼轩在他的笔下就曾向吾人展示过: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15]
这种安居乡里,逍遥于天地间之素朴恬淡之美,被科学所带来的物质之富丽、财富的堆积所破坏。那么,华丽浓郁之色泽何以一定不美呢?这不是一个外物的表象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提撕与砥砺问题。因为华丽浓郁的色泽常“重”且“深”,给人以压迫感,使人止步退却,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得精神的提撕与砥砺成为不可能。因此,华丽浓郁之色泽一定与“德”之作用是相左的。
三、心性学与素朴恬淡
《中庸》结句曰:《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人在色泽上表现华丽浓郁,那么,他的生命一定是“重”而“浊”的,并未纯化。
同时,在声色上显示华丽浓郁,以其“重”且“深”御民,不但是有违德性原则,亦是有悖于天道的,因为天道是“无声无臭”的。天道是最高的原则,亦是素朴恬淡之美的原则。
庄子在其着作中多次提到天道之色泽: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14](538)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14](457)素朴恬淡不但是天道的色泽,而且更是万物的本色,故庄子又曰:“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14](457)管子亦曰:“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15](814)既然天地万物之色泽皆以素朴恬淡为本,那么,人当然要就天地万物而任之。
管子曰:
君子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自用则不虚,不虚则仵于物矣。变化则为生,为生则乱矣。[15](776)人于天地间只须“感”与“缘”,即因物而任之,违此而“自用”、而“变化”,皆为逆大道、仵万物。
科学就都是“自用”“变化”。庄子亦曰:
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14](546)从管子与庄子的论述中可知,只要人于天地之间泰然任之,则其生活色泽亦必是素朴恬淡的,如此,才是“真人”,才能够“不亏其神”。但人之所以追求如此之色泽,并非是一种主观爱好,乃是依天道而行。
前面说过,人自身有一个与天道相契合与呼应的内在根基。这个根基若充盈笃实,则不但“不亏其神”而成为“真人”,且其色泽必定素朴恬淡。因为这个根基自身之色泽亦是素朴恬淡的。故明儒聂双江曰:“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养于己者也。”[17](381)这个根基,这个本性所固有而可豫养者,就是孟子所说的“四端之心”,如果存养修持工夫到家,则心必呈现素朴之色泽。
中国传统儒者都有切实之证会,如:
存诸心者,素矣[18]。所以澡雪其心者,素也[19]。
“四端之心”虽是一个质实的“大体”,但它却不可能被外“观”,而只可能被内在地直觉之,因心之大能而直觉之。因而,吾人对于“四端之心”的直觉常不是其色泽之素朴恬淡,而是其大能之虚灵明觉,因后者更易于被直觉故。所以,中国文化传统多从虚灵明觉处论心之大能: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9](67)。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4](147)。
不见不闻只是虚。虚者,心之本;实者,心之质可见者也。心也者,虚而实,君子之道,费而隐。[17](1268)以上所云之“虚”皆从心之本与心之能立论,但心之虚亦来自天道,“唯道集虚”即是明示,张横渠亦论曰:“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20]
这便说明了作为本体的心一定是虚灵的,且这虚灵来自天道。只要存养修持工夫笃实,这虚灵之本心是一定可直觉到的。明儒湛甘泉曰:
吾常观吾心于无物之先矣。洞然而虚,昭然而灵。
虚者,心之所以生也;灵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观吾心于有物之后矣。窒然而塞,愦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虚焉灵焉,非由外来也,其本体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内往也,欲蔽之也。其本体固在也,一朝而觉焉,蔽者彻虚而灵者见矣。[17](876)这一段话有本体,通过工夫进而说到心之大能。
心之本体固“虚”,但若工夫不笃实,则亦不能生“灵”之大能,进而其“虚”之本体似亦闭塞而不可见。所以,宋明儒多从工夫处见本体,特别是阳明以后,儒者雅好良知之学,良知固然是本体,但更是工夫。从良知论心,更显其虚灵明觉之本体及其大能。阳明后学多有所论:
盖天性之真,明觉自然,随感而通,自有条理,是以谓之良知,亦谓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条理;良知者,天理之灵明。[17](361)性之灵明曰良知。良知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酢万变。[17](721)良知之教乃从天命之性,指其精神灵觉而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无往而非良知之运用。[17](334)良知,不是以科学之知去建构乃至宰制自然,乃是尽吾人虚灵明觉之本体让万物回到天、地、人、神共处一域的大美中。这种大美,就其色泽言,则素朴恬淡;就其境界言,则空灵静默。一源而发,不但源于天道之本,亦发于人性之根。
前文说过,美是与绝对的“一”作存在的呼应,既而纯化自家生命,照亮乾坤、朗澈世界,吾人若能以自家生命固有之“四端之心”或良知之能照亮乾坤、朗澈世界,既而倾之笔端,泻诸纸上,即是艺术。这样,真正的艺术亦应呈现素朴恬淡之色泽,空灵静默之境界。中国传统的艺术,特别是诗歌与山水画多能呈现此种色泽与境界,即是这种精神在艺术中的落实:
“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杜甫:《野望》) “雪意未成云着地,秋声不断雁连天。”(钱唯演:《奉使途中》)应该说,以上诗句所表现出的素朴恬淡之色泽,空灵玄远之境界,并非诗人主观的艺术爱好,而是诗人尽心、知性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尽自家之本心即是尽天地之心。明儒张阳和曰:
人之生,以天地之心为心,虚而灵,寂而照,常应而常静。谓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谓其无物也而万物皆备。无物、无我、无古今、无内外、无始终。谓之无生而实生,谓之有生而实未尝生。浑然廓然,凝然炯然。[17](826)从这个意义上看,上述诗句并非一种纯粹的写景,而是一个仁者存养尽性后的必然境界。这个境界既是大仁(善),复是大美,亦是大真,因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物才回到自身之中,“真”得以实现。这个“真”不是科学之“真”,而是万物尽得其性的“真”。《二程遗书》卷三载: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5](60)所谓“与自家意义一般”就是在本心之大能中朗澈天地万物,所谓“民胞物与”也。这正与《中庸》之意合。《中庸》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52)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尽物之性”呢?“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到底是何意?中国传统的儒者多在心性工夫中证会,而不费言辞以说之。然不说之,今人多在科学之思维模式下,以生物学之性或物理学之性为“物之性”,则此段话之大义必淹没。这里不妨以海德格尔的理论申述之,以明其大义。
科学的进步可以把物的生理特征或物理性质研究得透彻明晰、曲尽玄微,由此,人们便以为把物带到了近前。但是,无论是把物理解为特性的载体,感觉多样性的统一,还是具有形式的质料,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从对象性来理解物之物性。但海德格尔认为,“从对象和自立的对象性出发,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物之物性因素。”[13](168)海德格尔以壶为例来说明物之物性因素。什么是壶之物性因素呢?答曰:具有容纳作用的器皿。这个器皿是由壶壁与壶底组成的,但壶壁与壶底并没有容纳作用,其容纳作用的是壶壁与壶底所围成的虚空。如果起容纳作用的是虚空,那么,陶匠就并没有真正地制作这个壶,因为他只是“为这种虚空,在虚空之中并且从虚空而来,他把陶土塑造成形体”[13](169)。因此,壶的物性因素并不是构成壶的材料,而是起容纳作用的虚空。一旦吾人把物性因素引证到虚空那里,“我们便让自己为一种半诗性的考察方式所迷惑了”[13](170)。这种“半诗性的考察方式”不再把物作为一种对象性的站出者,而是要求“物向思想显现出来”[13](171)。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壶之虚空容纳液体并倾而出之。正是“在倾注的馈赠中,这个器皿的容纳作用才得以成其本质”[13](1172)。至此,壶之物性才真正绽开来。海德格尔说:
在赠品之水中有泉。在泉中有岩石,在岩石中有大地的浑然蛰伏。这大地又承受着天空的雨露。在泉水中,天空与大地联姻。在酒中也有这种联姻。酒由葡萄的果实酿成。果实由大地的滋养与天空的阳光所玉成。在水之赠品中,在酒之赠品中,总是栖留着天空与大地。但是,倾注之赠品乃是壶之壶性。故在壶之本质中,总是栖留着天空与大地。[13](1172?1173)海德格尔的这段话颇具诗意,意味着一个“物”带给吾人一个世界。这有类于《礼记》中的一段话:
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21]“风雨霜露”“庶物露生”所教给吾人的决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一个别样的世界。《华严经》则把这个世界明白显露出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不要以为一花一叶就只是一个对象,它们让一个神性的世界威临,而这个世界才是吾人真正面对并归属于它的东西。海德格尔说:
世界决不是立身于我们面前能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对象。只要诞生与死亡、祝福与亵渎不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始终归属于它。[13](265)世界总是有诸神威临的世界,因此,倾注是奉献给不朽诸神的祭酒,祭酒是真正的赠品,在其中,倾注的壶才作为馈赠的赠品而成其本质。相反,如果倾注的这种本质一旦萎顿,壶就可能变为单纯的斟入与斟出,直到最后在酒馆的沉醉迷狂中腐烂掉。就壶之物性,海德格尔最后说:
在倾注之赠品中,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这四方是共属一体的,本就是统一的。
它们先于一切在场者而出现,已经被卷入一个唯一的四重整体中了。[13](1173)这四重整体乃是一纯一的澄明之境,这是物作为物而存在的在先境域。海德格尔说:
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一种澄明在焉。从存在者方面来思考,此种澄明比存在者更具存在者特性。因此,这个敞开的中心并非存在者包围着,不如说,这个光亮中心本身就像我们所不认识的无一样,围绕一切存在者而运行。[13](273)物只要站进或出离这种澄明之际,才作为存在者而存在,这样的一个存在者,乃是真正“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存在者。反之,如果物逸出这个澄明之境而以纯粹的对象性自立,那就是“刍狗”万物,物即不成其为物。海德格尔之论,决非孤明独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已有之,《中庸》所说的“尽物之性”
就表述者就是海德格尔所欲论者。明儒王龙溪的“四无教”更为显豁地表达了海德格尔的意思:
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22]
这里的“心”“意”“知”皆不是科学知识意义上的“心”“意”“知”,所以,“物”也不是科学知识意义上的“物”,这样的“物”决非一个对象性的自立体,而是澄明的“虚灵”,故谓之“无物之物”,它召唤天、地、神、人灵现共聚。所以,海德格尔认为,物是“那种使纯一的四重整体入于一种逗留的有所馈赠的纯粹聚集”[13](1174)。这是真正的物,这是物自身,它是一抹澄明的虚灵或境界,这不是在因果关系中的“物”,而一切因果关系中的“物”皆为“计算”的产物,而不是物自身。可见,要到达物自身,不能依据科学的追寻与概念的解析,需要“物向思想显现出来”,需要从“说明性的思想返回来,回到思念之思”[13](1182)。
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思想”或“思念之思”不是一般的思索、分析或文学性的想象,而是中国传统中的心性工夫,可谓之“尽心”而“知性”。吾人“尽”了作为大体的“本心”,一定可“知”物之为“物之性”。
故周濂溪谓“与自家意思一般”。“与自家意思一般”不是一种由文学性的比拟而生的爱惜,而是由物而居有一个天、地、神、人共有的圣域。此时,不但人栖居于此圣域而化,物亦栖居于此圣域而化。海德格尔称之为“物之物化”。他说:
物化之际,物居留统一的四方,即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让它们居留于在它们的从自身而来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中。[13](1178)很显然,这样的物——作为真正的物自身——不可能出现在科学知识之中,海德格尔认为,出现在“艺术”中。这样,才有了海德格尔那句着名的话:
艺术的本质就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13](256)由此,吾人可以来讨论艺术的意境问题了。
四、素朴恬淡与艺术之意境
既然艺术作品意味着“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13](292),那么很显然,只有艺术才能灵现那真正的美。所以,海德格尔又说: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13](276)。
为什么在存在者之真理即物作为真正的物而存在的地方,才是艺术,才有美呢?因为此时“在存在者中间打开了一方敞开之地,在此敞开之地的敞开性中,一切存在遂有迥然不同之仪态”[13](293)。这种迥然不同的仪态就是“居有之圆舞”,物“在居有之际照亮四方,并使四方进入它们的纯一性的光芒中”[13](1181)。物物化而居有自身,“物化本身是轻柔的,而且每一当下逗留 的 物 也 是 柔 和 的 , 毫 不 显 眼 地 顺 从 于 其 本质” [13](1183)。这不是一般的技艺制作之美,而是天地无心而成化的大美。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3](735)这个“大美”就是原天地之道而成万物之美,故庄子又曰:“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3](735)可见,真正的“美”一定源自事物之“真”,但真又不是科学知识意义上的对象的客观性,而是在人之存养尽性的工夫中灵现与淳化。《坤文言》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23]
由此可知,真与美一定在仁者之尽性工夫中方为可能,这是真实的真、善、美之合一,且仁者之尽性(善)是首出的条件。海德格尔说:
诗并非对任意什么东西的异想天开的虚构,并非对非现实领域的单纯表象和幻想的悠荡漂浮。作为澄明着的筹划,诗在无蔽状态那里展开的东西和先行抛入形态之裂隙中的东西,是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并且是这样,即现在,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13](256)诗、艺术与美固然不是异想天开的虚构,也不是非现实的幻想,但海德格尔用“筹划”一词并不的当,因为“筹划”总有造作的意思。实际上,澄明之境、无蔽着的敞开领域一定来自仁者的尽性工夫中,外此别无它途。海德格尔在这里以澄明之境来灵现一个真、善、美的合一之境,“真”是这一澄明之境,“美”亦是这一澄明之境,“善”依然还是这一澄明之境。因此,真、善、美的合一并非是三个独立的元素的综和,而是即真即善即美,以类似庄子的话说:俄而“真”“善”
“美”矣,而未知“真”“善”“美”之果孰为“真”、孰为“善”、孰为“美”耶?此是消融自体相而淳化。王龙溪曰:“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17](238)其实,无所谓真、善、美,只不过是一澄明之境之灵现与淳化,只看吾人之“机”落在哪里。
若“机”在“真”,澄明之境就是最确“真”;“机”在“善”,澄明之境就是最良的“善”;“机”在“美”,澄明之境就是最大的“美”。牟宗三尝雅言,美的原则乃是“无相原则”。[24]其实,岂止是美以“无相”为原则,“善”与“真”皆以“无相”为原则。只是一个澄明之境的如如灵现,淳化之域的寂寂威临。
从色泽与意境上讲,这个境域一定是素朴、静默、空灵而禅悦的。在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中,对于这样的色泽与意境自然有其必至的证会,前文已有所引证,这里不拟重复。即便是海德格尔,尽管他可能并不熟悉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当他真正沉入到这个境域去之后,以其真切的灵觉自然亦有所证会,因此,当多次说到澄明之境是素朴的、柔和的、静默的。这表明,艺术或美的色泽与意境就是素朴恬淡、静默空灵的,并无多样化之色泽与丰富性之意境,这色泽与意境是定然而必然的,因为心性工夫自身之色泽与境界就是如此,而与艺术家的个性、情感与才能无关。所以,海德格尔说:“愈伟大的大师,其个性就愈纯粹地消失在他的作品的背后。”[13](1231)吾人居常曰:艺术是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达与天才独创性的展示,故艺术之风格与意境是丰富多彩的。这种艺术观丝毫没有触及到艺术自身,因为如果只是与情感、个性与才能相关,那么,艺术永远就是主观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客观性可言,自然就无“真”可言,亦无“善”可言,真、善、美的合一亦落空,艺术自身也就消失了,除非吾人认为艺术就是一种游戏。如果果真是一种游戏,那么,艺术就决非真理的绽开方式,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其实,艺术只须灵现与绽开那个澄明之境、神圣之域即可,决不要情感、个性与才能的显露,切忌呈气使才。而要让艺术做到这一点,就是让人居有空灵之物,而人自身则不显现。居常吾人常把诗分为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此皆不经之论。诗一至于抒情,则重而浊;诗一至于叙事,则乱而绕;诗一至于说理,则尖而酸。尽失素朴恬淡之色泽,空灵静默之意境。
王观堂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过”,“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王观堂谓“无我之境”为“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此则不谛当,应为“仁者所能自树立耳”。但诗人“写有我之境者多”,可见存养工夫之难,非艺术旨趣之异也。“宝帘闲挂小银钩”(秦少游:《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无我之境也。但“无我之境”并非所谓的“写景诗”,“无我之境”是要居有空灵之物而灵现澄明之境、神圣之域,既而召唤天、地、神、人之欢聚。
故诗不必言情、不必叙事、不必说理,只须有个空灵之意境即可。但这个空灵之意境徒才情不可至,徒技巧亦不可至,须在心性工夫方可。程子曰:
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旸,无所不通,无所不应者,正而已矣。正者,虚中无我之谓也。以有系之私心,胶于一隅,主于一事,其能廓然通应而无不徧乎?[5](1212)若无心性工夫而只有才情与技巧,则为“胶于一隅,主于一事”。其“隅”也,板固而沉浊;其“事”也,纷繁而缴绕。此决非廓然、通应、空灵之澄明之境、神圣之域。所以,艺术或诗根本不是才子的事,而是圣贤的事,仁者的事。
然而,吾人何以需要艺术与诗?乃因为人总是被抛在世,被抛在世就意味着在物与事的胶固与纷扰中沉沦,而不能祈望或证会那天、地、神、人共欢的澄明之境、神圣之域,故人总需要教化,但教化非情感之激动而使然,亦非理性之疏导而使然,乃空灵意境之感召而使然。人之灵光爆破,窥破天机常于此时。故抒情与说理皆人进入澄明之境之准备,若无心性工夫之笃实潜存,则抒情与说理甚或为澄明之境的障碍。
无论如何,人之最后截断被抛之沉沦而入澄明之境必不在抒情说理时,必在空灵意境之灵现处。西人黑格尔谓哲学高于诗,此是其陷于思辩之泥潭而不能自拔,以世智之冷光照射之限度,抽空诗意人生之结果。实则诗必高于哲学。人最后之圆成以三点说之:一曰本体良知之全尽呈现;二曰个性与情感之放下;三曰澄明之境的绽开。抑或可如此说:若本体良知全尽呈现,则必有个性与情感之放下,亦必有澄明之境的绽开。故诗或艺术决不只是供人作美的观赏,它们必然是“教”,且是圣贤之教。
参考文献:
[1] 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 岳麓书院, 1985.
[2]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3] 刘劭. 人物志[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22?23.
[4] 黄庭坚. 黄庭坚全集[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308.
[5]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6] 黄宗羲.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78.
[7] 陈亮. 陈亮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02.
[8]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9.
[9]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0]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505.
生态美学是个包含存在论与价值论的美学范畴,肯定自然界的内在审美价值,倡导回归自然和亲近自然的审美趣味。根据生态美学的存在论构成和价值观指向,无论把自然生态视为审美对象,还是把生态维度纳入审美实践,生态美学的基本诉求始终明确和统一,即把自然...
在中国文化史上,自先秦以来,一直是以思想启蒙为主题的理学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到了明代,理学文化开始出现裂痕,并从中产生了阳明心学及异端李贽的童心哲学,促使明代价值观的更迭和审美观的新变。在文学创作方面,随着市民文化娱乐的要求日益增长,明代文学发生了...
休闲美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目前,我国的休闲美学还处于理论建构阶段①.其建构也应该是一个沉下心来才能做好的休闲过程,一味追求快速立论或不加选择地追随西方休闲学、美学的构架,本身就违背了休闲美学的基本精神。能不能从反省自身、汲取中华文化一贯...
一、蔡仪的美学观点蔡仪观点的科学之处在于他承认了美的客观性,是唯物主义无疑。但他认为美是不依存于人的客观存在,否定美的主观性,却是完全错误的,否则你就无法解释美在阶级、民族、时代以及个体等的差异性。说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更是错误的,根据经...
再好的厨师要烹饪出美味佳肴,都必须要有上好的肉食、蔬菜、佐料等作为原料,所谓巧妇安能作无面汤饼。中国美学研究要想在新世纪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也需要中国美学文献资料作为原料,否则便不免空疏。皮朝纲先生数十年致力于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特别是禅宗...
现代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影响下被动地创立的。这一认知无疑有其道理,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并非中国本有的,而是经由日本从西方引入的。关于西方美学具体的引入过程乃至美学这一名称的由来已经一些学者考定,不需本文重述。但对于中...
一、生态美学理论针对生态危机和美学自身理论的困境,生态美学运用整体性思维方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美学和从美学的角度思考生态环境建设。1.形成与发展随着20世纪下半叶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促使了生态学与自然科学之外的学科的渗透与结合。人们...
王国维是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他的美学思想萌芽于西方文学思潮之中,诞生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新认识中,他一开始便非常注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的相互印证,特别是西方哲学与文学的联系.他的美学思想作品多创作于青年时期,当时他深受西方哲学思想...
绪论从建构论立场看身体,可以发现文化对身体的塑造已进入到如此全面和深刻的地步,它能更好地解释很多为本质论对身体的不可解之处。但是仅仅解释是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建构论和本质论本身并非完全对...
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首次界定了崇高范畴并做出了全面、深刻的理论分析.康德的哲学类属先验哲学体系,崇高论作为一个关键的环节被确立下来.康德把自然界作为背景进行崇高的分析,认识到实践、感性到理性、自然到自由,崇高论是这诸多环节中的强有力的一环.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