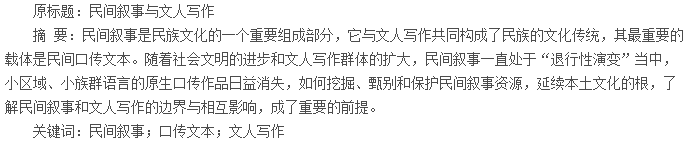
一、民间与文人:传统的分野
民间叙事研究近年来受到了叙事学界的重视。
探讨民间叙事问题,必须廓清什么是“民间”。“民间”是指与文人相对而言,这是最普遍的看法。但自从有文人创作以来,民间创作与文人写作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纠结难分。一方面,文人们不断地向民间学习,吸取创作的养分,使民间叙事不断转化为文人手法,《诗经》的比兴最为典型;另一方面,文人写作也不断被民间所模仿,成为民间创作(包括口头创作)的传统,明清以后文人话本对于悬念的设置,就逐步为民间说书人所运用。就创作的群体而言,文人写作的队伍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扩大,民间创作的群体事实上也在日益缩小。所以,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民间创作的“民间性”,一直处在“退行性演变”的过程之中。
但是,对于“民间”含义,实际上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从单纯的文学角度说,民间则意味着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以口头创作、流传为主要形式的作品体系;而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民间意味着与官方相对,它是一个区别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及其表现形态的文化和观念体系。对于后一点,以往我们是把它放大了:民间文学是什么呢民间文学就是世代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语言艺术。它有自己的艺术传统、表现方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学尖锐对立,与作家创作、俗文学、通俗文艺也有差别。它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等特点。它是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也是劳动人民知识的宝库。[1]
但这种对立也并非没有根据。以小说为例。小说可谓叙事文体之冠冕,但小说在中国有着从排斥到接受到变革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小说发展的由民间俚俗到文人高雅的转变相关。从大的历史阶段说,成熟的文人小说虽到明代才出现,但其雏形却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甚至更早。而此前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说的“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虽然也不是指的严格意义的小说,但事实上已经影响了正统观念对于小说的看法。至清代,小说仍屡遭查禁。康熙查禁小说的圣谕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惑焉。所关于风俗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八)[2]
这样一种正统小说观,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并长期流行于民间(坊间)的小说,其叙事上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淫词”和“荒唐俚鄙”,与“崇尚经学”、承载“正理”的其他文体,是相悖甚至是对立的。这起码说明一点,从正统(官方)的观念看,在官学正宗之外,是有着一个属于民间的叙事观念和话语体系的。
当然,在民间创作的作品体系当中,与官方相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无疑会构成其内容的重要部分并且影响着整体表现形式的选择和发展。因此,民间创作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就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的区别而言,起码有以下几点。比如说创作者与接受者身份的不同:民间的创作者和接受者有可能是“文化人”,也可能不是,更多的是游离于社会“文化圈”之外的下层民众;而文人创作的接受者主要是文化人,作者一般都属于社会文化的精英群体。又比如说表现语言的不同:一般认为,由于创作传达与解读接受是同步进行,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能产生理解转换上的阻隔和时间上的延宕,因此民间创作的语言是透明感较高的未经加工的口语化、生活化的,其中部分只是经过小族群、小地域的通约,因而是不规范的甚至是粗俗的语言;文人创作则较多地运用大族群、大地域通约的语言,不但讲究规范,还讲究典雅,由于创作和接受的不同步而不必过多关注语言意指的清晰程度,有时为了适应文体格式的需要和有意造成理解心理的阻隔,还刻意地使用偏离日常生活或“陌生化”的朦胧语言。还有情节结构的不同:民间创作更多是受情感逻辑(按人之常情本该如此)或生活逻辑(按人之常理本该如此)的引导,或者以纯主观想象(纯粹的“异想天开”)来构造情节事件的因果联系;文人创作则不仅要考虑情感逻辑的生活基础,同时必须考虑情节结构与现实生活逻辑的内在联系,即使是所构想的故事情节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发生,也必须从理论上寻找其现实的合理依据。此外还有时空转换和人物设置的不同:民间叙事往往多使用自然视角和“共名”(无特定姓名),而文人创作则多使用交叉视角和“专名”(有特定的姓名);这后一点,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民间叙事(传统讲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不确定、大时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确定、大空间),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山(无特定、大地点),在山的半中腰(中地点),有一座庙(小地点),庙里有一个和尚(人物,无专名),和尚的脸上有一道疤痕……(特定点)文人写作则可能是:当神秀走进庙门(小场景,特定时间、人物、地点),看到和尚脸上的疤痕时,(特定点)着实吃了一惊(特定心理描写):这不是慧能吗!(特定人物)他怎么在这里这样的大山(大地点),这样的小庙(小地点)!
用电影镜头比较,民间叙事的自然视角就有点类似从远景镜头、中景镜头到近景镜头、特写镜头的转换;而文人写作除了心理上的渲染外,时空的顺序是完全打乱并重新组合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间叙事和文人写作还有诸多表现,上述的区别更多的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和大致的划分。由于文人与民间的复杂联系,有时会变得很模糊,在具体的作品中,尤其是在民间口传作品被转化成书面文本后,我们很难判断某一作品更具有民间性,而某一作品更具有文人特点。
文明的进步和文人群体的不断扩大以及“大通约”语体的文本转换,都是造成这种模糊甚至消弭了两者的区别的重要原因。
通常,对于许多作家和读者来说,对“民间”作品的理解,一部分是来自于口传作品文本,一部分是来自于经过文人记录整理的书面文本。人们是以这两类文本作为文人作品的参照系来作出以上种种区别的判断的。对于口传作品来说,民间文学理论一直认为它有较稳定的传承性,同时又认为它有较大的变异性。民间文学有着这两个特点是无疑的。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一些民间作品为何有如此大的生命力世代流传,而类似的故事在不同地域又有着如此不同的版本。但传承与变异却又是矛盾的。
如果一个故事跟另一个故事仅仅相似而不是相同,我们又凭什么认为它们是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而不是两个故事呢“类型”说似乎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但类型说仍然面临同样的质疑:它们首先是不同的,因为有相似,才被视为同类型,不然就是同一。变异同时意味着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变异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变异。这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但遗憾的是,不管是哪种情形,我们都很难看到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更多的只是看到某一时期在某一个地域流传的某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甚至已经是经过文人筛选、综合,甚至或多或少改编过的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民间作品,大多都不是本来面目的民间作品。当然不排除部分文人以严肃而尊重民间意识的态度进行搜集记录,但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民间作品的本原性和原生状态始终难以保存。首先,真正的民间作品几乎是口传作品,而口传的同一作品只要经过另一个讲述者转述,都会发生变异,地域越广,时间越久远,变异越大,文人记述的不过是其中极少数甚至个别转述者的作品;其次,口传作品的民间语言有着较大的地域性、族群性差异,但文人记述使用的基本是大通约语言,这种大通约究竟对民间语言所传达的信息造成了多大的损耗和带来什么样的变异,读者是无法判断的;此外就是文人记述的文本与民间口传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很多作品流传的过程中,民间口传与文人文本究竟孰先孰后其实是一个难以扯清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关系到民间文学的本原性与原生性的理解,一个民间艺人的口头创作和把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进行转述毕竟不是一回事。而恰恰流传广泛的故事就存在这样的现象。
以中国四大民间传奇之一的《孟姜女》为例。
顾颉刚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对这一故事的搜集研究可谓完备,但无论顾自己所搜求的,还是其他学者提供的,大多数都属于文人记述的材料。其《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孟姜女故事历史的系统”中所辑录的由先秦至近代的材料均属历代文人记述自不用说,即便是“地域系统”中涉及作者近时的材料,以及第三册(通讯)中各地学者同好提供的材料,也大部分是文人记述的文本,在今天看来最具有民间色彩的也就是一些民间词曲唱本和戏剧。
而这些唱本和戏剧,即使不是活动于民间的文人创作,也是文人记录的文本。[3]
由此看来,从古至今如此多的文人记述的孟姜女故事,不管其源自民间与否,对当时或其后的民间创作,无疑也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既是孟姜女故事变异的原因,同时也是人们把可能本来不是孟姜女故事归结于其中使得这一故事的本来面目变得扑朔迷离的原因。人们甚至可以追问:究竟《孟姜女》还算不算民间故事或者孟姜女的故事中有多少民间成分
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追寻民间作品的本原性和原生状态,或者,用帕里的话说,寻找“未曾被污染的传统版本”,① [4]就显得越来越困难。
二、口传与书写:逐渐消弭的界限
这种趋势在当代会愈加明显。当代社会的变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融了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的界线。农村的城镇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而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来属于城市人特有的生活内容已进入了广大乡村的普通家庭,生活方式的趋同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乡村田园生活为主体内容的民间文学题材正在日益消失,起码是退缩到边远的山区。教育的普及和信息化具有城镇化同样的文化力量,它们的触角甚至比城镇化伸得更远,对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同样深刻。这些改变无疑对民间文学的生产根基构成了冲击。
当然,城市仍有它自己的“民间”。宋明以来的市井文学几乎成了民间文学的主流。市井的民间文学仍然具有其不同于文人创作的某些特质,尽管宋明以来的话本等民间文学作品已十分接近文人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社会的发展也会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新的市井生活也可以成为民间文学的创作内容。但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叙事话语的改变。社会的城市中心化强化了强势语言的传播及其对乡村的覆盖,城里的人不会说乡村里的话,但乡村里的人却学着城里人的腔调了。小区域、小通约语言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其原生态的口头创作不复存在。
其次是创作者身份的改变。以往的文人写作者往往首先是作为民间文学的“听者”身份出现,对“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进行搜集、记录和整理或者再创作,从干宝到蒲松龄一直下来无不如此。而讲述者则不一定自己写作。同样,乡村的歌手、“讲古”者和城市的说书人也不一定写作。而从后者的口头创作到前者的书面记录,往往会有一个流传过程,这才有了民间口传文学的传统。但当今社会的文化发展使这个过程迅速改变。尤其在城市,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时尚,一些故事的发生还没有进入口传过程,便已经成为书面文本。这无形中改变了民间文学创作的集体性格局。我们可以设想另一种情形,即同一个生活事件(故事)可以同时以口头的版本流传。但这种情形只是在传播媒体较单一甚至匮乏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如虽然唐代以后有了雕版印刷术,书面文本得到较广的流传,但各种口传的历史演义仍与书写历史并行不悖。或者说,当文化的传播仅仅是口头和书写两种途径实现时,由于书写文本的相对滞后,口头文本可因其占得先机拥有大量的民间受众而得以广泛流行。
而当今的现实是,各种传媒的网络几乎覆盖了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其传播的速度远远超出口头流传。
传媒的高度发达,不仅仅是取代了口头传播的许多功能,更主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个故事由于口传所导致的变异。当今流传的由各类写手搜集或创作的网络作品和短信文本,其版本的高度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民间文学的发展趋势。但网络文学和短信文学究竟是属于文人书面文学还是民间口传文学,毕竟还有待讨论。传媒的发达与个人化写作的流行是互为因果的。在两者相互促进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民间口头创作,其“民间”的本原性和原生状态已经很难保持。对此,早些年出版的《简明大英百科全书》对“民间文学”的解释倒是揭示了其发展的命运:民间文学是文化的口传知识,并无文字记载,各民族均曾产生民间文学。在先进的文化里,民间文学甚至与文字记录同时并存,由儿童以及不识字的人口口相传,不过在许多都市化地区,民间文学已逐渐由书本、报纸、广播及电视取代。[5]
如果《简明大英百科全书》该词条的作者现在再来撰写,恐怕除了增加“网络”、“手机”等媒体内容外,同时还会删去“都市化”这些字眼。
另外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作家对民间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本土写作和本土文化,还有通过文人作家作品这一中介,同时裹挟着西方的文化和叙事方式。自从上个世纪初中国小说家开始接受、学习、模仿西方小说的叙事手法之后,中国的文人叙事模式在不断地发生转变。[6]
到了上世纪 80年代,这种模仿和运用已经成为普遍自觉的写作意识。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由本土文人写作所裹挟的西方叙事对民间形成了怎么样的影响,但可以想象,如果本土文人不回归本土传统的文化书写,叙事模式上仍向西方靠拢,民间叙事的文人化继而西方化,也就是迟早的事。
这样一个过程都在表明:民间叙事的“‘民间性’退行性演变”其实远没有结束,而且一直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发生着。这种的演变最终结果就是,民间和民间叙事依然延续,但具有本土文化和原生口头传统的“民间性”却踪迹难寻。
三、紧张与趋同:文人的“民间”与“民间”的文人
在古今文人的眼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同于自身群体的“民间”,甚至“民间”也往往成为各个时代文人先锋写作的一面旗帜,而向民间学习或者标举民间旗帜也的确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写作潮流。
这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这里有一个文人如何看待“民间”与“民间”如何看待文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民间文学与文人写作的分野的设想是否能够成立。以往我们较多的关注到文人眼中的民间,而极少注意到民间对于文人的态度。而事实上后者要比前者复杂得多。毕竟文人(或知识分子)对自己所理解的东西能够用语言表述清楚,而民间则未必。民间常常以文艺的形式如故事、笑话、歌谣等来表达他们的态度。壮族彩调剧《刘三姐》中三姐与三秀才对歌一场,历来颇招非议。尽管歌剧和电影均为文人改编,然而其中反映出来的民间对文人的态度却有着悠久传统。孔子是中国文人的祖师爷,活着的时候地位虽然没有身后崇高,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毕竟名声还是很显赫的,身居鲁国,但声名远播,边远地区的楚国人都并不感到陌生。但从家乡鲁国一直到南方楚地,周游路上,孔夫子却受尽了冷落与讥讽。特别是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样的指责,历来成为民间百姓讽刺文人的口头禅。孔子本人以及注疏《论语》的后学都认为那些奚落的人是些隐者,依我看来,“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植杖而芸(除草)”的丈人等等对孔子的奚落与讥讽(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微子》),事实上已隐含着民间对文人或“劳力者”对“劳心者”的抵触态度。退一步说,即使奚落孔子的是一些隐者,他们身居山野,躬耕自足,尽管不一定完全融进民间,也已经以民间的立场或文人另类的眼光看待文人。以上只是经典记载的,民间故事中对孔夫子的讥讽更多。如《孔夫子与采桑娘》“:孔夫子名气很大,周游列国但却穿不上一个九曲弯孔的珠子,不如一个采桑娘。这个传说强烈地歌颂了劳动智慧,有力地批评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懂诗书,不懂实际的封建文人。”中国民间流传各种类型“三女婿拜寿”的故事,“大女婿、二女婿总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元、秀才之类,而三女婿则是劳动者。故事从宴会上对诗、行酒令开始。这是专门在于难为三女婿,出他的洋相的。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恰恰相反。真正的才智并不属于大女婿、二女婿,而是属于被他们认为土里土气,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三女婿”。[7]
对类似的故事,我们当然可以从阶级论等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释,但不可忽视的是,不管何种原因,民间劳动者始终把文人知识分子视为自己的异类,穷酸、迂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几乎成了文人秀才的代名词,这已经成为一个悠久的传统。
文人对于民间的态度,常常取决于文人自身的社会境遇。一般而言,仕途失意文人容易走向民间,对民间有认同感;置身或归属于官场的文人,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的平民意识和启蒙思想的文人才会对民间有认同感。即使是这样,对于作为一个群体的文人知识分子而言,民间始终是一个“他者”,认同感不过是在文人有着走进民间的需要时对“自我”和“他者”的心理距离的一种消弭,从身份而言,始终不可能达到同一。文人也始终以“他者”的眼光看待民间,“走向民间”,“向民间学习”的口号在历代文人中不绝于耳,这种营造文人对民间的亲近感的努力背后,隐含的是文人自我与民间“他者”的疏离,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文人失意(在仕途或文坛)或者对文人自身不满时的走向民间,以文人另类的身份或民间的立场写作,赋予民间写作反叛正统文坛的意味,不过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人心目中自身与民间的紧张关系。
但民间与文人也有趋同的一面。文人对民间的趋同来自于文人对自身的反叛,而民间对文人的趋同首先来自于民间对于以文人为表征的文化的趋同。文人尽管可以划分为许多类型,但作为群体,在民众的心目中,他们毕竟已经脱离了蒙昧,成为智者(中国古代“智”与“知”通,现代汉语把文人称为“知识分子”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文化的先锋人物,加之历代的文人可以通过各种科考途径而晋身为“治人”的“劳心者”,对知(智)与识的推崇,便导致了民间对文人的仰慕与效仿。文人作为先于蒙昧者掌握文化的人,可以起教化和引导的作用,是试图脱离“劳力者”阶层可利用的资源,这也是文人获得仰慕的一个原因。于是文人就普遍有了“先生”的尊称。文化的价值赋予了文人高尚的地位,于是导致了民间对文人的趋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光是读书人的自诩,也是民间的一种认同。但这种趋同并非能够完全实现,一旦民间发现文化这只“金苹果”不过是一颗吃不上的“酸葡萄”时,趋同便走向反面。而从整个文化史看,晋身高尚地位文人毕竟是人群中的少数,因此民间与文人的紧张关系也就成了最为常态的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是我们理解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区别的一个重要文化依据。由于这种紧张关系的存在,文人和民间都会试图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操作不同的话语体系。尽管民间不如文人那样自觉,但民间毕竟也有着自己的传统。“文”“野”之分,“雅”“俗”之分,不仅仅存在于文人的视野。上述“三女婿”的故事,在民间有很多流传的版本。而所有的版本中,“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三女婿,所作的“诗”或“对”,从文人看来,都是粗野到极致,自己所不为的。举一孩童时期听来的类似的例子:老丈人要求三位女婿即兴吟诗,每联必须以“摇”结尾。
文人(秀才)女婿诗云:“远远看见枝头鸟,鸟摇枝也摇;鸟飞枝还在,空枝摇几摇。”而文盲女婿则说道:“远远看见 × 拉尿,尿摇 × 也摇;尿完 × 还在,空× 摇几摇。”不可否认,类似的故事也有文人戏作,有讽刺村野匹夫的意思。但不管出自何人之手,文人与民间的对立,却是显而易见的。以相同的形式,而不同的话语,叙述不同的事件,所隐含的,显然不仅仅是“粗俗”与“文雅”的对抗。叙事的对立,不过是文化(甚至社会)身份对立的表征。文盲女婿之话语,文人之所不齿;同样地,文人所操作的话语,民间也常常不屑,不然就被认为是“鹦哥学舌”,或者“酸气”。这不同的叙事话语即便是在“一团和气”中的对话,其中都带有嘲弄的意味。《红楼梦》中刘姥姥与大观园的小姐们的“对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这种对抗或者紧张关系下的民间与文人,不管自觉与否,都形成了各自的对话交流的群体,有着各自的生活与文化语境,并沿着自己的话语路径前行,这才保持了各自的叙事传统。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也有相互间影响和某些趋同的方面,但也不过是“各取所需”,不会同一。
四、关注与保护:延续本土文化的根
了解民间叙事与文人写作的区别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民间叙事在文人写作的影响下“退行性演变”趋势的把握,以引起对民间叙事资源挖掘、甄别和保护的关注,毕竟,这也是我们民族本土文化的根。在多年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已不断地看到和听到民间叙事及其载体——民族语言和口传文本逐步消亡的事实。
在当下,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普及,文人与民间已经边界消弭并走向了前所未有的融合,大通约语言的写作在网络文化的推动下,使得小通约语言的口头传承失去了应有的空间;民族文化的多样生态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正迅速被以商业文化所代表的都市文化所覆盖,小区域、小族群的语言文化身份也正在消失,丰富多彩的本土民间叙事将成为历史的记忆。
不可否认,当今也有文人作家做着本土写作的努力,一些族群的文化个性也能部分地通过他们的作品得以延续。但文人的写作最终还是运用强势语言,族群的民间叙事也因写作者的超越文人母语的交流而走向趋同。而且,在当今时代,与不断提高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情形相反,能有明确族群个性意识的写作者已不多见,即使有,也不过停留在族群生活题材的选取上,远没有进入到植根于族群本源的民间叙事和与族群的历史文化、接受心理紧密相关的叙事方式的把握与运用。对本土民间叙事的集体遗忘已使得一些文人的族群个性写作成了无根的游移,其对族群文化个性的传承作用也就很有限。
因此,在了解不同类型叙事的基础上,加紧对正在“退行性演变”中的民间叙事资源的挖掘保护,以延续我们本土文化的根,已显得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 张紫晨.民间文学基本知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8.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
[3] 叶春生.典藏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4]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着,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M].北京:中华书局,2004:5.
[5] 曾永义.俗文学概论[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19.
[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 张紫晨.民间文学基本知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29,53.
第二章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的社会生态生态美学的内容不仅仅指的是自然生态,对生态美学中社会生态的探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萨克民间文学作品中具有深刻的社会生态内涵,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2.1反对强权的生存之道。哈萨克族在宗法封建时代的...
前言:在中国民间文学中,有众多的箭垛式人物。他们在原有的形象之外,衍生出众多新的形象,从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符合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在众多的箭垛式人物中,武圣关羽的形象尤为突出。关羽死后被封王封神,在各地建庙供奉,在民间文学中更是...
螺女型故事是我国民间传说中一个重要的故事类型,在福建、江浙一带流传甚广,两省各县的卷本中共收录40余篇。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将田螺姑娘列为400C型,收录古今异文30余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统计螺女型故事异文共61篇。目前各...
前言中华民族悠长的文化和淳朴的民众,在漫漫时间长河中,孕育了丰厚的民间故事宝藏。在众多的民间故事类型中,有一类专门表现女主人公善于解决各类难题,从中体现女主人公过人智慧的的故事,这些女主人公的身份有待字闺中的女儿、妹妹,也有已婚的媳妇、妻...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世界瞩目东方文化,中国文学也在经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开始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在此背景下李锐也开始倾心乡土,并在80年代末创作了《厚土---吕梁山印象》。《厚土》一经出版,广受好评,以其创作机制、价值影响为...
通过分析鄂伦春民间文学的故事形态, 这个“山岭上”的民族丰沛的情感展现在读者面前, 故事中承载的文化心理内涵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性, 反映了“鄂伦春人勤劳勇敢、豪放淳朴的性格和社会生活。”...
中国西南的纳西族因东巴文化着称于世,2005年,东巴古籍列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东巴叙事传统指纳西族民间祭祀-东巴在东巴仪式及民俗生活中进行叙事活动的文化传统;它以宗教信仰及行为实践作为叙事动力,以仪式及民俗活动为载体,以神话为叙事内容及表现形态...
一、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现代性是极具争议性的学术话题,不仅有各种困惑和理解,而且有各种批判和解构。现代性涉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走出西方,走向全世界。下面我们择其要点,对现代性进行简要的分析。谈到...
一本文语境下的雷州,是指以雷州半岛为主的湛江行政区划,包括现今的湛江市、徐闻县、雷州市、遂溪县、廉江市、吴川市,它东面向南海,西濒北部湾,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北与祖国大陆接壤.三面临海的地理条件使当地文化带上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海洋文化是指...
民间语文不一定有文采,也不一定讲究谋篇布局,因此常被正统的、常规的语文教学所排斥,甚至是忽略。但是,民间语文作为一种重要的写作资源,有其本身的价值,笔者试从时尚性、创新性、生动性、趣味性、大众性五个方面浅析民间语文的个性特征。一、时尚性...